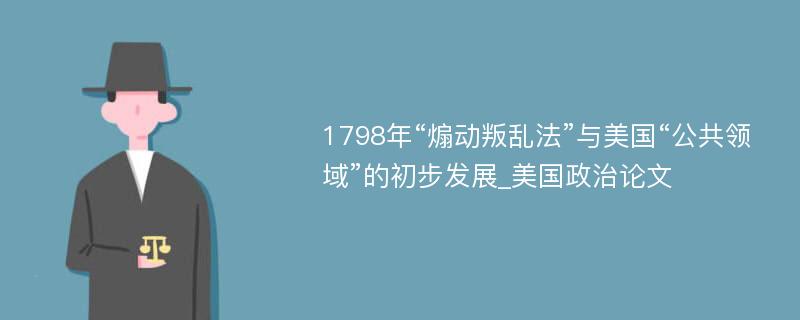
一七九八年《惩治煽动叛乱法》与美国“公共领域”的初步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叛乱论文,美国论文,领域论文,一七论文,九八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世纪90年代,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激烈的党派冲突。1798年,在一些联邦党人的倡导下,国会通过《惩治煽动叛乱法》(The Sedition Act of 1798),谋求加强对出版物的管理,限制反对派言论,制止他们“煽动颠覆政府”。法令的颁布源于党派之争,而其反响的范围与程度却超越了党派。法令不仅遭到民主共和党(简称共和党)① 的激烈反对,而且引起更广泛的抗议,从城市报刊到乡间酒馆,反对法令的“声音”不断扩大。联邦党、共和党、众多报刊编辑与普通民众通过报刊、小册子以及公共场所等公共媒介围绕法令进行深入争论,并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
因为法令的颁布涉及美国的党派之争、政治思想的演变以及公民权利等重要问题,美国学术界围绕法令进行了比较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对于法令颁布与实施过程中的分歧以及引发的一系列反响,有学者从两派的政治思想分歧以及政治思想变化的角度来分析;② 有学者从美国言论与出版自由的视角考察法令颁布后的争论;③ 也有学者提出,在法令引发的争论与行动中,办报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美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④ 还有学者探讨了法令颁布后反对派的思想与言论。⑤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该法令的关注较少。⑥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公共领域”理论,梳理法令颁布后联邦党、共和党、众多报刊编辑与普通民众的言行,分析法令引发的反响对“公共领域”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而探讨“公共领域”在美国建国初期政治生活中的功能。
一、党派斗争与《惩治煽动叛乱法》的制定
1798年夏颁布的《惩治煽动叛乱法》,原本是一场党派交锋。在党派冲突激烈的18世纪90年代,联邦党与共和党纷纷借助报刊等出版物互相指责,树立各自的“正面”形象,希望获得“人民”的支持。⑦ 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与党派冲突的推动下,联邦党认为共和党与法国力量联合,在报刊以及公共场所发表的“煽动”言论会颠覆政府,威胁国家安全,试图通过法令消除共和党的影响。可以说,党派矛盾是法令颁布的导火线。
制宪会议之后,政府精英尽管都在追寻“共和制”的建国理想,却因个人经历、个性与思想不同,在治国理念上产生了分歧。在内政上,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设计出一条依靠国家信用和公共金融体系发展商业与制造业的建国之路。在他看来,过于“虚弱”的联邦政府极易葬送革命成果,导致国家处于无序状态。他支持创办合众国银行,确立新的消费税补充财政收入,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集权式联邦政府。然而,时任国务卿的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汉密尔顿的主张有悖共和主义原则。无论是合众国银行,还是联邦税收与债务制度,都只会使商人和投机者受益。他担心工商业精英会在经济与政治上压迫平民,使平民丧失独立与自由。他与其支持者坚持认为,“共和主义应该建立在独立、美德和自治”等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才能团结起来,无私地为公共利益”服务。⑧
在外交政策方面,政治精英也有不同主张。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不久,一方面,联邦党人害怕法国强大的革命势头会冲击已建立的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倾心于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以维持英美贸易往来,增加财政收入。所以,他们要求乔治·华盛顿在当时的英法战争中宣布中立。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反对派并不反对中立政策,但更倾向于支持法国革命。他们认为,法国革命继承了美国革命的“衣钵”,掀起“共和革命”,取代了君主制和贵族制,杰斐逊曾将法国革命看作“欧洲自由史的第一章”,⑨ 对法国革命的赞美溢于言表。1794年,联邦党人约翰·杰伊受华盛顿派遣与英国进行谈判,协商处理贸易与土地问题。11月,双方签订条约,以海上贸易权的退让换取英国在北美大陆的让步,但是同时《杰伊条约》也令法国与支持法国的美国人不满。时值英法交战之际,在法国人与支持法国的美国人看来,这项条约打破了美国在英法战争中一直保持的中立,损害了之前关于在英法战争时不单独与英国媾和的承诺。
面对种种分歧,当时身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的詹姆斯·麦迪逊公开撰文指责联邦党人违反了共和宪政的原则,将国家推向君主专制,声称自己一方维护共和原则,保护“人民”利益。⑩ 杰斐逊也认为党派分歧不可避免,希望通过反对党制约联邦党对政策的垄断。治国之路上的分歧使政治精英决裂,联邦党以约翰·亚当斯与汉密尔顿为代表,而共和党以麦迪逊和杰斐逊为首,在一系列冲突中逐渐形成两个党派。两派不仅在国会辩论与党内日常通信中进行政论,报刊与小册子等公共媒介也成为他们论战的阵地。
从党派之争伊始,共和党就通过报刊等公共媒介强烈批判联邦党。1791年,杰斐逊暗中支持菲利普·弗伦诺(Philip Freneau)在费城创办《国民报》,树立了反对派报刊的形象,同时他还为弗伦诺在国务院提供了一份翻译工作。1792年,《国民报》刊登题为“共和主义者的随想”的时评,文中表达对政府腐败、社会不平等以及革命思想遭背叛的忧虑。(11) 麦迪逊则在1791—1792年间,以《国民报》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表达对政治现状的不满。他认为,现在的分歧产生在两个集团之间。反共和制的派别偏袒富人,不顾多数人的利益,主张由富人通过军事威慑力管理政府。共和派则厌恶世袭权力,反对不征求“人民”意愿的公共政策,拒绝不符合共和政府原则的政策。(12)
《国民报》之外,一些支持共和党的报纸与小册子相继问世,对联邦党及其行政当局发起了猛烈的舆论攻势。富兰克林·贝奇(Franklin Bache)的《曙光女神报》、约翰·戴利·伯克(John Daly Burk)的《时报》(Time Piece)以及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的《独立新闻报》(Independent Chronicle)等在各地都小有名气。贝奇出身显赫,外祖父为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曾留学法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法国革命推崇备至。1790年他在费城创办报刊《费城综合广告报》,1794年末更名为《曙光女神报》,刊登不满联邦党内外政策的文章,传播民主共和观念。《杰伊条约》签订后,贝奇和他的伙伴不仅参与政治讨论,而且对1796年竞选施加影响。(13) 他“反驳联邦党对杰斐逊的攻击,批评亚当斯的反共和主义思想”。(14) 伯克为爱尔兰移民,1798年6月入股纽约的《时报》。在他的领导下,这家报纸的语言犀利,思想激进,成为令联邦党人最为头疼的报刊之一。1793年,马修·莱昂(Matthew Lyon)在佛蒙特的小城拉特兰创办《农夫文丛》(Farmer's Library),指责联邦政府与当地的支持者。(15) 在波士顿,《独立新闻报》的办公室成为共和党人的聚会场所与活动中心。除了反联邦党的报刊,激进派人士詹姆斯·卡伦德(James Callender)撰写小册子《1796年的美利坚史》与《美国年鉴》,支持杰斐逊,批评汉密尔顿的金融政策。(16)
有声有色的共和党报刊与小册子令联邦党人忧心忡忡。他们在自己控制的报刊上刊登大量政府文件和国会记录,传播官方信息。同时,他们借助报刊等出版物,对共和党进行反击。汉密尔顿以《合众国报》为喉舌,连续匿名发表题为“警告”的文章,号召警惕那些鼓动同英国作战、却亲近法国的美国人。(17) 他谴责《国民报》的编辑拿着政府的钱,却成为政府的反对派。(18) 在联邦党人看来,共和党的用心在于激起“人民”的热情,煽动反对政府,为自己赢得支持。汉密尔顿认为,《国民报》就是为了诽谤管理者的名誉而创办,共和党报刊不停地重复谎言,而任何名誉都难以在反复的谎言中得以保存。(19)
“XYZ事件”(20) 发生后,美法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即将开战的谣言在首都蔓延。联邦党坚持认为法国同国内共和党联合,对共和党传播反联邦党言论尤为敏感。亚当斯发表演说,批评那些自称是美国人、却又攻击美国的人,“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对我国的宪法非常了解,却极力侵害本意良好的公民理念”,使“人民”不支持政府,他们是煽动与破坏秩序的工具,其中很多人可能受其他国家的雇佣,破坏美国。(21) 1798年6月之后,共和党“亲法”的行为加剧了两党矛盾。6月13日,费城共和党领袖、贵格派教徒乔治·洛根(George Logan)前往法国,进行非官方的友好活动,联邦党却认为洛根的行为十分恶劣,他们认为,“他出于对法国的热爱和对美利坚体制的憎恶”,投奔法国。他可恶的计划是“法国军队侵占美国的前奏”。(22) 6月16日法国外长塔列朗与美国代表在巴黎的通信刊登在费城《曙光女神报》上,而6月18日,总统亚当斯才将信件与代表的回复转交给国会。联邦党立刻认为,《曙光女神报》是“法国派别”的报刊,它在法国政府的授意下,刊登了信件内容。(23)
美法之战似乎一触即发,此时,民众的反法情绪高涨,但凡同情法国的人或政府的反对派都被视为公众的敌人,而一向警惕法国革命的联邦党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一些联邦党人认为颁布一项反煽动法令势在必行。6月至7月,在他们的鼓动下。国会相继通过《归化法》、《客籍法》和《敌对外侨法》,防范在美国的国外侨民的威胁。6月25日,来自马里兰州的参议院议员詹姆斯·劳埃德(James Lloyd)提出议案,对那些通过煽动性的语言向公民传达反对观点、违反国家法律与削弱政府的行为,政府要通过法律进行限制。他特别指出,支持法国政府的美国人都要被视为叛国者,将处以极刑。(24) 6月26日参议院将议案提交联邦党人组成的委员会,经过三次审议与修改,委员会保留了议案中关于惩治煽动叛乱的条款,但删除了对支持法国行为的具体惩治措施,并于7月4日通过议案。
联邦党深信共和党是“法国的派别”,痛斥共和党阴谋推翻政府。在众议院会议中,来自康涅狄格的联邦党人约翰·艾伦(John Allen)拿出精心准备的讲稿慷慨陈词。他指出,当前存在一个反对政府的叛国联盟,他们受到法国势力的支持,是美国的“雅各宾派”,其中包括共和党报刊编辑、共和党国会议员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他们以出版物为武器,发表谬论,宣扬暴力,鼓动“穷人、无知者、狂热分子以及道德沦丧的人”,反对人民代表制,甚至意图推翻政府。他们敌视自由,伤害社会共同的利益,收缴他们的“武器”是联邦党的职责。(25) 他继续质疑道,“因为宪法保护……出版自由,我就能毫无根据地荒唐指责你是小偷、杀人犯或无神论者吗?……从来不能因为出版与言论自由,就有权发表诽谤性的言论,免除因煽动、叛乱与杀戮而受的责罚。一个人总是要对恶意而充斥错误的出版物负责。”(26) 有联邦党人赞同说,即使言论自由,也应对伤害他人权利的言论加以限制,自由言论是以不伤害他人为准则的。(27) 国会之外,亚当斯在全国发表一系列演说,号召根除阴谋反对政府的行为,与联邦党的国会辩论桴鼓相应。(28)
7月6日,联邦党人罗伯特·古德洛·哈珀(Robert Goodloe Harper)提出修改议案的意见,要求扩大惩治对象的范围,凡通过公开集会或秘密会议、策动危害国家和平的“阴谋”、反对任何法律执行的个人,都要受到惩罚,即使没有参与,如果同这样的人有来往,也要受到惩罚。(29) 7月9日,众议院在未改变议案意图的基础上,对细节条款作出进一步修改。7月10日,在联邦党占多数的众议院,议案以44票对41票获得通过。7月12日,参议院通过该议案。经总统签署,《惩治煽动叛乱法》在7月14日正式生效。
法令旨在通过限制言论与出版物的方式,压制共和党。它对煽动叛乱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规定任何人非法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政府政策、阻碍法律的执行或阻止政府官员执行公务,书写、发表任何丑化、中伤美国政府、国会或总统的文字或言论,都属于煽动叛乱的范畴,将被处以不超过5000美元的罚款、5年以下监禁的惩罚。另外,法令中还规定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若被告所言所写为事实,则不会受到惩罚,但如果被告恶意破坏政府、国会或总统,有阴谋反对政府的举动,“无论此阴谋、威胁、商议、提议或企图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都将受到惩治,由陪审团作出最终裁定。最后,规定法令的有效期截至1801年3月3日。(30)
二、共和党反对法令的话语逻辑与民众的广泛响应
自该法提交讨论到正式生效,再至开始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共和党的“反对声”始终没有停止。他们按照自己的一套话语逻辑抨击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进一步塑造“联邦党暴政”的形象。一时间,国会中,唇枪舌剑;国会外,口诛笔伐。在激烈的交锋中,法令没有使反对派销声匿迹,反而引发了更广泛的反对。
实际上,共和党并不赞同绝对的言论与出版自由,认为政府对污蔑与诽谤应该加以惩治。有共和党人提出,尽管污蔑不会毒害大多数人,“但是也会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破坏公共秩序,因此“任何国家惩罚煽动诽谤都是不可缺少的”。(31) 也有共和党人表明,反对针对政府的不道德诽谤和攻击,并应该由合适的权威作出惩罚。(32) 弗吉尼亚最高法院的共和党人圣乔治·塔克(St.George Tucker)则认为尽管言论、写作与出版权利都是绝对的,但公众的意见需加以适当的控制。他指出,各州需对蛮横的恶意辱骂、伤害与人身诽谤进行惩罚,例如弗吉尼亚就采用了民事诉讼的方式应对诽谤行为。(33) 总之,他们认为各州应该拥有惩治煽动诽谤言论的权力。(34)
问题的关键是,在共和党看来,法令并非惩治煽动诽谤者,而是要压制“反对声”,迫使反对派失去表达政治异议的余地。他们的理由是:审判人完全来自对立派别,根本不能达成公正的审判。爱德华·利文斯顿(Edward Livingston)在众议院辩论中诘问,“试想若有人因诽谤总统而被起诉,在由总统安排法官和陪审团的法院中,会得到公正的审判吗?”(35) 共和党纷纷表示,法院要保证不受派别影响、不由总统安排,才能保证公正。(36) 设若审判结果来自被审判者的“敌人”,“这难道不是要压制除了赞同政府政策之外的所有政治观点吗?”(37) 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预言说:“人们可能因为发表不正确的言论而受罚。”甚至有礼貌的抗议和谦卑的请愿都会被歪曲成煽动叛乱的演说。法案似乎要禁止“人民”对政府的任何评说。(38) 塔克也表示,“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赞同会被认为是煽动;最小的抱怨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任何为某种观点辩护的讨论会被曲解为煽动的演说”。(39)
对于共和党来说,这项法令无异于剥夺了言论和出版自由。激进的托马斯·库珀指出,这个“新式的不会犯错的教义”剥夺反对派的权利,强迫公众支持政府。对那些讲述真相的人或是出于真诚表达意见的人进行惩治,压制出版自由。(40) 结果是,政府可能禁止了谬误,也可能限制了真理。(41) 在抗议法令的各种文字材料中不难发现,共和党经常以宪法为武器,指责联邦党人剥夺言论自由。1798年10月至12月,杰斐逊与麦迪逊分别以匿名方式拟定《肯塔基决议草案》与《弗吉尼亚决议案》,二人在文中批评法令违背宪法精神,“剥夺新闻自由”以及“监督公共政策的权利”。(42) 如果任何以“人民”意愿建立的政府通过任何法令剥夺言论自由的权利,那么就像“人民”以不合宪的方式剥夺政府所代表的权力一样,是违法的。(43) 《独立新闻》发表的一篇文章言辞更加激烈,文中质问:“压制自由讨论的强制力难道能成为法律吗?”它建立在违反宪法的基础上,它压制了永恒的自然法赋予每个人的神圣权利。所有自由的人都为被剥夺宪法赋予的权利而愤怒。(44)
言论与出版自由,不仅是《权利法案》保护的权利,而且其重要性源于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代表制政体,所以共和党不仅抨击法令侵犯言论自由,还要从建国体制的视野批判这一法令。因为国家遵循“人民主权”原则,“人民”作为“主权者”,在政治事务中“应当而且必须拥有代表权、选举权、同意权和知情权”。(45) 这四项权利中,“人民”充分运用选举权、同意权和知情权是实践代表权的前提。在代表制政府中,“人民”并非直接参与政治机构的工作,而是依靠他们选举的代表行使政治职能。但是,当要举行一些重要选举时,开始施行法令,“竞选人面临什么情况?不平等。因为法令限制了他们的讨论。人民面临什么情况?不自由,因为他们被迫选举的候选人并没有得到平等地考察和讨论。”(46) 限制出版物,丧失选举中的信息,也就毁掉了选举原则,这与剥夺选举权无异,只是这种方式是篡夺。(47) 掌权者通过破坏选举权,继续掌握着他们的优势。(48) 在共和党眼中,法令通过损害“人民”的知情权,使选举丧失意义,“人民”选出的代表并非真正得到“人民”的“同意”,代表制政府随之名存实亡。除了通过伤害选举权使代表制政府失效外,反对派还认为,法令直接违反了代表制原则。他们提到,在代表制民主国家中,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对“人民”的“唯一保证就是,遵从选民的利益和原则”。但是法令伤害了“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人民”的代表失去了对选民的承诺,“代表制的原则与实践之间发生了冲突”。(49)
总之,根据共和党的逻辑,法令限制了言论,就相当于剥夺了“人民”在政治事务上的权利,人民不再是“主权者”,代表制政府也并非体现“人民”的利益,政府将彻底与“人民”脱节。塔克说:“制宪会议中的天才们宣称人民才是主权的源泉;政府由人民建立,为人民的利益而建;管理政府的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他们的统治者和暴君。政府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为了加强他们的责任,人民应该询问他们的行为,细察他们的动机,详查他们的意图,洞察他们的设想,批评、称赞、拒绝或采用他们的做法。”但是“如果被剥夺了言论自由,这些都无法完成。”(50) 詹姆斯·奥格尔维质问,当联邦党“挥舞权力之剑砍向那些揭露篡夺阴谋的人的头颅时,谁还会向人民解释政府的运作呢?”(51)
共和党宣称,法令背后隐藏着联邦党更可怕的用意:建立专制政权。在他们的话语中,时常出现联邦党“专制统治”的形象。加勒廷指出,该法令强行压制针对政府的反对意见,使大多数“人民”只听到片面的“声音”,是联邦党“渗透他们权威,保全他们现有地位”的工具。(52)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通过法令,将联邦权力扩大。(53) 弗吉尼亚决议案警告说,联邦党的侵犯最终会使共和国转变为“一个绝对的,或至少混合式的君主制”。(54) 而库珀告诫读者,亚当斯是集权的专制暴君,是人民主权的敌人,是贵族和有钱人的朋友,他要通过反煽动法与常备军建立专制政府。(55) 他提到,剥夺言论自由不会避免党派之争,反而激化双方矛盾。当一个党派压制他们的反对意见时,“人民”不能行使公民权利,也不能理性地投票选举代表,只能听从单方面意见,国家就会陷入专制。(56) 而另外一派则成为从属,“暴力、恶意与深仇伴随而来”。(57) 于是,共和党号召各州联合起来,抵制法令。(58) 约翰·尼古拉斯呼吁,“所有的爱国者都要联合起来宣称法令是政治怪兽。”(59)
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的反对话语是在尖锐的党派冲突中提出的。在建国初期,政治精英对“党派”十分厌恶。他们普遍相信,“‘合众国人民’有着一致的根本利益”,政府的目标就是为了推进“共同福祉”,(60) 而政治“党派”代表了腐败的个人利益,会破坏社会的“共同福祉”。共和党人约翰·泰勒(John Taylor)在解释“党派”的含义时表示,“党派”就意味着整体被分割,宪法是为了推进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不是为了满足一部分公民的利益,所以“党派”是宪法的对立物。(61) 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也指出,任何联合阻碍法律和政策执行的活动都破坏了政府的“根本原则”。这些联合创造了党派,他们通常代表了少数狡猾和投机的人。由党派领导的政府只会反映派别关注的问题,而不会关心“共同福祉”。(62) 在党派斗争激烈的1790年代,联邦党与共和党都将对方视为企图分裂国家的“党派”。在共和党看来,联邦党实行等级制度,依靠财力和军事力量管理国家,国家陷入少数人集权的威胁中;而联邦党则认为,他们的反对派就是要颠覆宪法和联邦政府。他们在认定对方是“党派”的同时,始终坚信自己不是“党派”,认为自己是“爱国者”,是“具有美德”的精英,为公共利益而团结在一起。麦迪逊认为“党派”不会最终建立统治。(63) 杰斐逊曾指出,共和党远远超越了“党派”,而是“国家”。(64)
因为共和党认为自己为公共利益服务,所以他们的话语逻辑就站在维护“代表制民主”的高度,批判联邦党“剥夺言论与出版自由,建立专制统治”。同时,这也意味着共和党将联邦党原本对准他们的矛头“转移”指向了“人民”。共和党的观点除了在国会辩论中被提出,更多地发表在报刊与小册子上。随着法令的推行与共和党反对意见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共和党。
共和党的支持者在各种公共场所展开各种反对法令与联邦党的活动。在肯塔基、弗吉尼亚、田纳西与纽约,众多群众聚集在一起,谴责法令,号召州议会反对该法,想出补救措施。(65) 在共和党议员杰迪代亚·佩克(Jedidiah Peck)的号召下,纽约民众开展撤销法令的请愿活动。(66) 在佛蒙特,深受民众喜爱的国会议员莱昂因违反该法被指控入狱后,数千名当地居民进行请愿活动,要求亚当斯赦免莱昂;他出狱时,民众又自发举办庆祝活动。在选民的支持下,他还重获国会议员席位。(67) 即使在联邦党占绝对优势的马塞诸塞,自诩为“劳动者”的戴维·布朗(David Brown)游历80多个村镇,宣传反对联邦党的政治理念,他拿出名为《刺向暴政之剑》的稿件,广泛同村民交流,充满感染力的话语激起当地民众对联邦党的不满情绪。在他的倡导下,1798年10月在马塞诸塞的戴德姆,人们竖起自由杆,重新诉诸革命时代的话语:“不要《印花税法》,不要《敌对外侨法》,不要《惩治煽动叛乱法》……美国的暴君垮台;总统退职,副总统与少数派长存。”(68) 为数众多的民众参与到围绕法令的冲突中,使原本的党派之争逐渐演变成一场发生在公共场所与报刊等公共媒介、参与范围广泛的政治争论。
三、“公共意见”与对立双方的分歧
正如反对派所言,联邦党意图扩大权力,剥夺言论与出版自由了吗?在一片“反对声”中,联邦党借助报刊、小册子以及公开演说等公共媒介阐述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反对者展开深入争论。在法令颁布前后,“公共意见”始终是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69) 双方表达了关于公共意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功能以及如何形成公共意见等问题的观点。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双方对公共意见的分歧逐渐明朗,他们对立的观点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行动。
实际上,无论是联邦党还是他们的反对者都普遍认为,公共意见在国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根据当时人的逻辑,“公共意见”的权威性来自“人民主权”原则,它是握有“主权”的“人民”的意志的体现。联邦党人泽弗奈亚·斯威夫特·穆尔指出:“在国家法律与制度形成过程中,公共意见是首要的指导者”。“当立法实体背离公共意见,不会获得成功”;“法令实施若违反公共意见,不会有效果”。总之,公共意见与社会繁荣密切相关,(70) 詹姆斯·沙利文解释说:“自由政府体系建立在公共意见支持的基础之上”,对公共政策以及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自由、公开和广泛的交流,是保持体制原则所必需的。(71) 麦迪逊曾经提到,公共意见同政府密切相联,“是每个自由政府真正的统治者”,“所有的权力都要追溯于意见”。(72) 纽约的反对派领袖、律师图尼斯·沃特曼甚至认为,“公共意见是万能的”,“任何政府若同公共意见抵触,都不可能存在”,而新政府是保护所有人民利益的政府,所以公众意见不可或缺。(73)
在联邦党看来,正是因为公共意见如此重要,所以要限制无约束的言论与出版物。他们认为,若滥用言论与出版自由,形成的公共意见会危及政府,破坏社会的稳定。当面对反对派在报刊与小册子中的攻击时,他们对绝对的言论与出版自由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联邦党人在为法令辩护时提到,长期以来,没有原则的错误和滥用盛行,使公共意见误入歧途,威胁毁掉整个政府。(74) 穆尔解释说:“自由的出版物是美国革命中最大的幸事,也是值得高度称赞的。若出版物是真实的,爱国的,它们就会产生有益的效果,清除政治中的不纯洁,促进政治的健康发展。但是毫无约束的出版物是不公正的、恶毒的源泉,它远比战争和瘟疫的破坏力更加令人担心”。(75) 亚当斯的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也认为,尽管美国人民的良知会引导他们作出正确的决定与判断,但是无约束的新闻自由会产生破坏性的言论,会毁掉“人民”对国家的信任与社会的稳定。(76) 在波士顿,联邦党与共和党看待反对派报刊《独立新闻》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对于报刊不断刊登批评亚当斯政府政策的文章,共和党赞扬其致力于推动真理与自由。而联邦党根据法令对编辑托马斯·亚当斯提出诉讼,谴责报刊是“新形式的毒药”,它“播下煽动的种子”,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推测”。(77)
联邦党人对无约束出版物和言论的忧虑,反映出他们对“人民”的认知,因为“人民”获取出版物传播的信息是形成公共意见的关键。联邦党认为,“人民”在理解政治问题时既不理性,也不高尚,容易被煽动性的话语迷惑。尽管国家遵循“人民主权”原则,“人民”有权质疑统治者,有权选择或者罢免管理者,但是联邦党仍然相信普通人很难对国家事务作出正确的判断。曾担任宾夕法尼亚民事法庭法官的联邦党人亚历山大·艾迪生解释说,政体、立法与行政管理也是一门科学,同其他科学一样,要想理解它,需要知识、研究与思考。很难想象,“以现有的教育与知识状况,所有的人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78) 而且因为“人民”极易被煽动和迷惑,所以政府需要防范“人民”的愚笨,应该被赋予足够的权力检查“人民”的热情与偏见。(79)
在联邦党眼中,“被煽动”的“人民”对遵循“人民主权”原则的国家有极强的破坏力。艾迪生指出,与君主制或贵族制相比,在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家中,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如果人民没有权力,误导人民的判断,不会产生危害;如果人民拥有全部的权力,误导人民的判断,就会产生可能的最大危害。”(80) 有联邦党人提到,“代表制民主”政府是危险的,如果交流的渠道与“人民”都受到错误的误导,那“人民”就会错误地将好的管理者排除出政府。(81) 1789年以来法国经历的一切证明,“人民”能够被唤起毁灭性的热情,他们通过俱乐部、印刷品以及社团可以摧毁最好的政府。(82)
对联邦党而言,形成公共意见就是政府要引导“人民”表达顺从,而不是对政府的批评。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指出,联邦政府通过发展商业与制造业满足大众的物质需要,使“人民”达成对政府的信任与服从,公共意见就是“人民”对政府充满信心的表达。(83) 他明确区分了政府与“人民”的职责,指出,政府的官员既然是“人民”的代表,由“人民”选举而来,“人民”就应该尊重并信任他们。“人民”的美德不在于警觉,而在于信任政府。(84) 联邦党人虽然承认“人民”拥有权利,能够自由地选举代表和监督政府活动,但是否认“人民”能够对政府发出指令。他们认为,如果“人民”超越了权利的界限,人民代表制就丧失了意义。(85)
而联邦党的反对派看待公共意见的视角显然不同,他们更多地强调公共意见监督政府的功能。麦迪逊提到:“只有公共意见才能把我们从头脑发热的总统冲动的举动中拯救出来。”(86) 在党派斗争中,他将公共意见视为“由开明而觉醒的人民为保护他们自由而行使的‘中央权力’”(87) 他指出,“人民”应该“监督”政府,反对那些不合宪的篡夺。(88) 麦迪逊的观点得到了反对派的普遍认同。有人赞同道,联邦党作为“人民的代表,他们的行为要接受所有人的监督”。(89) 泰勒则认为,自由地监督人民“公仆”是美利坚人生来就有的权利,也是首要的权利,剥夺了这条权利,他们所有的自由就会丧失。(90) 佛蒙特州拉特兰地区的一张海报也清晰表述了公共意见具有监督功能:“自由地监督代表的公共活动,是防范权力膨胀与腐化的最有效方式。如果出版物不能正常出版,人民不能自由地表达,选民就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选,也不能防范政府官员权力扩张。政府沦为社会的祸根,自由与稳定的福祉就会消失。”(91)
至于如何形成公共意见,发挥“人民”的“监督权”,反对派因为个人身份、地位、经历、教育背景与个性的差异,对此的观点不尽相同。以麦迪逊为代表的政治精英提出,一方面要进行广泛的交流沟通。麦迪逊甚至表示:“自由地审视公共特征与相互交流是维护每个人权利的唯一有效方式”。(92) 沙利文进一步解释说,代表制政府要注重公开的政治讨论,使公众形成对管理者的意见。自由广泛地交流思想,可以暴露官员的缺点、不当举止以及制定的不合宪政策。(93) 另一方面,麦迪逊也没有否认政治精英对“人民”的引导,他“不相信每个公民的意见都同等重要”。(94) 他提出,“人民”简单地讨论并不能形成公共意见。汇聚公共观点进而形成公共意见,需要依靠各州和地方政府对观点的提炼,受过良好教育人士的引导,代表与选民交换意见以及代表之间的讨论。(95) 总之,“社会中开明的成员承担着塑造公共意见的重要职责”。(96)
然而,有人并不主张政治精英对公共意见的引导。威廉·曼宁生前默默无闻,他当过兵,是一名农民,写过很多政论文章。在他看来,普通人可以通过期刊聚集各地民众的想法,组织反抗,促进有效的地方民主,形成地区交流网,再将民主发展至全国范围中。因为通过报刊宣传,知识可在不同的团体中自由流通,这样人民联合无需强大的中心权威。(97) 他认为,“公共意见应自下而上组织,而非自上而下操纵”,政治精英不能将观点强加于公众,人民的代表应站在选民立场上行使权力,成为人民的公仆而非人民的主人。民意是保护自由的,反映多数人利益的关键,不能被压缩。(98)
还有更加激进的人士极力反对限制公共意见。纽约的约翰·汤姆森甚至解释说,同小孩无理由地喜欢不同的玩具一样,人们的思想也总是不同,因此表达不同的思想不能受到限制。(99) 沃特曼指出:“人类的心智本质上要扩展到每个方面”,因为思想的运转是不能控制的,总会对环境自发地作出反应。思想之间通过交流而联合,不可能为“思想的帝国”划定疆界,因而也就无法限制意见的形成。而且,公共意见也不能受到限制,因为在“人们所有的权利中,交流情感是最神圣和最宝贵的”。他相信公共意见是道德与理智的一部分,心智通过获取知识与理智,受到开导,摆脱感情的干扰,所有人都拥有将每个人指向真理的美德。在无限的公共讨论中,真理自然会胜利。(100)
在面对如何形成公共意见时,反对派提出的观点中既有精英的思考,也包括来自平民的意见;既有温和派,也有激进者。尽管各自的观点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但是他们却对重要的一点达成共识,这就是:“人民”获取了政治生活的相关信息,才能保证公共意见发挥实效。在题为“出版自由”的时评中提到,形成公共意见的前提是信息共享,并且得到大多数的同意。通过印刷品,原先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信息被更多的人了解,并且比口头指令更加令人印象深刻。(101) 麦迪逊则指出:“国土面积越大的国家,越不容易弄清真实的意见,越容易伪造意见”。“公路、商业、自由的出版物,特别是报刊在人民中的流通”,都能“促进情感的交流”。(102) 他在“1800年的报告”中写道,出版自由是“唯一有效地保护其他权利”的基础。他相信“自由交流,自由地监督公共政策”都离不开出版自由的权利。有才能并诚实守信的公民通过出版物自由讨论,传播观点,有效地监督政府行为,保护“人民”的权利。(103) 曼宁在小册子《自由的关键》中表示,为了防范少数人权力的扩张,人民需要“了解不同利益集团对政治制度产生的影响;知晓自由政府的原则以及国家的政体;熟悉对个人行动与利益产生影响的法律;探究竞选中官员的真正原则、性格与能力”。在获取这些信息时,“所有自由的人不能受到他人的误导与欺骗,而应该依靠自己的判断力”。但是“若没有连续的出版物,这些知识不能获取”。(104)
联邦党与其反对派截然不同的观点,既反映了各自不同的政治观念,也受到党派斗争中所处不同政治角色的影响,还包含不同的利益需求。从两派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歧集中在如何形成公共意见以及形成什么样的公共意见等问题上。联邦党认为,政府要防范言论与出版自由被滥用;反对派却表示,要保证言论与出版自由。联邦党提出,公共意见就是要引导“人民”表达对政府的信任;而反对派却强调,公共意见要发挥“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功能。
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中,两派的不同观点引导着他们“针锋相对”的行动。从颁布法令到共和党的反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联邦党与共和党的分歧。而在这场广泛参与的政治争论中,联邦党、共和党、支持共和党的报刊编辑与一些民众又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联邦党促成法令之后,根据法令相继指控“有煽动或诽谤”举止的人,其中波及共和党议员、支持共和党的报刊编辑与印刷商,还包括一些生平难以稽考的普通人,先后发生了14起案件。与此同时,他们在争论中,借助大量报刊和小册子阐述自己的观点。而共和党积极促进公共传媒的发展,增进与民众的交流与沟通。在1797—1800年间,至少33位共和党人成为办报人,其中12位在州议会任职,4人是市长,两位是国会议员。(105) 共和党还将他们的主张运用到随即到来的总统竞选中。在1800年总统选举前,他们在各州联合反对联邦党政策的选民,对有地方影响力的选民加紧游说和登记工作。他们在各种公共场所穿梭组织集会,甚至在跑马场、斗鸡场和宗教集会中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除此之外,他们向民众发放宣传单与小册子。约翰·贝克利(John Beckly)的小册子《为公共生活的辩护与托马斯·杰斐逊的性格》在费城、纽约、康涅狄格与马里兰共发送4000册。(106)
共和党的支持者也纷纷加入办报的行列。普通劳动者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收购某报社,更名为《自由之光报》(the Sun of Liberty),发表与联邦党格格不入的言论;约翰·斯诺登(John Snowden)与威廉·麦科克尔(William McCorkle)在他们的报刊中,也谴责法令,赞美当地的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巴德(Robert Bard)对法令权威全然不顾。(107) 在法令颁布前,联邦党报刊数量远远超过共和党。在1795年,将近四分之三的报刊或者支持联邦党,或者保持中立。全国大约只有18家共和党报刊,而且力量分散,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到1798年春,绝对支持共和党的报刊数量不超过10家。而如今支持共和党的报刊数量明显增多。在1800年增加的71家报刊中,有超过30家为共和党报刊;至1800年,支持共和党的报刊共有85家。(108) 支持共和党的编辑或印刷商纷纷更改了以往“公报”、“新闻”或“记录者”的题头,启用含有捍卫言论自由意味的名称,在题头加入“之光”、“之树”、“护卫者”,甚至“自由的胜利”等字样,比如《自由先驱报》以及《自由守护神报》(Genius of Liberty)。共和党报刊编辑更是在题头标明“共和主义者”字样。(109) 可以看出,当更广泛的群体参与到这场争论中,并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时,这个动态的过程极大地促进了公共传媒的发展。
四、政治争论与“公共领域”的发展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报刊、小册子以及公共集会等公共载体与媒介被广泛调动起来,承载着传播信息与相互沟通的使命。联邦党、共和党、众多报刊编辑与普通民众都参与到对话与交流中,“人民”与政治精英在这个广阔的空间中展开互动。20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将报刊、书籍、沙龙以及团体等联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媒介视为“公共领域”。(110) 从出版业与其他公共媒介的繁荣程度来看,法令没有限制住反对派的“煽动”言论,由法令引发的争论与行动反而推动了“公共领域”的成熟与发展。
争论中,报刊、小册子、咖啡馆和小酒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构建起信息交流的桥梁。尤其是共和党报刊编辑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他们建立起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沟通网络。大量的政治信息传播到各地,不仅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参与政治生活,更多普通劳动者通过报刊获取信息,参与政治事务的讨论。因为报刊的邮费低廉,订阅时可赊账;各个报刊之间的内容无限制地转载;各地的咖啡馆与具有旅舍功能的小酒馆中,人们能够阅读到免费报刊;甚至目不识丁的普通人也通过别人的大声朗读了解到政治,所以报刊成为人们获取政治生活信息的重要工具。在宾夕法尼亚,几乎每间小屋中都有《曙光女神报》。(111) 来自英国的游历者对有声有色的报刊印象深刻,他们描述到,酒馆与农户家中,报刊随处可见,生意人甚至在回家的马车上阅读报刊。(112)
当然,具有政治功能的出版物与其他公共媒介并不是瞬间产生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演变而成。哈贝马斯提出,在近代欧洲,通过组织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以及宗教社团,私人自发聚集在一起,在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咖啡馆、茶室以及沙龙等公共场所中谈论艺术与文学,随着参与者数量增多,“公共领域”初具规模。由于王室之外的知识分子的参与,原先属于贵族特权的自由辩论很快就发展成为公开的批评,在公共讨论中,时常涉及与国家实践相关的问题,谈论的主题由艺术与文学转变为政治。这个空间成为“自由的”公共意见能够产生的土壤,也是市民社会作用于国家政治的领域。
而在早期北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日渐成熟,各殖民地议会下院力量不断增强,推动公众广泛讨论政治议题。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口数量增加,私人生活空间悄然发生转变,各式咖啡馆与俱乐部诞生。清教徒禁酒运动失败后,具有旅店功能的小酒馆在18世纪繁荣起来。乡间酒馆成为讨论村镇事务的平台,各候选人与选民在其中交流理念;而城市的咖啡馆中,消费者不仅免费阅读时事报刊,而且进行政治讨论。(113) 除了酒馆与咖啡馆之外,报刊、小册子等出版物成为殖民地居民讨论时政的重要媒介。18世纪以来,波士顿、纽约以及费城等地先后创办多家报刊,詹姆斯·富兰克林在波士顿创办的《新英格兰报》成为政治评论报刊的先驱。这份报刊不仅登载抨击精英尊贵阶层的文章,而且转载表达自由权利的《加图信札》(Cato's Letters 1720-1724),为当时陈腐呆板的新闻界注入一股生气。18世纪30年代之后,政治评论开始在报刊上形成一些气候,在纽约,以英国报刊《独立辉格党报》(Independent Whig)为蓝本,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约翰·莫林·斯科特(John Morin Scott)以及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等人创办《独立思考者报》(Independent Reflector),抨击时政。
自从英国政府推行“新殖民地政策”,开始谋求强化对殖民地的管理和控制,各地的公共媒介更加活跃。殖民地人士通过出版物,唤起民众行动,达成共识,使他们有限的力量达到最佳的效果。(114) 他们在各地竖起“自由树”与“自由杆”,张贴海报,鼓舞斗志的话语间时常配有鲜活生动的图片。在一篇署名“弗吉尼亚人”的海报中写道:“美利坚人!醒来!醒来!你们的自由危在旦夕:看看你们的敌人,蜂拥而至,面临战争,武装起来!武装起来!”(115) 在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的年历中,他们也不失时机地利用各式格言、小诗、政治评论鼓动人民。除此之外,他们还将熟悉的旋律填入新的歌词,谱写出一曲曲号召联合追求自由的歌曲,在民间流传。他们用铿锵洪亮、朴实而激昂的话语,向北美居民传播自由的理念,“即使是最下层的人民,都比以往更加注重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更加喜欢对此刨根问底,更加坚定地加以捍卫”。(116)
众多出版物与公共场所成为抵制英王统治,争取北美殖民地自由独立的工具。它们将北美居民的情感和行动连接起来,使他们对“美利坚”的认同感进一步巩固,在称呼自己的时候,不再使用诸如“纽约人”或“弗吉尼亚人”,而光明正大地称自己为“美利坚人”。殖民地居民间的相互认同感与自由理念得到升华,有效地推动北美独立。
从哈贝马斯笔下的近代欧洲社会,至早期北美社会,再到美国革命时期,报刊、小册子以及公共场所将民众从日常生活引入政治生活,推动他们有意识地保护个人权利,防范王权。美国建国之后,合众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民”成为一切权力的源泉。“人民主权”原则为“人民”在政治生活中表达意见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法令颁布后,蓬勃发展的报刊、小册子与公共场所成为“人民”表示“同意”或“反对”的媒介,报刊维护“人民”权利的功能的话语又反过来诠释了“人民”作为“主权者”的地位。在联邦党势力占优的康涅狄格,《自由之光报》的莫尔斯直截了当地说,他们要独立思考,“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不能受联邦党左右。(117) 《独立新闻报》的编辑托马斯·亚当斯大声疾呼:“我们再一次发誓,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人民的自由被侵害,公众被压制。我们要尽力抵制侵犯者,将罪恶拉入正义的轨道,无论冒多大的危险,无论是谁保护和参与侵犯的行动。”(118) 他重复着约翰·亚当斯在美国革命时说的话语:“当英国货物税、《印花税法》、土地税(Land Taxes)以及具有野心的权力威胁到我们,使我们贫穷,走向毁灭”,“自由的新闻会维持人民的权威”。(119) 在《黄蜂报》的创办者查尔斯·霍尔特看来,报刊要为民主的讨论树立榜样,为真正的共和利益服务,支持国家有益的法律与宪法。(120) 在法令引发的争论与行动中,通过出版物等公共媒介,“人民”与政治精英开始广泛的交流与互动,“人民”的“声音”与共和党的主张配合,形成浑厚而响亮的“合唱”,推动了联邦党阻止“反对派煽动诽谤”的行动破产。
不可否认,政治精英通常在报刊等公共媒介中充当“引导者”的角色,公共媒介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公共领域”。在党派冲突的情境中,共和党号召“警惕联邦党扩张权力”,批评联邦党“剥夺言论与出版自由”,扶持反对派报刊,使民众在报刊与公共场所等公共媒介的言论和行动不同程度地受到共和党的影响,民众对联邦党的批评也并非反映了联邦党的真实意图。曾有历史学家指出,公共交流的模式并非是一种理性的商议,文学、艺术和表演都是一种情绪化的或者情感的表达,而不是理性的批评。(121) 在现实政治世界中,自由讨论往往夹杂偏见和个人情感。可以说,共和党成功地运用这种公共交流模式,报刊、小册子与其他公共媒介为共和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就在杰斐逊当选美国总统后,共和党在州范围内对联邦党的“反对言论”提出诉讼,联邦党同样发表公开言论谴责共和党伤害“言论与出版自由”。(122) 可以看出,公共媒介实际上成为党派斗争中可以利用的工具。
关于政治精英利用出版物等公共媒介引导“人民”,在18世纪末就有人提出批评。曼宁将社会中的人分为“少数人”与“多数人”。他认为,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自财富不均。而“世界上一直会存在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少数人管理政府,运用财富权力“操纵知识的建立和传播,阻止大众觉悟。”而多数人出于自我满足的无知,接受“附属”的状态,从政治生活中退出。在他看来,“公共领域”被少数人创造了有力和主导的对话,他们通过解释和构建,使对话远离法律和制度真实的含义,并取得了他们的优势。(123) 实际上,曼宁的观点颇具前瞻性。在19世纪20年代之后不断成熟的政党政治中,各党派在对抗时,时常与社会财富集团联合,国家权力介入公共媒介进行操控,在一段时间里,办报人不得不为了其生存而同政治家建立密切的联系,而大多数人对政治生活表现冷漠,这成为美国民主政治中的突出特征,也是现代政治理论家探讨的核心问题。
附识:感谢三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另外,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导师李剑鸣教授赐赠书籍,并多次得到他的悉心指导,谨此致以诚挚谢意。
注释:
① “民主共和党”也称“共和党”。在美国18世纪末的文献中,党派冲突中的两派通常被时人称为“Federalist”和“Republican”。18世纪末的“Republican”不同于美国现代政党政治中的“共和党”,作为“联邦党”的反对派,他们主张忠于美国革命精神与宪法,建立共和形式的政府,所以称之为“Republican”。在19世纪初的文献中,时常出现“民主”与“共和”两个词交替使用的情况,之后的一部分学者在著作中称其为“Democratic-Republican”,即“民主共和党”。文中与18世纪末大多数美国文献保持一致,将“Republican”译为“共和党”。关于两党的分歧与来历,学者做过细致的分析,可参见James Roger Sharp,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Early Republic:The New Nation in Crisi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
② Richard Buel,Jr.,Securing the Revolution: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s,1789-1815,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pp.214-291.
③ 代表性著作有:John C.Miller,Crisis in Freedom: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51; James Morton Smith,Freedom's Fetters:The Alien and Sedition Laws and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6; Michael Kent Curtis,Free Speech,“The People's Darling Privilege”:Struggles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American History,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pp.52-116; Leonard W.Levy,Legacy of Suppression: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in Early American Histor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176-309; Leonard W.Levy,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276-337; Donald Stewart,The Opposition Press of the Federalist Period,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69,pp.466-486.
④ Jeffrey L.Pasley,“The Tyranny of Printers”:Newspaper Politics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2001,pp.105-195.
⑤ Saul Cornell,The Other Founders:Anti-Federalism and the Dissenting Tradition in America,1788-1828,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9,pp.230-273.
⑥ 相关论著参见李龙:《试论美国1798年〈惩治煽动叛乱法案〉》,《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6期。另外,有一些论著也涉及法令的内容,这类论著包括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8—119页;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0—321页。
⑦ 给“人民”一词加上引号,是根据李剑鸣在《“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一文中的解释。他在文中提到,“在英语文献中,一般只有带定冠词‘the’的‘people’,才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因而在中文的行文中只能给‘人民’一词加上引号,以对应于英语中‘the people’的用法。”参见李剑鸣:《“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1页。
⑧ James Roger Sharp,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Early Republic,pp.40-41.
⑨ 转引自Merrill D.Peterson,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New Nation:A Biograp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385.
⑩ James Madison,“The Union:Who are Its Real Friends?” National Gazette,Apr.2,1792,http://www.constitution.org/jm/jm.htm,2005年9月15日。
(11) “Sentiments of a Republican,”National Gazette,Apr.26,1792,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5年12月13日。
(12) Madison,“A Candid State of Parties,”National Gazette,Sep.26,1792,http://www.constitution.org/jm/jm.htm,2005年9月15日。
(13) “Philadelphia,Tuesday-October 13,” Aurora General Advertiser,Oct.13,1795,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5年12月24日。
(14) Jeffrey L.Pasley,“The Tyranny of Printers,” p.97.
(15) 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1788-18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709-710.
(16) 参见 James Callender,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1796,Philadelphia,1797; James Callender,The American Annual Register,or Historical Memoirs of the United States,for the Year 1796,Philadelphia,1797,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5年12月25日。
(17) 参见 Alexander Hamilton,“The Warning,No.1,” The 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Jan.27,1797 “The Warning,No.IV,” The 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Feb.27,1797; “The Warning,No.VI,” The 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March 27,1797,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5年12月25日。
(18) 转引自 Jeffrey L .Pasley,“The Tyranny of Printers,” p.74.
(19) “The Reynolds Pamphlet,” in Henry Cabot Lodge,ed.,The Works of Alexander Hamilton,New York:G.P.Putnam's Sons,1904,vol.7,p.377,http://oll.libertyfund.org/,2006年1月24日。
(20) 为了缓解因《杰伊条约》造成的美法紧张关系,寻求与法国政府谅解的途径,1797年,亚当斯派遣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Charles Cotesworth Pinckney)、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和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三人,作为美国和平使团代表出使巴黎。然而,法国外长塔列朗却派他的代理人(美国代表的文章中用“W”、“X”、“Y”、“Z”先生称呼)向美国和平使团索要贿赂,调停未果,马歇尔与平克尼返回美国,格里继续留在法国斡旋,此事件被称为“XYZ事件”。
(21) John Adams,“To the Grand In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Claypoole's American Daily Advertiser,Apr.16,1798,http://infoweb.newsbank.com/,2010年12月3日。
(22) “Communication,”The 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June 18,1798,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5年12月25日。
(23) Annals of Congress,5th Congress,House,2nd Session,pp.1972-1973,http://memory,loc.gov/ammem/amlaw/lawhome.html,2005年11月14日。
(24) Annals of Congress,5th Congress,Senate,2nd Session,p.589,http://memory.loc.gov/ammem/amlaw/lawhome.html,2005年11月14日。
(25) Annals of Congress,5th Congress,House,2nd Session,pp.2093-2094.
(26) Annals of Congress,5th Congress,House,2nd Session,p.2097.
(27) Annals of Congress,5th Congress,House,2nd Session,p.2112.
(28) Adams's Addresses of May g,8,10,12,22 and 28,1798,in Charles Francis Adams,ed.,The Works of John Adam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1856,vol.9,pp.186-187,191-195,http://oll.libertyfund.org/,2010年12月2日。
(29) Annals of Congress,5th Congress,House,2nd Session,pp.2115-2116.
(30) The Sedition Act,in 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vol.1,pp.596-597,缩微胶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资料室藏。
(31) An Address of the Fifty-Eight Federal Members of the Virginia Legislature to Their Fellow-Citizens,Augusta,1799,pp.25-26,http://infoweb.newsbank,com/,2010年3月1日。
(32) “To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Virginia,1798,http://infoweb.newsbank.com/,2010年3月1日。
(33) Note D,Section 12,“Restraints on Powers of Congress,” in St.George Tucker,ed.,Blackstone's Commentaries,Philadelphia,1803,http://www.constitution.org/tb/tb-0000.htm,2006年1月20日。
(34) Annals of Congress,5th Congress,House,2nd Session,p.2151.
(35) Annals of Congress,5th Congress,House,2nd Session,p.2153.
(36) Annals of Congress,5th Congress,House,2nd Session,p.2153; James Ogilvie,A Speech Delivered in Essex County in Support of a Memorial,Richmond,1798,p.6,http://infoweb.newsbank.com/,2010年3月4日。
(37) George Nicholas,A Letter from George Nicholas,of Kentucky,to his Friend,in Virginia,Philadelphia,1799,p.17,http://infoweb.newsbank.com/,2010年3月4日。
(38) 转引自 John C.Miller,Crisis in Freedom,pp.75-76.
(39) St.George Tucker,A Letter to a Member of Congress,Virginia,1799,p.31,http://infoweb.newsbank.com/,2010年3月1日。
(40) Thomas Cooper,An Account of the Trial of Thomas Cooper,Philadelphia,1800,p.19,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5年11月25日。
(41) The Proceeding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5th,3rd Session 1798-1799,Philadelphia,1799,p.24,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3年12月27日。
(42) Thomas Jefferson,“Draft of the Kentucky Resolutions”; James Madison,“ The Virginia Resolutions,”in Lance Banning,ed.,Liberty and Order:The First American Party Struggle,Indianapolis:Liberty Fund,2004,pp.233-237,http://oll.libertyfund.org/,2005年12月20日。
(43) 转引自 James Morton Smith,Freedom's Fetters,p.203.
(44) 转引自 Michael Kent Curtis,Free Speech,“The People's Darling Privilege,” p.73.
(45) 李剑鸣:《“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46) James Madison,“The Report of 1800,” in Banning,ed.,Liberty and Order,p.258.
(47) Annals of Congress,5th Congress,House,2nd Session,p.2144.
(48) James Madison,“The Report of 1800,” in Banning,ed.,Liberty and Order,p.258.
(49) George Nicholas,A Letter from George Nicholas,of Kentucky,to his Friend,in Virginia,p.19.
(50) St.George Tucker,A Letter to a Member of Congress,p.43.
(51) James Ogilvie,A Speech Delivered in Essex County in Support of a Memorial,p.6.
(52) Annals of Congress,5th Congress,House,2nd Session,pp.2162,2110.
(53) James Madison,“The Report of 1800,” in Banning,ed.,Liberty and Order,p.246.
(54) James Madison,“The Virginia Resolutions,” in Banning,ed.,Liberty and Order,p.237.
(55) Thomas Cooper,“Mr.Cooper's Address to the Readers of The Sunbury and Northumberland Gazette,” in Thomas Cooper,Political Essays,Philadelphia,1800,pp.24-32,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5年12月19日。
(56) Thomas Cooper,An Account of the Trial of Thomas Cooper,pp.18-19.
(57) Thomas Cooper,“On the Propriety and Expediency of Unlimited Inquiry,” in Cooper,Political Essays,p.67.
(58) Thomas Jefferson,“Draft of the Kentucky Resolutions”; Madison,“The Virginia Resolutions,” in Banning,ed.,Liberty and Order,pp.233-237.
(59) George Nicholas,A Letter from George Nicholas,of Kentucky,to his Friend,in Virginia,p.19.
(60) 李剑鸣:《“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61) John Taylor,A Definition of Parties,Philadelphia,1794,p.4,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9年5月6日。
(62) George Washington,Farewell Address:An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New-Castle[Del.],1796,p.16,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5年12月13日。
(63) James Madison,“A Candid State of Parties,”National Gazette,Sep.26,1792,http://www.constitution.org/jm/17920926_candid.htm,2010年4月2日。
(64) 转引自 Merrill D.Peterson,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New Nation,p.931.
(65) Donald Stewart,The Opposition Press of the Federalist Period,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69,p.469.
(66) James Morton Smith,Freedom's Fetters,p.393.
(67) James Morton Smith,Freedom's Fetters,pp.242,244-245.
(68) “Boston Brown,” Massachusetts Mercury,Apr.2,1799,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5年12月25日。Chronicle.Nov.12,1798,转引自 James Morton Smith,Freedom's Fetters,p.260.
(69) “公共意见”对应的英文是“public opinion”,在中文译著中,学者将“public opinion”翻译为“舆论”、“公众舆论”、“公众意见”和“公共意见”等。本文采用《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论文集中《市民社会的模式》一文的翻译,参见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市民社会的模式》,冯青虎译,邓正来、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页)。作为政治概念的“公共意见”,这个词汇出现于18世纪前半叶。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当时的政治理论家并没有为“公共意见”下明确的定义,但从他们对“公共意见”的使用中,能够了解到他们对“公共意见”的认识。英国政治理论家大卫·休谟用“意见”表达共同承认或接受的思想或者观点。他认为,政治生活中的“公共意见”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对政府的尊敬和附属,而是通过自由社会中的公开交流,表现出公众“广泛的同意”。在美国建国初期,当麦迪逊谈及“意见”时,时常通过各种词汇表达这个概念,其中包括“预先形成的印象”、“偏见”、“判断力”、“情感”、“习俗”、“精神”、“依靠”等。他不把“公共意见”只看作“意见”的总和,同时,他还提到,公共意见不同于政府的技术安排。现代政治理论家根据前人对“公共意见”的认识与运用,概括了“公共意见”的定义。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提到,公共意见是“有关公众事务的”意见,“是一群公众或数群公众的散乱思想(意见)状态与有关公共事务状况的信息流的相互作用。当然,思想或意见状态包括许多成分:各种要求、欲望、偏好、态度以及整个信仰系统等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还有学者提到,公共意见是受过教育和知情的公众形成某种意见后,经过广泛讨论而形成的,是公众共同承认的。这一词汇涉及对政府职能部门的批评。参见Colleen A.Sheehan,“Public Opin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ivic Character in Madison's Republican Theory,” Review of Politics,vol.67,no.1(Winter 2005),pp.40-41; Alan Gibson,“Veneration and Vigilance:James Madison and Public Opinion,1785-1800,” Review of Politics,vol.67,no.1(Winter 2005),p.11; Colleen A.Sheehan,“The Politics of Public Opinion:James Madison's Notes on Government,”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49,no.4(Oct.1992),p.619;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104页;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77页;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邓正来、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第38—39页。
(70) Zephaniah Swift Moore,“An Oration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harles S.Hyneman and Donald S.Lutz,eds.,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1760-1850,Indianapolis:Liberty Press,1983,p.1210.
(71) James Sullivan,A Dissertation upon the Constitutional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Boston,1801,pp.9-10,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5年11月26日。
(72) James Madison,“Public Opinion,” National Gazette,Dec.19,1791; James Madison,“Charters,” National Gazette,Jan.19,1792,http://www.constitution.org/,2005年9月15日。
(73) Tunis Wortman,A Treatise Concerning Political Enquiry and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New York,1800,pp.24,28,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5年12月20日。
(74) Communications from Several States,on the Resolutions of the Legislature of Virginia,Richmond,1800,p.11,http://infoweb.newsbank.com/,2010年3月10日。
(75) Zephaniah Swift Moore,“An Oration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1216.
(76) “Abigail Adams to Her Sister,” April 7,26,May 10,1798,in Banning,ed.,Liberty and Order,pp.225-226.
(77) 转引自 James Morton Smith,Freedom's Fetters,pp.256,251.
(78) Alexander Addison,Reports of Cases in the County of the Fifth Circuit,and in the High Court of Errors & Appeals,of the State of Pennsylvania,Washington [Pa.],1800,p.212,http://infoweb.newsbank.com/,2010年3月15日。
(79) John C.Miller,Crisis in Freedom,p.16.
(80) Addison Alexander,Analysis of the Report of the Virginia Assembly,Philadelphia,1800,p.42,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5年12月5日。
(81) Annals of Congress,6th Congress,House,1st Session,p.412; Annals of Congress,6th Congress,House,2nd Session,pp.981,956,http://memory.loc.gov/ammem/amlaw/lawhome.html,2005年11月14日。
(82) Annals of Congress,5th Congress,House,2nd Session,p.2098.
(83) 参见 Colleen A.Sheehan,“Madison v.Hamilton:The Battle Over Republicanism and the Role of Public Opin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8,no.3 (August 2004),pp.409-410; Robert W.T.Martin,“Reforming Republicanism:Alexander Hamilton's Theory of Republican Citizenship and Press Liberty,”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vol.25,no.1 (Spring 2005),p.34.
(84) Robert W.T.Martin,“Reforming Republicanism,” pp.32-33.
(85) “From the Minerva,”The 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Aug.7,1794,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7年12月23日。
(86) “To Thomas Jefferson,Feb.1798,” in Gaillard Hunt,ed.,The Writings of James Madison,New York:G.P.Putnam's Sons,1900,vol.6,p.309,http://oll.libertyfund.org/,2010年7月14日。
(87) “House Address to the President,” 27 November,1794,in William T.Hutchinson,et al.,eds.,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vol.1-1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11-17,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62-1991,vol.15,p.392,转引自 Alan Gibson,“Veneration and Vigilance:James Madison and Public Opinion,1785-1800,” pp.9-10.
(88) James Madison,“Charters,” National Gazette,Jan.19,1792.
(89) Henry Lee,Plain Truth:Addressed to the People of Virginia,Richmond,1799,p.25,http:// infoweb.newsbank.com/,2010年7月14日。
(90) The Proceeding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5th Congress,3rd Session 1798-1799,pp.7-8.
(91) “To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reeme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utland,1799,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5年11月25日。
(92) James Madison,“The Report of 1800,” in Banning,ed.,Liberty and Order,p.256.
(93) James Sullivan,A Dissertation upon the Constitutional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p.20,34.
(94) “Madison to Thomas Jefferson,13 June,1793,” http://www,constitution,org/jm/17930613_tj.txt,2010年4月3日; “Madison to Thomas Jefferson,2 March,1794,” in William T.Hutchinson,et al.,eds.,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vol.15,p.269,转引自 Alan Gibson,“Veneration and Vigilance:James Madison and Public Opinion,1785-1800,” Review of Politics,vol.67,no.1(Winter 2005),p.24.
(95) 参见 Colleen A.Sheehan,“Madison v.Hamilton:The Battle over Republicanism and the Role of Public Opin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8,no.3(August 2004),p.420.
(96) Colleen A.Sheehan,“Madison v.Hamilton,” p.416.
(97) Michael Merrill and Scan Wilentz,eds.,The Key of Liberty:The Life and Democratic Writings of William Manning,“ A Laborer,” 1747-181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60-162.
(98) Michael Merrill and Scan Wilentz,eds.,The Key of Liberty,p.162; Saul Cornell,The Otker Founders,p.251.
(99) John Thomson,An Enquiry,Concerning the Liberty and Licentiousness of the Press,and the Uncontrollable Nature of the Human Mind,New York,1801,p.13,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5年11月26日。
(100) Tunis Wortman,A Treatise Concerning Political Enquiry and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pp.146,123,160.
(101) “Liberty of the Press,” Time Piece,July 13,1798,http://www,proquest.com.proxy-remote,galib.uga.edu/,2009年3月13日。
(102) James Madison,“Public Opinion,” National Gazette,Dec.19,1791.
(103) James Madison,“The Report of 1800,” in Banning,ed.,Liberty and Order,p.256.
(104) Micheal Merrill and Scan Wilentz,eds.,The Key of Liberty,pp.159-160.
(105) Jeffrey L.Pasley,“The Tyranny of Printers,” p.168.
(106) Bernard A.Weisberger,America Afire:Jefferson,Adams,and the Revolutionary Election of 1800,New York: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0,pp.246-247.
(107) 转引自 Jeffrey L.Pasley,“The Tyranny of Printers,” p.150.
(108) Jeffrey L.Pasley,“The Tyranny of Printers,” pp.106,118,126.
(109) Jeffrey L.Pasley,“The Tyranny of Printers,” pp.153-154.
(110) 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看作联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桥梁,而西方“公共领域”概念的产生源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合为一体,社会的身份由它的政治组成来界定。进入17、18世纪后,“市民社会”的概念出现新内涵。一方面,随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迅速崛起,社会外在于政治的特征明显,政府不仅不能侵犯个人自由和财产权,而且需要提供合法的保护。另一方面,欧洲不断出现各种反专制主义思潮和改革运动。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衍生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经过洛克、亚当·斯密、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以及黑格尔等思想家的探索,他们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进行分界,“市民社会”具有某些基本特征。首先,它由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成,有别于政治社会;第二,它是个人权利,特别是财产权的基础。哈贝马斯将“市民社会”划分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其中私人领域是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的领域,包括家庭的内部空间。公共领域则是由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构成的私人有机体,它包括团体、俱乐部、党派、沙龙、报纸杂志书籍等,通过它们,连接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哈贝马斯认为,理想中的“公共领域”对国家集权进行批判性的公共讨论,形成所谓公共意见,以监督国家权力并影响国家的公共政策。参见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邓正来、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第25—49页;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李强译,邓正来、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第50—53页;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67页。
(111) Samuel Miller,Brief Retrospec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vol.2,p.254,转引自 Jeffrey L.Pasley,“The Tyranny of Printers,” p.197.
(112) Jeffrey L.Pasley,“The Tyranny of Printers,”p.202.
(113) Jon Butler,Becoming America:The Revolution Before 177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10-111,171-172.
(114) Richard Buel,Jr.,“Freedom of the Press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The Evolution of Libertarianism,1760-1820,” in Bernard Bailyn and John B.Hench,eds.,The Press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Worcester,Mass.: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1980,p.73.
(115) 转引自 Arthur M.Schlesinger,Prelude to Independence:The Newspaper War on Britain,1764-1776,New York:Knopf,1958,p.39.
(116) “Dairy of John Acdams,Dec.18,1765,” in Charles Francis Adams,ed.,The Works of John Adams,Boston Little,Brown and Co.,1850,vol.Ⅱ,p.154,转引自李剑鸣:《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辩论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87页。
(117) 转引自 Jeffrey L.Pasley,“The Tyranny of Printers,” p.163.
(118) 转引自 James Morton Smith,Freedom's Fetters,p.251.
(119) 转引自 James Morton Smith,Freedom's Fetters,p.252.
(120) Charles Holt,“The Bee.New-London:Wednesday,November 14,1798,” Bee,Nov.14,1798,http://infoweb.newsbank.com/,2005年12月10日。
(121) John L.Brooke,“Consent,Civil Society,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and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in Jeffrey L.Pasley,Andrew W.Robertson and David Waldstreicher,eds.,Beyond the Founders:New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4,p.225.
(122) John C.Miller,Crisis in Freedom,pp.231-232.
(123) Michael Merrill and Sean Wilentz,eds.,The Key of Liberty,pp.136,61,151,63-64,140,146.
责任编审:姚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