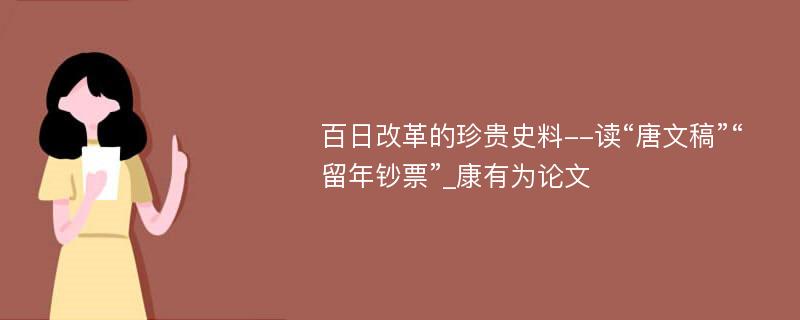
难得一见的百日维新史料——读唐烜稿本《留庵日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百日维新论文,稿本论文,史料论文,读唐烜论文,留庵日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4)-01-0105-13
唐烜的日记是二十多年前,我在为《清代人物传稿》搜集史料时,偶尔发现的一个稿本。这部日记的原名叫《留庵日钞》。日记的作者唐烜,字照青,直隶盐山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乙丑科二甲第九十四名进士,授刑部主事,此后一直滞留京师,在刑部任职,大约从光绪初年开始,唐氏养成了写日记纪事的习惯。日有所闻,晚则记之。长期坚持,甚少间断。唐氏于《留庵日钞》开首即对其家世及撰写日记之缘由,有详细说明。其文曰:
予自未冠时即窃有记录。日间趋庭之暇,……故家父老过从,偶谈旧事,凡岁时之丰歉,方里之变迁,以及土风乡俗之有涉今昔升降之故者,悉缕述无遗。盖阅世太浅,酬畣绝寡,依依膝下,皆宽闲之日月也。光绪戊寅,年二十四,值岁大祲,比屋流离,饿殍载道,家无宿粮,……,春间时疫流行,连遭灭族之丧,情绪尤恶。先严染疫几危,经用汤药,幸早痊愈,而甘旨之奉缺如,东西求乞,仅代藜藿,二麦既登,稍释饥困。三弟年十九矣,学理家计,颇有条理,忽忽疡亡,肝肠崩碎,万念俱灰,不握管作书者数月,而日记遂止于斯。迨通籍后,在都门因应略烦,惧有遗忘,辄复逐日登记,然已非复少时之蹊径矣。戊戌冬奉派监督陵工,有蓟门之行,归后为二老庆七旬寿,已岁暮矣。作行纪未果,而先严即于次年正月见背,苫块昏迷,忽为纤人交构,侮难纷沓,自知罪戾悼悔,几不欲生,由此贫病无聊,百忧丛集,杜门不出者年余,无可省记。至夏五月,而拳匪之乱作,六十日中炮火惊心,举家槁饿,城将陷,急走郊外,奉先柩浅厝,仓皇回寓,引领待尽,侥幸无恙。……回忆三载以来,国祸家难,所遭之不幸,有非笔舌所能宣者……。
光绪廿七年岁次辛丑除夕守岁记。唐烜时年四十七岁。(注:《留庵日钞》稿本,第1册,第1页。)
唐氏此记,叙述了他在戊戌前后所遭遇的家破人亡与艰难困苦,他还在这篇守岁记文章的下面盖有两方印章:一曰唐烜,一曰浩劫余生。唐氏之经历可谓一般小京官缩影,颇具代表性。
在唐氏所有日记中,以戊戌年最为精彩纷呈。盖因京师轰轰烈烈进行的百日维新,对这位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刑部官员,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光绪皇帝的新政谕旨,犹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因而对唐氏和他的同伴们产生了从来未有的震撼。唐氏的一切感受与日常交往,均在日记中留下了生动的记载。
多年前,为纠正黄彰健先生《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的明显错误,我曾撰写了《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刑部传抄本之发现及其意义》一文,(注: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94-206页。)稍稍引用了《留庵日钞》。此文发表后,不少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同行颇感惊喜,有人甚至撰文指出:《留庵日钞》堪称近年来发现的有关戊戌维新颇为重要的原始资料之一。为了使近代史同仁,对此日记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兹结合当前戊戌变法研究中一些极有争议的问题,再撰斯文,以供参酌。
一、康有为是变法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近年来,随着戊戌维新研究的不断深入,有的论者对康有为是不是变法运动中心,表示怀疑;对康有为是不是戊戌维新的主角提出了疑问。邝兆江教授的《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提出新说“康有为政变前不是中心人物,政变后由于他和他的弟子梁启超鼓吹宣传,才使康氏的地位上升”(注:《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还有的学者,过多强调了康氏变法期间的消极面,较多地否定他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对康有为的历史作用及其在百日维新中的真实处境,并不完全了解,对康有为的历史作用估计过低。
其实,关于康有为真实情况,在唐氏的《留庵日钞》中有十分翔实的记述,用了许多笔墨来写康有为在京师之活动。唐氏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898年7月8日)写道:
近日中朝政教,一切改用西法,力革旧制,月内恭读邸抄上谕,几于三令五申,涣汗之颁,伦綍之出,几于无月无之。其大者,尤在于立京师大学堂一事,继废时文试帖之诏,相距不过旬余。
盖自今岁春间,谏垣枢部相继条奏,请嗣后武科改试枪炮,部议章程允行。又饬各省督抚,各陈所见,议论参差,最后为陕甘陶子方模制军之奏,详明痛快,遂有暂废武科之议。因而裁冗兵,改用洋操,废时文改试时务之旨,而大学堂之议上,得旨允行。其间更张者不一而足,而发难之端,则由于月初宋芝洞伯鲁,杨殷存深秀两侍御,奏参许筠庵大宗伯,以守旧愚迂谬,阻挠新政为词,谕令许应骙,明白回奏。许回奏则力辨并无阻挠之说,而於新进之康有为则排击甚力,请旨罢斥,疏上,谕为调停。
康有为者,广东南海县人,乙未科进士,签分工部主事。此人才气极大,好议论,尤喜谈西学,在籍为孝廉时,即自命为孔子而后一人。粤省官绅士庶,拜门求教者甚伙。所著书说,专崇西学,以为合乎唐虞三代,中国劫运将至,若不亟思变法,则四万万之众必至靡有孓遗种类强矣。又遍谒大僚,餂以富强之策,咸以为宣尼复出。其弟子辈,亦多以四配十哲自命者,若汉唐宋明诸大儒,视之蔑如也。
原名康祖诒,字长素,即祖述尧舜之义,长素云者,孔子为素王,而伊之神圣则又过之。通籍后,易名有为。去冬遍干当路及台谏之知名者,又纠合同党,立为保国会。大意谓:欲保全中国数千年来之道统,与四百兆人之性命,非专攻西法不可,而于朝廷无涉也。何也,盖自古无不亡之国,中国时势已不可为,将来易号改朔,有伊等一辈人,自能立致太平云云。都下士大夫识与不识,或目为奇士,或斥为妖人,气焰尚未大盛。
自四月间,徐子静致靖学士专折保荐人才,请召对录用,奉旨允之。召见后,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所望甚奢,私意破格超擢,比旨下,颇失望。又以同乡许大宗伯素薄其无行,且因其在广东会馆立会一事,饬馆役驱逐之,衔次骨。而许方为总署大臣,必不得任所欲为。遂暗嗾宋、杨两御史,联衔参许,意在将许罢斥,或撤出总署。及计不行,遂扬言于众曰:章京不过奔走之差,我决不为也,竟不到任。而自上次召见,自陈著作,面谕以进呈所著书籍,以故迭次谕旨,及新法各条,详细章程,皆伊所进书中语也。(注:《留庵日钞》,第1册,第85-86页。)
唐氏上述日记,详细记载了一个普通的京官在百日维新开始后,对康有为认识逐步加深的过程。它如实叙述光绪皇帝在实行新政过程中,痛斥许应骙、文悌等人的疯狂阻挠,坚定不移地为康有为撑腰的详细过程。尽管唐氏当时思想尚趋守旧,对康有为活动颇多微词,但是,他也不能不承认:“而自上次召见,自陈著作,面谕以进呈所著书籍,以故迭次谕旨,及新法各条,详细章程,皆伊所进书中语”。说明康有为在变法其间的重要建议,非但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重视,而且作为迭次谕旨颁行。可见,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确是言听计从。那种认为光绪皇帝对康氏“关系暧昧”,“并非言听计从”的观点实在是局外人之谈,与事实不符。
而且,唐氏所记并非孤证。拙作《百日维新密扎考释》曾披露的李符曾致张之洞密扎亦谓康有为“有所建白,皆直达御前,每日旨从中出,盖康笔也。”(注: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李符曾的密札与唐氏日记不谋而合,均强调百日维新时光绪皇帝所颁布的新政谕旨,大多来自康有为进呈的奏折与有关各国变法的书籍。可见,康有为乃百日维新的核心与灵魂。这是当时清廷大小官员的普遍认识,与档案所记亦相符合。故宫博物院所藏康有为变法奏议之所以命名为《杰士上书汇录》,即体现了皇帝对康有为之赞赏。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没有康有为即没有百日维新。
关于康有为在变法中之影响,唐氏于戊戌政变后的日记还有进一步的补充记载:
八月十七日,早起,辰初入西长安门,伺候朝审。上班事讫,已巳正矣。遂入城,偕同司诸君至福隆堂公宴,邀李莹如到。渠为广东香山县人,稔康有为及保国会事甚悉。据云:伊等党羽甚众,约四百余人,皆与康逆为死友,中外二、三品大员中,有具贽拜为门下者,倡为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互相煽诱,终日若狂。而林煦小儿与谭嗣同逆子,持之尤力。林已自剪辫发,家居即为洋人衣冠,唯出门酬应,不得已始服袍褂、冠顶,盖蓄志变夏亦已久矣。日夕始散。(注:《留庵日钞》,第1册,第120-121页。)
读唐氏此日之记,便可看出康有为非但只是对光绪皇帝有影响之人,他对一般的官僚,在当时也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至于谭嗣同、杨深秀、林旭等变法时期的活跃人物,则更是把康有为视作精神支柱。
因此,我们绝不能认为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官位低微,仅仅是工部主事,以及他的召开制度局的计划未得实行,便认为光绪皇帝对康氏“态度嗳昧”,未加重用,康氏并非变法主角。读了唐氏之《留庵日钞》,上述错误结论便会不攻自破了。
二、对王照等重要人物的翔实记载
《留庵日钞》不仅对变法的主角康有为有翔实的记载,对其他百日维新中的活跃人物亦有精彩纷呈的记述。
作为在刑部入值的京官的唐烜,与王照兄弟为直隶同乡,他们之间关系颇为密切,交往亦相当频繁。王照,字小航,直隶宁河人,光绪甲午进士,后由庶吉士改官至吏部主事,具有典型的北方人性格,言语诚实,办事仗义,“身躯奇伟,治事有能名”(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1953年版,第84页。)唐氏与王照兄弟百日维新中颇有往还。《留庵日钞》六月初三日记曰:
入署。拟午后赴贡院,为同人辈送场,遇王湘岑游戎至,不果行。湘岑乘骑而来,路途泥泞,溅污於裤……又话移时始别去。湘岑连年颇究心西学,谈及近日朝廷变法事,与予见不甚和合,然治法治人之说,则湘岑亦无以易也。犹忆甲午之秋,朝鲜乱起,中东构难,兵端甫开,即有叶志超牙山被困、丁汝昌高升轰沉之信,嗣有讹传,济师获胜,倭人退兵之说。时予与湘岑已数十日未见,偶出永定门访之,晤谈数语,即是此事。湘岑不以为喜,而以为惧,愀然向予曰:果尔则祸患深矣。予讶之。湘岑云:若我师不甚得手,朝中诸老,或有转圜罢战,行成不至大吃亏也,若狃于小胜,则枢府必高兴,中外主战者幸己说之偶验,以娇惰不经战之将士,而当处心积虑,坚忍猛鸷之强敌,势不至丧师失地大辱国不止,可惧哉!又云:今岁正届我皇太后万寿六旬,普天同庆,正当修好邻邦,保全大局,且日本初入朝鲜之时,与中国本无深怨,不过小有波折,所需索者,於我无甚伤损。倘专任合肥相国,事已了矣,何至决裂如此。今情见势诎,恐辽东一带无安枕之日也。是时,东兵尚未至平壤也,左冠亭宝贵尚未阵亡也。予疑信参半,唯以湘岑论和局为失。其后所言乃一一验矣。达人先见之明,知几之哲,审势料敌,了如指掌,良深愧服。(注:《留庵日钞》,第1册,第88-89页。)
这是一则很有意思的日记。据唐氏所述,王照在甲午战争中颇以李鸿章的主张为正确,这在帝党官僚极为少见。唐氏又于六月十一日记曰:
是日散值甚晚,回寓已二钟矣。……今早王湘岑游戌遣专足来,询及《校邠庐抗议》各衙门分给者,尚有余书否?拟倩予代借一观,盖湘岑故未见此书也。来札云急思一阅,斟酌论断,将来留刊文集中,以搏身后名云云,言极沉痛。予复札谓,署中更无余书,唯冯公此议,已载于《续经世文编》,散见各门,可于坊肆购一部观之,即得其全貌矣。(注:《留庵日钞》,第1册,第92页。)
对于轰动一时的王照弹劾礼部六堂官一事,唐氏记载尤详。其文曰:
七月十七日,晴,入署。……昨日邸抄,上谕严斥礼部诸堂官,并交部议处,缘礼部司员王小航照者,条陈事件,呈堂阅看,许大宗伯筠庵,以折中多有违碍,且有力请銮舆,恭奉皇太后巡历外洋,及中国士民当改从泰西衣冠,以一耳目定心志之论,不愿代为陈奏。王乞请再三,堂意颇不怿,乃当面抵牾,语多胁制,许筠翁大怒,遂于奏折中参劾,乃谕旨竟将礼臣责斥,而王疏留览,举朝大骇,然以此事观之,上意可知矣。灯下姜宝兄遣人来询及严亲……札中并及王仪部事大为不平。筱航为湘岑之弟,卓生之兄,弱冠后曾得有疯疾,数年始愈,遂掇科第,与其兄弟皆不睦,于卓生尤参商,为人乖愎自用,虽才气极大,而同人中多落落难合。近来专主西学,闻其在城外自立学堂一所,用直省公款,而凡事不谋与众,措置任意,人多怨之。与广东康有为交最密,凡所议论,皆康所著录者也。
予独怪王氏同胞三人,为宁河王刚节公曾孙。刚节名锡朋,道光年英夷掳江浙,陷定海,三总兵同日殉难者也。刚节战尤力,以无救败,死事尤烈,故褒恤有加,其孙曾当与夷人为不共戴天之仇,即以今日时局为西学当兴,不应推崇夷俗若是。乃渠昆季虽志趣不同,而左袒西人西法,直是和身倒入。
湘岑与余交最久,且厚,每晤谈,辄极口称泰西不置,至以中国人当如西人之尊奉耶酥,不如是不足以为治。予一笑置之,不与辩也。王小航乃竟以改衣冠,易民主为言,其情理殊不可解。(注:《留庵日钞》,第1册,第108-109页。)
上述数则日记说明,唐氏与王照三兄弟过从密切,无话不谈。双方政治观点虽有很大分歧,然而,由唐氏日记中亦可清楚看出,王照推崇西学,倾向维新的显明立场。尽管在其奏疏中并没有涉及“改衣冠,易民主”的内容。正因为王照具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在百日维新中始终站在康有为为首的改革派一边,同守旧朝臣当面抗争,毫无惧色。当然,王照与康氏变法之政见并不完全相同,王照主张让慈禧拥变法之虚名,而皇帝行新政之实事,比康有为更讲策略。
《留庵日钞》对维新派的对立阵营,也有很翔实的记载。戊戌闰三月初五日(1898年4月25日)日记,对徐桐仇视西学,蛮横无理的情状叙述得栩栩如生。其文曰:
同慕丈谈许久,道及刘仲鲁同年,不悦于许荫轩相国事,深为抑闷。盖相国素负清正之望,近年中外亟言变法,士大夫一意趋骛西学,相国深恶此辈人,以虽正揆席,未入政府,事权不属,居恒太息激愤。仲鲁自为孝廉时,即以敦品励行见知于相国,入词苑後,尤所属意,都下官学、义学,凡相国所经理者,皆延仲鲁为之教督。今春忽有进蜚语于相国者,相国颇为所动。及蒋艺圃侍御、张玉叔铨部、王筱航礼部创建八旗奉直洋学堂,仲鲁稍稍与议,比公启同乡后,相国知其事之创始,有仲鲁在内,遂大恚,斥为离经叛道,前后异趣,逢人必痛斥其非,大有鸣鼓示小子之意。仲鲁向有清秘堂差事,去岁已送京察一等,闻相国近日从不至清秘堂。以掌院到日,凡编检之与差者,皆逐一进谒,相国不愿目中再见斯人,故竟不往,而又屡向人道及之仲鲁之,意在自行辞差,尚未知果否也。(注:《留庵日钞》,第1册,第49页。)
上文中仲鲁,系指刘若曾,直隶人士。清秘堂,则为翰林院之办事机构。所谓八旗奉直洋学堂,乃直隶京官所办之新式小学,位于南横街,百日维新期间,曾请大刀王五教授武艺体操课程。(注: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第125页。)徐桐利用作为翰林院之掌院学士的地位,排斥打击一切与新政有关的人员。“凡言改制者皆削弟子籍”,“凡门人言新政者,屏不令入谒”(注:《清史稿》,卷471,徐桐传。)专横霸道,蛮不讲理,其对刘仲鲁的态度可谓一个典型事例。
除了徐桐之外,《留庵日钞》对两面三刀的满人御史文悌,亦有精彩记述。其文谓:
有满洲侍御文仲弓悌者,前以户部司员,京察记名,简放河南知府,在任三载,丁艰回旗。起服后仍在原衙门行走,保送御史,去冬传补。此人向在户部有声,阎文介深重之,学问亦淹雅绝伦,上月中旬,专折纠参康有为暨宋伯鲁、杨深秀多人,折中备言:康某为人,有才无行,语多不法,曾托人向文侍御先容,往来数次,具见底里,而宋、杨以风宪官,受其指使,可为无耻,洋洋数千言,语极痛切。奏上,上谕斥其迹近朋党,难保无受人指使情事,不胜御史之任,著仍回原衙门行走。
近日折已发抄,都中人士盛传诵,以为朝阳鸣凤,虽不见听,亦足作中流之砥柱矣。(注:《留庵日钞》,第1册,第86页。)
文悌在京师是那种“媚若九尾狐,巧如百舌鸟”的人物。他随风转舵,巧言令色。他先入了维新阵营,而后又背而弃之,且嫁祸于人,故守旧朝臣称之为“中流砥柱”。唐氏当时对文悌即充满了同情。对于文悌被光绪皇帝罢斥御史之职后的穷困潦倒处境,日记亦有记载,略谓:
六月初九日,昨晤英鹤龄,谈及文仲弓侍御抗疏事,并言侍御近况,清苦殊甚,家中几于不能自给。又见鹤龄所持折扇,皆侍御书画,书为近作七律二首,闲中雅兴句也。
末首结句云:明日荒厨无宿米,料应梦不到黄粱。
窘乏之状毕露,而句恰风趣。侍御因论新进事,改官户部撰纪恩七律四首,都下一时传诵,其词肫贽,蕴蓄怨而不怒,无嚣张叫呶之习,可谓今之古人哉!(注:《留庵日钞》,第1册,第91页。)
由于唐氏在政治上倾向守旧,故而对文悌这样的两面派文人,不是口诛笔伐,而是歌功颂德。其实,文悌以人品而言,一无足称,他为了自己的一官半职,不惜对维新志士栽赃陷害,血口喷人,实在是两面三刀的投机者。
三、“招外兵,劫大内”,关于戊戌政变最早的私人记载
有声有色的百日维新,由于突然发生的政变而嘎然中止。历史航船非但没有驶往胜利的彼岸,反而回过头来开了倒车。六君子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被推上了断头台,血洒京城菜市口。第二天,清廷颁布上谕称:
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求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设施,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注:光绪二十四年上谕档。)
这是清廷首次在上谕中提到康有为“谋围颐和园”。然而,政变之真相究竟如何?政变何时发生?袁世凯有没有告密?有许多疑问至今还争论不休。究其原因,盖因为没有确凿的史料。作为与政变有关的当事人,慈禧与清廷的执政者,以为砍了六君子的头,便可以杀人灭口;而维新阵营中的梁启超,直到亡命日本数月后,办起了《清议报》,才在该报中揭示了戊戌政变细节。至于他的老师康有为,亦于是年底才在其自编年谱中有所涉及。而政变的告密者袁世凯,直到1926年,《申报》才发表了他的那篇不知改了多少遍的《戊戌日记》。偌大京城,当事者诸人居然没有人在戊戌政变后,当即留下一些可信的文字。
然而,《留庵日记》的发现,却能给人一个惊喜,给学者们提供研讨新的线索。这些文字可视为戊戌政变后,最早有系统的私人记载。
唐氏由于在刑部任职,而关押、处决六君子都是刑部具体执行的。作为一个颇有头脑的官员,唐氏在日记中留下了不少与政变有关的史料。除了拙作《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刑部传抄本之发现及其意义》一文中引述的关于谭嗣同、杨深秀在狱中写诗明志的有关片断外,唐氏还在刑部同僚那里,了解到有关戊戌政变发动的详细过程,都在日记中作了翔实的记述。其中,慈禧发动政变的当天,唐氏留下了如下记载:
八月初六日,阴,入署。……是日在署,忽喧传步军统领衙门奉皇太后懿旨,查抄张荫桓,并捕拿康有为等辈。出城后街市纷纷相告诉,及探听数四,始知系奉口诏严拿康某。及番役到城内掩捕,则康某已脱身赴津,遂将其弟康广仁搜获,并抄出信件无数,按名点查,大半京外大员居多。因伊素与张荫桓交甚秘密,疑在该处藏匿,派兵围其宅,二次穷搜,弗得。又至一曾姓户部家,及王小航照京卿寓所,徐子静致靖侍郎宅皆不获。立即遣干员乘轮车,赴津追捕,未知能漏网否也?
薄暮始阅邸抄,上谕恭请皇太后听政,以今日为始,至初八日率王大臣在勤政殿举行典礼。(注:《留庵日钞》,第1册,第115页。)
此日所记“奉口诏严拿康某”十分重要,它说明清廷捕康有为显系突发的紧急行动,事发前一点也未对外宣露,故而军机大臣来不及拟旨,而以口诏捕拿,实属不同寻常。又搜出信件无数,大半京外大员居多,亦可见康氏之交往与影响。
八月初九日,晴,入署。在署闻步军统领衙门奉旨,查拿康有为之党,指名搜索六人:御史杨深秀,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煦及户部侍郎张荫桓,均交刑部治罪。张自四月间,都下讹言,奉旨拿问,不知因何而起,至是果然。(注:《留庵日钞》,第1册,第117页。)
此日所记再次说明,步军统领指名搜索杨深秀、谭嗣同等六人应系八月初九日之事。
八月初十日,晴,入署。是日闻昨日查拿诸人,均送到刑部收监。杨侍御先为刑部员外郎,去冬始转御史,夏间为文仲弓侍御奏参,同宋伯鲁党附康有为,往来甚秘云云,近闻其上封事廿余首,力主变法。杨为己丑同年,且同出浙江张肖庵先生之门,询为山右才子,素讲汉学,著述颇多,唯性情迂执,与朋友多落落寡合,不知何以阑入康党,殊所不解。刘为癸未科进士,分刑部广西司,性尤孤僻,每入署辄不上堂,谈及公事,亦颇谙悉。印稿拉之同往终不肯,自以随行逐队谒上司为耻。自议新法後,湖南巡抚陈右铭宝箴,列保通晓时务贤才,刘与杨锐均与焉。刘、杨皆四川人,素交好,杨与湖南巡抚有旧,常为刘游扬其才品,故并登荐剡。(注:《留庵日钞》,第1册,第115页。)
请注意,唐氏所记杨深秀被捕入狱原因,完全是由于他参预新政,丝毫未提康梁所说“独抗疏诘问皇上被废之故,援引大义,切陈国难,请西后撤帘归政,遂就缚”(注:梁启超:《维新政变记,杨深秀传》。)与拙作《杨深秀考论》相符。日记所述刘光第性格行事,亦与实际相合,盖刘与唐氏均在刑部任职也。
八月十五日,晴,风。赴城内外各处拜节,旋至薛家湾鄞县馆谒肖庵先生不遇,……昨日邸抄上谕,张荫桓革职发往新疆,徐致靖永远监禁。本日赵展如侍郎入署,点解将张荫桓送交兵部发配,同日谕旨宣示正法诸臣罪状,有谋为不轨,图围颐和园,劫持两宫之语,询为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矣。先事发觉,天下之幸矣。(注:《留庵日钞》,第1册,第120页。)
八月十九日,晴。入署晤王兰亭,渠谈及康逆事甚详。据云:伊等死党,已定议召外兵,劫大内。林逆意在召董星五军门,而谭逆则欲合袁慰廷廉访。时袁方来都陛见,后谭逆突于夜半叩袁寓门求见。袁延之入,匆匆寒暄毕,卒然问袁曰:君欲得侍郎否?袁大惊异。谭乃告以所谋,并云已得旨矣。袁唯唯。谭去次日,即请训召见,时上令其带新练军三千人入京。袁退下,始信谭语非妄。当日诏袁开臬司缺,以侍郎候补。先是,都下有知其逆谋者,喧传已旬余矣。众咸弗信。唯夏间文侍御悌参杨深秀折内,有杨深秀到臣宅内二次,向臣丞称康有为之贤,且有臣所不敢出口之言。隐约其词,当即指此,故士大夫中亦间有虑及者。自袁召对后,事益急,谋益泄,袁侍郎急驱出都,由轮车抵津,谒长白相公(国),具陈逆状。适江苏杨星伯崇伊侍御亦赴津告变,长白相国微服旋都,直至颐和园求入见。皇太后立召入,碰头泣诉。太后具悉伊等奸状,立传内侍启銮,还西苑,时初四日。既驻跸,太后尚迟回未发,佯语上以初六日卯刻还颐和园。至是日,上御中和殿看版毕,至西苑送皇太后还颐和园毕,回宫办事,召见军机。及上至,太后已御便殿,召见军机大臣,拟旨示上。上始知为康有为等所惑,力请皇太后训政,密诏拿康有为。初八日,上率王大臣朝贺礼成,即诏拿问张荫桓等六人,锁交刑部治罪。时长白相国二次入都,密奏宜速行正法,恐逆党众多,事有中变,贻祸不测,于是有十三日之事。连日密旨严拿王照不获,伊已畏罪潜逃,仍著提督顺天府五城,一体严拿,并著顺天府尹饬宁河县查抄家产,李苾园大宗伯自行检举,并请治罪,上谕革职发往新疆。(注:《留庵日钞》,第1册,第122-123页。)〔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唐氏此日所记,前半部分,与坊间笔记所云大同小异,后半部分则是至关重要的记载,细审此日所记,可得出许多重要的线索。
其一,唐氏所记谭嗣同在“召外兵,劫大内”活动中,立场鲜明,与毕永年《诡谋直纪》所述,谭在此问题上被动消极的立场迥然不同。此记更符合谭嗣同的性格。谭嗣同是心甘情愿地去铤而走险,而不是被康有为兄弟逼迫而为之。而且,《诡谋直纪》在记述谭氏八月初三日夜访袁世凯时,记载毕永年次日问谭氏:“昨夜尽以密谋告袁乎?”谭曰“康尽言之矣。”(注: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1990年版,第28页。)似乎谭夜访法华寺时,康有为亦在场。《诡谋直纪》在最关键的环节上,出现差错,此种记载实在令人费解。故对照唐氏所记,似乎应对《诡谋直纪》的形成过程及原因,再予探讨。
其二,杨深秀所以被清廷初九日抓捕,十三日被杀头,真正原因是由于他在变法中立场激进,主张包围颐和园制服太后,唐氏称“先是,都下有知其逆谋者。喧传已旬余矣。众咸弗信,唯夏间文侍御悌参杨深秀折内有杨深秀到臣宅内二次,向臣备称康有为之贤,且有臣所不敢出口之言,隐约其词,当即指此,故士大夫中亦间有虑及者。自袁召对后,事益急,谋益泄”,显然,清廷相信文悌之血口喷人,认为杨深秀涉嫌组织参与了“召外兵,劫大内”的密谋,故而予以严惩,并非如黄彰健所考“杨深秀的被捕与他八月初五日上折请雇工三百人挖圆明园金窖、想调袁军入京有关”。(注: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研院1970年版,第504页。)
其三,关于袁世凯告密的时间与地点,比一般记载更可信。
唐氏指出,谭嗣同初三日夜访之后,“事益急,谋益泄”,袁世凯感到事态严重,于是立即启程,赴津告变,长白相国荣禄亦立即“微服旋都”,到颐和园向慈禧泣诉。慈禧则立传内侍,驾还西苑,这些行动一环紧叩一环,都发生在初三晚到初四日的一天之内,更符合事态之发展的逻辑。因为对袁世凯来说,当他获悉维新派之密谋后,应尽快向其主子荣禄告密,方显示出他的真诚。至于为什么初四日慈禧、荣禄得到告密消息不抓康有为与谭嗣同,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慈禧他们认为有能力控制局势,已布好天罗地网,要静观维新派的表演,俟光绪皇帝召见伊藤博文,然后再采取行动。二是与袁世凯告密之内容、告密的方式以及告密的程度亦不无关系。日本档案中有大隈重信外务大臣致在外驻扎各公使,通报清国戊戌政变事情的文件(机密送递)云:
明治三十一年十月十三号发
关于这次清国政变的情况,驻清国林临时代理公使等呈送电报之内容,已于上月三十号大概申述了。关于此事件,据事发后到今天从该代理公使发来的几个电报的概要来看:直至受到惩罚时,康有为一派付诸实行的改革都是小的。不过,他们最初是下定决心要乘机实行大的改革的,袁世凯看似也参与其计划。他在北京短期逗留,其间屡次谒见皇帝,并且官升至侍郎。多半是他给西大后和当时的直隶总督荣禄泄露秘密的。皇帝和康一派的意图未必明确,但无疑被认为有损满洲派的利益。该月十九号西太后突然回到北京,且直隶总督也于当日乔装打扮进宫。他们已决定彻底打击改革派。伊藤侯爵谒见的次日才确证此事。结果,康有为之弟弟康广仁、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及刘光第等康有为一派六个人被逮捕而处以死刑。只是张荫桓之罪名与其他人不同,得“居心巧诈,行纵诡秘”的罪名而被处以流刑新疆(大概是伊犁)。就这次政变的各国之意向而言,除我和英国公使尝试拯救张荫桓,其他尚不明白。(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589号。译者大桥义武。)
又据日本《朝日新闻》明治31年10月7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登载来自北京的消息称: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後,九月十九日(八月初四日)西太后突然从万寿山离宫返回北京,直隶总督荣禄微服到京,谒见西太后,决定对新党加大打击。
上述日本方面的材料,都说明八月初四日这一天慈禧突然提前返回大内,这一行动的导火线,则应是谭嗣同八月初三日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对后党采取行动所引起的。因此,不能因为谭嗣同未被抓,以及对其他几位章京亦未采取行动,便轻率得出戊戌政变的爆发,并非由袁世凯告密的结论。因为林权助由於对戊戌政变观察深入,被当时驻京外国人称为最了解该事变的人。他推断事件的起因,是由袁氏之告密而起。这种论断为后来袁世凯被荣禄信任所证实。
其四,唐氏日记对八月初五、初六日慈禧活动的记载甚为准确,颇中款要。
直到八十年代,国内的近代史教科书叙述政变事,均记袁世凯八月初五日被光绪召见后,才回津告密。慈禧则于初六日还宫,采取行动。
大约是1980年末,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见到的光绪朝《起居注册》记载却是慈禧于八月初四日卯刻还宫。于是,我对当时流行的戊戌政变的说法顿生怀疑。并随即与戴逸老师讨论甚久,他鼓励我写了《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并亲自转送给黎澍同志,希望刊载于《历史研究》,几经周折,还是退稿。据说是证据仍不充分云云。又过了一两年后,才于《历史档案》刊出。而当时黄彰健院士之《戊戌变法史研究》尚未见到也。
由於在《起居注册》发现了所记八月初四还宫一事,我用了许多笔墨,论证戊戌政变发生在八月初四日。现在,用唐氏日记再审视政变之过程,我郑重声明,放弃八月初四日政变说,而改为初六日。因为慈禧虽然于八月初四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但不足以说就发生了政变。光绪皇帝初五日还正常召见了伊藤博文,康有为亦可自由自在地离开京师。(注: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经过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正修正》,《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5、6期。)唐氏初六日的“奉口诏严拿”,也说明政变是慈禧在初六日早上仓促发动的。
当然,唐氏此日所记,是与刑部同僚交谈戊戌政变情形的谈话记录。时在八月十九日,即六君子被杀后的第六天,刑部官员对政变内幕的探测,并非政变的原始档案,故而亦有其失误处。诸如,袁世凯请训回津的日期应为八月初五日,并非唐氏所记之初四日;至于光绪召见时要袁氏:“带新练军三千人入京”,似不足信,因为它与光绪赐杨锐之密诏所记相抵触。因此,即使唐氏有此记载,我还是不敢相信光绪皇帝有此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