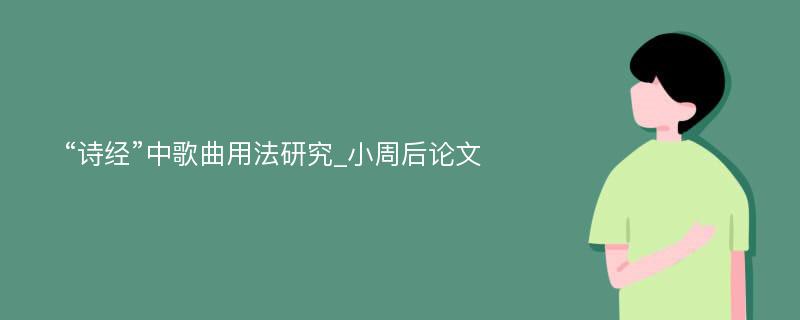
厲鶚詩歌用典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厲鶚詩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之說首開詩歌重學之源,引起後世無數詩人的隔代呼應,作爲一名學者型詩人的厲鶚對此也深表認同。厲鶚(1692-1752)是清代雍乾時期的詩詞創作大家,杭世駿評價其詩歌時曾謂:“太鴻之詩……求之近代,罕有倫比。”①又云:“樊榭稱詩,介江淮以南,無敢抗手者,匪以其才,蓋其淵旨粹思,骨堅而神邈,希風者並氣力學之,終莫得其似。”② 即使不考慮杭堇浦作爲樊榭摯友的溢美之詞,厲鶚詩歌以其獨特的藝術成就而倍受時人的贊譽與推崇,並在清代中期詩壇上享有極高的聲譽,亦是不争的事實。而建立在“以學爲詩”理論基礎上的詩歌典故運用,則是樊榭詩歌創作藝術手法最爲重要的特徵之一。也有研究者注意到此點並撰文論述,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張仲謀先生《清代文化與浙派詩》一書中的觀點,認爲厲鶚之詩用典“生新奇僻,多前人未用之典”,“集中典故千百,出于宋人者太半”③,所論頗有見地。但就厲鶚詩歌用典的理論依據、用典的方法和原因、後人對樊榭詩歌用典評價等問題,目前尚鮮有人論及,本文擬對此加以探討。 一、厲鶚詩歌用典的理論基礎與創作表現 厲鶚是一個對理論闡釋不太擅長也不甚感興趣的詩人,他没有系統的詩學著作,這種情况雖然與文學史上多數長于創作的詩人相同,但在理論著作蔚爲大觀的清代,還是比較少見的。然而作爲一個“生平詩歌逾萬首”④的詩人,他在詩歌創作實踐當中所獲得的寶貴經驗和獨到見解,仍然通過其詩文作品和所作文集序跋的隻言片語中表現出來。在厲鶚詩歌創作的理論體系中,對學問的重視居于核心地位。在爲友人徐以泰作的《緑杉野屋集序》中,他明確提出了“以學爲詩”的詩學觀點: 少陵之自述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詩至少陵止矣,而其得力處,乃在讀萬卷書。且讀而能破致之,蓋即陸天隨所云“淩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异,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者。前後作者,若出一揆。故有讀書而不能詩,未有能詩而不讀書……夫煔,屋材也;書,詩材也。屋材富,而杗廇桴桷,施之無所不宜;詩材富,而意以爲匠,神以爲斤,則大篇短章均擅其勝。⑤ 這段文字首先追溯了杜甫的創作成就,爲“以學爲詩”的詩學思想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的雙重依據,接著便闡釋了自己對于“詩”與“學”關係的辯證看法。厲鶚肯定了源自書本的“學問”是作詩的基礎,他認爲有了學識的積累,不一定能够作詩,而如果缺乏學養,就一定無法作詩。只有具備學養的基礎,復參之以獨特的運思,纔能成就佳構。 細繹厲鶚此文之意,又可見出在“以學爲詩”的觀念上,他與杜甫的側重點各有不同。老杜所言“讀書破萬卷”,更多强調的是從書本中汲取營養,最終在藝術上達到渾然天成、“無一字無來處”卻又毫無綴合痕迹的審美風貌。而厲鶚所言則更偏重從書本中提煉作詩材料,如同築屋所需木材,將“書”作爲構建詩歌的基石。這一理論所倡導的最高境界是使詩作達到“清恬粹雅,吐自胸臆,而群籍之精華,經緯其中”⑥的狀態,並且,只要詩歌能够有所創新,至于是否讓人看出詩材之所自,倒在其次。 “以學爲詩”的理論主張在厲鶚自己的詩歌創作中從兩個方面體現出來:一是將書齋生活與相關文化活動作爲固定的抒寫對象,這屬于以學爲詩的表象。二是真正將“學問”運用到詩歌語彙、詩歌句子及意境的創造當中,這是以學爲詩的核心。而後者在樊榭詩中最爲直接、突出的表現,就是典故的大量運用。 所謂用典,最通行的概念,是指詩文中所引用的有來歷的故事及相關語詞、佳句。厲鶚讀書博雜,知識淵博,自言“平生嗜讀書”(續集卷七《大圜上人惠紫菜補陀茶,用山谷集中食筍韻》)⑦,讀書是他除了游賞山水之外的另一項重要愛好。他還標榜說“人生至樂無如讀,莊叟曾云學爲福”(續集卷八《題友人北墅耕讀圖》),“疏梅半樹展書卷,剩欲此中尋好懷”(卷一《歲暮答王既咸》)。友人全祖望謂厲鶚“于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于詩,故其詩多有异聞軼事,爲人所不及知”。⑧王昶也云:“徵君性情孤峭,義不苟合,讀書搜奇愛博,鈎新摘异,尤熟于宋元以來叢書稗說。”⑨正是由于知識儲備的豐富,厲鶚詩歌用典能够信手拈來,且典故使用紛繁密集,一首詩中數典連用的情况屢見不鮮。如《題禹尚基畫白桃花》(卷八): 樂府争傳渡口歌,淡妝奈此折枝何。冶春合就雲爲夢,笑月應憐玉作渦。盧女後時鉛粉薄,劉郎重到鬢絲多。亭亭付與徐黄手,輕著宮衣襯碧羅。 禹尚基即禹之鼎(1647-1716),清初畫家,擅畫肖像、花鳥。在厲鶚這首題畫詩中,詩歌首句中運用了東晋王獻之爲愛妾桃葉作《桃葉歌》之典。⑩次聯中用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所載胡銓爲歌姬梨倩題“旁有梨頰生微渦”詩句之典。頸聯當中,首先使用了《北堂書鈔》所記北齊盧士深妻以桃花和雪,爲兒洗面之典,後用唐代詩人劉禹錫重游玄都觀,見桃花而感慨人生之典。以上六句中,没有一處出現實寫的“桃花”二字,但又處處暗含著桃花的影子。尾聯中的“徐黄”,特指五代畫家徐熙與黄筌,兩人均善畫花鳥,因得以並稱。詩歌至結尾處,纔算點明本詩題畫的主旨。幾乎無一句不用典,但是卻因此而避免了前人對這幅畫卷反復吟咏而趨于圓熟與模式化的表述,同時由于對相關典故選擇與運用的巧妙,全詩用典毫無堆垛之弊,甚至一向對厲鶚詩作要求苛刻的翁方綱,評論此詩時,也不禁贊道“劉郎句大雅”。(11) 可見,密集的典故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使樊榭詩作情思愈發幽隱,意藴也更加豐富,這成爲其詩歌創作的一大特點。再舉厲鶚《題周兼南唐小周后寫真四首》(卷五)爲例說明此問題: (其一)未合雙鬟最小身,秦淮明月白門春。漢宮莫話昭陽事,更有人間返臥人。 (其二)已識君王尚待年,新詞側艷外邊傳。銷魂貌出提鞋樣,壓倒南朝步步蓮。 (其三)群花偃亞小亭孤,卯酒朝酣倦欲扶。可記畫堂南畔見,背人無語問流珠。 (其四)命婦隨朝掩泪光,虛聞龍袞紀興亡。畫師自有春風筆,不寫傷心入汴梁。(自注:龍袞《江南野史》今所傳不全載,小周后事見王銍《默記》) 小周后是南唐後主李煜的皇后,此詩所咏小周后寫真圖,爲清初畫家周兼的名作。張庚《國朝畫徵録》載:“周兼,海寧人,工畫士女,衣紋清古,設色淡雅,布置俱有來歷,有識者賞之。有南唐小周后圖,意致俱佳。”(12)無獨有偶,在厲鶚稍前,浙省著名詩人查慎行亦曾題此畫,有同題之作《題周兼畫南唐小周后寫真六首》傳世(13),正可與厲鶚此詩進行比較,以見二人詩作之异同。查作如下: (其一)人間姊妹工相妒,遺恨茫茫豈有涯。怊悵瑤光梅信晚,一枝潜進未開花。 (其二)湘裙如水不抬風,鳳咮携來倒挂紅。色色丹青無著處,泥金一縷在雙弓。 (其三)月暗花明霧氣多,盈盈羅襪步淩波。外間誰管深宮事,偷唱新聲子夜歌。 (其四)不須更減一分肌,周昉繇來善貌肥。如此丰姿如此畫,當初猶道未勝衣。 (其五)開寶初元議禮遲,待年承寵已多時。在廷只有韓熙載,曾托元和諷諭詩。 (其六)垂鬟分綹發初長,想是南朝時世妝。指與俗工從未識,可憐絶筆付周郎。 (自注:時兼惜已下世) 從總體上看,兩人詩作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典故的使用。查慎行素以白描著稱詩壇,他曾說過“詩成亦用白描法,免叫人譏獺祭魚”(14),明確反對在詩中過多運用典故。他的這組詩作,除了對畫中景物及人物肖像的直接鋪陳,主要對小周后相關史事加以鋪叙。小周后的故事,以馬令和陸游兩種《南唐書》所載最爲詳細:小周后爲昭惠後娥皇之妹,娥皇病時,爲李煜招入宮中。待娥皇殁,立爲皇后,開寶元年,後主命人考古今禮儀,立小周后爲繼室,被寵過于大周后娥皇。查詩中的史事完全本于此二書。馬令《南唐書》中還載小周后“至納後,乃成禮而已。翌日大燕群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譴”(15),這一細節,亦被查慎行寫入詩中,可見其詩作對故事叙述的完整與平實。 相較而言,厲鶚這組詩作筆調則完全游離于史事之外,每一首都用不同的典故襯托詩意,使詩意呈現出極强的跳躍性,與查詩風貌全不相同。《其一》“漢宮莫話昭陽事”句以漢代趙飛燕姐妹喻周氏姐妹。在《其二》“壓倒南朝步步蓮”句中,用《南史》東昏侯寵愛潘妃之典,以示李煜對小周后的寵愛。《其三》“可記畫堂南畔見,背人無語問流珠”句中點化李後主之詞(16),並又融入陸游《南唐書》所載宮人流珠事:“又有宮人流珠者,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17)《其四》中則使用了南宋王銍《默記》中有關小周后的記載:“龍袞《江南録》有一本删潤,稍有倫貫者云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駡後主,聲聞于外,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18) 厲鶚整首詩中的典故運用給人以目不暇接之感,但本意並未遠離畫中之事,可以看出詩人創作時煞費苦心。但是,他的這種寫作方法也招致了論者的不滿,翁方綱評點樊榭此詩就云“此則何苦如此乎?是必自以爲博聞乎?”並批評道:“查初白亦有此題,若將並讀,則樊榭竟縮小一圍矣。”(19)其實,兩種不同的創作方法,均源自于兩人不同的創作理念,藝術上本無高下之分。翁方綱批評厲鶚,主要嫌其詩用典過多,致使詩意支離,不如查詩境界完整闊大。但反之,亦可以說厲鶚憑藉用典,使詩歌在表達效果上化直爲曲、易近成迂,詩歌的內涵更加悠遠豐富,打破了查慎行詩歌平鋪直叙的板滯。這正如《蔡寬夫詩話》所載:“荆公嘗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藉事以相發明,情態畢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20) 實際上,“以學爲詩”最初是以一種文學現象出現的,隨著創作者們對“學”與“詩”的關係越發重視,也不斷的引發相關理論探討,逐漸形成兩種對立統一的評價觀念。一種如黄庭堅謂“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爾”。(21)南宋樓鑰亦指出:“詩之衆體,惟大篇爲難,非積學不可爲,而又非積學所能到。必其胸中浩浩,包括千載,筆力宏放,問見層出,如淮陰用兵,多多益善。變化舒卷,不可端倪,而後爲不可及。”(22)另一種對以學爲詩持否定意見,代表者是南宋嚴羽《滄浪詩話》對本朝人“資書以爲詩”的批判,認爲“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23)嚴羽强調詩與學的界限,乃爲了突出詩歌的特殊審美價值。關于這一問題,厲鶚顯然贊同的是前者。他主張以學問提高詩人的素養,同時要求將學問融入詩作當中。經過學問浸潤後的詩心,創作出的詩歌就不會流于膚淺。基于此點,厲鶚在詩歌中大量使用典故。可以說在整個清代詩壇中,他都能被視爲是最喜愛、並且擅長在詩中用典的詩人之一。 二、厲鶚詩歌用典的方法與原因 清人重經學,清代詩人所謂的“學”,大都以“經史”爲根坻。朱彝尊說:“凡學詩文,鬚根本經史,方能深入古人竅奥。”(24)又云:“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25)沈德潜以“格調”論詩,亦認爲詩學淵源于經學。翁方綱更明確指出應把“通經學古”作爲詩歌創作的根本和品評詩篇的標準。而厲鶚出身貧賤,身處江湖,遠離主流意識形態,他作詩從未刻意强調以正統經學爲根坻。因此,厲鶚所言之“書”的內涵遠比其他人更加寬泛,在學問的範圍上由“經史百家”擴大到“群籍”。由道光年間董兆熊爲樊榭詩歌所作的箋注來看,佛典、說部、山經、海志都在他用典涉獵的範圍之內,這亦是厲鶚用典的獨到之處。 在浩如烟海的歷代典籍中,厲鶚對宋代典籍與故事具有濃厚的興趣。如今人趙杏根《論浙派詩人厲鶚》一文所揭:“他用典也是力求生新,好用常人不大用的典故,特別是宋及宋以後典故。許多典故本于《墨莊漫録》、《曲淆舊聞》、《鐵圍山叢談》、《咸淳臨安志》等宋人筆記、方志和其他著述。”(26)張仲謀也曾在其《清代文化與浙派詩》中論及這個問題。雖然厲鶚詩中所用宋典並非如張仲謀所說“出于宋人者太半”那樣絶對,但是大量宋代典故的運用,不能不說是厲鶚詩歌的一個顯著特點。 以下就以宋典爲代表,一窺厲鶚詩歌用典的方法與原因。《樊榭山房集》中使用宋代典故的方法可以分爲三種情况。 其一,使用語典。其方法是直接將宋人著述中的語詞置入自己的詩作。如“漸有放生團社約,魚苗如蟻水初肥”(卷一《人日游南湖慧雲寺七首》其七),葉夢得《避暑録話》載:“(浙東)土人率以陂塘養魚,乘春魚初生時取種于江外,長不過半寸,以木桶置水中,細切草爲食,如食蠶,謂之魚苗。”又如“蛤潮傷楚稻,魚淰賤吳羹”(卷四《秋半苦雨》),“蛤潮”一詞,乃點化姚寬《西溪叢語》所云“海上人云,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續集卷一《趙意林添構隱幾山樓,爲三層,賦詩紀事,屬予次韻》詩中“俯檻恣窺臨,拔地獻蛾緑”句,以“蛾緑”指山,語出錢易《南部新書》:“青黛螺,光明鮮翠,每一斛直十金,當時名之曰‘蛾緑’。”續集卷一《由繇金家堰入皋亭西麓至崇先寺,寺爲宋顯仁韋太后功德院》“春似合江堪載酒,朅來古寺記迎鑾”句,自注謂“太后北歸,曹勛作《迎鑾七賦》”。“半醉半醒行樂客,不晴不雨養花天”(續集卷四《曉行蘇隄作二首》),“養花天”一詞,脫胎于《全芳備祖》中所載“牡丹時,最喜陰晴相半,謂之‘養花天’”之語。厲鶚將這些筆記、雜著中的詞彙作爲語典運用到自己的創作當中,不僅具有以故爲新的作用,對擴大詩歌語彙也不無裨益。 其二,使用事典。將宋人的故事加以抽繹,濃縮入自己的詩句。如《樊榭山房集》卷一《城西讀書雜興二首》中“世路淹回魚上竹,歲華飄忽鳥驚弦”句,前半句中使用了歐陽修《歸田録》中所載梅堯臣事:“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館職。及授一勅修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對曰:‘君之仕宦,亦何异鯰魚緣竹竿乎?’”卷二《東園》詩寫道:“麂眼籬邊豆葉零,機絲一半掩荒扃。舊游慣識東門菜,秋露秋風十里青。”詩下自注云:“宋時東門絶無民居,彌望皆菜圃,故土人有東門菜之諺,見周必大《二老堂雜誌》,至今俗猶然也。”續集卷三《西林過月滿精舍》“學多先識字,年長欲依僧”句中,又化用了《邵氏聞見後録》所載王安石之事:“王荆公初執政,對客悵然曰:‘老欲依僧耳。’客曰:‘急則抱佛。’公微笑曰:‘投老欲依僧,古人全句。’客曰:‘急則抱佛脚,亦全俗語也,然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爲的對邪。’公遂大笑。” 厲鶚在創作中使用這些宋代典故,並非生搬硬套的牽引入詩,而是結合詩歌所描寫的情境或者一己之心境,將典故點化于無形當中,看似無迹可尋,實則暗藏玄機,增加了詩句的內涵。 其三,化用宋人詩句。毋庸置疑,厲鶚在詩中亦常化用唐人詩句,也喜歡化用宋代大家如蘇軾、黄庭堅、陸游等人的詩句。除此之外,宋代那些爲一般人不太注意的小家詩作中的佳句,也爲厲鶚所關注。 如卷一《同南畹二兄游河渚,飲沈晴川書齋》一詩中“峰陰含古色,梅凍得清愁”句,化用張良臣《過西溪》“梅花到得吹成雪,盡是清愁不是香”之語。《吳興歸舟作》“自牽賤事匆匆去,不爲蘋花住一年”(卷一),化用姚鏞《霅溪》詩“幾回罷釣思歸去,直爲蘋花住一年”。又如卷六《正月十一日,同尺鳧、功千泛舟湖上,期敬身不至二首》其二有句:“水邊歌鼓元宵近,詩裏光陰白髮多。”上句點化宋末方回《涌金城望次韻》“舊隄燈火元宵近”,下句化用吳處厚《青箱雜記》中所録張士遜詩“青雲歧路游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再如卷二《題陳楞山秋林讀書圖》“西風日日翻書葉,吹得數峰如許青”,則將宋代詩僧惠洪《乾上人會余長沙》中的“兀坐思歸不舉頭,窗風爲我翻書葉”,與唐代詩人錢起的名句“江上數峰青”連綴一處,接縫無痕,可謂“融化剪裁,運古語若己出,毫無費力之痕”。(27)化用前人詩句的例子在《樊榭山房集》中並不多見,然而經過他的重新加工,卻使舊作和新句均情韻焕發,亦構成其喜用宋典的一個主要方式。 由以上三個方面,可以見出厲鶚對宋代典故的喜愛與熟悉,故沈德潜說他“學問淹博,尤熟兩宋典實,人無敢難者”。(28)《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亦謂其“生平博洽群書,尤熟于宋事”。(29)而考察厲鶚究心宋典的原因,似又可從以下諸端找到答案: 第一,側面原因。杭州本爲南宋故都,厲鶚生長于此,終老于斯,對此間的宋代遺迹與故事至爲熟悉。全祖望爲厲鶚所著《湖船録》一書作序稱:“西湖爲唐宋以來帝王都邑,一舉目皆故迹。”(30)言下之意是人們在此間生活,舉目投足均會聯想起宋代的軼事掌故與風物人情。用這句話來解釋厲鶚詩中多寫宋代故事的原由也同樣是合適的。僅從《樊榭山房集》中的詩歌題目來看,與宋代相關之詩就不在少數,如《寶蓮山是韓平原故宅》(卷一)、《八月十八日同丁敬身游龍華寺,尋石壁上宋人題名登慈雲嶺觀永壽院宋仁宗佛牙讃吳越摩崖篆字》(卷五)、《同授衣、廉風游建隆寺,用沈傅師游道林岳麓寺韻》(續集卷三),詩歌題下自注:“在揚州城北。宋太祖征李重進駐蹕于此,勅建爲寺。”這些詩作涉及到的地點,都是厲鶚親身游歷之所,詩歌的內容,自然也要涉及到宋代的相關人事。 第二,主要原因。喜用宋典與厲鶚自身的知識儲備密切相關。樊榭一生留意鄉邦文獻,其著述多與宋代相關,從早年寫作《南宋雜事詩》起,即閱讀並積累了大量宋代史料。他四十歲時,又曾被聘修《浙江省志》與《西湖志》,必然也會接觸相關典籍。更重要的是,厲鶚還曾主持編纂《宋詩紀事》,搜羅宋代詩作,徵引書目多達一千餘種。此書從厲鶚三十四歲開始編纂,五十五歲方始竣工,基本貫穿了他一生詩歌創作的黄金階段,這些經歷對樊榭詩歌典故運用的影響是持續而直接的。 第三,主觀原因。即厲鶚本人出于對詩歌創作創新性的考慮。清人蔣士銓曾有一句衆人皆知的名言:“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爲。”而生于宋、元、明之後的清人,這種焦慮感則應當更加强烈,與之相應,他們在詩歌創作中要求創新的願望也越發强烈。厲鶚亦相當重視詩歌“自鑄偉詞”的創新性,蔣德《孟晋齋詩集序》嘗載:“太鴻之論詩曰:辭必未經人道而適得情景之真,斯爲難耳。”(31)厲鶚一生游踪不廣,識見有限,所以他更願意從詩歌內在技巧層面用功,從而達到創新的目的。在詩中頻繁運用典故,特別是使用事典和語典,成爲他作詩“務去陳言”行之有效的手段。 事實上,即使就典故運用技巧來看,前人留給清人的開拓空間也已經异常狹小了。因此,厲鶚纔于經、史之外廣泛采摭典源,且多用宋代及宋以後的典故,以此豐富詩歌創作的語料,力避熟易,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搜奇抉險,往往有得意句”(32),使其詩作具有出人意料的生新風貌。以下還以宋典爲例,來看厲鶚詩歌用典給創作帶來的創新之處: 天柱峰頭見晴雪,瑤壇玉洞暗相連。石林夙具看山癖,也復知宮三十年。(卷一《西溪月夜懷大滌山二首》其一) 此詩詩下自注云:“葉石林提舉洞霄宮,嘗曰:‘吾知宮三十年,未暇一至,孰謂吾愛山者乎?’”很明顯,厲鶚在詩中所要表達的是自己的愛山之癖,但是他卻並不直言,而是反用南宋葉夢得喜愛游山之典,寄托己意,造成詩意的曲折和生新。樊榭寫給友人施安的《施竹田移居》詩,也是一個運用典故達到創新的絶佳例證,此詩中有句云: 後洋街畔城西隅,客來愛君屋上烏。清凉居士跨驢處,君今寫入移居圖。妻孥絶類楊通老,板輿况有白髮扶。人生鄉里聊自足,勝比蓬轉無根株……(卷八) 詩中的“清凉居士”,典出自周密《齊東野語》所載:“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絶口不言兵,自號‘清凉居士’。時乘小驢,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淡然若未有權位者。”“楊通老”之典,乃用劉克莊《楊通老移家圖跋》:“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髫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貓,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帛槌之屬又繼之。處士帽席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坐母前,持棰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服用之具,極天下之寒酸襤縷,然猶蓄二琴,手不釋卷。”這兩個典故的使用,將友人安貧樂道的瀟灑情態簡潔而恰切的展現了出來,又具有不落俗套的新奇感。 固然,詩歌中那些耳熟能詳的慣用典故,具有恒久之情愫。而對那些尚未完全進入到詩人們創作視野的典源,如果使用得當,在詩歌中往往也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厲鶚在創作中敢于去開發新的語言材料,與其深厚的學殖修養密不可分。這不僅擴大了他詩歌創作的藝術張力和語言範圍,也進一步豐富充實了古典詩歌的語彙。 三、厲鶚詩歌用典批判 由于厲鶚在詩壇所具有的影響力,其大量用典的創作現實,在清代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與褒貶不一的評價,構成了清代詩歌發展史中一道別致的風景,值得給予考察。 首先對樊榭詩歌用典藝術提出批評的是袁枚:“樊榭短于七古,凡集中此體,數典而已,索索寡真氣。”(33)不僅是“七古”,袁枚從整體上評價厲鶚詩歌用典時亦表現得不屑一顧: 吾鄉詩有浙派,好用替代字,蓋始于宋人而成于厲樊榭。宋人如“水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輈”,不過一蟹一鷓鴣耳。“歲暮蒼官能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含風鴨緑鱗鱗起,弄日鵝黄裊裊垂”,不過松、霜、水、柳四物而已。廋詞謎語,了無餘味。樊榭在揚州馬秋玉家所見說部書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有《庶物异名疏》、《清异録》二種,董竹枝云“偷將冷字騙商人”,責之是也。(34) 袁枚也非常强調讀書對于提高詩歌創作水準的重要意義,贊同“凡多讀書,爲詩家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35)的觀點。然而在創作實踐中,他卻反對“填書塞典,滿紙死氣”。(36)他還說過:“用典如請生客入座,必須探名問姓,令人生厭。”(37)他對厲鶚的批評,正基于兩人詩學觀之間的差异。晚清朱庭珍的《筱園詩話》中也有一段對于樊榭詩歌用典的微詞: 好用說部、叢書中瑣屑生僻典故。尤好使宋以後事,不惟采冷峭字面及掇拾,小有風趣,諧語入詩,即一切別名、小名、替代字、方音、土諺之類,無不倚爲詞料。意謂另開蹊徑,色澤新异,別致生趣,姿態並不猶人也。殊不知大方家數非不能用此種故實字樣,大方手筆非不能爲此種姿態風趣,乃不屑用,並不屑爲,不肯自貶氣格,自抑骨力,遁入此種冷徑別調耳。是小家賣弄狡獪伎倆,非名家之品也。(38) 朱庭珍論詩,主張詩歌的根坻在于“積理于經,養氣于史,煉識儲材于諸子百家”。(39)仍然是要以經史爲基礎,而稗乘小說、野史逸事,不符合“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詩學精神,亦不符合傳統詩教“温柔敦厚”的審美理想。由此,他也對厲鶚詩歌的用典方式提出批評。 袁枚和朱庭珍的出發點有所不同,但是卻都可以視爲對厲鶚用典批評意見的典型。尤其是袁枚,他在乾隆時期詩壇的影響較大,故此論一出,後人往往因襲其說,如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補編》亦云:“鶚詩喜用僻事,時人效之謂之浙派”。(40)甚至忽視了袁枚這段話之後還有“不知先生之詩,佳處全不在是”(41)的補充之語。前人對厲鶚用典特點的論述雖多,大都片言隻字,並没有舉出具體的例證。且很多觀點都有層層相因之弊,甚至有的論者,在未細讀樊榭詩作的基礎上就隨前人妄下定論,致使厲鶚好用生澀僻典的偏見被無限放大,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樊榭詩歌的誤解。 今人張仲謀先生在《清代文化與浙派詩》中對此論述較詳,他說:“其(厲鶚)取資淵救,不在《六經》、《四史》,而在野史筆記,間及于佛道典籍。二是多用宋人軼聞。”又說:“前人爲詩,往往藉助于類書,厲鶚之詩出,人始知《藝文類聚》、《册府元龜》等不足于用。厲鶚所用典故既出自己雜學旁搜得來,又經自己精心熔鑄麗出之,遂成一大‘絶活’,其詩亦因此而形成生新奥博的特色。”(42)爲了說明厲鶚用典生僻,他例舉了《南歸夜行趙北口同範希聲作》(卷三)、《二月三日同少穆、竹田諸君集湖上,題酒樓壁》(續集卷四)兩首詩分析其中的典情况。 《南歸夜行趙北口同範希聲作》詩中有“參差人語知异方,作事五角與六張”句,董兆熊注此句時引宋人馬永卿所著《懶真子》之語:“五角六張,此古話也。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張仲謀說:“五角六張,雖然《懶真子》稱之爲古語,然而用者甚少,一般工具書查不到。”(43)實際情况並非如此,“五角六張”是唐宋時期的一種習俗,唐代鄭棨《開天傳信記》中即載“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44)宋代王安石《清平樂》詞中亦有“丈夫運用堂堂,且莫五角六張,若有一卮芳酒,逍遙自在無妨”之句。這種習俗雖然到清代已經消逝,但還常作爲一個成語出現在詩文中。朱彝尊《閑情八首》中即有“五角六張看過了,何愁作事兩難諧”(45),查慎行《虎林與同年許莘埜話舊,時初自蜀歸四首》詩中,亦有“五角六張成底事,人間吉日是歸期”。(46)可見這並非時人少見之生僻典故。 《二月三日同少穆、竹田諸君集湖上題酒樓壁》中有“魚羹宋嫂猶遺俗”句。董兆熊注引宋人袁褧著《楓窗小牘》語:“舊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盤案,亦復擅名。若南遷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皆當行不數者。宋五嫂,余家蒼頭嫂也。”張著認爲:“至于‘魚羹宋嫂’之類地方掌故,也許只有參與編纂《西湖志》的厲鶚等少數人纔知道。然而竟不加自注,不知他只是寫了給他的朋友看呢,還是以爲他的讀者都應該看過《楓窗小牘》。”(47)這一論斷也有失準確。“魚羹宋嫂”之事,除《楓窗小牘》外,宋人筆記如《都城紀勝》等書中都有類似記載。對于生在杭州而又曾主編《宋詩紀事》的厲鶚而言,他對這一典故必然非常熟悉。但即使對于其他清代詩人來說,這一典故也不鮮見。如《敬業堂詩集》卷二十《與王方日》詩:“一燈相對話蒼凉,舊京風物吾猶記。宋嫂魚羮薛嫂羊,馬嘶門巷客將還。”甚至曾經批駁過厲鶚的蔣士銓和袁枚也分別在詩中運用過這個典故,蔣氏詩云:“宋嫂魚羹李嫂羊,御厨疊進至尊嘗。”(48)袁枚詩云:“轉愁此後真州過,宋嫂魚羮價益高。”(49)若說作爲浙人的查慎行與袁枚較熟悉杭郡故事,而蔣士銓則非江浙士人。同時,查慎行與袁枚作詩多不用典或只用熟典,喜用白描手法。所以,僅以此例證明厲鶚用典的生僻是缺乏說服力的。 針對時人的責難,詩壇也不乏有爲樊榭用典辯護開脫的聲音出現,如陳文述《書厲樊榭詩後》云:“古來詩人曹劉、陶謝、李杜、韓蘇數大家外,互有興替,獨樊榭以浙派著。迄今將及百年。後學遵守宗法,未之有改,顧或以生字僻典爲浙派,誚之者即以是爲口實。非知樊榭者也。”(50)晚清邱煒萲亦說:“後人因以浙派尊之,其近體清雅遒健,雄視一時。其古體間有僻典澀句,昔人嘗譏爲‘偷將冷字騙商人’者……樊榭遇之(馬曰琯、馬曰璐)正屬嘉賓賢主相得益彰,訾議者至謂冷字騙商人,亦太刻虐矣。”(51)所論較爲公允。 綜合以上諸家的觀點,客觀審視厲鶚詩歌,他的確有一些作品因用典生僻而過于新奇,不過這類作品在《樊榭山房集》中所占比例極少。比如卷八《同吳西林城東看花遇大風,戲爲長歌》詩中“今朝風氣花韝扇,莫使遲來花似霰”句,董兆熊注引《清异録》:“俗以開花風爲‘花韝扇’,潤花雨爲‘花沐浴’。”又如《是日春社晚歸坐雨寄諸君》“句無劉夜坐,興比薛春游”句(卷五),分別用馬令《南唐書》及范縝《東齋記事》中“劉夜坐”、“薛春游”這兩個人名,代指自己的詩情和游興。再如《沈石田合子會詞真迹次韻》中“平章風月秦淮風,小軸歸君篋衍中”(卷七),若無句下自注“秦淮伎有私印曰‘同風月平章事’,見《野獲編》。”一般人應該難以知道這些典故的出處。 昔者許尹爲任淵作《黄陳詩集注序》,評價黄庭堅詩歌時說:“其用事深密,雜以孺、佛、虞初、稗官之說,《隽永》、《鴻寶》之書,牢寵漁獵,取諸左右,後生晚學此秘未睹者,往往苦其難知。”(52)其中也涉及到生典與熟典的問題。爲前人常用之典,初創時不一定人人可懂,但是經過人們的代相沿用,漸漸就失去了初始的魅力和效果,甚至流于陳腐。而新的詩學資源的開發,並不是人人能够得以進行的,這需要自身的積累和一定的機緣。厲鶚詩中的用典情况,與此即有幾分相像。但敢于創新的創作方式,也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自己詩歌的接受群體,至少具有一般特殊知識儲備的群體,纔能够欣賞的了。今人葛兆光說:“典故作爲一種藝術符號,它的通暢與晦澀、平易與艱深,僅僅取决于作者與讀者的文化對應關係。”(53)厲鶚所與交游之人,多爲飽學之士,其詩集中用典生僻的作品,大多便作于和這些友人交往的場合,它們本身就有特殊的接受群體。 但大多數情况下,厲鶚詩中所用之典雖然爲他人少用,卻能够不露痕迹,自然貼切。如《北郭紀游四首·散花灘》中“當年張外史,此地有行窩。”(卷一)“行窩”一詞語出《宋史·邵雍傳》:“好事者別作屋如雍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又如《皋亭看桃花,舟中同孫瑤圃、右階作》“不逢漁子應迷路,喜有詞人共踏莎”句(卷七),用《能改齋漫録》中之典:“懷寧城上莎,猶是錢文僖公所植。公在鎮,每宴客,命廳籍分行剗襪步于莎上,傳唱踏莎行,一時勝事,至今稱之。”即使讀者不知到“行窩”、“踏莎”等典故的來歷,也並不妨礙詩歌的接受與閱讀。從這個層面来看,陸廷樞所云“厲樊榭之沉博,而其神理若專熟南宋事者,亦平日精詣所到,流露于不自知也”(54)的評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綜上所述,無論從理論基礎的宏觀角度考察,抑或從使用方法和發生原因的細節審視,典故運用都是厲鶚詩歌創作藝術技巧不可忽視的組成。正如文章第一部份中所言,從主觀上說,厲鶚也希望將“學”與“詩”完美統一在創作中。除了《緑杉野屋集序》和《汪積山遺集序》外,他在《查蓮坡蔗塘未定稿序》中還說過:“少陵所謂多師爲師,荆公所謂博觀約取,于體是辨。衆制既明,爐鞲自我,吸攬前修,獨造意匠,又輔于積卷之富,而清能靈解,即具其中。”(55)所以呈現在世人眼前的樊榭詩集,既有清雅幽隽、空靈淡遠的一面,也有不少作品呈現出較爲繁縟的風貌。空靈與學問,清空與質實,構成了厲鶚詩歌風格的兩極,並都達到了很高的造詣,故蔣德《孟晋齋詩集序》云:“太鴻之詩多清疏窈眇之思,其博奥足以副之,自諸子百家雜出于神林魁冢金石、可喜可异之事,能令讀者蕩心震目。”(56)鍾駿聲《養自然齋詩話》易謂“吾浙詩派,至樊榭而極盛,亦至樊榭而一變”。(57) 典故運用本是詩歌創作的一項重要藝術手法。在詩歌發展史上,不乏善于運用典故的大家,如杜甫、蘇軾、黄庭堅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厲鶚詩歌創作用典步前賢後塵,在他自己生活的時代,成爲清詩學問化的一個有力實踐者。同時,在即將到來乾嘉詩壇學問化興起的大趨勢之下,其詩歌用典從某種程度上說又能够得時代風氣之先,以致于其殁後不久,就出現了洪亮吉所謂“近來浙派入人深,樊榭家家欲鑄金”(58)的盛况,這也是厲鶚詩歌典故運用的另一個意義所在。 ①杭世駿:《詞科掌録》,《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一輯第1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475頁。 ②杭世駿:《符南竹傳》,《道古堂全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2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540頁。 ③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234頁。 ④杭世駿:《詞科掌録》,《四庫未收書輯刊》,475頁。 ⑤厲鶚:《綠杉野屋序》,《樊榭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42頁。 ⑥厲鶚:《汪積山遺集序》,《樊榭山房集》,747頁。 ⑦《樊榭山房集》,1558頁。按,本文中厲鶚詩作均引自此本,後文中引詩僅隨文標明卷數。 ⑧全祖望:《厲樊榭墓誌銘》,《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364頁。 ⑨王昶:《蒲褐山房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4頁。 ⑩按,標校本《樊榭山房集》收録道光年間董兆熊爲是集所作之注。本文中所論厲鶚詩歌中的典故,如非特別說明,均用董兆熊注,故文字或與董氏所引原著有差异。 (11)翁方綱評點:《樊榭山房集》,乾隆間武林綉墨齋本刻本。 (12)張庚:《國朝畫徵録》,《續修四庫全書》第1067冊,126頁。 (13)查慎行:《敬業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39~640頁。 (14)查慎行:《東木與楚望疊魚字凡七章,連篇傳示,再拈二首以答來意》,《敬業堂詩集》,1628頁。 (15)馬令:《馬氏南唐書》,《四部叢刊續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 (16)李煜《菩薩蠻》詞:“花明月暗籠輕霧,今朝好向郎邊去,剗襪出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南唐二主詞校訂》,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40頁。 (17)陸游:《陸氏南唐書》,《四部叢刊續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 (18)王銍:《默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44頁。 (19)翁方綱評點:《樊榭山房集》,武林綉墨齋刻本。 (20)蔡啓:《蔡寬夫詩話》,《宋詩話輯佚》,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419頁。 (21)黃庭堅:《論作詩文》,《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1627頁。 (22)樓鑰:《雪巢詩集序》,《攻愧集》,《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723頁。 (23)嚴羽:《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26頁。 (24)陳廷敬:《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朱公彝尊墓誌銘》,《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1269頁。 (25)朱彝尊:《與李武曾論文書》,《曝書亭集》,上海:世界書局,1937年,393頁。 (26)趙杏根:《論浙派詩人厲鶚》,《文學遺產》2000年第3期。 (27)朱庭珍:《筱園詩話》,《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333頁。 (28)沈德潜:《清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969頁。 (29)《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2353頁。 (30)全祖望:《厲太鴻〈湖船録〉序》,《全祖望集匯校集注》,1244頁。 (31)蔣德:《孟晋齋詩集序》,《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8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4頁。 (32)厲鶚:《盤西紀游集序》,《樊榭山房集》,751頁。 (33)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502頁。 (34)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320頁。 (35)袁枚:《隨園詩話補遺》,565頁。 (36)同上,626頁。 (37)袁枚:《隨園詩話》,235頁。 (38)朱庭珍:《筱園詩話》,《清詩話續編》,2367~2368頁。 (39)同上,2351頁。 (40)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補編》,《續修四庫全書》第539冊,279頁。 (41)袁枚:《隨園詩話》,320頁。 (42)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234~235頁。 (43)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236頁。 (44)鄭棨:《開天傳信記》,《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59頁。 (45)朱彝尊:《曝書亭集》,20頁。 (46)查慎行:《敬業堂詩集》,1342頁。 (47)《清代文化與浙派詩》,236頁。 (48)蔣士銓:《湖上雜咏》,《忠雅堂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11頁。 (49)袁枚:《九月七日以真州蕭美人點心饋麗川中丞,蒙以詩謝,敬答一章》,《小倉房山詩文集》,960頁。 (50)陳僅:《頤道堂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06册,52頁。 (51)邱煒萲:《五百石洞天揮麈》,《續修四庫全書》第1708册,180頁。 (52)黃庭堅:《山谷詩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5頁。 (53)葛兆光:《漢字的魔方》,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134頁。 (54)陸廷樞:《復初齋詩集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454冊,361頁。 (55)《樊榭山房集》,735頁。 (56)蔣德:《孟晋齋詩集序》,《清代詩文集彙編》,4頁。 (57)鍾駿聲:《養自然齋詩話》,轉引自《清詩紀事》,南京:鳳凰出版社,2003年,885頁。 (58)洪亮吉:《道中無事偶作論詩截句二十首》,《洪亮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12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