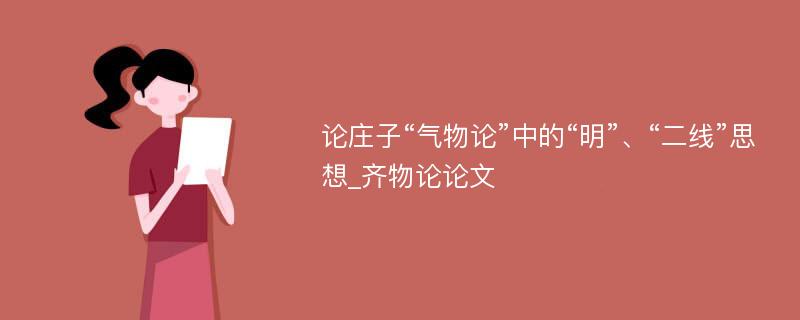
略论庄子《齐物论》的“以明”与“两行”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两行论文,思想论文,齐物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秦时代是由于“周文”解体而面临世界观的危机。即依靠“周文”所维系的人和天、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由于“周礼”的崩解,而普遍地受到怀疑,甚或发生动摇。因此,先秦诸子面临当时的文化危机,重新思考宇宙人生的各种关系,企图透过他们对“道”的理解,重建天—人—社会的合理秩序。换句话说,由“周文解体”与宗法“礼治”的瓦解而带来的突出现象是“失和”的人间世,即乱世的民生疾苦。庄子处于“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人间世》)的乱世,所谓“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人间世》)的描述,正道尽战国的惨状。从宗法制度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先秦诸子所关心的问题,就在如何彻底解决民生疾苦,将“失和(分裂)”的人间世点化为和谐(一统)的人间世的问题。庄子也不例外,陈于廷说:“庄子拯世非忘世,求入世非求出世也。”又胡远浚说:“庄子救世之情与孟子同。”(《庄子诠诂》)
在战国时期,由于“士”集团的扩大和思想自由,引发“百家争鸣”,即“物论不齐”的局面。他们针对宗法礼治所造成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危机,儒家创始人孔丘提出了对“周礼”的“损益”的主张。墨翟在对待宗法礼治的态度上要比孔丘激烈得多。墨翟不满于儒家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墨子·非儒》),主张更为彻底的贯彻“尚贤”原则,这就完全否定了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定贫富贵贱的宗法礼治的原则。在政治思想上反对宗法礼治最为突出的是老聃,《老子·三十八章》明确肯定:“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等。如此,百家由于理论分歧而互相批驳,一方面促进了认识的发展深化,另一方面引起了无穷的“是非之辩”及“利害之争”,以此造成诸子之间“丧己丧人”的人间世,“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人间世》)。庄子在《天下篇》里,对此描述为:
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制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针对儒墨等百家因其“一曲之士”,“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而“丧己丧人”的困苦,撰写了《齐物论》,解其所受之困苦。那么何谓“齐物论”?
一、“两行”与“齐物论”
纵观历代对“齐物论”的注释来看,盖有二种解释。唐以前大都“齐物”连读,《文心雕龙》说:“庄周齐物,以论名篇。”自宋以后分为两派,一为以“齐物”连读,另为齐“物论”。但若把此二种注释与《齐物论》的内容互相比较,则此二种解释实皆可通,虽形式冲突而实融合。陈鼓应先生说:“齐物论篇,主旨是肯定一切人与物的独特内容及其价值。齐物论,包括齐、‘物论’(即人物之论平等观)与‘齐物’、论(即申论万物平等观)”(注:参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94年,第32页。)。然而这种解释也需要更详细的说明。庄子针对乱世所提出的救世之方,一言以蔽之,即是“两行”(《齐物论》)。何谓“两行”?所谓“两行”,从历代注释来看,约有二义;其一谓是“是非并行”的意义,郭象说:“任天下之是非”(《庄子注》),林希逸说:“两行者,随其是非而使之并行也。”(《南华真经口义》)王先谦说:“物与我各得其所,是两行也。”(《庄子集解》)意思是说,在“天钧”的立场上,是非同根生,是非无分别,是非“两行”,都可以合理地存在。其二是“内外并行”的意思,如陈寿昌说:“惟圣人勘破物情,翛然自得。外则和同乎尘境,以遣其是非各执之偏;内则休息乎天君,优游于均平自然之境,应俗栖身,并行不悖。”(《南华真经正义》)本文采取陈寿昌的注释,且以《天下篇》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为“两行”的本义,即内则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外则“不敖倪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就庄子内篇思想而言,人若“为道(心斋、坐忘)”,而成就其大觉的“真人”境界,则将有其“逍遥游”的“行(活动)”。此“游(行)”是指内能“与道游”、外能“与人游”;换言之,“游”意指超越世俗人之为常规所束缚的情状,是一种超脱“有待”的羁绊,而达到“与天(道)为徒(行)”(《大宗师》)的精神,“无待无碍”之境界;同时,“游”也是不避人间世,随顺世俗,“入世”而“虚而委蛇”的“与人无伤”的境界。此“游(行)于道”及“游(行)于世”的“真人”的“行”,庄子称之为“两行”。因此,钟泰说:“游者,出入自在而无所沾滞义。……庄子一书以游字足以尽之。”(《庄子发微》)此庄子的理想人格的“行”,“游”的“两行”境界,从庄子内篇而言:
“圣人”和之以是非(游于世),而休乎天钧(游于道),是之谓“两行”。(《齐物论》)
古之真人,……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游于道),其不一与人为徒(游于世),天与人不相胜(两行),是之为真人。(《大宗师》)
至人神矣!……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游于道)……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胜物而不伤(游于世)。(《齐物论》《应帝王》)
神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游于道)。其神凝,使物不疵疬,而年谷熟。……之人也物莫之伤(游于世)。(《逍遥游》)
“真人(圣人、至人、神人)”的境界,就其“两行”而言,内则能“与天为徒(行)”,即超越万物而“游于道”者,外则能“与人为徒(行)”,即“虚而应物,以游于人世”的“物莫之伤”者。因此,就庄子而言,人若“为道”而有德,而成就其大觉的“真人”境界,则足以将“失和”的人间世化为和谐的人间世。
鉴于上述庄子内篇的“两行”思想,我们可以说明“齐物”论和齐“物论”都可通。所谓“齐物”,是就“真人”的内面精神境界而言,并不是把种种不齐之物强使之齐;而是去除人类的偏见我执,则物即不再以大小、长短、美丑等面貌呈现于真人之前,而是以其唯一无二之独与真人相见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而物既已经齐一,则种种之物论即无从起,则物齐而物论自齐。
然而还有另一问题,亦即“化其道”的真人,虽然他能齐物而物论自齐,然而主张种种“物论”的对方仍在“是非之争”之中,如何应付其“是非之争”而能避免互相“丧己丧人”之困苦,以达至“两不相伤”的和谐之境呢?由此,庄子提出“以明”作为“两行”境界之齐“物论”之方,即外能“游于世”的境界。何谓“以明”?在齐物论篇内有与“以明”相对的“因是”观念。笔者首先说明“因是”之义,其次说明“以明”之方。
二、“因是”之义
面对百家的“是非之辩”,庄子说: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哉?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彀音,亦有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
言之有异于“风吹”、“彀音”者,在其有“成心”、有主见,由此成心主见而造成“是非之辩”。“道”在“真知”之下,才呈现,然而却在“小大之知(辩)”之下,被隐蔽。“言”本身是“无是非”(中立性符号)的,如“彀音”和“风吹”一般,但却造端于一己之偏见,执之以为“是”,便变成“是非之争”的工具,“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各有“是非”,他们总是以别家认为的“是”为“非”,以别家认为的“非”为“是”,儒家重“礼”、“乐”;墨家则“节用,节葬,非乐”,各家囿于所见,成为牢不可破的定见成心,由此产生“因是因非”的无穷循环,如庄子说: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齐物论》)
这不是“物论”,只说明“因是因非”的实情而已。从“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这两句话可以看出,这里的“彼是”即“彼此”,是指认识主体而言的。“彼”是“那方面”,“是”是“这方面”,凡“物”有“那方面”,即有“这方面”,若从“那方面”的观点观察,则所见无非是“那方面”,如从“这方面”去观察,则所见无非是“这方面”。见了那面,则不见这面,见了这面,则不见那面。自己知道的一面,总认为是真的一面,他人(站在与自己不同的角度)知道的另一面,总认为是不真实的。故说“那方面”是产生于“这方面”,“这方面”亦由于“那方面”,因此,“彼是方生之说也”。蒋锡昌说:“此段言物之是非,起于对待,对待不破,是非无穷,乃儒墨病根所在也。”(《南华真经正义》)庄子接着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此处所说“方生方死”是指《天下篇》所言惠子的“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之说,其大意即万物皆变,万物都将走向自己的反面,赤日当空,必定西斜;万物萌生,必归消亡。生的过程就包含着死的趋势。方生方死的论题肯定了生与死的相互渗透,也肯定了生与死的相互转化(注: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189~19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庄子藉惠施“方生方死”之说而说明“因是因非”的途径。即“生死”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同样地“是非”问题也是“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故此,这段言论的重点不在于说明“方生方死”之“物论”。以“方生方死”而推论,则肯定立即变成否定,否定又立即变成肯定,是的变成非,非的又变为是。故“是非之辩”,遂如环之无端,永无穷尽。
在此“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的无穷循环中,“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对此文中的“因是”,历代有两种解释:一是作圣人“无是非”之境,郭象说:“因天下之是非而自无是非也。”(《庄子注》)又如林云铭说:“因其各自为是而不参之以己见也。‘因是’两字是《齐物论》本旨,通篇俱发此义”(《庄子因》)。另是作“因是因非”的省文,如林希逸说:“前说因是因非,此又只言因是,省文也。”(《南华真经口义》)。宣颍也说:“因则是非两化。”(《南华经解》)此两种解释中,本文采取后者之说,从上下文义的联结来看,后者较妥当。就是说,圣人不走此“因是因非”之路,即由同一层次的“物论”之间的“是非之辩”而翻越上不同层次的“天”,而在其“天”的层次照明人间世的各种“是非”。然而他一旦把此高层次的“天”说出来,他仍然不可避免“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的途径。
庄子又说:
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曰:狙公赋芓,曰:“朝三而莫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莫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齐物论》)
“朝四莫三”和“朝三莫四”,实质上无甚差别,朝晚合起来还是七个,但是猴子的情绪却差别那么大。不该喜而喜,不该怒而怒。自以为“是”则喜,“非”则怒。这也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的途径。由此产生,“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之纷争不已的“是非之辩”,其结果是“丧己丧人”。由此,庄子提出“以明”的“解悬”之方。
三、“以明”之方
何谓“以明”?严灵峰先生说:“以,用也。以明,犹用明……。此应上文滑疑之耀而言。盖以明与因是相对,俱为庄子之特有用语。”(注:见严灵峰:《道家四子新论》,第 507 页, 台湾商务印刷局,1968。)“以明”就是“用明”,“以明”作为“两行”境界,就其“行于道”的境界而言,“明”即是超越彼是的对立或超越物我之对立而达到的“明于道”或“明于一(独)”的大觉境界(“朝彻”→“见独”)。因此,庄子说:
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若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
“莫若以明”即犹如“不若两忘而化其道”,“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指”“马”是当时辩者辩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尤以公孙龙的《指物论》和《白马论》最著名。庄子只不过用“指”“马”的概念作喻,原义乃在于提醒百家不必斤斤计较于彼此、人我的是非争论,更不必以一己的观点去判断他人。“以指喻指之非指、以马喻马之非马”,即用儒家的“指”、“马”反对墨家的“指(指之非指)”、“马(马之非马)”,或者相反,则只能是“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到头来只能争论不休。庄子要求只有用“道—非指、非马”来看待种种物论,如此则“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即天地万物皆“道通为一”。因此,儒墨等“百家”若能“为道”以人我双忘,物我两忘,彻底泯除主观与客观界限而达到“明道”的境界,则由“物论不齐”而导致的“丧己丧人”的困苦,自然地解决,如释德清说:“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明乎大道,则了无辩矣。”(《庄子内篇憨山注》)又如宣颍说:“二家欲己之是非正彼之是非而愈生是非,无益也。莫若以明,原无隐言。原无隐言,同相忘乎本明之地,则一总不用是非,大家俱可省事矣。”(《南华经解》)
然而还有另一问题,亦即“化其道”的儒或墨,虽然他们能“物论自齐”,然而对方仍在“是非之争”之中,如何应付其“是非之争”而能避免互相“丧己丧人”之困苦?由此,庄子提出“以明”作为“两行”,其“行于世”之方。故庄子接着说明“以明”为: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故曰莫若以明。(《齐物论》)
陈寿昌说:“此亦申言以明之旨也。”又说:“夫彼者此之偶,是者非之偶。执偶丧枢,去道远矣。惟……物我两忘,混沌不凿,斯可谓会其元极,而得道之要枢也。凡物奇圆而偶方,环者圆也。非执枢忘偶,不足体此圆相。若大夫圆而得其中,则空虚不倚,离种种边,以之应物,不为物所穷矣。”(《南华真经正义》)“以明”是“明于道”的自觉境界,此境界是犹如“得其环中”,即是陈寿昌所说的“体此圆相”的境地。由上可知,“明”是“知常”(《老子第16章》)境界,即明于“道动”的“由无而有,由有而无”的境界,其“道动”的旋转如“环”,如“圆”而又如中则“空虚”。此“空虚”即是“彼是莫得其偶”之处,抓住这个中枢好比占据了环的中心。不论环怎样转动,它的中心是不动的,这样,人就可以用“空虚—无是无非”来对付无穷的是非。意谓只有在“明于道”中,才能彻底消除彼是之间的对待关系,同时“应物”,可以容纳或宽容任何是非之辩。此“应物”之方,庄子接着说:
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然于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道通为一……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
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上文所说的“天地一马也,万物一指也。”和“道通为一”以及“滑疑之耀”是相应的,这是指“明于道”的“圣人”能明照、能包容天地万物而言的,天地万物皆“通为一”。这是由“明于道”而来的一种智慧之“明”、“光”,然而“光而不耀”(《道德经·第五十八章》),因而称为“滑疑之耀”,即是庄子“德不形”(《德充符》)境界的开显。潘柏世先生说:“这滑疑之耀就是晃动于‘有无’,只能说成晃动或闪耀也可以。……它是一个光明,所以称耀。这一种不好捕捉,又不那么明朗的光耀晃动于‘有无’。”(注:参见潘柏世:《齐物论讲解》,第50页。)释德清说:“滑疑之耀者,乃韬晦和光,不炫己见之意。言光而不耀,乃圣人之所图也。……圣人与道为一……以游人世,故和光同尘,光而不耀,是谓葆光。葆光之圣人,其心广大,如天府”(《庄子内篇憨山注》)。诚如潘柏世先生所说的一般,“滑疑之耀”晃动于“有无”,因而能明照万物为“道通为一”,又包容万物,然而“光而不耀(葆光)”,此意谓“圣人”,面对纷争不已的“是非之辩”,却“和光同尘”,“不炫己见”,即“德不形”地应之,即“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然于然,不然于不然”,就是“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为是不用”是指“不炫己见”即“葆光—光而不耀”;“寓诸庸”乃指“和光同尘”,即“随俗而行”,即“随世俗所通行通用者而行”,就是说,儒墨各有的理论既有道理、可通行通用,圣人也随儒墨的意见而行,犹如释德清说:“唯达者之人,知万物本通为一,故不执己是,故曰不用。既不用己是,但寓诸众人之情。庸,众也,谓随众人之见也。”(《庄子内篇憨山注》)“庸”字,就其字义而言,乃指人在自然世界中所建立的人为世界,它与“城市(郭)文明”的种种因素有关。《说文》:“庸,用也”,“庸”字一般解释作“用”,但“庸”字与“郭”字同源,因此,“庸”字的基本作用应从“郭”的原始意涵来了解。“郭”的字形在甲骨文中表象着“有守卫亭的城垣”。“城”是“庸”与“郭”的字根。城邦产生于野蛮向文明过渡之初,“城”的兴起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指人藉助人力在自然中所建立的居住点。它同时指人在自然世界中所欲建构人类世界的基地,或指人类在自然世界中所建构的各种存在方式和各种成果的基地。因此,若就“庸”字之哲学作用来思考,它在“城”的意蕴上乃指“人可有,既有,所立的领域”。它指谓著因人的因素而建构的世界与在此一世界中所具有的特性。此种特性为“用”。由此看来,庄子说“寓诸庸”,他以肯定的态度来看待人间世的各种价值世界(庸)或人类在自然世界中所建构之人为文明世界(庸)的种种因素。如庄子说:
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斫,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聱乎大哉,独成其天!……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
“圣人”,就其“超世”作为“两行”之“游于道”精神境界而言,“不用”人间世的“知、约、德、工”等的价值世界,“独成其天”,与道冥合,其精神超然于物外,故“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斫,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无人之情,是非不得于身”。但就其“游世”境界而言,圣人不避世而与人间同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属于人”。圣人的思想虽超然世外,但他毕竟是人,也就生活于世间,既然如此,就必须使用或遵守世间的各种价值事物。“圣人”并不否定人间世“知、约、德、工”的价值世界,因此,“圣人”以“知、约、德、工”为“天鬻”、“天食”,即天所以养人者,即“天”赋赐给人的,既然是“天”给“圣人”的,“圣人”也可以用,但“圣人”却不以其“天鬻”来人为妄作,只“虚”而应物。即圣人用“天鬻”用得“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矣”(《齐物论》),即用得“通于当下之几而得其中”。王元泽说:“故对人所游者,所谓乘物以游心也。乘物以游心则处于无为之境而任其自然之理。虽知、约、德、工,非我有而我恶用哉?然我之恶用于四者,皆天之所付于人而养于人,我恶可废?废则灭天而已矣。既不可废又不可益,益则助天而已矣。灭天则致累,助天则反害。如此则天人安得和同矣?惟圣人不废不益矣。故既受于天又恶用人?”(《南华真经新传》)“圣人”,对“知、约、德、工”所采取的态度是“不废,不益”,其意谓“圣人”仅“虚而应知、约、德、工”,故能达到“不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无伤”境界。庄子又说: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为八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齐物论》)
道只是自然而无封,言只是天籁之吹而无常仪。然而人心毕竟对外在世界要有所取舍、有判断,则必有其所是、所非,由是而必有其畛域,此即“八德”。此八德就是范畴,也就是人类用以理解、掌握世界的基本概念。因此,在不同的心灵要求下,就可能有不同的范畴划分和理论系统,儒墨各有互相不同的范畴及理论系统,而“八德”只是划分之一种而已(注:参见高柏园:《庄子内七篇思想研究》,第92页。)。蒋锡昌说:“左指卑或下言,右指尊或上言;伦对疏戚言,义对贵贱言。此谓儒家所述人类关系,有此四种大别也。分者谓分析万物,辩者谓辩其所是;竞者谓竞说不休,争者谓争得胜利。此谓墨家(包括其他各派辩士)之术,此谓儒墨之畛,合而计之,有此八种也。”(《庄子哲学》)今范畴既是主观之划分,则只要范畴能满足人类生命实践的要求就可以,其间不必有绝对正误之标准。然而两者之间若互相寻求绝对正误的标准,即“为是”,“众人辩之以相示”,则一定造成“丧己丧人”的困苦。因此,“圣人”“怀之”,即“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议而不辩”,即“为是不用”,而只“寓诸庸”,即随诸家的意见。“为是不用而寓诸庸”的具体表现是:
何谓朝三?曰:“狙公赋芓,曰:朝三而莫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莫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为两行。
“圣人”“为是不用”的态度和“众狙”“因是”是相对的。“圣人”,以“道”观之,“朝三莫四”和“朝四莫三”皆“通为一”,因此,“朝三莫四”也“可(“可乎可”)”,“朝四莫三”也“可(“不可乎不可”)”,只以“为是不用(虚)”而“寓诸庸(随众人之见)”,即是按照“众狙”的情况,把原来的“朝三莫四”改为“朝四莫三”。其结果是:
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因是已”。
庄子又言:
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
“和之以天倪”的“天倪”是“天钧”,即“道枢”。“和之以天倪”意指以“道”观之,“声之相待”,即由百家“是非之辩”而形成的原本对待的“是”与“不是”,“然”与“不然”皆是“通为一”。因此,“明于道”的圣人,只以“无辩”、“为是不用(虚)”的态度而应“是”、应“不是”、应“然”、应“不然”—“若其不相待”。“是”者,是“是”,“不是”者,也是“是”;“然”者,是“然”,“不然”者,亦是“然”。比如,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两者都言之有理。“仁爱”是由己推人,由近及远,以自己为起点,而渐渐扩大之。“兼爱”则是不分人我,不分远近,对一切人,一律同等爱之助之。而渐渐扩大之。“兼爱”则是不分人我,不分远近,对一切人,一律同等爱之助之。仁是有差等的,对不同等级的人,爱助之道即有所不同。兼则是无差等的,对不同的等级,都同等的爱之。仁强调现实社会制度的伦理血缘秩序(“礼”),兼则强调超越血缘伦理关系的普遍的、理想的爱,双方各自言之有理。虽然如此,我们可以把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合为一个“爱”,那么我们在现实社会的伦理血缘秩序里面,能够领略到、能够保存着超越的“爱”,而在超越的“爱”的关照中,仍然赋予伦理血缘的一个秩序。因此,面对“仁爱(是者)”之说,圣人以“是(肯定)”来应之,面对“兼爱(不是者)”之说,也以“是”来回应。由此“圣人无辩—虚而待物”,即“因之以曼衍—不拘常规,随物因变而悠游一生”而达到“人我两不相伤”的“穷年”的境地。如此则能继续保持着“寓诸无竟”的“自足于道”之“无待无事”之境。同时,如“众狙皆悦”一般,“是”者也可成就他的“是”说,“不是”者也可成就其“不是”之说,即“百家”亦可成就各自的学说、各得其所。这正是庄子“德不形(葆光、滑疑之耀)”境界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