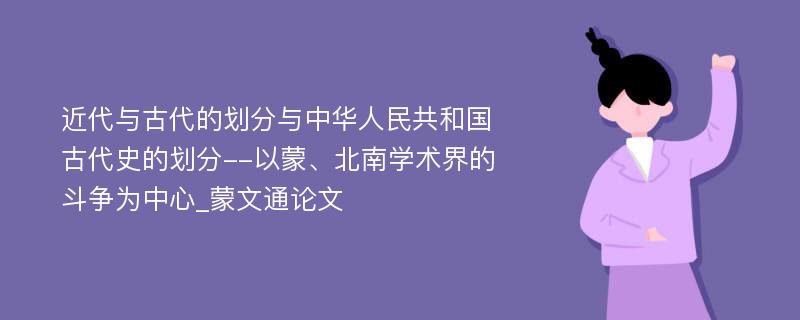
今古分合與民國古史派分——以蒙文通與南北學界之争爲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分合论文,古史论文,中心论文,與民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學術,經史遞嬗,創新史學成爲學術轉承的關鍵,追尋中國文明的起源、重建上古國史成爲民國學界的當務之急。民國有學人指出:“苟欲徹底的明瞭整個之中國文化,無論哲學、文學、史學、教育學等各方面,非溯源于古代,追其根蒂,窮其流別不可也。”近代古史研究,“一方承受歷代之疑古精神,一方接收歐美之科學方法,在此東西思想交流中,新舊傳說衝突中,遂愈覺自由奔放而不可遏止”。①近代中國各階段的新史學大都是歐美史學的折射,疑古精神與西方科學方法促成近代古史研究的勃然興起。同時,“以復古爲解放”本是清代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民國學術承襲清代學術之餘緒,整理國故和古史辨運動的起點正是回歸原典,在繼承乾嘉漢學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錢穆認爲:“考論古史一派,實接清儒‘以復古求解放’之精神,而更求最上一層之解决。”②創新與復古可謂近代古史研究的一體兩面,重寫古史成爲重估中華民族文化價值的重要議題。
誠如有學人所言近世中國史學界最大的“新”“舊”分野形成,關鍵在20世紀“新史學”之建立,形成由“史學方法”來承擔全域的主流,以此“新”來與傳統劃清界限,而有“舊”之認識。③以科學方法區分新舊成爲民國古史研究分派的準繩,民國學術與清代學術僅在“材料”與“方法”層面存在關聯,中國學術流變的內在理路則被截斷衆流式的派分所割裂。整理國故運動蔚然成風之時,以柳詒徵爲首的南高史學與北大國學門相頡頏,從諸子學到古史等問題争鋒相對,此争論被視爲民國古史研究乃至近代學術南北、新舊分派的關鍵。④恰逢此時,廖平門生蒙文通游歷吳越之後,倡議蜀學,主張弘揚廖平今文學,分別今古文家法,扭轉整理國故運動的流弊。此後,蒙文通屢次出川,相繼執教于中央大學與北京大學等高校,與民國各學術流派深入交往。經今古文立場的分歧導致蒙文通與南北學人研究古史的方法與旨趣迥异。若以清末民初經今古文流變爲綫索,考察蒙文通與民國南北學界的分合,或可呈現民國古史研究的多元路徑,進而反思近代學術的“新舊”派分。
一、經今古文之争與民初古史學
民初,在總結二百年清學時,梁啓超指出:清代學術,“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在前半期爲‘考證學’,在後半期爲‘今文學’”。進而認爲清代學術乃“對于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一言蔽之,曰‘以復古爲解放’。第一步,復宋學之古,對于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于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而得解放”。⑤“復古爲解放”是認知“清代學術”的典範,經今古文之争成爲“復古求解放”的關鍵環節。廖平分別今古,宣稱“由西漢以追先秦,更由先秦以追鄒魯。言新則無義不新,言舊則無義非舊”。⑥廖平根據家法條例研究周秦禮制,探尋今古文的起源,啓發晚清今古文之争轉入古史領域。
廖平學術前三變都是以解釋今古文的起源爲中心,重構道與六經的關係,最終走向孔經哲學。廖平主張經史分流,以家法、條例建構古代文獻的歷史層次,分別“六藝”與“六經”,認爲“六藝”是孔子之前的舊史,六經則是孔子創造的新經。廖平否定六經皆史說,認爲六經是孔子空言垂教的產物,六經中的歷史愈古愈文明。康有爲更進一步,宣稱孔子托古改制,六經所載三代盛世是虛構的歷史,徹底否定六經記載的真實性。章太炎提出“夷六藝于古史”,將六經歷史文獻化,認可六經作爲古代歷史文獻的史料價值,以此瞭解中國古代文明的進化與制度沿革。康有爲、章太炎均通經致用,托古改制論與“六經皆史說”成爲清末民初經今文之争的核心議題,經今古文之争由此影響了清末民初政治、學術的走向。重新審查與研究上古三代歷史成爲清末民初學人争辯今古的焦點。一方面,經今文學研究衍化爲考察古史。李源澄指出近代古史研究,實導源于晚清今文學,廖平與康有爲提倡托古改制,本以解經學之糾紛,一變而爲古史之探索。⑦另一方面,經史异位的學術環境必須以史學來爲經學顯真是,“經學上之問題,同時即爲史學上之問題”,“夫治經終不能不通史”。⑧
六經皆史說是近代經史轉型的媒介,托古改制說成爲近代疑古思潮的重要源頭。1923年,蒙文通評議二十年來漢學時,指出:最風行一世的,前十年是以康有爲爲領袖的今文派,後十年是以章太炎爲領袖的古文派,所謂國學,也就在這兩派的範圍內。二十年間,只是他們兩家的新陳代謝,争辯不休,這兩派的争議便占了漢學的大部份了。⑨1929年,蒙文通重申:“在昔浙中學者善持六經皆史之論,綴學之士多稱道之,誦說遍國內。晚近托古改制之論興,綴學之士,復喜稱道之,亦誦說遍國內,二派對峙,互相詆諆,如冰壇不可同形,已數十年于此也。”⑩經今古文之争成爲清末民初學術轉型的主綫,近代今文學的疑古思潮爲整理國故與古史辨運動變經學爲古史學,以史代經提供思想資源。顧頡剛認爲其“上古史靠不住”的觀念來源主要是清代今文經學。
在經史遞嬗的洪流中,近代學界研究今文學集中于劉歆造僞、托古改制;自廖平《今古學考》所開啓的以家法、禮制考察經今古學的傾向却寥落無聞。呂思勉注意到廖平、康有爲的分別,康長素提倡孔子托古改制,導致“後古勝于今之觀念全破,考究古事,乃一無障礙”;廖平以禮制分別經今古文,“而後今古文之分野,得以判然分明。”廖平、康有爲二人學說是“經學上之兩大發明”。(11)呂思勉還强調“後來人所謂托古改制,多非康長素的本意”,“所謂疑古者,亦合康長素無甚關係”,但仍認定康有爲極大影響後來史學思潮,“古史的不確實,這在今日,是人人會說的,而說起這話來,往往引起‘托古改制’四個字”。(12)康有爲破除“後古勝于今之觀念”,爲進化史觀開道,古史辨運動揚棄康氏學說。蒙文通重構近代今文學系譜,表彰廖氏《春秋》學,志在復古求解放,由廖平以今古講兩漢,進而以《春秋》論先秦。
繆鳳林認爲“六經皆史”與“托古改制”說都是儒家正統派的支流餘裔。章學誠與崔述同時申明六經皆史,乾嘉漢學號稱治經,“然治經實皆考史,疏證三代制度名物政教文字之書”,從而導致六藝之學變爲考證學。“二帝三王之行事,反缺如焉。文士以媐蕩自喜,又耻不習經典,于是有今文之學,務爲瑰意眇辭,以大義微言相杜飾。末流遂有儒家托古改制之說。雖以六藝言古史,而認六藝爲孔子所托造,雖奉儒家爲正統,又謂儒者所傳非信史。其所論支離自陷,乃往往如囈語。”也就是說,“六經皆史說”變爲考證學,古史學暗而不彰導致托古改制說興盛。那麽,厘清古史脉絡,應當以崔述爲旗幟。繆鳳林將崔述歸爲儒家正統派學者,稱贊其“疏證之勤,考辨之細,過去之古史界,實無其匹,今之新史學巨子,猶多受其沾溉焉”,“儒者言史,崔氏極其盛”。(13)
蒙文通自稱:“余少習經學,好今文家言,獨于改制之旨,則惑之未敢信。”他認爲:“今文、古文之界別且不明,徒各據緯侯、倉雅爲根實,以訕鄭、阿鄭爲門戶,則近世言今、古學之大本已乖,又何論于托古改制、六經皆史之怪談。”“今、古學之義不明,則古史正未易理”,“二派根本既殊,故于古史之衡斷自別”。蒙文通撰述《經學抉原》、《古史甄微》,有意與托古改制、六經皆史說立异。(14)蒙文通從“事實”與“義理”兩個層面分別經史。一方面,六經僅爲上古歷史的一種記載,一種解釋。另一方面,經學可貴之處並不在于它對上古史迹的合理解說,而在于儒家經學中有孔子所確立的價值標準,即“變魯以協道”。在《古史甄微》中,蒙文通以古史三系說爲儒家起源提供合理的歷史解釋,又從上古三代歷史出發認定儒家義理實爲中國文化的精華。至此,“素王之說既搖,即改制之說難立”,證明“六經皆史之談,既暗于史,猶病于史”,“孔子所傳微言大義,更若存若亡”。(15)
經今古文之争促使晚清經學紛争演化爲古史研究。“六經皆史說”從歷史的起源處,爲建立特殊的民族歷史文化提供知識資源;托古改制論所衍生的疑古思潮,成爲古史辨派超越儒家理想化古史系統的思想來源;蒙文通以地理、民族、文化的視角創立古史三系說,重新解釋經史關係,以史證經,申明儒學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經今古文立場的差別導致民國學人研究古史旨趣判若雲泥。
二、“儒家正統史觀”與“諸子百家之言”
北伐前後,南高與北大學人奔走各地,國內的學術格局有所改變,古史研究更加爲世所重。齊思和便指出:“(顧頡剛)倡‘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之說,近世史學方法,始應用于我國古史。斯說既出,舉國大嘩,或據理痛駁,或信口抨擊,往復辯難,至十餘萬言,誠我國史學界稀有之盛舉。惜當時反駁者,既昧于近世史學方法,復不明顧先生之要旨,惟據‘禹爲爬蟲’一點,反復辨雜,棄其根本而窮其枝葉,故毫無結果而罷。此後顧先生挾其學走閩越,所至學者響應,蔚然成風。”(16)從“舉國大嘩”到“蔚然成風”,短短數年,古史辨的影響力可謂與日俱增。柳詒徵認爲:“今人疑經疑古,推翻堯舜禹湯周孔,而轉喜表彰王莽,即由此根本觀念不同,故于古史争辯最烈。”(17)19世紀20年代末,柳氏門生繆鳳林、范希曾、陳訓慈、鄭鶴聲、張其昀發起成立南京中國史學會,發行《史學雜志》。由于弟子星散,原來辯論古史的幹將劉掞藜畢業後,任教成都大學,《史學雜志》前三期未登載任何上古史之類的文章。恰逢此時,蒙文通二度出川,寓居支那內學院,隨即由歐陽竟無、湯用彤等師友引薦結識柳詒徵、繆鳳林師徒,執教于中央大學。蒙文通的參與彌補了南京中國史學會“中國上古史”領域的空白,繆鳳林與蒙文通的辯難也成爲了當時南京史學研究會上古史研究的主綫。
廖平曾暗示今文經中上古帝王各傳數十世、地域四至各殊的記載與由來已久的古文經的五帝一系相承說明顯矛盾,向蒙文通提示上古多元觀念。考證三皇五帝系統,成爲蒙文通研究上古史的起點。蒙文通認爲,三皇五帝說起自晚周,三皇之說,本于三一,三皇五帝原本是神祇,初被視爲神,帝與皇的稱號本來不關人事。“孟子而上,皆惟言三王,自荀卿以來,始言五帝,《莊子》、《呂氏春秋》乃言三皇”。五帝說始見孫子,三皇說始見莊子。蒙文通推論三皇五帝說皆起于南方,鄒衍藉此提倡五運之說,“三五之說”便傳到東方、北方。晋人言五帝,就是兼容齊、秦的說法。《大戴》、《史記》五帝之說,則是源秦、晋而次第轉變的最後說法,司馬遷是采納“既有三皇說以後之五帝說”。孔安國、皇甫謐以伏羲、神農、黄帝爲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三皇五帝之說最後確立。(18)
蒙文通考察三皇五帝說的衍變,整理三晋古史系統,認爲三晋之說本已“去古義益遠”,後起三皇五帝說更是“無當于義猶昔也”。伏生本于魯學提出的三皇說是最爲可信:三皇並非人身相接,三皇更替之間易姓王者百數十代,從遂人氏到黄帝,其間易姓稱王者多至三百姓,而三皇三百姓間可能有萬代。繆鳳林在三皇、五帝是人或神及其起源流變等問題上並不認同蒙文通的意見。在繆氏看來,“神五帝”之說起于國神(取人爲神),“人五帝”之說起于假帝號以尊王,二者本不相涉。三皇說起于道家理想的具體化。三皇五帝是人而非神,五帝說起于東周,三皇說確定于秦人。(19)孫正容也認爲:秦漢之際,三皇五帝人神之說暫且分明,王莽之後,“神、人與生爲人而死爲神三者遂雜糅不分,而說五帝者益紛紜而莫所遵循也”;史籍中三皇五帝的順序,“僅就其人與書中所稱述之事有關者言之,與後先次序無涉”。(20)
蒙文通以魯學爲根本,質疑古文經的古史系統,經傳並重,博采諸子百家學說,甚至“多襲注疏圖緯之成說”。繆鳳林治古史信經疑傳,守儒者正統學說而排斥百家之言。二人古史研究的分歧頗有今古之争的意味,對三代世系的分歧就在于此。長久以來,關于三代的世系,多依據《史記·三代世表》,《史記》所利用的材料多爲《左傳》、《國語》,特別是《世本》。章太炎對《世本》推崇備至,認爲它爲中國開創了一個新的歷史典範,它的編年方式與記載內容爲中國民族界定了一個特定的三代紀年,“推闡《世本》,《帝繫姓》、《居篇》、《作篇》之旨尤精”。(21)繆、柳二人著述言及三代世系,多以《史記·三代世表》與《本紀》爲依據。在蒙文通看來,《史記》中自相矛盾之處太多,《三代世表》、《世本》的很多記載不足爲據。相反,《命曆序》中“自炎帝、黄帝、少昊、顓頊、帝嚳皆各傳十數世,各數百年”的說法較爲可信,“《命曆序》、《含神霧》各篇皆守今文師法,自相扶同”。對于三代世系,夏、殷、周的年歲,《世經》上的說法“與古無征”,僅與《左傳》有相合之處。蒙文通認爲“自劉歆橫斷年數,損夏益周”,五帝三王年歲便亂。“班固《世經》,即本之劉歆《三統曆》,自爲妄書,不足爲據”。既然古文一系的《世經》與《三統曆》惹人懷疑,那麽《命曆序》與《殷曆》就更爲可信。何休治《公羊》所用的正是《殷曆》,“與《三統曆》抗衡者獨爲《殷曆》,治今古學者宜各知所尚”。(22)
廖平對蒙文通所提出的論題,是要論證中國立國開化之早,東西各民族無法企及,所謂“破舊說一系相承之謬,以見華夏立國開化之遠”。那麽,回應“中華民族西來說”本是蒙文通古史研究的題中之意。繆鳳林針對漢民族文化西來說,曾先後發表了《中國民族由來論》、《中國民族西來辯》、《中國史前之遺存》諸文,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國通史綱要》中辟專章再行論列。蒙文通特意發表《中國開紀于東方考》,自稱與繆鳳林“一破一立,相待相濟”。蒙文通破除黄帝與少昊的父子關係,澄清在西來的一系之外,還有東邊本土的一系,進而從地理與文化的視角證明中華文化起源于東方。可以說,就反對中國民族文化西來說而言,蒙文通、繆鳳林站在同一立場,認爲中國文化發源于本土;不過,柳詒徵認爲“中國古代文化,起于山岳,無與河流”。蒙文通則認爲中國文化源自海岱的泰族,“自昔以魯地文化爲最高”,魯學爲儒學的嫡傳,經今文學的正宗。
蒙文通闡發古史三系說,旨在申明儒學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然而,今古文立場的分別使得蒙文通與柳氏師徒的分歧日益彰顯。《古史甄微》剛一發表,中央大學史學系學生張崟發表了一篇《〈古史甄微〉質疑》,張氏抓住《古史甄微》一以貫之之道——古史分三方傳說,他指出“史說既曰三方,則似應此疆彼界,無所出入”,但比較“晋、楚、鄒魯之所傳”,“三方之說爲大謬”。蒙文通“所以證各方學者自成一系之說之證”,實乃“已胸具成見,徵嫌阿私”。張氏對《古史甄微》最大不滿在于蒙文通申六經非史之旨,以諸子百家之言質疑六經在史學上的正統地位:
儒家之說,則先聖列賢博古通今,雅意述作,以示來葉;故其所述,前後相應,略無抵牾;此其所以爲諸子所莫逮,抑其已成正統之史說,所以未應輕事平反也!矧蒙先所舉以爲三晋南方史說之代表最宿者,不過《山經》及汲冢之書;而前者即决非禹制,《紀年》又顯成于戰國;本身真僞,猶未分明,則吾後學者于古史傳說之從違,自不容捨去古未遠之孔門儒家傳說,而反仞晚出諸子百家之讕言耳!(23)
張崟十分明白《古史甄微》的學術立場,認爲蒙文通有意用三系說、諸子學說來否定儒家信史,批駁六經皆史說。不過,張崟認爲儒家史說自成系統,諸子學說不僅雜糅百家,毫無統紀,晋學、楚學基本文獻《山海經》、《汲冢紀年》的真實性都值得懷疑。若要通曉古史真相,要依據“儒家傳說”。孫正容也批評西漢以降,“因儒信讖,以讖傳儒,輾轉傅會,上古史遂益上溯而益神話”。(24)這並非一己之見,而是南京中國史學會研究古史的風氣。
繆鳳林贊譽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元明以來所未有”,根據便是此書“以六藝爲經,而緯以百家,亦時徵引新史料,而去其不雅馴者,持論正而義類宏”。(25)柳詒徵摒除“不雅馴者”就是蒙文通《古史甄微》所依據的“注疏圖緯之成說”。柳詒徵治學不以漢宋爲門戶,然其治史與古文經學若合符節,周予同曾指出,《中國文化史》在學術傳承上主要受古文經學影響。(26)崇六經、斥諸子是柳詒徵的一貫作風。柳詒徵認爲清儒治經皆爲考史,甚至“今文學家標舉公羊義例,亦不過說明孔子之史法,與公羊家所講明孔子之史法”。(27)蒙文通主張經史分流,《古史甄微》多采納諸子、圖讖學說,有意針對六經皆史說。蒙文通不以六經(魯學)爲史,此與托古改制說近似,只是他没有否定上古三代歷史,而是以晋學爲本重構上古三代歷史,《古史甄微》中有一個主旋律,即三代是“權力”角逐而非“道德”興盛的時代。柳詒徵篤信《周官》,在《中國文化史》中盛贊三代道德、文化之盛。胡適批評柳詒徵“所據材料多很可疑,其論斷也多不很可信,爲全書最無價值的部份”,與其“臆斷《王制》、《周禮》所載的制度何者爲殷禮何者爲周禮,遠不如多用力于整理後世的文化史料”。(28)
從廣泛交游到論學,無疑會使人產生蒙文通與柳氏師徒同屬一系的印象。在中央大學史學系同仁贊譽蒙文通的著作,“內容豐富,議論詳實”。(29)中央大學擬將蒙文通《古史甄微》、《經學抉原》收入中央大學叢書予以出版,稱贊此書“凡研究吾國古史者不可不一睹斯篇”。(30)然而,1930年9月,在中央大學任教纔一年的蒙文通應成都大學聘請,蒙文通自稱“應成大聘,殆遮醜之詞”。“遮醜”的論調或是蒙文通與柳詒徵師徒學術分歧的影射。實際上,蒙文通的學術同道對柳詒徵師徒的學術也有所保留。歐陽竟無曾批評繆鳳林竟無“所學既淺,而在外妄談”。(31)或可說,蒙文通與柳詒徵師徒的分歧是在中國學術傳統內部的今古有別,蒙文通與古史辨學人在學術方法都受到今文學與西方學術的啓發,但學術旨趣存在中西之分。
三、“考信”與“辨偽”
《古史甄微》完成後,蒙文通開始探尋周秦民族問題。20世紀30年代任教河南大學、北京大學,均講授“周秦民族與思想”一類的課程。國難之際,激于世變,顧頡剛發起禹貢學會,致力于地理沿革史和民族演進史的研究,仍主張“地理方面實在不知道保存了多少僞史,我們也得做一番辨僞的工作纔好”(32),禹貢學會和“古史辨”的精神可謂一脉相承,更側重以民族、地理爲中心重建國史。此時致力于周秦民族史研究的蒙文通遂與禹貢學會也結下不解之緣,童書業在介紹《禹貢》時,還特意提到“蒙文通、錢賓四諸先生都常有文字在裏面發表”。(33)1935年蒙文通爲北大解聘之後,顧頡剛覺得傅斯年的做法太過分,旋即舉薦蒙文通至天津女子師範學院。(34)抗戰前後,蒙文通與顧頡剛及其弟子廣泛論學,過從甚密。顧頡剛的學術受經今文學啓發,贊譽蒙文通能“批判地接受西洋史學史權威的方法”。(35)不過,顧頡剛考辨古史旨在解决經學的癥結,使經學史學化;蒙文通研究上古三代、周秦民族問題仍以今文學爲立場,闡發儒家的文化理想。
在《古史甄微》中,蒙文通拆解古史一元體系,以三皇五帝爲後起,質疑禪讓說,打破了由美德築成的三代理想。對于這些說法,童書業給予極高評價,認爲“在他以前,没有人像他這樣把‘三皇’徹底研究過”,並將其學說歸結爲“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觀”。(36)三皇五帝問題是民國重建古史系統的重大環節,以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而言,三皇是“層累”的第二層。顧頡剛、楊向奎、楊寬、呂思勉紛紛撰文考證其淵源脉絡。就繆鳳林、蒙文通、顧頡剛三人而言,童書業的分派或可有所啓發。
蒙、繆二人《三皇五帝說探源》文章剛一發表,顧頡剛就特意取《史學雜志》參閱,未置可否。(37)童書業在爲顧頡剛、楊向奎合著的《三皇考》作序時稱,“在近人中辨‘三皇’說的僞最力的人,據我所知道的有三位大師。第一位便是本文的著者顧頡剛先生”,“不久便有第二第三懷疑三皇五帝說的人起來,那便是經今文學大師廖季平的高足蒙文通先生,和我們的右翼驍將繆鳳林先生”。童書業的排序,看似按照三人質疑三皇五帝說的時間爲序,實際暗含了三人辨僞力度的差別。繆鳳林之所以被稱爲右翼驍將,因爲繆氏素以“信古”著稱。童書業認定繆鳳林“實在受崔述的影響很大,他只是一個儒家正統派的古史學者”。崔述無疑對顧頡剛影響至深,顧頡剛接受崔述“辨僞”的一面,而繆鳳林則吸收其“徵信”的一面。童書業格外强調蒙文通是“今文學大師廖季平的高足”,或有提示蒙、顧二人有共同的思想來源,蒙文通也有“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的痕迹。不過,蒙文通以《周官》爲三晋之書,而古史辨派視《周禮》爲“王莽的書”。因此,蒙文通的議論“有些倒果爲因”。(38)
錢穆認爲“考信必有疑,疑古終當考。二者分辨,僅在分數上”。蒙文通與顧頡剛最明顯的分歧就在對待上古文獻運用的“分數”之上。蒙文通在今文學家的立場上運用了大量的讖緯材料,用他自己的話講“本爲究論史乘,而多襲注疏圖緯之成說,間及諸子,殆囿于結習而使然也”。(39)楊向奎在《〈禪讓傳說起源于墨家考〉書後》將蒙文通對禪讓制的觀點定性爲争奪說者,認爲蒙先生所依據的史料足以破錢穆、郭沫若等選舉說,但仍是彌縫的工作,弊端尤大。顧頡剛考究史源,提出儒墨創造宣傳說,相對較優。也就是說,蒙文通並没有科學的考察史源,仍是在相信上古史料的前提下,彌縫各家之說。顧頡剛之所以較優的原因就是能大膽懷疑上古史料並有所取捨。即前者“對于原來史料先取信任態度,而後加以解釋”,後者“乃先估定此種史料之價值,然後考其來源”,前者多因信而牽强彌縫,後者多因疑而得事實真相。(40)
辨僞書是重建古史的第一步。20世紀30年代,學者紛紛關注“僞書”的形成及其與辨僞的關係。顧頡剛强調以歷史的觀念,使僞書脫離所托的時代,“而與出現的時代相應”。這與其說是破壞,不如稱爲適當的移置。顧頡剛寫就《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依循康有爲、崔適之說,坐實劉歆造僞《周禮》和《左傳》等先秦典籍。蒙文通將“僞書”提高到“僞學”的層次,“必皆先有僞書之學,而後有僞學之書”。《周官》等書雖爲僞造,但“義仍有據,事必有本”。作僞者各有家派,辨僞應考察“學派所據”,辨明“作僞者屬于何學、果爲何事,一書之間孰爲僞、孰爲不僞”,而不當“以作僞二字抹殺古代之書”。(41)蒙文通考察僞學,以家法條例、辨明禮制,分別今古,梳理魏晋南學、北學分流一脉相承。蒙文通與疑古辨僞者關于“僞書”、“僞學”的分歧,不僅在于“客觀”的考辨方法,更在于“主觀”的文化理念。
錢穆認爲“懷疑非考據家病”,“疑者非破信,乃所信之廣”,“懷疑非破信,乃立信”。(42)考據家以懷疑的態度,不受“經”與“道”的束縛,以歷史觀念平視各家學說,所“信”自然“廣”。蒙文通肯定“幾十年來,疑古辨僞的工作是有很大的成績”,但“總覺過火點”,“有些疑古派學者一方面疑某書之僞,却有時又還引用;既不信歷史之真,却時又在講述,就表明疑古者也自信不過”。(43)蒙文通認爲疑古派“自信不過”,但疑古派自身却相當自信,之所以疑信參雜,那是因爲心中早已橫亘著“進化”的歷史觀念,古書中符合此“主觀”者,自可“引用”、“講述”,不合者必然懷疑,乃至認定爲“僞”。“疑”“信”之間的分寸不同源自雙方“辨僞”系統的差別。有學人在30年代初曾對民國辨僞書之風,總結到:
辨僞書之風,近十餘年來最盛,然辨僞書非有意與古人作對,亦非求嘩衆取寵,以爲得名之法,自有不可不辨之故在也。其所以辨之之理,皆自有一貫之系統。此系統分主觀與客觀兩面;主觀者,先確定一種歷史進化觀念,凡違此觀念者,皆改定其歷史上之價值,甚至否定其歷史上之價值。自鄭漁仲以至顧頡剛,主觀派也。若閻百詩以至惠定宇,則爲客觀派。其法乃從客觀上取得作僞之證據,然後定本書爲僞作。雖然持主觀之概念者,亦有待乎客觀之證據而後成定論,有客觀之證據亦必須構成一貫之歷史系統,然後成一家之學問。(44)
辨僞僅是學問的初步,尋求客觀證據的一種手段,關鍵在于背後的一套“主觀”、一種“主義”。熊十力批評今日考史者以科學方法相標榜,“不悟科學方法須有辨,自然科學可資實測以救主觀之偏蔽,社會科學則非能先去其主觀之偏蔽者,必不能選擇適當之材料,以爲證據,則將任意取材以成其僻執之論”。(45)疑古未爲不可,但如何疑古,爲何疑古,其背後牽涉的“主觀之偏蔽”大有討論餘地。古史辨學人堅信,誰都知道古代史有問題,誰都知道古代史的一部份是神話,並非事實。甚至有人著中國通史,不敢提到古史隻字。顧頡剛最初提出“層累造成的古史說”時,認爲古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話”,到了童書業、楊寬直接以神話學解釋上古史的研究,商周以上的歷史只是傳說,這些傳說都來源于神話,這些神話按其來源可以分爲東西二系民族,二系民族神話由混合而分化,演變出上自黄帝下至夏代的世系,因此推斷三皇五帝時期歷史是完全不存在的。蒙文通是依鄒魯、晋、楚三方民情創立“古史三系說”,楊寬基于“神話演變分化說”批評蒙文通“各以民情不同,而分别演化,若據鄒魯晋楚分別演化之傳說,謂即初相,則未免過于近視”。(46)蒙文通認爲疑古派將三代歷史一概抹殺,把歷史縮得太短,把中國歷史壓得太低。他在《古史甄微》中對古史傳說中的女媧、燧人氏、伏羲、神農、共工等傳說非但不加以摒棄,且賦予他們特定的歷史地位,將中國文化的源頭定在燧人氏。所以,有學者認爲在蒙文通與楊寬之間,似可以認爲存在著歷史神話化與神話歷史化兩種不同觀點之争(47),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蒙氏肯定上古三代的歷史文化傳統,楊寬認爲此皆神話傳說,僅能以神話學來解釋其演變分化。童書業即稱:“吾人根本不信夏以前有更高之文化,故吾人之古史系統與蒙先生完全不相同,吾人言古代史只敢斷自夏商。”(48)
民國學界諸人始終有一個縈繞心頭的夙願,即編著一部全新的《中國通史》。在新史學“重建古史”的序列中,蒙文通常被引爲同道。抗戰之初,蒙文通打算在成都重建禹貢學會。(49)1941年,饒宗頤計劃編修的《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中就收録了蒙文通五篇文章,數量與呂思勉等同,僅次于饒宗頤與顧頡剛。(50)抗戰勝利後,顧頡剛在總結近百年史學發展時,以《古史辨》爲代表的古史研究承前啓後,視蒙文通爲同道而予以表彰。(51)蒙文通自稱“壯年以還治史”,不過,蒙文通史學的“統宗”與古史辨學人大相徑庭。“古史辨”運動作爲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環節,以歷史進化觀念指導,期望再造文明:解構上古一元史觀,疑古非聖,破壞儒學的神聖意義,爲建構科學的社會文化理想鋪平道路。顧頡剛與蒙文通都受到晚清今文學的影響,顧頡剛接受康有爲公羊改制的疑古精神的啓發,“古史辨”以進化的眼光“辨僞書”,視古史爲神話;蒙文通認爲晚清公羊學近乎僞今文學,以家法條例研究《穀梁》纔稱得上成熟今文學。蒙文通澄清今文學源流,以多元的古史觀來維護傳統儒學在中國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四、方法和宗旨
梁啓超斷言:“清代學派之運動,乃‘研究法的運動’,非‘主義的運動’也。”(52)清代漢學就是以經學爲重心,以考據爲表徵。考據方法成爲民初學人溝通中西的媒介。胡適宣稱整理國故就是要用科學方法條理中國的材料,完成一部中國文化史。整理國故運動被時人冠以“新考據學”,被視爲乾嘉考據學的變相復興。1928年,胡適發表《方法與材料》,調和方法與史料,“同樣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績也就不同。但同樣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績也就有絶大的不同”。(53)以科學方法辨析新舊材料成爲近代學術區分新舊、劃分派別的重要依據。後來,馮友蘭認爲民國史學界有三種信古、疑古、釋古三種。集疑古學大成的楊寬進一步細分爲信古、疑古、考古、釋古四派。柳存仁認定這種派分的標準是“進行方法與實際工作”。重建中國上古史的途徑就是新方法、新見解的成立與新史料的發現,近代古史研究乃至新史學的譜系由此展開。(54)若以科學方法截斷衆流式的勾勒民國學人重建古史的系譜,《古史甄微》打破上古一元的古史三系說暗合了“新史學”所高舉的古史多元觀,蒙文通自然成爲被視爲“由經學向史學過渡”的典型。(55)楊向奎將蒙文通與顧頡剛並舉,認爲時間發展中有層累,空間分割上有不同,二人之說相得益彰,都是探討古代歷史傳說的門徑。(56)但若以溯源浚流的方式,考察民國學人争辯今古與溝通中西的時代語境及其旨趣,中西、新舊等分派標準均有削足適履之嫌。
1933年,有學人綜述學界古史研究,認爲近代古史研究可分爲“持科學方法以研究古史者”與“承清代朴學大師治學之精神以研究古史者”。前者以胡適、顧頡剛爲代表,“胡氏之學,在揚新漢學之徽,而彌縫于疑古者也,顧雖以實驗主義爲方法,而所謂大膽的假設則常陷于謬妄,小心求證則多雜以主觀。”顧頡剛“借胡適之說而有所啓發,遂致力于古史之辨僞”。其他如衛聚賢、郭沫若、鄭振鐸等學人,“雖其鵠的不盡同,方法不相合,要之爲受西方學說之影響則一也”。後者以柳詒徵、繆鳳林、蒙文通爲代表。柳詒徵“持正統穩健之論,不爲非常异義可怪之談”,“考信古籍,不輕于疑。與北方之高談疑古者殊科矣。本柳氏之說,專精力學,以一人之力,編著通史者,則有其弟子繆氏鳳林”。蒙文通“由經子騷以考其同异,確然有以見古代民族學術一一之不同,條別以明其義者”。繆、蒙二者“雖持論不同,所見各异,要其本于師說,出于力學,無二致也”。前一派可稱爲“標榜主義”,而後一派柳、繆二人則信古太過,有“剿襲雷同”之嫌。蒙文通受業于今古文大師之門,“承其遺緒,豁然貫通,擬之標榜主義與剿襲雷同者,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蒙氏與柳、繆師徒同屬“承清代樸學精神一脉”,“一則創爲通史,不屑考證;一則勤力考證,顯微闡幽。然要歸于義則一,是柳氏、繆氏之于蒙氏,雖貌异而心實同也”。(57)
或可說,以多元古史觀而言,古史辨學人與蒙文通若合符節,蒙文通與柳詒徵師徒旗幟各异。若以中西文化理想而言,顧頡剛與蒙文通、柳詒徵師徒截然分流,蒙文通與柳詒徵師徒貌异心同;但就經今古文立場與經史關係立論,顧頡剛、蒙文通、柳氏師徒研究古史的學術旨趣迥异。
顧頡剛認爲鴉片戰争以後,“中國文化不能不换一條路走”。今日治學的目的是要使古書及古史料都成爲史家的材料,研究古史要從辨析經學的家派入手,否則“仍必陷于家派的迷妄”,必須“從家派中求出其條理,乃可各還其本來面目。還了他們的本來面目,始可以見古史的真相”。研究古史是以古史激發愛國思想,知曉中國文化確實的優缺點,糾正盲從的傳統思想,不必爲中國文化本位,變經學爲史學:“吾人今日治經,宜立新系統,新見解,以經說所得匯爲各科知識之資料,構成中國文化史之主要內容,此或爲現代學者治經之目的,而有异于昔日抱殘守缺、篤守家法之經生。”(58)顧頡剛認同錢玄同“超今文”的態度,研究今古文問題目的是爲研究古代政治史、曆法史、思想史、學術史、文字史奠定基礎。(59)
辨析史料是史學求真的前提,繆鳳林强調:“史學以求真爲鵠,研究之對象爲人事,根據之材料爲載籍與實物。”“上焉者則以舊史料釋新史料,復以新史料釋舊史料。”(60)顧頡剛與柳詒徵師徒看待儒家經典,有疑古、信古之別;就考證方法而言,則道一同風。錢基博認爲:“北大爲懷疑的國學運動,而東大則反之而爲宗信的國學運動,宗風各倡,然而重考據,尚佐證則一。世所謂新漢學者是也。”(61)柳詒徵師徒的學術理念與晚清國粹派一脉相承,以史學爲中國傳統學術的源頭與核心。若要維繫國家民族文化的精義,必須通曉史地之學,古史學爲經世之學,以致用爲依歸。中華民族精神以“禮”爲核心,研究古史的首要目的在于尊崇國族,闡揚固有文化,振興民族精神,使國家與民族在儒家精神層面統爲一體。(62)
研究學術必先知家法,今古文學各有家法,古文偏于考證之學,今文學偏重義理。古史辨的考據精神,古史凡無實證之處,皆可抱有懷疑態度。蒙文通以家法條例辨析學術源流,不僅著眼于一經之義,更關注六經之間的整體關聯,形成統一宗旨的今文學說。蒙文通治學恪守以家法條例澄清兩漢周秦儒學的原貌,以窮源溯流的方式闡述經學流變,實現“通經明傳”再“明道”的抱負。蒙文通創立古史三系說,旨在申明儒學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此後,蒙文通構思《中國哲學史》,即“先從史說入,以見周秦之哲學根本;從民族說到思想與文化”。蒙氏研究周秦民族史,考察周秦之際民族變遷與先秦學術流變的關聯,最後落實于今文學的興起,“新起儒學即以推倒周秦貴賤貧富之階級制度而建立平等民主(禪讓)之政治,遂成功爲今文學制度之基礎”。(63)針對“超今文”的主張,蒙文通以理想與事實分別今文與古文,以“秦漢新儒學”闡明今文學的革命理想與制度精義。蒙文通考察經說與古史的關聯,期望建構儒學義理與歷史變遷的能動關係,闡發儒家內聖外王之義。
近代學術分派以方法爲準繩,潜在割裂了傳統與現代之間學術與歷史、價值與知識間的聯繫。(64)錢穆認爲:“此數十年來,國內學風,崇拜西方之心理,激漲彌已,循至凡及義理,必奉西方爲準則。”“治中學者,謹願自守,若謂中國學術,已無義理可談,惟堪作考據之材料。”(65)近代新學術的成立正是以此爲前提。蒙文通以今文學爲立場,試圖建構義理與經史之學間相互能動的學術體系。以新學術的眼光看來,蒙文通“能以經學分析古史,各歸其方士流別”,但“時流于想象主觀,而不免荒唐”。(66)因此,蒙文通古史研究的本意在民國學界隱而不彰。不過,近三十年來,考古學的發展又印證了蒙文通此類“主觀想象”的“科學性”。(67)蒙文通學術的彰顯要依靠考古發現來定性爲“科學的預見”,此事本身就體現經史易位的時代趨勢,但又引發如是思考:新史學以史代經,將經學視爲史料,誠爲近代學術轉型的樞紐,但經學“義理”是否全無意義,畢竟史學既有考據與科學的一面,還有義理與藝術的一面。考察民國學界古史研究的多元旨趣,似乎暗示了二者之間並非截然對立,誠有珠聯璧合的可能。以此爲綫索,不僅能爲認知近代學術提供新的視角,或許還能爲時下古史研究走出新史料的擴充與理論無法突破的無奈局面提供思想資源。(68)認知中國學術流變的本意,以國故整理科學,溝通中西,更是當下建構中國學術本位的重要途徑。
注释:
①李悌君:《關于中國古史問題及其研究法》,《勵學》第6期,1936年7月。
②錢穆:《國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30頁。
③參見王爾敏:《百年來的史學風氣與史學方法》,《漢學研究通訊》第20卷第4期,2001年11月,第1~2頁。
④關于近代新史學流變與新舊之争,可參見桑兵:《近代中國的新史學及其流變》,《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⑤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6頁。
⑥廖平:《與康長素書》,《中國學報》第8期,1913年6月。
⑦參見李源澄:《論經學之範圍性質及治經之途徑》,《理想與文化》第5期,1944年2月。
⑧錢穆:《自序》,《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6頁。
⑨參見蒙文通:《經學導言》,《經史抉原》,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第12頁。
⑩蒙文通:《論先秦傳述古史分三派不同》,《成大史學雜志》第1期,1929年。
(11)呂思勉:《論經學今古文之別》,《呂思勉讀史札記》(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25頁。
(12)呂思勉:《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月刊》第2卷第3期,1946年。
(13)繆鳳林:《古史研究之過去與現在》(上篇),《史學雜志》第1卷第6期,1929年12月。
(14)參見蒙文通:《論先秦傳述古史分三派不同》。
(15)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第4頁。
(16)齊思和:《最近二年之中國史學界》,《朝華月刊》第2卷第4期,1931年。
(17)柳詒徵:《史學概論》,柳曾符選編:《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1頁。
(18)參見童書業:《三皇考·序》,呂思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7册(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8~39頁。
(19)參見童書業:《三皇五帝說探源·按語》,《古史辨》第7册(中),第334頁。
(20)孫正容:《三皇五帝傳說由來之蠡測》,《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30年5月。
(21)繆鳳林:《古史研究之過去與現在》(上篇),《史學雜志》第1卷第6期,1929年12月。
(22)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28~33頁。
(23)張崟:《〈古史甄微〉質疑》,《史學雜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0年9月。
(24)孫正容:《三皇五帝傳說由來之蠡測》,《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30年5月。
(25)繆鳳林:《古史研究之過去與現在》(上篇),《史學雜志》第1卷第6期,1929年12月。
(26)參見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3頁。
(27)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下),《民國叢書》第二編(42),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47年,第119頁。
(28)胡適:《評柳詒徵編著〈中國文化史〉》,《清華學報》第8卷第2期,1933年6月。
(29)《史學消息》,《史學》第1期,1930年,第253~254頁。
(30)《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第1卷第16期,1930年6月。
(31)參見中國革命博物館整理:《吳虞日記》(下)。
(32)顧頡剛:《趙貞信來信之“編者按”》,《通訊一束(24)》,《禹貢》第4卷第6期,1935年11月。
(33)童書業:《古史學的新研究》,《東南日報·讀書之聲》,1934年11月7日,第15版。
(34)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3),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56頁。
(35)蔣星煜:《顧頡剛論現代中國史學與史學家》,《文化先鋒》第6卷16期,1947年9月。
(36)童書業:《三皇考·序》,呂思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7册(中),第37頁。
(37)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2),第347頁。
(38)童書業:《三皇考·序》,呂思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7册(中),第36~38頁。
(39)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1頁。
(40)參見楊向奎:《〈禪讓傳說起源于墨家考〉書後》,《古史辨》第7册(下),第108~109頁。
(41)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經史抉原》,第108-109頁。
(42)錢穆:《古史辨第四册序》,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頁。
(43)蒙文通:《治學雜語》,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26頁。
(44)《新書介紹·今古文尚書正訛》,《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6卷第4期,1932年7~8月。
(45)熊十力:《關于宋明理學之性質·復張東蓀先生》,《文哲月刊》第1卷第6期,1936年3月。
(46)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呂思勉、童書業編:《古史辨》第7册(上),第97頁。
(47)參見吳少瑉、趙金昭主編:《20世紀疑古思潮》,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第398頁。
(48)童書業:《中國疆域沿革略》,上海:開明書店,1946年,第1頁。
(49)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4),第25頁。
(50)參見饒宗頤:《編輯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及論虞幕伯鯀等附擬目》,《責善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41年9月。
(51)參見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2~139頁。
(52)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39頁。
(53)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文存》(三),合肥:黄山書社,1996年,第93頁。
(54)關于近代古史學的研究主要圍繞古史辨爲中心,相關成果集中于陳其泰、張京華主編:《古史辨學說評價討論集》,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年;文史哲編輯部編:《“疑古”與“走出疑古”》,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55)參見王汎森:《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寥平與蒙文通的例子》,《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
(56)參見楊向奎:《我們的蒙老師》,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增補本),第56頁。
(57)沅思:《近代古史研究鳥瞰》,《無錫國專季刊》,1933年。
(58)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臺北: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第2406、1997、2411頁。
(59)參見顧頡剛:《古史辨第五册·序言》,顧頡剛編著:《古史辨》(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頁。
(60)繆鳳林:《古史研究之過去與現在》(上篇),《史學雜志》第1卷第6期,1929年12月。
(61)錢基博:《孔子聖誕演說》,傅宏星編:《大家國學·錢基博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8頁。
(62)參見柳詒徵:《致教育廳長函》,《盋山牘存》,1948年,第57頁。關于柳詒徵的學術旨趣可參見李洪岩:《史術通貫經術——柳詒徵文化思想析論》,《國際儒學研究》第3輯,1997年。
(63)教育部編:《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教員研究專題概覽》,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360頁。
(64)參見丁紀:《疑古史觀及其方法評析》,《二十一世紀》,1999年8月號;張志强:《方法與宗旨之間——試論現代學術嬗變中哲學、義理學、經史之學的離合及現代佛學對其的導引》,《哲學門》第16輯,2008年。
(65)錢穆:《〈新亞學報〉發刊詞》,《新亞學報》第1期,1955年8月。
(66)姜亮夫編著:《楚辭書目五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62頁。
(67)參見童恩正:《精密的考證科學的預見——紀念蒙文通老師》,《文史雜志》1986年第1期。
(68)參見侯旭東:《中國古史三十年:成績與挑戰》,《當代學術狀况與中國思想的未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8~7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