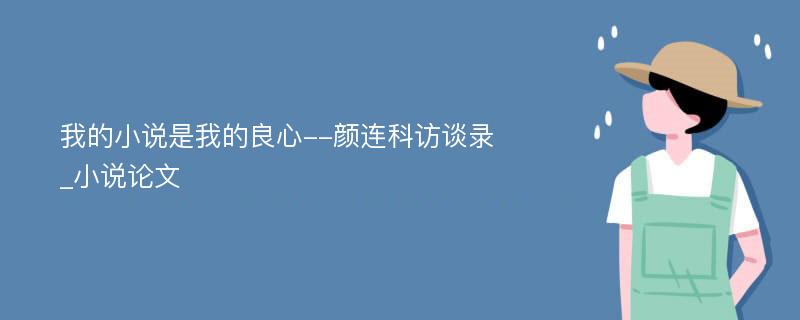
我的小说是我个人的良知——阎连科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良知论文,说是论文,阎连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新军旅小说和新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家,这些年阎连科在这两个领域中不懈地探索着 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路,他具有新潮意味的《年月日》、《黄金洞》、《大校》等中篇小 说在全国广泛地产生影响之后,他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更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小说, 是二十世纪的一部奇书力作。新近的《坚硬如水》,更让人深深觉察到阎连科坦然而珍贵的 艺术探索精神。
我不是专门写苦难的
石一龙(以下简称石):你最早发表作品是什么时候?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作品,有一种什么 样的感受?
阎连科:最早发表是在我入伍那年的下半年,即1979年8月。那是个短篇小说,写一个战士 为了入党给指导员送礼的经过,叫《天麻的故事》。现在想来,觉得特别亲切。当时作品 发表在原武汉军区《战斗报》上,有8块钱稿费,我拿出4元买糖请了全班战士的客。还有 许 多战士把那篇小说抄在笔记本上,这让我很感动,有力地鼓励了我今后的创作。
石:在你的小说中,苦难成为了一个常规视角,但也是沉痛、孤独、深重中现实的原现。 有时,你呈现给读者的似乎是悲剧的美与生的艰辛以及更多的思考,比如你的《年月日》给 我所带来的阅读痛感是无法言说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写……
阎连科:是的,有不少人认为我是专门写苦难和生存的,我觉得这种认识有失偏颇。但就 《年月日》来说,它似乎对生存有更深的透视,比如人在生存中所表现的勇气和钢性,比如 人 与自然的对抗与无奈,比如人的孤独与寂寞等等。问我为什么这样写,我觉得很难回答,只 能说我不能不这样写。从开始发表作品到1996年底创作《年月日》,16年过去了,一个人的 创 作没有变化就只能是死亡,一个人的思想没有变化就只能是死亡,而在写《年月日》之 前,如90年代初发表的中篇小说《寻找土地》、《天宫图》等,都已经和前期小说大不一样 ,在艺术追求上有着质的区别。
石:每一部作品究其根源,都有着一种经历。它也许是心头无法抹去的一种创伤吧。在你 的小说中你延续了你成长中的所有经历,首先就有你故乡耙耧山脉的经历和贫穷的经历。但 你一直在你的经历中写作,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你在城市中有了新的经历。你是不是试图 对新的经历进行抵抗和消解,不去写其他与故乡经历无关的作品,或者新的经历会以给你带 来什么呢?
阎连科: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只能用最简短的话说,我从小就崇拜三样东西:一、城 市;二、权力;三、生命,即健康,或说力量。入伍以后,生活在都市以后,这新的环境不 会 带给我任何东西,它只能加剧我对故乡的怀念,加剧我对都市的痛恨和对权力的恐惧,加剧 我对生命的热爱。
石:你在一部小说自选集序言中提出一个“土地文化”的说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地域 文 化”的另一种说法。好像都是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作注解,比如福克纳的南方小 镇、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沈从文的湘西水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还有你的耙耧山脉。给人 的感受是大作家非此不可,你认为是这样吗?
阎连科:“土地文化”不是地域文化,但土地文化包涵了地域文化。我不赞成笼统地说“ 越 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那种说法,尤其是对小说。就小说而言,中国的小说创作,再土,再 民族,你能土、民族过“山药蛋”吗?山药蛋派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小说,但我们不能说是 山药蛋派的作家就是世界级的大作家。你小说中的文化可以是民族的,或说必须是本民族的 ,但作家的思想、思考还是应立足于民族,超越于民族。可惜这个事情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至少说我想做的我却做不到。
石:近十年以来,你的中短篇小说几乎覆盖了全国的著名刊物。但比较起来,这些小说中 非军事题材似乎要多了一些。作为一个军旅作家,是否也像大多数作家一样对军事文学本身 的“局限性”有着某种顾虑,还是有别的原因。
阎连科:情况是这样。军队有他的特殊性,军事文学也就有它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不过,就军事文学而言,我觉得对军旅作家来说,最大的局限不是我们日常说的外来的“ 意识形态”,而是我们的大脑中已经形成的意识形态。别人不束缚你的创作,而是作家自己 束缚自己。还有,就是难以逃离的媚俗现象、功利主义,也是军事文学最大的局限。
关于《坚硬如水》
石:你新近的长篇小说《坚硬如水》是戏仿的,也是寓言的。可以说是第一次使之成为一 个寓言化的结构从而赋予了悲剧与喜剧双重的消解意义,构成了对它的忍俊不禁的戏弄和漫 画 化。
阎连科:我一直想写一部文革的小说,就是想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坚硬如水》写了高 爱军和夏红梅的革命与情爱史,小说的故事性很强,用文革语言把那个时代真实地表达出来 了,对文革进行了原始与野性的再现,把主人翁高爱军和夏红梅的癫狂与痴迷和对革命的高 度 崇拜及原始情欲的揉合都建立在文革的荒诞上。其实这不是一部虚构的小说,是一本现代的 小说,就不特别传统,为什么?因为文革本身的荒诞性超过你的虚构性,只要把大家的对话 、言行等写出来就行了,而且让现在的人相信,作家很容易让读者看到的确是这样的事,这 就是小说的材料。
石:引导读者一口气读完《坚硬如水》的是故事,而不是语言,能说故事在小说不占重要 地 位吗?
阎连科:对我来说,编一个好故事并不难,让故事中有奇胜的情节也不难,而难的是把这 个故事讲出来的叙述态度和方式,是叙述故事的语言。在《坚硬如水》中,正是高爱军和夏 红梅那段奇异而真实,真实而陌生的故事给了我表达那种“红色语言”的载体,而这种语言 又反过来使故事中的人物进入到人性和灵魂深邃的真实中。
石:你是长在“文革”一代的人,那种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阎连科:当然有影响,完全可以说,我的全部病根子都出自文革。我们那时老传言美国、 台湾的特务过来,说遍地都是,干这干那坏事情,全国人民都相信是真的,吓得你晚上不敢 走 路。现在想来,文革对我今天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坚硬如水》的人物和情节,许多都是 有原型的。我写这本书,就是要从人性层面上反思文革。性善性恶的问题争论了几千年,至 今没有定论,现在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人性恶的问题还是重视得不够。人一半是魔 鬼,一半是天使,恶的东西一旦有机会,就会大发作。文革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石:“耙耧”很早就已成为你的一个完整、独立、令人关注的小说世界,据说你即将开始 创作的《耙耧时空》更是一个庞大的计划,那么你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吗?
阎连科:没有什么更具体的打算。我在“后记”中说的都是实话,与其说那是庞大的计划 , 不如说那是狂妄的写作谋略,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我的心力,更取决于我的体力。我已 经42岁,外表很结实,其实是外强中干,身体毛病很多。就是说,我的写作早几年就开始力 不从心了,许多时候都在为写作无能为力而烦恼。
日光流年中写作
石:在你的所有作品里,我对《日光流年》有着特殊的偏爱,我一直认为评论界对它的重 视程度不够,评论在偏离作品本身的大气精纯。最近听说复旦大学中文系把你作为课题研究 ,感到特别兴奋,我想他们是发现了你《日光流年》的价值了。它的结构的倒着写,从主人 公之死直写到他回归母亲的子宫,我觉得有着神示的隐喻。你谈谈这部作品吧,我想知道它 是怎样写成的?
阎连科:其实,评论界对《日光流年》已经给予了很多关注,已经有了不少的评论文章, 现在这年月,写小说你还想指望什么?写《日光流年》我用了将近4年时间。大约是1994年前 后,我回河南老家,在火车上听到了两个人的谈论,说河南安阳地区村县有一片山区,那儿 的 人大都在40-60岁之间,要患上不治之症食道癌。这就是《日光流年》最直接的生活来源和 全部现实资源。至于这部作品的结构,无论研究人员如何评价,对我来说,它来的也同样简 单,有一天我在看录相带时,有一段没有看清,把带子倒回去重新放时,那倒播的画面也就 促成了《日光流年》结构的根基。
石:你的作品中人物的生命线都设定在40岁,这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阎连科: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但毫无疑问,40岁是人生中最为艰险的一道必须逾越的门槛 。就人生而言,说起来非常漫长,又非常短促,从童年、少年至青年再到结婚生子、育儿成 长,整日忙忙碌碌,不经意间,一晃就是40岁,人生的苦难和各种劫难可能都在这个年龄段 向你澎湃而来,使你不能不面对这些,不能不担当这些。
石:有人说,《日光流年》中似乎有一种巨大无比的宿命力量。不可逆转的宿命的车轮在 《日光流年》的每一页、每一个情节、细节中滚滚转动,你认为呢?
阎连科:噢,你也这么看?
石:不。《日光流年》给我感受最深的是你对生命无限的热爱,并把这种热爱倾注到对死 亡奋力抗争的描写中,这在其他作品中几乎是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我认为《日光流 年》写出了对生命之爱的巨大热情和人类生存的勇气,而并不是写生命的绝望。
阎连科:非常感谢你对《日光流年》的理解。的确,我想要表达的正是这些。我写的,实 际是一种人生在世的勇气和精神,面对生活生存的勇气精神。有人说,这部小说是写宿命的 ,我不能同意。当然每个人的看法各不相同,不同的人对作品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不可企 望一致。《日光流年》最大限度地提供了读者和评论家多角度阐释的可能,这也是我对作品 感到欣慰的一点。
石:《日光流年》中对苦难的描写,又让我大吃一惊,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阎连科:我都没有刻意地去表现苦难,我注重的是对精神,对生命的描写,或者说对人在 某种生存状态中力量的展示。贫穷不一定就有苦难,有苦难的人不一定就贫穷,有钱的人同 样也有苦难。如卖皮与卖肉这些情景完全是我虚构出来的,实际上,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 。教火院同样也是一种虚构。设计这样一些极端的情节,我觉得更能表达我的某种内心的 感受和某种思考。生命中的苦难在所难免,但那不是我着力表现的地方,也不是人类的希 望所在。而苦难中的某种精神才是我的用笔之所在。我以为,那种生存中的精神和勇气,是 人类的希望之光。正是这种精神把我们人类带到文明的今天,也将带到未来的明天。
石:你曾写过你父亲临终前,你赶回家见最后一面后,他只向你说了一句话“回来了,吃 饭去吧”。
阎连科:这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所以我总觉得,许多民间俗语说得非常深刻。如“ 人 死如灯灭”,“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等,与那些学者在书本中研究出来的哲理不同,这些 民间哲理是百姓用生命实践了生存之后总结出来的,而那些书本上关于生死的论述,则是用 知识总结出来的。
石:在《日光流年》中,人们对死亡的坦然表达了一种豁达的人生观,那么从某种意义上 来讲,也是一种对死亡无奈的顺从吗?
阎连科:前边我们已经谈了不少这类问题。杜拐子临死前对大家说,等我咽气后,让那些 孩娃都来守棺,让他们知道死没什么可怕的,人死了就是没气了。这或许是一种豁达,但决 不是无奈的顺从,在生死循环过程中,在知道自己活不到40岁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切, 如种油菜、换土、修渠引水等,都是对死亡的战斗、抗拒和奋争。他们这战斗、抗拒、奋争 的过程是失败的,而其精神是胜利的。我以为,《日光流年》中的众多人物,无论男女,他 们大多数都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人在生存过程中的楷模,生命虽止,而精神不息。生命 在年复一年中流淌,生活在日复一日中延伸,所不同的是人在生活中的支撑点不同。不论遇 到什么艰难险阻人终是要顽强地活下去,这也是我对生命的理解。
写小说最难的就是语言
石:在《日光流年》里,你的语言显得更加密集。有人说是一种“新巴洛克”式的语言, 你对此有何种看法?
阎连科:这是大家谈论得比较多的地方。对我来说,写小说最难的就是语言,这也是长期 困扰我的问题。写小说考验作家功力的就是语言,我看别人的小说也非常怪,别人都说好的 ,我一翻,语言不行就再也吸引不了我继续看下去,就扔到一边。其实,这是一种偏激,有 的小说语言不好,其他的可能很好。比如它的故事、人物、情节等。
石:在《日光流年》里,你通过语言的方式,调整了空间和时间对人的压抑,全篇40多万 字,无处不在地使用通感使无声变有声,无形变有形,无味变有味,而且语言充满狂欢气息 。这就是你追求的语言风格吗?
阎连科:我不追求这样的语言风格。我也说不清楚我要追求什么样的语言风格,但在这部 长篇里,我只能动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比如说死亡“嘭”的一声就死了,如果不是这样一 句话,我觉得这部小说就无法开头,无法来表述那种对死亡的感受。我并不期望我的小说语 言过早地形成风格。比如这篇一看是沈从文的小说,那一篇是汪曾祺的小说。虽然那些语言 我都很欣赏,但用一种一成不变的语言进行一生的写作,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也是我不甘 愿的。
石:在写作的时候,你最注重的是语言的特色和对语言的打磨吧?
阎连科:我在意语言的特色,但不主张长久不释地保持一种语言风格。比如《年月日》, 大家都以为我一定在语言上打磨了三遍、四遍、五遍。事实恰恰相反,我写行非常顺,一遍 就成了。而不是像人们猜想的那样苦心经营,反复打磨。《日光流年》也一样,我改了三稿 。主要是觉得没有必要那么长,删掉10万字,三易其稿并没有在语言进行刻意打磨。
石:在写作中,你与人物之间构成什么关系?你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
阎连科:不是人物牵着我走,是写作的那种激情牵着我。不是我展现人物,而是人物在展 现我。以后再写长篇,我会千方百计地去写得短点。一个小说的长短不在于用多少字来表达 。《百年孤独》也就二、三十万字。如果我们写就得100万字。它之所以那么短,不在它文 字、内容,而在结构方式决定了它必然那么短。
石:《日光流年》是否也给你留下了某些方面的遗憾呢?我冒昧地认为,在司马笑笑舍身唤 来乌鸦那一段写得不够展开,没有出彩。
阎连科:你说得很对,我自己也意识到了。当时写到那块时,禁不住流泪,我是伴着眼泪 写完的。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感情中。就是说非常动情,我一旦动情就会写得非常毛糙。当 时写完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出彩,没有写出来。
石:你曾经被人誉为是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的快手,但是你写作《日光流年》用了三 年时间,这是为什么呢?
阎连科:写了《黄金洞》、《年月日》、《大校》3个中篇和一些散文,我可以很欣慰地说 一句,以前那种“疯狂写作”的阶段让我很理智地打发过去了。对于写作我已经非常谨慎、 负 责了。我不会再疯狂写作了。除此之外,在写作过程中,身体不太好也是我写得较慢的原 因之一,如果身体好些,我会写得快一些,多一些。这也是一种遗憾。
石:在《日光流年》的序言中,你说出了自己写完书之后的那种被掏空的感受,那时你是 不是写得太累了?
阎连科:由于出书时,出版社要补一个序,于是就赶写了那个序。这个序写得不好,王蒙 也反对那个序。实际上,当我写那个序时,我的身体及心理等各种状态都已恢复和调整过 来了。
石:请你比较《日光流年》和《坚硬如水》的写作过程,谈谈它们各自的特点。
阎连科:《日光流年》写得很顺畅,写《坚硬如水》也很顺畅。《日光流年》结构方式比 较特殊,肯定影响了它的阅读效果。《坚硬如水》的故事性、可读性强一些,它也是一个陷 阱,对文革熟悉的人有这种经历,感觉就特别好,但过了30年、50年怎么看这部作品,我很 关心这个问题。
一天一天地生活,一点一点地写作
石:最近读到你发表的一篇文章《写作是一种日子》,你是如何看待现实生活与写作的?
阎连科:就我来说,现实生活和写作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空间。写作是一回事情,现实生活 又 是另外一回事情,如果说他们有联系的话,那么就是现实生活对我写作的支持,犹如流水对 土壤的支持和催生一样。我在生活中是要写作的,就是要过日子,是日出日落地对写作的努 力和继续,和农民不种地没有粮食,没有粮就要挨饿是一样的道理。不写作便使人觉得饥荒 ,心烦,没有着落,像吃了上一顿饭找不到下顿的米儿一样。重要的是我要能把过日子化成 写作,一日一日地写下去,如此,也就够了,满足了。现实生活中过好日子固然是一种愿望 ,但过日子才最是根本。不会过日子,就没有好的生活,我就是一天一天地生活,一点一点 地写作——除此,我还能想什么呢?
石:那么,你不认为生活是写作的惟一源泉?
阎连科:是的。生活是写作的重要源泉,但不是惟一的源泉。一般说来,某一些作家一生 都 要依赖现实生活进行写作,而另一些作家,依赖生活只是一个阶段。或者说,他所依赖的生 活只是他写作资源中的一部分,或说较为重要的一部分而已。
石:能具体谈谈你自己这方面的创作情况吗?
阎连科:我刚才说过,对我来说,生活经验、经历可能是我不可缺或的写作土壤,但想象 则必须是这种土壤中必不可少的水和阳光,没有这些水份、阳光,那土壤就是一片沙漠。反 过来说,想象是土壤的话,经验可能就是水流和阳光,没有经验的照耀和湿润,那么想象就 是一片沙漠。总之,在现阶段,我已40多岁,有了许多阅历,我的写作反而更依赖于想象, 要靠想象来激活自己生活过的经验。
石:很早以前,一位评论家曾对你以往的小说评价道:过分地粘滞于土地,与现实贴得太 近。近几年你的小说中“虚”“实”的结合,是否表明你已经开始新的思索?
阎连科:写作,是作家个人在生活与心灵之间寻找的秘密通道。我不能确定我已找到,但 我知道自己告别了以往凭生活体验单纯写感悟的阶段,开始进入超拔的想象空间的创造。这 种创造不是超越现实生活,与现实脱钩,而是对现实生活的另一种思考和沟通。如何把这种 沟通处理的更好一点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石:有人说作家是一个民族的良知,而其作品应该是这个民族的历史,你怎样解释这句话?
阎连科:这话是对大作家的要求,我不这样苛刻我自己。我只希望我的小说是我个人的良 知就行,不奢望它是一群人、一个阶层的良知和声音,更不敢奢望它是民族的什么。
石:你喜欢的外国作家有那些?你受到过谁的影响?今天回过头看你是如何反思这些影响的 。
阎连科:许多人问这个问题,我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实话说,卡夫卡名振天下,可我直 到两个月前去西安看病才把《城堡》和《审判》看完,《百年孤独》看得早一些。福克纳的 小说,最吸引我的是《熊》和《老人》,《八月之光》的开章部分的平静使我目瞪口呆。博 尔赫斯的小说我看了不少,很想从中汲取营养,但我不知道我的神经如何才能和他接通,为 此经常和博尔赫斯作品的一个主要译者、研究者进行讨论,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通往博尔赫斯 的道路在哪里。我非常喜欢日本作家德田秋声的《缩影》,看了两三遍,别人都对他的作品 并不看好。所以说,我说不清我喜欢谁,受谁的影响,我也非常害怕别人说我受谁的影响。 一个作家受另一个作家影响是很正常的事,但别人看不出受了那个作家影响才是了不起的事 。
石:你如何看待小说和传统?民间传说对你的小说创作有帮助吗?
阎连科:正好我最近写了一个短篇,写完了就觉得特别传统,有点传统得无法再传统,自 己 一看就觉得特别舒服。从语言到叙述到故事到人物都是传统的,我就发现传统居然有那么大 的魅力。而这个故事非常简单,讲的是一个小村庄的事情,但这个小说没有人物,只有几个 人找了个理由在一起吃饭,议论长议论短。突然有一个小伙子说,我喝酒时碰到有一两个人 说北京要搬到洛阳,郑州要搬到我们县,洛阳没地方放就要放到我们村里来了。说着说着有 一 个老头就死掉了,70多岁,死了还面带笑容。这个老头无儿无女,总得把他埋掉吧。村里就 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居然按国葬的形式把他葬了,降半旗,最后半旗在老头住的屋头上 飘着 。我读完就发现小说居然可以这样写,这就是小说传统的魅力吧。
我觉得传统对小说家很重要,像余华就找到了自己的传统,很多作家自己都回不到传统里 去,这是现在小说家遇到的一个难题。小说永远也离不开传统,或多或少。因为我们用汉语 写 作,可每一个汉字就是一次传统。传统是小说的生源之一。对于民间传说,我以前重视不够 ,现在非常喜欢,它会对我的小说创作产生很大影响。
石:你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阎连科:《日光流年》。
石:如果你不写作了,你最喜欢去做什么?
阎连科:将来不写作了,我就带孙子或孙女玩,让他们干什么都行,但不要写作。
石:为什么?
阎连科:写作太苦,太消耗身体。
阎连科,1958年生于河南嵩县的一个偏僻小镇,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 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为二炮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剧。曾先后获 全国、全军等小说奖20余次,系新乡土、新军旅代表性作家。
创作年表
1991年,长篇小说《情感狱》;
1992年,小说集《和平寓言》、小说集《乡间故事》
1993年,长篇小说《最后一名女知青》;
1994年,小说集《朝着天堂走》;
1995年,《阎连科文集》(五卷);
1996年,长篇小说《生死晶黄》、小说集《欢乐家园》;
1997年,长篇小说《金莲,你好》、小说集《黄金洞》。
1998年,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阎连科小说自选集》、散文集《褐色桎梏》;
1999年,小说集《朝着东南走》;
2001年,长篇小说《坚硬如水》、《日光流年》(再版)、小说集《斗鸡》、长篇小说《情 感狱》、小说集《耙耧天歌》、小说集《穿越》、《阎连科系列小说精品文集》(五卷)、散 文集《转身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