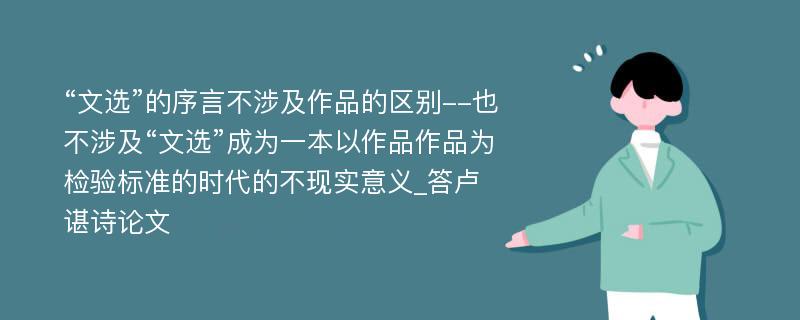
《文选序》“以时代相次”不涉及作品辨——兼论以作品之作时考《文选》成书时间无实际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作品论文,成书论文,之作论文,实际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10)03-0171-06
《文选序》在说到《文选》的编例时,有云:“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1]卷首乍一看,“以时代相次”云云,应是就《文选》所录作品本身言,或既关乎作家,又及于作品。于此,骆鸿凯先生合《文选》之实际情形于《文选序》,故云:“赋自‘京都’至‘情’凡十五类,诗自‘补亡’至‘杂拟’凡二十三类,所谓‘又以类分’也。而每类之中,文之先后,以时代为次,如赋之‘京都’类,先班孟坚,次张平子,是也。”[2]这是对的。不仅如此,即使仅就《文选序》以观《文选序》的高步瀛先生之“赋自‘京都’至‘情’凡十五类;诗自‘补亡’至‘杂拟’凡二十三类。所谓‘又以类分’也。而每类之中,文之先后,以时代为次”[3]说,似亦没有问题。因之,学者或为研究《文选》的成书时间而考察其所录作品之作年,便是十分自然的。问题是,“以时代相次”云云,其果真是就《文选》作品本身而发,或兼及作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弄清这一问题,对我们研究《文选》的成书时间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且就本人目力所及,尚未见有学者对这一问题做过专门之研究①,故今为此小文以说之。不当处,祈海内外之方家有以启之云。
一
近人何融先生,盖为考察《文选》所录作品之作年与其编撰成书关系之最早者。何先生在发表于1949年的《〈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中云:“欲知《昭明文选》编撰时期,宜从《文选》本身求之。”[4]109接着,其对包括任昉、丘迟、沈约、陆倕、刘峻、徐悱共六家的15篇“确可考知之梁代作品”以表的形式加以说明。为便于研讨,今摘其要(为方便计,更其形式)如下:
任昉的《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天监元年)、《奉答七夕诗启》(天监元年或三年)、《出传舍哭范仆射》(天监二年)、《天监三年策秀才文》(天监三年)、《奏弹曹景宗》(天监三年)、《奏弹刘整》(天监三~五年),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天监四年),沈约《应诏乐游苑钱吕僧珍诗》(天监五年),任昉的《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诗》(天监六年),陆倕的《新刻漏铭》(天监六年)、《石阙铭》(天监七年),刘峻的《广绝交论》(天监七年后)、《重答刘秣陵沼书》(天监?年),徐悱的《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天监十三年后),刘峻的《辨命论》(天监十五年后)。[4]109-111②
其本表之结论云,“《文选》中时代最晚之作品为刘竣之《辨命论》”,而“《辨命论》之作不早于天监十五年,亦即可证《文选》之编成必在天监十五年以后也”[4]111。其后,台湾学者林聪明先生承何说而表述得更为明确,其云:“欲论《昭明文选》之编成年代,可就其所录之作品及其作者考求之。盖所录作品之年代下限,当为成书年代之上限;而作者之生卒年,亦足为成书年代之重要参考资料。”[5]2“《文选》所录最晚之作,当为刘竣之《辨命论》。……则《辨命论》不早于天监十五年可知,亦可证《文选》之编成,必在天监十五年之后。”[5]5何、林两先生以《辨命论》为《文选》所录最晚之作未为得,《文选》所录时代最晚之作乃《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徐悱此诗当作于天监十八年或其后的普通一、二年,甚至更晚,且以入普通以后的可能性为大。另外,《重答刘秣陵沼书》之作时亦晚于《辨命论》[6]。此又何、林两先生之失。至于何先生此说,虽被认为“开创了从《文选》所录作品的写作时间研究《文选》成书时间的新思路”[7],不过,其能否成立,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乃《文选序》之“以时代相次”是就作品而言,或至少必须兼顾到作品本身。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这一前提是否存在,无论何先生还是其后的林先生,均没有加以考察。
当然,就考“《文选》编撰时期”说,何氏之说最终还是落实到“作家之卒时”,而非“最晚之作品”如何上的。在我们前面所引其“可证《文选》之编成必在天监十五年以后也”下面,何先生接着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窦常谓‘统著《文选》,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盖其人既往,而后其文克定,然则所录皆前人作也’”后,云:“……谓《文选》不录逊文,以其在世,虽与事实不符,然谓《文选》不录现人之作为其选文之一原则,则甚合理而可信。根据上论,则《文选》中梁代诸作家之卒时,亦(之按:“亦”当作“更”,才合逻辑)为考证《文选》编撰时期之一重要资料。……《文选》诸作家直至普通七年始尽卒,可见《文选》之编成,应不早于普通七年。”[4]111-112即为明证。此其一。
其二,就何先生本文之考《文选》的编撰时期言,其既然据作品之作时说“可证《文选》之编成必在天监十五年以后”在前,便不当再据“作家之卒时”断“可见《文选》之编成,应不早于普通七年”(“应不早于普通七年”即“应在普通七年后”)在后。反之,如果最终认定以据“作家之卒时”断“《文选》之编成,应不早于普通七年”为是,则应改前面的“可证《文选》之编成必在天监十五年以后”说就之,以免前后矛盾。而结合前面所引何先生之“《文选》不录现人之作为其选文之一原则,则甚合理而可信”说,则其“亦即可证《文选》之编成必在天监十五年以后也”云云,显而易见,实因思未密之所致。
前引林先生之“盖所录作品之年代下限,当为成书年代之上限”云云,同样疏甚。既云“《文选》所录最晚之作”,当为“不早于天监十五年”的《辨命论》[5]5,就不能同时云“考《文选》诸作家至梁武帝普通七年始尽卒(原注:“《文选》所录之作家,以陆倕为最晚。”),则书之编成,当不早于普通七年”[5]6。道理十分浅显:由于《文选》所录最晚之作的作时与其所录最晚卒者之卒时非同时,故两者中之时在后者,才有可能成为《文选》“成书年代之上限”或其“成书年代之重要参考资料”,而其时之在前者对考察《文选》成书情况如何没有实际意义。这本是常识,而研究者往往忽之。怪哉!
同样的道理,曹道衡先生之“《文选》所录作品,其作者均已逝世,而陆倕之死,在普通七年”[8],“《文选》所录的作品,不是以作者的卒年为断限,而是以天监十二年或天监末产生的作品为断限”[9]云云,似亦未达一间。既然“《文选》所录的作品,不是以作者的卒年为断限,而是以天监十二年或天监末产生的作品为断限”,何以“所录作品,其作者均已逝世”,且最晚者至“普通七年”?显而易见,“以天监十二年或天监末产生的作品为断限”云云,是难以成立的[10]。许逸民先生云:“倘以为‘普通七年之后’成书,却又把收录作品截止在天监末,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11]137的然。不过,许先生《〈文选〉编撰年代新说》之“《文选》的收录下限只取决于诗文的作年,和该作者的生卒年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文选》收录作品与作者存在世与否无涉”[11]137云云,亦有所未照[10]。如上所述,“从《文选》所录作品的写作时间研究《文选》成书时间”成立之前提,乃“以时代相次”是就《文选》所录作品言,或至少必须兼顾到其所录作品本身。然与上述之何、林两先生一样,许先生亦始终没有考察该前提是否存在。实际上,《文选》是不存在这一前提的。个中原因,下节说之。
二
由于“以时代相次”云云是就《文选》之实际情况说的,故考察其究竟如何,必须回归《文选》本身。而在这里,即仅从逻辑的层面上看,便可判断这只关乎作家而不及其作品。道理非常简单:由于《文选》“类分”后以人为纲,故无论其如何,即序作家是否“以时代相次”,都无法再使“类”内之作品“以时代相次”。而有的学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故云:“《文选》中所收作品除了按文体与内容分类外,对作家和作品是按时代顺序编排的。”[12]至于王晓东先生之“《文选序》中所说的‘各以时代相次’,并不是指按作品的创作年代先后,而是指按作家的卒年先后编次的”[13]说,则可谓得其大者矣。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下面,我们再从同“类”所录不同作家之作品与录同一作家两首以上作品这两个方面对其做具体的考察。
(一)关于同“类”所录不同作家的作品之序次情况
“以时代相次”云云,在《文选》这里,要么仅就作家言,要么仅就作品发,无论如何,两者不可兼而得之。今试举数例以证之如下。
1.卷20“诗·祖饯”,其序次为:谢幺晖(464-499)《新亭渚别范零陵诗》、沈休文(441-513)《别范安成诗》③。
按:此谢诗撰于[齐]永明十一年(493),而沈诗作于[齐]永明九年(491)。这里置玄晖于休文前,不言而喻,“以时代相次”者乃就作家言(《文选》序次作家,主要是据其卒年),而不管其作品具体写作之先后如何。
2.卷22“诗·游览”,其序次为:谢玄晖《游东田》、江文通(444-505)《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沈休文《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按:此谢诗作于[齐]永明八年(490),江诗作于[宋]泰始六年(470),沈诗成于[宋]大明五年(461)。于此,作家“以时代相次”而作品则非。否则,当先列刘宋时之作而后才排齐世之诗。易言之,在这里,“以时代相次”若就或亦就作品言,则其时代严重倒置矣;反之,其若顺朝代之先后序次作品,又势必造成颠倒作家所在之朝代。以人为纲类总集,无法在“以时代相次”作家的前提下,再使“类”内不同作家之作品“以时代相次”,于斯可以一斑见豹。
3.卷25“诗·赠答三”,其序次为:刘越石(270-318)《答卢谌诗》《重赠卢谌》,卢子谅(284-350)《赠刘琨》。
按:《答卢谌诗》之“刘越石”下,李善引王隐《晋书》曰:“段匹磾领幽州牧,(卢)谌求为匹磾别驾。谌笺诗与(刘)琨,故有此答。”[1]而房玄龄等撰的《晋书》卷44《卢谌传》云:“建兴末,随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领幽州,取谌为别驾。”[14]考“建兴”共四年,故“建兴末”即“建兴”四年(316)。而《重赠卢谌诗》作于“大兴”元年(318),为越石被害前之绝笔。又,越石与卢氏同时,然其生卒年均略前;而越石所以作《答卢谌诗》乃因回卢氏的《赠刘琨》,即《赠刘琨》作在《答卢谌诗》前。因之,《答卢谌诗》《重赠卢谌》《赠刘琨》的编排,正说明“以时代相次”无关乎作品,而是纯就作家言。
4.卷27“诗·行旅下”,其序次为:谢玄晖《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桥》……江文通《望荆山》、丘希范(464-508)《旦发鱼浦潭》、沈休文《早发定山》……
按:此谢诗作于[齐]建武二年(495),江诗作于[宋]泰始四年(468),丘诗作于[梁]天监三年(504),沈诗作于[齐]隆昌元年(494)。显而易见,如此序次仅着眼于作家时代之先后,而其各自作品作时之孰早孰晚,概不在《文选》编者考虑之域中。否则,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出现如此之乱:齐、宋、梁、齐(且后“齐”早于前“齐”)。我们知道,《文选》序次作家,亦有“失序”,然无一是造成时代倒置的[15]。“以时代相次”云云无关乎作品,此亦一显例。
5.卷40“弹事”,任彦升(460-508)《奏弹曹景宗》与《奏弹刘整》、沈休文《奏弹王源》。
按:考彦升两文之前者作于天监三年(504),后者当作于天监四(505)年或五年(506);而沈奏撰于[齐]永明八年(490)⑤。若“以时代相次”涉及作品本身,此自然亦是先《奏弹王源》而后《奏弹曹景宗》与《奏弹刘整》——时序为齐、梁而非梁、齐。今先彦升而后休文,乃因《文选序》之“以时代相次”仅就作家言,且以其卒年为准。
当然,《文选》中亦存在类卷24-25(“诗·赠答二”——“诗·赠答三”)之陆士衡(261-303)《赠冯文罴迁斥丘令》(294)、《答贾长渊》(296)、《于承明作与士龙》(296)、《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296)、《赠顾交址公真》(296)、《赠从兄车骑》(289)、《答张士然》(298-300)、《为顾彦先赠妇二首》(289)、《赠冯文罴》(294)、《赠弟士龙》(296),潘安仁(247-300)《为贾谧作赠陆机》(296),潘正叔(247-311?)《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294)、《赠河阳》(282)、《赠侍御史王元贶》(298),傅长虞(239-294)《赠何劭王济》(284),郭泰机(250?-300?)《答傅咸》(?),陆士龙(262-303年)《为顾彦先赠妇二首》(296)、《答兄机》(296)、《答张士然》(289)这样之序次④。即作品与作家之“相次”在时间上均“失序”。不过,如上所述,由于“以时代相次”不涉及作品,故其“失序”不是问题;而作家之“失序”,只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观之才是问题,然“以古还古”,这一“问题”本不是问题[15]。
(二)关于同类同作家的两首以上作品之序次情况
那么,《文选》中的同一类别的同一作家,其两篇以上作品之序次是否“以时代相次”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知道:《文选》所录作家,其作品于某“类”中二见以上者不少,尤其是“诗”之“赠答”“杂诗”等子类。今即以此二子类及“表”“启”“论”“铭”四大类为例以考察这一问题。
1.卷26“诗·赠答四”序次作家、作品为:颜延年《赠王太常》、《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直东宫答郑尚书》、《和谢监灵运》,谢玄晖《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在郡卧病呈沈尚书》、《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酬王晋安》,范彦龙《赠张徐州稷》、《古意赠王中书》。
按:此中,颜诗之作年分别为[宋]孝建三年(456)、[宋]元嘉十四(437)至十七年(440)、[宋]永初元年(420)、[宋]元嘉三年(426),谢诗分别作于[齐]建武二年(495)、建武三年(496)、永明十一年(493)与延兴元年(494),范诗之前者作于[齐]建武二年(495)、后者成于[齐]永明六年(488)前后。据此可证:《文选》即使于同一作家之作品,其序次亦非“以时代相次”,而是十分随意的。
2.卷26“诗·行旅上”录陶渊明两首诗,其分别为《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按:两诗分别作于[晋]元兴三年(404)与隆安五年(401)。关于前者,李善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1]房玄龄等撰的《晋书》卷10《安帝纪》云:“(元兴三年三月)壬戌,桓玄司徒王谧推刘裕行镇军将军、徐州刺史……”[14]陶渊明始作刘裕的参军,即在本年⑥。关于后者,以甲子推算即可知。昭明太子编过《陶渊明集》,其序是集有云:“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搜校,粗为区目。……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16]而据此推测,昭明太子对渊明作品的写作情况应是很了解的。故此处之“失序”,当为其随便之结果。
3.卷30“诗·杂诗下”序次为:陶渊明《杂诗二首》、《咏贫士诗》、《读山海经诗》,沈休文《和谢宣城》、《应王中丞思远咏月》、《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学省愁卧》……
按:此中,陶诗之作年分别为[晋]义熙十三年(417)、[宋]元嘉元年(424)、[晋]义熙二年(406),沈诗之作年分别为[齐]建武三年(496)、[齐]建武元年(494)、[齐]永明十年(492)、[齐]隆昌元年(494)。可见,“类分之中”,《文选》对同一作家的作品之处置十分随意,即使颠倒朝代,亦非问题。
4.卷38“表下”与卷39“启”共录任彦升八文,其序次分别为《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为萧扬州荐士表》、《为褚谘议蓁让代兄袭封表》、《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五文与《奉答敕示七夕诗启》、《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启萧太傅固辞夺礼》三文。
按:其前后者之作时分别为[齐]延兴元年(494)、[梁]天监元年(502)、[齐]建武四年(497)、[齐]永明六年(488)、[齐]建武三年(496),[梁]天监元年(502)、[齐]永明元年(483)至永元二年(500)、[齐]延兴元年(494)。《文选》序次同一作家的作品之随意,于斯亦可概见。
5.卷54-55“论”与卷56“铭”分别录刘孝标与陆佐公各丽文,其序次分别为《辨命论》、《广绝交论》与《石阙铭》、《新刻漏铭》。
按:何先生考佐公《石阙铭》、《新刻漏铭》及孝标《辨命论》之作时分别为“天监七年”(508)、“天监六年”(507)与“天监十五年后”(516后),均没有问题。不过,孝标《广绝交论》当作于天监九年后(“天监九年[510]冬或天监十年[511]冬”),故其《广绝交论》作于“天监七年后”说,未达一间也。何先生之失,乃因“忽略了任昉‘诸孤’在守丧期间是不可能‘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的这么一个细节”,而这一细节“对考本论写作时间至关重要”[6]。此其一。其二,刘之二论与陆之二铭均先后倒置,不言而喻,此亦“以时代相次”不及《文选》作品之一力证。
《文选》中之类此者尚多,然据上面所举之例,已足以证明即使是同一作家,其作品之处置亦是十分随意的,而断非有意识之“以时代相次”,故兹不复说之。
或曰:此乃昭明太子弄不清这些作品的作年之所致。应之曰:非也。如《文选》次刘孝标《辨命论》、《广绝交论》与陆佐公《石阙铭》、《新刻漏铭》而“失序”,便是极好的证明。其果真连这些“当代作品”的作年都不知道(个别作品,另当别论),何以能弄不清楚“近代”以至“古代”作品之作年?而既然昭明太子对所选的各时代之作品多不知其写作年代,又怎么会说“以时代相次”呢?因之,不管从哪一层面上说,“以时代相次”者,均仅关乎作家,而不涉及其作品。这是我们研究《文选》的成书时间时,尤当知之者。明此,便知考察《文选》所录作品之作年与了解其编撰成书关系如何无实际之价值。
另外,我们知道:不管怎么随便地将不同作家的若干作品与同一作家的若干作品放在一起,其都会有部分与“以时代相次”说吻合。如将某“类”中的四位作家之各一首作品或某一作家之四首作品随便编排,其于“以时代相次”合与不合的概率分别为25%与75%;将某“类”中的两位作家之各一首作品或某一作家之二首作品随意编排,其如此之合与不合的概率均为50%,等等。因之,尽管上述两个方面的作品序次均存在与“以时代相次”相合的情况,然了解《文选序》之“以时代相次”是否就《文选》所录作品本身言,与其考察其“合”,不如考察其“不合”。即“合”者不能说明其“是”,而“不合”者却可证明其“非”。学者或未明个中道理,故据《文选》作品排列之合时序者断昭明“以时代相次”次之,而认为其不合此者为昭明之这方面之疏失。此可谓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结语
综上所述,《文选序》“以时代相次”云云,是就《文选》之实际情况说的。故考察此编序原则所指如何,必须回归《文选》本身。《文选》“类分”后以人为纲,故“以时代相次”的编序原则只能是就作家言而非关其作品。因之,(一)据《文选》所录作品之作年如何以探讨其成书时间,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二)“《文选》的收录下限只取决于诗文的作年”说,断不能成立;(三)高步瀛先生以“每类之中,文之先后,以时代为次”释“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实未达一间。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之“(《文选》)全编中所有的文体和类别都按作品的时代先后排列顺序”[17]说,亦然;而海峡两岸相关学者同于高先生说者众。另外,某些学者据《文选》编排作品存在着不合于“以时代相次”的编序原则,而断其仓促成书,同样显非圆照。
收稿日期:2010-01-10
注释:
① 李大明先生《〈文选〉编诗“以时代相次”考辨》(载四川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编《高校编辑出版工作论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一文以昭明太子编诗是否做到“以时代相次”为研讨的重点,且非探讨“以时代相次”是就作家言还是就作品言的问题。
② 关于任昉等六家的这15篇梁代作品之作年,我们后面将论及的林聪明先生除定《重答刘秣陵沼书》“作于天监初”外,全同何先生此说。
③ 有关谢朓作品之作时,主要参考陈庆元《谢朓诗歌系年》(载《文史》第21辑),曹融南《谢朓事迹诗文系年》(载《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上册,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沈约作品之作时,主要参考铃木虎雄《沈约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侯云龙《沈约年谱》(载《松辽学刊》2001年第1期);江淹作品之作时,据丁福林《江淹年谱》(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任昉作品之作时,主要参考熊清元《任昉诗文系年考证》(载《黄冈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颜延年作品之作时,主要参考缪钺《颜之推年谱》(载《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韩晖《〈文选〉编辑及作品系年考证》(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丘迟、范彦龙作品之作时,主要参考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与韩晖《〈文选〉编辑及作品系年考证》。又,此中个别作品如谢玄晖《游东田》、沈休文《学省愁卧》等之系年存在着不同看法,然这不影响我们的结论,故兹不辨之,以免过于枝蔓。
④ 据《梁书》之“(天监)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围刺史蔡道恭。时魏攻日苦,城中负板而汲,景宗望门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陷,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卷9《曹景宗传》)与“(天监)三年,魏围司州……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众赴援,景宗到凿岘,顿兵不前。至八月,城内粮尽,乃陷”(卷10《蔡道恭传》)说,知《奏弹曹景宗》作于天监三年八月或稍后;《奏弹刘整》中之“‘今年’当是天监四年或五年”(参熊清元《任昉诗文系年考证》)。至于《奏弹王源》,据李善于“沈休文”下引吴均《齐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约为中丞。”知其当即作于“永明八年”。又,铃木虎雄《沈约年谱》亦系之于是年(第28页)。
⑤ 这里的作品之作时,主要参考韩晖《〈文选〉编辑及作品系年考证》。
⑥ 参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晋安帝元兴三年甲晨”条,《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上册。又,后面引卷30“诗·杂诗下”之陶诗的系年,参韩晖《〈文诜〉编辑及作品系年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