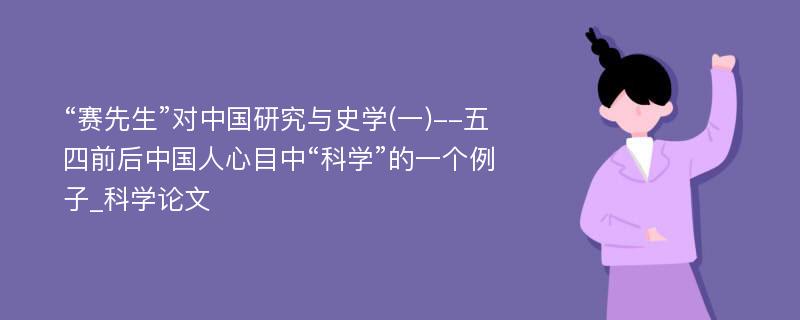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之一)——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心目中论文,国学论文,一例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赛先生”是五四人标举的两大口号之一,与我们今日将“科技”合起来讲迥然不同的是,当时人讲“科学”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往往提高到“文明”层次。我们今日说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数理化一类学科;但五四人更注意的是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而且这些“精神”和“方法”其实多来自生物进化论(对多数人来说恐怕意味着严复版的“天演论”而已),又渐成为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其与“格致”一线之自然科学的关联反而是相对松散的。本来“科学”的概念在西方和近代中国都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量,大体言之,可以说五四人意识中的“科学”与我们今日所说的“科学”有相当的距离。(注:关于五四人的科学观,参见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而且,时人对“科学”角色的认知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实有区别:科学在欧洲仍像早年传教士所引导的那样与“物质”相连而常常落实在“技术”之上;但在中国则更多体现为“精神”,在实践层面更首先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以及史学的“方法”之上。造成这样一种异地两歧式认知的原因甚多,只能另文讨论,但理解时人这样的科学观则有助于我们认识五四后“赛先生”何以会走向国学和史学这一特殊现象。本文不拟论述从整理国故到古史辨和社会史研究这些重大学术“事件”的具体学术内容,仅针对这些当年的学术大事与“科学”的关联进行侧重于发展脉络的初步考察,大致是一种介乎思想史和学术史之间的探索。
一、“科学”与近代中国的学与术
五四人之所以特别注重“德先生”与“赛先生”,在思想上是前有渊源的。康有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曾广游欧美诸国,他当时就注意到中国“文明之本皆具,自由平等之实久得,但于物质民权二者少缺耳。但知所缺在物质民权,则急急补此二者可也。妄人昧昧,不察本末,乃妄引法国夙昔半开野蛮之俗、压制苛暴之政以自比,而亦用法国革命自由之方药以医之。安平无忧而服鸩自毒,强健无病而引刀自割;在己则为丧心病狂,从人是庸医杀人。”(注:康有为著、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列国游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康口中的民权即今所谓民主,而他那时所谓的“物质”,实际多指“物质学”,即后之所谓科学也。(注:可参考康有为当时著的《物质救国论》,此书至1919年始由上海长兴书局出版。)这应该是较早将此二者连在一起视为中国最缺少而急需补救者,可以说开新文化运动的先河。(注:康有为此说主要是针对当时开始流行的“自由”和“革命”的观念,他主张中国只需引进民主而不需自由。这个主张是否合乎当时中国的国情暂不论,西学有限的康有为能看出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与自由的大区别,说明他的观察力确实相当敏锐。惟彼时中国“野蛮”已成众口皆出的共论,所以在一般人看来针对野蛮的自由观念正适合于中国,有此想法的又岂止“妄人”而已。但后来的新文化人却相对忽略了自由与民主的重大区别,新文化运动早期得到提倡的个性和人的解放很快就为团体倾向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冲淡,正因为前者其实与自由的关联更密切,而后者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民主所包容。所以新文化人在具体主张上虽然与康有为大不相同,其标志性的口号在思路上却继承了康。这方面的问题牵涉甚宽,只能另文探讨了。)
说到物质和物质学,就牵涉到晚清思想言说中一个持续而重要的论题,即“力”与“学”之间的紧张及“学”与“术”孰轻孰重的问题。古代中国关于“学”与“术”概念的区别,朱维铮先生概括为“学贵探索,术重实用”,后来或因“术”渐同于君王南面之术而曾引起乾嘉学者试图区分“学”与“政”的努力。(注: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这里所指出的“术”与“政”的渊源的确重要,这一关联曾引起晚清士人的困扰,而“政”在晚清其实也一度继承了“术重实用”的特点。 梁启超在其1896年著的《西学书目表序例》里便将西学分为“学”与“政”两大类(另有“教”一类不计),今日属于“理科”的各学科多归入“学”,而“政”则不仅有接近朱先生所谓“统治术”的史志、官制、学制、法律一类,还包括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实用”科目。(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23页。)
这里的船政、矿政等,其实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科技”那后一半,显然是传承了“术”的早期含义。“政”的这种跨越今日所谓文科和工科的宽广包容性显然与后来逐渐为中国人接受的西学分类不甚相合,所以后来“工科”的那一部分渐被“艺学”取代,在张之洞的《劝学篇》里,“西学”便有“西政”和“西艺”的明确区分,此后“西政”才逐渐落实在西方制度之上(但仍不时包括今日涉及“管理”一类的学科,与后来确立的“政治学”一科尚有较大区别),而同时“术”已基本和“学”连在一起使用(如麦梦华编的《经世文新编》便有“学术”一目)。这一学术史的演变相当曲折复杂,只能另文细考,但五四人正是在这样的学统之下思考和认识问题。
虽然有不少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实用,其实中国人轻术(实用)而重学(探索)有长期的传统(这与儒家所说的道、器关系也极有关联)。上古似乎是学与术不分的,如《大戴记·夏小正》和《小戴记·月令》用今天的眼光看更多只是与农事相关的“术”而已,却包括在儒家典籍之中。又如司马迁所述的“九流”中包括的“农家”,即将持此观念的社群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因其与“立国”之道有关,也可视为一种政治主张。现在可以看到的先秦农家学说几乎不及具体的农技,或也可以认为与后来四部中讲务农书籍者并非一类,但我们不能因不知而断其为不有。记载后世撰务农书籍者与先秦农家的关系或类似道教与道家的关系,若严格区分虽可视为不全相同的两种观念,其间毕竟有切不断的内在关联:先秦“重农”学派既然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能不涉及怎样生活的技艺,其书或不过或因为轻术重学的传统及其他原因而失传,也有可能其技艺根本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但得以流传只是非实用的内容,提示着若非最初记载者注重的是其义理而非务农的技艺,就是后世选择传承者有此倾向。
到学与术分之后,重义理轻技艺的倾向就演变为凡是“术”都力图使之上升到“学”的层次这样一种思路。如《隋书·经籍志》始列入的《齐民要术》,虽多讲技艺,却悬“齐民”为鹄的,欲将技艺提高到义理层次的精神是非常明确的(此仅大体言之,详细的叙述还需要专门考证后再论)。更明显的可在书籍四部分类的“子部”中看到,汉代刘歆的《七略》中除《辑略》为总论外,余六略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到魏晋时兴起的四部分类,则兵书、数术、方技等皆合入诸子一部。这当然可能是社会转变导致某些行业或社群的衰落因而相关门类的书籍减少所致(正如《史记》和《汉书》都有的《游侠传》到《后汉书》即无),其实也可能不过是官家藏书中此类书籍流失太多所致,但仍不失原来即有的强调某一流派的义理而非实际操作方法的观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序》说:“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也”;农、兵、医等能列入重在“立说”的诸子之中,正与五四人从科学中多见其“精神”相类,后者很可能正是脉承了前者的思路。
正由于重学轻术这一传统的持续存在,从晚清开始中国士人要想将重心从“学”或“理”转移到具体的“术”或“力”之上便至感困难,而要反其道而行之则相对容易。近代学西方从制造到政制再到文化的转变(仅大体言之),每次都不那么困难,而反对转变者则多从别的方面立论,说制造尚未完成不宜转移注意力者便少得多(也有,如王先谦)。这应该与道咸时“新学”更重义理的倾向有所关联,两者的合力更强化了关注“精神”甚于“物质”或“技术”的倾向。
然而,近代中国在每一次中外冲突中的失败都或隐或显地增强了注重物质一边的言说的力量,本受今文经学影响的康有为一面要保“教”,一面又非常强调“力”或“物质”的作用,相当特别,显然与时代语境的严重刺激相关。康的弟子梁启超1896年说:“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智又“开于学”。(注: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4页。)稍后张之洞也主张“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注:张之洞:《劝学篇·益智》,《张文襄公全集》(四),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566页。)。张说实本梁说, 至少两人已具共识。这里的关键是胜败之分在力,故虽以“学”为最初本源,最后却必须表现在“力”上面。
其实,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与重国甚于重民的倾向以及欧化更急于保持国粹的倾向是共同的,都是晚清强调“富强”这一思路的自然发展,也就是先在力的层面实行国争,然后再说其他不迟。康有为指出:“昔者民权发轫,其重在民;今者国争,其重在国”。而“方今国争,吾中国所逊人者最在物质。儒生高蹈空谈,皆拱手雅步而耻工作,乃以匠事付之粗人。岂知今日物质竞争,虽至浅之薄物末技,皆经化光电重图算诸学而来,非不学之人所能预;而乃一切薄之不为,故全国皆无制作之精品,何况有创出之新奇哉!”(注:康有为:《列国游记》, 第149、264页。)说中国读书人善动口不动手本是传教士的口头禅, 大致也符合事实,但同样的叙述出自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领袖,意义就大不相同了。
类似的观念复因大量日本留学生也具同感而增强。王先谦在研究日本近代史时发现,当初日本在西力冲击下“捐弃故技,师法泰西”的过程中,对于是否“举一国之政,而惟外邦之从”,特别是怎样学西方,也曾有内部的争论。但因甲午战胜中国,得到战争赔款,于是“彼国之士气咸伸,而更新之机势大顺”。(注:王先谦:《日本源流考序》,《虚受堂文集》卷6,1932年葵园四种版,页26A—27A。 )此说极有所见,盖谓日本的内部问题已导致学西方之改革是否正确的疑问,后因战胜中国而获得肯定的解答。若进而言之,则正因为西式改革的正当性得自对外战争,就同时提高了对外征战的地位,从而隐伏了走向军国主义之路。这样一种重“力”的倾向当然会影响到甲午后大量涌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战败国的留学生接受此思想后必然寄希望于复仇,则因重“力”而军事强大后必转而反诸其“师”,这恐又非日本人始料所及)。
在这样的语境下,五四人专强调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真是个异数,这与民国最初几年实行西式宪政不甚成功故进而欲学西方文化直接相关(注: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同时也远承了古代重学轻术的传统。那时梁启超讲科学就注重其“精神”,且落实在方法之上,即“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但他同时也在关注科学与艺术、文化的关系,到1923 年1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明确指出:西方人讲人生也用科学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只能“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梁同时也不认为西方的形而上学的方法适于研究人生,他主张“文献的学问”可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而“德性的学问”则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注:梁启超:《美术与科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7—12页;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3、110—117页。)
将西学区别看待固然表明中国学人对西方学术和思想的了解已较前深入,但同时也是针对那时中国思想界关于“科学”的讨论。陈独秀在1920年春曾说:“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也〕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他主张,“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从陈独秀的话看,自然科学的威权在中国早已树立,社会科学却不然,所以他那时说到“赛先生”往往特别关注其所谓的“社会科学”。由于陈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思想界(包括支持和反对者)的注意力也开始向此方向倾斜。当时另一个鼓吹科学而影响巨大的人物胡适正提倡整理国故,熊十力后来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但提倡之效,似仅及于考核之业。”结果是“六经四子几投厕所,或则当做考古资料而玩弄之”。(注:熊十力:《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并为林宰平先生祝嘏》,《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第28—30页。)这与前引梁启超将学问区分为“客观的”和“德性的”两种所关注的相同,即担心现代“学术”的专门化使“学”失去了原有的教化作用,学术即学术,也仅仅是学术,不再与“作人”有多少关联了。但熊一则曰“考核”,再则曰“考古资料”,实看到了当时“科学方法”的真正走向,即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多落实在整理国故之上。
二、科学怎样走向整理国故
创造社的郑伯奇1924年说:“新思想与白话文学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随声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的亦颇不少。”(注: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创造周报》第35号,1924年1月6日,第6页。)伍启元后来也观察到,文学革命运动后, 其领袖人物“不是努力于创作和翻译新文学,就是回头向所谓‘国学’方面去努力”。胡适用实验主义整理国故,“同时梁启超氏等(如研究系的一班人)和许多国文教师和许多学者,都舍弃了其他的事业而钻到旧纸堆里”,于是“所谓整理国故运动就这样兴起来”。(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57页。)本来新文化运动是以反传统著称于世的,为什么会在短期内出现这样的转折呢?这里原因甚多,而其中一个即是体现在具体治学方法上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衔接问题。
王先谦在戊戌维新时已说:“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注:王先谦:《复毕永年》,《虚受堂书札》卷1,页34A—B。 )王氏能知西学比中学更“繁重”,显然是下了点功夫了解西学的。他看出那时旧派反新部分也因西学繁重而思回避,尤有识见。在西学之内,又如严复稍后所说:“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注:严复:《论教育书》,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 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13页。)西学比中学难, 而理化等“科学”尤难逐渐成为清季许多士人的共识。
那时留日学生观察到的西学东渐的过程是:“其始也,西国之科学既稍稍输入;其继也,西国之文学更益益发见”。这样一种“今日之学由西向东”的趋势本来可能导致“支那文学科学之大革命”,但可惜中国士夫“其始以为天下之学尽在中国,而他国非其伦也;其继以为我得形上之学,彼得形下之学,而优劣非其比也;其后知己国既无文学更无科学,然既畏其科学之难,而欲就其文学之易,而不知文学科学固无所谓难易也”。且不论文学是否真的就更“易”,但可知“科学难”确是时人的共识。关键在于,“以今日之学言之,则欧美实世界之母也”。(注:《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第413—414页。)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 大体即今人所说的文科。既然西学已成“世界之学”,而科学又更难,最佳者莫过于口称科学而实际从事(西式的)“文学”,这正是后来新文化运动之师生两辈人中许多人的取径(虽然未必是有意识的)。
胡适标举的杜威实验主义的吸引人处也正在此,杜威曾说自由主义即把科学的思想习惯运用于社会事务之中,胡适恰最提倡此点。(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7页。)当科学由具体的数理化转化为相对抽象的“思想”甚至“方法”后,人们就可以不必实际从事那较难的“科学”,只须运用此“思想”或“方法”于其所熟悉之学问,即可同属至尊之“科学”。因此,当最早系统论述“整理国故”的北大新派学生毛子水提出“世界上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时,胡适马上指出:“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注:胡适:《论国故学》,《胡适文存》第2卷, 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第286页。)学者仍操故技, 实不过转变态度(具体方法上当然也有变化),居然大家都“科学”且不甚难,又何乐而不为。可以说,理化等“科学”的难是科学走向原属“文学”的国学和史学的一个潜在原因。
不论国学与史学,对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大多数中国学者而言,其方法也就是传统的考据方法。我在讨论“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时已说到,考据是否科学方法虽只是那次论战中的一个支题,对胡适、丁文江和张东荪这些当时的一流学人来说,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张东荪最看重科学的西来性质,他认为“科学当然是Science的译语”, 所以中国汉学家的方法不可能是科学方法。但对胡适来说,这里正意味着中西间是否平等的问题;前引他对毛子水所说的“学问平等”,针对的即是“世界学术”。西方人尽可去发现恒星,中国人也可去发明字的古义,只不过是同一科学精神的不同运用而已。既然同是科学发明,则整理国故即进行“科学”事业,这或者即是胡适终其身都在进行考据的一个原因吧。(注:说详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而张东荪在十年后仍重提旧议,再驳考据是科学方法之论(详后);他在那么长的时间后仍在关注和强调这一问题,说明当时学人对此相当重视。
近代“科学”概念进入中国本经历了一个以西方分类为基准的“分科之学”的阶段(注: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汪晖《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 《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225页。),而史学毕竟是西学中既存的一个学科,其与“科学”的距离还比较近,而同样与考据关联密切的“国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后,国学究竟算不算一门学问曾引起持续的争论。不过,国学的学术认同之所以产生问题,主要还是其与“中学”的继承关系所致,部分也因其与当时学人心目中西学的分类体系不甚相合有关(这个问题将另文探讨)。基本上,只要考据是科学的,运用这一考据的国学也好、史学也好,都应该是“科学”。这是一个关键。所以在国学早已淡出学术舞台或者移位到史学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关于考据的争论仍在继续。
反对考据的大致属于偏旧的或趋新而不居主流者,但对于整理国故,则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也有非常不同的看法。陈独秀在1920年春曾主张,一切有关社会人事的学问,“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而“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所以他那时显然是支持“整理国故”的,且其对科学方法的认识也与后来不甚相同;陈在文中引用了杜威关于现代的三个哲学家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演讲,说“前两个是把哲学建设在心理学上面,后一个是把哲学建设在数学上面,没有一个不采用科学方法的”。(注:本段与下段参见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新青年》第7卷第5号。)到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时, 新文化人便都不太承认柏格森的哲学是科学的了。
陈独秀在1920年虽然大体赞同整理国故,但也注意到“现在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重哲学;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对于东方文化,“西洋人也许有几位别致的古董先生怀着好奇心要倾向他;也许有些圆通的人拿这话来应酬东方的土政客,以为他们只听得懂这些话;也许有些人故意这样说来迎合一般朽人底心理;但是主张新文化运动底青年,万万不可为此呓语所误。”很可能即因这方面的忧虑,他到1923年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已转变,认为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是“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徒然“自寻烦恼”。(注:陈独秀:《国学》,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17页。)
国故与“东方文化”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陈氏有此转变也可以说是渊源有自。同时这与那时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以及1923年《小说月报》刊发的一组“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专题讨论也有关联。《小说月报》的编者郑振铎在按语中说,“这个讨论的发端,是由几个朋友引起的。他们对于现在提倡国故的举动,很抱杞忧,他们以为这是加于新文学的一种反动。在这种谈话里,我们便常常发生辩论。究竟整理国故对于新文学运动有什么影响呢?到底是反动不是呢?抱这种同样怀疑,想必不少。所以我们便在此地把我们的辩论写在纸上公开了。”但实际上持反对论调的人“都未曾把他们的意见写下来。所以此地所发表的大概都是偏于主张国故的整理对于新文学运动很有利益一方面的论调”。(注:《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年1月,第1页。)
郑氏未说这些认为整理国故是走向新文学运动的反面者究竟是哪些人,但公开发表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吴稚晖便主张将国故“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吴氏把国故看成“世界一种古董”,古董是应该保全的,不过“各国最高学院应该抽几个古董高等学者出来作不断的整理,这如何还可以化青年脑力”呢?(注: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页。)换言之, 少数人不妨做的事不应引导多数青年去做,或至少不应在还不能“用机关枪对打”的眼前阶段提倡青年去做。
当时在美国读书的前北大学生罗家伦认为:“国内许多人认为科学方法就是那种‘整理国故’方法可以代表”,其实后者只是前者“很小的部分”,实不足“代表科学方法”。(注:罗家伦:《科学与玄学》,《罗家伦先生文存》第3册,台北,“国史馆”、国民党党史会1976年版,第243页。 )前引张东荪后来的观念其实与罗家伦此时的看法差不多。 当年《新潮》派的另一主将傅斯年也对整理国故甚有保留, 他在1927年回忆说:“五年前在欧时,见到中国之大兴国学、大谈其所谓文化,思著一小书,姑名为‘斯文扫地论’,其中章四:一、绝国故,二、废哲学,三、放文人,四、存野化。”(注:《朱家骅、傅斯年致李石曾、吴稚晖书》(1927年5月16日),《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01页。 )这一“斯文扫地论”的前两章皆直接针对傅非常尊敬的老师胡适,大概是终于未写的原因之一,但很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学生一辈中反对整理国故者还不少。
但傅、罗那时皆在国外,与国内的“国学运动”或有些脱节。身处国内的顾颉刚则积极参与了整理国故,并到1926年仍在反对“我们应当研究科学,不应当研究国学,因为国学是腐败的,它是葬送青年生命的陷阱”的观点。盖“所谓科学,并不在它的本质,而在它的方法。它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科学的材料是无所不包的,上自星辰,下至河海,变幻如人心,污秽如屎溺,没有不可加以科学的研究。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如其是用了科学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可与科学对立的东西。倘使科学不是腐败的,国学也决不会腐败;倘使科学不是葬送青年生命的,国学也决不会葬送青年生命。”他继承胡适当年的观点说,要研究科学,“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的”。(注: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第3页。)
尽管当时许多学人不承认国学是“学”(详另文),但真正落实在具体治学之上时,学者们又发现比较有成就的还正是国学,也只有国学。顾颉刚就注意到“别的科学不发达而惟有国学发达”的现象。他认为这是因为“国学方面的材料是极丰富的,就是手头没有,要去搜集也不甚困难;加以从前人的研究的范围又极窄隘,留下许多未发的富源;现在用了新的眼光去看,真不知道可以开辟出多少新天地来,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凡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土地,在初施种植的时候,很容易得到极好的收获。我们在这新天地中从事研究,得到的成绩的可观是不足奇的……别的科学不发达而惟有国学发达,足见国学方面还有几个肯努力的人,还有几个具有革新的勇气而精神不受腐化的人。”(注:《一九二六年始刊词》,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第10页。)
其实,别的科学不是更属未开发的“新天地”吗?国学之所以独有成绩,即因学术积累深厚,学者轻车熟路,才使“新眼光”有用武之地。缺乏积累和训练的别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便有再新的眼光也无大用。时人虽然尊西,但若换一个纯西学的什么题目,便无多少人能做(如当时各种“科学”中地质学可能是中国最接近世界水平者,且基本以中国范围的地质为研究对象而不存在认同问题,但受过系统训练的人太少,其中不少且先后为官,终未能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明确将国学定义为“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但他又说北大国学门“并不是(也不能)要包办国学的。我们需求于别种科学的专门人才之处真是非常的多”。实际上,“别种科学不发达时,国学方面也要因为没有帮助而不得十分进展的,所以我们酷望别种科学的兴起”。如果各种科学都发达,“中国方面的各科的材料都有人去研究,那么我们的范围就可缩小,我们就可纯粹研究狭义的历史,不必用这模糊不清的‘国学’二字做我们的标名,就可以老实写做‘中国历史学门’了(要放大一点,可以称‘东方历史’,或单称‘历史’,都无不可)”。(注:《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第9—10页。)
研究“中国方面的各科的材料”是否也算国学?史学之外的“别种科学”与国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顾先生在这里说得不甚明晰。不过根据他1924年的看法,20世纪初兴起的新式国学共有五大派,分别是考古学、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地质学、学术史、民俗学,则可知他在此文中提及的“别种科学”也多半都包括在国学之内。所以他一则说“我们看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科学中的一部分”;再则说“整理国故,即是整理本国的文化史,即是做世界史中的一部分的研究”。(注:《顾颉刚致殷履安》(1924年7月5日),承顾潮女士提供抄件,特此致谢。该信论学内容十分重要,已部分录在顾潮主编:《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6—97页;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第11页。 按顾先生关于中国的文化史是“世界史中的一部分”这一观念也非常值得注意,这是他那时一贯的看法,他在1922年已说:“我们虽是做的中国史,也必使他在世界史中得到相当的关系和位置”(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教育杂志》第14卷第4号,1922年4 月, 第19661页)。1926 年他给丁文江的信中再次表示要“在世界的古史中认识中国的古史”(原件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丁文江档案”,承杜正胜所长惠允使用)。“世界史”对近代中国治史者的影响还可深入探索,王先谦就是读了外国史才对《山海经》所述上古史事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王先谦:《外国通鉴序》,《虚受堂文集》卷3,页49)。 吴宓年谱中曾记述陈寅恪初到哈佛大学,即广购多卷本剑桥通史,自称“我今学习世界史”。余英时先生已注意到这一早年经历与陈治史取向的形成和转变的关系(参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增订新版,第343页)。 而一向被认为是多得传统蜀学真义的蒙文通先生也说,他写其成名作《古史甄微》时,“就靠〔少年〕读书时学过些西洋史,知道点罗马、希腊、印度的古代文明,知道他们在地理、民族、文化上都不相同,从这里受到启发”(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页)。)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顾先生看来,史学其实是国学最基本的成分。
也许即因为国学与史学在很大程度上的重合,在整理国故兴盛之时,中国的史学反一度有被掩盖的趋势,至少不为趋新士人所看重。留学美国的孔繁霱注意到,“近年以来,我国士子留学海外者,稍知人生学科之重要。政治学也、经济学也、社会学也、心理学也、哲学也,问津者渐渐有人。惟专治史学者,则全美不三数人”。这正因为“新文化运动中,谈经济学、谈社会学、谈哲学、谈文学,莫不风靡一时,而亦绝少谈史学者”。还留在史学领域的“抱残守缺之老宿,又多墨守麟经褒贬之旧义,欲以邃古之史法治二十世纪之史事;极其量不过史料之加增,万不能显史的真精神真作用。”(注:孔繁霱:《与梁启超讨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改造》第4卷第8号,1922年4月,第1页。)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五四前后的留学生不仅专治史学的甚少,像罗家伦这样原本习史学的回国后也未曾长期留在史学领域,在后来中国史学界享盛名的陈寅恪、傅斯年以及何炳松等,反皆非史学专业出身(很明显的对比是20世纪30—40年代的下一辈留学生则多是学历史者回来也治史学)。其实不仅是留学生,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人文组史学一门当选的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不论新旧,无一是学历史出身的(其余提名的各位也极少出身史学),反而除傅斯年外皆与各校国学机构有关。这最能说明史学在那时的学科认同仍然混淆,所以学者们可以较随意地进出,而进入者又多与国学有密切的联系。(注: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学术分科在中国的确立相关(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但更重要的则与中西学术科目的衔接有关,若纯西学的科目则当选者多为受专业训练者(如哲学类除吴稚晖因与胡适等人的特殊关系滥竽充数外,余多科班出身)。)
实际上,从整理国故的开始阶段起,所谓国学或国故学从取向到具体研究题目等都一直就与史学密不可分。胡适提出:“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他认为:“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这就叫做“专史式的整理”。胡适并自述他“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一个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注: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第685页;《〈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第1卷, 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10—12页。)前述顾颉刚对国学的定义应该便是本胡适此说。
研究任何题目都应“从历史方面着手”是胡适留学时西方流行的一个重要观念,李弘祺先生据西人研究指出,“发展”(development )这一概念是19世纪西方思想史上一个极重要的突破,既然所有的人事现象都是依时间发展的结果,了解人与事就必须了解其历史。(注:李弘祺:《泛论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意义》,《读史的乐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88页。)问题在于, 若人与事皆自有其发展的历史,便会因此产生某种独特性,这与五四人最欣赏也最提倡的“世界性”是相当对立的。换言之,顾颉刚提倡的“从世界的古史中认识中国的古史”与“整理国故即是整理本国的文化史”两者之间其实潜存着一定程度的紧张(注:更广义地说,胡适最强调的“历史的眼光”(这是他从杜威那里学到的基本工夫之一,恐怕也是影响顾颉刚史学思想的最重要观念)所附带的人与事的独特性与启蒙时代普遍流行的信念“人性是共通的”几乎恰好相反,且前者是19世纪的观念,后者是18世纪的思想。不少学者将“启蒙”的头衔加在胡适这样一个坚定的进化论者和明确的趋新者身上,恐怕忽略了胡适服膺的现代自由主义是后启蒙时代的产物这一事实。胡适只有从视中国较西方“进化”更晚的角度看问题时才偶尔“引进”一些18世纪或更早的西方观念,但他从来都在强调其所持的基本观念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即西方)思潮。对趋新的胡适来说,19—20世纪的思想已“非启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故说胡适“启蒙”至少在这一点上有问题。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年7月。),而时人似尚未充分认识及此。
这种潜存的紧张部分因时人认知的“科学”而调和,顾颉刚说:“科学是纯粹客观性的,研究的人所期望的只在了解事物的真相,并不是要救世安民,所以是超国界的”。不仅如此,它还是超时代的,“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在此基础上产生出学术平等的观念,“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可以着手研究的”。(注:《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第5、1—2页。)各种“东西”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或“材料”后,“科学”便使它们平等,而它们在科学面前的“平等”实际也掩盖了其各自的“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正因为这一独特性被掩盖,国学的存在价值就产生了问题,当时及后来许多否定国学或反对研究国学的人恰是以科学的超越和普遍性作为其立论的基础(详另文)。
专为研究国故正名的顾颉刚自己也很希望能“不必用这模糊不清的‘国学’二字做我们的标名”这一点提示着“模糊不清”的确是当时国学的明显特征。陈独秀在1923年说:“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他认为,“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注:陈独秀:《国学》,《陈独秀著作选》中册,第516—517页。)这里陈独秀大致已按西方学术分类来认识国学,但在他的认知中只有章太炎一人长于历史,可知其所说的“国学”与顾颉刚定义的国学有相当的区别。
最使时人困惑的是,即使这样一种学科认同有问题而独特性又不成立的“国学”,还不能不与外国发生关系。基本没有参加关于国学和整理国故讨论的鲁迅在1922年注意到,“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斯坦因已将西北的“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同时,若“真要研究元朝的历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纳夫’的国文”。而外国译名的进入中国学术言说使文字的标点更为必要,结果是“要清清楚楚的讲国学”,也“须用新式的标点”。所以,“中国的国学不发达则已,万一发达起来,则请恕我直言,可是断不是洋场上的自命为国学家‘所能厕足其间者也’的了”。(注:鲁迅:《不懂的音译》,《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8—399 页。)后来吴宓为清华国学院写的“旨趣”也明确指出,该院“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即在于他们要“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注: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374—375页。)。
既然国学已与西学挂钩,且还不能不依赖西方汉学(以及日本汉学),则其作为学术的存在价值也降低。更重要的是,中西新旧之分到底是民初思想言说中一个带根本性的区分,无论用什么标签和怎样科学化,国学总是隐隐露出在近代文化竞争中已失败的“中学”的意味,且与富强这一晚清开始推崇的国家目标不相适应(甚至被认为有所“妨碍”)。结果,反对国学之见越来越占上风。到1929年,曾支持整理国故的《小说月报》再次讨论“国学”问题,这次郑振铎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完全站在反对“国学”一方,而该刊所发表的也几乎都是反对的意见(详另文)。北伐结束后不久,国学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基本退出中国的思想言说。(注:国学在学术领域的影响持续得更长久,吾友桑兵教授甚至认为20世纪“20—30年代前期,是国学研究的鼎盛期”(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第36页)。不过,1926年《古史辨》出版并风行一时, 势头显然压倒“整理国故”,而胡适自己也在1928年将整理国故诠释为“打鬼”,约同时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已喊出“不国不故”的口号,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复因多方面的原因而停办,同年《小说月报》反对国学的讨论与学术界这些变化显然是呼应的,故国学的“鼎盛”期或未必持续到那样长。)
标签:科学论文; 赛先生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国学论文; 饮冰室合集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读书论文; 胡适论文; 梁启超论文; 康有为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