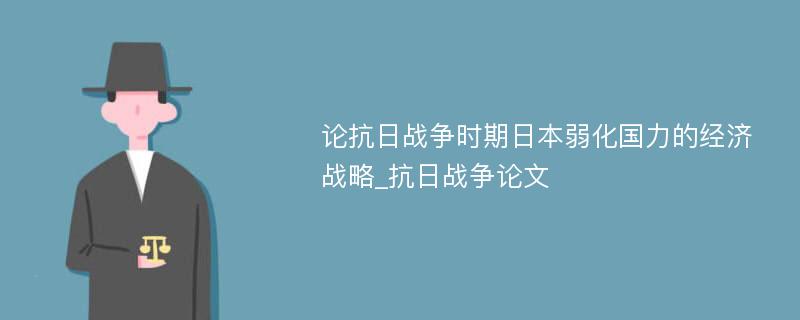
论抗战时期日本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日本论文,国力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往对战时中日经济关系的研究,着重于日本对华经济资源的掠夺,而忽视其削弱中国国力的一面,没有把日本的经济行为研究和战略行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本文试图以后者为切入点,从二者的结合上对日本的经济侵略作一研究,以深化对战时中日经济关系的认识。
一、削弱中国国力是日本对华经济战略的重要目标
日本削弱中国经济力的战略目标可以分解为个重要的子目标:一是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二是遏制中国的财政和金融。掠夺经济资源是从经济资源的总量上削弱中国的可控能力。这一战略目标的思想相当广泛地体现在日本有关侵略中国东北、华北以及其他地区的计划、纲要、方案等文件中。比如,在1937年12月27日创立的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机构——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的一份材料中写道:“满洲国的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兴办重工业的三大要素——铁、煤炭、轻金属;就是把这些资源放在一个系统下,加以综合开发,并在这个企业的统筹下,进行从开发地下资源到飞机、汽车的制造事业,建立一个在日本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的重工业系统,这才是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的办法。”(注:《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6页。)按照这种逻辑, 中国的资源只配日本来开发和利用,而日本开发和利用的中国资源愈多,中国的国力就自然愈被削弱。这正是日本对华经济战略要达到的一个效果。财政金融关系到国家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战时财政金融则又直接关系到国防和军队的经费的筹措和运用,因而它成为国民党政府战时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和矛盾的焦点。日本削弱中国国力,财政金融自然成为它重点攻击的经济目标。对此,曾任国民党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在1939年6 月呈蒋介石的财政密报中指出:“近代战争非但恃武力之强弱,尤以经济力孰能持久,判断其最后之胜负。敌人除以武力侵略外,并处心积虑破坏我经济金融,妄冀削弱我抗战力量。”(注:《孔祥熙关于1937年—1939年财政实况密报》,《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日本的破坏明确的指向中国的币制改革。为防止白银外流, 稳定金融和经济,国民党政府在英国顾问李滋罗斯的帮助下,于1935年11月进行币制改革,废止银本位制,采用纸币流通制,并规定流通纸币即法币与英镑和美元的汇率。孔祥熙于11月3日宣布币制改革后, 日本马上做出反应,说什么“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于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制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密录》,第10 册, 台湾中央日报社1977年中文版,第73页。)即以武力制止币制改革。南次郎则认为,应通过策动华北“独立”来破坏币制改革。他在给广田外相的建议中说,如使华北“独立”,“结果将使作为英国借款的担保品——关税余额和铁路收入的价值几乎都减少一半,同时,防止现银集中,以破坏币制改革的根本条件,借此使南京政府自己放弃这一企图。”(注:《南〔次郎〕驻满大使关于促进华北分离工作对广田外相的建议》,《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80页。)真可谓一箭双雕。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军民奋勇抵抗,日本看到不可能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便愈发重视对中国的经济战, 以削弱中国的经济力。 1938年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在关于所谓对中国的谋略中指出: “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外国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注:《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同上,第270 页。)所以,日本一直把破坏中国的财政金融作为其重要经济战略目标。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日本是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战略方向上来实施其削弱中国国力的战略。
日本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不是一种单纯性破坏,而是企图在削弱中国的同时使自己获益,这就是日本经济力量运用的双刃剑。日本把削弱中国和掠夺中国是合为一体的。1934年10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制定了《华北重要资源调查之方针及要领》,提出要“助长帝国发展对华经济,使战时我国国际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和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并促成日、满、华经济圈”。(注:〔日〕近代日本研究会:《东亚与日本》,山川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162页。转引自军事科学院编:《中国抗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这种“经济圈”表面看来是一种“合作”, 与日本的“削弱”战略相悖,实则不然,因为日本所说的“合作”对象必须是肯与日本合作并有利于日本发展经济的势力。这种势力在中国东北,就是伪满洲国;在华北,就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类的伪政权;在华东和华中,就是汪记伪国民政府梁鸿志伪维新政府。这样的“合作”实际上就等于发展日本自身。用日本近卫内阁智囊团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向形成日满华的经济集团、通货集团的目标前进”,使之“有效地完满地开展与此相适应的我国战时经济”,“把经济开发计划从属于目前进行战争的目的”。(注:《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资料选编》,第268页。)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日力量的打击和削弱。 至于对蒋介石政权,日本的经济战略总的来说是将其削弱,并力图“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注:《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同上,第269页。)
二、日本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对策
(一)掠夺工农业资源。日本掠夺工业资源的战略对策主要是资本垄断与控制。日本在占领区成立了许多垄断性集团,如成立于1906年的“满铁”(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曾在中国东北经济中处于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1914年其企业财产约占日本在华投资额的55%,占日本在东北投资的80%,到1930年底在东北的投资总额达90464.6万日元。 (注:清庆瑞:《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第125页。)“满铁”的营业务也较广泛,除主营以铁路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外,还兼营煤矿开采、电气、仓库、房地产等,并对铁路附近属地有行政管理权,因而有“满铁王国”之称。七·七事变后,日本又在东北成立了“满业”(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其创力资本为45000万日元, 除经营“满铁”原经营的重工业企业和伪满洲国经营的企业外,还在东北创办了汽车、机械制造、化学、冶炼、飞机制造等企业。除“满铁”、“满业”外,三井、三菱、住友、大仓、浅野、安田等日本财团也在我东北大量投资,扩张势力。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伪资本在东北工业中已占99.15%。日本对工业资源的垄断和掠夺还具有战略计划性。 它制定了两个“产业五年计划”。第一个“产业五年计划”从1937年开始执行,重点放在钢铁、煤炭、电力、液体燃料、轻金属、非铁金属等生产上,并且生产指标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大幅度加码。 生铁由原计划的253万吨增加到450万吨,钢锭由185万吨增加到316万吨,煤由2716 万吨增加到3110万吨,液化煤由80万吨增加到177万吨,挥发油由82.6 万吨增加到174万吨。(注: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0页。 )这就必然要加大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和对中国国力的削弱。1941年9月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三个月, 日本又制定了第二个“产业五年计划”。该计划更着重于战争资源的掠夺,将重点放在煤炭、钢铁、水力发电、液体燃料、非铁金属、盐等生产上,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这些资源将进一步遭受劫掠。
日本掠夺农业资源的战略对策主要贸易统制和封建性剥削。贸易统制也是一种垄断性政策。日本通过所谓《米谷管理制度纲要》、《米谷管理法》、《主要特产物专管法》等法令实行贸易统制,规定对稻米、小麦、土豆、棉花等实行统制,购销、加工均由日伪控制。对农产品收购还实行所谓“粮谷出荷”,即压价收购。“出荷量一般在产量的50%左右,有的高达70%,加之苛刻的“粮食配给”制,使农民难以度日,以至倾家荡产。日伪还通过苛捐杂税、高利贷等封建性剥削来榨取农业资源。1938年,伪满岁入总额30455万元,其中租税收入就达17295万元,占56.8%。(注: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经济》,中国现代史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20页。)在晋察冀游击区捐税名目不下70多种,抗战8年间被勒索的粮款折合粮食达223亿石。(注:《抗战时期的经济》,第618页。 )日本对农业资源的大肆劫掠使土地大量荒芜,产量大幅度下降,农民陷入破坏,农业生产力被严重破坏。
(二)破坏财政和金融。从战略对策上分析,日本破坏中国财政经济的主要方式是:一是劫夺税收。税收是国民党政府主要的经济来源。战前税收主要是关税、盐税、统税三大类。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特别是全面侵华后,沦陷区的税源自然被切断,悉数落入日本人手中。象沿海、沿江的海关,辽宁、淮北、江浙、福建、广东的产盐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城市的厂矿(统税来源),均为日本侵占,三大税也就被其劫掠。二是降低关税。日本在其控制区实行特别关税,其关税额仅为中国关税的四分之一,大量日本商品得以减征或免征关税进入中国市场。象冀东特别关税,砂糖每包(135斤)4—5元,干贝每包(100斤)15—20元,人造丝每包(100镑)20—40元; 而中国关税上述三项则分别是9.8元、40元、120元。这就使日货犹如洪水般地从冀东海关涌入,直奔天津,南下上海,流向中国各地,形成对中国市场的巨大冲击。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因此它同财政一样成为日本攻击和破坏的重点目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就很快控制和垄断了中国东北的金融。七·七事变后,日本又想方设法破坏关内的金融,以进一步扰乱和削弱中国的经济。其手段主要是:1、发行伪币。伪币名目繁多, 诸如“蒙疆券”、“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等。这些伪币都是通过日本设立的伪察南实业银行、伪察北实业银行、伪冀东银行、伪江苏地方银行、伪华南信托投资公司等许多伪金融机构发行的。这些伪币缺乏或根本没有准备金,是依靠政治和军事的强制力发行的不能兑换的纸币,目的就在于掠夺财富,取代法币。2、打击法币。 日本采取各种手段打击法币。比如,禁止法币流通,强使法币贬值,限制持有法币量等。拿法币贬值一项来说,从1941年1月至1942年5月一年多时间里就接连贬值,从军用票1元兑换法币2元1角,贬到军用票1元可兑法币10元4角8分(注: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湾综合月刊社1974 年版, 第636页。)为禁止法币流通,日方还颁布法律来限制,即持有法币1元者没收,6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套购外汇。国民党政府在1938 年曾实行外汇管制,规定外汇不能自由买卖,但在上海仍存在外汇黑市,由中英共同提供的平准基金来维持,以求稳定法币。日本就利用这一时机,用搜刮来的大量法币套购外汇,一方面可消耗中国财力,另一方面也可用以去国际市场购买军需物资。日本破坏中国金融的情况,孔祥熙在其财政密报中慨叹:“我流通于游击区域之法币,敌人既百端压迫,强为兑换,或用武力收兑,或以日货贸易,法币当有一部流入敌人手中。此项流入敌手法币,以之购买外汇,则影响我汇市;以之收买我物资,则间接取得外汇,亦均具威胁之势。”(注:《孔祥熙关于1937年—1939年财政实况密报》,《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 )这反映了日本此项经济战略对策的危害性。
(三)封锁和统制贸易。为切断中国外援,日本对海陆交通进行封锁。七·七事变爆发后仅一个月,日本就封锁了我国北方至上海的航路。1939年5月,又禁止第三国船只在中国航行。1940年, 日军侵入越南,滇越铁路逐被切断,大后方交通几乎断绝。加之日伪在沦陷区与抗日根据地交界处遍设关卡,使国统区和解放区的经济陷入困境。与此同时,日本利用对我进行经济封锁以及降低关税等办法,使其占领区贸易进口额大幅度增加。据统计,从1937—1940年,沦陷区进口额从15600 余万元增至52130余万元(法币)。七·七事变后, 日本还实行严格的贸易统制,限制军事战略物资流向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据日本昭和十六年(1942年)度经济封锁要领等规定,所谓“直接战力补强原材料”,如军器、弹药、硫磺、火药,以及军需重工业原料,如钢材、钢块、铣铁、石棉、电极用原料等,均限制贸易,实行管制。(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页。)1943年3月,日本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并下设各专业委员会,形成一个严密贸易统制网,以遏制中国抗日经济。
分析日本经济战略对策,可看出具有下述特点:
以资源掠夺作为重点。掠夺中国工农业资源以及其他资源,是日本削弱中国国力经济战略对策的重点。从日本侵占东北到其全面侵华,它掠夺中国资源的活动就没有停止过,直至它战败投降。资源掠夺又是削弱中国国力的重要方法。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条件下,一方占有的愈多,另一方必得之愈少,正符合资本帝国主义国际战略中经济力量运用的要求,自然为日本重点运用。
经济手段运用的多元性和广泛性。日本为达到削弱中国国力的目的,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从经济手段上看,有经济垄断、经济封锁、资源掠夺、走私贩私、扰乱金融,等等。在工业、农业、交通、贸易、财政、金融等领域都有其经济手段的运用。从战略学理论上说,战略对策愈具多元性和广泛性,其力度就愈大,就愈有利于战略目标的实现。日本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国力造成严重削弱,应当说,与其在战略对策运用上的这一特点是分不开的。还应看到,日本上述经济手段的运用并非纯经济性的,而是与非经济手段融合在一起的。
对策狡诈多变。日本对策的狡诈主要表现在利诱、诱骗、变换上。利诱,就是打着“合办实业”的幌子,进行经济引诱。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日本就宣称:在华中华南,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51%,日资占49%;在华北,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49%,日资51%,并允许将各中国资本家原有产业发还他们,折合计算,充作资本。比如,实行“合作”的淮南煤矿公司和华中盐业公司,中方出资有200多万日元, 日方是否投资却不得而知。即使投资,也不过是军用券、伪钞、公司债券之类的废纸。因此,正如经济学家许涤新所指出,所谓“合作”完全“是一种骗人的花样,实际乃是利用汉奸资本吮吸我国人力与物资的毒计罢了。其所谓开发,不外是尽力掠夺沦陷区的劳动力和原料而已”。(注:许涤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变换,就是根据形势变化而改变手法。这集中表现在日本对法币的策略上。中日战争全面开始后,日本对法币总的政策是破坏其信用,以利于其控制金融。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尚有法币外汇市场,日本想利用法币套购外汇,因而还不想过分贬低法币的的价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外汇市场不复存在,日本转而对法币实行打击和排斥的对策,就极力贬低法币价值,以便用日钞、伪钞兑换更多的法币,去收购中国的物资;同时禁止沦陷区流通法币,以防中国方面到沦陷区购买物品。日本对法币对策的前后变化,反映日本为削弱中国国力而用尽心机。
三、日本经济战略对中国国力的影响
首先,国家资源严重流失。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为例,它所掠夺的资源就相当巨大。苏联经济史学家斯拉德科夫斯基指出,日本占领东北后,大大地削弱了中国的经济,因为占全国铁矿藏量的37%、生铁产量的79%、石油开采量的93%、黄金开采量的55%的资源悉数被日本掠去。(注:〔苏〕斯拉德科夫斯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简史》,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版中译本,第203页。)1943年, 国民政府经济部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日人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占领东四省后,该四省一切煤矿权几全入敌人掌中,以民二十三年为例,则每年遭其掠夺之煤矿近千万吨,十年则损失千亿吨左右,事实上尚不止此。以抚顺煤矿为例,近年产煤每年为一千五百万吨,即超出二十三年东四省全年产量五百万吨。芦构桥事发,我国本部各地泰半沦陷,沦陷各区之所有一切煤矿俱受敌人控制,……与东四省合计所受损失达千数百亿吨,此实为最低之估计。”(注:《抗战时期日本掠夺我国汽车燃料工业的调查报告》(1943年),《档案史料与研究》1995年第1期。 )报告还举出日敌对我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以煤炼制焦油副产品,每年汽油达4 万吨,重油10万吨,灯油10万吨,以及机器油、精蜡副产品,“其量不胜计,以十年累计,损失实属不赀”。此外,象林业资源,也遭野蛮掠夺。东北的森林,日伪时期砍伐的原木达7500万立方米,由于采伐不合理又损失了40%,总共被掠夺的原木就达1亿立方米。 (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这些还远不是完全的统计,却已怵目惊心,可知日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对我造成了究竟多么巨大的损失。
其次,国家财源被大量劫夺。税收是国家的重要财源,日本劫夺中国财源主要拿税收开刀。 日本占领东北后,肆意增加税种和数量, 从1932年的1.14亿元增加到1940年的4.65亿元。从1941—1943年又进行三次战时增税。第一次每年增幅为1.5亿元,第二次每年增幅为1.6亿元,第三次增幅每年为2.46亿元。到1945年,除继续修改税制和增税外,又大量提高香烟和鸦片和价格,增收金额达3.5亿元。 (注: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14),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85—786页。)另外,日伪巧立名目,超负荷征收,榨取民旨民膏,也是对国家正常税源的透支和掠夺。日本全面侵华后,所劫夺的税源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关税、盐税、统税三大税收。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国民党政府三税收入只有4.1亿元,1939年只有4.3亿元,与1936年10.14亿元相比。减少五分之三左右。其中,尤为对关税劫夺最甚。国民党政府《财政所鉴续编》对此统计如下:(注: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经济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12页。)
1937年14308928元 占全体关税收入4.17%
1938年159271424元 占全体关税收入62.57%
1939年277369688元 占全体关税收入83.72%
1940年423685072元 占全体关税收入89.06%
1941年415158416元 占全体关税收入85.17%
1941年11月以后,日军霸占海关总税务司署,收入不详。但据国民党政府估计,关税被敌伪劫夺在226亿元以上, 而此期间国民党政府逐年关税收入总和不到30亿元。此外,日本还通过走私逃税,变相劫掠中国财源。据日本1935年10月20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从1月至9月(1935年)由上海向日本走私输出的白银约有1.44亿余日元,而日本年产白银仅1000万元,故由日本输出之白银主要是由中国向日本走私之白银。”(注:《抗战时期的经济》第179页。)另据统计,1935 年初至1936年5月,日本在华北地区走私贸易额达3亿元,损失海关税达1亿元。(注:《抗战时期的经济》第180页。)
日本对中国财源的另一严重劫掠就是套购外汇。如前所述,日本通过发行伪钞、打击法币、控制关税等手段“收兑大量法币,再利用法币套购外汇,致使我国外汇大量流失。从1939年3—6月短短3 个月时间里,用以支持外汇市场的中英外汇平准基金1000万英镑几乎消耗殆尽,其中绝大部分系被日伪套购。同时,日本还通过贸易统制来夺取外汇。如1939年3月,日伪对华北12种商品实行出统制,即使该地区60 %的外汇被敌攫取。 (注:《抗战时期的经济》第209页。)此外,用倾销日货、 走私战略物资、掠夺我国黄金和白银等办法也攫取了大量外汇。
第三、工农业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力是最基本的国力。中国工农业生产力在日本侵华期间遭到严重破坏,这一方面是毁于日本战火,另一方面则是毁于日本的经济侵略。从日本经济侵略造成的破坏来看主要是:
工业方面一是中国民族工业被排济。日本通过资本垄断和扩张,极力排斥中国民族工业,使我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几无立足之地。比如,日本占领东北后,工业资本急剧扩张。据1940年调查,在全部东北工业中,日资占资本总额的80.8%,中国民族资本仅占17%,其他国家占2.2%,这还不包括日伪垄断的官营工业的军事性工业。 (注: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出版社1958 年版,第951 页。)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其资本在东北工业中已占99.15%, (注:孙健:《中国经济史1840—1949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02页。)基本上垄断了东北的工业。即是说, 民族工业此时根本不可能在东北寻求什么发展,无疑,中国国力也要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二是侵吞中国工业资本。侵吞方式用得最多的是“军管理”和“委任经营”。象由“兴中公司”在华北、华中、华南实行“军管理”工厂就有54家,包括煤矿、铁矿、电力、钢铁、造船、化学、棉花加工等行业。(注:《抗日经济史》,第182页。 )“委任经营”是日本私商对中国资本的吞并方法。如华中地区,由“委任”吞并的中资工厂有:纺织厂40家、面粉厂18家、造船厂11家、造纸厂9家、树胶厂9家、烟草厂8家、 染织厂6家、金属制品业5家、机器业4家,以及其他行业27家。 (注: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出版社1958年版,第439页。)另外,通过“中日合办”、“租赁”的方法,也吞并了不少中方工业资本。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档案披露,到1942年日本侵吞华北、华中、东北的中资工厂为325家,资本额为1.9685亿元,其中有165家的资本未能计入,有26家资本额为战前注册,数字小于统计时价值。(注:《1942年前日本在中国沦陷区掠夺公私工矿业经济及收益调查报告》,《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三是破坏中国产业结构。 这明显地表现在东北地区。日本奉行“原料满洲,工业日本”的殖民掠夺方针,把东北变成其发展工业的原料基地,而工业企业则为日本所控制。在工业发展上,则以重工业为主,如到1942年,重工业资本额占工业资本额的79.2%,而轻工业仅占20.85,(注:《抗日经济史》,第140页。)造成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在重工业内部也比例失调,冶金业相对发展,而机械工业却很差,到1943年机械工业比重在东北整个工业只占6.7 %, 机械生产只能供给需要的40.2%, 其中精密机械的自给率为15.9%, 蒸汽机仅能供给2.7%。 (注:《抗日经济史》,第141页。)冶金工业内部同样比例失调,采矿能力大于选矿能力,选矿能力大于炼铁能力,炼铁能力大于炼钢能力,炼钢能力大于轧钢能力。近代中国产业结构原本失衡,加之日本的这种破坏,使中国工业经济更具对外依附性,而无法全面合理地发展。
农业生产力毁于日本侵略也相当严重。七·七事变后,关内有6 亿亩土地被破坏,占关内耕地总量的52.6%;全国2300万头耕牛中损失了800余万头;主要农产品的损失,最少的为19%,最多的达80%。 (注:《抗日经济史》,第194页。)从日本经济侵略角度看, 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一是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剥削使农民不堪重负而陷入破产。破产后的农民背景离乡,或沦为日本垦殖会社的农奴,良田集中到日伪手里,部分则变成了荒田。1941年,仅河北一省荒田就增至40余万亩。(注:《抗日经济史》,第197页。 )二是掠性价格政策使农业产量急剧下降。日伪对农产品实行统制,用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农产品。象华北地区,小麦、玉米、高粱的收购价格只有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即使市场价上涨,收购价仍不动,(注:《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译本,第56页。)这是对农民的超经济性掠夺,必然导致其破产,造成耕地面积和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减少。如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棉花耕种面积由1932年10万亩减至1942年的7.9万亩,产量同期由2365千担减至1615 千担。日本学者就此指出,导致这种状况的决定性原因,“就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农业的破坏”。(注:《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译本,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