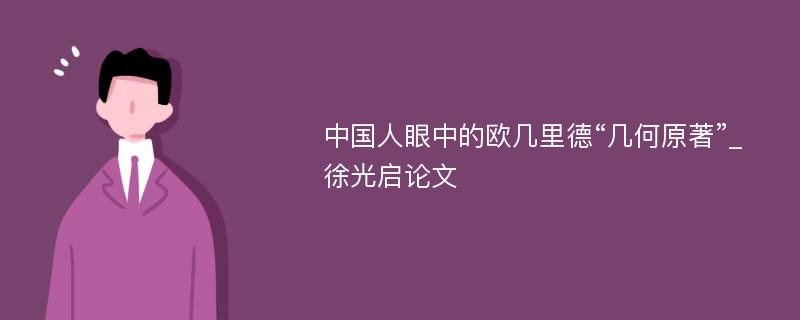
中国人眼中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几里得论文,几何论文,眼中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森伯在《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这样说[1]:“今天,当人们谈到现代物理学时,首先就想到原子武器,……并且都心悦诚服地承认物理学对一般政治形势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但是,现代物理学的政治方面真的是它的最重要的方面吗?……每个工具都带有用来创造它的那种精神.因为每个国家和政治集团,不管它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如何,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关心这种新武器,所以,现代物理学的精神必将渗透到许多人的心灵之中,并以各种不同方式和老传统联系起来.”对于某些地区和某种文化传统,它“将同本地文化的宗教基础和哲学基础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可能引起全新的、难以预料的发展”.现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恰好证实了这个论断,这一过程是漫长而且充满冲突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传入中国就是一个例证.
1 “几何原本”的传入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意大利传教士耶苏会士利玛窦(1552-1610)传入中国的,利玛窦曾受教于克拉维乌斯(1537-1612),著名数学家,耶苏会士,曾受教皇格里高里十三世之命,主持了Gregory历的制订,完成了主要的计算工作).根据教皇保罗二世当时向东方派遣传教士的决定,他于1582年(一说为1581年)来到澳门,次年到达广东肇庆,但是,他遇到的是一个不友好的环境.原来,明皇朝一直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后因经济方面的原因有所松动,传教士来华也多起来了,但对他们的活动的真实目的及其对于中国人民可能的影响,朝廷仍抱有极大的疑虑,因此,直到1600年他才获准进入北京,当时,他向皇帝献上了贡物:其中有圣经、圣像、时钟、世界地图,据说还有圣骨.但是,这反而引起了更深的怀疑.据明史记载,当时即有官员说,基督教义已属无稽之谈,教徒升天又何来遗骨留在人世?但是,诸如地图,时钟等等,却引起了不少读书人的兴趣,传教士们为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义,力图找到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利玛窦曾向教皇报告,认为接近中国人的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向中国人传授西方数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翻译.
时至16世纪末,传统的中国数学已经衰落了,许多古算典籍甚至已经失传了.但是当时手工业、冶金工业、商业以及原始的银行业,却都有了相当的发展,这就需要数学有相应的发展.毫不偶然,《几何原本》的著名中译者徐光启(1562-1633)出身于商人家庭,最终官至大学士,终身关心农业、防洪、灌溉、乃至国防.另一方面,历法问题在中国各皇朝中又有特殊的重要性.天文异象如日月蚀.彗星出现等等,被看作灾难,如政变、篡权的先兆.自古以来,各朝各代,常设钦天监,其负责人(钦天监正)需就天文异象的出现向皇帝作秘密报告.因此,历法问题不仅关乎农业,更关系到皇朝的命运,明代沿用元代大统历与回回历,因年代久远,误差甚大,修正历法,乃成急务,但精通历法人才难得.1596年9月22日日蚀即有误报.时利玛窦在南昌按西法准确预报了这次日蚀,因此名声大振.许多人向他学习西方历法.他以Clavius所著《观象仪》一书教授Ptolemy的天文学,主要是Tycho Brahe的方法,是年,邢云路上书奏请修历,但直至1629年,在旧法多次预报日蚀失败以后,才决定开设历法局着手修历.并命徐光启主其事,但其时利玛窦已经去世,主持历法修订的是由徐光启推荐的汤若望(1591-1666),他是德国传教士,于1620年受教皇保罗五世直接派遣,同另4位传教士来华,他们带来了许多天文仪器,包括望远镜,以及图书七千余册.徐光启则奏请任命他进入历法局.因此,利玛窦并未参与修历的实际工作,只是与徐光启共同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他们根据的是C.Clavius注释的拉丁文本,但是,《几何原本》全书共15卷,利玛窦只翻译了前6卷,所有的注释都没有译出,翻译的方法是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翻译从1606年开始,1607年完成并付印,原刻板留北京,以后几年中,又多次校改,参加者还有另一些传教士,如庞迪我、熊三拔等人,在北京以外也有刻印者,可见有相当的影响.应当指出,除几何学以外,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知识还有平面和球面三角学、对数、测量学等等.为了修历的需要,1634年,由罗雅谷(与汤若望同时到中国的传教士之一)、邓玉函(与汤若望同时到中国的传教士之一)、汤若望等汇集所译的西方天文数学书籍137卷,编成《崇祯历书》,包括了这些内容.除了《几何原本》以外,当时还翻译了另一本有关实用算术的《同文算指》(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它其实是中国传统数学书,由明朝程大位著的《算法统宗》与C.Clavius的《实用算术》(1593)合编而成,把中国传统数学与西方数学结合起来,这是非功过很值得注意的.
在这期间,还翻译了不少西方经典著作,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也通过付泛际和李之藻合写的《名理探》一书传入中国,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传教士们只介绍了托勒密的地心说的天文学.实际上,在《崇祯历书》中,就详细介绍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刻卜勒的《论火星运动》等书.1621年,邓玉函在给朋友(Faber)的信中也说:“中国人所渴望者,乃更精密之日月蚀推测方法,第谷之方法虽佳,但有时尚可差至15分钟.”[2]应该说,这是中国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一次高潮.
但是,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遭到了强烈的反抗,这不只是关于历法的不同观点,更是由于统治者感到天主教义与儒家学术的矛盾,对自己的统治有了威胁,因此“教案”迭起,直到明朝灭亡,新历也未实施,清皇朝建立后,顺治皇帝敕令行新历,并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正,但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杨光先“不得已”案,康熙登基不久,杨光先就在鳌拜支持下,诬告汤若望新法十谬,他写的《不得已》(1664年)一书就为的是反对天主教.并以李祖白所著《天学初概》为口实,“请诛邪教”,而在新的历书上确实写了“依西洋新法”.试问,如果历法可以“依西洋新法”,那么,是否有朝一日,根据制度也可以“依西洋新法”呢?于是,部议将汤若望等9人凌迟处死,另5人斩立决.后汤若望得赦,处死了5个中国人(包括李祖白).康熙8年(1669年),康熙亲政后,令新旧法同时在殿前作实测,而平反此案[2],但汤若望已死于1666年,而且“依西洋新法”几个字也不再出现了.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有作为的皇帝,他希望了解这个世界.他喜爱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很喜爱西方的文化(如音乐).当时,法国皇帝路易十四也希望扩大法国在中国的影响,以对抗葡萄牙人,于是派了6位传教士,以塔沙尔为首(后塔沙尔应暹罗国王之清,留在暹罗),包含白晋,洪若翰,李明,张诚和刘应来到东方.他们带来了许多天文仪器.在一段时间里,康熙要求白晋、张诚等人每天进入内廷为他讲授数学.他还组织了人们把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翻译为满文,他甚至组织了撰写《数理精蕴》,全书计53卷,除几何以外还包括了实用算术、对数和直到高次方程为止的代数知识.几何方面,大体仿照“几何原本”,但不太严格.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书中,康熙认为一切数学知识都源于中国,后来才传到希腊.其实徐光启也说是中国原来什么都有,只不过被秦始皇烧了.这种缺少根据的妄自尊大心理对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是有害的.但是康熙确实是想要了解世界的皇帝.他派白晋回到巴黎,请路易十四增派懂数学和天文的传教士来到中国[3].
康熙支持传教士的活动与他想建立较密切的对外关系有关.他还派遣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出使俄罗斯,希望建立中俄关系,闵明我是莱布尼兹的朋友,在他回罗马途中,向莱布尼兹介绍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情况.莱布尼兹大感兴趣,甚至误认闵明我是“北京数学院院长”[4].其实,外国传教士参与中国政治活动颇多,白晋和张诚就参与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更早,崇祯皇帝还要求汤若望为他造大炮以抵御满人入侵.
不论如何,西方数学传入了中国,尽管范围还十分有限.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中国数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梅文鼎,其工作主要是解释初等数学范围内的知识,而同一时期,西方出现了牛顿.这样,中外数学水平的差距就越来越大,康熙死后,雍正继位,实行更严厉的思想专制,海禁也更严厉.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消化也中断了.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了.
至于历法,汤若望死后,就由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接任钦天监付,制定永年历,由康熙敕令颁布通行(1683年).此后,直至1826年,钦天监中总有外国人任监正或监付,历法问题至此解决.
从利玛窦来中国到南怀仁新历施行的100年中,数学在中国的发展一直与政治不可分.政治的影响过大,甚至皇帝本人的性格也起了过大的作用.这与数学在希腊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由希腊至西欧,数学的发展当然也不是与政治绝缘的,但是,数学以及一般的科学.作为对自然界规律的探索,其独立的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早已得到确立,在中国则不然,科学最多也不过作为一种技术,它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明清之际,以翻译《几何原本》为例,西方数学在中国的遭遇,恰好说明了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对科学发展的一个妨碍.
2 徐光启眼中的“几何原本”
外国传教士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的文化,于是也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与我们的固有文化比较,它有哪些优点?1632年有人这样写到:“天载之义,格物之书,象数之用,律历之解,莫不穷源探委,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自鸣之钟,照远之镜,举重之器,不鼓之乐,莫不精工绝伦,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贾万国,五金山积,我中土之富饶不如也”[5].老大自居是不行了.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代表的《几何原本》,更是中国人前所未见的,自然也给中国人以深刻的印象,徐光启除了为《几何原本》写了序言以外,还写了一些短文,十分值得注意,翻译《几何原本》原是为修历之需,不懂几何学,就不能解决修历中的具体问题.几何学的作用,徐光启说,就在于它能帮助人们“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之基”.他在“刻几何原本序”中引述了利玛窦的话:“是书也,以当百家之用,庶几有羲和般墨其人乎,犹其小者;有大用于此,将以习人之灵才,令细而确也.”徐光启进一步说:“余以为小用大用,实在其人,如邓林伐材,栋梁榱桷,咨所取之耳.”[6]他在“几何原本杂议”一文中进一步展开说:“下学工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気,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闻西国古有大学,师门生常数百千人,来学者先问能通此书,乃听入.(这自然是指柏拉图的学院)何故?欲其心思细密而已.”所以徐光启接着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习人之灵才,令细而确”,人的灵才是需要“习”的,人具上资而意理疏莽,即上资无用,人具中才而心思缜密,即中才有用,能通几何之学,缜密甚矣!故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很明显,与柏拉图一样,徐光启也认为,几何学的作用在于铸造人的品格,开发人的潜力.几何学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功用?由于它提供的是确定无疑的知识,对于几何学提供的知识,我们“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对它的结论和论证“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整个几何学“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它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它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它物之至难,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就是说,几何学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出发点是最明显不过的真理;而它的推理方法,徐光启说:“至于文句,则尔日推敲再四,显明极矣.倘未及留意,望之似奥深焉,譬行重山中,四望无路,及行到彼,蹊径历然,请假旬日之功,一究其旨,即知诸篇自首迄尾,悉皆显明文字.”这就是说,极深奥的推理,整个看来“四望无路”,如果一步步地走,则“及行到彼,蹊径历然”,每一步都是明显不过的.所以,整体看来“自首迄尾,悉皆显明文字.”
我们可以把徐光启和笛卡儿做一个比较.笛卡儿在1637年写了一本《论方法》,比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稍晚,笛卡儿是近代哲学的鼻祖之一,他的哲学和大体同时代的许多哲学家一样,深受《几何原本》的影响.他想提出一种他认为可以应用于一切科学探索的方法.其实,他的方法正是以《几何原本》为模式的.他的方法包括4条规律:(1)“凡余未能清晰地承认者,均不接受其为真:亦即,作判断时需细心避免鲁莽与偏见,此时仅接受在余心中为清晰而判然使余无从怀疑者.”(2)“将余正在研究之难点分解为尽可能多之部分,且每一步均为必不可少,使能尽可能好地解决之.”(3)“按适当次序思考,由最为简单易懂者开始,以逐步达到最为复杂者,使得看来不依从自然次序的步骤之间,亦有一定次序.哪怕为虚构的亦佳.”(4)“列举情况必需完备,总括必需全面,使余能以断言,未曾有所遗漏.”笛卡儿明确指出:“这一思维之长链,简单易行,正是几何学家用以完成最为困难的证明之方法,故余念及,凡人类认知领域中之一切,其相互之间亦有联系如斯;故若吾人能戒以伪者为真,且能按必要之次序,由一结论达另一结论,则必可无远弗届,无隐弗现矣.”当然,笛卡儿和徐光启不同.前者由“几何原本”的方法达到了一种一般的科学方法,然后反过来用这种方法于几何学自身,得出了解析几何学;后者则只是看到了《几何原本》的方法论的特点.然而,两人都指出,思维的出发点必须“清晰而判然”,“综其妙在明”;思维的过程应分成许多小步,每一步虽然均极简单,却可“无远弗届,无隐弗现”,如人行深山之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步步行来,却又峰回路转,“蹊径历然”.应该承认,徐光启的见解是很深刻的.
当时的西方哲学家,大多与笛卡儿相似,深受“几何原本”的影响:如欧洲大陆的斯宾诺莎,莱布尼兹,英国的洛克,霍布士.而中国学者不同,对逻辑推理不甚重视,而常以类比、比喻,乃至聪明的寓言故事来阐述自己的结论,甚至直接宣布自己的结论而不作任何论证.与《几何原本》比较,徐光启做了以下的评论:他在《几何原本杂议》中比较几何学与他过去所学的学问说:几何之学,深有益于致知.明此,知向所揣摩造作,而自诡为工巧者皆非也,一也.明此,知吾所已知不若吾所未知之多,而不可算计也,二也.明此,知向所想象之理,多虚浮而不可挼也,三也.明此,知向所立言之可得而迁徙移易也.”如果说,这一评论还比较含而不露,则他对中国传统数学衰落原因的分析就确定无疑了.他在“刻同文算指序”中说:“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廖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无不效,卒于神者无一效,而实者亡一存.”其实,名理之儒看不起的不仅是技术,即“天下之实事”,而且轻视一切有关自然界的规律的科学知识.他们甚至没有自然界的科学规律这一概念.因此,不仅科学(包括数学)无法发展,而且,人类心智的这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就很容易地成了迷信、巫术乃至邪教活动的天地了,非常遗憾的是,徐光启以后的将近4个世纪,我们在这方面成就并不大.这使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感到内疚.
3 “几何原本”翻译的完成
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是西方数学传入中国的第二个高潮.这不是说,进入20世纪后西方数学传入中国反而变慢了,而是因为中国社会发生了进一步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已经和明清之际大不相同了.那时,西方科学还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连同宗教一起进入中国,尽管中国和外国的皇帝们和教皇都关切这件事,主要角色还只是传教士及其信徒;科学的传播主要也只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正因为如此,徐光启的那些极精彩的评论主要还是文化方面的评论(我们没有介绍他在其它方面.如农业和水利方面的活动和言论).鸦片战争以后,清皇朝面临两个威胁:一是殖民主义,西方列强发动的多次战争:两次鸦片战争,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略等多次侵略战争,使中国面临灭顶之灾;一是农民起义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几乎推翻了清朝统治,为了挽救国家于垂危,当时最直接可以看到的是,外国人既然倚仗船坚炮利打了进来,中国人也只能用新式武器来反抗,后来“洋务运动”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魏源在洋务运动前几十年的鸦片战争前后提出的.魏源是当时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为此,就需要西方科学技术,首先需要数学,这就是西方数学传入中国再现高潮的背景.
“几何原本”全书15卷的翻译是李善兰(1811-1882)与英国人伟烈亚力(1815-1887)合作,于1856年(咸丰6年)完成的.在此前后,他们还翻译了棣.莫根的《代数学》(1834).(他的《概率论》(1835)也于1880年由另一位数学家华蘅芳译出,当时书名《决疑数学》.Laplace的名字也传到了中国).还有Elias Loomis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学原理》.当时从事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人很多,就翻译工作而言,华蘅芳的成绩就很大,他的译文明白流畅,对读者帮助很大,其它地方还有许多从事这种工作的人.翻译工作通常是中国人与外国人合作,而外国人多数仍是传教士,不过是新教而非天主教,是英国人或美国人,而非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这反映了老牌殖民大国西班牙、葡萄牙已经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新殖民大国——英国.
这个历史阶段,舞台上的角色也起了变化.伟烈亚力是一个商人(也是传教士),曾在上海经营一个书店(墨海书馆).他懂一些中文,还自己用中文写了一本算术书.李善兰在上海与伟烈亚力合作翻译过好几本数学与科学书籍.自己也从事了一些独立的数学研究,主要是关于幂级数与高阶等差数列的研究.他同时也是一个工程师,懂得冶金和造船,后来他长期为曾国藩做幕僚,在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以后,又参加了“江南制造局”,1868年任北京同文馆算学层教习,最后于1882年在北京去世.李善兰的经历是很典型的.他以及另一些同时代的人(如华蘅芳),与徐光启,李之藻不同.他们不是大官,没有决策的权力,但是,许多重要的技术政策主要由他们来执行.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下的职业数学家和第一代现代意义下的教学教授.这一点正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几何原本》后9卷是根据巴罗(1630-1677)的英文本译出的.据伟烈亚力说,原版颇多毛病,他们在翻译时都做了认真的校订.他说:“如果现在谁要找《几何原本》的一个好的版本,就应该找中文本了.”可见,他们的翻译是很认真的.
上面讲到整个时局的变化,清皇朝在如何应对这一变化上,有尖锐的政策分歧.一派主张进行改革,其要点是学习西方,即所谓“洋务运动”.这一派人的首领是李鸿章和恭亲王奕欣.另一派人则主张一切都原封不动.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说:“列强各国‘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总之,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而尤以人才为亟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当时的改革派——洋务派在练新军、整武备,建立军事工业和其它基础工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的保守势力,多为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极不愿意科举正途有任何改变,极不愿意让科学技术取代了他们所熟悉的章句旧学.因此拼命地攻击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提倡科学技术不但不是救国,反而是误国.1866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议选拔五品官员到北京同文馆向外国人学数学,大学士倭仁就上书反对.倭仁是著名的理学名臣,蒙古人,他的思想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且夷人,吾仇也.……能一日忘此仇耻哉!议和(指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令正途从学,恐所学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尔.”对此,恭亲王奕欣代表几位军机大臣上疏论辨说,英法联军和约虽然签定,和平却是很不稳定的,为长久之计,必需整军备武,建立工业,开展外交等等,“臣等复与李鸿章……等往返函商,佥谓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因而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以为制造轮船各机器张本.并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为此不急之务.”他说:“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无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工夫,即学皮毛仍无补实用.”[6]所以他建议在京师同文馆中开设数学课程.同文馆学制8年,从第四年起,依次开设代数、三角以至微积分,还有航海测量等课,其后各地的“方言学堂”许多都开设了数学课程.这些“方言学堂”后来就成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的大学的前身.至于倭仁的顾虑,他这样回答说:“又恐学习之人不加拣择,或为洋人引诱,误入歧途,有如倭仁所虑者.故议定考试,必需正途人员……倭仁谓:夷为吾仇,自必亦有卧薪尝胆之志.然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存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如谓当求其实,试问当求之愚贱之人乎?抑当求之士大夫乎?此臣衙门所以有招考正途之请也.”总之,他们在维持科举制度上作了让步,一方面可以减少保守派的阻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洋务运动仍是为了维护和加强清皇朝的统治,科举是这种统治的重要支柱,而他们的改革主张,远没有达到废除科举的高度.废科举,办学校,那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了.同治皇帝也批准了在科举中增加数学,可是士大夫仍不买帐.后来,李鸿章想了多种办法,仍是应者寥寥,以至李鸿章在一封信中说:“从前每觉才多,今名位已极,责任尤重,恒无可用之人.独来独往,将何已时?为之三叹!”其实,今天看来在科举中增加数学是可笑的.试想,如果没有在西方式的学校中学过西方数学,又怎能应付这种考试呢?当时的保守势力当然看到了这点.可见,改革问题,其实是利益分配问题.再怎么“给政策”,“效益”总比不上一篇八股文就可以当一辈子的官.这种利益再分配才是阻力真正的根源,清朝洋务运动总的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6];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幻想能够不改变哪怕是经较重要的制度,更不必说是根本改变专制制度,就可以挽救国家的危亡.所以,数学的传播必须服从于这一原则,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更何况这一点有限的改革也阻力重重.
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几何原本》的译者李善兰和他的同事们长时期做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帅曾国藩的幕僚.据说当时李善兰和华蘅芳等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并在曾国藩当时镇压太平天国的司令部安庆大营为曾国藩表演.曾国藩十分高兴,因为他觉得很快就会有自造的新式武器,既可用于抵御外敌,又可用于镇压农民革命.于是,李善兰呈上了《几何原本》全译本,申述其重要,请求曾国藩协助出版.曾国藩当即同意,并为之作序和题写书名.所以,《几何原本》全译本出版于天京(即南京)陷落后对太平天国起义农民进行最残酷的屠杀的司令部金陵大营中.这样,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时的数学家对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的认识水平远不及徐光启,因为,对于他们,数学就简单是一种“工具”.
我们看到,西方数学(以及一般的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伴随着尖锐的斗争.洋务运动没能挽救清朝的衰败.1895年中日战争中的惨败,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必须进行根本的政治变革.谁也不能置身事外,这以后的血腥斗争,使得当年的历法之争看起来不过是一场“儿童游戏”而已.然而,现代的数学,来自西方,终于在中国生了根.
我们再回到海森伯讲的话,在一个与西方国家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都大不相同的国家(如中国),现代科学的传入必然会与原来的传统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可能导致无法预计的后果.如果我们不只是从战争和流血来预计这种后果,就应该想到,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数学和一般的科学.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意义下的“工具”,而是与我国固有文化极不相同的一种文化.因此,必须要问,现代化是否就只是引入“高技术”?它是否需要把现代科学技术也作为一种文化加以吸收,使得能在新世纪中把一种独特的但仍然是现代化的文化贡献于新的多样化的人类文化?这是一个只能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期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做出成绩的事.
标签:徐光启论文; 汤若望论文; 传教士论文; 数学论文; 数学文化论文; 数学中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几何原本论文; 中国历法论文; 历史论文; 科学论文; 利玛窦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