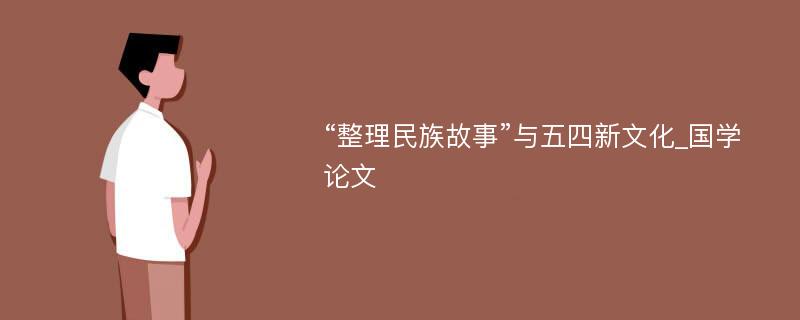
“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故论文,文化论文,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 2826(2000)01-0036-08
五四以后,“整理国故”风行一时,国学刊物和研究机构纷纷出现,十多所大专院校建立了国学系或国学专修科。这与五四激进思潮有异,提倡最力者是颇有争议的胡适。一些人对此不无异议,其中既有西化派人物如吴稚晖,也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以及转向“革命文学”的新文化人。他们不是否定“整理国故”本身,而是反对宣传过头,评价过高。较有代表性的郭沫若认为,“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价,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从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221页,上海,光明书局,1934。 )由于种种原因,“整理国故”长期遭到学术界的否定或贬低。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肯定“整理国故”校释、考辨古籍之功,但仍将之置诸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对其思想本质和客观作用认识不清或重视不够。先贤们发表不同看法并不奇怪,但这种“批评”不能成为学术定论。事实上,郭沫若后来也长期潜心于“整理”先秦诸子,研究古代社会,本质上关怀着另一种“新文化”。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不失为“整理国故”的佳作,其中蕴藏着“新文化”因素。本文不想赘述“整理国故”的具体细节,而主要探讨它与五四新文化的本质关联。
一
“整理国故”校注古籍,考辨史事,似乎沉迷故纸。顾颉刚说:“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计划”。(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78页,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章太炎是五四时期的思想落伍者,胡适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因而“整理国故”似乎脱离五四,回到“晚清”。其实,就新文化的学术基础而言,晚清与五四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整理国故”不是回到“晚清”,而是发展了“晚清”以来存疑、平等的学术精神,深化了五四的民主主题。
代表晚清进步思想的维新派、革命派知识分子,学术见解同异互见,思想关怀也有差异,但都体现了存疑、平等的学术精神,具有否定文化专制的意义,也程度不同地关怀着文化创新。梁启超致力于“史界革命”,阐发先秦墨、法学说;谭嗣同融会儒学、墨学、佛学和西学,建立“仁学”体系;夏曾佑重视墨家;严复评点老庄,发掘其自由、民主思想……。他们的“国学”不是“抱帖括考据词章之俗陋”,而是要构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学派。国粹派也调和新旧,认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契合者也”,从而肯定了新文化与国学的相通性。他们既否定孔教和独尊儒学,又肯定孔子整理“六籍”之功,重视和阐扬非儒学派,犹如梁启超所谓“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乃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
这种学术精神为五四知识分子所继承。钱玄同自称“疑古玄同”。胡适一再强调学术研究需要存疑精神,甚至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郑振铎说:“我的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便是‘无徵不信……。我们怀疑,我们超出一切传统的观念——汉宋儒乃至孔子及其同时人——但我们的言论,必须立在极稳固的根据地上”。(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209—210页。)从晚清到五四以后的进步学者,以实证为基础的“存疑”精神一脉相承。所谓“存疑”,当然不是盲从,也不是迷信学术文化正统,实质上包含着批判和创新精神。与此相关的“平等”观念同样重要。“整理国故”的力行者、“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说:“我们是立在家派之外,用平等的眼光去整理各家各派或向来不入家派的思想学术。我们也有一个态度,就是:‘看出它们原有的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我们没有‘善’与‘不善’的分别,也没有‘从’与‘弃’的需要。”(同上书,第221页。 )这说明,存疑、平等精神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一直得到倡导和贯彻。
“整理国故”直接孕育于五四之中,明显汲取了五四民主精神。首先,它是作为保守阵营的批判者、对立面而出现的。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了《国故》月刊,标榜“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上基本沿袭了清末国粹主义。在此背景下,新文化阵营提出了“整理国故”问题。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这一看法得到胡适等人的支持。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揭橥“整理国故”的旗帜。他认为“新思潮的意义”,只是一种“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因而对“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的态度应该是:“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可见,“整理国故”是针对文化保守主义而产生的,一开始就有别于旧式国学家,而打上了新文化的烙印。
“整理国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跨越了国粹主义的泥坑,而把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问题引向深入。胡适等人的“国故”不限于精华或国粹,“整理”也不同于守旧者的“保存”、“昌明”。他强调:“‘国故’是‘过去的’文物,是历史,是文化史;‘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织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不论国粹国渣,都是‘国故’。我们不存在什么‘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北大研究所的态度可以代表这副精神,决不会是误解成‘保存国粹’、‘发扬国光’”。(胡适:《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月刊》,第1卷,第1号,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这种辩证地认识传统的态度,摒弃了迷古、恋古心态,有利于客观的评判和研究。“整理国故”没有局限于资料“整理”,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他们既以现代观念发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胡适说,“输入新知识与新思想固是要紧,然而‘打鬼’更是要紧”,“只为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 )发见的种种病菌。只为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所以,要“整理国故”,“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 4册,117、11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重在给经、史、子、集“辩伪”的“古史辨派”贯穿了这一宗旨。罗根泽编成《古史辨》第四册(主要为诸子学论著)时,顾颉刚在序言中指出:“我们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帝系代表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为伦理的偶像,经学为学术的偶像。研究古史就是要打破这些偶像。“我们的破坏,并不是一种残酷的行为,只是使他们各回复其历史的地位”。可见,这与批判孔教迷信的实质是一致的。
就研究范围和重心而言,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整理国故”也体现了对全部传统,尤其是非儒学派的重视。胡适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773页, 北京,中华书局,1991。)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承批孔之余波,下开“整理国故”之先河。蔡元培认为此书有四个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反映出五四新文化的部分特质。他们还研究民间白话文、歌谣、民俗,从而把学术重心由清末的经、史、子、集扩大到民间文化与社会心理方面。这不仅进一步剥去“正统文化”的光环,而且适应了五四“白话文”的学术需要,凸显了传统文化的平民性。这都是晚清学者不能企及的。因而“整理国故”既继承、发展了晚清进步学术传统,又融入了五四民主精神。
二
“整理国故”并非自然科学,却与五四的科学主题相通。五四以后,思想界发生科学与玄学的争论,涉及如何认识科学的本质和功用问题。与“玄学家”把科学局限于“自然科学”不同,丁文江强调科学精神及方法的普遍适用性。他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要屏除个人主观的成见……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53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这是丁文江、王星拱等“科学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当时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文学者也在向传统学术领域推广“科学”。他们是“科玄”之争中“科学派”的支持者,又“以‘国故’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科学也”。(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64页,上海, 群学社,1927。)就此看来,“整理国故”立足于弘扬五四的科学主题。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整理国故”的“科学精神”与自然科学的表现形式不无差异。邃于国学的曹聚仁认为,“科学的态度”应该包括:崇尚事实,包括高度之精确与不杂私意;审谈结论,包括论断时之不自是与怀疑;力求明晰,包括不喜隐晦、模棱及无结果等。像丁文江一样,胡适把“科学”化约为“科学方法”,并把美国的“实验主义”与传统的实证学风融会起来。“整理国故”者不排斥西学方法和观念,但重视具有实证精神的考据学。吴文祺认为,国故学主要有下列几种学问:考订学、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清代“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胡适分析了清代“朴学”如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订学包含的“科学精神”,认为汉学家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撇开汉学家思想观念的局限性不谈,胡适的看法不无道理。
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倡导者对“整理国故”的科学性充满信心,即使对此运动心存疑虑的毛子水也认为:“‘国故学’可以算做——而且必须算做——现在科学的一种。‘科学的精神’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就是从前人所说的‘求是’”,“国故的研究,大半的事情就是疏证。三百年来,这种疏证的学问,倒是一天比一天精密。他的最大的利益,就是能够使人生成‘重征’‘求是’的心习”。(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133、13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在吴文祺看来,“国故学”之于社会科学,犹如数学之于自然科学一样重要,既是“研究中国的哲学、文学……的基本学问”,“也可藉此养成我国人所最缺乏的重征求是的科学精神”。(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49页。)傅斯年也认为, “整理国故”的贡献超出了传统学术本身,“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140页。 )当时一些科学家和新文化人都把“整理国故”看作科学的必然延伸和结果。杨杏佛认为,“自科学思想输入中国以来,惟整理国故一方面略有成绩”,因此,“真正懂科学的人,都承认国故学是科学的一种”。(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 第46页。)
近代科学思想的普及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从“新”到“旧”的过程。最先接受科学及其精神者主要是新式学校的学生,传统文人学士知之不多。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人们对科学本质及功用的理解多限于器物层面。不妨说,“整理国故”也是向人文学术领域范示、普及科学精神的有益途径。胡适指导下的北大固然如此。在南京,东南大学国学院于1923年制定了“整理国学计划书”,规定成立“以科学理董国故”的“科学部”和“以国故理董国故”的“典籍部”。计划分“学说”、“图谱”、“器物”三端,“以科学方法理董国故”,并强调这些都与其他科学发生关系,“例如图谱则入专家之范围,器物则取考古之方法。或共同搜罗古图谱古器物,或仿造之,改作之,不待言也”。(《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国学丛刊》,第1卷, 第4期,1923。)这反映出国学领域的科学意识有所增强。
清代实证主义学术确有一定的科学精神,对于改变中国士大夫的模糊性、会意性思维不无作用。然而,如果把普及“科学精神”的任务完全寄托于“考据学”,则显然过于自信。事实上,“整理国故”没有局限于考证方法,而是更借助于近代西学方法和观念。胡适多次总结“整理国故”的途径,如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研究的范围”,“系统的整理”,以及“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西学方法和材料)。关于“系统的整理”,胡适阐释尤多。他认为这应包括:1.索引式的整理,给浩瀚的古书编制“索引”,便于使用、阅读,这是“提倡国学的第一步”;2.结帐式的整理,把历代的校勘、音韵、训诂、注解成绩进行总结研究,如清代的《墨子间诂》、《荀子集解》等书;3.专史式的整理,应写出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各种专史。(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197—202页。)这里,“专史式的整理”不是传统的“学案”,而是以现代学术方法撰写的著作。正如曹聚仁所说,“国故学者,记载此思想之生灭,分析此思想之性质,罗列此思想之表现形式,考察此思想之因果关系,以合理的系统的组织的方式述说之也”。(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64页。 ))这种研究非“考据学”、“义理学”所能胜任,而是主要依靠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思想。事实上,“整理国故”不仅产生了重在考据的《古史辨》,也出现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先秦政治思想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等大批贯穿近代方法和思想的“专史”。因此,“整理国故”的科学精神不限于考据学一隅。
三
“文学革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与“整理国故”当然不同。前者重在文体、文风的革新,后者重在传统学术的研究、阐述,但两者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革新”针对“传统”,又以“传统”为基点。陈独秀、胡适等人指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时,必然对传统文学进行一番研究、清理。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传统”成为越来越不可回避的环节。五四以后的学者认为,“新文学运动”贯穿着现代精神,而“整理国故”则体现历史观念,两者不可偏废,而且“新文学运动”需要“整理国故”。何以言之?文学家郑振铎指出:“第一,我觉得新文学的运动,不仅要在创作与翻译方面努力,而对于一般社会的文艺观念,尤须彻底的把他们改革过。因为旧的文艺观念不打翻,则他们对于新的文学,必定要持反对的态度,或是竟把新文学误解了。……第二,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
如果说,这里“第一”条重复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主题,那么,后者则总结了“文学革命”的经验,体现出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质言之,“新文学运动”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问题,而且是如何运用新思想解决“传统”与“创新”的问题。这是文学家“整理国故”的主要根据,王伯祥也有类似看法:文学的价值不专在“片面的艺术欣赏”,而在“作家的内心”,所以既要传播外国的文学原理和思想,也要汲取中国文学的营养,“中国历来的文学精神都散附在所谓‘国故’之中,我们若要切实地了解他,便不容不下一番整理的工夫”。(王伯祥:《国故的地位》,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在此意义上, 顾颉刚不仅肯定“整理国故是新文学运动中应有的事”,而且把“新文学与国故”看作“一种学问上的两个阶段”,因为“生在现在的人,要说现在的话,所以要有新文学运动。生在现在的人,要知道过去的生活状况,与现在各种境界的由来,所以要有整理国故的要求”,“国故里的文学一部分整理出来了,可以使得研究文学的人明了从前人的文学价值的程度更增进,知道现在人所以应做新文学的缘故更清楚”。(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212页。)
在这里,他们统一了两者的辩证关系,把“整理国故”看作“新文学”的必经途径和深化阶段。事实上,两者在五四以后可谓互相推动,相得益彰。一方面,新文学运动促进了整理国故的兴起和发展,如勃然而兴的民间文学研究、古典小说考证都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成就并非完全移植西学,而是广泛地汲取了中学营养,郭沫若的新诗汲取了《楚辞》的营养,鲁迅的小说、周作人的散文受《庄子》影响尤深。五四以后的文学家大多经受了传统文学的陶养。现代文学形式、思想观念程度不同地植根于“整理”后的“传统”土壤中。
“整理国故”与新文学在组织上的代表性事件是新南社的出现。清末的南社重在提倡民族气节,不无国粹主义色彩。民国初年,民族主义思潮低落,南社活动也因思想、组织分歧而停顿。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南社面临新的调整、选择。1923年5月,柳亚子、叶楚伧、 胡朴安、余十眉、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徵等人发起组织新南社,原来的“南社”则逐渐解体、消亡了。新南社以建设新文化为标帜,支持新文化运动,欢迎“民主”和“科学”,“只有打倒旧文学一点,因为习惯的关系,最初觉得不能接受。到后来,也就涣然冰解了。不过,我应该用怎样的方法,才可以参加这一个运动呢?于是就有改组南社为新南社的计划出来”。(柳弃疾:《南社纪略》,110页,台北, 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除柳亚子和余十眉外,其他发起人都是《民国日报》的骨干。可以说,新南社以《民国日报》为大本营,实际上成为新文化阵营的羽翼。
那么,如何推动新文化的深入发展?叶楚伧起草的发起宣言表示,除了“对于世界思潮,从此以后,愿诚实而充分地向国内输送”外,“新南社对于国学,从今以后,愿一弃从前纤靡之习,先从整理入手。……国学本身是否占有世界学术中的相当位置,在未经整理以前,谁也不能下这断语。我们既不是神圣,怎敢代世界支配一切,所以第一步工夫只是整理”。(同上书,第112—113页。)作为文学团体,新南社的活动重心并非“整理国故”,柳亚子甚至还对南社宣言中列入“整理国故”一条心存疑虑,担心走入“迷信国学万能”的歧途。但是,像胡适等人一样,新南社成员已不同程度地将新文化与“整理国故”统一起来。《民国日报》在传播新文化的同时,开设了“国学周刊”,出现了胡朴安等国学大家。
四
如果说20世纪初年的国学思潮多受民族主义和西学东渐推动的话,那么,“整理国故”的思想主旨则是创造新文化。当时“整理国故”的批评者多置身其外,虽能发现不良苗头,但并非完全理解倡导者的主旨。
就主流来看,从事整理国故者大多调和新旧,将“国故”作为新文化的基础之一。张煊的言论代表了比较保守的《国故》月刊。他认为,“国故”和西学都是创造新文化的原料:“譬诸造纸,将来之新文明为新纸,国故犹败布,欧化犹破纸,为造新纸故,破纸固不可弃,败布亦所当宝,败布与破纸其能改造为新纸则一也。……吾人之研究国故,非为保存败布,实欲制造新纸”。(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144页。)他强调“国故”的价值,但没有拒绝新学, 而是融合中西。被看作东方文化派开创性人物的梁启超也呼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救西洋的文明,将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文明。大体而言,这代表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如东方文化派、某些国学家)的基本看法。他们融合中西,注重以旧开新,但缺少对“国故”的批判精神,汲取西学也多局限,思想上不无“中体西用”的色彩。然而,他们并非“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导者和主体。
“整理国故”的呼声出自新文化阵营,他们始终把创造新文化作为终极关怀。胡适把“新思潮的意义”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前三者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再造文明”。这可以看作是“整理国故”的纲领。吴文祺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他认为新文化需要“整理国故”,主要因为:我们无论评判何种学说,“先须明其思想学说的本来面目”,“否则赞成便是盲从,反对便是盲抗!”再则,“无论何种新学术新思想,都不是从天神首中爆发出来的,或是凭藉过去的基础而继长增高,或是根据了前人的研究而另辟新基。……章太炎音韵学上的创见,未始不是食乾嘉学者之赐;胡适之的文学革命论,不能不说章实斋和王静庵都有启示的力量。这是温故创新的好例”。(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39、36—37 页。)这种总结反映了部分事实,又折射出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实际需要。
“整理国故”的争论主要发生于新文化阵营内部,实际上涉及如何理解“新文化”的本质问题。关于“五四新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在当时及其后都不一致,即使新文化阵营一致认同的“民主”和“科学”也是如此。接受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人,一开始就因西学渊源的不同而潜伏着分歧,而且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扩展而加剧。正如胡适后来所说:陈独秀等人接受“苏俄”思想后,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才是真正的‘民主’”,“但是在我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210页,北京, 华文出版社,1992。)当然,不能说胡适阐述的“民主”、“科学”完全准确,但也不能认为只有陈独秀等人宣传的“苏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和民主。“整理国故”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并非同道,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其背离新文化的本质和主流。
“新文化”是一个广泛而多层次的概念,内容丰富。它既可涵盖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层面的国民性改造,也应包括学术领域的批判、创新。“整理国故”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歧异反映了人们对不同文化层面的关注和运思。胡适、顾颉刚等经受严格学术训练的大学教授们,更多地着眼于书本,偏重学术思想层面。他们不仅注重深化、扩展新文化运动的“批孔”和“文学革命”,也率先注意传统文化的价值,凸显本国学术对于文化创新的意义。另有些新文化健将们,由于专业的关系(如李大钊之于经济学),或由于编辑、记者的身份(如陈独秀)则更多地关注社会、政治层面,赞赏改造社会的“主义”。这种“主义”不能从传统文化中直接找到,而不能不借重俄国“方案”。于是,在他们的观念中,“新文化”也主要被“俄化”取代。
“新文化”是通过具体途径和领域实现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学术与文化总是共生共荣,学术是文化的基础。政治层面的“主义”反映了社会趋向、民众意识,学术则是民族文化的根基,也是新文化深入发展的基础。因而,“整理国故”虽与“政治”相距较远,但不能据此断定它背离新文化的本质。其二,新文化不仅需要汲取西学,而且必须批判、改造、转化传统。创造新文化是一个融合中西、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我们不能根据“西化”或“传统”的程度而判定思想文化的优劣,自然也不能因“整理国故”涉及“传统”而否定其“新文化”性质。
五
当然,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有时难免圆凿方枘。胡适等人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古籍,关怀着“再造文明”,研究方法和思想观念也博采西学。然而,“整理”者并非尽然。国学家的思想差异很大:有些国学家局限于传统的考据方法,拘泥于文字考训;有些学者不无崇古、恋古心态,评价、阐释也有夸张成分;有些深通西学的研究者,以西释中也多附会之处,或者夸大古学的现代因素,或者把古学生硬地纳入现代概念中。学者的思想倾向也是鱼龙混杂。曹聚仁认为,当时北大国学研究所、无锡国学专修馆和上海同善社的国学专修馆,“虽同标一帜,其实三者必不能并立”,“北京国学研究所之‘国学’,赛先生之‘国学’也;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冬烘先生之‘国学’也;上海之国学专修馆,神怪先生之‘国学’也”。(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 第84—85页。)这种评价虽非完全准确,但反映了国学家思想分野之一斑。少数国学刊物确有保守色彩。宋育仁的《国学专刊》就与北大《国学季刊》对立。该刊一面宣传孔教和旧道德,一面又与新文化阵营为难。当然,宋育仁及孔教会的“国学”并非学术主流。
“整理国故”的倡导者胡适也有缺陷。他创办《读书杂志》,赞赏青年像王念孙父子那样读古书,又为青年开列宽泛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甚至肯定“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第327页。)这显然不切实际,不免分散了青年学生对自然科学和西方学说的注意力。胡适本想以“整理国故”来普及“科学方法”,但到1928年,他认识到:“纸上的学问也不是单靠纸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单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够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帮助方法”。因而,他强调:“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术”。(同上书,第4 册,第114页。)这体现了倡导者对这一运动的反省和纠正。
“整理国故”虽有偏差,但没有改变其主旨。综观其学术成就和思想主流,它仍然沿着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发展,“整理国故”成绩巨大。重在价值评判和以西学方法撰写的学术专史,明显地包含了五四精神。它们在改造、更新传统,推动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无需赘述。应该指出的是,“整理国故”中的考证之作也不同程度地具有新文化意蕴。曹聚仁指出:国故学之新倾向,昭然显呈于吾人之前。新考证之盛行,即昭示吾人以国故学中心之所在。案考证之工作,清初已发其端,乾嘉而后益盛。近顷之考证,原无以出清儒之范围,所不同者:清儒之考证,其方法东鳞西爪,不可捉摸;近顷之考证,其方法较为具体,学者得袭取而用之也。考证之已著成绩者凡三:胡适、俞平伯之小说的考证;梁启超、顾颉刚之史的考证;陆侃如、吴立模之诗歌的考证。
这些“考证”大多深化了新文化运动的本质。顾颉刚、钱玄同、罗根泽等人发扬存疑、平等的学术精神,形成“古史辨派”。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不失为“批孔”之后的又一轮学术革命。它在否定“独尊儒学”之后,进一步廓清了正统儒学造成的学术迷雾。此论轰动一时,赞誉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其具体观点存在不准确甚至片面之处,但对中国学术更新、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的批评者郭沫若在1930年承认,“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见识是有先见之明”。(《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版,第1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古史辨”的另一事例是五四后关于老子生活年代的考证。清末康有为否定《史记》说法,主张“孔先老后”,为尊孔提供了学术依据。二三十年代,老子年代的讨论成为学术热点,发表论文数十篇。虽未达成共识,但关于先秦诸子年代的研究却不断深化,成果累累。论者平等论争,畅所欲言,传统学术界经受了现代学术精神的陶冶。
五四以后,经、史、子、集的校勘与注释成就巨大。这些校注的基本方法与前人并无大异,但思想观念和客观效果则有所不同。有些校注成果实已融会近代进步思想。例如,一些老庄注本(如陈柱的《老子集训》)重视阐发“民主”、“自由”思想。又如,《墨经》校注繁荣一时,梁启超、章士钊、胡适均发表论著,反复讨论。这不仅揭开长期尘埋的学术谜底,而且在传统学术领域撒播了科学的种子,推动了中国逻辑学的兴起和发展。
五四新文学不限于“创作”层面,还应包括学术研究。在众多的古典文学考证成果中,“新红学”便为典型事例。清末民初,西方思想和文学理论开始渗入《红楼梦》研究,但仍不能驱散“索隐派”的迷雾。胡适于1921年写成的《〈红楼梦〉考证》算得上“整理国故”的一个范例。它突破“索隐派”的附会、臆说,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从而认为“《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中做的”,“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这篇“考证”给“红学”研究带来新气象。次年俞平伯写了《红楼梦辨》一书,完善了“自传说”,顾颉刚为之作序,支持此说,从而形成“新红学”。“新红学”不是激进的西学思潮,但摒弃了“索隐派”的主观臆测,而更接近于历史真相。此后,考证《红楼梦》作者、版本的论著迭出,“红学”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也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更新。“整理国故”的方法不尽相同,撇开那些以西学方法和思想撰写的众多论著不说,即使“考证学”也与沉迷故纸的乾嘉学派或空谈性理的道学家显然有别,而不同程度地普及或深化了民主和科学精神。
“整理国故”不无偏差和缺陷,也不可能短时期内实现胡适“再造文明”的期望。然而,除了少数抱残守缺的国学家外,“整理国故”的主流非但没有背离了五四新文化的本质,而且是“新文化”在学术层面的深入发展。认识这一点,不失为理解五四精神长期影响于民国学术文化的重要途径。
[收稿日期]1999-10-25
标签:国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胡适论文; 读书论文; 新文化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古史辨论文; 民国日报论文; 科学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