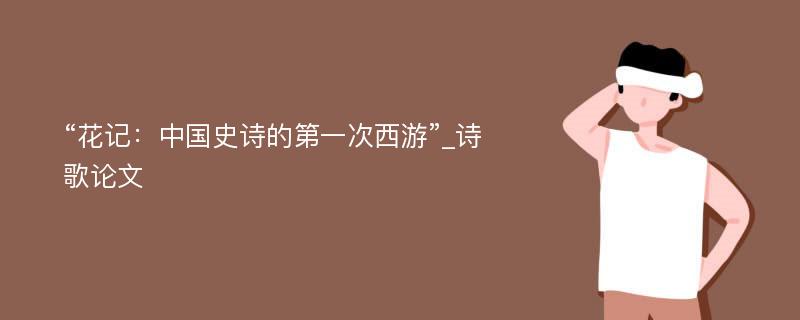
《花笺记》:第一部中国“史诗”的西行之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行论文,花笺论文,之旅论文,第一部论文,史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木鱼书《花笺记》是产生于明末清初的广东说唱文学作品,在东南一隅以文笔声调冠绝一时,所谓“曲本有《西厢》,歌本有《花笺》”。该作全文三万余字,演绎梁亦沧与杨姚仙的才子佳人故事,就内容而言乏善可陈,近现代以来罕为人知,实属正常。不同凡响的是,这部方言作品,在19世纪,意外地搭上了西去列车,成为环球旅游的“世界文学”读本。《花笺记》开启这一国际旅程的发端之作是1824年英国人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英译的Chinese Courtship。此后,德、荷兰、丹麦、法译本相继问世。据统计,在19世纪,仅目前所见西译本就有5种文字、6种全译本①。译作语种之夥、游历之广,在早期中国文学西译史上极为罕见。它在西方的影响,以德国诗人歌德(Goethe,1749—1832)的评价臻于至点,他称赞《花笺记》是“一部伟大的诗篇”,并据此创作了闻名遐迩的《中德四季晨昏吟咏》。美国学者梁启昌指出:严格地说,既然歌德看不懂中文,启发歌德灵感的并不是《花笺记》原文,而是汤译《花笺记》。“奇怪的是,虽然汤氏的译作对歌德有一定的影响,但至今似乎尚未有一位现代学者对Chinese Courtship 作一番深入的评价。”②梁氏此论,发表于2008年,几年过去了,关于汤译《花笺记》的研究,依然罕有力作。 19世纪《花笺记》以多种文字“游历欧洲”,如果说这是它生命的第一春,那么20世纪的“荣归故里”,则可以看作是它生命的第二春。20世纪初期,随着郑振铎、柳存仁、陈铨等著名学者的海外访书与汉籍著录,《花笺记》这部在中国文学转型之际几乎被遗忘的作品,因海外藏本的丰富、歌德的赞赏峰回路转而屡被引述。最近几十年,竟先后出了三个校本。不知是有意的屏蔽,还是无意的忽略,在相关序言中,论其艺术成就,学者们不是引述郑振铎的赞词,就是借用歌德的嘉奖,对于该作在英语世界的真实处境,尤其是汤译本遭遇的种种尴尬,却始终没人提及,这显然不利于现代读者以平常心评估这部作品的真实价值。这种文学批评上“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为笔者平添了一份责任,即,结合汤姆斯的努力与英语世界的反响,还原该作西行之旅的历史生态,进而反思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承受的重压、承担的使命。 一 选译缘由:史诗、才子书、木鱼书 尽管被歌德视为“一部伟大的诗篇”,但是,在明清通俗文学作品中,《花笺记》算不得上乘佳作,相比于《三国》、《红楼》等经典之作,更是叨陪末座、屈居下品。有趣的是,《花笺记》既非经典,何以在19世纪早期就搭上了西去列车,顺利地被引入西方语言系统? 首先,汤姆斯欲藉《花笺记》这一长篇叙事诗弥补中国诗歌、尤其是史诗(Epic poems)在英语世界的阙如。 “木鱼”作为一种地方说唱文学,一方面讲究韵律和节奏,具有诗歌的文体特点;同时又贯穿以多个人物和复杂情节,具有小说的文体特点。清代评点者钟戴苍评点《花笺记》时,在文体上将之定义为“歌本小说”③。这种文体上的双重属性,很早就被英语世界的读者捕获。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在他编著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指出:《花笺记》是一部用“诗体”(in Verse)创作的“中国小说”(Chinese Novel)④。汤姆斯在《花笺记》的英文书名中也表明该作以“诗体”翻译。何以采用“诗体”?汤姆斯在序言中说:“尽管关于中国的作品已出版了很多,但他们的诗歌却几乎无人问津,这主要是因为汉语带给外国人的困难。除了偶尔翻译的一个诗节或几句诗歌,汉语让所有的人知难而退。现有的译作不足以让欧洲人对中国诗歌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于是我尝试着把《花笺,第八才子书》翻译过来。鉴于他们的多数诗歌仅由几句组成,可以想见,写起来或许一挥而就,相比之下,这部诗歌远长于一般的作品。尽管中国人喜欢诗歌,他们却没有史诗。”汤姆斯显然把《花笺记》看作是一首长篇叙事诗,将之比附为西方的“史诗”。 “中国无史诗”这一判断是随着黑格尔的《美学》广为传播的,但黑格尔本人并不懂汉语,他对中国诗歌的认识应该来自早期来华西方人士的汉学研究。在英语世界,据笔者调查,除了汤姆斯,较早提出这一判断的还有马礼逊,他在1825年出版的《中国杂记》(Chinese Miscellany)中说: The Chinese,we believe,have nothing that can be called Epic Poetry(我们相信,中国人没有可以称之为史诗的作品)。在同一著作中,关于中国诗歌,马礼逊还提出:中国诗大多篇幅短小。又说,诗歌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惊天地、泣鬼神。汤姆斯是为了印刷马礼逊编辑的《华英字典》而被东印度公司聘请到澳门的印刷者(printer),他对马礼逊的上述观点理应格外熟稔,这些观点无不促动粗通汉语的汤姆斯奋力一搏,尝试着翻译一部相当于“史诗”的长篇巨制,以弥补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阙如。 其次,汤姆斯译《花笺记》还在于他认识到这部作品在中国享有“第八才子书”的盛名。 “才子书”这一概念在19世纪中期的欧洲格外风靡,它几乎是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代名词,它对于中国作品质量高下的品定,甚至是歌德的“世界文学”都不能取代或超越的。汤姆斯或许是第一个提到“才子书”的英国人。1820年,《亚洲杂志》(The Asiatic Journal)分四次连载了汤姆斯摘译的《三国志》(San-kwo-che),题名《著名丞相董卓之死》(The Death of the Celebrated Minister Tung-cho)⑤。汤姆斯首先翻译的是出自金人瑞(Kin-jin-suy)之手的一篇序言,据此推测,他采用的《三国演义》底本,应该是毛氏评改本,该版本在清代曾被称为“第一才子书”,汤姆斯把“第一才子”译作Te-yeh-tsae-tsze the work which evinces the highest literary talent,即“最具文采的书”。他虽然误把《三国演义》当成了史书,但却认为这是“描述中国内战的最著名的史书”,“它备受中国人青睐,不仅因为它的文学价值,还因为它对于彼时战争灾难的丰富而准确的描述”。显然,汤姆斯在译介《三国演义》的同时,也肯定了“才子书”这一评价体系自身的合理性。既然有所谓第一才子书,被钟戴苍推许为“第八才子书”(The Eighth's Chinese Literary Work)的《花笺记》自然值得翻译。 需要注意的是,汤姆斯引入的“才子书”在西方世界不胫而走、广为流传。比如,1838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在《中国开门》(China Opened)中将“十才子”理解为“十位天才的著述,精选小说集”⑥。1897年,美国传教士丁义华(E.W.Thwing)在《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中,把中国小说一分为二:历史小说和罗曼史,位列罗曼史之首的就是“十才子”。有趣的是他竟将“十才子”错译为“十个天才的儿子”(The Ten Sons of Talent)。其中第八种即《花笺》,英译名直接沿用了汤姆斯所译的Chinese Courtship⑦。直到1936年陈铨写作《中德文学研究》时,他还慨叹:“其实这十部书里面,真正够得上称才子书的,也不过《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其余比较相差太远。”但是,这个观念却被根深蒂固地沿用下来,以至于“最近德国人孔(Franz Kuhn)在他《好逑传》译本跋语里边,仍然把十才子书的标准来审定《好逑传》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⑧。“才子书”这一概念影响如此深远,或许是汤姆斯始料未及的。 再者,汤姆斯之所以选译《花笺记》还因为他当时身居澳门,作为广东说唱文学,该作在当时颇为流行。 汤姆斯于1814年9月2日抵达澳门,迅速建立印刷所,很快研制出适合中英文合印的活字,这批活字被看作是“中国第一批铅合金活字”⑨。第二年他就用这批活字印出了《华英字典》第一部,这部字典的封面,除了编辑者马礼逊的名字,还赫然列着印刷者汤姆斯的名字。《华英字典》主要依据《康熙字典》编译而成,但某些字词例句却并没照搬原著。比如,马礼逊在“花”字下援引《花笺记》作为例证⑩。仅此一条,汤姆斯就不难注意到《花笺记》的存在。木鱼的演唱在当时非常盛行。1828年澳门出版了马礼逊编译的粤语方言词典《广东省土话字汇》(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其中有一短语:“个头唱木鱼(They are there singing ballads)”(11)。在此,马礼逊把“木鱼”译作ballad,意思是民歌、情歌或叙事诗歌。这种说唱艺术如非喜闻乐见,马礼逊又何必将之纳入现行的汉语教材?汤姆斯说:《花笺记》“在中文中,其原来的文体,被称为木鱼(Mǔh-yu)”(12)。显然,虽然把《花笺记》译作“诗歌”,汤姆斯对其文体属性并不陌生,这或许正源于这一艺术形式本身的风靡。 此外,《花笺记》在当时应该不难购得。根据杨宝霖的研究,《花笺记》作者乃广东东莞人,书成于明末清初,存世之本,始刻于清(13)。在地理方位上,东莞与马礼逊、汤姆斯所居澳门仅一江之隔,两人之于《花笺记》可谓近水楼台。清政府对于西人购买中国图书虽有禁令,但他们还是可以通过中国助手或佣人设法购得。马礼逊在华购买的部分书籍现收藏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图书馆,笔者在特藏部发现了《静净斋第八才子书花笺记》和《第九才子书二荷花史》两种木鱼(14)。前者为“福文堂藏板”,这是清代中后期广州本地大量刊刻通俗文学作品的一家书坊。第二任香港总督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翻译的《好逑传》(The Fortunate Union)所用底本,也是“福文堂藏板”。由此可见,木鱼的演唱与坊间唱本的印刷在当时都是极为寻常的。就此而言,汤姆斯选译《花笺记》确实带有就近取材的特点。 二 翻译文体的选择与主流媒体的评论 很多迹象表明,汤姆斯最初决定用诗歌文体翻译《花笺记》时颇为纠结。这从他序言中援引的两个当代著名人物的评论就可见出。曾经觐见乾隆皇帝的小斯当东(Sir George T.Staunton,1781—1859)在《中国杂记》(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中说:“中国诗歌的难度尚未被充分估计到。”又说“中国诗歌既美且难,产生的原因与英国诗歌相似,即意象、隐喻、典故以及个别字眼的运用,如果不是那么陈腐或平庸,睿智而有教养的读者就会立即欣然接受。”(15)为说明中国诗歌的难解难译,汤姆斯还借用了第四任香港总督包令(Sir John Bowring,1792—1872)的相关论述。1821年,包令的《俄国诗歌选》(Specimens of the Russian Poets)第一卷出版后,有人指责“这些诗歌缺乏独创性”(16)。包令著文加以反驳,汤姆斯化用了包令的自我辩护词,指出:如果把沙俄换成中国,那么包令先生关于俄国诗歌的论述也适用于中国:“许多词语无法逐字直译,许多联想我们无从感知。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红’和‘漂亮’是同义词,可以一词两用。难道一个中国人会觉得还有什么比太阳更明亮,比海洋更宽广,抑或比晴朗的夜晚更美好的吗?还有什么比高山更庄严,比溪流(或花园)更富有诗意的吗?”(17)这些特殊的意象,对于西方人来说,不是显得过于陈旧,就是有些莫名其妙。汤姆斯引述小斯当东与包令的论述,旨在委婉地传达自己在翻译中面临的困难。 在当时,翻译诗歌,尤其翻译中文诗歌被视若畏途,这不是汤姆斯的个人感受,而是一个时代的畏惧。英国的《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评论员说:“事实上,以散文书写的中文作品或许被认为是极其简单的,并且也是容易读懂的;难懂的主要是他们的诗歌。在翻译散文时,我们通常可以借助那些表示数量、性别或时态的辅助性的文字;但在中文诗歌中,很多情况下,一个单独的字就代表一个完整的意义,而那个意义又隐喻或暗示着某种当地的习俗、或亦真亦幻的历史;而且也没有前边所提到的辅助性的文字。一首诗有的八行,有的只有四行,一个完整的句子由没有词性变化的单音节的字组成。所以,很明显,诗里的每个字都得精挑细选,因为诗句的美妙和优雅主要依靠它所使用的象征的力度、表达力和贴切,象征既要悦目,又要悦耳。因此要把中文诗歌翻译成外文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用口语翻译(verbally translated)诗歌,就会粗俗;此外也可能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如果意译(paraphrastically),原来的精神就会消失殆尽;也许译者会使用一种不那么有表现力的习语,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使用令人反感的概念。”(18)由此可见,在19世纪初期,英国人就充分意识到语言的不同、文化的差异为诗歌翻译带来的困难几乎是难以逾越的。 尽管如此,汤姆斯还是打算奋力一搏。因为包令翻译的《俄国诗歌选》出版后,在英国评论界受到的激赏远远大于批评,这让汤姆斯看到了希望。1823年6月《加里尼涅杂志和巴黎每月评论》(Galignani's Magazine and Paris Monthly Review)指出:“在文学研究和知识竞争频繁的时代,包令先生为自己赢得了一枚幸运的勋章,在这方面,很少有人会去追求,真正做到的就更少了。他让本国的有识之士第一次熟悉了一种以陌生的语言创作的诗歌,并且,通过诗歌,还让我们熟悉了一个全新的民族的国民情感和国内习俗——对我们而言,俄国人,在任何方面,都堪称是一个全新的民族。……我们之中,有谁会想到俄国人是智慧的、善于思考的、充满想象的书籍的阅读者?有谁会想到一个俄国人会去阅读诗歌,或者体验写诗的韵律?就算再异想天开,又有谁会相信世上竟然有一个具有诗人品格的俄国人?”(19)写作这段文字时,英国正逐渐步入工业革命和帝国巅峰的“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1837—1901),随着海外扩张的突飞猛进,通过异国文学作品展示一种陌生的语言、一群陌生的人、一个陌生的国度的文学尝试,是如此具有诱惑力!包令的成绩让任何一个踏上异国土壤、接触异国文化的人热血沸腾,出身低微的汤姆斯自然按捺不住,跃跃欲试。 除了包令译作的启发,法国人阿米奥(P.Amiot)与杜赫德(Du Halde,1674—1743)的中国诗歌翻译也激励着汤姆斯,并促使他小心翼翼地思考着自己的翻译文体。阿米奥翻译的乾隆诗歌(Eloge de la Ville de Mougden,Poёme composè par Kien-long Empereur de la Chinae)被小斯当东称为“欧洲人拥有的最完美的中国诗歌译本”。但是,小斯当东并不赞成他翻译文体上的“以文译诗”,他说:“如果以散文翻译诗歌,哪怕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会被认为是极不恰当又不尽人意的。”(20)对此,汤姆斯在《花笺记》前言中进一步说:阿米奥翻译的中国诗歌“没有保留原文的形式,翻译得再怎么准确,也只能给欧洲读者一个关于中国诗歌结构的不完善的概念”。同时,汤姆斯还提到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中辑录的几首《诗经》,他说像阿米奥的翻译一样,这些译作虽然形式上更为自由,有利于表达原作者的感觉和意图,但却因“文体过于散漫而不能反映原作的勃勃生气”(21)。小斯当东是19世纪早期最有权威的汉学家,他给予阿米奥译作的肯定,必然会激励汤姆斯在中国诗歌翻译领域有所作为;在翻译文体上,他也必然会主动规避“以文译诗”的前车之鉴。要保留《花笺记》这部“东方文学作品”的“原作精神”(the spirit of the original),汤姆斯自然会优先选择“以诗译诗”。 汤姆斯在翻译文体上的考虑不可谓不周详,但他的译本出版后,仍然在英语世界遭到猛烈抨击。《评论月刊》(The Monthly Review)指出这部译作缺少生动的叙事,尽管在形式上披着诗歌的外衣,却完全不具备诗歌的韵律,甚至很少有超过一般水平的散文性的书写(prose-composition)值得称道。还批评译作最后附录的中国女诗人小传和中国税务资料与该作内容迥异,附在最后实在不伦不类(22)。《东方先驱》(The Oriental Herald)指责汤译本用词野蛮拙劣,毫无美感。还说:“汤姆斯先生似乎不懂语法,他对英语语言的美妙,也所知不多。”又说:“我们相信他在很多地方都不幸地歪曲了原作。也许因为他对中国知识的一知半解,也许因为他对英语知识的了解更不全面;更有可能的是,他对两种语言都不甚了了。或许久居东方,破坏了他对记忆中的词语的精确辨析;无论如何,再也没有哪个作者能给一个词语做出更为不幸的选择了。”紧接着,评论员毫不客气地逐页挑出了19个带有语病的句子(23)。《评论季刊》(The Quarterly Review)的评论员称汤姆斯的翻译是“反韵律的译作”(anti-metrical translation);他结合故事发展脉络,找出了许多在西方读者看来荒诞不经的情节。文章结束时甚至不惜以侮辱性的口吻揶揄道:“在英国读者看来,中国诗歌碰到这么一个无能的译者实在是太不幸了!而且为了他自己的声誉,我们强烈建议他放弃中文研究,至少要等到他对自己的母语掌握得更加熟练之后再去研究中文。到那时我们再建议他继续从事铸字、排印的机械作业,而不要投机取巧地去做自己不懂的事。这种建议或许会被认为是与本时代的自由精神格格不入,而且,‘向知识进军’(march of intellect)的口号是想把我们的鞋匠和裁缝都变成哲学家和政治家,我们坚信这就是我们能给汤姆斯先生的最好忠告。”(24)这种夹枪带棒的忠告,无非是讽刺身为“印刷者”的汤姆斯就不该梦想着成为一个翻译家或汉学家。 除了这种正面的批评,西方学界对于汤译《花笺记》更大的否定来自于根本上的漠视与忽略。最典型的莫过于第二任香港总督德庇时,他1815年翻译的李渔小说《三与楼》(San-yu-low, or The Three Dedicated Rooms)就是由汤姆斯印制的,两人应该彼此认识,但对汤姆斯翻译的作品,德庇时显然不屑一顾。他1829年出版的《汉文诗解》(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是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诗歌的第一篇长篇大论,1834年出版了单行本,在英国汉学史上可谓史无前例。该作在时间上比汤译《花笺记》晚出5年,其中提到小斯当东、马礼逊等人关于中国诗歌的看法,对于汤姆斯及其译作却只字不提。不但不提,有时还暗讽。有评论员指出,德庇时在他翻译的《好逑传》(The Fortunate Union)序言中讽刺有人用“女主人”或“小姐”来称呼中国的婢女,实际上是剑指汤姆斯翻译的《花笺记》和《宋金郎团圆破毡笠》(The Affectionate Pair)(25)。又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在论及中国诗歌时,对于汤姆斯的译作同样三缄其口、避而不谈,直到1883年推出修订版时,才添加了一句:“被译成英文的最长的(中文)诗歌是汤姆斯翻译的《花笺记》;该诗采用七步格(Heptameter),译文相当乏味。”(26) 从主流媒体来看,汤译《花笺记》几乎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人们很容易单纯地从诗歌翻译质量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事实上,汤姆斯的身份与汉学界的偏见在当时或许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汤姆斯是为印刷马礼逊字典来华的印刷工。笔者发现,经汤姆斯之手刊印的书籍,封面上除了印着作者或编者的名字,往往同时还印着“印刷者汤姆斯”的名字,我们不该把这一举措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最初以印刷工招聘来华,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和卫三畏,除了以作者的身份署名的情况之外,笔者至今没看到他们以印刷者署名的作品。汤姆斯执着地把名字印在自己刊印的书上,或许恰恰因为这是他唯一的身份代码。没有资料表明他在来华之前受过良好教育,而当时从事汉学研究的英国人——小斯当东爵士、马礼逊博士、德庇时爵士等,或者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具有显赫地位。与他们相比,汤姆斯难免自惭形秽,为了自我推销,他似乎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哪怕是作为一个印刷者。 汤姆斯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个印刷工,遗憾的是这个身份却陪伴了他太久,甚至是他一生的职业标签。他没有像麦都思和卫三畏那样成功地完成了由印刷工向传教士或外交官的身份转型,更没有像此后来华的英国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那样成为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但在书籍印刷和出版过程中,汤姆斯的身份确实发生了变化。2013年,笔者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借到汤姆斯于1851年编译的另一力作——《中国商代古器》(A Dissertation On The Ancient Chinese Vases of the Shang Dynasty from 1743 to 1496,B.C),书里夹着一份汤姆斯同年翻译的罕见小报,虽然这时他早已结束了澳门的工作回到英国20余年之久,汤姆斯名字后面唯一的身份标签还是印刷者。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商代古器》译者的名后,却悄然添加了新的身份标签:“《宋金郎团圆破毡笠》与《花笺记》等著的作者”(Author of“the Affectionate Pair,”“Chinese Courtship,”&c.,&c.)(27)。两年后出版的汤姆斯的新作《中国皇帝与英国女王》(The Emperor of China V.The Queen of England)的作者名后,同样添加了类似的身份标签,只不过作品中又多出此前出版的《中国商代古器》(28)。由此可见,汤姆斯一生引以为荣的是他的文字著述,这是他用来定义自己的最大荣耀。 三 中西文化史上的价值 汤姆斯本人如此珍爱的译作,难道真的如英国媒体和汉学界说的那么一无是处吗?笔者认为,在中西文化史上,汤译《花笺记》在文献学、文学、社会学方面,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一,汤译本为《花笺记》保存下一个独特的中文版本,这虽与语言翻译无关,但该译本的文献学,尤其是版本学价值却在不断显现。 汤译本是中英合璧的双语版本,上中下英。上排中文虽是竖排,但行列顺序已根据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做了调整,从“由右至左”而“由左至右”。下排英文与上排中文逐行对应,虽乏韵律,表面看来却呈诗行。学界至今没有发现汤译本中文部分所依底本,这使该译作具有了版本学的价值。梁启昌说:“汤氏译本所附的中文原文可以作为研究《花笺记》版本问题的宝贵参考资料。”(29)但他本人并没有深入展开这一话题。有效利用汤译本版本价值的学者是梁培炽,他整理的《〈花笺记〉会校会评本》以现存最早的静净斋版《第八才子花笺》为底本,同时集海内外所见珍本会校会评而成。梁注本为《花笺记》的整理和传播做出了显著贡献,该注本根据汤译本做了不少修订,但仍有某些地方有待完善。 一是梁注本没有注出汤译本存在的所有不同之处,有的虽被校出,在注释中却写错了。比如,“棋边相会”一节中,汤本“会娇娘”梁本误注为“今娇娘”;“步月相思”一节中,梁本注曰汤本缺“泪湿花边谁为止,伤心无伴倚栏杆”一句,实际这一句并非缺失,只是被误放在了“留连不觉天将晚,日沉西岭正得回窗”一句的后面。由此可见,解决版本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梁注本的现有结论。校勘虽然琐碎,但却是一切文学研究的基础,容不得丝毫马虎。 二是汤译本中某些更为合理的文字经梁译本筛查后反被忽略,甚为可惜。如,“杨爷回拜”一节:女主角杨姚仙的父亲听说梁生尚未定亲,有心将女儿许配给他,却又不便开口,此处,某些版本为“杨君已有招婚意,此时未爱就开言”,显然不通。梁注本采用的是“杨君已有招婚意,此时心爱就开言”,不免唐突。汤译本为“杨君已有招婚意,此时未便就开言”,最近情理,反而没被梁译本采纳。根据情节发展,到了后面的“夫妻贪婿”一节,杨君夫妇还在犹豫:“几好便时开一句口”;再到“差仆接主”一节,梁生前来饯别,杨家再不开口,可能永远错失良机,此时,杨父才不得不亲自为女提亲,说:“老夫一女年登对,不鄙寒门愿结亲。”又如,“复遇芸香”一节,梁生请婢女芸香通情后,一直焦急地等待姚仙的回音,在后园再次见到芸香,喜形于色,梁注本云:“梁生望见丫鬟到,叫一声贤姐喜欢天,想必那人传密约,今宵曾否会神仙。”汤译本是:“梁生望见丫鬟到,叫声贤姐喜欢天,想必已经传密约,今宵曾否会神仙。”对于梁生来说,此时最想了解的是芸香是否“已经”向姚仙传达了自己的心意,完全没必要强调是否是“那人”传的密约,因为密约相会一事原本就只有梁生与芸香两人知道。 此外,汤译本的某些“错误”有着特殊的研究价值。如,汤译本中的“返”几乎全部写作“番”,有时“归”亦写作“番”。如“托眷钱衙”一节中,“一年任满返京日”汤译本作“番京日”;“待我归朝方接你”,汤译本作“番朝”。梁启昌曾指出,汤译本保留了番、胡等字眼,意味着他所采用的底本可能是明末版的。汤姆斯在序言中也说《花笺》“首次出现于明朝”(30)。虽然不敢就此断定该版本就是明版,但至少可以说它是现存最早版本的一个姊妹篇。汤译本所犯的另一独特错误是多数“睇”字写作“體”。如,“过婢陈情”一节中,“举头睇见一婵娟”,汤本作“體”;“闺门达情”一节中,“谁人睇见不心酸”,汤本亦作“體”。有趣的是,梁启昌发现四年后出版的马礼逊编辑的《广东省土话字汇》也犯了同一错。如,“你试體吓佢在處唔在”(You see whether he be at home or not)、“佢定要拉我但體戱”(He would drag me away to see the play)(31)。不知这一错误,究竟是该归因于该书的编者马礼逊还是印刷者 G.J.Steyn and Brother?这实际上从另一侧面显示了汤译本在当时的影响。 第二,在英国读者看来,汤译本虽然平淡朴素(plain and simple),但某些流畅的译文还是博得了评论员的赞赏。 如,《东方先驱》的评论员说:“‘柳荫哭别’一节,哪怕是在汤姆斯的译本中,都是极其优美的;因为心里的自然情感以真挚纯朴的方式喷涌而出。”(32)此外,《评论月刊》与《东方先驱》的评论员都很欣赏“主婢看月”一节的翻译,前者全文引述了这节内容,认为它足以显示译作的优点;后者节录了部分译文,指出主婢间的交谈如同出自哲学家之口。原作中,姚仙的婢女碧月说: 个年种得一带垂丝柳,小小青青到膊肩。 近日枝条都长大,屈指算来有几年。 近被西风吹几日,转番黄色冇乜光鲜。 我想人生亦似垂丝柳,中年就似立秋天。 秋过身衰和叶败,形容枯槁有谁怜? 绿杨尚有春归日,人老何曾转少年? 上述文字,汤姆斯翻译为: Some time has elapsed,since I planted a row of silken willows, Though small they were then green and reached to the top of my shoulders. I perceive to-day,the branches have grown long and stout; Let me count with my fingers,how many years have elapsed. The western wind,having of late blown for several days, I perceive they are blighted,and are stripped of their blooming hue. I think mankind in general,resemble those delicate willows, For on attaining manhood their autumn commences, When autumn is passed,the human trunk becomes weak and casts its leaves, Who has compassion on it when it appears withered and decayed? The blighted willows will again experience the return of spring; But man,as yet,when old has never become young.(33) 婢女借景抒情,以眼前的垂柳比喻青春易逝,劝小姐姚仙时不我待,及时行乐。整段文字是一个豁朗的明喻,没有浓缩的意象或暗指,翻译起来没有大碍,译文明白晓畅。在中文读者看来,这个明喻司空见惯,并无深意;但在英语世界,以柳喻人,却令人耳目一新。这段文字甚至使评论者联想到苏格兰诗人贝蒂的《隐士》(Beattie’s‘Hermit’)和希腊诗人彼翁的《墓志铭》(The Epitaph of Bion),并引述后一首诗的英译文进行对比。同样是用英语翻译的外邦诗,彼翁的《墓志铭》不但在内容上富于理趣,在形式上还兼顾了诗歌的韵律,相比之下,汤姆斯的译文充其量只做到了文从字顺而已。由此可见,在文字翻译方面,哪怕是赞赏,英国主流媒体对汤姆斯的肯定也是谨慎的。但无论怎样,译文的文学感染力终于得到了有限度的认可。 第三,汤译《花笺记》不仅个别章节的翻译受到评论者的赞赏,在当时,它还被当作西方人了解中国语言、社会、文化、经济的综合性读本。 汤译《花笺记》虽然在英语世界饱受批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借助译文,所有评论员都能完整地转述故事,他们对于人物的理解和情节的把握大致也是正确的。比如,当梁生为救杨父身陷重围时,评论员说他豪情有余、谨慎不足,显然不是个所向披靡的干将;故事以梁生娶姚仙、玉卿为妻,收芸香、碧月为妾收尾,评论员对中国的“一夫多妻制”虽多微词,但却理解这是中国作品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评论员对人物的宽容、对情节的体谅,至少说明一点:尽管汤译本缺乏诗趣、不合韵律,却是一个在内容上忠于原著的译本。由此,它被当成了一面反照中国的镜子,甚至有读者把这看作是它的根本价值。《亚洲杂志》的评论员就说:“如果《花笺记》不是一部有关中国的作品,对于该国的历史、习俗和文学,相比之下,我们了解得太少,它就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34)职是之故,汤译《花笺记》成了西方读者全面了解中国的文化工具。 有的读者把它当作汉语学习教材。《花笺记》的第二位英译者包令说:“汤译本附有中文原文,逐行译出(a lineal rendering),对于学习汉语的人来说是一大助益。”(35)有的读者从中捕捉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对之做一番社会学、文化学的解读。如,有评论员明确指出,“作为一部韵文小说,这部作品并没有置常见细节的讨论于不顾,如,女子们是如何涂脂抹粉的,是如何责骂婢女的,以及她们的闺中密谈,或者喝茶品茗。当男主角出游时,我们也可以一探他的‘行囊’;当他访亲问友时,我们也可以一窥他的宴饮。简而言之,除了没有秽语、缺乏才智,《花笺记》可以说是有些像《唐璜》。它使我们熟悉了中国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妻妾;而且,通过描述与故事相关的人物的职务和日常生活、友情及社会交游,关于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社会,作品传达出一个更为清晰的概念,它比我们看到的所有关于天朝帝国的描述都更为明确。事实上,作者似乎是想要精准地照搬人们的生活,生活简陋的部分与尊贵的部分旗鼓相当,而这是诗之为诗的唯一正当的旨归;而且,他还小心翼翼地实践了这一想法,因为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比他的画面更为真实和自然的了。”(36) 还有读者透过《花笺记》了解中国当时的国内经济状况。如《东方先驱》的评论员说:“文中有一段描述内容值得在此一提,即梁生由居所而被吸引到花园时的场景,因为它体现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即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只见史书层层堆满架,四围花气喷人香。桌上瑶琴安玉轸,金炉一个炷茗香。银筝玉笛悬墙上,双陆围棋放两旁。古画名诗垂两便,鲜花盆景列成行。起来窗外观风景,只见曲栏杆绕白莲塘。白鹤避人轻步月,风摆杨花飐水狂。塘上红桥通内苑,又见一带微波漾月光。两岸垂杨相对舞,采莲船系柳荫旁。游鱼浪起波中锦,水中云影白茫茫。”(37)这段文字出自“棋边相会”一节,西方人对它的兴趣或许缘于18世纪以来的“中国园林热”,但由此考察中国的经济,未免牵强附会。 需要注意的是,本着社会学、文化学立场阅读《花笺记》,中西差异就会以一种匪夷所思、光怪陆离的面貌呈现出来。某些措辞在西方读者看来莫名其妙、不可理喻。如,汤姆斯把“嫦娥”(Chang-go)看作是“中国的维纳斯”(the Venus of China);把哈德斯(Hades)看作是“中国的天堂”(the Chinese paradise)。在故事情节与内容方面,站在西方读者的角度,某些翻译非但不可思议,简直荒诞离奇。比如,《评论季刊》指出,中国男女婚前无缘见面,彼此之间也就不可能产生爱情。这部作品中的爱情本来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姚仙的为情焚物、玉卿的为情投江,在他看来就不免显得夸张做作,乃至滑稽可笑(38)。又如,“誓表真情”一节,梁生与姚仙私定终身,名香三炷,禀知神灵,在西方读者眼里,这种宣誓方式简直异想天开、荒唐至极。评论员甚至将这种习俗与文化上的差异转嫁到译者头上,他说:“汤姆斯先生翻译的古怪行为相当可笑,虽然这出自诗中最好的章节。”(39)由此可见,种种文化差异引起的惊诧比比皆是。 了解起于误解,止于理解,作为第一部以中国式“史诗”翻译到西方的长篇叙事诗,《花笺记》虽然不足以代中国“立身立言”,但它却使双方站在了通往彼此的路上,真正的交流终于成了一个可以企及的目标。 注释: ①③[美]梁培炽:《〈花笺记〉会校会评本》,第4页,第67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29)[美]梁启昌:《论木鱼书〈花笺记〉的英译》,《逸步追风:西方学者论中国文学》,第256页,第257页,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 ④(10)Robert Morrison: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in Three Parts:English and Chinese,Vol.Ⅲ.Part Ⅰ,London:Published and Sold by Kingsbury,Parbury,and Allen,Leadenhall Street.Macao,China: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By P.P.Thoms.1823.p.152.p.152. ⑤The Death of the Celebrated Minister Tung-Cho.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London:printed for Black,Kingsbury,Parbury,& Allen,Booksellers to the Honorable East-india Company,Leadenhall Street.Vol.Ⅹ.July to December,1820.p.525. ⑥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China opened,Vol.1.London:Smith,Elder and Co.,1838.p.468. ⑦E.W.THWING:Chinese Fiction,from The China Review,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Vol.22.No.6(1897),p.p.760-761. ⑧陈铨:《中德文学研究》,第19—20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E.W.Thwing与陈铨所列“十才子书”具体书目略有差异,前九种相同,分别为:三国志An Account of the Three Kingdoms;好逑传A Pleasing Love Story;玉娇梨The Two Fair Cousins;平山冷燕Two Young Literary Girls;水浒传An Account of the River Robbers;西厢记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Halls;琵琶记The History of a Lute;花笺Chinese Courtship;平鬼传The Pacification of the Devils。最后一部作品,前者为《白圭传》(The Story of the White Jade),后者为《三合剑》。 ⑨William Miln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alacca:Printed at the Anglo Chinese Press.1820.p.130. (11)(31)Robert Morrison: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Part.Ⅲ.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Macao,China.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by G.J.Steyn and Brother.1828. (12)(17)(21)(30)(33)Peter Perring Thoms: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London:Published by Parbury,Allen,and Kingsbury,Leadenhall-street,Sold by John Murray,Albemale-street; and by Thomas Blanshard,14,City-road.Macao,China.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24.Preface.Vii.Preface.Xii.Preface.Xiii.Preface.V.p.p.77-78. (13)杨宝霖:《花笺记研究》,东莞理工学院学报,第13卷第5期,2006年10月,第102页。 (14)Andrew C.West魏安(comp.):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马礼逊藏书书目),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1998.p.263. (15)(20)George Thomas Staunton: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and Our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at Country.London:John Murray,Albemable-street.1822-1850.p.p.65-68.p.114. (16)Sir John Bowring:Specimens of the Russian Poets: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Part the Second G & W.B.Whittaker,1823.Introduction. (18)The Quarterly Review,Vol.XXXVI.Published in June & October,1827.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p.498. (19)Galignani's Magazine and Paris Monthly Review.June.1823. (22)The Monthly Review.from January to April Inclusive.1826.Vol.1.London:Printed for Hurst,Robinson,And CO.p.540. (23)(24)(37)(38)Chinese Courtship,The Oriental Herald,and Journal of General Literature.Vol.Ⅸ.April to June,1826.London:Printed for the Editor,and Sold by all Booksellers.MDCCCXXVI.p.25.p.22.p.18.p.19. (24)(39)(40)The Quarterly Review,Vol.XXXVI.Published in June & October,1827.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p.511.p.505.p.507. (25)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London:Parbury,Allen,and Co.,Leadenhall Street.May 1830,p.32. (26)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London:W.H.Alien.1883.p.704. (27)A Dissertation On The Ancient Chinese Vases of the Shang Dynasty from 1743 to 1496,B.C.Illustrated with Forty-two Chinese wood engravings.By P.P.Thoms,Author of “the Affectionate Pair,” “Chinese Courtship,” & c.,& c.London:Published by the author,12,Warwich-square; and sold by James Gilbert,49,Paternoster-row.1851. (28)The Emperor of China V.The Queen of England.A Refutation of the Arguments Contained in the Seven Official Documents.Transmitted by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at Hong-kong Who Maintain That the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ain Insulting Language.By P.P.Thoms,Author of“the History of Sun-king”:“The Chinese Courtship”:“The Vases of the Shang-dynasty”; & c.,& c.London:Published by P.P.Thoms,Warwick-square.1853.“the History of Sun-king”即“the Affectionate Pair”,这是汤姆斯1820年翻译的《古今奇观》中的《宋金郎团圆破毡笠》。 (32)The Oriental Herald,and Journal of General Literature.Vol.Ⅸ.April to June,1826.London:Printed for the Editor,and Sold by all Booksellers.MDCCCXXVI.p.23.汤译本“柳荫哭别”误译为“竹荫哭别”Taking Leaving Beneath the Ramboos. (35)Chinese Poetry,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London:printed for Kingsbury,Parbury,& Allen,Booksellers to the Honorable East-india Company,Leadenhall Street.Vol.XX.July to December,1825.p.408. (36)Sir John Bowring:The Flowery Scroll A Chinese Novel,London:WM.H.Allen & CO.,13,Waterloo Place,Pall Mall,S.W.1868.pre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