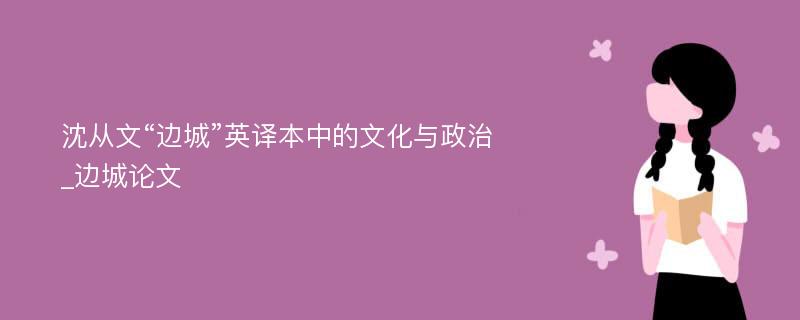
沈从文《边城》四个英译本中的文化与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城论文,文化与论文,政治论文,英译论文,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1934)迄今已有四个英译本,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外译史上,是少见的现象。第一个译本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直译为《翠翠》)由美国作家、翻译家项美丽(Emily Hahn,1905-1997)与中国现代诗人、作家、出版家、翻译家邵洵美(1906-1968,笔名Shing Mo-Lei,辛墨雷)合译,在《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1936年2卷1—4期连载。第二个译本The Frontier City由翻译家金隄(Ching Ti)和英国作家、翻译家白英(Robert Payne)合译,1947年由英国伦敦的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公司出版;该译本在1982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再版。第三个译本The Border Town由翻译家戴乃迭(Gladys Yang)翻译,1962年初刊于英文刊物《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10—11号,1981年收入戴乃迭翻译的沈从文小说集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边城及其他》)中,列入中国文学杂志社的“熊猫丛书”(Panda Books)出版。第四个译本The Border Town由美国汉学家、翻译家金介甫(Jeffrey Kinkley)翻译,2009年由HarperCollins Publishers出版。四个英译本跨越了73年时间,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英译的历史,也透射了《边城》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的前世今生和沧桑巨变。 一 想象中国:从浪漫到写实 项美丽1935年作为《纽约客》杂志派驻中国的记者来到上海,不久认识邵洵美。二人当年合作翻译《边城》,1936年初在《天下月刊》连载。项美丽、邵洵美的《边城》译本(以下简称“项译本”)没有显著改变原作的语序与段落,没有对原作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和删减。在中国新文学翻译缺乏经验、市场,目标语趋向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项译本在“忠实”与“传神”方面,能做到如此程度,实属难能可贵。① 项译本唯一对原作明显的背离,是书名的翻译。译者没有直译“边城”,而选用女主人公“翠翠”(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的名字作为书名,赋予其“翠玉”或“碧玉”之意。项美丽在译本前言中对此解释说,之所以没有把“边城”直译为“the Border Town”或“the Outlying Village”,是因为这容易让西方读者联想到英美文学中的西部故事或边疆故事;而在中国文学英译中,如此处理方式也有先例可循,她举的先例是京剧故事《红鬃烈马》被译成Lady Precious Stream(1935年英文版《王宝钏》)。其实,在西方,以人物名作为小说标题,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此翻译,倒也切合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习惯。唯独两个“Green Jade”的重复,直接把汉语中表示人物小名、昵称的重叠词转换成英语,使中文中的单数,变成了英语中的复数,一个“翠翠”,变成了两个“Green Jade”,这显然是不适当的。 对于《边城》中大量存在的地方习俗、历史人物的翻译,项美丽反对用脚注的方式处理,她认为在句子的中间打断读者阅读,让他们把视线转到页下或书后去看注释,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情。为解决读者阅读上的障碍,译者采用了增量翻译的方式,即在正文中通过增加句子成分和容量,对富含文化信息的词语加以解释。译者对如此处理方式抱有信心:“我们发现这部小说是如此有魅力,以致我们甘愿冒失去原作的散文节奏,也愿意与读者分享它。因为我们相信,《边城》还会在英语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下来。”②项译本中,这样的增量翻译有多处采用。如第五章写到端午节时,顺顺知道渡船老人一家生活困难,就送了他们许多粽子。项译本把“粽子”译为“rice puddings”,然后加入了一大段文字解释粽子的形状、成分和来历:“which were wrapped in palm leaves in the shape of small bound feet.These little cakes are especially made for Dragon Boat Festivals,in memory of a Chou Dynasty courtier who drowned himself because of grief.The cakes are made of sticky rice,but as to why they are moulded into the shape of little feet,nobody knows.”再如第三章介绍湘西端午节习俗时,有一句“用雄黄蘸酒写王字”,这一句被增译为“painted the character ‘Wong’ with orpiment wine on their foreheads,like this—王—because tigers wear this pattern of wrinkles on their brows,and they thought it would frighten away all the devils who come out for the Dragon Boat Feast.” 虽然译者有此信心和意愿,但在涉及地方习俗和历史人物的翻译时,仍然经常出错。如上述第二例中,说岳云是“宋朝最著名、最英俊的武士”,就显得牵强附会。有时候,译本对一些民俗还会做出完全错误的解释,如第二章:“邀会的,集款时大多数皆在此地,扒骰子看点数多少轮流作会首时,也常常在此举行。”这句话是说茶峒河街吊脚楼的功用有三个:集会、集款、选会首,而项译本却以为“邀会”是全句唯一的主语,并把它解释为“一种掷骰子的游戏”:They played “yao hui”—a game played with dice; of those who won most of them collected their money here,and they rolled dice to decide which of them would be leader of the “hui” at this place.这与原意南辕北辙,令熟悉原作的读者不禁莞尔。 项译本最引人注目之处,还是对原作呈现的诗意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重造。刘洪涛曾在《〈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一文中,系统阐述过《边城》如何塑造诗意中国形象,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也论及了《边城》与美国作家赛珍珠《大地》(原文为The Good Earth,可直译为“美丽大地”)的互文关系。③赛珍珠的《大地》塑造了崭新的中国形象,一时好评如潮,也引发中国文坛极大的关注,1933年即有两个中译本出版。数月之后,沈从文开始写作《边城》;一年多之后,项美丽与邵洵美开始合作翻译《边城》。可以说,《边城》及其英译是在对《大地》热议的氛围中完成的,都受到了《大地》的鼓舞和影响。项译本追求的目标,是在异文化空间中重造原作中的诗化中国形象。考虑到异文化空间的读者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陌生感,以及难以区分地方文化的特异性,译本采取了与原作不同的策略:原作努力将湘西茶峒边地化,译作将其建制化;原作强调茶峒地方文化的特异性,译作将其“中国化”;而对于具有丰富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词语、意象,译作则将其普遍性,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误译、漏译、增译和个性化翻译。 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当然还是小说标题的翻译。原作明言,“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为孙女取名“翠翠”。显然,这“翠”是“青翠”、“碧绿”之意,但译者却将表达色彩的词引申到“翠玉”、“碧玉”,使一个来自乡野、自然的女孩子,与有丰富中国文化内涵的“玉”联系起来,化身为温润、纯洁、坚韧的形象。前文还提到,译者在前言中强调其不用“边城”而用“翠翠”作为书名,是为了避免读者联想到英美文学中的“边疆故事”或“狂野西部故事”。与此相一致,译本中对“边城”、“边境”诸词也经常刻意回避,转而努力营造茶峒作为一个有着正常行政建制的中国“城市”形象·如第一章第一段“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一句就被删除了。还是第一章第一段的原文中,作者将茶峒称为“小山城”,译本却是“a city”(一座城市)。在第五章开头第一段的“凡在这边城地方”一句中的“边城”也译成“the city”。与这种“建制化”的努力相一致,第一章中的“渡船为公家所有”一句里的“公家”变成了“city Government”(市政府)。 众所周知,湘西自古是苗族聚居区。清代中叶,在数次苗民大起义之后,清政府为彻底根除“苗患”,开始在当地修筑长城,将未“开化”的“生苗”圈在保留地,并派绿营军驻守。这些绿营军是屯垦部队,战时打仗,平时生产。清朝覆灭后,绿营军的军事功能虽然消失,但其建制在湘西一直续存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县,当年就是湘西镇压苗民起义的军事中心,而《边城》故事的发生地茶峒,是绿营军驻扎的一个前哨站。《边城》中写到的军队和士兵,都来自这支绿营军;死去的翠翠父亲,以及渡船老人的好友杨马兵,也是绿营军的士兵。译者对这段涉及作品背景的湘西历史一无所知,在翻译相关文字时,只保留了一般军队、军人的信息,对其余信息,或予以删除,或进行简化和概括。如把“绿营军勇的装束”译成dressed in the old-style uniform(穿着旧式军服),把“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简化为soldiers(士兵),把“其余多数皆为当年戍屯来此有军籍的人家”译为all the rest were the families of the soldiers(其余的都是军人家庭)。第十章提到的“中寨人”,是指住在茶峒城外名为“中寨”的山寨里的居民,这些人通常是苗民,译者却望文生义,将其译成Army people(军队里的人)。第十三节提到的“漂乡生意人”指的是乡间的游商货郎,译者只简单地译为the tradesmen(商人),过滤掉了其中的地域文化内涵。 项译本中的一些误译,也有美饰原作人物的动机,例如对人物杨马兵名字的翻译。杨马兵是翠翠父亲当年在军中的伙伴,身份只是一介马夫,职责是照料马匹,但项译本将其译成Cavalryman Yang,等于把他的身份转换成了骑兵,大大拔高了杨马兵的社会地位,也植入了对这个人物的浪漫想象。总之,沈从文在原作中即存在对湘西原始自然特征进行美化、归化和牧歌化的现象,而项译本在这方面走得更远。译者给读者提供的只是“中国”形象,湘西特色则被消解于无形。 金隄与白英的《边城》译本The Frontier City(以下简称“金译本”)收在二人合译的作品集《中国大地》(The Chinese Earth)中,于1947年出版。二位译者的模式是金隄完成初译,由白英对译文进行润色、定稿。这部英译本收录了《柏子》(Pai Tzu)、《灯》(The Lamp)、《丈夫》(The Husband)、《会明》(The Yellow Chickens)、《边城》(The Frontier City)等14篇作品。译者将主要表现湘西世界的小说选集命名为《中国大地》,用国家符号统摄之,显然针对的是赛珍珠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和斯诺选编翻译的《活的中国》,并与其构成了对话的关系。而与项译本相比,其对“中国”的理解,已经从浪漫的想象,向现实主义转变。 具体到《边城》的翻译,金译本从项译本中受益颇多,包括对许多物产、制度、习俗、器物名称的翻译,都沿用了项译本。当然,一些错误或含糊的翻译,像“青盐”(green salt)、“官青布”(blue cloth)、“细点心”(little cakes)、“桐油”(wood oil)、“双料的美孚灯罩”(a good-quality chimney for their kerosene lamps)等,也都沿用了项译本。金译本中,不少句子也有挪用项译本的情形,如第十章中,老船夫告诉媒人,“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这是用下棋的术语,比喻求婚的不同方式,其中的“车”不读“che”而读“ju”。但项译本却误解为车辆走的路和马走的路(there is a road for carriages and there is a road for horses),金译本则沿袭了这个错误。此外,翠翠在第八章唱的傩辞的翻译,金译本在句式、词汇、叙述语态等方面对项译本同样亦步亦趋,删节部分高度重合,当然,项译本的错处也在金译本中被原样复制了。 二 作为政治任务的翻译 戴乃迭的《边城》译本The Border Town(以下简称“戴译本”)初刊于国家外文局主办的《中国文学》1962年11—12期,1981年列于“熊猫丛书”再版。尽管戴乃迭是英国籍,英语是其母语,但她随丈夫杨宪益先生长期在中国生活,供职于官方翻译机构;她翻译《边城》系出于“对外宣传”的政治需要,是由国家机构主导的译介活动,必然更多顾忌源语国内部的政治文化生态,而不会多考虑译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接受习惯。《边城》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按照译者所处时代的流行说法,这是“万恶的旧社会”,理当“暗无天日”、“民不聊生”。但《边城》却是一曲洋溢着浓郁诗意的“牧歌”,在阶级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样的倾向就有了“歌颂旧社会”嫌疑。沈从文曾因巨大的政治压力,在修订《边城》时,有意把初刊本中明确的时间界定做了模糊处理,并在序言中为自己辩护。出于同样的顾忌,戴译本在处理涉及“旧社会”的政治、军事、宗教、阶级和性的用语时,往往采取多种翻译策略,或凸显、或遮蔽、或模糊、或曲解原意,以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戴译本对《边城》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顺顺的“美化”。顺顺是大老、二老的父亲,是边城茶峒地方的名人,小说第二章在介绍他的资历时写道:“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这里的“陆军四十九标”原是晚清新军的一个建制单位,1911年10月,它在湘西人陈渠珍的率领下,起兵响应武昌起义,为推翻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且看戴乃迭对这段文字的翻译:The wharf-master,Shun Shun,served under the Qing Dynasty banner before becoming an officer in the celebrated 49th detach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y in 1911.这段译文有两个突出特点:(1)强调时间的先后序列,把顺顺的生活分成“前清时”和“革命后”两个阶段;(2)强调顺顺的身份转变,此前是“在前清营伍中混日子”,现在则成为“革命军队”的军官。由于辛亥革命头顶耀眼的政治光环,把陆军四十九标引申为“革命队伍”,把顺顺附会为弃暗投明的革命者,有助于保证顺顺政治身份的“清白”;而原文中其实并未强调陆军四十九标是“革命队伍”。同样在《边城》原作中,在介绍顺顺目前在茶峒的身份时,用了三个不同的称呼:“掌水码头的”、“掌水码头的龙头大哥”、“船总”,这些称呼,其实都显示顺顺是晚清民国时期流行于川黔湘西一带的民间帮会组织哥老会(或称袍哥会)的地方首领。但戴译本将这三个身份一律译为“wharf-master”(码头管理员),显然是为了降低顺顺是“统治阶级”或“反动组织”成员的嫌疑,用心可谓良苦。 戴译本在翻译《边城》其他涉及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词语时,遵循着同样的原则。如在第21章有一句:“皇帝已不再坐江山,平常人还消说”。原文并没有赋予改朝换代以任何价值评判,只是说时代巨变,造化弄人,而戴译本对应的“If even the emperor has been dragged off his golden throne,what vicissitudes must be the fate of lesser mortals!”则强调大清皇帝是被拉下王位,被推翻的,有明显的政治评价意味。《边城》原文中还有不少称呼地方军人的术语,译文都抹去了其原意,以泛称代之,如“粮子上人物”译为“Acquaintance”,“副爷”译为“master”或“friend”,“营上人”译为“Someone”。对涉及宗教、丧葬、卖淫等内容的词语,译者或不译,或曲译,或以泛称代之。戴译本还把原文中的“妓女”泛称为“Women of a special type”或“these girls”,把“上帝”译成“Jade Emperor”(玉帝),把“道袍”译成“gown”,而老船夫葬礼上出现的“第绕棺仪式”、“纸幡”、“丧堂歌”都没有翻译,从而技术性地回避了“旧社会”才会有的“封建迷信”、“丑恶的社会现象”和西方宗教的内容。 戴译本除了高度的政治禁忌,在还原《边城》诗意之美方面,也乏善可陈。例如,原作中出现的“虎耳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也是翠翠被唤醒的情欲的象征。但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这一植物又无情爱寓意,项译本因此将其译为“tiger-ear plants”,试图通过突出这一植物的“虎耳”形状,把其中寄寓的情感呈现在译文中。金译本将其译为“tiger-lilies”(卷丹类植物,又称虎皮百合),虽是误译,但征用西方文化的意图十分明显,可称为“美丽的错误”。而戴译本只译出了“虎耳草”的学名“saxifrage”,并没有文化上的引申附会,也就无从再现其在原作中唤起的美丽想象。《边城》中有许多关于湘西自然、历史、风物的描写,关于翠翠纤细、复杂、朦胧的情爱心理的描写,如第二章第三段(“那条河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第十三章第一段(“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第十八章第二段(这并不是人的罪过。……),字里行间,散发着浓郁的抒情气息,尽显湘西的乡土诗意之美。而戴译本分明轻视这些描写,要么化繁为简,作概括处理,要么干脆删节。如此肢解了《边城》原作的文化底蕴,译本的精气神也就涣散了。 当然,戴译本也不是一无是处,它纠正了前两个译本中的一些误译,特别是地方物产名称的误译。如“青盐”,这其实是产于四川自贡火井镇的井盐,因呈淡青色,故名。项译本和金译本都作green salt,理解显然是错误的,而戴译本用的“Rock salt”才是正确的翻译。戴译本中还有一些增量翻译,用以解释西方读者不容易理解的中国文化。如第二十章对“王祥卧冰,黄香扇枕”的典故,就补充了一句“From the Twenty-four Acts of filial Piety”,说明其来自“二十四孝图”。戴译本也采用页下注的形式解释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如第二章的“岳云”,第三章的“太极图”,第四章的“划拳行酒”,第五章的“粽子”,第七章的“观音样子”,都有页下注,而且释义准确,言简意赅,不失为戴译本的亮点。 三 乡土中国的精细化呈现 第四个《边城》的译本由金介甫一人独立完成。金介甫是一流的沈从文研究专家,对沈从文小说及湘西区域历史文化有精深的了解,加之有前三个译本的经验得失可供借鉴,他的译本以严谨、精确、细腻、流畅著称,不仅完整传达了原作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湘西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而且实现了与译语国文化的完美统一。 在这方面,金介甫译本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书后所附的32个注释。这些注释详解了作品中影响读者阅读的文化内容,涉及地名、人名、版本、谚语、头衔、动物、植物、食物等。它们是:(1)边城;(2)茶峒;(3)“她长到十三岁”(解释不同版本中翠翠年龄的差别);(4)辰州;(5)龙头大哥;(6)四十九标;(7)雄黄酒;(8)梁红玉、牛皋、杨幺;(9)龙船水;(10)“狗咬吕洞宾”;(11)粽子;(12)镇筸;(13)宋家砦;(14)观音样子;(15)关公;(16)尉迟恭;(17)张果老;(18)洪秀全、李鸿章;(19)水上的张衡;(20)梁山;(21)楠木(第9章,71页);(22)鲁班;(23)“三年零六个月”;(24)“萝卜白菜,各有所爱”;(25)杨马兵;(26)“亲舅舅也必一是一二是二”;(27)“一个‘初生之犊’的黄花女”;(28)草莺;(29)第13章最后一句(在该注释中补上了1949年前版本有而其后版本删除的一句话“祖父于是沉默了,不曾说‘唱出了你后也就死去了你的父亲和母亲。’”);(30)虎耳草;(31)“这事有边”(第19章开头);(32)第20章最后一段。(补上了1981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的《边城》重校本中独有的一段话:“老道士原是个老童生,辛亥革命后才改业,在那边床上糊糊涂涂的自言自语:‘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天亮了吗?早咧!’”并解释其中的“老童生”一词。)这些注释基本厘清了《边城》中的文化疑难,扩大了西方读者理解《边城》的文化纵深。 金介甫译本不仅采用注释的方式呈现小说中的区域历史文化,还通过增量翻译的方法,努力把原文中隐含的文化信息细节挖掘出来。例如《边城》开头的句子:“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前三个译本都把其中的“官路”译为“highway”,这当然没有不妥之处,只是提供的信息如原作一样模糊。唯独金介甫译为“old imperial highway”,表明这是一条大清帝国时代修筑的道路,将湘西边境地区动用国家力量修筑公路的隐秘历史背景揭示出来。其他一些口语化的军事词语,如“粮子上人物”(Army friend),“副爷”(Honorable soldier),“兵营中人”(Man from the garrison),“王团总”(Militia Captain Wang),“什长”(sergeant),“绿营军勇”(The Army of the Green Standard),“营上人”(Someone else at camp),“营管”(The military camp),也都有精确的翻译,不像前三个译本或者翻译错误,或者作大而化之的处理。 金介甫译本甚至还纠正了原作中的个别疏忽。如第五章有一句“到了十五夜晚,城中舞龙耍狮子的镇筸兵士,还各自赤裸着肩膊,往各处去欢迎炮仗烟火”,其中提到的“镇筸”是沈从文家乡凤凰县的旧称,与归属花垣县的茶峒并不在一处,沈从文可能是下意识中把两处地方混淆了。金介甫发现了这个问题,在翻译时,省略了“镇筸”,而把“兵士”改译为the garrison soldiers,增加了“戍屯”(garrison)之意,比原文更加明晰。还有第十四章中的“你把宝贝女儿送给会唱歌的竹雀吧”一句,其中提到的“宝贝女儿”指的是翠翠,但翠翠是老船夫的外孙女,并非女儿。沈从文在初刊本、初版本和改订本中,都误写为“女儿”,只是在重校本中才改为“外孙女”。金介甫译本主要依据的是改订本,但此处却译为“precious granddaughter”,把《边城》早期版本的错误纠正过来。 金介甫译本不仅充分挖掘和呈现了原作中丰富的区域历史文化,还能忠实把握原作的文体特征,呈现原作的诗意之美。例如第二章中的一段,原文与金介甫的译文如下: ……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到手上,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又不是小孩,还问人吃甜酒?”那么,酽冽的烧酒,从大瓮里用竹筒舀出,倒进士碗里,即刻就来到身边案桌上了。 Anyone willing to plunk down the money could edge up to that table outside the front door,take a seat,and pull out a pair of those chopsticks.A woman with a white powdered face and finely plucked eyebrows would come over and ask,"Elder Brother,Honorable Soldier,what'll it be? Sweet wine? Clear Liquor?" A male customer who was witty and waned to get a rise out of her,or who fancied the proprietress a little,would feign anger and retort,"Sweet wine,for the likes of me? Do I look like a child? Sweet wine,you say!" Potent white spirits were then dipped out of the wine vat with a wooden ladle into an earthenware bowl set immediately upon the table. 这段原文的语法结构十分复杂,是沈从文作品中常见的“反复叙事”类型。这种叙事类型因追求概括性和整体图景,轻视个体特征,造成句子主语的游移不定、模糊或不确指。此处列举的例子中,“不拘谁个”和“这人”作为主语,本身所指就十分模糊。“妇人”之前的“眉毛扯得极细”、“擦了白粉”作限定性定语,并不能使这妇人从众多妇人中区分出来,因为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妇人,几乎都是这样装扮。妇人的问话“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其中又隐含了对第一个句子中主语“不拘谁个”和“这人”的颠覆:“大哥”指商人或水手一类人,“副爷”用以称呼列身军籍者,它使前边的主语由任意选择的单数变成复数,所指更加含混。“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又是对“大哥”或“副爷”的一次筛选,看似范围进一步缩小,事实上并不能令主语更明确一些。一个短促的买卖过程,主语就这样数次游离、置换,表现出沈从文对人物个性的冷漠;他把单个的人还原到他所属的类,再把群体的人还原回泥土和大地,人物成了风俗、物景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段复杂而精彩的文字,前三个《边城》的译本都没有领会其中的奥妙,都把复数变单数,删繁就简,使原文的丰富内蕴尽失;只有金介甫译本用“单一叙事”最大限度地传达出“反复叙事”的文体特征和意蕴。 美中不足的是,金介甫译本也有个别误译。如第二章提到“毛手毛脚的水手”,其中的“毛手毛脚”用的是本意,指水手的腿和胳膊上长满体毛,而金介甫误会为引申义,因此错译为“Fidgeting boatman”(毛躁的水手)。第六章提到的“皮纸”,是一种湘西特产,以韧性树皮纤维为原料制成的纸,可供糊窗和皮袄衬里之用,金介甫误译为“wrapping paper”(包装用纸),也不符合原意。在第八章中,翠翠看到过渡的一个少女穿着“一双尖头新油过的钉鞋”,其中的“油过的”指用湘西出产的桐油漆过的鞋子,有防水功能,并非指为了美观而刷油擦亮。金介甫的译文是“Her newly polished shoes had pointy toes and spikes on the bottom”,却没有把这一层意思翻译出来。不过瑕不掩瑜,与《边城》的另外三个译本比起来,金介甫译本仍然堪称完美,无疑也是最忠实于原作的。 《边城》四个英译本跨越73年的发展,还引出一个有趣而重要的学术话题。按照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达姆罗什的“椭圆折射”世界文学理论(World literature is an elliptical refraction of national literatures),当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时,必然要穿过诸如语言、文化、时间等“介质”,因而会产生折射,使其呈现出与原作不同的面貌。也就是说,世界文学不是民族文学在大尺度上的同质化,而是原语国文化与译语国文化杂合、混生的作品。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学者对肆意改写原作的译本持赞赏态度,认为这是进入世界文学空间的必由之路,是后发国家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必须做出的“牺牲”,甚至是原作在异文化空间的重生。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所译莫言小说,为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译本存在大量删节、改写的情形,这似乎印证并加强了学者们的这种论断。但《边城》四个英译本的发展历程,尤其是金介甫译本的出现,展现了另一种可能:随着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译语国将逐渐培养出越来越广大的读者群,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以“异国情调”的心态看待中国作品,而希望在欣赏中国文学作品的同时,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因此,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的优秀译本在译语国广泛传播,是可能的,也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另一种选择。 ①与之相反的例子是同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编选、翻译的《活的中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把选入的沈从文短篇小说《柏子》结尾的三段文字悉数删除,代之以改写的两段文字,以便把原作中作为湘西蒙昧人的柏子形象,改塑成一个觉醒者的形象。 ②Emily Hahn and Shing Mo-lei,"Preface",T'ien Hsia Monthly,Vol.2,No.1(1936):92. ③参阅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