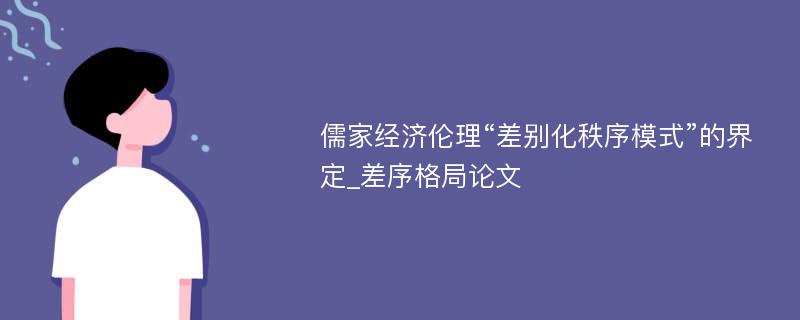
儒教经济伦理观念“差序格局”界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教论文,伦理论文,格局论文,观念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最初是费孝通先生在研求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时所使用的一个极富概括力的描述性概念。按费老的观点,中国乡土性的基层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相比,社会关系是沿循着亲疏远近的差序性原则来建构的,因之他称之为“差序格局”。本文借用这一社会学概念喻指传统儒教社会经济伦理观念的梯级差序形态。对社会整体而言,它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最深层的价值评判基础;对社会个体而言,它又表现为制约或促动私人经济和社会行为的最深刻的内驱力。
一、论题因由
传统儒教社会的超稳态结构是中外诸多学术课题追逐的焦点问题,求解的视点不同以及分析工具的差异,自然导致了不同的结论。就国外研究的情况来看,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李文森( LevensonJoseph R),从费正清(Fairbank John King )到费维恺( AlbertFeuerwerker),西方五、 六十年代占主流的观点几乎都着力突出传统中国社会孕育的惰性人文因素。李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芮玛丽(Wright Mary )的《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防线》等饮誉中外的严谨著作都持有一个共同观点,即儒教与近代社会基本上水火不相容,“阻碍(中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的并不是帝国主义侵略,满清的统治,官员的愚昧,或者一些历史的偶然事件,而恰恰是儒教体制自身的各个组成部分”。 (注: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Conservatism:The T' 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 rev.ed.(New York:Atheneum,1965),PP.9—10;又见P.300.作者说, “同治中兴的失败异常清楚地证明,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无法把真正近代国家嫁接到儒教社会身上。”)尽管这一论点曾经受到有关论者的批评,但它确实在较大程度上关注到传统中国社会惰性结构的体制性负面影响。不用说,我国学术界也有较多的人作过类似的考证。这种考证的重要结论之一是发现维系和导控这一惰性结构的中枢系统便是根深蒂固的“伦理中心主义倾向”,伦理本位主义、泛道德主义、政治伦理化等话语成为涵括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极有份量的分析语言。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始终是统一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它成为调控人们言语、行为,矫正人们心态的官方话语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伦理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性或体制性的伦理,换言之,在传统的人文、经济制度内部蕴含着儒教色彩的伦理追求、道德审核和价值判断。这种制度性的伦理观念是相对于儒教社会中的个体道德而言的,在社会转型之前,它表现为儒家政治、经济等系统赖以运作的权利、义务和规范体系,它们基本上是经由社会关系、政策、法规、条例等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性因素表现出来。事实上,制度伦理、体制伦理这种分析范式来源于经济学研究中新制度主义对伦理现象研究的启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道格拉斯.C.诺斯将“制度”界定为“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 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它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力、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所组成”。(注:转引自方军:《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因之, 制度伦理观念也基本上来源于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约束”。这种缘于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伦理分析范式对于我们疏解儒教伦理形态和特征是非常合适的,它可以弥补仅仅用个体伦理来观照传统中国伦理性状的缺憾,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较好地解释儒教伦理作为整体性的强韧力量来控制社会中的每一个体所具有的强效果力度。
儒教经济伦理观念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来源于儒家制度性伦理和宗法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等级差序格局。众所周知,伦理学即是研究“人伦之理”的学问。何为“人伦”?《孟子·滕文公上》即作了诠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大致包括了社会上最常见的人际关系。由儒家伦理视角来解释中国人伦“关系”的差序性是基本的分析方法,儒家人文观念中的伦理准则是反映传统社会建构的最基本的理念。其基点在于对人的设计,这里的“伦”也就是儒家制度性伦理观念所框范的社会个体之间的“等级差序”,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个体之间等级区分的种类,诸如儒家早期经典中关于等级差序伦理定义的描述,像《祭统》中的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这“十伦”;《礼运》中也有“十义”的关系规范,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二是社会个体应建立的关系的种类,诸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根据人类学的研究,这种分类的观念,正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构成原则。由此观之,儒家那套规范人与人相处之道的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儒教体制性“约束”对社会个体进行角色定位,并藉此来形塑社会结构与秩序的基本原则。
就儒教制度性伦理对社会整体的控制而言,“伦理本位”强调的正是中国社会最深层的价值基础和建构原则;就对社会个体的框范而言,它又表现为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以道德形式出现的差序性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可以说,传统儒教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行为取向,已被这一制度性的伦理重新加以定位,从而呈现出极其明显的梯级差序形态。正是在这种学理背景下,费孝通先生才提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序格局”概念,认为乡土性的“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而,“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有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47年版,参见第21—28页。)费老对乡土中国社会的研究以及所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社会学概念,对后来有关课题的研究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后来对于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的一系列研究,几乎都受到该观点的启发。对于本文所设定追问的儒教经济伦理观念的格局特征,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序格局”更显示出其描述性价值,对此进行跨学科研究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本文使用此概念进行经济伦理概念的研究,当然也倾向于它所具有的描述性功能。
二、“差序格局”的范畴和语境
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可以发现,中世纪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建立在农业文明和封建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伦理观念来加以维系的。高度重视伦理道德学说,将伦理道德观念渗透甚至是泛化到各个领域,如由伦理推及政治,使得政治呈现出伦理化形态;文学强调“教化”功能,使得文学成为张扬伦理的重要工具;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竟使其品评标准极具伦理意味。儒教伦理功能的扩张,自然不能不涉及经济,中世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潮涨潮落以及人们经济行为的背后动机无不渗透着一定的经济伦理观念,其渊薮正是传统的儒教伦理观念。儒教伦理观念的差序性也就理所当然地导引出经济伦理观念的“差序格局”。
传统经济伦理观念“差序格局”的话语情景和范畴主要表现在历代典籍、文录和撰述中蕴含的“体——用”、“本——末”、“道——器”、“义——利”、“理——欲”、“主——辅”、“贵——贱”等“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种思维定势。较早的儒家典籍《大学》上即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观念之一,也正是这些以差序性为特征的语汇和范畴调控着经济主体的一系列行为,进而给社会经济的发展施加多方面的影响。它们的确切含义和延伸意境,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多有论列。它所暴露的思维定势在于确认经济生活中道德评价的善恶之分、贵贱之别、主次分明,最主要的是它们勾勒出经济伦理观念和精神结构中的序化形态。正如儒家身份伦理(Status ethics)的等级差序形态一样,“本末”、 “义理”等话语折射出儒教制度文化对社会主体不同经济行为的促动或制约作用,蕴含着张扬与鞭挞、褒奖与惩罚这种道德情感上的两极性,导致传统社会中的一切经济成分和生产方式无不受制于这一两极性价值的规约。这种伦理价值和情感始终与“仁”的伦理境界相关涉,可以说儒家的“仁”是以“严等差,贵秩序”为基本架构的,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虽然是专就一般的人伦关系而言,但它泛化至经济伦理观念时,也就将所有的经济性动机、诸业人士都置于由人格善恶、身份差序以及荣辱贵贱心理所构筑的“格式”中。
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货殖贸易耕织仕读等经济和社会行为,大都与儒教社会中梯级式的人伦关系密切相关,低下匮乏的社会经济水平,萎缩不展的社会分工现状以及专制高压的“寻租政体”的强化统治,极其有力地将儒教经济伦理与宗法社会结构纠缠在一起,从而将社会经济生活纳入到它所创制的“差序格局”之中。“本末”、“理欲”等则是反映这种差序格局的重要语境。
这些以梯级差序为主要特征的伦理话语,因其调节的对象和涵括的范围不同,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阐释主体与部分、主干与枝节等逻辑层次的范畴,诸如体用论、道器论、本末论、主辅论等,自然经济社会中的耕织为本,工商为末,重农抑商,崇本贱末的经济伦理观念即反映了产业经济、社会分工方面的伦理梯级形态;另一类旨在申明经济动机和社会行为的善恶、贵贱这种两极性逻辑的范畴,诸如义利论、理欲论、贵贱论等等。宋代以后的儒家士子、社稷重臣中占主流地位的伦理观念是重义轻利、贵谷贱金以及“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甚至是“存天理,灭人欲”。这类崇义重理、抑利泯欲的价值评判标准,其功能就在于将各种经济成分、经济行为的运作加以伦理意义上的框范,使得各业行为和社会分工也呈现出一种差序尊卑的格局。依此而论,近代社会转型之前,身份地位在伦理观念上的典型程式也就只能是“士——农——工——商”的排序方式。上述两类经济伦理范畴之间虽然有着一定的差别,但却存在着不可暌离的关联性。就经济生活中的产业观念和职业分类的评判价值而言,首先,儒教伦理所阐扬的“本”、“体”、“主”、“道”等范畴直接对应着“义”、“理”这些肯定性的伦理语汇,并获得后者的学理支持和价值提升,情感上的评价当然也是积极的,是产业行为和职业抉择中褒奖性的伦理因子,如业儒、为士、务农等即与此相关。在这一层面上,“义”、“理”这之类的伦理范畴直接地影响着“本”、“体”的对象确定和内容排序;其次,儒教经济伦理语境中的“末”、“用”、“器”等倍受鄙视和压抑的范畴则对应着“利”、“欲”之类的伦理语境,并且由后者规约了前者的低贱性,诸如为工、经商这类崇欲重利的“末业”即被视为“贱业”,贬斥它、抑制它的发展扩张便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
概而言之,近代社会转型之前,经济伦理观念的主要范畴所反映出来的“差序格局”,集中地体现在产业行为、职业观念和价值的梯级形态。经济伦理价值和情感中善恶、尊卑的评价取向在泛道德主义的影响下,极其深刻地规约着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并牵制着对社会地位的认知判断。
三、经济伦理观念的序化形态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农业经济的崛起使得人类实现了由攫取性经济向生产性经济的重大转轨。就中国来说,夏商以降,小农经济日益发达,耕织合一的自然经济形态渐趋成熟。这种生产方式倚重于种植业,而轻于畜牧业和商业贸易。在“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这种根深蒂固观念的支配下,社会经济生活中农耕的地位始终很突出,历代朝廷都极力强调农业的“本业”地位,与此相联系,古代社会的商业、手工业则被视为“末业”,“重本”与“抑末”向来可悲地联系在一起,安邦定国以务本重农为主,而丧国亡朝则缘于末业兴,游业起。据此,儒教社会中的经济伦理观念在较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序列排定,在这个意义上,它的序化形态不但外化为本业与末业之分,经济发展的体、用之别,经济形态的统、属之辩,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这种序化形态也进行着极为浓烈的伦理价值和情感的评价,即以“理——欲”、“义——利”等层级式的价值判断来内化经济主体的观念动机,进而调控其经济行为。
应该说,诸业衍生,百工涌现是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产物,作为一个客观的物质性过程,它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历代王侯将相、经生儒士莫不对其进行伦理意义上的选择剔梳和规范匡正,由此形成了儒教经济伦理观念上的差序梯级形态。即便是较为开明的桑弘羊“本末并举”的理论也还没有脱离本末、义利这一类伦理窠臼。他认为:“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盐铁论·本议》),在对农业进行伦理价值提升的同时,桑弘羊也对商业的地位作了较高的评价:“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盐铁论·力耕》)。史学界较为肯定东汉时期王符开明的经济思想,但在他的有关论著中实际上也是以伦理观念来定位产业次序,诸如,“除去仁恩,且以计利言之。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愿察开辟以来,民危而国安者谁也?下贫而上富者谁也?”(《潜夫论·边议》)针对东汉时期“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的现象,王符主要从批评奢侈性工商业恶性发展的角度,阐发了他的“重农务本”的经济伦理思想,他认为,农、工、商三者虽然皆能富民,但三者之中有本末之分:“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所以他强调:“故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伪;困辱游业,勿使擅利,宽假本农,而崇遂学士,则民富而国平矣”(《潜夫论·务本》)。他们在有关著述中所显现出来的经济伦理的本末观,在漫长的农耕时代自然不占主流,相反的情况是制度层面的伦理观念严格地将社会诸业进行高低贵贱的伦理定位。可以说,“本”与“末”,“统”与“属”,“体”与“用”等从来就是一切经济观念矛盾中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两个端点。
商鞅是最早明确地对产业经济进行价值排序,认定“重本抑末,崇农贱商”观点的政治家。他认为,“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奚为轻治?其农贫而商富——故其食贱者钱重,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商君书·对内》)荀况的学生韩非子甚至视商人为“五蠹之一”,从而“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韩非子·五蠹》)。看起来,这种重本末、贵贱的伦理差序从农耕文明的起始时期即已俨然明晰。众所周知,中国作为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文明之国,以农立国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其经济伦理的序化形态正是创制、繁衍于这一社会经济土壤之上。历史上农业一旦废弛,或遭受巨大的自然灾害,或农业之外的百工崛起,社会矛盾便处于碰撞激荡状态。由此,每一新王朝的立国之君以及各级官吏莫不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作为基础,经济伦理观念上崇尚“本业”自有其合理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从理论上讲,“崇本”与“抑末”并不一定是对立的,但历代制度性伦理大都将两者相对而置。时至明朝初立,朱元璋于洪武十八(1385)年仍旧张扬这种传统经济伦理,他曾谕户部臣曰:“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涂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明太祖实录》卷175)。
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儒教经济伦理的主导价值目标在于实现对其中心观念——“仁”的追求。学者会注意到,儒教对人的伦理关注根源于人的存在,因之可以说是本体论的。所谓伦理的关注就是如何使人这个社会存在活得充满价值与智慧。人具有向上追求的精神需要,也有向上提升的精神能力,自觉自主地实现这一价值和欲望也就是儒教观念中“仁”的自觉。孔子谓之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所以说,具有仁的自觉的人就能行于社会,带来社会的安宁与和谐,可以成为社群的模范和集体的表率。在这一意义上,“仁”之为德,可视之为一种工具理性。时至孔子时代,“仁”又成为一个人内涵的能力,而且是任何人应该坚持的作人原则,如此,“仁”的价值泛化为使人与社会得到“安”与“和”。儒教这种以“仁”为主体的价值观念后来更演化成一套文物制度以及行为规范,儒教经济伦理的价值追求与调控导向也就顺理成章地与上述主导观念联系起来。正如日本的现代化问题专家依田憙家所言:“中国的统治者总是强调‘重本抑末’(重农抑商)、‘重食轻货’、‘贵义贱利’等等,经济性行为被视作‘言利’(即讲‘利’)之举而遭受道德上的非难。”(注:依田憙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历史地看,儒教经济伦理极其有效地规约着士、农、工、商等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行为,这种规约的范围是极其宽泛的,从衣着服饰到饮宴宅第,从如乐方式到行为趋向,无不显示出等级差序的基本格局。其规约方式较多地体现在以公众舆论形态出现的伦理褒扬或歧视。譬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宣布“上农除末”,有所谓“谪戍”政策,将商贾及其子孙一类的“尚利之徒”视为罪犯。西汉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然市井之子孙不得士宦为吏”(《史记·平准书》),“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魏晋南北朝时,晋令曰:“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太平御览》卷828)。 唐代有“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旧唐书·食货志上》)等规定,直到明代对商人的服饰仍有限制,明洪武十四年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准穿绸纱”(胡侍:《真珠船》,卷二)。这些不准商人入士,限制商人生活水平,贬黜其社会地位,甚至对其进行人身侮辱的抑商法令,恰好与儒教经济伦理观念中耻于言利、义先于利的道德律令相吻合,再加上人们对商人获利时所用的欺诈手段的厌恶情绪,自然也就形成了整个上层建筑中的贱商道德观念。
为了框范诸业中的经济行为,历代封建政府以“伦理+法令”的规约力量来促进耕织结合,抑制社会分工的倾向在前近代社会是非常明显的。耕织结合通常被视作“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实际上,这也是儒教经济伦理观念追求的主要内容,将这两种生产方式弥合为一体,是它的重要调控目标。自明太祖始,力促耕织结合的伦理和政策倾向更趋明显,“不分地域,指定农家植棉亩数,将棉花列为常赋对象,不论自然条件是否适于种棉,人民必须种棉纳棉,不种棉也得纳布”(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工业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8—19页。),这样,专业化生产受到严重压抑,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社会分工反而萎缩。明季初年,工商业最为发达的松江府,“各地赋则每亩不过斗升”,但苏、松、嘉、湖地区有“每亩课至七斗五升的……以弘治十五年松江府纳粮百万余石,多于金闽八府一州五十七县之输将;嘉靖间松江府纳粮一百二十余万石,举北直隶八府十八州一百十七县之粮,庶几近之。 ”(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工业史稿》, 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8—19页。)结果,农业生产不足以应付赋税,还必须通过手工业生产来补充,这从另一方面加深了耕织结合,致使商业资本转向生产无利可图。可以看出,此种经济伦理的政治化倾向更增加了对社会经济主体的调控力度。
对儒教经济伦理观念差序形态的进一步研究也可以窥见当时世人的某些虚妄心态。这种伦理观念的基点,在于它认为农、渔、林、畜牧、养蚕、纺织等行业是“生物”、“生财”的领域,而商贾却是“耗物”、“费财”的行当,它导致社会陷入奢侈欺诈而不能自拔,因而是一个使“仁”、“义”丧尽的行业。在这个意义上,制度性的儒教经济伦理观念也就只能把农业、手工业限制在“小小营生”状态,“严示衣食用度不可逾越所规”。退一步说,工商业的危险性也较大,而且获得金钱也容易很快花掉,“听其倏来忽去而已”,“通都大邑之富,辄易世而亡”(刘锡鸿:《录辛未杂著二十二则寄答丁雨生中丞见询》,《刘光禄遗稿》卷二),“世有十世之农,而无三世之贾”(谢阶树:《约书》,《保富》卷八),农家地产“能传十数代,不使子孙有饥寒”,而“商贾之家百年间无不破产者”(《梦园丛说》,《内篇》卷八)。这些虚妄的比较仅仅是经济观念中的表层反映,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工商业尽使人为“利”,欺诈、取巧之风会将“仁义礼智信”吹荡殆尽。时至近代前期,人们仍将西艺西技视为“奇技淫巧”,此种语境仍旧折射出浓厚的伦理评判色彩。
作为儒教经济伦理观念序化形态的外在表现,业儒、务农、经商等社会性的经济行为呈现梯级格局,这仅仅是经济伦理“差序格局”的一个方面,形塑这种格局的是义利、理欲、尊卑等情感性的伦理范畴,对于儒教经济伦理来说,这是最具制约力的中枢因素。中国历史上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经济伦理思想,据王小锡先生研究,主要有“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理想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和“自然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等,而影响广泛、持续时间较长的应该是“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在道德和利益的关系上,尽管认可“以义取利”,反对不讲仁义的谋利行为,但在较长的时间内,对道德和经济利益一直是从“本末”、“体用”、“主辅”层面上来诠释和理解的。在这种观念定势的牵制下,“义利之辨”成为一个永恒的伦理话语,似乎无义即无从谈利,徒言利即小人之利。从实际情况来看,儒教德性主义经济伦理观念的主导趋向是“恶利贱金”与“崇义尚理”。尽管传统社会中也不乏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观点涌现,诸如王安石、李觐等人提出过“义者利之和,义固所以为利也”,“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以及讲仁义就是为了“利”的思想,但从全局看,利从义,欲制于理则是主流观念。儒教经济伦理也就是以此来规约诸业行为,观照百业分工,因之,它必然会凸现出错落有致的差序格局来。
四、差序格局的一个诠释:以日本早期文明为例
就文明历史的整个“抛入状态”而言,一种伦理形态的存在必然不是孤立的。借助文化人类学提出的“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的研究范式可以更方便地俯瞰本文所关注的儒教经济伦理观念的形态。
本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家C.威斯罗尔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中提出“区域与年代”学说,其中特别使用“文化中心”这一全新概念,原指一个文化区域特有的文化类质最集中的部分,而且也涵指这一部分文化的辐射力量和外向动态意义。在所设定的文化区域内,一组文化类质接近的民族群落中,必有某一民族处于中心地位,起一种得风气之先的文明牵引作用,从而在此区域内承担着凝聚和支撑的角色。“边缘文化”(Mavginal Culture)显然在“文化中心”的对称意义上得以形成,M.J.荷尔柯维兹将其定义为“边缘文化是一种可以辨别其文化元素从邻区进入的文化”(注:M.J.Herskovits:<Man and His Work>,译文引自《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11页。)。 依理而论,任何意义上的“中心”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地位必然随着历史发展中各民族生存格局的变化而升落起伏,显然,“中心”的存在必须以时空限定作为前提。换言之,“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在文明裂变和聚散过程中,常常可能发生角色转换,这就是文化人类学中所谓的“文化萎缩”(decuitu ration )和“文化取代”(culturalsubstitution)。近代社会转型之前,东亚文明区域即是典型的文化人类学理想的一个设定地域。
“东亚儒教文化圈”是时下知识界经常进入的一种语境。它对于本论题的启发意义在于我们能够循着“文化中心”和“边缘文化”的思路,将处于“文化中心”的中国儒教经济伦理形态与当时处于“边缘文化”方位的日本等国家进行比较,以此来证明或推断经济伦理观念差序形态的共时性特征。
应该加以说明的是在“东亚儒教文化圈”内,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教文化较早地存在着对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等周边地区持久的文化吸附现象。关于这一点,日本的学者也多有论断,林屋辰三郎在对谈《历史夜话》中说:“日本人对外国人、外国文化本来就没有偏见。明治的文明开化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这种素质早从3 世纪就有了,从那时就一直接触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比较自然地接受和学习了中国文化”(注:转引自依田憙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第179、239—241页。)。既存的文化吸收现象是本文能够比较的依据。
尽管文化接纳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边缘民族对文化因子转换的情况,但梳理日本早期文明的典籍时,依然可以看到中国儒教经济伦理观念在日本民族早期变迁中的巨大影响力,也清晰地折射出他们经济伦理中的差序格局的征象。尚农论、俭约论、重本抑末论以及贵谷贱金论等经济伦理趋势非常明显。
农业文明时代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人文观念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经济伦理观念表现在产业经济行为上就是人为地对产业序列和社会分工施加伦理影响。日本在明治前后也大体表现出类似的倾向。元禄十六(1703)年,贝原益轩在其所著的《君子训》中明确地表达了日本中世纪时期的经济伦理特征:“古之明王重农而抑工商,贵五谷而贱金玉,行俭约而禁华美,乃为以重本抑末之道而治国安民之政也”。在大致相同的时代,荻生徂徕在其《政谈》中也以类似的伦理标准来裁判社会诸业中的经济行为,他说:“重本抑末者,古圣人之法也。本,农也;末,工商也”;其门下太宰春台的经济伦理观念也具有差序性特征,他认为“民之业有本末之分。农为本业,工商贾为末业。四民者国之宝也,缺一而不成其国。然农民少则国乏衣食,是故先王之治尤在重农”,“治天下者,贵谷贱货,古之善政也。谷者,民之食也,一日不可或缺之物也;货者,金银钱也,金银至宝人每思之,然啜一碗之粥可以免死,金银堆积如山,居于其中而不暖,有一布被则可免病寒。是故金银非救人饥寒之物也。”(注:转引自依田憙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第179页。)可以看得出, 对于社会诸业百工的经济性行为,中世纪的日本也分门别类给予相应的伦理定位,传统的耕织产业获得了最有力的伦理、法规和情感上的支持,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显业”、“本业”;比邻相依的工商业则是伦理观念中倍遭鄙视的产业。最典型的是藤田东湖(1806—1855)在幕末所著的《封年》中反映出来的伦理倾向,他对商贾之辈的伦理情感与韩非子毫无二致,将其视为“国之大蠹”,厌恶鄙薄之情溢于言表:“商贾之职,不过彼此贸易(这里指从事商业买卖之意),以通有无而已。今之富商大贾则与此相异,贷出金钱以收利息,坐营素封之业。锦衣玉食,王侯难比;天下无事则乘诸侯之拙以牟大利,天下有事则不肯养一卒出一马以赴邦家之急,此岂非国之大蠹,贫我士民,资彼辈之富,何似割赤子之肉,以饱豺狼无异也!”(注:转引自依田憙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第239—241页。)日本中世纪时代伦理观念的差序形态尽管没有中国儒教经济伦理那样典型、完备,但的确已经形成一种以儒教伦理来观视和制约产业经济行为的总体倾向,这一论断大致是不错的。
应该说,西欧诸国的中世纪时代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经济伦理评价的梯级状态,这恐怕是中世纪农业文明时代的共时性现象。但日本的儒教型文化既与中国有别,也与西欧诸国在伦理语境上有着迥异之分。仔细推究开来,文化中心区域对边缘文化区域的文明扩散、辐射所产生的同化作用应该值得重视。尽管我们承认近代社会转型以来,中国和日本两个文化区域在“中心”与“边缘”区位上已发生较大的变化,但在传统的儒教时期,儒家文化作为强有力的信息扩散中心,一直持续不断地将器物、精神和观念文化传导给周边的日本等地;况且,日本民族在文化的吸附类型上属于“全面摄取型”。如果要比较中国“文化中心”与日本“边缘文化”有什么不同的话,设若从经济伦理的角度看,这两类区域受儒教观念的导控力度、影响时限和作用范围上存在着差别,日本较早地冲破了这种传统的经济伦理差序框架的束缚,较中国更迅速、顺利地实现了经济伦理观念的近代化转型;而中国的转型则艰难得多,儒教伦理的韧性强度,世界中心主义、华夷之辨、文化吸附中的本末、体用之辨等思维定势极其顽强地阻遏了儒教经济伦理观念的理性化进程。
时至近代社会,伦理观念的理性化进程也不容乐观。史家皆知,经济理性主义是马克斯·韦伯在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而经济伦理是经济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领域,如果按照韦伯所界定的经济理性主义这一评判标准来看,近代中国社会所创造转换的经济伦理至多是一个处在儒家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两个端点中的一个中介形态,也即是走向经济理性主义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所谓“过渡形态”由哲学层面界说,是“非此即彼”二值逻辑判断的悖论,它尽管消弥了两极对立的鸿沟,但却蕴含着新旧两种时代性质素,使得事物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特征。近代中国经济伦理观念的过渡形态,就是在转承调适过程中既达到了一定的理性程度,使伦理观念中含有资本主义的理性成分,但也裹挟着传统儒家经济伦理观念的杂质,呈现出异质同构的复杂形态,它直接导致了近代社会伦理调节功能的紊乱和矛盾色彩。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通官商之邮”的张謇在举办工商业中所产生的困惑,“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致以皭然在待自身,混秽浊不伦之俗”(《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平心而论,这种困惑感来自多方面的原因,传统文化根性的延续,政府经济现代化导向功能的模糊,经营管理中的“非理性”操作等等,但是,经济伦理对整个社会工商产业界的调节功能的模糊性和矛盾性不是不容忽视的。由此可以确信,鸦片战争以后,经济伦理观念变迁中的理性主义倾向虽已较快地孕育发展,但至多也是一种亦中亦西的过渡型的经济伦理状态,儒教伦理所特有“差序梯级”色彩依然清晰可见。
标签:差序格局论文; 儒家论文; 经济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经济学论文; 读书论文; 人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