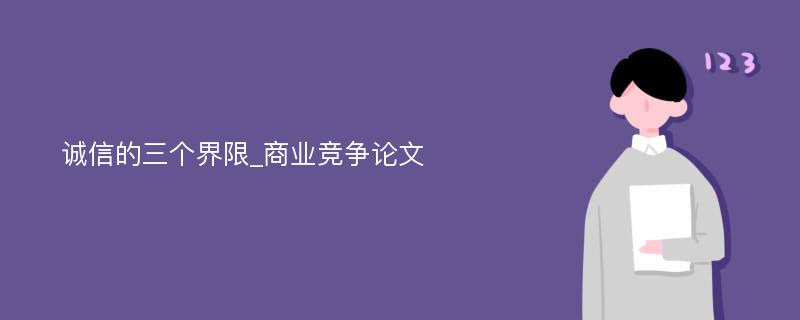
诚信的三个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限度论文,诚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06)01—0015—04
在当前中国学界的诚信研究中,许多论者痛感社会诚信危机而提倡大力加强诚信建设,建立各式各样的软硬制度,以强化的“他律”促使公民和组织遵循诚信要求,防止某些人从不诚信的言行中获得长期的或巨额的不义之利。这些建议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在强调诚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它在适用上的局限性。任何规则都有例外。诚信作为一种德性或规范并非绝对普适,而是有其限度。
在追求诚信德性时,人们应当思考以下三个渐进的问题:(1)我想做一个诚信的人,但我因理性极其有限而做不到,我该怎么办?(2)我有足够的理性做一个诚信的人,但客观情势不容许我这样做,我该怎么办?(3)我有足够的理性做一个诚信的人,而且客观情势容许我这样做,但经过慎重考虑我觉得我不应当在某些事情上对某些人保持绝对诚信,我该怎么办?类似地,在适用诚信规范时,人们应当思考以下三个渐进的问题:(1)某人因理性极其有限而达不到诚信的要求,他可以怎么做?(2)某人有足够的理性达到诚信的要求,但客观情势不容许他那样做,他可以怎么做?(3)某人有足够的理性达到诚信的要求,而且客观情势容许他那样做,但审慎的考虑表明他不应当在某些事情上对某些人保持绝对诚信,他可以怎么做?在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人们就会发现,诚信至少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限度:个体理性的限度、根本利益的限度和社会正义的限度。这三种限度也可以分别被称为心理的限度、生存的限度、道德的限度。
一 诚信的个体理性限度
人之所以有道德,是因为人有理性。先秦时期一些中国思想家(如孟轲、荀况)以是否有道德(“道”、“义”)为区分人类与其他物类的根本标志,这虽然有道理,但还不够深入,他们没有认识到人类为什么能够有道德。而古希腊时期一些雅典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理性界定人的本质,更深入地抓住了人类与其他物类的根本区别。由理性是道德的必要前提可以推论出,向人提出道德要求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理性使人能够遵循道德要求。根本没有理性的存在者(如一般动物)享有完全道德豁免权;理性尚未萌生或者刚刚萌芽的人(如婴儿)享有完全道德豁免权;理性欠发达或被认为欠发达的人(如幼儿和少儿)享有部分道德豁免权;理性严重遭破坏的人(如精神病人)至少享有部分道德豁免权,有时甚至享有完全道德豁免权。法律上情形亦如此。
就诚信这种德性或规范而言,人们不会向动物提出诚信要求,不会向婴幼儿提出诚信要求,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向精神病人提出诚信要求。这其实是不言自明的,但理论往往试图给常识一个说法。
诚信要求的实现需要主体具有起码的理性行为能力。一个缺乏起码的理性行为能力的人是不能够讲诚信的,因为他无法自知自觉地完成诚信所要求的行为——即便他有时碰巧完成了这样的行为,那也只是一种出于运气的偶然性,而非一种出于能力的必然性。对于缺乏起码的理性行为能力的人,社会不能提出诚信要求。例如,理性行为能力尚未发展起来的婴幼儿(0—3岁的儿童)和理性行为能力严重遭破坏的精神病人,两者都不能够讲诚信,因此社会就不能要求他们讲诚信,不能要求他们保持言语与行为的一致性,也不能要求他们保持言语及行动的真实性和一贯性、言语及行动与心意的一致性,更不能要求他们保持心意的真实性和一贯性。婴幼儿和精神病人甚至没有诚信观念,至少没有明确的诚信观念,因此他们无法分辨自己的言行诚信还是不诚信。如果他们的某些言行不违背诚信要求,那么它们也仅仅碰巧是“诚信的”,不能被预期必定如此。
如何界定起码的理性行为能力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学—社会学问题,在此我们不打算涉及。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理性行为能力的底线可能是不一的。在不同的心理学理论视域中,理性行为能力的底线也可能是有别的。此外,人的具体情况非常复杂。你不能断定任何精神病人都缺乏起码的理性行为能力,事实上,有些病情较轻的精神病人就拥有足够的理性控制其言行。你也不能断定所有幼儿都缺乏起码的理性行为能力,事实上,有些“早熟的”幼儿比某些大他们好几岁的少儿还机灵。
诚信的个体理性限度是被动的和单向的。也就是说,缺乏起码理性行为能力的人迫不得已可以不对其他人讲诚信,但其他人(如果拥有起码的理性行为能力)不可以不对他们讲诚信。例如,父母不能因为处于婴幼儿期的子女不能讲诚信而不遵守对子女的承诺,医生不能以精神病人不能讲诚信为借口而抛弃对后者应尽的诚信责任。
二 诚信的根本利益限度
道德在社会关系中生成,并且是为了调控可能或实际包含利益冲突的社会关系而生成的。不同的道德规范调控不同性质、类型或范围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诚信所调控的社会关系自有其特殊范围。
诚信的社会基础是交往双方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共同根本利益的存在。如果交往双方没有任何共同利益,或者其根本利益冲突,诚信就不可能产生,即便一时产生,也不可能持存。近代英国著名哲学家D.休谟在其《人性论》中指出,“许诺是人的以社会的需要和利益为基础的发明。”许诺或承诺是诚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像许诺或承诺一样,诚信的其他方面也以社会的需要和利益为基础。而社会的需要和利益就是特定社会中人们共同的需要和利益。因此,交往双方共同的需要或利益构成诚信的社会基础。诚信只能出现在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而不可能出现在没有任何共同利益特别是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的双方之间。也就是说,诚信所调控的社会关系不能超出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若超出这一范围,它就会失效。
例如,在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战争中,交战双方之间的诚信基本上是多余的,甚至是愚蠢的,因为它们各自最根本的利益——保存自己人的生命——是相互冲突的。对于战争中的交战双方,如何巧妙地做到“不诚信”倒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情。军事谋略家们绞尽脑汁策划各种欺骗性战术以克敌制胜,正所谓“兵不厌诈”。他们有意违背行动与言语的一致性,声东击西,指南攻北;有意违背言语及行为的真实性,虚张声势,故设疑兵;有意违背言语及行为与心意的一致性,诈降内应,诈败诱敌,围魏救赵,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如此等等。认真追究起来,军事谋略家们几乎违背了诚信本质规定的所有方面。应当强调的是,交战双方之间的诚信豁免权不能延伸到非交战双方之间,也不能延伸到非战争时期。
又如,在你死我活的商业竞争中,敌对双方之间的诚信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他们或它们之间即便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至少也不存在共同利益。商业竞争中的敌对双方总是想方设法隐瞒真实信息或以虚假信息蒙骗对方,绝对不会受行动与言语的一致性、言语及行动的真实性和一贯性、言语及行动与心意的一致性、心意的真实性和一贯性之类诚信规定的限制。必须指出,商业竞争中的敌对双方之间的诚信豁免权不适用于商家与顾客之间的关系,也不适用于现实的或潜在的商业合作关系。
当然,战争和残酷商业竞争中的对立双方并非一点诚信都不要讲。例如,在战争中,交战双方要遵循不斩来使、不虐待战俘等少数几条战争伦理规则。在商业竞争中,敌对双方要遵循不诋毁对方、不窃取对方机密等起码的竞争规则。不过,这些诚信要求都是消极的被动的不作为,而不是积极的主动的作为。较之战争和商业竞争中“不诚信的作为”,这些“诚信的不作为”是无足轻重的。相对于以各种诈术消灭敌方成千上万的年轻生命来说,不斩个别来使、不虐待少数战俘能意味多少?相对于竭尽其能以各种虚假信息蒙骗对手来说,不诋毁对方、不窃取对方机密又能意味多少?
至于说世上根本不应有荼毒生灵的战争和尔虞我诈的商业竞争这种责难,在此我们不打算回应。因为我们探讨的问题是:世上已经有了这些不受欢迎的现象,诚信要求是否适用于它们?依据“爱仇如邻”的基督教伦理或其他倡导博爱的理想主义伦理,敌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对方要你的外套,你把内衣也脱下来送给他,如此一来,自然没有了荼毒生灵的战争和尔虞我诈的商业竞争。不同于单向的个体理性限度,诚信的根本利益限度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的一方可以对另一方不讲诚信,而后者也可以反过来对前者不讲诚信。在战争和残酷商业竞争中,人们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有人在战争和残酷商业竞争中愿意忍受对方的不诚信策略而不愿意实施针对对方的不诚信策略,那么他就是一个“高尚的傻瓜”。而高尚的傻瓜在人类社会中是难以持存的。
三 诚信的社会正义限度
人类追求多种多样的道德价值,而它们处于不同的层次,一些更基本,另一些更高级,一些优先于另一些。这就是道德价值的层次性。在种种道德价值中,正义被公认为一种基本的、具有优先性的道德价值。因此,在探讨诚信时,诚信与正义的关系是不能绕开的。
是否一切承诺都要兑现?这是人们在诚信实践中深感困惑的一个问题,也是思想家们在诚信探究中颇多争议的一个问题。
有些思想家力主,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兑现其承诺。近代西方一些义务论伦理学家就持有这样的观念。例如近代德国大哲学家Ⅰ.康德在其《道德形上学基础》中把“勿撒谎”当作一条绝对命令,力主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遵循它。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观念,我们不取。
也有些思想家认为,一个人是否应当兑现其承诺,取决于他所处的情境是否适合于这样做。古代中国一些思想家就持有这样的见解。例如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提出“常则守经,变则行权”。在通常的情况下遵守普遍的规则(如诚信规范),但遇到某种特殊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变通的策略。这是一种情境论或温和相对主义的观念,其中又有道义主义与机会主义之别。
机会主义情境论宣称,一个人是否应当兑现其承诺,取决于他在特定情境中这样做是否有利于他自己。这种情境论带有利己主义倾向,我们也不取。
道义主义情境论倡言,一个人是否应当兑现其承诺,取决于他在特定情境中这样做是否合乎正义。古代中国不少思想家持有这种观念。他们把诚信分为“义信”(合乎道义或正义的诚信)与“非义之信”(违背道义或正义的诚信),认为“义信”是真正的诚信而“非义之信”则不是,主张坚执于“义信”但不必拘泥于“不义之信”。如战国时代成书的《谷梁传》的作者云:“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不从道,何以为信?”北宋著名思想家张载云:“君子宁言之不顺,不规规于非义之信。”(《正蒙·有德》)朱熹云:“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盖信不近义,则不可以复。”(《朱子语类》卷二十九)在他们看来,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否承诺某件事情,是否履行其承诺,要看该事情和该承诺是否符合道义或正义,若符合,则做,若不符合,则不做;而一个道德平庸甚或卑下的人则承诺那些不符合道义或正义的事情,并履行这样的承诺。他们把不辨是非(承诺和履约是否符合正义)而固执于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称为“小人”,而把明辨是非且符合正义则承诺和履约、反之则不承诺和不履约的人视为“君子”、“大人”甚至“圣人”。如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丘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论语·子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孟轲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上》)战国时期管仲学派云:“圣人之诺己也,先论其义理,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小人不义亦诺,不可亦诺,言而必诺。故其诺未必信也。”(《管子·形势解》)
我们认为,道义主义情境论是可取的。的确,在承诺之先,人们要判断其承诺是否符合正义,“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而在承诺之后,人们要预测履约是否会导致不义的结果,“信近于义,言可复……信不近义,则不可以复”。其中,第一步比第二步更重要,因此应当更慎重对待第一步。走好了第一步,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如对遭受违诺骂名的担忧、为迫不得已的爽约进行辩护等。而第二步则比第一步更复杂,因而需要更多的实践智慧。要预测履约是否会导致不义的结果,不仅需要了解特定情境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具体情况,而且需要弄清适用于特定情境的正义原则。
正义,又称公正,有多方面的内涵,其中最基本的规定是机会公平、程序合理、分配合比例均等。机会公平要求特定群体给予其有资格的成员们以教育、发展、就职、晋升等方面同等的选择或竞争机会,不可厚此薄彼、偏逆偏向。程序合理要求特定群体中的人们按照当事者们所共同认可的程序处理相关事务,不可随欲任性、独断专行。分配合比例均等要求特定群体中的人们依据基于贡献的公认标准分配社会利益,贡献大者多得,贡献小者少得,无贡献者不得,而不可无功而获、小功多获、大功小获,也不可功大功小一样获。正义是诚信的一条重要边界,诚信应当在正义的范围内活动。逾越正义的诚信是自我背叛、自我否定的诚信,因而不是真正的诚信。
也许受到儒家的义高于信的观念的影响,明代著名作家罗贯中在其《三国演义》中肯定地描述了不少因义毁信的事例。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主题可以说就是弘扬义诚义信——合乎正义的诚信。作者并不笼统地称颂一切诚信的人和事,也并不笼统地谴责一切不诚信的人和事,而是依据其正义观对不同类型的诚信或不诚信的人和事采取不同的态度。概括说来,作者(1)称颂诚信且合乎正义的人和事——对冒着身家性命危险维护东汉刘氏皇朝及其代表刘备(三国鼎立之前被认为是东汉皇朝的忠实代表,之后被认为是其合法传人)的利益的一切人都加以肯定甚至高度称颂,例如肯定甚至赋诗讴歌反对跋扈朝廷、觊觎皇位的太师董卓而以身殉国的人(荆州刺史丁原、尚书丁管、越骑校尉伍孚、司徒王允等),肯定甚至赋诗赞颂反对专国弄权、擅作威福的丞相曹操而被残杀的人(车骑将军国舅董承、名士祢衡、名医吉平、国丈伏完、尚书崔琰、侍中少府耿纪和司直韦晃等),高度称颂忠于刘备而坚决不向其敌对方投降或屈服的人(谋士徐庶、蜀国丞相诸葛亮、蜀将关羽、蜀将赵云、蜀将傅彤和祭酒程畿、女杰马夫人李氏、蜀国驸马诸葛瞻及其儿子诸葛尚、北地王刘谌等);(2)谴责不诚信且违背正义的人和事——对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而损害东汉刘氏皇朝及其代表刘备的利益的一切人都加以否定甚至严厉谴责,例如毫不留情地谴责藐视皇威以至废旧帝立新君甚或篡权自立的人(太师董卓及其手下将军李傕和郭汜、丞相曹操、南阳太守袁术、渤海太守袁绍、魏王曹丕等),指责背弃东汉皇朝或其代表刘备而依附曹操及其子曹丕的人(水军都督蔡瑁和张允、老臣华歆和王朗等),严词谴责背弃刘备及其继承人刘禅的人(将军吕布、公安守将傅士仁和南郡守将糜芳、上庸守将孟达、蜀将黄权、蜀将魏延等);(3)对不诚信但不违背正义的人和事不仅不谴责反而有所褒奖,例如对背叛刘备的敌对方而投靠刘备方的人(从事胡班、老将黄忠、少年将军姜维、新城太守孟达、老将严颜、魏将夏侯霸等)一般加以肯定,对那些背叛与刘备并未交恶的主人而投靠刘备方的人(将军马超等)基本上加以肯定,至少不谴责;(4)对诚信但违背正义的人和事不仅不称颂反而有所非议,例如对忠于刘备的敌对方而不愿投靠刘备方的人(魏将庞德、魏将张郃等)往往有所否定,至少不称颂。罗贯中所理解的正义的要旨就是维护东汉刘氏皇朝及其代表刘备的利益,包括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尊重和加强其威权等等。他的正义观出自封建正统意识,为我们所不取。不过,他以正义原则评判诚信或不诚信的人和事,值得我们借鉴。
在谈论正义与诚信的关系时,人们通常设想的例子有二:(1)医生是否应当把真实的病情告诉脆弱的绝症患者?(2)军官是否应当把一个士兵阵亡的消息告诉其老迈多病的母亲?对所有这类问题的否定性回答可以统归到所谓“必要的谎言”之下。如果一个谎言不会给直接相关人造成任何损害反而可以给他们带来某种利益,而相反的真话会给直接相关人造成某种严重的损害,那么人们就可以暂时违背言语真实性之要求,而在有限的范围内撒出这个谎言。不过,在辩护“必要的谎言”时,人们应当周密考虑并审慎权衡它所可能涉及的所有直接相关人的利益,而不只是第一直接相关人的利益。例如,当一个医生决定是否透露一个绝症患者的真实病情时,他不仅要考虑患者本人的利益,而且考虑其配偶、子女或父母等直系亲人(如果有)的利益,因此他的比较明智的选择是,在一定时间内不把真实病情告诉脆弱的绝症患者本人,但告诉其直系亲人并嘱咐后者保密。如果医生出于避免心理伤害之考虑而甚至不把绝症患者的真实病情告诉其直系亲人,那么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1)绝症患者的直系亲人未能为病人的突然去世做好准备从而承受不必要的损失或不便。(2)绝症患者的直系亲人因未能尽心尽力照料病人的最后岁月而深感愧疚甚至痛苦。而这两种情形都违背了正义的要求,也违背了医生的初衷。周密考虑并审慎权衡一个决定所可能涉及的所有直接相关人的利益,这需要人们具有比较成熟的实践智慧。
不同于被动单向的个体理性限度,诚信的社会正义限度是主动单向的。也就是说,主体是基于正义原则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决定在某种特殊情境中不对某个特定的对象遵循诚信的某个内在规定,而这种决定不能成为对象不向主体践行必要的诚信义务的借口。例如,一个医生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把真实的病情告诉一个脆弱的晚期癌症患者,这不应当成为该患者不向该医生提供其真实的病史和临床感受的借口。
限度并不意味着虚无。谈论诚信的限度并不等于为不诚信的行为辩护。深入认识诚信的个体理性的、根本利益的和社会正义的限度,正是为了更适当地要求诚信和更合理地践行诚信。
[收稿日期]2005—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