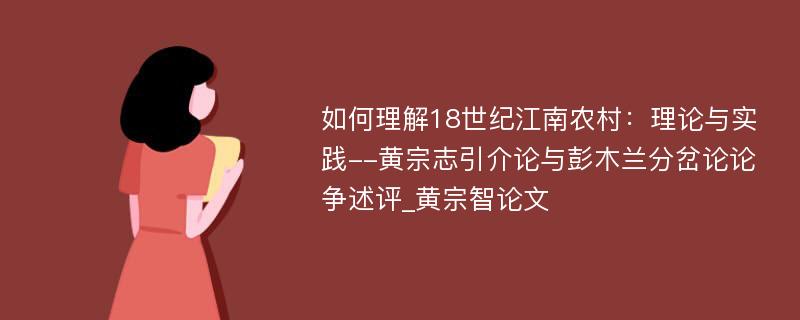
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岔论文,述评论文,江南论文,之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叶以来,对如何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在西方汉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由于中国在20世纪以前基本是农业社会,因此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认识也主要是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认识,对此西方汉学界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最新的解释是彭慕兰所提出的分岔论,在他看来,18世纪以前的中国(江南)农业与欧洲(英格兰)基本相似,江南甚至不少地方领先,只是约1800年后才出现根本性的分岔,主要原因则是英国能从美洲殖民地得到大量原材料及英国国内有容易开采、接近的煤矿(而江南均没有)。此说法在不少方面对既有的学术成果进行挑战,最重要的即是认为18世纪江南不存在黄宗智所说的内卷现象,从而从根本上否认黄宗智内卷化理论的成立。对此黄宗智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2年5月号发表长篇书评阐述自己的观点,彭慕兰亦予长篇回应。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从中国与西欧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他们人口史某些观点的解释。
2002年6月3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下面即简要综述各人的主要观点,然后是笔者的几点评论。
一、讨论会主要观点综述
此次讨论会虽然是围绕18世纪中(江南)西(英格兰)是内卷还是发展的分歧展开,但会上双方争论的实际是两个分开的议题,即一、从总体上综合讨论18世纪英格兰(欧洲)与江南(中国)两个经济体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分岔,亦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还是在劳动生产率、人均产量、劳动分工、收入与消费等方面均基本相似或甚至江南更为领先?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彭慕兰与杰克·戈德斯通重点讨论的即是此一议题;二、中(江南)西(欧洲)人口行为的差别。前一议题的作者在各自的研究与评论中分别引用了不同学者对此的看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些学者包括武雅士(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等引证其观点)与李中清、王丰和康文林(彭慕兰、杰克,戈德斯通引证其观点)。
(一)两个经济体的比较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认为,为了认证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相似,彭慕兰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可以简称为“五大变化”(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的证实。他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尽量写成是发展性(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增)的变化,由此求得他希望的中英、中西等同。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以及它们和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巧合交叉,而18世纪长江三角洲则不见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它呈现的不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起源,而是19世纪巨大社会危机的形成(其中症候之一即是穷人在生存压力下溺杀女婴)。中国后来进入现代经济发展的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是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而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减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在与中国有关的实证上,彭书则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经验研究错误。譬如,他以为一匹棉布的生产过程中,要用3天来织布(并因此估计一个从事棉布生产的农妇收入会高于一个男雇工)。其实,织布一般只花1天,4天纺纱,余下来的是弹花、上浆等工作的时间。又譬如,他想象江南农民每人每年消费10匹棉布和2匹丝绸,甚是无稽。国外经济史研究倾向于轻视关于具体生产状况的知识而偏重时髦理论和书面数字,彭书正犯了那种错误(注:该文已译成中文,中译文全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针对黄的批评,彭慕兰《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多未正面回答,相反,他主要是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从实证到概念进行全面的否定,以进一步强调中(江南)欧(英格兰)18世纪的相似性及美洲原料与国内煤对英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彭认为在比较劳力集约时应比较单位总产而非每亩劳力投入(他认为如果在一亩土地上比别人多干一倍时间但多一倍收入,这不是内卷),在总计劳力时应将成年男女与儿童予以区分(他们的生产力不同),同时还应考虑确保食物的生产占全年劳动的时间(江南比英格兰少)。彭又认为植棉并纺织的日收入并没有黄所认为的那么低,且在前现代条件下,农业中平均劳动生产率总是极大地高于家庭纺织业,这与内卷没有关系。彭还认为黄的内卷定义“劳力边际报酬递减”对所有生产都适用(一位精心播种第一块地而粗心播种第二块地的农民并未陷入内卷化生产),并非中国经济的特别现象;内卷应该表示每天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而这在中国不曾出现,却在早期欧洲有。他不认为18世纪江南存在人口压力。
针对黄就彭某些硬伤的批评,彭回答:其一,他对纺织工序中时间安排的误解并不影响其总的观点,即纺织收入高(经重新计算他认为一天布的收入可抵够一人20或30甚至40天消费的大米)。其二,他认为不是江南所有人都是穷农民,布也不只是用来做衣服,而黄所依赖的徐新吾的资料大成问题。因此彭不仅坚持江南棉布消费与英格兰相似、糖也消耗相当(江南人均年消费10磅糖),且认为江南一般人吃得比一般英国人好。
最后,彭不认为易于得到煤与美洲原料乃大分岔的全部,但中/欧与江南/英格兰的比较表明此二因子被低估了,他认为是煤与蒸汽机的结合诞生了新世纪。煤在英国缓解了燃料危机,而江南仍靠植物燃料。总之,彭坚信18世纪后期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能把中国、欧洲纳回到完全分开的“发展的”、“内卷的”只存在对立的范畴。
但黄宗智《回到实质性问题:对彭慕兰就我的评论所作的回应的反驳》认为,彭与黄在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内卷的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不同意见。因为在纺织业收入与种稻收入的比较中,彭把儿童劳力转换为成年劳力后得出的结论(1比2或3)其实是强调棉纺织业代表的是比农业低的劳动回报——而这正是黄的主要观点。小麦生产也是。但黄认为彭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换算来掩盖他其实同意黄的方面,比如彭指责黄把总劳动投入与总产弄混,但黄认为他说的只是劳动投入的差别,没有说回报也有同样的差别;又如彭没有注意到人均消费(含小孩)(2石)与成人平均消费(3石)的差别及粮食消费与维生所需(含粮食及其它)的差别。
从实际生产条件出发,黄认为要比较江南水稻生产与英国小麦生产就得比较稻与麦或米与面粉,要比较两者农业就得考虑英国的动物产品(折算成谷物当量)而不能只将英国谷物生产与江南粮食生产相比(江南乃谷物农业),比较两者还得考虑农场规模的巨大差别(江南农场只及英国的1%)。黄认为彭无视差别而强求两者相似的作法也表现在处理英国的种种巨大变化上,包括农业革命(18世纪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翻番,江南则下降)、新城市化(英国中小城市增加)、原始工业的革命(英国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江南仍留在农家且为农业的辅助性生产)、消费革命(英国出现更多的农产品及农村对城市产品需求扩大)等。黄因此质问:如果18世纪长江三角洲劳动生产率真的下降且贫穷压力明显(溺杀女婴、售妻女等),而英格兰却有大量长江三角洲没有的变化,包括农业劳动生产率翻番、城市人口增加(三倍于江南)、原始工业增加(江南仍留在农户内)、急剧的消费变化、煤的极早发展……彭对所有这些并不反对——那么如何使人相信这两个经济体保持大致相等?黄强调指出这种只注重数字运算而忽略当地情况(生产与生活条件)的研究方法会导致大量严重的错误;他的比较也因此注重的是农场大小、劳动投入、作物组合、肥料使用、技术、产量等实际生产条件,而不是其它。
上述比较侧重中国史方面,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则侧重从欧洲史角度出发进行比较。他们认为英格兰与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英格兰本身的社会经济制度从早期近代之初就已与中世纪不同)。两者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或经济再生产方式而导致不同的发展型式。1500-1750年间英格兰农民为竞争租佃而作出其生产决定,由此而迫使利润最大化。农民被迫寻找增加总产同时降低劳动投入的途径。农民视大农场为更有效而不愿通过使用更多的劳力而降低利润。农民经济条件差时晚婚、独身多;田块日益集中,劳动生产率提高;英格兰农村农工结合是为谋利,等等。表明它所经历的是斯密式经济演化。而同期江南农民往往拥有部分或全部的产权(永佃权、田面权等),缺乏真正的租佃市场,地租由政治、非由市场竞争决定。地主攫走约30-40%的收成却无意投资农业。佃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民为续香火而早婚、求多子,但田产多子均分。人口压力日增而田产日小,结果只有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求最大的毛收入,劳力集约。糊口的同时每日劳动力产出下降,剩余积累少。长江三角洲农工结合是为了生存,等等。它所经历的是马尔萨斯式经济演化。他们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已经分岔。从1750年至1850年则是此前发展路径的延长。按世界史标准衡量,18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是发达国家(1800年时英国已不再是农业国),而长江三角洲变得更穷。作者还指出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国内也不存在燃料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否认彭所谓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约1800年之前没有分岔,而约1800年的决定性分岔来自于英国得到了美洲的原料与英国国内的煤供应的观点。
对于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批评,彭慕兰《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几乎予以全面否认,首先,他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有关英格兰与江南经济体差别的某些陈述,如他否认英国有市场竞争的租佃市场,否认英格兰低生育率与社会产权系统之间的联系,否认英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等。他认为是总人口的增长而不是农业中分流出的人口为新工业提供了人力,而且这种“释放”量也比江南强不了多少;英格兰地主从农业中获得的利润并没有都投资在工业上;江南也有非常活跃的土地市场;1500-1750年间英国土地所有权比江南更集中;等等。其次,彭也反对江南在人多地少压力下为糊口而投入劳力更集约的纺织业生产的说法,他认为即使那些要把稻谷收成的1/2交租的佃农,其剩余(1800年时5口之家人均4石米当量)仍超过最低生存所需(人均2石);且从纺织中所得不比农业中所得低。江南纺织扩展的原因与在几乎任何地方一样,是比较优势使得江南能进口长江上中游的米而生产其它东西。第三、彭从根本上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以农业产权关系解释江南、英格兰经济1750年时巨大差别的观点。他认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指数只能比较趋势,不能比较某一特定时间的生产力水平。相反他反复强调以人均农业产出与单位劳动产出而言,18世纪的英国农业无甚优势,不少方面反而是江南占先:人均农业产出——1700年江南人均产出为1409磅小麦当量、英格兰为1260磅小麦;1800年江南为987磅小麦当量、18世纪末英格兰为1121磅小麦。单位劳动产出——1800年英国农民每天产出是0.21石小麦、江南农民是0.20米(谷?)当量。每劳动力产出——明末至清中期江南每劳动力产出增加30%,而英格兰600—1850年增加为43%,大致接近。因此彭认为1750年两地劳动生产率的大分岔不存在,考虑到江南的高土地生产力,说江南农业在总体上占优势仍是合理的。总之彭认为迟至1750年,英格兰尚不如江南。真正的大分岔始于1750年,更多的是在1800年后,且来自于农业之外。
杰克·戈德斯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以貌似第三者的角度提倡各种社会之间、长时段的比较,他的主要观点是认为英国并没有农业革命,但长江三角洲有,或至少存在农业生产的“繁盛”。他认为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水平在1800年前从各个方面衡量都比英国强:1750年长江三角洲农业人口人均主粮产出(6.32石小麦当量)高于1700年的英国(4.62石小麦);1750年长江三角洲总人口人均主粮产出(3.53石小麦当量)高于1700年的英国(2.36石小麦当量?)。亦即1750年长江三角洲劳动生产率比1700年英格兰高50%。1750年长江三角洲只有极小部分农田弃稻植棉,绝大多数农家仍以产稻麦为主,且仅靠此即可维持高于糊口水平以上多得多的生活水准;1750年长江三角洲只用了38%的务农人口就可以养活全部人口(如加上交租量、第二季作物、豆油菜等消费),劳动生产率比英格兰高。此水平英国1800年才达到。他重点指出在户均耕地减少的情况下,长江三角洲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扩展双季栽培、使用牛耕、大量施用肥料(特别是饼肥)的结果。1750年时江南农业生产有极大剩余。这有助于支撑此期内长江三角洲迅速增长的人口。但1750年到顶点后即急剧下降(因没有新的技术改进)。工业化之前英国、中国不存在大分岔的发展途径。但他反对彭有关美洲原料与英国国内煤对英格兰经济发展作用巨大的看法,他认为是科学技术(特别是蒸汽能源作用)而不是其它(农业、可利用资源等)促进了英格兰与世界其它农业经济的分岔。
黄宗智《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有农业革命而英格兰没有?》主要针对杰克·戈德斯通涉及中国方面的问题,亦即他认为有革命性变化的地方(牛耕、肥料、双季栽培)及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变化作出回应,说明杰克·戈德斯通认为英国没有农业革命而长江三角洲有(或至少存在农业生产的“繁盛”)的观点之不成立。首先,杰克·戈德斯通认为晚明江南农业中没有用牛而清中期用牛普遍。黄认为他的这一错误主要在于依赖李伯重著作所引《天工开物》的孤例。其实宋应星讲的是太湖盆地中央桑稻农作区,土壤湿润、人口密度又高,因此牛耕不普遍;但其它地区在明清时期牛耕其实一直很普遍。他是把两种不同局部地区间一直存在的差异转化为整个地区不同时间的对立比较。其次,杰克·戈德斯通认为江南从1600年双季栽培很少到1750年无处不在,耕作制度发生急剧变化。黄认为他在此是把明末140%的复种指数说成双季栽培“很少”,而清初170%的复种指数被说成双季栽培“无处不在”。再次,杰克·戈德斯通认为增施肥料(饼肥)主要是为了补充双季栽培条件下土壤养分的损失(而不在于将已有的产量提高多少,即没有认同李伯重饼肥施用带来了肥料革命的观点),否则在同一块土地上一年收获两季会很困难。黄对此表示认同。最后,杰克·戈德斯通认为江南发生了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剧变:明代妇女分担所有农活,而清中期性别分工明显——男人干重农活、女人纺织。黄认为他所依赖的仍是李伯重的书,但李并没有这么提。妇女实际是一直参加各种劳动的,即使是以后纺织的兴盛也没有出现如此明显的性别分工变化。在黄看来,杰克·戈德斯通所谓1750年长江三角洲农业生产有极大剩余的说法显然不存在,他想象中的江南农业(除了肥料部分之外)要么夸大其辞、要么不存在、要么误解,他对农业的理解完全不能令人相信。
(二)中西人口行为的比较
武雅士《晚期中华帝国存在生育控制的证据吗?》表示,他虽然接受李中清、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中国人口行为基本特征的表述,但对他们的证据及对低婚内生育率的解释有不同看法:武认为他们的资料贫乏(主要材料为清皇室户口册薄、清辽宁道义屯户藉及1982年对3万妇女进行的1%人口生育率调查),低估出生率,其结论对中国没有代表性(如清皇室成员是城里人、不从事生产、满族,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住在农村、为生计辛劳、汉族;又道义农民为汉人旗民,系国家仆役,且存在资料不全的问题)等。武全面否认李中清等人的主要观点,即大多数中国夫妻采用晚生、早停生育与生育间隔长等方法(均相对欧洲而言)来有意控制生育。他认为中国家庭绝对不会限制而是力求多子(如通过早婚)。20世纪初调查表明中国的生育率至少是每妇女生7.5人,而大量以族谱为基础的研究表明1900年前中国生育率变幅为6.77-9.19人。武认为中国婚内生育率低于西欧部分地区的主要原因是贫穷:营养不良、没钱治病、干重体力活及因经济原因而异地分居等。最重要的经验证据包括作者在1980-1981年亲自对中国8省582位育龄妇女的访谈。作者反对中国夫妻比欧洲夫妻晚生(头胎迟)是刻意的推迟,相反中国夫妻总是想早生孩子。他对头胎迟的解释是早婚、晚潮、及未成年母亲小产率高等;早停(停止生育)的主要原因则是贫穷导致的营养不良。作者同意中国夫妻生育间隔比欧洲夫妻长,但没有那么长,而原因仍是穷而非有意减少同房次数(有意控制)。总之,他认为中国夫妻有意控制生育率之说根本不成立。
李中清、康文林、王丰《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方式认为如果武雅土中国妇女生育率为7.5的观点(黄宗智引用)成立,则中国人口在1700年至1900年的200年间会从2亿飙升为近100亿。这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此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就黄认为18世纪中国的社会危机及普遍的溺杀女婴对中国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的说法,他们反对死亡危机特别是饥馑在抑制中国人口增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危机既不是人口过剩的产物,也对长期人口增长没有影响。相反他们的研究表明,长时期内中国死亡率是相对稳定的。至于溺杀女婴,他们认为他们并未否认穷人及灾时更趋向溺女婴,但他们强调的是不光是穷人、也不仅是在危机时才溺女婴,而溺女婴对中国人口规模长期波动的影响则有待更多资料的证实。在他们看来,对长期人口规模调节起最重要作用的可能是有意调节婚内生育率。因为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总和已婚生育率(从清室的5.3到20世纪台湾的6.5不等)均比欧洲历史上的婚内生育率(8-9)低。新马尔萨斯主义认为中、欧婚内生育率类似及中国人口系统由死亡率内卷变化决定的观点站不住脚。而且近300年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却慢于世界人口增长,因此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渐降。这也是老马尔萨斯主义难以解释的。中国人口发展的独特轨迹最可能是个人和家庭有意识的行为积累的结果。
对此,武雅士认为:第一、李中清等人在进行计算机模拟测算时误解了他的数字的意义,他讲的是总和生育率,不是总和已婚生育率,两者当然有差别;第二、针对他们对其样本过小(主要是他本人的实地调查)的批评,他提出了别的地区的例子进行回应比较。黄宗智则认为,李中清等人的计算机模拟测算中没有考虑溺杀女婴,这被当作“产后堕胎”处理而被排斥在生育率与死亡率的计算之外,如果算入的话,结果完全不同。不能仅凭数字游戏反驳别人通过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注:此段中武雅士与黄宗智的观点系讨论会上的口头反驳。)。
二、几点评论
交流的目的是为了求同存异,加深理解。但此次论争双方并未形成多少共识,反而是更加强化了各自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观点的分歧更鲜明、对立。产生分歧的有不同的史实(如黄认为彭根本误解了江南纺织业生产的劳动时间分配),也有对同一历史现象的不同理解(如针对中国人口婚内出生率低的现象,李中清等人的解释是存在人为控制,而武雅士则认为是受制于以贫穷为主的其它社会经济原因)。双方均力图从实证、理论两方面证明对方观点之不成立。胜负对错读者自有明鉴,但就讨论会本身而言,则存在避实就虚不直接回答问题的毛病,有的被批评者并不认真对待批评者提出的问题,反而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强调自己被批评者批评的观点。听众在更多时候觉得大家在各说各话,并未形成对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更谈不上形成什么共识。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这场争论不仅仅是不同理解间的争论,更是两种研究学风的较量。虽然都力图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各有侧重。其中如黄宗智曾多次赴长江三角洲实地调查,并特别重视发掘、谨慎地使用原始中文资料;而武雅士更不断强调他曾从南到北走访过数百位中国妇女(没有谁比他访问得更多),他们在结合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李中清等也作了长期的实地调查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因此黄宗智对这些资料本身并无异议,他批评的是李中清等人对这些资料的使用与解释)。但彭慕兰对江南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因而出现被黄宗智认为属于无稽的硬伤,这些错误本不该出现。至于戈德斯通根本就对江南农村缺乏感性认识。他在唯理论上也表现得最明显最突出,他的目的是建立一套反西方中心论的学说,彭慕兰等人有同样性质的研究无疑给他极大的支持,于是曲解加误解演绎出一段并不存在的江南农业史。
这一特点说到底是对具体生产条件的不同态度。黄宗智对彭慕兰的批评主要即是认为彭忽视了具体的生产条件,而对生产条件的重视则是黄一以贯之的特点。因为在他看来,农业史研究脱离了生产条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典马克思主义比较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黄则进一步强调生产条件(conditional production),这可以认为是对马克思经典经济学的一种重要修正。所谓生产条件就是在有限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在黄看来,农业生产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用价值、价格等东西来度量的。而这种偏重理论与数据、轻视具体生产状况的知识的作法正是西方学术界的时髦。他认为国内经济史研究也受此影响而有忽视生产实际研究的趋势,他呼吁国内研究者要重视自己的传统,尤其是农业史研究与农学史研究的传统,亦即生产实践研究的传统(注:此系笔者与黄宗智先生的个人交流。)。所以黄的长篇书评所强调的主要是经验论证问题——这既是立论之基,也是彭书的核心。黄讨论的重点即是具体的生产条件,如农场大小、劳动投入、作物组合、肥料使用、技术、产量等,而较少讨论价格等其它因素。另外,大量研究已经表明,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进行解释,如果过于拘泥所谓经济学“常识”认为边际报酬太低时农民就不会投资(劳力资金),则中国农民恐怕都要在家里喝西北风了。
对不熟悉江南农业史的读者来说,这场争论引发出来的问题之一则是谁更接近18世纪江南(中国)农村的真实。虽然双方都有各自认为可靠的材料以为经验认证的基础,但却存在谁的事实更客观的问题。绝对复原“客观”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对历史事实的了解也随材料的不断发掘而深化,但历史也不能是随意的想象(为符合某种理论而度身量做、曲解史料等)。一户18世纪江南农户(5口之家)每年消耗50磅糖、用掉50匹布、10匹绸?且其中女的因纺织收入还比男的高出许多倍?任何一个有过在中国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一定会纳闷二、三百年前这种农家存在的可能性。难道江南农民也在茶里放糖吗?或者每年都换一床新棉絮、做一套新棉衣——否则那么多的棉布如何消耗得了?如果妇女单纺织其收入就是男人的许多倍,为什么(正如讨论会中一位听众提问的那样)男子不去纺织?他们都蠢笨至极?
产生这种虚幻的境象涉及到如何解释中国历史(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及美国学界提倡标新立异的研究作风(力求与以往研究不同)。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激发学者们去寻找其根源,而东亚研究又与其经济发展有微妙的关系,上世纪中后期当日本经济已走向世界前列时,有学者开始认为日本19世纪甚至更早就与西方一样了,所以它能成为非西方社会中唯一成功西化的国家。现在中国经济地位日益强大,也有人开始认为中国与西方原来其实也没有大差别。而标新立异、以提出新的理论为胜更是典型的美国学风,正是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美国中国学(至少在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面)新人辈出、新说纷呈,从冲击说到内卷化到分岔论代表了不同的阶段,然而越来越偏向理论的趋势却未能与重视生产条件更好地结合,所以引发大量对基本史实及由此派生出的解释的质疑。就学术发展而言,质疑、争论是好事。这也是保持学术活力的重要前提。
彭慕兰此作是弗兰克《白银资本》等类著作的延续,他们的总基调是18世纪前中国(江南)与西欧(英国)经济并无大的不同。但农业在1850年以前的西欧及20世纪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因此比较两者的经济不能不提农业。然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完全没有涉及农业,该书虽曾喧嚣一时,但推波助澜的并非经济史学者,因为中国的经济史学者对他的观点毫无兴趣。他们认为弗兰克认证的不过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注: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未刊稿))。但彭慕兰的《分岔论》则以农业为重点,且比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具体得多,他不仅利用了不少有根据的材料,而且直接挑战不少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见解。但如果说江南农业并不比英格兰农业更劳力集约,则等于是否认中国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就要改写。这与接受李中清等人的观点等于要改写中国人口史乃至中国史一样。对李中清等人的观点,国内人口史学者如曹树基已先期作出了的回应(注: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有关彭慕兰等对中国农业史的理解,国内的经济史界尤其是农史界应该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毕竟他们是最应该提出自己看法的人。
国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此次争论双方莫不如此。这又涉及到如何对待中国本土学者研究成果的问题。有的人大量引用中国不同学者的研究并表现出相当的尊重;有的人则仅有选择性地采用个别人的研究而置其它多数人的研究于不顾,或认为这些研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既然大家的比较以相当篇幅涉及农业问题,各位就应注意农业生产的有关知识,这并不需要历史学者一定也得接受农学知识的培训,但参考农学界、农史界已有的成果并非难事。如果参考了这些著作,有些所谓的争论可能根本就不成立。比方说有关肥效递减的问题,这早已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又如豆饼的施用,并不是想当然的直接扔在田间,因其系高效有机肥,未腐熟前不能直接施用,否则作物非但不能吸收反而会因在田间腐熟而烧坏作物。因此施用前先须将豆饼打碎,然后堆起来发酵,并里外翻动多次,过几天等充分发酵后方可施入田间。考虑这些工序后对施用豆饼的用工显然与直接施用有不同的理解。在此方面,黄宗智对中国农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示出充分的尊重。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都特别倚重国内农史研究的成果。
不过,彭慕兰其实是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视野中进行考察,进行这种欧亚大陆的大跨度比较也许只能主要依赖二手文献,或者因为研究者的某些个人原因而难以进行必要的一手调查而不得不选择依赖二手文献,所以彭慕兰与杰克·戈德斯通大量依赖李中清等人的清代人口史研究与李伯重的清代江南农业史研究成果。只是引证者可能因此忽视了被引证者想要强调的主题。如李中清等人要证明的是中国、西欧人口行为如何的不同,他们的目的是要提出自己的一套对中国人口史的解释。而彭以他们的研究为基础要证明的却是18世纪两者经济如何的相同。如果说不同的人口行为与相同的经济结果并不一定矛盾的话,在农业方面即中西比较的核心方面出现的不同就令人困惑了。在杰克·戈德斯通看来,李伯重无疑是清代江南农业史的唯一权威;彭慕兰虽然引用了更多的二手研究,但在他看来,任何人的研究差不多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唯有李伯重的研究几乎无可挑剔(这一点恐怕李伯重自己也不敢首肯)。而且,在《江南农业发展1620-1850》一书中李伯重所要竭力证明的是中国与西欧如何地不同,他以此想要表达的概念也是不能用西方的一套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可彭以他的研究为基础却拼命证明1800年以前中国与西欧并无不同。是不是说李伯重所强调的不同只是1800至1850年所发生的事呢?不能否认50年可以有很大的变化,但这并不是李伯重的本意,他要强调的是中国明清以来的持续发展(而非如西方学者认为的长期停滞)及中国与西欧的不同,他提倡的是要用不同的理念来理解中国。因此他甚至批评黄宗智的研究(其研究被公认为是最“中国式”的研究即用中国的资料解释中国历史,提出符合中国的模式解释)也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反倒是彭慕兰、杰克·戈德斯通等人大量利用他的研究成果却得出了中国与西欧在1800年前并无大差别的结论。这多少有点讽刺的味道。
此次论争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即是双方在行文中有不少简单但量大的演算(虽然不是经济学上的复杂数学运算),这种量化无疑可以提高表述精度、增强说服力,这也是国内学者要加强的地方。但唯数字是否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当这些数字掺入太多的不确定成分时(即一个又一个的假设)?比如经计算得出中英劳动回报率相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时就反而令人有不精确之感。如果大量貌似精确的计算所得出的总的结果乃虚幻的境象;这种计算又有多少意义?另外,历史研究有时并不能全靠数字统计,而且并非什么都是可以量化的,当一般说中国历史上因生态变迁而导致老虎大象等动物分布范围不断缩小、数目不断减少时,人们并不能提供每年减少多少头、只的数字。这一结论主要来自相关文献的文字描述,但谁又能否认此种描述的真实性?如果某人碰巧得到一份皇家狩猎园的记载说明其中的老虎数量其实是在不断增长,这一准确的局部数字记载能推翻上述靠文字描述得出的总的结论吗?
这同时也牵涉到局部与整体的比较。为什么某些单个例证就可以用来表示一个时代或甚至几百年间全江南或甚至全中国的情况?今日上海的发达可以代表全中国的水平吗?如果一则研究指的是上海如何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另一则研究说(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中国仍处在较穷的欠发达阶段,为什么一定要用一则研究的结果去否认另一则研究的结果?因为两者说的都是实情。还有比较的标准或一致性问题,象杰克·戈德斯通那样把不同时段发生的事拉在一起比较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各方在挑战对方时另一较普遍的现象是指责对方对原材料的误解、曲解或遗漏。作为历史研究对原材料的理解是最基本的方面,如果在这方面出现硬伤肯定要严重影响其研究质量。另外彭等人选择自己中意的二手资料时往往指责别人使用的成果是旧的,但历史研究并不表示新的就是对的、好的。而要看这一研究所依赖的材料的可信度及其结论的可信度。
最后,此次争论也引发对研究方法的思考,究竟是凭想象的纸面推论还是从实地考查中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是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争论中有些非常实质性的质问并没有得到回答,答辩者反而是回避问题而从别的方面来反复强调自己受到批评的观点而不是力图拿出更多的实证来。究竟是需要无视实际、惊世骇俗的理论,还是提倡没有理论光环但材料详实的实证研究?
这是一个看起来答案简单但实际上见仁见智的问题,争论双方的文章本身对此已经表现出各自的偏好。所以讨论会虽然结束了,争论绝对没有终止,论战双方及其支持者之间的争论肯定还会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场合继续下去。从大的方面看,此次争论也不过是长期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的延续,只是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已,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这一争论不仅引起了中国研究学者的兴趣,而且引起欧洲史学者、世界史学者的兴趣,从而有助于扩大中国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这对整个西方中国经济史研究乃至中国学来说都是好事(而国内学界周仁肯定也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它将推动该领域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