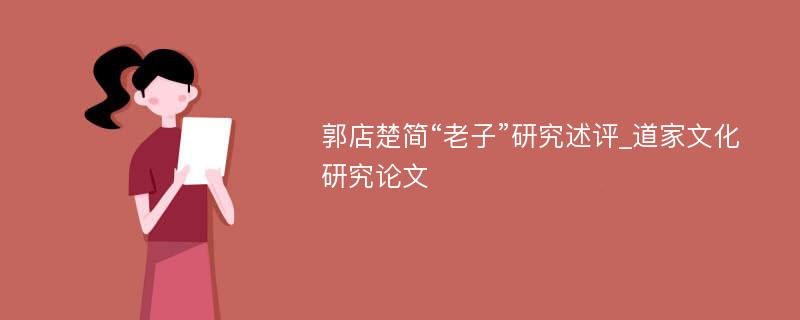
郭店楚简《老子》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子论文,郭店楚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627(2003)02-0033-07
自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面世至今,学者们对楚简《老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发表并出版了许多论文和专著,使我们对老子其人其书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和评价。当然,学者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比较大的分歧。因此对目前学界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和看法,进行一次全面的总结和梳理,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一、如何认识早期儒道关系
关于早期儒道关系,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曾有过如下论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可见,在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他所见到的先秦文献中对早期儒道关系的记载,是十分紧张的。自郭店楚简《老子》出土后,人们开始对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今本《老子》十九章中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句,楚简《老子》为“绝智弃辩”、“绝伪弃虑”。由此看来老子并不反对“圣”,也不反对“仁义”,这便为我们重新评价早期儒道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庞朴说:“谁都知道,圣和仁义,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德行,……令人惊讶的是,现在的竹书《老子》居然未曾弃绝这些,……如果这里不是抄写上的有误,那就是一个摇撼我们传统知识的大信息”(《古墓新知——漫读郭店楚简》,《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解光宇、刘焕藻也认为“郭店竹简《老子》的出土,表明了儒道两家在早期是和平共处的”(解光宇《郭店竹简〈老子〉研究综述》,《学术界》1999年5期);“道儒两家学派的创始人都主张‘仁’,说明我国哲学史上最早的两大学术派系于发轫时,彼此的学术思想是相通的,并非泾渭分明,格格不入”(刘焕藻《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理论月刊》1999年5期)。以上的观点代表了多数学者的看法,但有的学者指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张岱年说:“竹简中也有‘大道废,有仁义’这句话,说明老子对仁义还是反对的”(王博《张岱年先生谈荆门郭店竹简〈老子〉》,《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吕绍刚说:“惟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逻辑思路与另两句不同。……其实《老子》讲‘绝伪弃诈’的伪诈,指的是儒家鼓吹的仁义。仁义在道家眼中与伪诈同义”(《〈郭店楚墓竹简〉辨疑两题》,《史学集刊》2000年1期)。许抗生说:“简本中不仅有贬抑仁义的思想,而且有与孔子儒家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如简本中有‘绝学亡忧’、‘绝智’和‘闭其门,塞其兑’(杜塞耳目)、‘绝为弃虑’等思想,皆是与孔子的好学、好思的思想相对立的”(《再读郭店竹简〈老子〉》,《中州学刊》2000年5期)。
我们认为早期道儒关系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不同的视角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简本《老子》与帛书本及通行本相比,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存在很大差别。特别是简本《老子》中对“仁义”的态度,与我们传统的认识差别更大。帛书本及今本《老子》十九章中“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简本作“绝智弃辩”、“绝伪弃虑”。可见简本《老子》并不反对“圣”和“仁义”。“故大道废,安有仁义”,表明“仁义”的地位仅次于“道”而居第二位,这表明早期道家对仁义学说的包容,这一点我们从简本与今本在文字上的差异也可以得到证实。今本十八章比简本多出“慧智出,有大伪”句,将“大伪”与“仁义”、“孝慈”、“忠臣”并列在一起,这无疑使“仁义”、“孝慈”、“忠臣”具有了否定和负面的意义。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简本《老子》恰好没有这句话,因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早期道家是排斥仁义学说的。另外,今本《老子》的“与善仁”(八章)、“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三十八章)等表述,也与简本的思想一脉相承。
虽然简本《老子》并不反对仁义,早期道儒之间的关系也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紧张,但两家学说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儒家崇尚仁义;道家追问人与自然之关系,儒家则注重探讨人与人之间的纲常伦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简本《老子》不反对仁义便忽视了道儒间本质上的差别。楚简《老子》中绝大部分是阐述自然无为、谦下不争、寡欲知足的,这是贯穿楚简《老子》甲、乙、丙本唯一的主题。而简本《老子》中对仁义的论述只出现一次,这说明老子虽然不反对仁义,但仁义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是显而易见的。早期道儒之间的差别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两者间的包容是次要的,有限度的。我们还没有理由认为早期道儒思想是相通的,更没有达到要重写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的程度,因为道儒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并没有改变。
总的说来,简本《老子》向我们展示的早期道儒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清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当充分注意到,老子虽然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然而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道家思想,是在经过庄子及其后学改造过的今本《老子》的基础上形成的。换言之,简本《老子》只是形成今本《老子》的一种过渡形态,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另外,无论早期道儒间的关系如何,都不影响道家哲学之成为道家哲学,道家哲学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是其自然无为的思想,而不是其是否反对仁义学说。
二、关于老子哲学中“有”“无”的关系问题
把形下之“有”、“无”抽象为形上之“有”、“无”始于老子。自此“有”、“无”便成为老学中非常重要的哲学范畴,也是老子道论之核心问题。如何理解“有”“无”之间的关系,是能否正确把握道学精髓的关键所在。
老子认为“有”、“无”“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一章)。即道是“无”“有”的统一体,两者同处于一个哲学层面,“无”即是“有”;“有”也即是“无”,两者“异名同谓”。然而,今本《老子》第四十章却有这样的表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与第一章中的论述显然互相矛盾。人们虽然明显地觉察到其中的矛盾、悖反之处,然而由于缺少有利的证据而无法使此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直到郭店楚简的出土,此问题之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楚简《老子》甲本中有这样的论述:“反也者,道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亡。”原来流传两千多年的“有生于无”本身却是无中生有,“有”乃是承上文“天下之物生于有”中的“有”字衍生出来的。老子哲学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有生于无”之命题,“有”、“无”是统一于“道”的,两者不存在本末先后贵贱的问题。道体之“有”、“无”是不可分的,正是“无”才使“有”有起来,也正是“有”使“无”有了存在之根据,无论“贵有”或“贵无”皆是对道的割裂。从这种意义上看,“有”、“无”乃一物也。
然而楚简《老子》这一重要之点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郭店楚墓竹简》对此句是这样注释的:“简文此句句首脱‘有’字,即上句句末‘又’字脱重文号,可据帛书乙本补。”整理者认为“生于亡”句首脱“有”字,仍然坚持传统“有生于无”的说法。赞同这种观点的人也很多,如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魏启鹏《楚简〈老子〉柬释》(《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沈清松《郭店竹简〈老子〉的道论与宇宙论》(《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等。陈鼓应说:“从老子整体思想上看,当以简本为是。而今本‘有生于无’之说,显然与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法对应”(《从郭店简本看〈老子〉上仁及守中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我们认为陈先生的主张是很有道理的。
老子之所以产生“有”、“无”不可分割性的认识,这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老子哲学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看,老子哲学具有辩证思维、直觉思维和模糊思维等诸种思维方式。作为辩证思维的基本观念阴阳,其本身含有对待、统一、变化之功能。辩证思维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能够采取完整而非孤立、变化而非静止、相对而非绝对的态度。模糊思维是自然界普遍联系之无限性及主体认识之有限性的产物,模糊思维在以整体思维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大量存在。在老子哲学中,特别是老子对其最高范畴“道”的论述中更加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特点。老子认为“道”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这种超视觉、听觉、触觉的事物如何来展示呢?老子用了三个模糊性词语“夷”、“希”、“微”来概括,如果把它抽象为形上之物那就是“无”。另一方面,这“惟恍惟惚”之物却“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可见“道”并非空无所有,把“象”、“物”、“精”抽象为形上之物便是“有”。老子之“道”本身就是有物和无物的统一,既“有”和“无”的统一。“有”只有在无之域才能向人们敞开,“无”亦如此,只有“有”和只有“无”都是不可想象的。
三、关于今本《老子》的作者
郭沂在《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一文中指出,历史上存在两个老子,一个是老聃,一个是太史儋。老聃写的是简本《老子》,太史儋写的是今本《老子》。此说在学界影响较大,尹振环、解光宇等人表示赞同此观点。高晨阳则对此说提出质疑,说见《郭店楚简〈老子〉的真相及其与今本〈老子〉的关系——与郭沂先生商讨》(《中国哲学史》1993年3期)。我们也认为郭沂主张太史儋为今本《老子》作者的论据并不充分,简述如下:
作者第一条论据是函谷关置于秦献公之世,正好是太史儋生活的年代,与老聃时代相距甚远。按:老子列传中写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遂去。至关。”书中只说“至关”,未言何关。《史记》索隐引李尤《函谷关铭》、正义引《抱朴子》皆以为散关,或以为函谷关。可见老子所至之关为何关尚无定论。
第二条论据是老子出关与太史儋见秦献公一事相符,当为同一人。按:《史记》中讲得很清楚,是老子在“关”为“关令尹喜”著书,而太史儋出关税秦献公是在“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二者间没有什么联系。太史儋出关见秦献公之事除老子传外,《史记》之《周本纪》、《秦本纪》亦有所记载,当实有其事,太史公应有比较准确的史料来源。如果太史儋出关时写了《老子》上下篇,《史记》自当有所记载,为什么老子传及《周本纪》、《秦本纪》史均未言及此事?
第三条证据为今本《老子》的君人南面之术,与太史儋游说诸侯的身份相一致,其贬儒言论与秦国尊法非儒的传统相合。按:“君人南面之术”的含义是什么,作者文中并未言明。我想这可能与后人对老子的误解有关,我们不能轻易把《老子》定性为“君人南面之术”。另外,作者说今本《老子》中的反儒言论与秦国尊法非儒的传统相合,好象太史儋专门为了迎合秦国或为了说服秦献公而写作《老子》的,历史上并未有人论及《老子》其书与秦国有什么关系。
作者的第四条证据是春秋末年,周虽衰弱但仍为共主,老聃离周出关的理由不充分云云。这一条与第一、第二条讲的是一个意思,无非是说出关的是太史儋而不是老聃。实际上老聃出关的理由是否充分,我们得很难说清楚的,主观的推测并无有证据的效力。
总的看来,作者1、2、4条论据只是想证明太史儋出关了,老聃没出关。我们且不管此种说法在先秦文献中找不到可信根据,即便出关的是太史儋不是老聃,我们又能得出怎样一种结论呢?是“关令尹喜”请求太史儋为他著书吗?那么“关令尹喜”又是何许人?是关令名叫尹喜呢,还是关令尹名喜?或者是守关的名叫令尹喜,或者“喜”作动词用,是高兴的意思呢?据高亨先生考证,“关令尹喜”就是关尹(《史记老子传笺证》),那么关尹与太史儋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史书上记载关尹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太史儋却是个喜好预言的前识者,是位游说之士,关尹能向他请求著书吗?这些无疑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考察并做出合理解释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仅凭这些证据来证实太史儋就是今本《老子》的作者,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四、如何认识楚简《老子》甲、乙、丙本的文本构成
如何认识楚简《老子》甲、乙、丙本的文本构成,是简本《老子》研究中争论的焦点问题。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1.认为楚简《老子》是全本。2.认为楚简《老子》是摘抄本。3.认为楚简《老子》甲、乙、丙本是在三个不同时期产生的三种不同抄本。下面我们对以上观点分别加以评述。
1.主张楚简《老子》是全本的代表人物是郭沂先生,他在《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兼及先秦哲学若干问题》(《中国哲学》第二十辑)一文中提出了这一主张。赞同这种主张的有尹振环等人。但学界多数人并不赞同此种观点。
我们认为,郭沂主张简本《老子》是一个全本的论据,可做进一步的商榷、讨论。
作者的论据之一是:简本的语言和思想都很古朴,甚至连今本中经常出现的“玄”、“奥”等令人难以把握的字眼都没有。我们不知作者立论的前提从何而来?为什么不能说正是由于缺少了这些内容,楚简《老子》才不是全本呢?全本《老子》为什么就不能有形上之思辨?难道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老子,本来就不应该有“玄”、“奥”的思考吗?反过来说,简本《老子》真的就那么“淳厚古朴”、甚至连一个“玄”字都没有吗?楚简《老子》甲本8简:“长古之善为士者,必微妙玄达,深不可识。”甲本28简:“闭其兑,塞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我们觉得“玄达”、“玄同”并不那么“淳厚古朴”,甚至用语言都很难把它解释得非常清楚。
作者还有一条论据是:简本中没有与儒家伦理观念针锋相对的文字,今本中明显反对儒家观念的文字,在简本中皆有异文或文字上的增减。作者列举了今本十九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简本作“绝智弃辩”、“绝伪弃诈”等句子。这些只能说明后人对《老子》原文有所改动,与简本是否为完整传本不知有何联系?
作者又指出:先秦古籍的最终定型,往往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非出自一时一人,而后来增补的部分常常被放在原始部分之后。简本所录皆为今本六十六章之前,后十五章不见于简本《老子》。我们认为简本《老子》甲、乙、丙本合在一起才相当于今本《老子》的五分之二,所以缺了哪一部分都是正常的。且简本《老子》本不分章,排列顺序与帛书本及今本大不相同,焉知简本所缺今本后十五章,一定要放在简本这个“原始部分”之后呢?又今本与帛书本相比,帛书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帛书本的最后一章即今本的三十七章,见于简甲本18至20简,我们能说这部分是后人增补的吗?
作者的后两条证据是在论证郭店的楚墓没有被盗,我想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即使墓中一枚竹简也没缺失,也不能说明简本是完整传本。道理很简单,所谓完整传本,是指在一个时期形成的,文字和内容都没有缺失的版本。而简本《老子》甲、乙、丙本却是形成于不同时期的、三者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为墓主人所收藏的《老子》传本。且先秦传世文献中引用《老子》的文字有许多不见于简本,这些引用之人有的生活于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如叔向、墨子、魏武侯、颜斶等人。总的看来,认为楚简《老子》是完整传本的主张难以成立。
2.认为楚简《老子》是摘抄本的代表人物是王博先生,他首先在美国达慕思大学郭店《老子》学术讨论会上提出此观点,后来王博又写成专文《关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结构与性质——兼论其与通行本〈老子〉的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进一步阐述其观点。他认为楚简《老子》甲、乙、丙本各篇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主题,这三个传本都是某种形式的摘抄本,而不是当时《老子》的全本。赞同此说的有张岱年、裘锡圭、陈鼓应等。
我们认为如果说简本《老子》是摘抄本则首先要证明在它之前,有一个规模相当于今本五千言的《老子》全本。
王博先生认为如果简本是今本《老子》的底本,后来编者没有必要打乱原来整齐的顺序,而代之一个较松散的次序。作者立论的依据是简本《老子》的排序整齐,因而简本《老子》是摘抄本,在此之前存在相当于通行本规模与次序《老子》全本。我们认为简本《老子》并不是按照主题摘抄的,其排列顺序更无整齐可言。就简甲本而言,无论从标志符号的使用、墨钉间文字的组成、各组所含字数的多寡、“义同形异”文字的使用、意义段落的衔接等方面看,都没有显现出任何“整齐”的迹象。张岱年先生认为只有流行了,人们才能抄录它的一些内容来学习。这说明《老子》在战国末年已经有了。裘锡圭先生也认为,老子言论的广泛传播,当在“五千言”编成之后。我们认为老子语录的流行,并不意味着相当于今本五千言的《老子》文本已经形成。古人著书无作者,无篇名,单篇别行,其书多为后人辑录而成。《老子》其书绝非一时一地之作,其中有的为老子手撰,有的盖为门人弟子对老子语的辑录,有的内容则来自古训。老子每一单篇的语录形成后,便在民间流传,相当于今本五千言的老子语录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陈鼓应认为简本《老子》为节抄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竹简繁重,抄写不易,二是抄写者根据自己的构思和意图来进行抄写。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我们自然要问,既然存在如此多的不易,那么《老子》的全本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且《老子》只有五千言,亦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繁重”。就简本《老子》而言,简甲本有39支简,简丙支只有14支简,晚于甲本的丙本,其简数却比甲本少了许多。就各文本内部而言,甲本1组有20支简,而甲本3组却只有1支简。由此看来,简数的多少并不能成为认定简本是节抄本的理由。作者的第二条论据是抄写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摘抄,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第一,简本《老子》并不是按照主题摘抄的。第二,楚简《老子》甲、乙、丙本的形成存在历时性差异,是经过长期的聚积后形成的文本。第三,简甲本和简丙本都录有相当于今本64章后半段的内容,这也可以说明简本《老子》并不是抄写者根据需要摘录的。以上论述表明,认为简本《老子》是摘抄本或节选本的观点是值得商讨的。
3.丁四新博士认为楚简《老子》甲、乙、丙本是在三个不同时期产生的三种不同抄本。他在《略论郭店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的历时性差异》(《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2期)一文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后来在其著作《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中又进一步论证了他的主张。他认为郭店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皆不是原始抄本,这从它们存在着大量的脱文、衍文等现象可推断出来,真正的原始本应该向公元前5世纪去寻找。并指出甲、乙、丙三组简文的同读异文现象,体现了三组简文历时性差异。他认为战国中期偏晚或整个战国中期,《老子》书的总体状况远较郭店简书完全,在分量上离五千言的本子相差不远,在结构上可能仍然是松散的。同意这种主张的有许抗生、李存山等人。
我们认为丁四新的观点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认为简甲、乙、丙本是在三个不同时期产生的三种不同抄本,三组简文存在着历时性差异,而每种文本的形成则是并时的。经过考察,我们发现不但楚简《老子》三组文本的形成是历时性的,各文本的内容同样存在着历时性现象,特别是简甲本中这种历时性现象尤为明显。我们认为楚简《老子》是经过长期的聚积而形成的一种文本,是尚在形成中的《老子》古传本,其中简甲本形成的时间较早,只是老子语录的简单缀合,简丙本形成的时间较晚,已经显露出人为编辑的痕迹。这一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将另撰专文加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