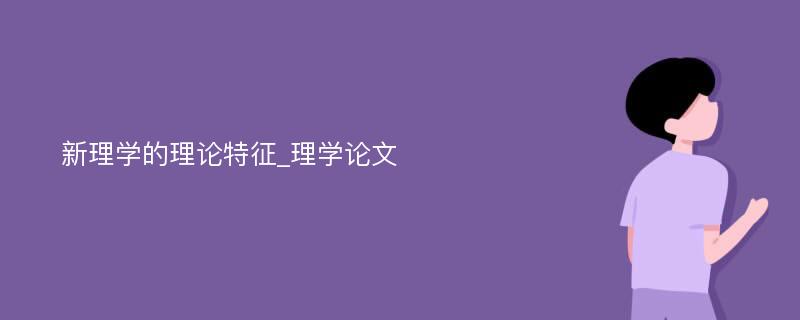
新理学的理论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品格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冯友兰先生是本世纪中国学术舞台上一位创造了丰富的精神产品、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哲学家,一位儒学大师。冯先生在我们民族灾难与复兴共存的抗日战争期间,撰作统称为“新理学”的“贞元六书”,无疑是他的学术生命中最重要的、不会被人们遗忘的组成部分。冯先生在晚年曾对他的这六部书的内容有一个总的概括:“这六部,实际只是一部书,分为六个章节,这一部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229页)深味“贞元六书”,每每会感到在冯先生的生命精神中,在他的理论思考中流淌着、迸发着一种根系于民族灾难而产生的痛苦感情和对民族复兴的热烈的期待和信心。新理学有它自己十分独特的、独立的哲学立场和眼光,在当时的背景下,从不同的、另外的哲学立场或理论角度对它提出批评,与它论争,都是十分自然的。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可以宽容地将这些作为一种历史经验、历史遗产来看待与研究了。对于新理学本身,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从冯先生所提示的这个主要内容上来进行观察和评价。从这个观察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新理学具有一种甚为可贵的、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理论品格。这种品格,可以说有三个重要的表现或内涵。
首先,新理学浸润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在准确理解和有拣择地吸纳西方哲学的理论观念的同时,顽强地保持着中国哲学的特质。正如学术界所共同判定的那样,与新理学在理论渊源上关系最密切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是美国的新实在论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在西方现代思潮中,这两个哲学流派有共同的西方近代经验主义的根源,但各自不同的理论主题,使它们逐渐分流开来。大体上可以说,支撑全部新理学的“共相潜在”的观点和作为新理学最鲜明特色的逻辑分析方法,分别来自这两个学派。但冯先生绝不是新实在论者,也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现代新儒家。美国的六位新实在论者曾一致界定说:“新实在论主要是研究认识过程和被认识的事物间的关系的学说。”(《新实在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所以新实在论的“共相”是一个认识论中的哲学概念,是一个与二元论、主观论(唯心论)皆不同的关于认识对象之本质的观念,其主要内涵是指认识对象的普遍的、共同的属性或逻辑性质的“类”。其与二元论的不同,在于这种事物本质并不是与心对立的外界客观对象(物),而是呈现于人的认识过程中的对象之某种属性。新实在论在事物间的关系问题上,采取“外在关系”说,所以与主观论也不同,共相虽然在认识过程中呈现,但与人之主观认识并无内在关系。这种普遍共同属性并不产生于人的主观认识,而是独立于人的认识并永远地“潜在”着的。冯先生新理学中的共相,当然也还具有新实在论的这种属于认识论性质的基本内涵,它是“类”,是物之“有以同”(《新理学》,《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23页),但更经常的是指“理”、“真际”。新理学认为“理之实现于物者为性”(同上书,第32页),“理世界在逻辑上先于实际世界”(《新原道》,《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150页)。新理学以此种共相说认同和诠释程朱理学的“理先气后”、“体用一源”的基本观点,表明新理学中的“共相”已越出认识论的范围,成为宇宙论(存在论)的实在,甚至具有本体义蕴的内涵,成为一种可称为“真际”的“纯客观”的实在。这样,新理学“共相”观念所要论说的理论主题和所处的理论层面都离开新实在论而归向中国哲学。因为承认“天”或“理”之最终客观根源的存在,正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的特质和传统。冯先生于此有十分明确的认定,他说:“中国旧日的理学,亦是纯客观论,中国人的精神为旧日理学所陶养者,亦是纯客观底。”(同上书,第四卷第25页)新理学的方法在形式上与维也纳学派有某种相似或关联,即新理学认同维也纳学派以逻辑分析为哲学基本方法的观点,亦认同其作为逻辑分析起点的对命题的划分和对命题意义的界定。但是,再进一步,新理学就显露了它与维也纳学派的差别。这种差别,用冯先生的话来说,是“辨名”与“辨名析理”的不同。他说:“照我们的看法,逻辑分析法就是辨名析理的方法。这一句话,就表示我们与维也纳学派不同,我们以为析理必表示于辨名,而辨名必归于析理。维也纳学派则以为只有名可辨,无理可析。照他们的意见,逻辑分析法,只是辨名的方法,所谓析理,实则都是辨名。”(《新知言》,《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233页)这种差别使新理学与维也纳学派分道扬镳,驰向完全不同的理论方向。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实际上是对命题作语言学意义上的约定论的解释,其目的在于拒斥并最终取消形而上学。新理学恰恰相反,它要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追寻到某种形而上的“理”之实在,建立某种“真正底形而上学”体质。冯先生毅然摆脱维也纳学派及新实在论的经验主义的羁绊,执着地追索形而上学,正是一种中国哲学灵魂、中国哲学物质的表现。冯先生对中国哲学精神有着深刻的洞察与自觉,他说:“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有一个思想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新原道》,《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7页),而这种最高境界的构成,就是要有对宇宙的全体的认识,要有对人生最后的觉解,这就是形而上学。所以冯先生宣称:“新理学的工作,是要经过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而重新建立形而上学。”(《新知言》,《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223页)完全可以说,新理学在其某种现代西方哲学观念外貌下保存着的是中国哲学的特质。
其次,新理学承接和诠释宋明理学(程朱理学)时,自觉地表现出崭新的现代理论观念和响应了时代要求。宋明理学(冯先生称之为“道学”)、尤其是其中的程朱学派(冯先生称之为“理学”),是儒学历史上一个最为完整、成熟的理论形态,也是历史上发生了巨大影响,而明末清初以来逐渐衰落了的国家意识形态。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是“理”。在理学中,“理”与其它一系列思想范畴都有丰富的内涵,这些内涵都是理学家根据对儒家经典(主要是“四书”和《易传》)的诠解来确定的。但在这种诠解中往往含有体悟性的个人经验内容,因而有时也是很模糊的、不一致的。对于这样的已经衰落了的儒学理论,冯先生为什么还要在民族危机最深重的抗日时期“接着讲”?他曾十分真诚地回答说:“我认为中国过去的正统思想既然能够团结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洋洋大国,居于领先的地位,也必能帮助中华民族,度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我当时的哲学思想,也接近于程朱道学。在当时希望对于抗战有所贡献的人,只能用他所已经掌握的武器。我所掌握的武器,就是接近于程朱道学那套思想,于是就拿起来作为武器,搞了‘接着讲’的那一套。”(《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260页)显然,在冯先生看来,理学中蕴藏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他的“接着讲”就是要给予这种民族精神以新的现代观念的阐释,以向处于艰难危亡中的我们的国家民族奉献自己作为一个学者所可能有的最好的贡献。新理学对理学的现代阐释,显然有两点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第一,新理学援用了一个经过它改造的现代西方的(新实在论)哲学概念“共相”来诠释理学的“理”之观念,将理学之“理”中被朱熹“以本体言之”和“以流行言之”所留下的那些实际的、冯先生称之为“不免著于形象”(《新原道》,《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146页)的内容全部剔除,转变成“以逻辑言之”的表示“同”、“类”的形式的概念。但是从宇宙论、存在论的意义上说,它却是“潜在”的,是“真际”、“本然”。第二,新理学运用分析方法(主要是援依逻辑概念的蕴涵关系),从“事物存在”这一唯一的经验事实出发,逻辑地分析出“理”、“气”两个观念,并进而又逻辑地综合出“道体”、“大全”两个观念。在这四个观念的基础上,新理学或同或异地重新解释了程朱理学的诸如天道性命等主要观念,和“无极而太极”、“理一分殊”、“心统性情”等主要论题,以及社会政治道德方面的主要观点。从对宋明理学的现代阐释的角度来看,新理学在一些具体理学问题上与宋明理学的或同或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新理学将宋明理学中的两个基本观念——理与气,从原是哲学本体论或宇宙论预先设定的实在,转换为可以逻辑分析出的实在。应该说,这是传统理学向现代观念转变的一种尝试,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实现。第二,新理学从逻辑分析立场上对宋明理学予以某种总体上的批评。新理学特别强调作为逻辑分析的哲学之思辨理智特质和形式化特质。冯先生界定哲学说:“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新理学》,《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7页),“哲学只对于真际有所肯定,但肯定真际有某理,而不必肯定某理之内容。”(同上书,第17页)从逻辑的形式化要求立场上,冯先生批评说:程朱理学“是有一定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成份,但是在新理学中把这些都避开了。按照我的意见,形而上学只能知道有理,而不知道每个理的内容,发现每个理的内容,那是科学的事。”(《中国哲学简史》第387页)从逻辑的理智要求立场上,冯先生又批评说:“宋明道学家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时,他们注重在人的道德方面,而我们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时,我们不只注重在人的道德方面,而亦注重在人的理智方面。宋明道学家所谓‘人之至者’,是在道德方面完全底人。而我们所谓‘人之至者’,是在道德方面及理智方面完全底人。”(《新世训》,《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389页)冯先生从逻辑分析立场上对理学的“有权威主义”、“不注重理智”两点批评,应该说是对那个时代“民主”与“科学”呼声的响应。
最后,新理学在审视中国历史上各种哲学派别时表现出同情的理解和宽容对待的态度。儒家学者自孟子“距杨墨”开始,对异己的学术思想皆持着批评、排斥的态度,攻击佛老并要求划清儒释、儒道界线更是理学家的经常的话题。但是,冯先生从他的新理学的“真际”的角度观察,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都是“本然”的、“正宗”的。他说:“就真际、形上方面说,哲学及各种哲学系统皆是本然底,皆本来即有,各自具备,毫无欠缺”(《新理学》,《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159页),“凡是实际底哲学系统,能自圆其说,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都是正宗底。”(同上书,第161页)冯先生因此具有十分宽容的学术心态。他虽然承接程朱理学,但并不拘束于理学的道统观,认为孔子之道“是一道统,但不是唯一底道统”(同上书,第164页);他虽然是位现代儒家学者,但却能突破儒学囿限,每每将完整的“中国精神”视为由中国固有的儒、墨、道等各家思想所共同构成。他说:“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是墨家儒家的严肃及道家的超脱,儒家墨家的‘在乎’及道家的‘满不在乎’。”(《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365页)冯先生此种宽容的、对儒外学说皆能作同情的理解和毫无成见的吸纳的学术态度,对于新理学所呈现出的理论面貌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这为新理学的理论体系的充实和发展奠立了一个比较宽广的、丰厚的观念基础。例如在新理学体系中较晚出现的《新原人》中,在对人生精神境界作划分时,于“道德境界”之上又立“天地境界”,在新理学体系中最后出现的《新知言》中,论形而上学的方法,于理智的逻辑分析“正的方法”之外,又增加了“负的方法”(直觉方法),这些都是新理学在认同、吸收道家佛家思想后发生的理论观念的变化或增新。新理学因此变得更丰满、更周延。但另一方面,新理学作为一个现代新儒学的理论体系,它的理论的统一性和纯粹性却因此受到破坏。新理学是以理智的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或特色的,又是以程朱理学中的理论观念为分析对象的,本质上是排斥整体直觉的经验体悟的方法的。在《新理学》中,新理学的四个基本观念都已经有了逻辑的“正的方法”的说明和定位,在后来,《新知言》却又认为气、道体、大全需要用“负的方法”才能显现,这似乎是不一致的。(当然,这对于新理学形而上学追求的实现来说,也还是必要的。)儒家的道德境界是以伦理的实现为主要内容的。它包括了由家庭,及社会,及天地,即由“亲亲”及“民吾同胞”及“物吾与也”的甚为宽广的领域。理学家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物也”(《二程遗书》卷十一),即在理学家看来,自觉地践履世俗伦理与“浑然与物同体”的宽广仁爱,只是儒家同一道德境界在不同境遇下的不同回应,并不是有高低区别的两种不同的精神境界。新理学将其分为“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就不再是纯正的儒家学术立场。(当然,离开儒家的立场来看,这种区分也还是精当的。)
新理学作为一个现代新儒学的理论体系,在异己文化的哲学思想面前,在准确的理解它和有选择地吸纳它的同时,能保持中国哲学的特质。对固有文化中的异己的哲学思想也抱着宽容的理解与借鉴的态度,从而能在某种意义上将一个已经凝固了的、衰微的儒学理论形态,展现出新的风彩。新理学的理论追求是否真正实现了,我们姑且不论,但它的这种独立而宽容,承旧而启新的理论品格,应该说是十分珍贵的,立得住的。它似乎还可以昭示我们,在现在和将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具有这种品格的现代儒学,会生生不息,既能与不同文化友好相处,又能挺立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