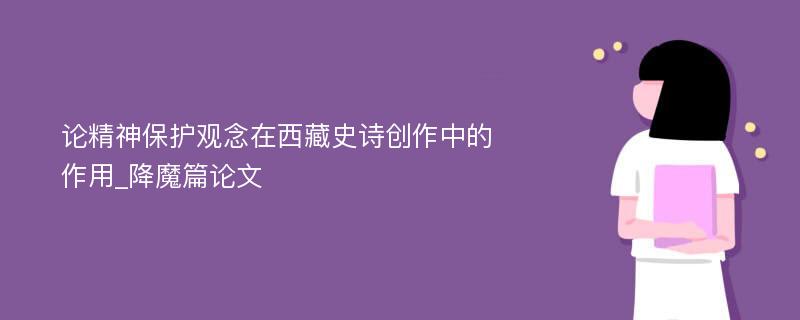
试论灵魂寄存观念在藏族史诗创作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史诗论文,试论论文,观念论文,灵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立在自然崇拜基础上的“万物有灵”观念,是早期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普遍存在的观念。藏民族也毫不例外,遵循着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在蒙昧时期,便产生万物有灵的观念。他们不仅认为万物有灵,而且还认为人的灵魂可以离体外寄,隐藏到别的物体上去。作为民间文学作品的《格萨尔》,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既带有极为浪漫的神话主义色彩,又具有历史与现实交感的写真情感。整个作品的空间既是一个充满神灵与鬼怪的世界,又是一个灵魂外寄的一个迷宫,从而将灵魂观念理解得更加世俗,表现得更加完美,运用得更加广泛。本文拟就灵魂寄存观念在《格萨尔》创作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一探讨,旨在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来展现史诗《格萨尔》的思想体系。
一、灵魂观念的内涵
灵魂观念是原始社会早期崇拜的一种形态,就藏族而言,并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完全消失,直到近代藏族社会,藏区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宗教的“沉积物”,特别是民间文学作品中,这种“活的化石”更是俯拾皆是。
藏语将“灵魂”称为“拉绍合”(bla-srog),其中包含着三个概念:“拉”(bla)即魂、“绍合”(srog)即命、“南木西”(rnam-shes)即识三者。(注: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词典》[Z](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915页。)这分别是灵魂在不同条件下的三种称谓。《藏汉大词典》解释说“绍合”为命或生命。《俱舍论》和《戒律论》等佛教经典将命诠释为体中暖、识所依的主要根器,而其他经典则解释说,自体存活之力以及呼吸气息为命。命亦名寿或生气。(注:同上,第2987页。)“南木西”指识了别对本体,分别思维各自所缘之心,总指眼识乃至意识等六识。(注: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词典》(上册),第1572页。)
关于“拉”、“绍合”、“南木西”三者的论述,还见诸不同的经论、典籍之中,如《俱舍论》道:“识(rnam-shes)所依是寿命(tshe-srog)”。《噶尔泽》(dkar-rtsis)中说:“拉(魂)是绍(命)所依”。
“寿、命、魂三者”之关系在《藏汉大词典》中作如是解:“佛书中以灯火比喻人生寿、命、魂三者互相依存之状,为寿如油灯,命如灯芯,魂如灯焰。”(注: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词典》(下册),第2283页。)贡唐丹贝仲美大师的《俱舍摄义》言:“命寿(srog-tshe)为一”。(注:恰日·嘎藏陀美整理:《贡唐丹贝仲美大师文集选编》[Z],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63页。)已故藏族学者毛尔盖·桑木丹认为:“无论如何,命与寿的区别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二者没有区别;一种说法,前世之业果是寿,今世之业果是命。”(注:毛尔盖·桑木丹:《俱舍摄义释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年11月,第73页。)
在人们看来,附着在活人身上的灵魂为“拉”,“拉”可以理解为人的生命之本,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体的精神体现。一旦“拉”消失远去,即其载体生命的终结;“拉”可以离开人体而远游,可以寄存在某种物体上。人们的“拉”之所以“不灭”,并不是单纯地指在一个人死了之后,其“拉”才离开肉体,而是说即使是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他的“拉”也可以离开其肉体而存在。离开的“拉”,不是去为神,也不是去为鬼魅,而是寄存于或动物或植物或物体之上。如寄存“拉”的树称为“拉兴”(bla-shing)即“灵魂寄存树”,寄存“拉”的石称为“拉道”(bla-rdo)即“灵魂寄存石”。在史诗《格萨尔》中还出现有“拉日”(bla-ri),即“寄魂山”,“拉错”(bla-mtsho)即“寄魂湖”,“拉仲”(bla-vbrong)即“寄魂牛”等等。
灵魂观念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人们意识中的特定的组成部分了,因而在英雄史诗《格萨尔》中,多有非常生动而形象的表达。如《征服大食》中珠牡在唱词中唱到:
上玛地荡漾着一湖泊,宽阔的水面上翻金波,金色天鹅嬉水起又落,这是长系的寄魂湖泊。中玛地荡漾着一湖泊,宽阔的水面上翻翡翠波,松石色水牛横卧其中,这是中系的寄魂湖泊。下玛地荡漾着一湖泊,宽阔的水面上翻银波,雪白的海螺逍遥其中,这是幼系的寄魂湖泊。(注: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搜集翻译:《征服大食》[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第317页。)
其中即形象地描述了岭部落“长系”、“中系”、“幼系”三系的三个寄魂湖。
二、《格萨尔》中的灵魂寄存体系
人们将灵魂寄存的物体称为“拉内”(bla-gnas),即“灵魂寄存处”。在《格萨尔》中,寄魂物体可以是动物、植物,还可以是山川、湖泊,以及飞鸟、走兽、爬虫、游鱼、树木等等。我们将《格萨尔》中所涉及到的灵魂寄存内容总结出来,可归纳为两大体系:即岭部落的灵魂寄存系统和其他部落的灵魂寄存系统。
1、岭部落的灵魂寄存系统
《格萨尔》中,岭国强大,英雄众多,上有天神之子格萨尔王,下有诸多的英雄豪杰,部落和个人都将各自的灵魂寄存在灵魂寄存物上。岭部落拥有共同的灵魂寄存物,各小部落也拥有各自的灵魂寄存物,如嘉洛、鄂洛和卓洛三大部落分别将自己的灵魂寄存在“扎陵湖”、“鄂陵湖”和“卓陵湖”三湖中。而董氏(注:董氏,在不同的翻译本中,还有译为冬氏、栋氏者,由于引文中应尊重原译,故本文中不作统一处理。)长、中、幼三支亦有各自不同的灵魂寄存物,长支寄魂于大鹏,中支和幼支分别寄存在青龙和雄狮上。
岭国的寄魂鸟(gling-lha-sde-bla-bya)有三种,正如《降魔篇》中记述:“白仙鹤是岭国鸟,黑乌鸦是岭国鸟,花喜鹊是岭国鸟,这是白岭三种寄魂鸟。”(注:《降魔篇》,《格萨尔文库》(藏文版)[M](第一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921页。)
格萨尔的寄魂山是“玛沁奔热”,即阿尼玛沁雪山,寄魂湖是扎陵、鄂陵、卓陵三湖。这座圣山和三个圣湖,同时又是岭部落的寄魂处。
岭部落总管王、格萨尔王的叔叔绒擦查根亦有自己的寄魂物,他的寄魂物是一顶被称做“朗拉古通卓奥丹”的大帐,即“解脱光明大神帐”(gling-lha-gur-mthong-grol-vod-ldan)。
2、其他部落的灵魂寄存系统
除了英雄诞生的岭部落的灵魂寄存系统外,《格萨尔》以及其他文献资料中还描述了岭部落的敌对势力、代表邪恶势力的灵魂寄存系统。
岭国的敌对势力一般指天魔、赞魔、木魔和龙魔等四种魔王。格萨尔所降服的四方妖魔一般指魔国的鲁赞王、霍尔国的黄帐王、黑帐王、白帐王、姜国的萨丹王等,他们就是这四种魔王的化身。这些敌对势力的寄魂物更是多得数不胜数。其中,龙魔鲁赞王的寄魂物有多种,如他的寄魂牛是红野牛(vbrong-zangs-twa-dmar-po),寄魂湖在黑魔谷(bdud-lung-nag-pu),寄魂山是九间铁围宫(lcags-ra-rtse-dgu),寄魂鸟是共命鸟王(bya-shing-ba-shang-shang-rgyal-po),寄魂树在森林。鲁赞王姐姐卓玛的命魂寄在一只装在珊瑚瓶子里的玉蜂身上。鲁赞王妹妹阿达拉茂有一个寄魂的蛙头玉蛇。鲁赞王弟弟才雏则有一只寄魂的箭。
霍尔国的白帐王、黄帐王和黑帐王,分别将自己的灵魂寄存在白、黄、黑三个野牛身上。霍尔四十九代大王的寄魂山是德载萨瓦泽(sdag-rtse-gsal-bavi-rtse,明亮虎峰)。霍尔国三王的寄魂树分别是白螺的生命树、黄色黄金生命树和黑色铁的生命树:
在那金制宝座的里面,有一棵白螺的生命树,它是白帐王的生命柱;有一棵黄色黄金生命树,它是黄帐王的生命柱;有一棵黑色铁的生命树,它是黑帐王的生命柱;是我三大王的生命树。(注:《降霍篇》,《格萨尔文库》(藏文版)[M](第一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373页。)
霍尔王的寄魂鱼是“寄魂鱼三兄弟”。白帐王的寄魂鸟叫赛沃灾鸟(bya-than-bse-bo),寄魂宝刀(bla-gri)名叫“挥斩千军的拖把镇国宝刀”(gri-stong-sde-sha-gzan),寄魂鸡叫做“沙鸡(bla-bya-sreg-pa-spun-dgu)九兄弟”。这些寄魂宝物都具有特殊的神力,如寄魂宝刀的“刀背能砍断牛腿,刀尖能剐骨剔髓,刀刃可挑断虎颈,刀把能舂掏谷米,刀光能映照人像,刀锋能斩杀飞蜂,刀面如流水细滑。”(注:同上,第1396页。)
黑帐王的寄魂山是“索日安沁山”(sol-ri-rngam-chen),山林中的大树是霍尔黑帐王的寄魂树。格萨尔征服霍尔白帐王后,将霍尔国的“九件宝贝”带到了岭国,其中就有霍尔王寄魂的寄魂物:
霍尔上等九件宝,一是一口寄魂锅,二是一副霹雳甲,三是一块寄魂铁,四是一颗白璁玉,五是一块银巴扎,六是摄取花精衣,七是三对金蟾蜍,八是万物同辉金屋顶,这些也已归岭国。(注:同上,第1457页。)
其中寄魂锅的形状和功用是“四面四个铜耳环,它会带来牛福运,里面能具奶精华,外面绘有吉祥图。”(注:同上,第1457页。)
此外,还有在霍尔国,黑泰让将其灵魂寄存于黄牛以及天魔神、地魔神和空魔神的灵魂寄存在黑熊的脑中的说法。
归结起来,岭部落和其他部落的两大灵魂寄存系统中,寄魂物不外乎有以下四类:
1、自然物:山、湖、岩石、玉。
2、动物:野牛、飞禽(如鸟、乌鸦、喜鹊、猫头鹰等)、走兽(如大黑熊、野人、黄熊、红虎、豹子、苍狼等)、水生物(如鱼、蟾蜍等)、爬虫(如蛇)。
3、植物:树木(如独脚恶鬼树等)。
4、物体:帐篷、锅、宝剑、铁、箭。
灵魂寄存物丰富多样,大凡具有自然属性的实物,只要能与自身的某些特征相联系,或引申出某些象征意义,都可以用来充作灵魂寄存物。从岭部落中众多的灵魂寄存物可以看出,岭部落及格萨尔的寄魂物的选定与他们生存的地域环境和早期图腾崇拜密切相关。阿尼玛沁是当地最高大险峻的山脉,人们认为它与天最为接近,因而引起对它的宗教幻想,视其为地域保护神。同样,三湖是岭域境内最圣洁的湖泊,是生命的源泉,这些山湖本身所具有的强烈象征意义,使其被选定为部落或英雄王者的寄魂物,自然在情理之中。而大鹏、青龙和雄狮这些寄魂物,则明显地带有原始图腾崇拜的痕迹,应该是董氏长、中、幼三部落从其原始社会时期遗存下来,并演变成为灵魂寄存的神圣物。除此而外,作为世俗物品的帐房,也成为了寄魂物,大概是因为绒擦查根总管岭部落事物,他的大帐渐渐成为统治势力的象征,也即他本人的象征,从而被选定为他的灵魂寄存物。
三、灵魂寄存观构成《格萨尔》故事情节的创作主线
史诗《格萨尔》中,格萨尔消灭恶魔、伸张正义全部过程,基本上都在捣毁对方灵魂寄存处这种基本思想指导下来完成。如降服鲁赞王、降服霍尔三王、降服祝古国王的故事便是如此。
在降服鲁赞王的故事(注:《降魔篇》,《格萨尔文库》(藏文版)(第一卷),第866—867页。)中,格萨尔在搭救爱妃梅萨的过程中,弄清了降伏魔王的秘诀,即首先要捣毁他的寄魂物“拉内”。可是除了鲁赞王本人外谁也不知道他的“拉内”是什么。魔王经不住梅萨的哄骗,讲出了自己的灵魂寄居处。原来,鲁赞王的寄魂湖在黑魔谷(bdud-lung-nag-pu),寄魂山是九间铁围宫(lcags-ra-rtse-dgu),寄魂鸟是共命鸟王(bya-shing-ba-shang-shang-rgyal-po),寄魂树在森林。格萨尔乘魔王外出巡视之际,打翻了魔王仓库里的一碗獭子血,弄干了寄魂湖;用魔王仓库里的金斧子砍断了寄魂树;用玉羽金箭射死了寄魂牛。魔王顿消妖气,身上的毒蝎毒蛇也变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天神、赞神和龙神又把愚痴和沉迷降到他的身上,魔王从此便不分昼夜,处在半死半活的昏迷状态中。”最后,“格萨尔挥起红刃断尘宝剑,拦腰把老魔砍作两段”,终于制服了魔国的鲁赞王。
在降服霍尔三王的故事中,霍尔国的黑帐王、白帐王和黄帐王三兄弟,武艺高强,凶狠残暴,他们拥有雄兵百万,趁格萨尔到北方降魔之机入侵岭国,抢走了格萨尔的另一位妃子珠牡。格萨尔知道后,只身前往霍尔国。但是格萨尔根本无法取胜,只好向霍尔国的卦师请教。卦师告诉他:霍尔王的寄魂物是几头雄壮的野牛,黄野牛是黄帐王的寄魂物,白野牛是白帐王的寄魂物,黑野牛是黑帐王的寄魂物。要想降伏霍尔三王,先要把黄、白、黑三条野牛的头砍掉,而且千万不能回头。格萨尔来到雪山背后,果真看见有几头野牛,样子凶猛,很难接近,于是格萨尔变成一只大鹏金翅鸟,闪电般落在黄野牛身上,砍掉它的一只角,接着又砍掉白野牛和黑野牛的一只角。此后,白帐王、黄帐王、黑帐王都得了重病,立即请来医生诊断并向天神敬奉供品,病虽好了一些,但却不能理政。于是格萨尔趁机潜入霍尔国王宫,向卦师求得彻底降伏他们的秘法。格萨尔再次来到雪山背后,使用法术,在三头寄魂牛的头上钉了铁钉,霍尔三王果然病情加重了。霍尔三王中,白帐王最为凶悍,因为他的灵魂不仅寄托在野牛身上,还寄托在阿钦山的一株千年古树上。格萨尔又设法砍倒了寄魂树,捣毁了寄魂山。随着寄魂树轰隆一声倒下,白帐王也立刻从宝座上摔了下来。站在一旁的宠儿阿吉也摔得脑浆迸裂。(注:《降霍篇》,《格萨尔文库》(藏文版)(第一卷),第1397页。)格萨尔杀死寄魂牛,砍倒寄魂树,捣毁寄魂山,最终降伏了霍尔三王,救回了珠牡。
在降服祝古国王的故事中,祝古国国王宇杰托桂扎巴武艺非凡,13岁便继承了王位。后来岭国与祝古国之间发生了一次恶战,岭国格萨尔大王命王子扎拉孜杰率领三个邦国的兵马向祝古国发动进攻,但激战数年,未能取胜。于是,天母贡曼嘉姆向王子扎拉预言:“宇杰托桂扎巴的寄魂物有五个:一是黑熊谷中的大黑熊,二是天堡风崖上的罗刹鸟九头猫头鹰,三是罗刹命堡大峪谷的恐怖野人,四是巴玛毒海的九尾灾鱼,五是富庶林海中的独脚恶鬼树。祝古大臣的寄魂物有凶猛的黄熊与红虎、华丽的豹子、强壮的苍狼,都藏在稀奇的黄金洞里。扎拉啊!要想降伏祝古君臣,先要消灭他们的寄魂物。”王子扎拉听了以后,还是没有消灭宇杰托桂的办法,因为除了精通巫术的晁通,无人知晓他的灵魂寄存在什么地方。晁通后来得意洋洋地说出了降伏寄魂物的办法:“九头猫头鹰该由长系赛巴消灭;恐怖野人该由仲系文布消灭;九尾灾鱼该由幼系的穆姜氏消灭;独脚恶鬼树由达绒部落消灭;那宇杰托桂的第一寄魂物黑熊该由岭国君臣十人前去消灭。”晁通带领岭国君臣来到石崖下,辛巴·梅乳泽劈死苍狼,森达砍死黄熊,玉拉抽刀杀死豹子,王子扎拉杀死猛虎,女英雄阿达娜姆将“闪电火焰铁箭”搭在“山岳宝弓”上,射死黑熊。众英雄一拥而上,把大熊剥开,从黑熊的脑子里取出三块鸡蛋大的弹丸,这正是天魔神、地魔神、空魔神的灵魂寄存所在。从黑熊心脏里取出精铁的九股金刚杵,是托桂王的灵魂寄存处。从肝脏里取出的鹫鸟翅膀,是众魔臣的灵魂寄存处。与此同时,长系赛巴消灭了九头猫头鹰寄魂鸟,仲系文布消灭了寄魂独树,幼系的穆姜氏消灭了九尾灾鱼,达绒部落消灭了恐怖野人。祝古大臣等人的寄魂物毁灭后,岭军顺利地攻占了祝古兵器城,最终杀死了作恶多端的祝古王。(注:《祝古兵器宗》(藏文版)[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这样的故事,在《格萨尔》中不胜枚举。
从《格萨尔》主要篇章故事情节的展开中我们不难发现,灵魂寄存在格萨尔与诸魔王的较量过程中,成为主导故事情节的主线。而灵魂寄存的目的和作用,是保护并延续寄存者的生命。灵魂寄存物一旦被破坏,生命就将难以保全。正是在这一点上,灵魂寄存观承担起了串联若干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成就格萨尔英雄形象的基础。可见,灵魂寄存观是支撑《格萨尔》活灵活现“躯体”的脊骨。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史诗《格萨尔》中灵魂观念的归纳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灵魂寄存观念由来已久。藏族先民将自己的灵魂寄存在动物之上,是由来已久的。据藏文文献记载,古代“董、珠、扎、廓、噶”“五大氏族”就有灵魂寄存的说法。各大氏族都将灵魂寄存在动物身上。“董氏属土,灵魂托于鹿;珠氏属水,灵魂托于牦牛;扎氏属金,灵魂托于野驴;廓氏属火,灵魂托于山羊;噶氏属木,灵魂托于绵羊。这就是著名的五大氏族。”(注:南卡洛布:《藏族远古史》(藏文版)[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28页。)这种将灵魂寄存在动物身上的灵魂寄存方式,在《格萨尔》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如,董氏长、中、幼三支分别将魂寄于大鹏、青龙和雄狮身上;岭国的寄魂鸟是白仙鹤、黑乌鸦、花喜鹊。霍尔国的白帐王、黄帐白和黑帐王将自己的灵魂分别寄存在白、黄、黑三个野牛身上等等。凡此种种,都体现了藏族原始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弗雷泽的人类学名著《金枝》中,槲寄生象征着祭祀权利与生命,灵魂则寄存在了槲寄生身上。灵魂寄存是一种普遍的原始宗教思维表现,可以说它展示了远古的一种文化信息。
第二、灵魂寄存观念是塑造众多人物形象的母体。通过大量的例子我们看到,灵魂外寄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保护并延续自己的生命,使之不受外来力量的侵害。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寄魂物体应该是生命的坚强堡垒,有了它就能确保生命安全,甚至在人体的肉体死亡之后,他的生命实质还能保存下来。如果寄存物遭到破坏,也就等于其神魂受到了损伤,其生命岌岌可危。只要灵魂能得到更好的保存,关键时刻就能够发挥重大作用。因为灵魂所具有的无边法力,可以任由你去想象,尤其当身处无助和无奈的景况之下,奇迹般的最后一线希望往往就是灵魂力量登台亮相的导火索。在这样一种意识驱使下,灵魂的存在在民间文学作品中就成为与作品主要角色相生相伴的重要内容。如在战争中,消灭对方的手段往往是极为玄妙的,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与敌人交锋,而总是先要想方设法找到敌人的寄魂物体,设法将它摧毁,然后就能轻易地消灭其肉体。否则,一切努力都将徒劳无益。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格萨尔》中,基于动物崇拜的观念,无论是岭国人物系统的灵魂,还是其他部落人物的灵魂,都已经超越了将灵魂寄存在单一的动物身上的这种格局,高大的雪山,无边的湖泊,都可作为灵魂的寄存物。在反映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远古时代文化信息的史诗《格萨尔》中,更是选择巍峨宏伟的阿尼玛沁作为生活在黄河源头的岭部落和英雄格萨尔的寄魂山,浩瀚洁净的三湖作为他们的寄魂湖。正是在这种灵魂寄存的观念意识支配下,《格萨尔》中出现了极其庞杂的原始神灵体系,寄魂体系五彩缤纷,灵魂寄存形式极为复杂。
第三、灵魂寄存观念是构成曲折动人故事情节的基本元素,是成就格萨尔英雄形象的基础。通过对《格萨尔》中人物灵魂寄存现象的分析,可以认为,在史诗的观念中,作品中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他由三部分构成,即躯体、灵魂和灵魂寄存处。灵魂是躯体的精神支柱,而灵魂寄存处则是灵魂的生命存在,它具有神秘性和不可知性。所以,灵魂寄存处是生命的核心,灵魂是生命的中介,而躯体仅仅是生命的载体,一旦灵魂寄存处不存在了,灵魂就像鱼没有了水,自然躯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一个人(或动物)可以只有一个灵魂,也可以有很多个灵魂;他(它)们的灵魂可以寄存在自身,也可以寄存在别的地方。灵魂越多,生命力越强,就越不容易受到伤害。“无论是英雄或是恶魔都是这样。”(注:降边嘉措:《格萨尔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5页。)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在史诗中,既能见到天神之子格萨尔大王降服妖魔鬼怪的刀光剑影,又能领略到格萨尔捣毁恶魔灵魂寄存处的聪明机智。灵魂寄存观念在《格萨尔》中,不仅承担了塑造人物形象的母体的重要角色,而且是构成《格萨尔》创作的重要基石。
总之,《格萨尔》中的灵魂观念,有着特定的表现形式,通过灵魂观念来塑造各种人物形象;通过灵魂寄存来推动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最终引入高潮。(注:当然,除了灵魂寄存方式外,构成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因素还有灵魂搭救、灵魂超度等,容他文论述,此不赘述。)灵魂观念在《格萨尔》中,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而且构成其主要艺术角色的塑造机缘,因而灵魂寄存观念无疑是英雄史诗《格萨尔》创作的重要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