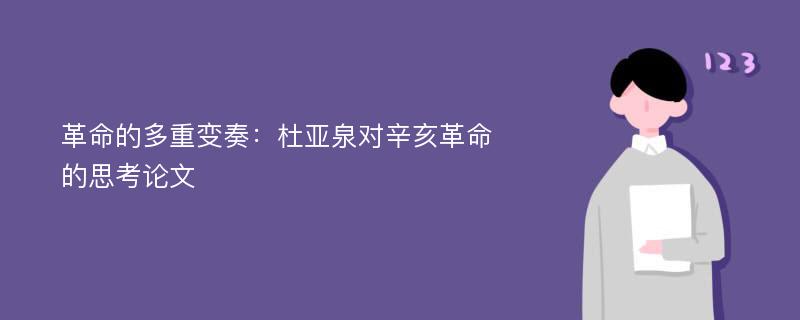
革命的多重变奏:杜亚泉对辛亥革命的思考
颜德如
(东北大学,辽宁 沈阳 101169)
摘 要: 杜亚泉是一位思想史中的边缘人物,他对辛亥革命做过许多新颖而深刻的思索。在他的思想中,辛亥革命呈现出多重变奏的面貌:它从“政治革命”异化为“帝王革命”;它是清廷失政与专政孕育的革命;它是以民主立宪为最终目的的革命;它是“物质主义之革命”;它是“思想战”的爆发;它是开局有功、建设不足的革命。这些洞见充分揭示了辛亥革命复杂深邃的内涵,这说明,对辛亥革命,是不能以一种符号化的语言加以教条式理解的。
关键词: 革命;杜亚泉;辛亥革命
目前,学界对辛亥革命已经作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但考察近代政治人物或思想人物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以审视革命的研究尚不多见,考察近代思想史中边缘人物对辛亥革命的思考以省察革命的研究则几乎付诸阙如。尤其是杜亚泉这样思想深刻又在当时颇有影响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几乎被历史遗忘了的思想人物,他对革命的体认应该能够给我们带来许多焕然一新的思索。一方面,杜亚泉经历了整个辛亥革命的时代,亲身体验到了当时的世道人心,能够获得关于革命的最直接的资料,他对革命的认识无疑要比当代人更加真切。另一方面,杜亚泉并非革命党人,亦不属于当时的任何政治派别,他一直以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观察政治社会问题,较少受到政治局势和政治见解的影响,相对超脱的身份使他的思考可能比处于政治漩涡的“局中人”更加客观理性。还有一点需要强调,杜亚泉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具有文理兼备、中西兼具的知识背景的思想人物,全面的知识结构使他的观点往往富有学理的深度。那么,在他的思想中,辛亥革命到底是怎样的?它是否仅仅只是一场暴烈性的国内变革运动?作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点,辛亥革命究竟呈现出怎样多重变奏的面貌?杜亚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为我们展现了一副全新的辛亥革命图景。
一、辛亥革命从“政治革命”异化为“帝王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杜亚泉即撰文热烈欢迎革命并讨论了革命的种种问题。他在1911年11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的《革命战争》一文中认为,人类战争根据其发生的原因可以分为人种战争、宗教战争、经济战争和政治战争四类,政治战争可分为外战和内战,内战又分为近于外战者和纯为内战者两种,后者即是革命战争,因此,革命战争属于政治战争一类。[1]57从后文可见,政治战争也就是政治革命。他认为辛亥革命迥异于中国历来的改朝换代,革命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欧美之政治思想输入以来,久苦于专制之国民,乃勃起而欢迎之,革命之声,渐流布于薄海内外,而革命之意义,亦大变其本来,几若专为推翻专制政府改建立宪共和政体之标志”,并认为自此之后,“我中国革命战争之兴起,不可不以转移统治权为目的。若复有觊觎王位专窃政权之举,则固为我国民族之所决不能容者也”。[1]58稍加分析,不难发现,杜亚泉的言论具有四层含义:首先,揭示了革命的原因,乃是欧美政治思想的输入和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其次,显示出他对辛亥革命的热烈欢迎并对之抱有极大希望;再次,表明他认识到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政治革命的嚆矢;最后,也隐隐透露出其对辛亥革命可能失败的忧虑。后三个方面的含义从该篇文章的结尾部分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来:一是革命是“政治革命”,即“非种族革命,是无人种战争之意味”;二是革命“主张人道”,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是无劫夺捕掳之行为”;三是革命“建设民国”,即“创立共和政体,是无争夺统治权之性质”。他热情洋溢地赞颂革命,认为辛亥革命“实为我革命民族中一种之异彩”。但同时告诫要警惕革命变质,“我国民今日所当兢兢注意者,即有维持此主义,不使稍有所动摇,以免他主义之阑入。盖战争一起,兵连祸结,其结果往往不可豫料,非赖国民之精神毅力以贯澈之,则转移统治权之战争,或一变而为争夺统治权之战争,若觊觎王位(如法国大革命后之拿破仑)竞争总统之类。又或由革命战争转化而为独立战争,由独立战争激荡而为霸权战争,驯至以内战而引起外战。是皆不可不思患而豫防者。至以满族之歧异而酿成人种战争,因生活之困难而迫为经济战争,主义一淆,即为我革命民族之污点”。[1]59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各界普遍对革命前途充满乐观情绪,连孙中山都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今后中国当致力于社会革命,而且“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2]但杜亚泉并没有盲目乐观,他已经开始理性地剖析革命的理路并关注革命的未来。
随着辛亥革命后一系列政治社会乱象的凸显,杜亚泉对革命的看法逐渐发生改变。在1919年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中,杜亚泉提出了“文化发展三期说”,认为人类文化的进化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贵族阶级和智识阶级结合为支配阶级,形成贵族阶级的文化;第二阶段,财产阶级和智识阶级结合为支配阶级,形成财产阶级的文化;第三阶段,劳动阶级和智识阶级结合为支配阶级,形成劳动阶级的文化。第一期文化向第二期文化过渡为政治革命,第二期文化向第三期文化过渡为社会革命。同时,他认为近世欧洲处于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国则仍然处于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辛亥革命以后,吾人方窃窃私幸,以为第二期文化从此成就矣。乃八年以来祸乱相寻,吾人平心静气以观察之,方知吾国此时非第二期文化之进行,而为第一期文化之堕落”。[1]489-491既然中国目前为第一期文化的堕落,那么中国社会就仍然处于以贵族阶级为代表的旧势力的控制之下,财产阶级和智识阶级并没有成为中国的支配阶级。换句话说,革命后与革命前的政权性质和社会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他甚至认为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异化为“帝王革命”,“辛亥革命,虽由欧洲第二期文化传播于吾国而起,然欧洲之政治革命,既由财产阶级发生,而吾国之财产阶级,大都不解立宪共和为何物,初未尝与闻其事,提倡之者为过剩的智识阶级中之一部分,加入者为过剩的劳动阶级中之兵,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异。其模拟欧洲之政治革命者,不过中华民国之名称,及若存亡之数章《约法》而已。革命以后,名义上不能建设贵族政治,实际上握政权之官僚或武人,大率为游民首领之贵族化者”。[1]492此时的他已经洞见到: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并没有真正成为革命发动的领导力量,革命之后政权被官僚和武人所把持,中国社会依然没有从旧势力的桎梏之中解放出来。简单地说,作为政治革命的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即打上了“帝王革命”的烙印。需要澄清的是,他所谓的帝王革命并不等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汤武革命”,他意在借“帝王革命”一词强调,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并没有真正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革命后封建主义披上各种现代形式的外衣继续活跃于政治社会之中。
其中,cθi为转角阻尼系数(单位:gcms/rad),cαi为间隙角阻尼系数(单位:gcms/rad),csi为线位移阻尼系数(单位:Ns2/cm).线位移阻尼系数csi相对cθi和cαi较小,在计算中可以忽略.上述方程可以化为:
二、辛亥革命为清廷失政与专政孕育的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革命志士等新势力不屈不挠奋斗的结果,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在杜亚泉的思想中,他更加注意探讨清廷本身与革命的关系,正如托克维尔在论述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时所言,“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3]245-246杜亚泉认为清王朝在以下几个方面孕育了革命:其一,大借外债实是清王朝的自我摧毁,“近一二年中,有主张大借外债,以整理币制、兴办实业及筑全国之干路者,舆论抗之。清政府之颠覆,未始不由于此”。[1]63关于政府依赖外债的危害,杜亚泉在《论依赖外债之误国》中作了专门的讨论,他认为政府大举借债,政费增加了,政府机构跟着膨胀,机构膨胀的后果是政治愈加腐败,社会风气败坏。对于国家的将来而言,依赖外债不仅加重人民负担,损害国家主权,更加关键的是使政府形成依赖之性。因此,“外债如醇酒,如雅[鸦]片,饮之吸之,非不足以助人血气增人神志,然其后则不复可离,乃沉湎憔悴以终其身焉”。[1]81-82其二,清季新政催化了革命,“清廷之预备立宪,民党之鼓吹革命,互相激荡,遂有共和民国之创立”。[1]187其三,清政府内部的派别倾轧,权力斗争加速了革命,“有清之失其政权,岂真革命党之力?亦以其时,有权者之间,树党相敌,排挤倾陷,已达极度,革命党加之,遂为所乘耳”。[1]238其四,辛亥革命体现了国家本能的作用,“辛亥革命运动之成功,与夫此次帝政运动之消灭,虽曰民意,而事态之变迁与时机之辐辏,均有人力不至于此之感。是皆国家之本能作用,有以致此也。国家本能之性质,亦与个人之本能无殊。一为普遍的,即发于国民内各个人心理上之直觉;一为非机械的,即其作用奇妙不可思议,而非武力智巧及其他之机械力所能及。大都普通之意义所谓国命、国运、国脉者,即指此本能而言”。[1]298究竟何为国命,何为国运?杜亚泉的言语有些含糊,我们还可从他之前一篇谈命运的文章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认为国家兴亡,民族盛衰,都有命运存于其间,这是由于“热带之民,智力常逊于温带。南方之民,体格常不及北方。版图辽阔之国,团结力多弱。永久孤立之国,战斗力必衰。若是者,命也”,“前清之季,西力东渐,日本乘机变法,而我国因循延误,日即危亡者,由于西太后当国,握政权至五十年之久。若是者,运也”。[1]250-251显然,“命”是不可改变的,“运”虽然可以改变,却掌握在旧的统治集团手中,而旧势力不合时宜也不思改变,其衰朽是一定的。在之前的《中华民国之前途》一文中,他曾集中总结了革命发生的原因:“总之,此次清廷之革命,其本因有二:一为远因。则以满人专有政治上之特权,种族间生不平之观念。一为近因。则由于世运变迁,专制政体不适于时世。而其助因有三:一为中央集权,二为大借外债,三则财政紊乱,政费浩大,税目繁杂”。[1]65在《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一书中,他亦专门探讨了革命爆发的原因,内容大同小异,“十年以来,革命思想之所以传播甚广而成功甚速者,推其原因,以迫于时势之要求为主。而其助因有二:一为远因,一为近因,远因者,满人之专政是也。近因者,西太后之失政是也”。[4]4由此可见,除了时势所迫之外,清廷在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和经济上的软弱无能成为革命最重要的诱因。
三、辛亥革命不外“民主立宪”之革命
(4)摊铺。基层摊铺前应将结合面清扫洁净,并适当洒水,使结合面保持湿润,以提高层间结合效果。运料车应倒车至摊铺机前0.1~0.3m处停车等候,严禁撞击摊铺机,摊铺机推动自卸汽车一同前进摊铺,开启螺旋布料器进行布料摊铺。摊铺速度应控制在4~5/min,摊铺机后应安排专员检测摊铺质量,同时进行辅助摊铺,对局部离析进行相应修整。
在1917年的《豫言与暗示》一文中,杜亚泉认为,“革命运动之成功也,以十八、九世纪之欧美历史,凡民党与君主贵族抗争者,皆著著制胜。有血气之青年,受此历史之暗示,欲取而演之于吾国,深信其必获最后之胜利,故屡蹶屡起,愈演愈剧。清室之君若臣,亦受此历史之暗示,深信革命之必不能免。平日既动色相戒,武昌起义以后,遂手足无措,甚至拥重兵之将帅受制于数十党人之手。一般国民,亦受此历史之暗示,深信民党之必能成事,故闻风响应,唯恐或后”。[1]236杜亚泉意在证明预言与暗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出,虽然人权自由等观念只是少数革命精英怀抱的理想,由于辛亥革命得到了广大国民的积极响应,以至于全社会都被卷入到革命之中。
四、辛亥革命主要是“物质主义之革命”
其实,早在1912年,杜亚泉就已经部分意识到这一点,在《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一文中,他认为我国国民是“现实的国民”,国民重视事实而轻忽事实后面的原理,此种国民心理使得我国本有的民主立宪原理在历代君主专制政体之下消散于无形之中,我国传统社会的革命不过是简单的改朝换代,“国民政治上之思想,数千年绝无改革”。[1]98而辛亥革命依然没有完全挣脱此种藩篱,“至此次革命,固以原理为动机,然特少数之先觉者怀抱此理想耳。就大多数国民之心理观之,则共和政体之发生,仍依据于事实,而非根本于原理”。[1]98具体而言,“吾国民对于共和政体之观念,乃歆于事实上之所谓利,非动于原理上之所谓是也。盖我国既惩于甲午、庚子以来之失败,又受日俄战役之激刺,就事实上之比较,知专制之终于覆国,立宪之可以兴邦,又以他国以往之事实推测之,则立宪政体之成立,非革命流血不为功。故武汉发难,全国相应。我国民之推翻专制创立共和者,固欲于事实上维持国家之势力,非欲于原理上主张天赋之人权”。[1]98-99从中可见,在辛亥革命中,天赋人权只是少数人的理想,多数人仍然视革命为事实上的政权转移而已。以民主立宪为最终目的的辛亥革命,其前途如何,从上文已可窥一二了。
杜亚泉在《精神救国论》中指出,19世纪后半期风靡欧美流行世界的为一种危险至极的“唯物主义”,该学说输入我国,初为富强论,继为天演论。[1]145那么,何谓“唯物主义”?“以孔德之试验论启其绪,以达尔文之动物进化论植其基,以斯宾塞之哲学论总其成,唯物论哲学,昌明于世,物质主义之潮流,乃弥漫于全欧,而浸润于世界矣。”杜亚泉接着简要介绍了孔德的实验论和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1]146-147他明确指出,时人对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每多谬解”,“其谬解达氏之说者,往往视进化论为弱肉强食主义之异名,乃主张强者之权利,怂恿弱者之死灭,于人类社会道德,置之不顾”,“至斯氏之学说,世或以为主张社会为有机体,专以生活的有机体之状态与社会之状态相比较,为达氏进化论之后劲,其重视生存竞争自然淘汰之理,与达氏大同小异”。总之,“世俗流传,仅窥二氏学说之半面,专以生存竞争为二氏学说之标帜”,[1]147-148他把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简单化地“谬解”为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非道德主义理论。杜亚泉进而指出,通海以来自西洋输入我国的都是唯物主义学说,李鸿章等提倡的富国强兵论导致甲午之辱,自此后变法之议兴,维新守旧争持不下,此时唯物主义中的天演论在社会中最具势力,由唯物主义产出的法律学同时由日本输出,而作为唯心主义的民权自由说也由民间志士鼓吹于国民之间。唯心唯物二大思潮,“磅礴郁结,而成我国前年之革命”。然而,“此伟大革命事业,果为唯心论所产出乎?抑为唯物论所产出乎?以记者之所见言之,则唯心论的革命,仅主动者之少数而已,大多数之赞成革命,实由唯物主义而来”。[1]149可见,作为唯心主义的民权自由只是少数人怀抱的理想,大多数人仍秉持“唯物主义”的理念。如此说来,辛亥革命和洋务运动都是“唯物主义”推动的变革运动,它们具有一脉相承的一面。杜亚泉鲜明地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生存竞争学说已经成为社会上不可动摇的定律,辛亥革命实为各阶级各阶层竞争权力的产物,革命已变成“饭碗革命”,革命成果已经被金钱利欲的物质势力所腐蚀,“革命之兴,其表面之标帜,为汉人与满族之竞争,其潜伏之势力,为官僚与亲贵之竞争,而一般之现象,则为攘夺权利者与占有权利者之竞争。故饭碗革命之新名词,在当时已哄传于道路。革命成功以后,一切外交、军事、政治、法律、殆无不可以金钱关系概之。物质势力之昂进,已达于极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物质主义之革命,其结果正当如是”。[1]150可见,辛亥革命自始至终被笼罩在生存竞争学说,或者说被“谬解”了的“唯物主义”的巨大阴影之中,生存竞争学说成为革命中最具有势力的理念,而民权自由等现代性价值只是少数人的理想。
光线调节系统是光学显微镜的基本结构,但也最容易被忽略,而光线的强弱在观察显微镜下标本时非常重要。普通光学显微镜的调光装置包括光源、集光器和光圈[3]。在观察标本时,并非光线越亮越好。如果视野范围内的光线太强太亮,会造成所观察的标本各部位的亮度低反差,导致有些结构模糊不清。如观察蛔虫卵形态结构时,若视野范围太亮,则只能观察到虫卵的大体形态,而卵壳内部结构就非常模糊。若把亮度调整至明暗适中,就可以看到清晰的蛋白质膜和新月形空隙。另外,视野光线太强还容易刺激学生眼睛造成视疲劳。
五、辛亥革命实乃“思想战爆发”
阿伦特说过:“在暴力领域之外,战争和革命甚至是无法想象的。”[5]7-8革命和暴力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翻阅杜亚泉的著作,他从未专门讨论过暴力在革命中的作用,但我们是否可以据此断定,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暴力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或者说,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辛亥革命同样也是一场暴力催生的革命?答案是否定的。他在《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中对革命志士的历次起义作了详尽的描述,从“十年以前之革命运动”,“甲辰丙午间之革命运动”,“丁未戊申之革命运动”,“宣统时代之革命运动”,直至“川省之激变”,“武昌之举兵”,“各省之响应”,“武汉间之战事”,“南京战事”,“民国之成立”。[4]7-22如果说他对其中的暴力因素没有认识,没有看到暴力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话,是不可能的。要之,尽管他没有明确强调暴力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但在其思想之中,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暴力催生的革命是确定无疑的。至于为何在对革命的讨论中没有给暴力留下更多的空间,前已述及,他极其留意思想对于革命的作用。相形之下,暴力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如思想重要的。也有可能,在他眼中,革命中的暴力因素是众所周知而无需赘言的。他在《真共和不能以武力求之论》中的一句话应该也可以给我们一些解释,“考之历史,则武力可以倒专制,而不可以得共和”。[1]396这意味着革命之后,暴力已经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在建设共和时期,过多地讨论暴力是无益于现实也是不合时宜的。由此可见,他并不仅仅是为了讨论革命而讨论革命,对革命的讨论是具有极强的现实关怀的。
杜亚泉在革命爆发翌年的一篇论文中,认为“我国革命之成功,虽不及葡萄牙之神速,然决非其他诸国所能比拟。自是以后,四千年来酝酿之文明,三百年来潜伏之民气,皆得乘时发抒,为东亚细亚方面开尹古未有之创局”。[1]61此时的他是热情歌颂革命的,认为革命使中国近代以来压抑屈辱的民族情感得以抒发,开创了中国乃至东亚历史的新局面。在革命两年后出版的《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中,他认为,“五千年来专制帝王之局,于此十年中为一大结束;今后亿万斯年之中华民国,乃于此时开幕。则非十年以来之小变,实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而不可以常例论矣”,“且此十年内之变局,不特在吾国历史中,为上下古今时势转移之枢纽;即在世界历史中,亦为东西两洋文化交通之关键”。[4]1在他看来,辛亥革命至少有两大功绩:从纵向看,它结束了中国五千年的专制帝制;从横向看,它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前一点是老生常谈,后一点却是新颖之论。但如果就此就说他认为辛亥革命已经完全成功了,那无疑歪曲了他 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事实上,一场成功的革命远远不止于此,正如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言,“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之制度化的阶段。成功的革命把迅速的政治动员和迅速的政治制度化结合起来”,[6]221-222“衡量一场革命成功到什么程度,则应看其所产生的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6]222随着局势的变化,杜亚泉对革命的失望之情日益增加,对革命已经失败的认识也逐渐树立,“吾人曩日倡言变法,希望立宪,赞成革命,欲借政治以挽回痼疾,施治者三次。而社会之病势,乃有增而无退”。[1]126他指出:“今之谈时事者,辄咨嗟太息曰:民国成立,倏已岁余,而内治之纷乱如是,财政之竭蹶如是,外交之危迫如是,长此终古,吾国将不足以自存。”[1]139民国成立三年,“徒拥共和之名,未举立宪之实”,[1]188“辛亥革命,丙辰靖国,用积极手段,虽达几分目的,然其结果徒增长武人之势力,扩张党派之私利,亦无实效可言”。[1]504从他的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之后,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依然阙如,对革命的消极看法亦逐渐成为社会共识。辛亥革命既没有完成救亡图存的任务也没有完成民主立宪的任务。辛亥革命虽然开局有功,但建设不足,革命确实失败了。
杜亚泉在1912年4月发表的《中华民国之前途》一文中,同意历史家将革命比作医生给病人施加手术的譬喻,“吾闻历史家论革命之性质也,曰国家政治上之革命,犹之于吾人身体上施外科之大手术也。盖吾人既罹重大之疾病,渐成慢性之痼疾,终非姑息之疗治所得愈,则不得不行根本上解除之大手术”。[1]60他认为,“吾中华民国,当此新施手术之后,其经过幸而良好”。[1]60既然革命犹如医生给病人施加手术,那么革命的目的则是去除国家民族的病变之处,使之重新焕发生机。换言之,“今日革命之目的,在救亡不在启衅”。[1]60庚子事变之后,中华民族陷入列强瓜分的危机之中,救亡压倒了一切,辛亥革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理所当然地以挽救中华危亡为鹄的。问题是,一场革命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救亡。阿伦特认为:“革命的目的是自由,它其实就是布莱克顿所称的‘构建自由’——以自由立国”,[5]138而“在现代条件下,立国就是立宪”。[5]108在《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原名《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一书中,杜亚泉在《通论》的第二篇《立宪运动之进行》中认为,“我中国十年以来之政治,自一方面观之,为革命运动之进行,自一方面观之,则又立宪运动之进行也。以立宪之进行言,则第一期为君主立宪之发动时期,第二期为君主立宪之预备时期,第三期则民主立宪之确定时期也”。然而,“民国创立,百务未遑,临时措置,亦难求备。今后之进行,我国民正宜努力,盖革命之伟业虽成,而立宪之前途尚远焉”。[4]23这些论述包含了多方面的信息:第一,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是并行不悖的,它们是中国近代两条平行变动的曲线。杜亚泉并没有一般地将辛亥革命和清末立宪对立起来,甚至认为革命与立宪是殊途同归的,“茫茫政海中,固有二大潮流,荥洄澎湃于其间。此二大潮流者,其一为革命运动,其一为立宪运动。革命运动者,改君主国为民主国;立宪运动者,变独裁制为代议制。其始途径颇殊,一则为激烈之主张,一则为温和之进步;及其成功,则殊途同归”。[4]2其二,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清末立宪事业的继续,因为既然将“君主立宪之发动时期”、“君主立宪之预备时期”和“民主立宪之确定时期”分别作为立宪的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那么作为第三期的民主立宪自然是第一、二期君主立宪的继续。其三,清季新政追求立宪,辛亥革命亦追求立宪,然立宪远未完成。换而言之,辛亥革命肩负起了立宪的使命,目前尚未实现。杜亚泉指出:“纵观我国十年以来之历史,不外乎改革政体、实行立宪之一事。革命运动,亦无非以此为目的。”[4]32这就是说,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民主立宪。综上所述,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救亡图存的革命,更主要的是一场追求民主立宪的革命。
杜亚泉极其重视辛亥革命中的思想因素,认为思想对于辛亥革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论思想战》一文中,他正式提出了“思想战”的概念,认为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战争的起因也由事实移入思想,在文明时代,战争的爆发是基于不同思想的冲突。[1]212-216在他看来,战争的起因依据人类进化的程序可分为三级,开始是争得失的事实战,接着是争利害,它既是事实战又是思想战,最后是争是非的思想战。得失之争可以由武力解决,战争结果,胜败分明,得失问题因此确定;对于利害之争,虽然可以由武力解决,但在武力之外,还牵涉到其它关系,所以战争的结果不能遽下结论;而是非之争则与武力毫无关系,战争胜利的一方未必是,战争失败的一方也未必非,战争的效率对于是非问题毫无价值。[1]213-214简言之,武力可以解决得失之争,部分解决利害之争,但不能解决是非之争。他进而认为辛亥革命导源于欧美思想的输入,属于思想战的范畴,“十九世纪民族思想之发达,意大利合并,巴尔干分裂,其他民族战争之爆发于各地者,更不知凡几。此回旋澎湃之思潮,更由太平洋、印度洋远渡亚东,波及吾国,而有辛亥之役。吾国之思想战,盖以此为著矣”。[1]214-215由于欧美思想传入中国,冲击我国固有思想,造成守旧、维新两派思想的激烈冲突,“辛亥一役,思想战爆发,民国由是而成立”。[1]215“辛亥革命,即戊戌以来极端守旧思想之反动。”[1]216辛亥革命既为思想战,表明革命造肇因于思想的冲突,因而暴力并不能在革命中担任主角,它不能解决其时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是非问题,而革命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也难以骤下定论。
六、辛亥革命可谓开局有功、建设不足的革命
对于思想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在《战争与文学》一文中,杜亚泉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他在考察了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后得出结论:“近世战争与文学之关系,其范围益广,不但以战争为文学上之材料,且以文学为战争中之器具。”[1]229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学著作及革命党人的文章为辛亥革命的发动播下了种子并推动革命取得成功,“我国辛亥之革命,亦于文学种其因,远之如宋明两代所流传孤臣遗老悲愤忧愁之著作,近之则新闻杂志所揭载党人志士激昂慷慨之文章,皆足以震撼人心,发扬民气,故革命军一起,不数月而蔓延全国焉。且革命之成功,文学上之功绩,亦多于战场上之功绩。当时一论文之发布,一电报之传播,举国震惊,较五千杆毛瑟枪为尤烈。世之论者,或称之谓新闻战略。可知辛亥之役,不但于文学上种其因,亦于文学上收其果焉”。[1]229对于杜亚泉所言,我们可以征引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一句话予以概括:“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3]182
杜亚泉对革命伤心失望之余,并没有消极沉沦,而是积极反思革命失败的原因。这些反思,在今天看来仍不乏睿见。第一,革命队伍渗入了大量腐朽的旧势力,他们蚕食了革命的果实,掌握了革命后的新政权,辛亥革命实际上是“旧人行新政”,新瓶装旧酒。“于是帝政末叶之官僚,一变为共和开幕之官僚;臣服一姓之官僚,一变而为国民公仆之官僚。究之人犹是人,官犹是官,即政治亦犹是政治,其所改革者,位阶职位之名称,薄书文告之程式,而其所不可改革者,即为官吏之个人”,“落拓不检之书生,庸懦无能之官吏,以至乡里豪强,江湖枭贩,一投入革命党旗帜之下,悉为共和缔造之伟人”。[1]176易言之,“辛亥之革命,亦尤非利用旧势力之甲部,以排除旧势力之乙部,冀达其调整之目的而已”。[1]442对于他的判断,我们如果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它们其实还隐含着一层意思,那就是不论是革命前还是革命后,广大的普通国民都没有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缺乏真实的群众基础。第二,革命者急功近利,不懂循序渐进,造成革命运动无根基无经验无条理。“夫吾人曩者,固尝屡用积极矣,初则要求立宪,继则创建共和,积极之精神,诚有不可一世之概。迨政体改变而后,全社会之思想之言论之行动,更觉发扬蹈厉,锐进无前,宜若可以致治而图强矣。乃所得之效果,不能入其所期,转演成俶扰纷沓而莫可救正者,此何故欤?则以积极而无根柢无经验无条理无轨途,故棼乱至于此极也。夫以如此不规则之积极,就令进行无阻,亦岂国家之福?”[1]183第三,辛亥革命是速成的革命,革命势力极不牢固,封建专制的污毒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继续盘踞于新制度之中,与新的体制格格不入。“自辛秋起义,不及半年,共和聿成,民国统一,以极短时间,成极大事业,不特中国所未有,抑亦先进之所无。夫成熟易者果实不良,代价廉者物品必劣,此自然之理也。吾国专制之毒,入人已深,一旦易名共和,而形成共和国家之内部分子,未尝受相当之磨折,俾与国体同化,则其杌陧凿枘,因不体合而生种种冲突,亦固其所。犹疮疡然,不清内蕴之毒,徒施表面手术以求愈合,其不酝酿而再溃者几何。”[4]202第四,革命后各种政治势力及同一政治势力不同派别之间(当然也包括革命党)认识不一致,行动不统一,互相攻讦,不懂妥协调和为何物。“辛任以还,全国政争纷纭俶扰,保守进取,各不相谋,激烈和平,互持一义,亦既极离奇变幻之致矣,然犹得谓政见不同,不妨各行其是也。然而同一政见之中,亦复参差百出。甲主协进,而乙独孤行;丙欲南辕,而丁乃北辙。军人各逞血气之勇,国会滥行弹劾之权,能发而不能收,知张而不知弛。凡此皆革命后所屡见欲讳之而无可讳之也。”[1]293他所说的问题,孙中山也有类似的反思。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认为,十三年来革命主义没有实行,革命还没有成功的最大原因是革命党人的奋斗“各自为战,没有集合,没有纪律”。[7]96因此,他要求“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步骤,象这样做去,才可以成功”。[7]98可见,孙中山强调的是革命队伍内部思想与行动的不统一,相较而言,杜亚泉的视角更加宏观,他的观点已经包括了孙的观点。第五,革命之后没有积极发展实业与教育,巩固共和国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文化基础。他认为真共和只能通过实业与教育才能够得到,“真共和之成立,不外二因:一为国内农工商业之发达,二为国民教育之普及。盖必国民之产业既丰,智德既备,能力充足,不至为少数有力者之所左右,共和之基础始不可动摇”。因而,“第实业不发达,教育未普及以前,仅仅依赖武力以获得者,其结果当不过如斯耳”。[1]395-396简言之,辛亥革命以武力改变了国家的政治机构,却没有以实业和教育改变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国民观念结构。
不仅缺乏具有乡村旅游开发经验的专业人才,也缺少葫芦雕刻工艺方面的大师级人物,且雕刻艺人多为中老年人,存在较为严重的人才断层现象。
七、余 论
自1840年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苦难深重的近代历程。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但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中越陷越深。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转折点,正如杜亚泉认为的那样,作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它结束了中国的千年帝制,抒发了压抑屈辱的民族感情,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开启了中国乃至东亚历史的新时代,这些都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但革命的成功之处并不能掩盖革命已经失败的事实。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杜亚泉看来,辛亥革命具有复杂深邃的内涵,呈现出多重变奏的面貌。辛亥革命为何会有这样的特点?原因是复杂的,包括革命的特殊时代背景,独特的国内国际环境,西学对革命的影响,革命对中国传统资源的路径依赖等等。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衍生,就会发现,杜亚泉对革命的这些思索不仅别开生面,而且具有不少真知灼见。革命的这种多重变奏对革命后整个中国政治社会的演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革命后诸多的政治社会现象都可以在辛亥革命的这种多重变奏中得到合理的解释,甚至只有在革命的这种多重变奏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辛亥革命不仅仅是“政治革命”,同时也带有“帝王革命”的烙印,使得革命后中国社会依然处于传统势力的支配之下,甚至出现多次复古逆流,其后,封建残余仍然像幽灵一样萦绕在中国社会之中。辛亥革命不仅仅是革命势力造就的革命,更是清廷失政与专政孕育的革命,这提示我们,革命的原因不仅存在于发动革命的新势力之中,也存在于旧的统治集团之中。辛亥革命不仅仅致力于救亡图存,更主要的是追求民主立宪,正是如此,辛亥革命才突破了近代中国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具有了超越的价值。辛亥革命主要是“物质主义之革命”,生存竞争学说是革命中最具势力的理念,自由人权等现代性价值自始至终只是少数革命精英怀抱的理想,故此,国人虽然受到了一次革命的洗礼,但现代自由民主观念并没有深入中国普通大众的心中,各种传统势力总能在中国社会找到生存的土壤。这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重大课题,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的现代化,根本的是人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正如阿尔蒙德所提出的观点,制度建设必须建基于公民文化才会有持久的活力。[8]辛亥革命是“思想战”的爆发,思想在革命中展示出巨大的力量,思想对于辛亥革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革命的这一特点也成为此后中国历次政治社会变动中的典型范式,革命后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更大规模的以思想为武器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视为辛亥革命的余绪。可以说,辛亥后的中国,思想成为社会变迁最重要的推动力,谁掌握了思想(而不仅仅是暴力),谁就掌握了社会动员的能力,谁就掌握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职是之故,思想建设对于近代中国尤为重要,尤其要警惕激进思想(可能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与民粹主义的结合。辛亥革命开局有功,但它建设不足,终究失败了,但它为今后中国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后来的国民大革命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可以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共产党人是不可能在短短28年的时间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的。毛泽东曾经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9]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仍然继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它早已经融入到中国社会的血脉之中。梁启超认为:“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10]以此而论,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场以一点一滴的改革为路径的革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质的飞跃。阿伦特在50多年前说:“革命乃是我们之前的时代深藏不露的主旋律。”[5]239总之,多角度地充实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正确利用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包括它的影响,它的经验教训,它的精神,在现代化的征途上不断前进,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任务。
从表1可知,风机盘管的风量和房间的温湿度以及系统冷水总流量是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102房间的总新风量为361m3/h,和该房间设计要求为1200m3/h的新风量相差较大,102所在的一层空调房间的面积约800m2,但是设计上只安装一台额定风量为2000m3/h新风机组,明显不符合人员密度新风标准的设计要求。新风系统对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有很大作用,但是没有引起建筑各方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319.
[3]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 杜亚泉,等.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 (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6]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美)阿尔蒙德,(美)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9]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4.
[10] 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4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16ZDA104)。
作者简介: 颜德如,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06-056-063
[责任编辑:翟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