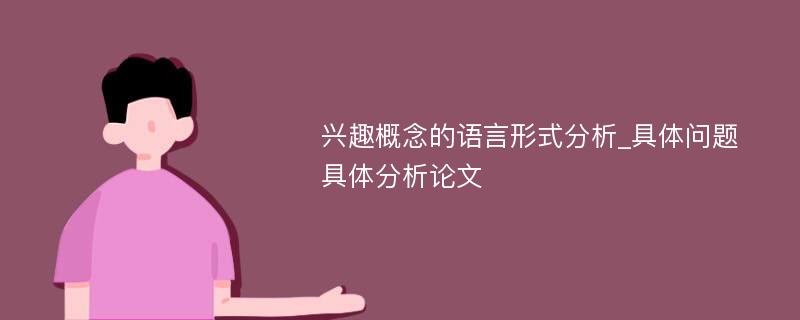
利益概念的语言形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益论文,形式论文,概念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H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7)01-0039-06
一、导言
在分析利益概念的过程中,只有将可能性在源头上从分析者的角度开放出来,才能使从分析者到分析利益概念的方法、利益概念的语言形式和利益概念内容的存在表象等诸环节中保持开放性。作为一种途径,分析具体个人的内在可能性,将所得到的分析结果作为利益概念的内容在方法上是必须考察的。但是,这种考察所揭示出来的内在整体性,包括非理性的秩序可能性、不可全知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理性参与到非理性的多种模式,使通过这一途径通达利益概念的语言形式不再可能。因此,从外在可能性的途径来获得利益概念的语言形式就变得重要起来。也就是说,利益概念不能从分析者对于具体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分析中来,只能从分析者对具体个人的存在现象进行外在观察中来。然而,从外在方面来说,分析者分析具体个人的存在现象同样面临着整体性的问题。
“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清楚的事情,就应该沉默。”[1] 20在保留以上两个方面的整体性的同时,能否直接进行利益概念的语言形式分析呢?这就意味着,分析利益概念的出发点不再着眼于有关利益的事实,而是将它保留为分析事实之前的某种视角、某种特定的眼光,保留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概念。分析利益概念语言要素的目的,不仅在于从认识上提炼出语言要素,而且还在于澄清能够作为其构成性语素的逻辑关系。
二、利益与利益概念
在中国政治学中,运用利益分析来解释政治现象已经成为主流理论。那些没有运用这种理论的学者也很少见到反驳它。李景鹏和王浦劬是利益政治学的两位重要学者,他们几乎与奥本海默、本迪特等西方学者同时提出了较为类似的有关利益的观点。80年代初,李景鹏就运用利益分析来解释改革开放早期的政治现象。他在总结自己的利益和权力思想时认为,“利益结构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一种转化功能,可以将人们外部的各种关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关系)转化为人们的内在要求,然后再通过利益结构的外在形式而表现出来。所以,它是以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的内在要求。”[2] 7王浦劬在《政治学基础》一书中提出了利益的四个内在矛盾,它们是:(1)自我实现要求与社会实现途径的矛盾;(2)形式主观性和内容客观性的矛盾;(3)目标性与手段性的矛盾;(4)具体有限性与发展无限性的矛盾。[3] 49-51显然,两位研究者都意识到了探索利益概念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诸多深刻的哲学问题,因此,在处理利益概念的过程中,他们都保持了足够的审慎。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短暂几年中,我国哲学领域曾经密集地出版了许多有关利益的著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王伟光等学者。这一时期的著作所采用的方法大致上是对经典著作进行检索,并将其归纳为某种利益理论。其间,将经典著作中提到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西方思想家作为利益概念的鼻祖,而未对利益概念在西方知识史中的源流进行更广泛的研究[4] 21-26,104。由于缺乏对利益概念的深刻讨论,同时又急于建构利益理论来解释现实,致使利益理论走上了泛主体的理性主义道路,在修辞学中称为拟人化。基于利益的分析方法长期阙如,直接导致了这种理论在近15年里踌躇不前。
利益概念关乎利益分析方法建构的基础性问题,分析利益概念不仅涉及语言学的诸多领域,而且也和哲学逻辑紧密相连。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利益概念的分析是分析哲学和哲学语义学的任务,是语言和逻辑两类方法的运用。从语言角度来讲,一方面,从利益的日常语义到概念的发展,仅仅将他人的利益概念进行归纳是值得怀疑的,归纳方法无法统一彼此对立的观点。另一方面,运用自然科学概念的“种差”方法,很难将利益概念交给一个更为广泛的种概念,中国目前多采取将利益概念作为“需要”这个概念的属类加以界定,但是这种方法未能有助于利益概念分析功能的发展。这也意味着,利益概念不再表述为偏正词组,而应当表现为句子的形式。从哲学逻辑角度来讲,首先,利益概念要的语素只有具备哲学基础性才能避免语义循环问题,那些从利益概念中能够引申出来的概念不能再出现在利益概念的句型中。其次,由于利益应用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中,不能仅用单个研究领域的语义来界定它。再者,利益概念既然表述为句子形式,那么,在该句中语素的语义以及不同语素语义的可能的逻辑关系需要得到完整的逻辑推演。当然,这样分析所得出的利益概念还需要到语境加以检验。本文将以构成利益概念的语素为标题,以这些语素的哲学语义逻辑为线索,展开对于利益概念的语言形式分析。
三、具体个人
通过对个人内在可能性的分析可以发现,具体个人内部意识要素之间的信息沟通远比分析者和具体个人之间来得透明。与具体个人相比,分析者可能会发现,他自己很难给出有关该个人的更具有确定性和必然性的描述[5]。而且,具体个人在内心独白时并不使用利益这一术语,因此利益概念就更可以卸下它本来就没必要承担的、去描述具体个人内在可能性这样的义务。
分析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许是恰当的:在特定的外部条件下,个人内在可能性当中的那些非理性和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会怎样相互作用呢?个人内心世界中的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在特定时刻和长期来看会怎样变化呢?这样的提问是值得考虑的。因为,从人生角度外在地、经验地观察具体个人,显然比直接就他的内在可能性做出断言来得审慎。从人类、历史和总体这些宏观视角出发,或许可以说,具体个人的内心当中时时刻刻都可能出现战争状态,但是,这些内在因素倾向于在集体行动问题上会变得越来越协调,这些因素大致上是向着紧密协作发展,而不是向着离散方向发展的。在“特定的外部条件”这个前提下,个人发展和变化的任意性、随机性和偏执性可能会收窄。然而,具体到某个具体个人身上,这样的判断可能是完全不成立的。
具体个人的内在要素向紧密集体行动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完全不意味着在方法上可以消除具体个人损害他人的现实可能性。在方法论上,排除这种可能性是不严肃的,但是,也不意味着任何情境中,他们都是相互伤害的。只有这样,具体个人在社会中的整体性才能得到保持。分析者对于整体性的维护,使以利益概念为基础的利益分析方法的使用者,可以在具体实践应用当中进行后续的分析工作。同时,这种整体性的保持也承认了这个具体个人是“在利益之中(in one' s interest)”的,他的出现到死亡之间(即他的人生)是由无数细微末节组建起来的,“他的利益”始终是“他的”,而不属于任何其他人的。
具体个人内在可能性问题不但本来就是由具体个人承担的,而且也应该交由具体个人来承担。对于分析者来说,这种可能不仅应该交给具体个人,而且是只能交给他。这样,分析者就可以放心地从具体个人的内部跃出来,从外部来观察具体的生存现象。从分析方法的角度来讲,将“具体个人”这个第一要素置放到利益概念的语言形式中,可以解决在分析利益概念的过程中“人是人”而非“人是人的一部分”的问题。在摆脱了分析内在可能性这一难题的基础上,对于利益概念分析就可以转向更为广阔的“利益是”的问题,即构成利益这样一个概念的其他必要语素是哪些的问题。
四、作为或者做
具体个人内在可能性的整体性阻碍了分析者从这条途径获得利益概念的内容,但是有时候,具体个人的主动性会通过行动表现出来。这种行动、作为又称为“做”,具体个人的“做”展现其内心的“有所定”。“做”虽然不过是具体个人的功能,但是对于分析者来说,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即具体个人的“有所定”是他的“何所定”的指引。
这个具有确定性的“做”成为沟通内外的环节,当然,理解它仍然需要费些周折。首先,这个“做”原始地就是“自然的做”,然后才是“社会的做”。“自然的做”要被理解为那些基础行为,而不是那些由诸多基础行为构成的复杂环节的概括。如,“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这个“建立”本身不是基础行为,而是由基础行为环节构成的。那么,对于“建立”的理解就需要进行解构。如果这个“做”首先被理解为由许多基础环节构成的概括性行为的话,那么利益概念就不能解析行为的环节。以“自然的做”为基础,“做”才能逐步进入道德理解、社会理解和法律理解的层面。具体个人的“做”要进入这些层面,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即“知道”和“能够”。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具体个人的“知而不做”形成了道德和法律上的“做”,例如故意放任有害后果的发生,这种做需要承担特定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后果。反之,有时候“能而不知”也需要承担特定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后果,例如过失,即具体个人所应当承担的自然义务。
其次,需要区分“要做”和“所做”。“要做”发源于内在可能性,而“所做”则能展现到分析者的面前。但是,“做”在这里产生了分野,分析者所知道的“所做”并非等同于具体个人的“要做”。也就是说,分析者不能外在地确定其内在的确定性。即:我知道你干了什么不等于我知道你想要干什么。“要做”的建构形式“如何做”与分析者所知的自然形式的“如何做”也是不同的,分析者只能以后面这个“如何做”去追寻前面那个“如何做”。这就意味着,分析者要通过具体个人的外在展现去尽可能地还原他心中那个“如何做”以及“要做”。而且,这种还原丝毫不必去援引任何抽象的论断。这与侦破刑事案件是一样的,你需要追寻事实的线索,而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去指导你。
再者,此时还完全没有牵涉到“应做”和“做对……好”这样的问题。对分析者来说,“做对……好”本来就蕴涵在“要做”当中。不还原“要做”,就不能进一步地还原“做对……好”这个问题。而且,不解决“所做”、“要做”、“做对……好”这三个环节,冒失地从分析者的角度提出“应做”,则是唐突和鲁莽的。因为,这样的意见此时还根本没有出场的资格。
这样说来,分析者对于具体个人内在可能性的切近不是直达的,而是曲折幽暗的。他不得不由远及近、由表及里地经过这样四个基本环节:外在可能性、外在确定性、内在确定性和内在可能性,贯穿这四个环节的关键就是“知道”。这四个连续环节不但针对于具体事件,也是分析者在这个“做”多次重复的基础上,认识该个人内在可能性及其结构的关键。这个“做”在利益之中构成了第二个要素,并从根本上标划了内在可能性和外在可能性的冲突——个人之所想,未必能够实现;而能够实现的,个人又未曾想到。
五、对象
从具体个人“有所做”的这个“所”出发,“做于何”的问题就会被提出来。它意味着,具体个人有其作用之于其上的对象,这是构成利益概念的第三个要素。在中文当中,对象有时也称为客体,但是中文的使用者常常忘记,客体总是在与主体的相对意义上使用的。同时,客体这样一个概念总是包含着具备某种外在形态的含义,不若对象所表示的那样明确。例如,当一个人希望赢得另一个人的爱情时,那个人可能对他产生的爱情是否是客体呢?爱情有“客”的成分,但没有“体”的含义。对象可以大致划分为自然物、具体个人、内心世界的某个要素或某些要素的组合这三种类型,它们在利益概念的语素结构方面是在以下层面上展开的:
首先,具体个人的“要做”有其对象,意向性是对象这个要素产生的原因。当具体个人的意向指向某种外在东西的时候,那东西就成为他的对象。意向性把对象从环境中区分出来。它通过某种确定性的信息,在对象和环境中间划出一条界限来。对于不同具体个人来说,这条界限可能是相当一致的,也可能是迥异的。无论如何,它在具体个人的意识当中是个有限信息集(某些信息是语言不可描述的),具体个人的所知囿于此信息集。在很大程度上,具体个人对这个对象的“做”不仅仅是为了“所知”,更多的是为了做后的“不知”。或者说,具体个人在其对该对象所知的基础上,对未来的“要做”进行想像,他按照他的想像去做,产生的结果总是包括不知的因素。因此,“要做”本身也意味着挖掘。
其次,对于对象的“有所做”受制于对象的有限性。一方面,对象对于具体个人的限制不仅在于他对于对象的所知是有限的,而且还在于这个所知也同时是他人的常识;他往往很难跳出这种常识,而产生出某种独特的意向性来。因而,在他看来,包围着他的“实体”是有限的,他认为他只能在这些“实体”对象中进行选择。另一方面,具体个人还受困于特定对象的不可分割性,在社会整体的意义上产生了“总量不平衡性”——即对象总体和由具体个人构成的人类全体之间的不平衡,对象总体又限制着这个由具体个人构成的总体(总体或者整体这个概念包含有无知这个因素)。为此,这个总体不得不通过挖掘对象的外在可分割性(通过时间和空间分割)来解决冲突、建立秩序,所有权问题以及其他权利问题都是如此。
再者,对象的多样性和个人内在可能性的多样性又多元地连接起来。一方面,同一“实体”对象的不同方面,可能与具体个人的不同内在可能性连接在一起。另一方面,不同“实体”对象也可能牵动着不同具体个人的内在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对象的多样性搅动着个人的内在可能性,进而导致内在可能性各要素之间的冲突和制约。历史地看,那些外在的“实体”对象的多样性是在偶然发现、有意发明和制造的基础上积累下来的。在新的对象被发现和发明以及社会化的过程中,旧的对象也在不断地消亡。
还有,这些外部环境当中的对象也可能成为他人的对象,从而诱使主体间性的问题出场。对于不同具体个人来说,可能没有完全相同的对象,而对象的不可分割性又不断地将更为广泛的属类牵涉进来,将不同具体个人的不同内在可能性牵连进来。那么,在下面这个链条上:某个具体个人的内在可能性——对象的多样性——其他具体个人的内在可能性,每个环节内部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其内部甚至还存在着某些不为人所知的结构)。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它们会排列组合成人类千姿百态的生活细节。同时,这也为驯服具体个人的内在可能性,进而建立社会意义上的制约创造了条件。
意向性是连接具体个人的内在可能性和对象性的中间环节。分析者对于对象的解释——即“为何”它成为具体个人的对象,实际上是对具体个人的内在可能性的追寻。这里涉及广为争论的哲学问题——即基于自我考虑和基于他人考虑的问题,这一问题是具备对象性视角的。弗莱斯曼在谈到本迪特误解他对利益概念的解释时认为,所谓基于自我考虑和基于他人考虑的问题,不过是在分析利益概念诸环节的过程中,分析者在认识层面上把哪里作为起点的问题[6]。这正如在蛋和鸡的关系中,在“鸡生蛋—蛋孵鸡—新鸡生新蛋”循环中把哪里作为起点的问题,这个起点是认识的起点,而不是考古出来的起点。实际上,每只鸡、每枚蛋和每次生蛋都不相同。
对于基于自我考虑和基于他人考虑的问题的讨论,可以按照笔者分析个人内在可能性和利益概念关系时提出的理性参与到非理性因素的三种模式去看待。在第一种模式中,这个具体个人是非理性的,那么他就是这种非理性,而你则是他的非理性的对象。在第二、第三种模式中,理性更强烈地参与到这非理性因素关系当中,这时他的利益是由两层构成的:你是我某个观念中的对象,我则是这种观念中的主体;同时,我的这种观念是我的对象,我又是这种观念的主体。因此,将基于自我考虑和基于他人考虑引申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并将它们作为伦理学的基本对立范畴是不合适的。与此相反,博弈论使用阶段性、结果(多段结果、单段结果和折现问题)、作为这些结果的原因的主体间性、特定结果对于能力的影响、价值观的变化和特定时间点的状态组合等来分析利益问题,远比上述那对范畴更为有效。
六、环境
除了具体个人作用于对象之外,实际上,在利益概念中还有第四个要素——环境。环境成为利益概念要素的原因在于意向性的消失,这要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环境是具体个人选择对象后暂时抛弃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具体个人不重视的、暂时无意向性的部分。另一方面,环境是那些具体个人完全无知的东西,它们是他不可能对之建立任何意向性也根本无法触及的存在。在自然界、社会关系和他人内心这三类对象中都存在着无知的部分。当意向性将对象和环境区别开来的时候,也将对于对象的无知和环境的无知区别开来。因此,在认识论上,所谓环境不是先在的、永恒的和统一的世界。即便是假设存在着这么个世界,其中的某些部分也总是交给“无知”这个认识论的基础概念的。
这里,环境这一要素所具有的三个特性要予以把握:(1)虽然环境有时指在一段时间内相对不变的那些东西的总称,但这里并非去假设环境具有自变性,而是说环境是随着意向性、对象的不断变换而变换的。(2)具体个人的理性试图将非理性的诸多对象总体性地纳入到视野当中来,并期望统观那些被称为局势、形势的对象,然而,这样的愿望是可以永远接近,但是永远不能达成的。(3)即便具体个人将对象之外的东西抛弃并将它们流放为环境时,随着具体个人作用于对象,在接下来的利益环节中,环境又不断地涌上前来。
返回来说,就要讨论使意向性原始地把对象与环境区别开来的指引——机会问题。机会是可能意义上的利益的线索,它向具体个人暗示有对象是可“做”的。机会这一指引弱于既得好处这样的水平,它只是说明具体个人认为有利于他,但是它也可能有害于他,因为机会也就是风险。进一步来说,机会从来不是客观的,它是外在可能性到达内在可能性过程中,闪烁出来的“灵光”。离开具体个人,也就不存在机会问题。所谓客观的机会标准是需要澄清的,以下这些流行的观点是可疑的:(1)多数人认这个机会符合他的利益,但是“多数人”都处“在利益之中”;(2)科学(科学家、科学文本)认为这个机会符合他的利益,科学要解决的是无知问题,但是它永无止境地去消灭无知,又永远也达不到全知,这是科学的宿命;(3)这个机会可能满足他的愿望,但愿望本身又不是客观的。对分析者来说,多数标准、科学标准和愿望标准都不能彻底地解释机会的客观性问题,该问题仍要保留给具体个人。
七、结果
从时间性来看,具体个人作用于环境中的对象后,会产生被整体性地称为结果的新状态,具体个人正是从做、做于对象、结果来体验外在世界的。结果由此构成了利益概念的第五个要素。对于这个结果,要从具体个人和分析者两个方面加以区别。
对于具体个人来说,做之前是想像的结果,做之后是反映到内在可能性当中的做后的结果。在他做后,他重新审视想像的结果,并将它与做后的结果进行对比。当两者一致时,内在确定性就转化成外在确定性。结果应该被理解为内在确定性向外在世界的抛出,这种抛出会对内在可能性产生诸多影响。
一般来说,想像的结果与做后的结果总是有差异的。当这种做后的结果只处于他所想像的结果的某种不成熟程度时,在非理性的情感方面可能会产生沮丧、失望;或者,与他想像的结果完全不符合时,他所面临的是惊异。两个结果的差异性将导致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这种抛出软化了原有的内在确定性,并使抛出原因的无知性绽露出来。另一方面,差异性又回落到内在可能性之中。例如,失败使其他在原先没有成为自我的内在可能性占据上风。这个自我对于原来的自我说:“你看,你失败了,这样不行,还是我来吧。”至此,利益完成了其全部的环节,回归到具体个人意向性这个起点。在利益的实现过程中,结果与具体个人的内心世界、对象、环境一样,渗透着越来越浓重的无知。
对于分析者而言,在具体个人对于自己尚且处于无知中的时候,分析者也不可能清澈澄明。分析者所观察到的结果不同于具体个人想像的结果、做后的结果。分析者只能从这个具体个人先前利益中所了解的内在可能性、他在当下的做、对象和环境,来和他所观察到的结果进行对比,去评估他的利益。从分析者角度来说,他所应用的利益概念只能是解构意义上的,利益概念要素在逻辑性上的完备性可以作为进一步工作的基础,但是这一工作只是分析者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利益概念从来不是对外在世界的描述,而是在分析外在世界前,需要准备好的方法。
八、语形
近30年来,西方学界对于利益概念的语言形式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讨论,分析其语言形式的焦点集中于in one' s interest这个短语中。在我看来,理解这一短语的关键就是要从可能性的意义上来理解in的含义。把in理解为“符合(according to)”是狭隘的,这种理解把利益和某种标准或目标等同起来。宏观上说,in使利益成为承载具体个人一切的无所不包的容器(其中包括无知部分),人人皆有利益,利益就是人的利益,在这种含义上利益成为具体个人的人生和生存的写照。微观上说,in意味着符合该具体个人的目标、他处在某种行动过程中、他的行动具备某种特定形式和属性、他处于某种状态或情境中,in这个英语词汇的这些原始含义是分别与内在可能性、做、对象、环境相对应着的。利益就是人的活动的无数细微末节,具体个人的人生就是由这些细节构成的,社会历史是由无数具体个人的人生构成。这就是说,in是理解in one' s interest这个短语的关键。in这个介词必须膨胀到“等于(is)”的时候,interest的边界才能显露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利益概念摆脱对于in one' s interest的日常语义的理解,使它从所藏身的状语中转变为句子的主语,而转化为Interest is……这样的句式形态。
考虑到本文在前面所分析的五个基本要素,这里对于西方学界近30年来对于利益概念语言形式的分析进行简要的评述:(1)奥本海默曾提出以It is in A' s interest to do x in situation S这个句式为核心来考虑利益的概念[7]。这个句式经过变形后,可以转换为Interest is A do X in situation S,但其中缺少对象,这是此句式的致命缺陷。(2)本迪特在x is in N' s interest at t(time)这一句式中强调了时间之维[8],但t已经蕴涵在形势(situation)和结果(result)这两个语素中。在时间维度上还有另外两种利益的变体,第一种变体是斯万顿提出的being in someone' s interests[9],它实际上就是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第二种变体是赫尔德(Virginia Held)提出的having an interest in,其含义更广泛些,即可指当下正在获取着的利益,也意味着当下未获得而将来可能和期望获得的利益,并不局限于过去发生的事实。在反驳巴里(Barry)的利益概念时,本迪特提到的“想要还没有想要的东西是符合某人的利益的”[8] 则是更为深刻的问题。(3)斯万顿在时间维度上将需要的可能性分为四个层次:(a)一个人当下有的对于未来要做、有和是什么的需求;(b)一个人在未来可能有的需求;(c)一个人被预测在未来可能有的需求;(d)一个人在未来特定环境下可能有的需求[9]。从她的分析来看,巴里提出的利益是外在可能性对于内在可能性的满足就显得相当狭隘[10] 175-176,这种提法使利益概念重归于边沁提出的基于快乐的理性计算。
故此,利益概念就是interest is a person(P) who act on(A) the object(O) in the situation (S)makes results(R),即“利益是具体个人在特定环境下作用于对象并形成结果”。这样一个利益概念在保持了内外在可能性的同时,也保持了自身逻辑的完整性和分析方法的开放性。从语言哲学角度说,利益概念通过这样一种语言形式从“有所指”发展到“指所有”的水平,进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中获得了基础地位。
九、结论
就国内目前对于利益概念分析的文献看来,以下两种方法是经常采用的:第一种方法,分析某个思想家有关利益概念的论述,并将其作为普遍性利益理论的基础;第二种方法,归纳思想史上某些作者关于利益概念的文字表述,将诸多不同的语素整合到一个统一的语言形式中。我认为,这样两种方法都是不充分的。实际上,只有在考察利益这个概念在思想史演进的过程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之后,超越主客观这对范畴的分析,以现代哲学的自我性、意向性、对象性和时间性作为提问的分界,去寻找利益概念语言形式才是更为完善的途径,本文所提出利益概念五个要素正是以上述四个基本性质为界限的。
在分析利益概念过程中,理解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涉及下面两个基本问题:(1)你知道吗?(2)在知和不知的基础上,你如何去判断好坏?因此,在这两个问题上保持中立性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对于利益概念的分析没有在这两个问题上妄下断言。首先,利益概念处于认识论层次,它是价值观的解释者,而不是相反。其次,利益概念的语言构成形式并未着眼于存在是什么,而是着眼于在认识论层次上保持自身逻辑上的合理性。再者,作为利益概念的分析者应该在自我与作为对象的利益概念语言形式之间保持中立,作为他人利益的观察者应该在自我与作为对象的利益内容之间保持中立。
总之,利益概念是在描述实践和事实之前,在分析者方面建立的认知意义上的简约框架,它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潜在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利益概念为解释人文社会科学中应用广泛的基础概念提供了途径,其中包括权利、权力(能力)、责任、义务、所有权、安全、特权、豁免、成本等,这些基本概念是人文社会科学最为重要的方法论范畴。另一方面,利益概念的这种语言形式本身也正是语言学中陈述句的完整形态,这种语言形式使分析者可以发现那些不符合利益的残缺话语。那些缺少具体个人、行动、对象、环境和后果的话语,也正等待着谁、如何、什么、哪里、何时和怎样等疑问词对于它们的追问。这种追问必定会使那些隐藏在后的潜在利益浮现出来,使分析者发现“残缺”的秘密。
标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