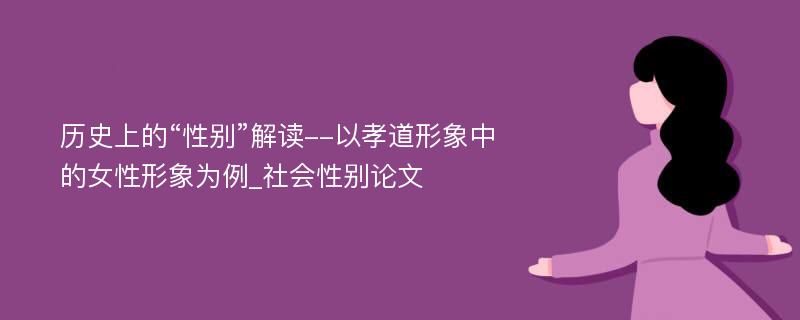
历史中的“性别”解读——以孝子图像中女性形象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孝子论文,为例论文,图像论文,性别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研究中的“社会性别”议题,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分析框架。美国纽泽西Rutegus大学的鲍尼·史密斯教授就曾通过分析“历史学”自身的历史来反省历史中的性别权力关系,她潜心20年撰述的著作《历史的社会性别——男人、女人和历史学的实践》(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论述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性别”如何影响了历史学的学科建构。在中国,无论是历史学或其他学科,尚未有类似的工作。但,历史中的性别课题已经受到相当多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史的研究无论在社会史、文学史、人类学还是女性学等领域中,有渐成显学之势。在文本文献的整理方面,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挖掘”工作。[1]但,正如一些社会史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要建构史书乏载或无载的所谓“另类妇女史”、“妇女形象史”或“社会性别史”,除了强调理论和方法的转变,即引入诸如社会学、人类学及文化研究(注: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自英国伯明翰学派以来,一直是一个与人类学、比较文学等并存而有交叉的独立研究领域。)(culture studies)中的“话语”(discourse)、“语境”(context)、“文本”(text)、身份认同(identity)等等新概念,新理论架构予“史料”以新的扩充与新的解读之外,还需要从单纯诉诸于政治、经济决定论的“女权史”、“妇女地位史”等宏大叙事的“大历史”中解脱出来,转变到对女性社会、社会性别、两性关系的多声道、多种面向与多种场景的综合分析,其中尤其应该加强对以日常生活、女性个体与群体的生命实践为中心内容的“小历史”的深入研究。
诸如从历史人类学、医疗史、区域社会与地方认同,甚至儿童史等视角或领域的研究,目前学界同仁在这些方面已有很多创举。举其要者,如李建民《小历史:历史的边陲》[2]、林维红《妇道的养成:以晚清湘乡曾氏为例的探讨》[3]和《中国人眼中的贞节:男女有别》[4]、李贞德《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5]、梅家玲《闺门之师》、熊秉真《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和《安恙:近世中国儿童的疾病与健康》[6]等等。1999年创刊的英文杂志《男女:早期与帝国时代的中国妇女和性别》更是集中了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的佳作。[7]因此,只有经过这些“小历史”的研究才能具体落实“社会性别”建构的历史线索、场景以及对具体社会文化内涵的发掘。
要揭示女性在历史中的形象是如何被有意或无意的掩盖与扭曲这一事实,发掘新的证据资料,重组或还原历史事件的真貌,确实是一项基本的工作。当然,也不反对要用新的眼光来“发现历史中的女人”。[8]但本文却无意于介入到一般女性主义学者所强调的,诸如要使历史诠释学来一场“全新的革命”等等论争当中去。[9]
要从史料、研究方法、分析范畴等中有新的突破,就目前的认识水平而言,人类学正在成长中的“社会性别”课题自然是一个突破口。而且,由历史材料来分析“社会性别”建构及其历史发展轨迹,这本身既是拓宽史学分析与诠释的空间,同时也回应“社会性别”研究本身面对的各种挑战——毕竟这一议题是从“当下的”而主要不是“历史的”社会事实中升华出来的。正如Scott所指出的那样,“社会性别”对历史学而言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策略,将其引入历史研究,将会开辟出一个新的天地。[10]
近年关于社会性别的多视角研究,有许多新的收获,一是表现在关于史实发掘和史料解读的方法论革命;二是用新的历史证据、新的民族志(ethnography)和案例研究(sase study)修正了那种妇女在正统婚姻、家庭中孤独,屈辱以及处境尴尬的形象。正如有的学者总结的那样“像母系亲属关系的支持网络、精英家庭为女儿提供的大量嫁妆、给寡妇的供应品、姐妹之间的互赖,以及夫妻间的感情,这些都指出了中国妇女比我们曾经所相信的有更多的回旋余地。”[11]试举几例加以说明。刘静贞以宋代560篇女性墓志碑铭所记载之“事迹行谊”为核心,分析了儒家史学宣称的“女正位乎内”与现实社会中女性之社会角色地位的落差问题,揭示出士大夫对理想社会秩序之坚持与现实情境冲突的种种纠葛,这既反映了“一元价值”而“生活多样”的辩证张力,也提出对“女性于史无载”的另类解读。[12]刘慧容对乡村社会于“现代阶级斗争史”的“无事件境”分析,揭示出村落视野中女性“诉苦文化”的“性别扭曲”,以及“历史事件”对于特定情景中的村民的意义,对当前流行的口述史与调查研究方法提出非常值得深思的案例。[13]Helen Siu《妇女何在——抗婚和华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无疑是中国女性研究的现代经典之作。她以华南地域社会里的“不落夫家”习俗为例,尝试将这一习俗置于更广泛的文化和历史脉络中来考察,特别是作者关注它们如何成为文化规范和文化策略的,等等,阐释了华南地域社会在“国家化过程”中对文化范畴的创造和重新解释等“地方意识”崛起之类的大问题。显然,这个分析融合了文化、社会和历史等多种解释维度,将妇女生活研究纳入更大视域范围内来审视分析,为社会性别研究开拓出更广的空间。[11]
本文以传统中国社会倡导的“孝道”实践入手,具体说是以考古发现的“孝子”图像材料为中心,并结合古代社会规范女性的“妇道”,来复述并分析“孝道文化”中所展现的女性形象。
二、作为独特文化展现方式的“二十四孝”形象
通常的理解是,“孝道”是传统中国用以规范男子的道德思想和伦理纲常,所谓“百事孝为先”是男子的责任,对女子是以“妇道”来要求。但,以下三层事实必须得到重视:
(一)“孝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对女子的要求和规范,甚至有专门的《女孝经》刊布。特别在民间社会里,“孝”是夫妻双方对父母的责任和义务。
(二)“妇道”并不是脱离“孝道”的存在,“妇道”里强调的诸如“孝敬公婆”与“孝道”中的“遵亲、奉亲、养亲、无违”等等行为要求也是一致的。某种程度上,“妇道”是在“孝道”基础上增加了对“丈夫”相关的义务要求。
(三)就时间上来说,“孝道”和“妇道”并不容易说清谁先出现的问题,但就目前掌握的文献和研究来看,系统的“孝道”比“妇道”在儒家的理论中出现更早,也更为重要。
从“孝子图像”材料看,“孝子”典型并非从一开始就完全排斥了女性的参与。而且,就孝子的施孝对象而言,有父有母,这里女性作为孝子“孝敬”的接受者和男人也是完全平等的。
希望这个以考古发现的图像材料为中心的研究能够摆脱以往女性研究中以文学和史学文本为基准材料的研究范式的限制,笔者当然也尝试突破以中国传统文人画中的妇女题材为主题进行研究所遭遇到的诸如女性形象色彩单调与过度程序化带来的不足。(注:目前所知道的这些“孝子图像”主要以墓葬所出土的材料为主,这些墓葬主人的身份基本上以中下级官吏和地方士绅阶层为主,尚没有发现王室墓葬中有类似图像发现的报道,这当然不排除考古发现自身的局限。民间发现的“孝子图像”则相当普遍,诸如建筑雕刻、年画、剪纸窗花等不胜枚举。)
这里所谓的“孝子图像”(当然包括孝女,以下同)是指反映孝子或孝行(以榜题或故事情节内容,并结合后世“二十四孝”人物活动情景来判断)的人物或活动的图像。这种图像自汉代开始出现,历代均有,且续有发展,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实在是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孝子图像”不仅可以复述/构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王朝阶段的“孝子典型”,而且其自身的历史刚好说明了“二十四孝”的形成与发展历史——由最初的几个人物典型、模糊的故事情节到宋元之际“二十四孝”的成型(甚至有不同的“二十四孝”版本人物)以及儒家士大夫阶层参与辑录、增削、整理、编撰而定型。
这些流传久远而有序的图像,因为大都比较“粗俗”,只有少量作品为艺术史家所称道,所以向来不为艺术研究者所重视,考古学者也因为这些材料太过分散而疏于系统整理。基本上,关于孝道文化的研究不甚关注孝子图像材料,当然也缺乏对女性特别是融合社会性别分析视角的研究,有限的针对《女孝经》的研究虽然涉及女性生活空间和女性话题,但缺少历史的纵深场景。[14]日本学者黑田彰的《孝子传的研究》,不仅讨论了大量与之相关的传世文献,并结合少量墓室壁画中以及唐三彩器物上的孝子图像材料,对“孝子传”的渊源、历史传承与版本关系等有很好考证,但他将“孝子传”与后世的“传记小说”等量齐观,实在是一种文化误读。[15]只有劳悦强在《〈孝经〉中的隐形女性》一文注意并讨论了这样一个现象:在唐代以前的文献中极少见到孝女和孝妇的记载(唐代侯莫陈邈之妻郑氏撰有《女孝经》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五子部五儒家类存目一有提要),尽管汉代以孝治天下,可是这种论孝、彰孝当中的性别偏失现象却明显存在。
“孝子图像”材料中是否也同样存在这样的性别缺失呢?为了辨析“孝子图像”,有必要先来介绍“二十四孝”以及“二十四孝”形成过程的诸“孝子”。
传统所谓“二十四孝”,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而是成型于元代。对其具体内容有三种说法:一是范泓《典籍便览》和《大田县志》称元郭居敬所辑者,人物有虞舜、汉文帝、曾参、闵损、仲由、董永、郯子、江革、陆绩、唐夫人、吴猛、王祥、郭巨、杨香、朱寿昌、庾黔娄、老莱子、蔡顺、黄香、姜师、王裒、丁兰、孟宗、黄庭坚。二是清家秘本《二十四孝诗注》所辑录24章孝行录,及晚凫山(老)人《重刊女二十四孝序》称郭居敬所辑者,人物有大舜、董永、丁兰、闵损、剡子、孟宗、朱昌寿、田真、郭巨、老莱子、吴孟、曾参、汉文帝、王裒、杨香、庾黔娄、张孝、黄香、黄山谷、陆绩、唐夫人、王顺、姜诗、蔡顺。三是狩谷掖斋藏《孝行录·古抄本二十四孝》和清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称郭居敬所辑者,人物有虞舜、老莱子、郭巨、董永、闵损、曾参、孟宗、刘殷、王祥、姜诗、蔡顺、陆绩、王武子、曹娥、丁兰、刘明达、元觉、田真、鲁义姑、赵孝宗、鲍山、韩伯榆、杨香、琰子。其中以第一个“版本”流传最广,一般所言“二十四孝”均指此。本文采多个版本的“二十四孝”之说法,而非以任一家为正宗,以包纳更广泛的“孝子图像”之内容。关于“孝子图像”与“二十四孝”之渊源关系当另文再述。
实际上,考古所见到的“二十四孝”连环故事题材的图像,在宋、金两代的墓室雕刻上已经出现了,且流传很广。1958年在河南孟津出土的一件北宋时期的石棺上,就有连续的二十四幅“孝子图”,有赵孝宗、郭巨、丁兰、刘明达、舜子、曹娥、孟宗、蔡顺、王祥、董永、鲁义姑、刘殷、元觉、睒子、鲍山、曾参、姜诗、王武妻、田真、杨香、韩伯俞、闵损、陆绩等24位孝子人物。另一件1986年出土于河南巩县的同时代石棺上也有连续的“二十四孝”线刻图像,有丁兰、董永、舜子、郭巨、睒子、鲍山、刘殷、子骞、伯榆、曾参、(王)武妻、陆绩、姜诗妻、元觉、田真、曹娥、孟宗、老莱子、王祥、蔡顺、杨昌(香)、赵孝宗、鲁义姑、刘明达。对比两件“二十四孝”人物,除了文字有不同的“俗写”外,完全相同,可知,“二十四孝”的程式在宋代已经成熟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石棺上的“二十四孝”人物与狩谷掖斋藏《孝行录·古抄本二十四孝》以及清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称郭居敬所辑的“二十四孝”人物完全相同(即前述第三种说法),这说明所谓“古抄本二十四孝”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山西长子县石哲金墓、长治安昌金墓以及永济金墓都出土完整的“二十四孝”图像。
其实,这些北宋、金代成型的“二十四孝”图像有更古老的渊源,是由“孝子图像”发展而来的,而“孝子图像”至迟自汉代开始流行,如汉代武氏祠石刻中的“孝子图像”,已经有舜、曾子、老莱子、丁兰、董永、闵子骞、韩伯榆、邢渠、孝孙、魏汤、鲁义姑等11位孝子人物。而整理、辑录孝子事迹的《孝子传》,也始自汉代,是有着同样久远的历史传统,而且以后历代几乎均有撰述或增补。现在知道的《孝子传》的不同版本中,就有萧广济、师觉授、徐广、郑缉之、宋躬、王韶之、虞盘佐等不同辑录者。据传,刘向的《孝子传》采用了图文并茂的形式,可惜早已失传,无法复原了。有不少现代学者因此认为,考古发现中的历代“孝子图像”是以刘向的《孝子传》为蓝本的。如果考虑到汉代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推行孝廉察举的政策,应该可以推想出存在相反情况的可能性,也许认为刘向《孝子传》正是以民间流传的“孝子图”为蓝本而加以整理辑录成册,更接近历史事实。不管怎么说,《孝子传》与“孝子图像”确可以互为补充,不仅仅因为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教科书”性质。这些材料可补充文献材料的不足,提供分析“二十四孝”的变迁线索,实在是认识中国古代孝道文化的另一种途径。
“二十四孝”人物虽然有三个不尽相同的版本,全部人物加在一起,只有38人。据目前所知,考古发现的“孝子图像”中的孝行人物,自汉至元代,有42人,两者差别并不很大。有意思的是,不管“二十四孝”人物,还是“孝子图像”人物都有女性存在。见于“孝子图像”而不见于“二十四孝”人物的,有6人,即原谷、尉、子路、李充、唐氏和李氏孝女,看不出有性别排斥或歧视的现象。
以这些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为基础,通过“孝子图像”中“孝子”、“孝女”以及“母亲”形象的分析,呈现出整个“二十四孝”形成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女性形象的建构与社会性别编码。有意思的是,由于这些材料的特殊性,即主要以反映民间对孝道思想的理解和孝行实践为特征,虽然也有以官方颁布的《孝经》为蓝本的痕迹,但基本上与《孝经》等儒家经典中所论述的“孝道”在形式上完全不同,它直接、形象,有具体人物、动人的具体情节以及融入佛教思想后的“得到回报”的场景,因此更具有教化和传播力量。
三、孝子孝行中的女性形象剖析
人们习惯将这些古代行孝人物称为“孝子”,但仔细考察便会发现如此并不全面和准确。孝子故事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到女性。[16]以下即利用文物图像材料并结合文献,对古代孝子及其行孝事迹中的女性形象做一简单梳理。
这些女性形象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作为行孝者的女性和作为接受者,即行孝对象的女性。
第一类是行孝者中的女性形象,相对于“孝子”而言的“孝女”(女孝子)或“孝妇”。在流传的几种“二十四孝”说法中,主要有杨香、唐夫人,曹娥和鲁义姑。目前所发现的历代孝子图像材料中这几个人物都有出现,此外见于孝子图像但未被纳入“二十四孝”人物的还有李氏孝女。以下概括述之。
杨香,事见《异苑》和佚名《孝子传》。香14岁时,与父在田里劳作,父为老虎所噬。香勒住老虎,其父获救。从孝子图像的资料来看,这一人物始见于宋代的壁画墓,画像石棺等,[17]此后在辽、金、元各代的墓葬中均有出现。[18]
唐夫人,其孝行事迹不见于史载。传统“二十四孝”人物中,“唐氏乳姑”题材讲述的是:婆婆有病不能吃东西,唐夫人每日用自己的乳汁喂养,数年而得康复。文物材料中也较少见,目前仅在四川广元○七二医院出土的南宋嘉泰四年墓中有见。[19]
鲁义姑,事见《说苑》:战国时,齐攻鲁,一妇人带着两个孩子逃亡,见到齐军,赶忙把小的扔了,拉着大的跑。齐兵追问缘由,妇人说:大的是兄长的,小的是自己的,救人之子是公义。这个人物题材表现的是义的内容,但却为二十四孝人物之一。考古发现中也多与孝子图像同出,自汉代始出后,宋、辽、金、元等时代墓葬孝子壁画资料均有此题材。[20]
曹娥,事见《后汉书·列女传》和《会稽典录》:娥父溺水而亡,不见尸骸,娥乃沿江号哭,不舍昼夜,七日未得,投江而死。此人物是孝子图像资料中较为常见的题材,首出于宋代,见于河南嵩县壁画墓,“王十三秀才”石棺,张君墓石棺,巩县宋墓石棺,乐重进画像石棺等墓葬材料。此后金、元代的墓葬材料中都有出现。[21]
李氏孝女,事见《新唐书·列女传》:汴州李氏孝女,年8岁,父卒,停于堂十余载,每日哭泣。及长,其母欲再嫁,遂截发自誓,在家终养其母。此题材在历代孝子图像中极为少见,目前仅见于重庆井口宋代画像石墓。[22]
孝子题材中,还有两个人物较为特殊,一是姜诗,一是王武子。姜诗的事迹见于《孝子传补遗》:姜诗事母至孝,母好饮江水,嗜鱼脍,于是舍侧乃忽涌泉,味如江水,每日一汲,则得双鲤。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列女传》则记载此孝行为姜诗妻所为。而从孝子图像资料来看,自宋代始出,辽、金、元代的墓葬材料中都有发现,或表现姜诗,或表现其妻行孝,而图像榜题也作“姜诗”或“姜诗妻”。[23]
王武子的事迹见于敦煌遗书《孝子传》:王武子征涉湖州,十年不归,新妇至孝,为治武母病,割股上肉做羹,奉送武母,母食之,病即愈。孝子图像资料自宋代始出,此后辽、金、元代均有发现,多表现为王武子或王武子妻为母割股的场面,榜题姓名也或为“王武子”,或为“王武子妻”。[24]
姜诗和王武子均为后世流传的“二十四孝”人物,文献记载和文物材料都清楚表明,此两种孝子题材中,都有其妻行孝的内容,或为主,或为辅,但最终却都以男子丈夫的名义入“二十四孝”人物,此当引为注意。
第二类是施孝对象中的女性形象,孝子/女的母亲。这些施孝对象有,“二十四孝”人物中的舜、闵子骞、曾参、郭巨、蔡顺、孟宗、汉文帝、陆绩、江革、黄庭坚、王裒、朱寿昌、韩伯榆、刘明达、鲍山、王祥、老莱子、剡子、子路(仲由)、丁兰等人的母亲,只见“孝子图像”中则有茅容、薛包和王延元等人的母亲。
具体分析这些女性人物,有三种情况值得关注:
一是有的女性是作为独自的孝行对象而存在,整个事迹不见父亲的存在,母亲独享“孝尊”的地位。这些人物有曾参、郭巨、蔡顺、孟宗、汉文帝、陆绩、江革、黄庭坚、王裒、朱寿昌、韩伯榆、刘明达、鲍山、茅容等人的母亲。
二是和父亲一起共同享有“孝尊”的母亲形象,这类人物有老莱子、睒子、子路(仲由)和丁兰等人的母亲。
三是行孝事件中作为“反面形象”的母亲,这通常是后母。这些人物有舜、闵子骞、王祥、薛包和王延元等人的后母。
以下分别概括述之。
先谈第一类。曾子之母。佚名《孝子传》载曾参门人“来候参,参采薪在野;母啮右指,旋倾走归,曰负薪后背痛,薪堕地。母曰:‘……故啮指呼汝耳’。”孝子图像中的这个题材,自汉代开始出现,宋、金、元代的墓葬中都有发现。
郭巨之母。郭巨行孝是魏晋以后孝子图像中的常见题材,见于北魏孝子石棺、固原北魏棺板漆画、邓县砖室墓彩色画像(砖)和襄阳贾家冲画像砖等。其事迹见刘向《孝子传》和宋躬《孝子传》:郭巨家贫,每供馔,其母必分与孙。为更好地供养其母,巨决定将儿子埋掉,掘地三尺却得一釜黄金,于是得兼养儿。自魏晋以后,宋、辽、金、元各代图像资料均有出现。
蔡顺之母。蔡顺行孝事迹有不同的版本,内容差别较大。北魏时期孝子图像多表现房屋失火后,顺身披重孝伏母棺号啕大哭的场面,北宋时期,蔡顺题材表现的是“蔡母怕雷”的场面,称为“闻雷泣墓”,这些事迹见于《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金代以后出现的蔡顺行孝图像,内容多为并为蔡顺“拾椹供亲”,其事见于《孝子传补遗》,蔡顺拾椹,以异器盛之,赤眉贼见而问之,顺曰“黑者奉母,白者自食”,贼知其孝,乃遗米肉放之。这一故事题材也被后世“二十四孝”所本。
孟宗之母。事见《孝子传补遗》和《孟宗别传》,以前者为据。孟宗母嗜好竹笋,至冬无笋,宗入竹林哀泣,笋突然生出。此题材为宋代最为常见的内容,中原几乎所有的孝子图像墓均有此题材。
汉文帝之母。“二十四孝”人物中,有“汉文帝亲尝汤药”的题材,讲的是汉文帝奉养无怠,在三年母病期间,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凡母服用的汤药必亲口先尝。宋金时期的孝子画像表现的是“为母煎药”的情节。
江革之母。事见《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和佚名《孝子传》:革与母居,时大乱,乃背母逃难。数遇贼人劫掠,革涕泣哀求,贼人感动,放其逃走。革“行佣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给”。孝子图像多见于金代,图像表现的正是“江革行佣”的情节,描绘江革背负一竹筐,其母坐于筐内,革正对一武士拱手。
刘明达之母。事见敦煌遗书《孝子传》:刘明达母年迈,吃饭时被孙夺去,刘明达于是将儿子卖与王将军,其妻呼唤。孝子图像资料自宋始出,此后在辽、金、元墓室孝子图像中为常见题材。
韩伯榆之母。事见《说苑》:伯榆有过,其母笞之,伯榆泣,母曰“他日未尝泣,今日何泣也?”伯榆说:“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孝子图像自汉代始出,仅有“伯榆”、“榆母”二人,情节简单。魏晋以后增加了“孝妇”、“榆子”和“孝孙”等人物。宋金时期,为墓室孝子图像常见题材。
鲍山之母。宋、金、元代孝子图像材料中常见这一人物题材,内容多表现一男子、一老妇和一武士的场面。鲍山系后世流传的“二十四孝”之一种的人物之一,但其事迹不见史载。考之史籍,发现《三国志·魏书·周温传》中注引鱼豢《魏略勇侠传》载有“鲍出”事迹,云:“贼略其母,出独追之,行数里及贼。救出其母与比舍妪”,内容与孝子图像表现相合。故由之推考,此“鲍山”当为“鲍出”之误笔。
黄庭坚之母。事见《宋史·文苑六》:庭坚性笃孝,母病弥年,昼夜视颜色,衣不解带。图像资料仅见于辽代的墓葬,[25]表现的是“庭坚为母洗涤便器”的情节。
王裒之母。事见《晋书·孝友传》和《孝子传补遗》:王裒母性畏雷,母亡后,每有雷,裒必到墓前,曰:“裒在此。”图像材料自辽代后为常见题材,表现的是“王裒闻雷泣墓”的情节。
朱寿昌之母。事见《宋史·孝义传》:朱寿昌母子五十年未得相见,寿昌寻找不见,便辞别家人,弃官入秦寻得母亲。此题材孝子图像在辽、元时代墓葬中有见。
茅容之母。事见《后汉书·郭符许列传》:郭林宗借宿,“容杀鸡为饮,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茅容为辽代常见孝子图像题材,后世不见。
下面再来谈第二类“母亲”形象,即与父亲一起共同享有“孝尊”。
老莱子之母。事见师觉授《孝子传》和佚名《孝子传》。年已七十的老莱子,常服斑斓衣,为婴儿戏,以娱双亲。这一题材的孝子图像自汉代始出,此后历代多有发现。
睒子之母。这一题材在孝子人物中较为特殊。在北周时期的敦煌壁画中有依据佛教《睒子经》绘制的“睒子本生故事图”,表现的是迦夷国名睒的孝子照料盲父母的故事。某日睒披鹿皮汲水时,被国王误射身亡。双亲痛哭,感动天神,使睒子复生,双亲复明。这一佛教题材人物至宋时已成为中原墓室壁画的内容,此后辽、金、元代都有出现,故事情节没有变化,唯将国王换成了猎人或军士、武将,睒子也成为后世流传的几种版本的“二十四孝”人物之一。
子路(仲由)之母。事见《孔子家语》和敦煌遗书《孝子传》:子路孝敬双亲,为亲于百里外负米。图像资料始见于宋代,且仅流行于四川、重庆一带的宋墓中。
丁兰之母。事见孙盛《逸人传》、佚名《孝子传》:兰年少时父母双亡,长大后刻木供养,视之若真父母。邻人醉酒辱骂木人,兰将其杀死。图像资料始见于汉代,此后历代孝子图像中都有此题材。
第三类的后母,一方面是作为行孝的对象,另一方面则多是令人痛恨之角色,也正是因为她们的恶毒、残忍,更反衬出了这些孝子孝行的不同寻常和深刻。
舜之母。《史记·五帝本纪》和刘向《孝子图》中都对孝子舜有记载。从发现的孝子图像材料看,自汉代始出后,各代都有这一人物题材,但表现的行孝内容却不相同。汉代多为单体“帝王”造像,并无孝行故事情节;魏晋南北朝时期舜的形象通常是一组连续性的图面,基本情节与《史记》当中所记载的内容甚为相符,表现的是舜遭后母、父与弟虐待的情形。而发展至宋代,内容又发生变化,“孝感动天,鸟耕象耘”成为主题,自此以后固定下来,“二十四孝”即沿用此种程式。舜在各种流传“二十四孝”版本中均位于首位,所言其孝行事迹均与宋代及其以后的孝子图像内容一致。
闵子骞之母。事见萧广济《孝子传》、师觉授《孝子传》及佚名《孝子传》:闵子骞早年失母,后母遇之甚酷,衣皆蒿枲为絮,其父也待之不公。图像材料自汉代始出,宋、辽、金、元墓葬中均有发现。
王祥之母。事见《晋书·列传三》和师觉授《孝子传》:王祥母早丧,因继母谗言而失父爱,但仍孝顺有加。天寒冰冻季节,继母想吃鱼,祥解衣卧于冰上,冰忽然自解,双鲤跃出。此题材图像资料自宋代始出,后代续有出现,画像表现的是王祥卧冰求鲤的情节。
王延元之母。事见《十六故春秋·前赵录》:王延元9岁丧母,后母待之不道,盛冬时令其抓鱼。不得,则遭毒打。延元叩冰而泣,冰裂得鱼“长五尺”。此题材的图像材料目前仅见于重庆井口宋画像石墓。从内容看,王延元行孝事迹与王祥很相似。
薛包之母。事见《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后母憎包,将其赶出家门,包号哭不走,遭殴杖。包仍行孝如旧,父母感动而接其回家。图像资料仅见于辽代,表现的是一老父坐于案后,旁坐一妇人,前有一男子向他们拱手施礼。
施孝对象中除了上述母亲的形象外,墓葬材料中所见的孝子刘殷题材较为特殊,他行孝的对象是曾祖母。关于刘殷的事迹见于《晋书·孝友传》和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殷9岁时,曾祖母在严冬时想吃芹菜,殷为此痛哭,感动了天地,在泽中长出了芹菜。孝子图像材料中,首见于宋代墓葬,此后辽、金、元代墓葬均有此题材。
此外,还有一位与上述诸种女性形象不同的反面例子,这就是见于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风的孝子李充(妻)题材的图像资料。[26]据《后汉书·独行列传》记载,李充家贫,其妻劝李充分家另过,充表面答应,待到母亲面前,去斥责其妻离间母兄,并将妻逐出家门。
综上,孝子图像中所见之女性,或为正面的孝女、孝妻、良母,或为反面的后母、不孝之妻,可见其形象是丰富而非单一的,这大大丰富了历代“列女传”中相对单调的女性形象。[27]而且,还应该注意到,这些女性也并非全部没有名字的“无名氏”,有配角,也有主角。从孝行故事展开的场所来看,有家内、家外和地点不明确等三种情况,所以空间上也并非完全局限于“家内”。诚然,作为施孝的母亲在这里多仅仅具有“符号”的意义,而不具有“事件”的意义,且父亲的形象也不例外,因为这些题材的核心是表现“孝子”自身,而非与相关的被孝顺的父母。
或有学者以为,这些孝子图像是源自“孝子传”,而刘向始作俑的“孝子传”具有“小说”的性质,自然包含了虚构的内容,而非实有其事。笔者认为,诸如“天人感应”、“报应”等方面的内容,与其说是作者们的虚构想象,毋宁说一种普遍的信仰。而且,从“文化展演”(culture representation)的立场来分析,这些所谓“虚构的”故事和情节,正是民间孝道思想实际轨迹的反映。因此,这些女性形象也大致和生活世界里的女性,具体说是实际生活世界里对女性的认识和定位,基本一致。
这样看来,孝道文化中女性并非完全处于从属的地位,换句话说,女性也要遵守孝道之要求。或者说,孝道作为调节家庭和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秩序,一开始并不排斥女性的参与,只是在妇道成为女性的内在规范之后,那些不符合该规范的内容才逐渐从“孝道”中剔除的。
四、“孝道”与“妇道”互渗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建构
通常以为,规定女性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是“妇道”而非“孝道”。而“妇道”的核心,则是《易经·家人卦彖辞》中所强调的“女正位乎内”的天地之大义。“内”、“外”之别,多见于儒家经典,如《礼记·内则》说:“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等等,因此在儒家传统中“女正位乎内”不仅仅具有职业/事业分工的意义,也具有空间分割的含义。现代学者将其作为所谓“女无外事”的“妇道”之本加以分析,是理所当然的。[28]
和“孝道”不同,“妇道”规范从一开始就具有性别分野的意向。“妇道”的基础是“男女之别”的合“礼”化,所以“妇道”之养成正是女性社会化,即社会性别培养和教育的中心内容。一般学者也都坚信,在中国传统妇女受教育的终极目的不外在成就“妇道”。至迟从汉代班昭《女诫》刊布以来,这种“妇道”即已形成为一种独特的中国传统。所谓妇道,班昭名之曰妇行,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为主要内容。[3]而且,班昭作《女诫》的原因是因担忧“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其目的是教导女性如何进入一生最重要的婚姻生活。所以,“妇道”的目标听众是全体女性中的“适婚妇女”和“已婚妇女”。《女诫》之后,历代都出现了许许多多类似专论妇道的女教书,这些针对作为“媳妇”或夫妇另一半的“妇”而言的“女学”,也都围绕诫言、诫行来限制和规范女性的。从儒家理念来看,女性存在的全部价值都是为了成就“妇德”而准备的,“妇道”自然可以忽略作为“女孩”(青少年)、“媳妇”(人妻)和作为“母亲”的女性身份差别,也就把女性形象定型化了。
林维红以晚清湘乡曾氏家族“妇道”养成为例,说明儒家理念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张力,得出“男女有别”的社会规范之下“妇道”是实现家庭成员之间互惠互助而达至和谐的途径。她说:
“所谓‘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粗看似显示一种教育内容的‘男女有别’或‘内外之别’,但从曾国藩务实的生活日用哲学作深一层的分析,则可以说他更希望家中男女共构一个共同的生活秩序,在这个生活秩序里,男女各有所长,互惠互补,以达成他认为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和’字。”[3]
问题是,在中国,建构性(别)家庭人伦理念的除儒家外,还有道家的阴阳学说,就是强调“阴阳协调”、“和谐平衡”。曾氏关于“男外女内之平衡和谐”的文化解释,就很难全然排斥融会了这样的理念。这就提醒研究者在分析社会性别的社会和历史建构时,除了儒家的学说外还要准备容纳道家、佛家,甚至基督教(特别分析近代中国时)的思想。
“正史”如何建构社会性别呢?其实,“忽视”是另外一种建构。中国向有“写史”的传统,于今留下了包括25史在内的大量的史学遗产。翻检这些史料,可知早期的编年体史书,如《春秋》、《左传》等所记均是政治、军事、经济等国之大事,除君王外的个人生平不曾是“历史”的主体。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创立记述个人业绩的“纪传体”,却不曾描绘过皇室以外的任一女性。范晔《后汉书》创立《列女传》之先声,范氏在《后汉书·列女传序》中说:“《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兴以后,综成其事,述为《列女篇》。”
但这个叙述却是残缺而不完整的,故现代史家才会发出如下的感叹:“其后诸修史者,虽未必有‘哲妇’、‘高士’、‘贞女’的见解,却因循而作《列女传》于其中。女性终于在正史中得到了一点位置。但即使如范氏的见解,所列诸传中除了像曹娥这样未婚女性外,凡已婚者一律冠之以某某妻。即使以蔡文姬之名声,亦不得不冠以陈留董祀妻,仍然是一个男性主体的历史面貌。而且随着社会理教观念的变化,到元明以后,列女传则更颇有烈女传之味道了。其实列女传的缘起,即不在作史,而在警世作则。”[29]
这一点恰恰点出了“列女传”作为“妇道”样板的非历史意义。其实刘向在撰写之初就已经指明了其主要目的:“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汉书》卷三六《刘向传》)。令人奇怪的是,据称《列女传》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戒天子”,而后才转为“戒女子”的,于是《列女传》就渐成为《女戒》了。这个由“戒天子”到“戒女子”的转变,其背后的文化以及制度的连接在哪里呢。
《孝子传》以及历代发现的“孝子图像”,也当可作如是观:不在记史而在警世作则!
“二十四孝”从其出现到形成,前后千余年,对中国社会有深刻之影响,但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有多少是可以真正做到的呢?“负米养亲”、“亲尝汤药”、“拾葚养亲”、“行佣供母”、“亲涤溺器”、“怀橘遗亲”等可以做到,“鹿乳奉亲”、“弃官寻母”、“恣蚊饱血”、“打虎救父”也可以勉强做到。而“孝感动天”、“埋儿得金”、“卧冰得鲤”、“尝粪心忧”及“哭竹生笋”等等,则是绝对难以做到的。因此,顺着上面分析“妇道”的思路,“孝子故事”本身是否实有其事或能否做到并不重要,其目的不在“作史”而在“警世作则”成就“孝道”。正是在这一点上,“妇道”和“孝道”的女性形象有着内在的社会和文化一致性,只是各有侧重罢了。
以往的研究总会得出如下结论:在古代中国,男人所做的事情通常被认为比女人做的事情更有价值,认为这是社会性别的文化呈现(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gender)和社会性别表现(embodiment of gender)的常见现象。以往研究孝道的学者也大多并不注意孝道文化中的“女性形象”议题,他们或者习惯地认为,孝道文化所涉及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男性社会”而不关“女子的小社会”。或者想当然的以为“孝道文化”的发生主要是在“厅堂”而非“闺房”或“厨房”。因此,孝道文化的研究本身也落入“社会性别”建构的文化机制当中。这样的见解显然误解了“孝道”可能实现的场合的复杂性、多样性,而且“孝道”实践中的“生养死丧”都有具体的女性“任务”,低估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形象。在“百事孝为先”的传统社会里,“妇道”实际上已经融会贯通了“孝道”的各种社会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