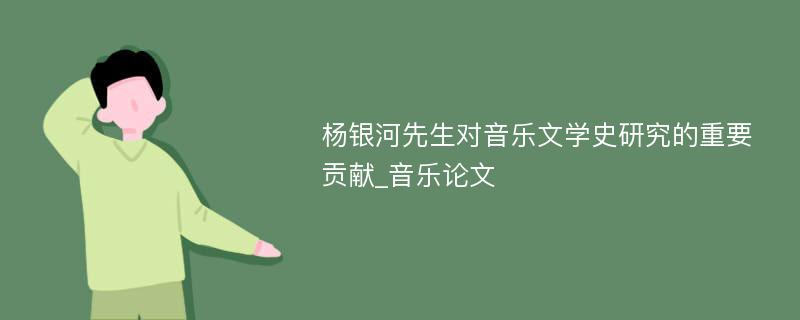
杨荫浏先生在音乐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若干重要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贡献论文,史研究论文,音乐论文,文学论文,杨荫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音乐与文学存在着天然的密切悠久的关系,被认为是一对“孪生姐妹”。歌曲以语言为重要表达手段,是有词之乐;而诗词本来就是配合音乐的歌辞,是一种音乐化的语言。因此无论是在文学史上还是在音乐史上,音乐文学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音乐文学研究者王昆吾先生说得好:“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或音乐史,其主体部分就是一部中国音乐文学史”(注: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第4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11月版。)。
杨荫浏先生是我国民族音乐学和古代音乐史学研究中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知识渊博,眼界宽阔,在音乐文学史方面也曾作出很多重要的富于启迪的贡献。但相比较而言,这些杰出成果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限于篇幅,更主要限于笔者的认识理解水平,这里还不能深入全面地评价介绍,仅试举几例,供广大读者窥其堂奥,略见其概。
一、我国语言音乐学的开创者
杨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具体问题入手并紧密结合中国音乐的实践。他在音乐文学史方面的研究也充分体出了这一特点。他不是形而上地、从抽象到抽象地演绎泛论音乐与文学的关系,而是从语言与音乐的关系、从歌曲字调与曲调的关系这类具体实在的问题入手,并由此开创了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门分支学科——语言音乐学。
音乐文学是音乐与文学相互结合的综合型艺术,而文学则是一种语言艺术,因此,音乐文学最直接具体的体现,就是可以歌唱的歌辞(语言)。作为音乐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早在40年代前期,杨先生就写出《歌曲字调论》(注:发表于1945年《礼乐》第1册。)。 他根据古今曲家及他的曲学老师吴畹卿的论曲之言,结合自己习唱昆曲的实践经验,深入地研究总结了中国歌曲中语言与音乐的相互关系。文中归纳出歌曲字调配音的30条原则和5则例外, 运用这些原则分析了《琵琶记·赏荷》等南北曲,最后还提出了“字调与歌音的向中性”、“字调的音势作用”、“南曲字调之北音化”等推论。他批评了某些新作歌曲或采用西方音调填词之曲不注意字调乐调分离背驰的现象,强调西方音节有轻重律,其音乐之律动“无不与文字之轻重相符”,而这和中国字调规律对歌曲音乐的影响是不相同的。
60年代初,杨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音韵学课。他认识到学习音韵学“应该有异文学方面的学习方法”,于是自己动手编写讲稿,“一开始就以结合音乐问题为重点。”70年代末经修改正式发表时定名为《语言音乐初探》(注:载《语言与音乐》一书,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1月北京第1版。)。文中进一步总结了汉语音韵、句逗与音乐配合的许多规律性特点,以及这些规律对中国音乐特色的重要影响,提出并奠定了我国语言音乐学的基本构架。例如,杨先生指出,虽然大多数声母、韵母各国所共有,但一些声母、韵母在我国歌唱中的作用与很多别的国家有所不同。汉语是单音节文字,声母、韵母的运用就不象一些多音节文字受其前后音节牵扯,比较自由。汉语每个字都可以有它的相对独立性,每一音节都能传达相当完整的意义,所以我们的歌词中有较多的由一个字构成的歌句,在歌唱中这个字往往会用上曼长、婉转的“拖腔”:需要时,还可以运用我国特有的“头、腹、尾”声韵因素,层次分明地曲折地传送歌音。独立存在的单音字,可分可合,便于造成各色各种长长短短的句和逗,形成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一字逗、二字逗……等变化复杂的歌词句式,这又影响到我国音乐的节奏特点。此外,还能利用双声、叠韵及叠字等等,来形成自己歌词写作和声乐表达上的种种特点。杨先生的这些见解非常深刻,对学习认知我国民族音乐的基本特点大有启迪。
文中还辩证地阐述了字调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作用和影响,认为忽视字调和片面强调字调都是错误的,同时指出国外和国内一些学者将我们的平仄理解为节奏的强音弱音或长音短音,也是错误的。对地方语言与音乐的关系,杨先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提出为了掌握地方音乐的作曲规律,应有计划地进行较全面的方言调查,包括方言录音、系统地进行古典诗文吟诵录音。可惜这一建议迄今未能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实施,象古典诗文吟诵调,经过“文革”十年浩劫,必然有很多已经消失,今天再也无法补救了。
文中以较多篇幅进行的中西歌词配音规律比较,也值得我们重视。如杨先生指出我们文字不以分别强弱为重点;我们歌曲的节奏,是为句逗的形式所决定,而句逗与西方诗歌的音步有许多差别。用逗,则节奏形式的发展可以比较自由,我国从古到今,能产生极其丰富的齐言的和长短句(杂言)的诗、词、曲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证明。文中类似的精采论述很多,无法一一摘引,有兴趣的读者应该认真阅读学习杨先生的原文。
杨先生开创的语言音乐学,不仅是研究音乐文学的基石,而且还成为民族音乐学中“一门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基础理论”。(注:参阅章鸣:《语言音乐学纲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年8月第1版。)
二、指出音乐在音乐文学中的决定作用
从古到今,音乐文学的形式变化从未停歇,音乐和文学这两个相互作用的因素,也都长期存在和发生着脱离音乐文学本体的独立趋向。文学独立的标志是用于吟、诵乃至阅读的“徒诗”(无乐之诗)产生,而音乐的独立则有无词之乐即纯器乐等形式发生。一种旧的音乐文学体裁词乐分离直至衰败消亡的同时,另外的新的音乐文学形式又崛起而代之。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曾说:
自《三百篇》降而骚、赋,骚、赋不便入乐,降而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降而以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则又降而为词。(明万历汤评本《花间集》叙)
他认识到词、乐的发展过程中会不断产生辞、乐不相配合协调的矛盾,从而导致新的歌辞体裁也就是新的音乐文学形式出现,推动音乐文学的发展更新。
但古来音乐文学的研究者主要是文学史家,多从文学的角度看问题而忽略音乐因素的作用,因而他们对辞乐关系的论述,例如对辞、乐产生孰先孰后的问题,关于音乐文学史几大阶段词乐关系的特点问题等,多未把握到要害和关键。例如,汉代毛苌《诗序》提出: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以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种看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如宋代朱熹《答陈体仁》(《文集》卷三十七)即说:
盖以《虞书》考之,则诗之作,本为言志而已。方其诗了,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以声依永,以律合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而作也。
当今许多音乐文学研究者也都沿用此说。于是“志—言—嗟叹—歌—舞”及“诗—歌—乐”的次序,便被视为情感表现由里向外逐渐强烈的固定模式,也被认为是从文学到各种表演艺术形式发生的先后时序。
又从古至今有不少论者主张我国音乐文学发展历程,有“先诗后乐,诗为主体”、“采诗入乐,依调作歌”和“倚声填词,言出于声”等几大阶段。他们所归纳的音乐与文学在不同时期几种相互关系,其实也是非常机械片面的,脱离音乐实践的。
与这些看法不同,杨荫浏先生通过民歌研究,一开始就捕捉到问题的关键,领悟到在音乐文学中,音乐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早在四十年代初,杨先生在《〈中国民歌〉序》(注:载1946年山歌社编《中国民歌》第1辑。又见《杨荫浏音乐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6月版。)中已得出这样的认识:“考证古代诗歌的学者,若忽略了音乐的方面,几乎不能达到透澈的境界。”1949年7月22 日他在南京中奥文化协会发表的演词《音乐对过去中国诗歌所起的决定作用》,则更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突出了音乐的作用。
杨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以下简称《史稿》)中,尤其是在探讨隋唐到宋代曲子至词的发展时,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进一步指出:“从远古到明清,诗词新形式的出现,常和音乐形式的新的创造,不能分开”(288页)。指出:“歌词形式的变化, 正体现了音乐艺术形式之发展”(287页)。这是因为音乐上既有继承, 又有发展;既有熟悉的旧调,又有新的发现;既有改编,又有新的创造。也就是说,音乐文学史上体裁形式的变化,主要不是“先诗后乐”、“以乐从诗”等词、乐配合方式的变化引起的,更重要的是音乐本身的内容形式发生了变化。
杨先生还指出,音乐上的新创造,“在历史过程中,一向是连绵不断地有着发展的。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新的音乐形式大量地得到了人们的注意,其歌词形式一下子得到了文人们的公认,就成为新的诗体、词牌、曲牌等等”(288页)。而新的音乐形式源于民歌, 也就是说,音乐文学新形式最终产生自人民大众,对此他很早就有过精辟的阐述(详后)。
《史稿》对各个时期音乐文学的记述,也明显地突出了音乐的特点和作用。例如,在春秋、战国部分,杨先生通过现存《诗经》、《楚辞》的歌词,探讨了相应的歌曲音乐的艺术形式。提出在《国风》和《雅》两类歌曲中,可以看到10种不同的曲式,诸如一个曲调的重复,曲调后面或前面用副歌,曲调重复中类似后代的“换头”变化,重复前总的引子和重复后总的尾声,以及两个曲调有规则地交互轮流联成一个歌曲等等。固然仅凭现存歌辞去推断原曲式难度很大,这些歌辞在记写过程也会有所删改整理,但从音乐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歌辞,仍是一种富有启迪意义的研究方法。《史稿》对《诗经》、《楚辞》的“乱”、“少歌”、“倡”等用语,也从音乐曲式的角度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杨先生的观点为音乐文学史的研究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突破。
三、突出民歌在音乐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肯定了音乐在音乐文学中的主导作用,杨先生还层层剥笋,探骊得珠,进一步找到了问题的关键——音乐的推进力来自民歌。历代统治阶级制定音乐的方针都是崇雅贬俗,力主复古,杨先生在《〈中国民歌〉序》中指出:“民歌活力的贯串于数千年来各类音乐之间,而造成今人之所谓古典音乐。”他还指出:“诗三百篇、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自来凡属诗歌一类的文学作品,在格调上无不受当时民歌音乐的推进。……诗学家们似乎都觉得自古而今,本国诗词,有着清楚的进化步骤,却很少人说起,在这进化步骤之后,是有着活跃的民间音乐为之推动。”
在《音乐对过去中国诗歌所起的决定作用》的讲演中,杨先生更明确地指出诗歌的最基本的来源是民歌。他说文人学士们根据民歌的原始或改变形式所填的词,一律被称为诗、词、或曲(都是诗歌),而且,可毫无例外的说,诗经时代以后的所谓诗、词、或曲,大多是些根据了民歌所填的词。例如:
屈原的诗歌作品,都是根据了楚地民歌所填的词。
乐府诗是在汉武帝采集民歌以后,文人学士们所填的词。相和歌是从演奏方法的观点,给民歌填词的一个名词;清商三调是从音乐调式的立场,给与同一些民歌填词的另一个名词;乐府诗里面的铙歌,是些根据了边区或外来民歌所写的词。
唐诗是一种节奏定型的民歌的填词。
宋词是根据了少数更古的民歌,多数隋唐以下的民歌和外来的曲调所填的词。
慢词是根据中、小令节奏放慢,音腔加多后所成之新调所填的词。
元、明、清的曲,与词一样,也是根据了民歌及外来曲调所填的词,若勉强要把它们与词分别开来的话,则可以说,曲是在时间之流中,词的引申与扩展。曲里面含有少数的词牌,但更含有很多词中所未曾有过的新牌子。这是因为曲在词后,经历了更长的时间,累积了更多的资料的缘故。
杨先生得出这样的推论:民歌是“唯一的核心”,把握这个核心,对可歌的音乐,对可歌的诗词,“便可以很容易的找出它们各自和相互间的因果关系来。我们因此可以说,过去的诗歌,诗三百篇,楚骚、乐府、唐诗、宋词、元及后来的曲,最初都是根据了民歌或外来曲调所填的词;后来许多不问音乐的诗人,他们但取前人所已填的词,作为自己写作时体式方面的蓝本,称它为诗律、词律、曲律等等;这种脱离原始基础的第二、第三、第四……级的诗体方面的转辗模拟,很不幸的,占据了中国整个诗歌历史的大部。我们可以说,在过去历史中,音乐抢先一步的进展,常引起诗歌落后一步的新创体式,音乐常领导着诗歌在前进。”
他还指出过去发展中的不幸,在诗歌方面,最重要的,“是不幸脱离了它的原始基础——音乐”;而在音乐方面,则是“不幸远远的落在时代的要求的后面。”
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杨先生身体力行,多次深入民间采访调查阿炳的二胡、琵琶曲,调查苏南十番鼓、十番锣鼓等民间传统音乐;而在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则采用了将各个朝代的音乐按民族音乐五大类分别叙述的体例,并将民歌放在最前介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史稿》指出人民群众大量创造民歌的过程中,也对流行的新旧民歌进行选择、加工,使其中优秀的、特别得到群众爱好的逐渐成为一种艺术歌曲“曲子”。《史稿》还注意到中国音乐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从汉代相和歌、清商乐以来,直至后来的戏曲音乐,常常利用同一曲调(曲牌)描写不同内容,抒发不同的情感,却又不会在音乐表达与内容要求之间造成矛盾,使音乐形式脱离内容。原来,人民群众在长期实践中,学会了一套变奏的手法,可以根据同一曲调的大体轮廓,进行各色变奏处理。同一曲调,在节奏的改变上,在旋律的细致处理上,可以千变万化,使之符合于不同内容的要求(197页)。
因此,各个时代音乐的新形式的形成,诗歌风格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就与这类曲子的不断丰富、不断改变有关,“那些以填写歌词著名的杰出的文学家往往正是那些在群众基础上简略、选定的新的歌曲形式的接受者与运用者”(196页)。
综上,杨先生精辟地指出音乐对诗词的决定作用,指出“音乐常领导着诗歌在前进”,而音乐发展则来自民歌的推进。他还指出各种新的音乐文学形式,并非都是文学家们的创造,它们是文学家们学习运用民间所创造选择的流行歌曲形式的结果。不难看出,古来许多音乐文学研究者没能把握问题的关键,他们的许多观点,如音乐晚于诗歌出现及“方其诗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等,脱离实际,只能给人予隔靴搔痒之感。他们不知道音乐的起源若不是早诗歌,至少也是一起诞生的孪生姐妹;不知道最早的“诗”就是歌,就是歌唱中的歌词;更忽视了在音乐文学史上是“音乐常领导着诗歌在前进”。
杨先生的精辟论述,还使音乐文学史研究中习见的“以乐从诗”、“采诗配乐”、“倚声填词”等几大阶段的划分方法显得非常苍白。如果深入研究古代文献史料,则不难发现这些词乐配合的方式,往往并存同一时期,在不同的场合条件下灵活地运用着。因此,以之作为时代划分标准是难免机械片面之嫌的。
杨先生正确地指出,对于现代民歌的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考证古代诗歌的进一步了解。(《〈中国民歌〉序》)这是一种引今证古、逆向考察的有效方法。现代保存的大量传统民歌,少数民族歌,其词曲结合关系、曲调的发展变化等,都提供了我们研究音乐文学史上诸多问题的生动参照。例如,民歌中的词曲从来都是紧密结合的,何曾有“方其诗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的普遍顺序与固定模式?
杨荫浏先生在音乐文学史研究以及传统音乐学音乐史学其它方面,还有很多好的观点和想法,是留给我们的富有启迪意义的丰厚宝藏,很值得我们努力学习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