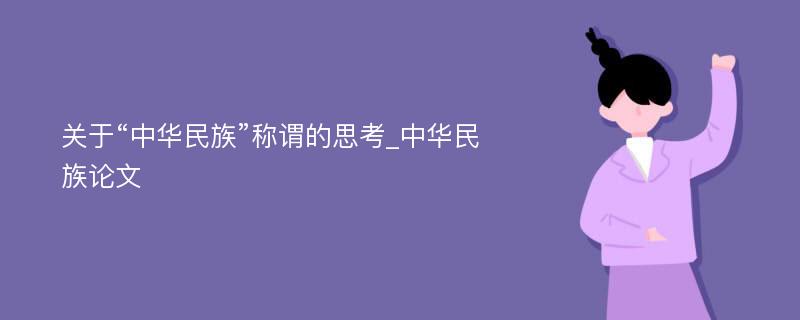
关于“中华民族”称谓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称谓论文,中华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族称是一个民族的称谓,一般是自称和他称的统一。在中国,目前存在着体现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个称谓,也存在着体现多元文化的56个民族族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便是这两个层次的辩证统一,中华民族这个称谓体现着一体,56个民族族称体现着多元。但是,目前国内民族学界对于“中华民族”称谓的内涵,有着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称谓在实践上也没有实现辩证的统一。以下笔者从对“中华民族”称谓内涵的讨论入手,谈一点个人不太成熟的思考,就教于学界同仁,并欢迎批评。
一、“中华民族”称谓内涵的诸家讨论
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称谓的研究,代表性的观点有:
谷苞:“目前,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的族名,同时,56个民族又有一个共同的族名,即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个名称的提出,并为全国各民族所乐于接受,虽然是近代的事,但是它的渊源却是长久的。”(注:谷苞,《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37页。)
费孝通:“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我用国家疆域来作中华民族的范围并不是很恰当的,因为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我这样划定是出于方便和避免牵涉到现实的政治争论。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注: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7 月版,第1页。)
陈连开:“中华民族的全部含义可以作如下归纳,即: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众多民族各有其发展的历史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有着长期在统一国家中共处并发展其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自觉地联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所以,中华民族的多元性与一体性的辩证统一,已有2000年的发展过程,只是在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这种极深刻的内在联系才被认识,从而上升为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和民族觉悟。”(注:陈连开,《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13页。)另外,陈连开先生在其《中华民族研究初探》一书中,也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以上三位大家是率先对“中华民族”概念内涵作出全面解释的民族学学者,其后,关于“中华民族”的全方位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关于概念内涵的解释,始终有所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上:1、什么是“多元”?2、什么是“一体”?3、 “一体”是否已经实现?由于在这三点上存在着争论,因此目前关于“中华民族”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大多都是依据自我的理解,或者依据费孝通、陈连开先生的表述进行论述。如“中华民族不是中国各民族相加之和的称谓,而是一个复合民族的称谓。它是指在中国版图这个共同区域里生息的各个民族的语言、经济、文化相互渗透、交融中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复合民族。汉族是形成中华民族复合体的主体民族,和各少数民族一样是一个平等的复合成份。”(注:许力心、冉景福,《论中华民族研究》,《天府新论》,1998年第6期,第86页。 )‘什么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指具有中国国家象征、由中国各民族共同组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与中国同义。”(注:吴宗金主编,《中国民族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5页。)“现在的‘中国’则主要是一个定义为具有56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政治概念了。因此,‘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应当表述为‘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的关系。”(注: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辩证》,《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页。 )中华民族并不是指汉族或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而是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统一体中所有的民族。(注:徐迅著,《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 第29页。)
由于对“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理解的不一致性,便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表述。在更多的书刊杂志和座谈讨论中,人们还提出了诸如下列的问题。“多元只包括56个民族吗?那么那些民族族属未定的人们呢?海外华侨、华人呢?”“多元只是民族的多元吗?多元的本质是什么?”“一体只是政治的一体吗?台湾没有统一,算不算?”“中华民族是否真的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这里列举的问题只是有代表性的几个,可见人们对“中华民族”内涵的定义,存在着许多疑问和模糊不清的认识,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作一全面准确的表述。
二、“中华民族”称谓内涵的个人思考
笔者认为“中华民族”概念内涵应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内涵可以宽泛一些,抽象一些,包含的内容丰富一些,不一定强求严谨;狭义的内涵就务必要严谨准确。因此上面列举的一些定义,作为广义的“中华民族”概念都是无可厚非的。下面谨以个人的学习理解,谈一下狭义的“中华民族”概念内涵。
1、“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内涵及其辩证关系
综合以上引述的诸家定义,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多元,首先是民族的多元,其本质是文化的多元,或文化的差异性。因为只有文化特质差异性的存在,才会有族际区别的可能性。其次是族源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特殊等等。“中华民族”的一体,首先是客观存在的国家的一体,版图的共有和完整,各民族血脉相连利害相关的不可分割性,各民族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致性,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相互交融与不可分割,其次才是在此基础之上,寻找各民族文化特质的共性,以及中华民族的大认同与凝聚力等,使之为“中华民族”实体的真正形成而服务。国家意识带动下的民族整体意识的形成,标志着中华民族已经“自觉”,但这种“自觉”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实体。“一体”绝不是主体民族对非主体民族的同化,而是各民族文化的互动,最终形成为各民族共有的“合文化”的过程,这个合文化的根本是各民族共创、共治、共有中华,国家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完全一致重合。这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自然发展过程。
多元和一体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始终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多元是以一体为前提的,是国家和民族统一条件下的多元;一体是以多元为载体的,抹杀了多元,否定了多元的存在,不尊重和保护多元的利益,就会危及一体的完整。“国家与民族是辩证统一的。民族是国家实体的社会基础,国家是民族社会的上层建筑。当国家代表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念与祖国意识相统一,并以爱国主义和具体民族感情为纽带,实现国家观念与各民族自我意识的高度统一。当国家不代表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只代表某一民族或某一阶级少数人的私利,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念与祖国意识必然分离,民族自我意识也就不会与国家观念相统一。”(注:龚永辉,《民族意识的调控方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第44页。 )中华民族的多元和一体往往在同一过程中相互作用。“在民族研究上,如果我们不关心和重视各兄弟民族之‘异’,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果看不见各兄弟民族的‘同’,也违背了中国民族发展的客观实际。在实践中,如果片面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不可分割性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忽视了各民族的特点和利益,或反过来片面强调民族特点与利益而忽视了中华民族的整体不可分割性与共同利益,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必然给中华民族和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发展带来损失和挫折。”(注:陈连开,《中国民族研究的识异与求同》,《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第247—248页。)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是辩证的统一,任何片面地夸大或忽视,都会给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带来损失,这一点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当前,国内外有一小撮民族分离主义份子,企图把“多元”与“一体”对立起来,否定历史,否定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否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不可分割性,我们必须给予坚决的批判。
2、 中华民族是近现代开始形成的一个带有总括性的民族和国家相统一的意识或概念
“中华民族”称谓的由来,陈连开先生已在其《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一个内在联系发展被认识的过程)》一文中,有了十分详尽而有力的考证,这里不再赘述。但文中对“中华民族”的定义,其中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把“中国古今各民族”都包罗进“中华民族”之中,二是认为“民族集合体”(费孝通表述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已经形成。
笔者不同意把“中华民族”概念上溯到千年以上的说法,当然也不同意那种把所有古代民族都包括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之中的说法。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定义都一致认为,“中华民族”是在近代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开始“自觉”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非常近代的社会语言中才出现的。既然是近代开始出现的,为什么又要把古代的民族包括进去呢?我们务必要牢记,民族是历史的民族,是时代的产物,任何民族都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忘记了这一条,“中华民族”的产生便无从谈起。我们追溯历史是为了摸清民族的根源,民族的轨迹,不割断历史,不使民族成为一个虚无的民族。但是当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整体结构发生了质的飞跃时,便有可能生成新的民族。新的民族脱胎于旧的民族获得了新生,尽管他继承了旧有的一切文化遗产,但他毕竟不再是旧有的民族,因为他发展了已有的,创造了没有的。虽然他“遗传”了先辈最优秀的一切,虽然他很象他的先辈,但他绝不是他的先辈,“中华民族”正是如此。
关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是否已经形成的问题。笔者认为非常值得讨论。因此,笔者用“中华民族”概念或意识代替了“集团”和“实体”。
历史上,中国长期处于一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状态,其间更多的斗争都来自于内部,阶级斗争、民族压迫贯穿始终。到了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针对的是整个“中华帝国”,因此这个国家所凝聚起来的所有人民都是西方列强的敌人,而西方列强也正是把所有的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对待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各族人民数千年积淀起来的民族感情得到了升华,那种深藏于人民内心深处的模糊意识终于被唤醒了,各族人民渐渐意识到,国家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各族人民应当不分彼此,联成一体,抗击共同的敌人,守卫共同的家园。正是在这种国家意识的带动下,“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开始“自觉”。“在各民族共同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中,出现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洋鬼子侵华的时候,我们各民族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一致感到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我们是一个根上长出来的,命运与共的人,能够坚持不懈地团结抗敌。尽管事实上中华民族里的人们来源不同,居住地点不同,语言有差异,但是有共同的所属,即我们在普通语汇里叫做自己人。因此,民族概念是活的,不是死的,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注:费孝通著《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1996年9月版,第24—25页。)
经历了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华民族的一体意识由对外的国家意识逐渐转化为自我的民族意识,并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笔者认为,对外国际关系是促成中华民族内部大认同的最根本的外部因素。“国际关系与民族——国家同时起源。”(注:Anthony Giddens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5月版,第5页。)这个整体意识是由最初的政治上认同,逐渐向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扩大认同发展。尤其是经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50年,中国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的认同不断得到巩固,经济文化上的认同进一步扩大深入,“中华民族”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中华民族整体概念和意识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民族实体已经真正形成。客观地说,形成民族的必备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尤其是各民族文化整合还有一条十分漫长的道路要走。我们应当准确地把握“中华民族”跳动的脉博,首先肯定“中华民族”意识已经产生,这个意识正在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各民族之间的较大差距,不主观、不超前,不要过早地认为“中华民族”实体已经形成。我们要吸取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经验和教训,以免在决策上出现重大失误。
3、“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民族实体已经形成, 而作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觉(自由)民族实体正处在形成发展阶段。
综合以上论述,笔者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清晰历史脉络,伴随着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在近代逐渐形成的一个带有总括性的民族和国家相统一的意识或概念。这个概念已被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这是一个民族、国家、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中华民族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意识,这就是民族统一的思想意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注:薛莹,《白寿彝教授谈中国民族关系和中国封建社会》,《群言》,1994年7期,第20页。 )“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民族实体已经形成,但作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觉(自由)民族实体,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走。目前,在“中华民族”意识的推动下,全体人民正在努力把一个抽象的概念向现实的民族实体推进,这已成为未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 “中华民族”的人民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内的所有中国公民(包括广大港、澳、台人民及侨居国外未放弃中国国籍者)
“中华民族”的人民基础也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中华民族不仅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内的所有公民,也包括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那么狭义的“中华民族”,其人民基础应严格限制在版图之内,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内的所有中国公民(包括广大港、澳、台人民及侨居在国外未放弃中国国籍者),不然我们会在许多国际政治交往中经常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地步。我们承认民族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现代国家中,民族的声音是以国家的声音为代表的,民族与国家的一致性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必须严格限定狭义的人民基础。如果我们任意扩大这个基础,必然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甚至可能出现新的排华事件,危及广大华侨、华人的生命财产,影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如果我们任意缩小这个基础,又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团结,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华族”(华人)虽与“中华民族”是同根生的民族,但目前,大多华族人已加入了所在国国籍,已经成为所在国的一个民族成份。“华族”已从国际间的侨民关系问题转变为各居住国国内的民族关系问题。他们经常要面对的是与所在国主体民族的关系,如何适应所在国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问题,而不是与“中华民族”和祖居国中国的关系。当然,对于海外华族在保持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维护自我民族利益,求生存,求发展等权利方面,中国始终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上支持的责任和义务。
另外,笔者之所以用严格的狭义,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定义,任何一个多民族的具有跨国民族的国家,可能都无法定义自己的国族。中国本身就有许多跨国民族,一些跨国民族的主体部分还在国外,倘若这些民族都被相邻的国家认为是自己的主体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便可能出现许多国际政治问题。因此,当今世界各国在处理此类问题时,都应慎重对待。实践证明,一般可行的方法,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方法是,鼓励那些跨国居住在外国的同一民族部分,更好地融入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而不是排斥与对抗,尤其反对政治上的分离主义。科索沃战争的爆发,有南联盟国内民族问题,也有阿尔巴尼亚国外同一民族的鼓励支持与挑唆,更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独霸世界一极战略的险恶用心,但跨国民族问题在其中的影响十分突出。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
三、“中华民族”全面振兴之时,当是“中华民族”真正形成之时,而实现全面振兴,需要充分发挥国家主导作用。
纵观历史,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国富民强的时代,都伴随着一次大的民族融合与认同。目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全面振兴的起步阶段,正处于形成发展阶段。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将是中华民族真正形成的根本保证。如果没有这个振兴,民族和国家可能在西方霸权主义的干涉下出现分裂,或者长期处于一种聚而不合,离而不散的状态。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首先使在政治上平等的各族人民,将真正实现经济上的平等。由于国力的强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将彻底改变,各民族文化也将依托强大的经济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同时,全国各族人民都将以伟大中国的公民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也空前繁荣,一体联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不可分割,各族人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已真正转化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总之,一切可能妨碍国内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因素已被彻底清除,因此,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真正的全新的民族实体便完全形成了。虽然“中华民族”的完全形成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还有待于“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但这是一个方向和目标,为了实现这个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就必须充分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
国家权力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独立性。国家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意识形态等多种手段,发挥其对内对外职能。对于“中华民族”意识及其民族实体的形成,国家同样具有无可替代的国家主导作用。“客观地说,除国家以外,任何一种社会势力都有可能对民族意识发生一定的影响,或者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民族意识调控。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势力,凡不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对民族意识的调控都不可能是彻底的,只能是局部的、零散的、不系统的。”“因此,要彻底实现良性调控,必须开动国家机器,由国家总揽调控大权。”(注:龚永辉,《民族意识的调控方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第42页。)
国家主导作用主要可在民族认同发生的横向扩展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如通过认同教育、社团推动、国家促进等手段,强化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目前,国内这种横向扩展已有很大的发展,如从小学开始就进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各种社团媒体大量宣传中华各族一家亲的思想,影视节目中“中华民族”的形象总是以中国各族形象为整体形象等等。另外代表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符号不断出现,如“中华民族园”、“中华世纪坛”等等,这些都是凝聚全体人民的文化载体,这些载体摆脱了某一民族的文化局限性,具有跨族际意义。中华民族的凝聚,不仅需要我们对历史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进行认知和认同,更需要我们对历史进行创造。笔者认为,以上横向扩展的手段,虽然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但这种国家主导作用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国家促进是一切横向扩展中最为有力的手段,这种促进应当更广泛更深入更有力度地进行。“在正常状态下,为了体现本国民族的利益,各个国家总是利用尽可能多和先进的手段(包括传播媒介)极力维护国内民族的统一,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以国家为界限的民族认同的促进工作:单一民族的国家极力维系原有的民族认同(同时也是维系国家认同);多民族国家则极力推进以国家为界限的新的统一民族的形成过程,为造就扩展新的民族认同而竭尽全力。”(注:王希恩,《民族认同发生论》, 《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34页。)“政府要注重符号导向,采取多种措施培养各族的爱国之心,使各族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要努力加强跨族符号语言,以国土意识代替族群口号。国家要考虑多宣传具有族际意义的英雄人物,考虑能够确实调动各族积极性而又符合各族切身利益的活动,还要考虑加强对族群感情和感情符号的研究。”“多民族国家只有促使各族遵守规则,自我约束,才能给他们更多的自由。文化多元并不与国家安定矛盾,关键在于如何不使文化现象政治化,不使文化多元变成国家多元,不使政治和经济问题转化成民族问题。目前,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是由一个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对于民族关系起着关键的作用。同时,只要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能够真正彼此尊重感情,沟通文化符号,关心对方的切身利益,双方就能构筑起具有积极意义的互动场。”(注: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辩证》,《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页。)
实践证明,在尊重和肯定各民族及其认同存在的基础上,重新培植与国家认同一致的民族认同,促进其发生,推进其扩展,是符合民族发展规律的。这种顺应民族发展规律的国家促进方式,在多民族国家是行之有效的。国家培植和扩展民族认同的终极结果是和国家认同的重合,并无意抹杀多元文化,而是要使多元文化成为全体人民共有的财富。因此,充分发挥国家主导作用,是中华民族凝聚形成,国家意识转化为民族意识的有力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