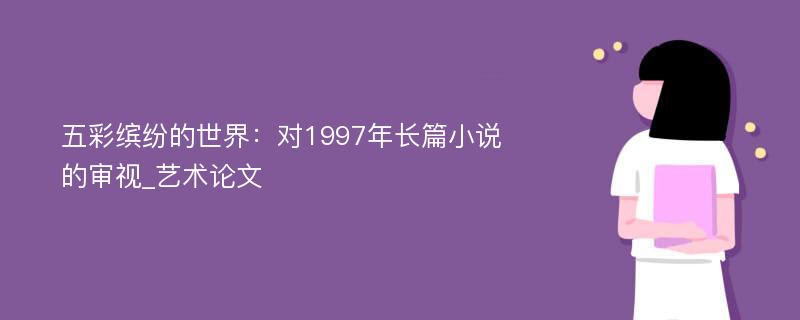
动人的七彩世界——1997年长篇儿童小说扫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人论文,儿童论文,世界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五次作代会后的1997年,长篇儿童小说创作中相继出现的四种文学景况,给儿童文学界带来了新的灵动与气息,在构筑新的文学气象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新的审美思考,对这些文学景况,我们做如下扫描:
第一,一些在儿童文学创作研究领域中有所收获的作家,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长篇儿童小说——现实生活的动人之处,是辩证的光辉与诗意的美丽;典型环境中人物形象的优美,是性格的真实与心灵的深刻。
因为现实生活永远像春天一样灿烂,所以,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必将不断地培育出崭新的艺术花朵。在我们有限的阅读中,继秦文君的《男生贾里》之后,朱效文的《青春的螺旋》(少年儿童出版社)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典型环境中的人物性格所含纳的艺术韵味与审美内涵,标示着现实主义的一种艺术力量。作家对于题材的深层次解读,对人物关系的对比与互动的设置,对情节所包孕的诗情的开掘,架构出作品结构的整体美,使文本语境流淌出一种清新的韵致。作家注重主要人物性格的刻画,对构成人物性格历史的情节的审美透视达到了艺术真实的层面,比如砸伤凌霄之后不断推进的情节,在人物关系、情感力度的传递与把握上显示出审美的品位。在时代精神的烛照下,凌霄的性格在多个侧面的状描中达到完整,在幻想与现实的撞击中诗意地成长为跨世纪新人。
梅子涵以女儿为原型编述的《女儿的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是一部具有审美特征的作品。作品的主人公梅思繁,虽然不是虚拟的典型化人物,但她具有艺术的真实,她生活的空间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多重的组合。当作家想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下女儿童年的真实时,就会自然地摈弃概念化和非理性的东西,也就必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审视点,在学校、家庭、社会关系的构筑中凸现女儿成长的真实,实现如黑格尔所说的——人的完整的个性。作品中的梅思繁也许并不是时代新人的典型,但她确实是具有艺术韵味的“这一个”。《女儿的故事》在叙事语态上是有特点的。简约的白描,叙事话语在重复推进中的节奏,人称之间的转换,显示了对事物具有空间感的把握,这是出于作家心灵的真实,其审美指向是走进和谐。
黄蓓佳在《我要做好孩子》(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中,成功地刻写了一个具有审美价值的当代母亲形象卉紫,她的浮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女儿金铃面临着升初中的严重课题。在卉紫看来,考不上重点中学就考不上大学就失去未来。她的这种心灵状貌,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的教育应由应试转变为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上大学不应成为唯一定向。因此,渴望女儿成材的心态,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代父母对商品经济发自心灵深处的恐惧,是生存意义上的现实需求而不是理想的光辉。当她的愿望与女儿的现况冲突时,心灵恐惧就以不同的浮躁形态表现出来。对儿童作为一个成长着的个体,卉紫没有科学认知。儿童的一些小毛病,要靠因势利导和个体的成长来克服;要想缩短这一过程,只能像作品中的孙奶奶那样在相互信任中取消代沟,给孩子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舒展童心。当女儿遇到困难时,卉紫怀着对女儿的爱给女儿加压,致使女儿在不同境遇中说谎。作为卉紫性格表征的浮躁,是变革中的现实关系的真实摹写和典型环境中展示的艺术真实,是一种美的形态。
在解析上述作品时,我们发现文本中有的人物的命运流程及其表现形态,还缺少统一的审美观照;有些事件的状写不够简洁,还有打眼的可删节的枝蔓;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集中概括的典型化过程中,情节与情节还没有构架出应有的诗意与灵运,对艺术语境的营造是一种消解。
第二,一些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作家加盟儿童文学,推出了他们的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现实的深刻变革,拓展了作家的心灵视野,作家心灵中的诗意形象是现实的赋予;奉献给孩子们的,无论是一份幻想般明丽的少年岁月,还是一份现实般迷人的命运轨迹,都是来自生活的诗与歌。
毕淑敏的《雪山的少女们》(明天出版社)描写了西藏阿里高原上一群年轻的女兵,作品中的“我”、河莲、果平、小如、小鹿构织出一组当代共和国女兵的群体雕像。对冰川拉练、雪野露宿、以及最后送别战友等典型环境中细节真实的状写,在人物关系结构中昭示出来的性格内蕴,艺术地传达了凝聚着民族精神与时代内涵的革命乐观主义,形象地抒写了壮丽的理想所焕发出来的精神力量,作品为青少年朋友展现了一个没有被金钱污染的圣洁的精神家园,这对于青少年心灵的丰富与充实,对于理想人格的构架与塑造,有着积极的审美意义。
张炜的《远河远山》(明天出版社)给读者的审美感觉是沉重压抑的,主人公“我”的性格塑造丰富而凝重。“我”的沉默不语,是不能与外部世界交流而转向内心,与自我心灵对话形式是找到任何纸片就写。当母亲病故、被继父撞残的永立自杀后,“我”离家出走——这是一种性格的能动指向和对既定生活秩序的否定,开始了不断地寻找写的人,在山区平原,在城郊省城,实际上在寻找心灵相通的人,也是在寻找与外部世界的对话过程中确立自我价值,展示“我”心中的善以及对美好的追求,认定生命形式是写作。在经历了一个个生与死的搏击、有认识价值的事物在现实重压下不断的粉碎中,“我”的人生结局既悲怆又幸运。这部作品不是理想主义的颂歌,却歌唱着心灵中对美好的向往与探求的艰难,它艺术韵味的深长,带给我们一个心灵中有亮色的独特少年形象以及一份沉重的思考。
王安忆的《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明天出版社)从三个审美切入点叙述故事,显示出结构意识的力度。这样的叙事样态,对青少年阅读定势也许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打破。作家对朦胧而又真实、动人而又痛苦的女孩情感历程的状描,具有真切逼真的艺术感染力。有些情节,比如资本家几房妻妾在文革中的尔虞我诈,人物关系的构成、场景的转换、矛盾冲突的操练,显示了作家的艺术直觉。
当作家遵循典型化的原则描写现实时,现实主义就呈现出开放的、无边的、运动着的形态。作家写什么是作家的自由,是作家心灵无限性的一种表征。但长篇儿童小说的创作有其固有的规律。当我们以历史的美学的标准来读上述作品和其他同类型作品时,我们想到:倘若作家是以成人的眼睛、成人的思维,来描绘处于变革时代的青少年,那么小读者必然被作家没有儿童审美情趣的文本所困惑。倘若作家的生活积累浅显而叙事欲望强烈,随意介入语境,用非真实的东西代替现实的鲜活,那么这样的文本,小读者必然难以卒读。倘若出现在作家笔下的生活,没有经过选择和提炼,没有经过作家眼睛的审美过滤和心灵的滋养孕育,而只是一些原生态描述,那么文本语境就不会成为艺术的审美现实。
第三,长篇儿童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些新作者,他们有过一定的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但长篇小说文本的制作尚属首次——内容在叙事话语中流淌,形式在内容流淌中完成;凡是能扩展读者人生视野和审美空间的,都是美的事物。
也许因为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也许因为有过一定的儿童文学其他样式的写作实践,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5 月出版的一套“花季小说”中的新作者,在其第一次长篇儿童小说创作中呈现出的审美特征,昭示着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现实主义。
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都是从自我的生命历程开始,人的心灵现实是外部世界的能动反映。一些新作者在长篇小说文本操作中,对于艺术个性的探求,是经过真诚地面对自我心灵世界,真实地也是理性地再现记忆中的历史真实,来实现艺术地把握世界与人生。他们注重于对构织青少年时代的往事的叙事完成,文本因而具有自叙传的意味。在拒绝自然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叙写中,显出因为生活积累的并不深厚、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制作功夫的并不老成——而造成的作品密度疏松,因而一些作品尚达不到典型环境的理想架构。
一些新作者在文本的叙事性操作中,对源于生活的情节的艺术把握,昭示出现实主义的美学力量,流淌出心智的灵动与文思的顺达。比如,在张洁(上海)《敲门的女孩子》中,“月亮之死”是具有文化含量的,人物关系构建出了诗情,情节的张驰见出功力。在殷健灵《玻璃鸟》中,“我”与同学时常到公园摘鲜花扎成束,插在老师家门把手上,以表达对同性老师的爱,这成长着的青春令人心灵颤动。在王蔚《外婆的无忧岛》中,小青从船上游到荒洲,走进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天地:失去了楼房切割的真正的天空,童话中蛋黄似的夕阳,会飞的红虾,刻写了一个美的况境。在章红《青春门》中,对“青春像一只鸟”的散文诗般的抒写;对校园明星那阳光一样的眼睛的钟爱,以及黎巧儿被对方称为“现代的简爱”时,心灵的泪水所标示出的青春生命力度。在上述情节以及简平《一路风行》、曾小春《蓝色故乡》、萧萍《春天的浮雕》中的一些情节,是塑造人物性格的有机构成,也是文本语境的艺术因子。
要实现恩格斯提出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富有诗意的独特艺术情节,只有环环相扣地流淌在文本中,作品才会有可读性,人物才会真实地站立起来。一些新作者文本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尚未达到典型形象,其原因在于此。
第四,一批在校的学生作者,推出了描叙青春的长篇处女作——人生是故事是艺术,青春是激情是体验;状描当代生活图景和青少年心灵风貌的作品,是人生形式的一种表达。
97年春天,《花季·雨季》在北京开了研讨会。97年7月,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自画青春”丛书:芦淼《福物祭旗》、肖铁《转校生》、米子学《闹心》、许言《黑白诱惑》、邢抒生《摇滚猫乐队》、朱佤佤《发芽的心情》、刘伟《迷彩》、顾捷《火之晨》、陈朗《灵魂出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人说:“让学生写青春,对他们全面发展不一定有利。”还有人说:“没有压力,石油不会从地下喷发,青少年也不会成材。”还是让我们来看他们的作品,向我们证明着什么。
也许,当我们从艺术的完整性来把握文本时,会感到作品并不老到,人物关系的构置还欠精致,为了保有一个学习时段的完整拉长了叙事时空,消解了情节的生动与故事的密度,语境艺术空间的架构尚欠力度;但这些学生作者对于改革时代学生心态的把握,对于处在不断变革的社会生活中师生关系的有机描摩,对于校内与校外世界撞击与交叉的观察认定,是贴切到位的,有许多新美的珍珠般闪光的东西,是已成名作家所无法感知的。他们从自身的成长出发,对内在心灵的开掘,对情感历程的体验是深入细腻的,他们审美视野中的校园环境具有某种典型意义。
也许,当我们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标尺来衡量他们的文本时,他们塑造的人物还不一定能达到新人形象的层面;但由于他们尊重来自生活的真实,生活本身就赋予他们一种表达方式一种艺术力量,现实主义使他们笔下的人物成为当代中小学生一种或几种类型人物,这些人物的真实与鲜活、力度感与诗性,使我们在审美观照改革时代的文学时,不仅读到了校园生活蓬勃着的诗情,也感知了将成为跨世纪一代新人的心灵状貌、理想追求、以及他们守望精神家园的那份执着与沉重。
这些学生作者自画青春作品的出现,给儿童文学界吹来了一股新鲜气息。他们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那种独特的心灵感受是其优势所在,他们的作品是对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补充。这使我们想起了恩格斯的主张:真实地描写现实。由于这些学生作者真实地描写了心灵中感知的生活,他们的作品成为他们生命的有机构成。因此,“自画青春”丛书、“花季小说”,荣获了奖掖文学新人的97年度第8 届冰心儿童图书奖。
扫描1997年长篇儿童小说,一批张扬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新人和长篇小说新作家的涌现,令人鼓舞;但创作的现实景况仍没有达到一种理想状貌。只要作家努力学习唯物史观,贴近时代,对人生对世界作出典型化的形象传达,就会在艺术创造中实现美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