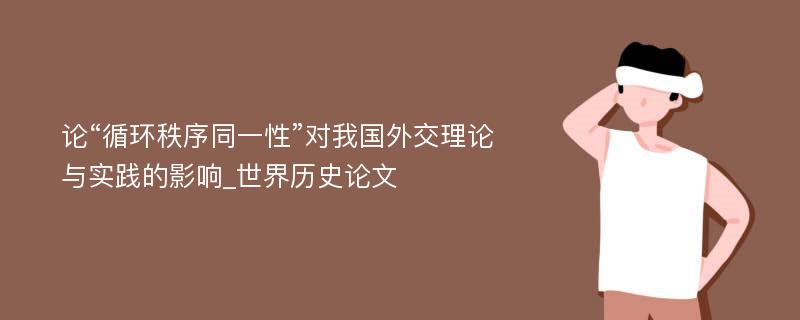
论“圈序认同”对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外交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9)12-0047-11
[修回日期:2009-07-19]
一 绪论:为何要研究圈序认同?
(一)从当代中国外交变化谈起
进入21世纪,中国外交出现了不少政策上的变化,中国不再提或很少提及“第三世界”,转而提“睦邻外交”、“周边外交”以及“大周边外交”;中国很少提“友好关系”、“战略同盟关系”而大提“战略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战略互惠关系”等;中国很少提世界新秩序,而是提建设和谐周边、和谐亚太、和谐世界。凡此种种,多少显出中国外交中的一种由近及远、认同递减、文化外推的精神现象。这种现象,我们不妨称之为“圈序认同”、“圈层思维”或“圈层意识”。它是古代以来的中国人观察世界的一种潜意识,构成了几千年的中国交往文化。
由于中国近几十年的持续迅速发展以及目前国际格局的显著变迁,世界越来越有兴趣观察与关注中国,了解中国向何处走,何以能够和平地发展。过去,我们从中国的和平主义文化来向国际社会解释,这对于化解“中国威胁论”,争取国际友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功莫大焉。现在,某些西方学者已不满足于和平主义文化的解释,它们希望从新的角度来寻找中国外交战略的文化基础。①东方和平主义主要源于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如果还能够对中国当代外交发挥作用的话,那么洞察儒家思想与东方和平主义之间的桥梁是什么?对于国际合作和国际义务等方面的问题,中国人是以什么样的思维来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呢?西方人可能正在卓有成效地研究这些问题,而中国学者也应拿出自己的大胆想法来。本文希望以圈序认同这个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假定方法,来重读古代中国外交的思维模式。
中国崛起其实是亚洲崛起的一个缩影。无论是中国崛起,还是亚洲崛起,都可视为东方文明的世纪性崛起。研究当代中国外交时需要研究中国人世界观中的圈序认同成分,研究东亚对外关系时也需要研究作为整体的东亚在世界观方面的圈序认同现象。从日本首先提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开始,东亚先后提出了“东亚经济圈”、“大中华经济圈”、“亚洲经济圈”,等等。而西方则常常提“经济共同体”、“经济区”等。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人②惯于以圈层思维来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并希望在这种差序结构中实现自身的安全感、经济繁荣与政治抱负。笔者这里冒昧提出一个假设,即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水平为何落后于欧洲与美国,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近代以来东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崩裂与混乱,迄今为止既未整合出一个类似于古代东方国际体系的文化差序结构,也未形成类似于欧美的完全同质性化的文化结构,而习惯于圈序认同的东亚人既建立不起来古代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也建立不起来欧盟模式的经济一体化。东方人是否在忙于从事一项不服水土的事业?其经济基础与文化结构是否冲突?
(二)“圈序认同”是中国的特质吗?
在民族国家体系的大时代里,任何民族都以自我利益为国际行为的基本出发点,都把本民族国家利益置于观察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民族的外交文化中都有着圈序认同的成分。这是外交文化研究中的普遍性问题。然而,中国的圈层意识或圈序认同似乎更加独特。对此,梁启超曾有过一段精辟的阐述:“人类莫不有同类意识,然此‘意识圈’以吾身为中心点,随其环距之近远以为强弱浓淡。故爱类观念,必先发生于其所最亲习,吾家族则爱之,非吾家族则不爱,同国之人则不忍焉,异国人则忍。由所爱以‘及其所不爱’,由所不忍以‘达于其所忍。’是谓同类意识之扩大。”③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圈层意识是不断扩大的同类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仁与爱的波浪式外延的过程,它不同于西方社会中以利益为中心、以民族间竞争为重要内容的同类意识。
那么何以形成中国特色的圈序认同呢?这里有很多的原因。除却梁启超先生从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和仁爱外推的角度加以阐述的因素外,一个更加基础性和物质性的原因是,古代中国独特的国际交往体系与民族间关系大不一样。古代中国较其他民族更加自成一体,其组织的国际体系更加封闭,其文明历史更加悠久且连续,其中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礼治文化更加发达。④另外一个原因是东西方世界的外交实践情况迥异。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外交圈不像西方外交圈那样曾经多次转移中心,而是几千年来呈现出一元性的特点,“始终稳定地以中国的中原皇朝为中心”。⑤因此,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中国传统外交文化中的圈序认同更加明显,其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也更大一些。本文就中国外交文化中的特殊性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圈序认同的基本含义
笔者提出“圈序认同”一词,并非想达到什么标新立异的学术目的,而是用它指代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中一种挥之不去的现象,即中国人处理外部世界的关系时,倾向于以一种自我意识为中心的、又有等级层次的、有序有礼外扩的认同序列来定义交往身份,确定活动范围与力度,并试图通过这种圈式交往的无限演进终致天下一统。这种思维模式或多或少存在于每个中国人、每个家族、每个王朝之中。
对于这种现象的阐述,古已有之。早在周朝时代,中国人就习惯于这种圈序认同:“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⑥这种圈层的核心是道德或宗族的一致性:“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⑦近代中国与世界体系碰撞之后,随着中国自衰落后又重新崛起的步伐加快,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加强了对中国社会及中国人世界观的研究,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人倾向于将对外关系想象为中国国内社会与政治秩序原则的外化,中国的对外关系也就相应具有等级,如同中国社会自身一样。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中国形成一种对外制度,大体相当于欧洲形成的国际秩序”。⑧中国的这种世界秩序的认同基础,其实就是五服制度所包含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有等级的、由内及外的国际认同模式。美国学者孙隆基较为明显地指出了中国人的圈层意识:“中国这个‘大圈’,在处理外面世界时,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按亲疏远近的关系来将它划分‘层次’的,而这种层次又常常变成一种等级序列。”⑨
可见,古代中国人的圈序认同,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认同的出发点是观察者的价值和利益(上升至民族层次上,就是优越的中国文化),以此来确定观察者与世界的关系,它是所有圈的中心。第二,这个圈式体系是由多个圈组成的,各个圈之间都贯彻和落实一以贯之的文化认同。第三,在圈层体系中,主体对于客体的认同度是由近及远不断递减的,亦即身份也越来越有差异。第四,中国人不是固化这种差序,而是通过这种差异的形式来推己及人,不断地把自己的先进文化渐次向外界扩大,最终达到天下归仁的境界。
二 两种不同的认同思维:东方的圈序认同与西方的二元认同
圈序认同并不是中国人世界观的全部,中国人也有二元认同(如华夷之辨等),然而,圈序认同的文化本源、制度保障及实现形式都有其系统的表达,因此它能够成为中国古代交往文化中的主流思维模式之一。反观西方,虽亦有多种认同类型,但地位突出的还是二元认同。即便是二元认同,东西方也有明显的不同,东方强调里与外、有与无、现象与实质的“将无同”,侧重讲“二元相成”,与基督教的二元相背与二元对立有很大的不同。⑩实际上,这种“二元相成”由于强调本质一致而形式不一,而包含了“圈序认同”的成分,我们宁愿把“二元相成”所体现的“本质的现象连续体”纳入圈序认同的范畴。
(一)西方观察世界的二元认同
西方观察世界以二元对立和二元相抗为主要思维旨趣。这种模式强调我与非我、敌人与朋友、光明与黑暗、教友与异教徒、民主与专制、科学与愚昧,等等。它的哲学基础是二元论,它的宗教哲学是基督教文化,其思想的来源可能与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有关。关于后者,许倬云先生曾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认为两河流域的泥版文字及其反映的内容“呈现对立的二元,彼此互斥而不能相容。二元论的思维,在两河思想体系,例如在波斯发展的祆教及后来的摩尼教,都是善恶两分的思维模式,颇继承了古代两河神话中神魔相争的传统”。两河流域文字中其中不乏救回春天与生命的英雄的故事,“凡此种种救赎与复活的主题,不仅在后世基督教教义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许多启示性宗教的特色”。(11)而西方外交思维中由于承载了基督教传统中的上述二元认同思维,因此无论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发展与合作,都大致摆脱不了对立的逻辑。
西方的二元认同思维强调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根本差异。西方著名的认同理论研究者、美国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把认同分为实体认同、类型认同、角色认同与集体认同四种,前两种都是以肯定自我、排斥他者为本质规定的。角色认同中区分了朋友、对手、敌人三种认同,但在分析过程中突出的还是朋友与敌人。集体认同是指把他人当做自己人、一家人的感觉,目前,这种认同模式只有在欧盟等少数几个安全共同体中程度不同地存在,集体认同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存在一个共同的敌人,且尚不构成目前认同政治的主体。可见,西方认同理论一般有一个二元对立的思维预设。
要形象地了解东方与西方在认同思维上的区分,一个很好的比喻是费孝通先生60年前关于西洋社会与乡土中国的对比。他讲得很形象:“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12)费孝通先生把西方社会的关系格局称之为团体格局,把中国社会的关系格局描述为差序格局。如果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之思维基面的特征,可谓二元认同,在这种认同模式下,团体内部是平等而团结的,团体向外有清晰不二的边界性,这种边界性意味着对于重视正义与非正义的分辨性,正与反的对立性。而中国社会的思维基础则呈现出明显的圈子化的特点,“圈序认同”一词虽不尽准确,但可能比较形象。一方面,中国人都以自己为圆心,形成大小不一的圈子;另一方面,每个人都不断地伸缩自己的圈子,尽量把圈外的人吸纳进自己的体系中来。前一方面重点在“圈子”,后一方面重点在“化”。这个“化”,在孔孟二圣那里,主要理解为“推”,即推己及人,“善推而已”。这样,圈序认同之下的中国人就不能像二元认同的西方人那样泾渭分明地自待世界,对于西方人眼中的边界、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持有一种模糊、变动的观点。相对而言,中国人的圈序融通思维长于求善(德性),而西方人的二元对立思维则长于求真(知性)。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在其势力可以达到的区域固然可以造就一个近似和谐的社会,但是对外交而言,由于缺乏工业文明支持,虽有天下的眼光,但只能偏安于东亚一隅。而西方人则由于在探索知性方面的优势,最终开出了一个繁荣的科学发达的局面,并造就了以主权制度为核心的国际制度体系。
(二)圈序认同与二元认同之间的相异点
圈序认同与二元认同是中国人和欧美人观察世界的两种重要认同模式,它们都以本民族、本国家为观察的中心,都以文化优越作为潜意识,都致力于强大的国际制度和世界体系来实现自身的世界主义理想。然而,两种认同模式之间仍然有着许多重大的区别。
首先,圈序认同更加体现伦理本位,而二元认同与宗教本位息息相关。(13)文化是社会的灵魂,中国社会文化从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本位的,“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14)因此了解中国人观察世界的圈序认同不能离开对于人心的洞察。圈序认同实际上就是讲“心”的认同,以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来定下亲疏关系,定下对外交往的认同感觉。由于在中国人看来,社会关系是由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由近及远的各种人伦关系组成的,而且整个世界也是由这种伦理关系拟人的,因此,圈序认同其实就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归结与抽象而已。然而,西方社会则不同,其本质上是宗教本位,欧美社会主要是基督教社会,基督教文明的核心是希伯来文化,而希伯来文化是强调二元对立的,强调正义战胜邪恶,自由战胜专制,光明战胜黑暗,企图依靠强力来实现一种观念的胜利。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有着希伯来文化中二元认同的影子。
其次,圈序认同拥有丰富的进程导向,而二元认同含有明显的结构导向。在中国外交文化中,各圈的内容与序列不是长久不变的,相反则是内外融通的。虽然孔子在《春秋》中提出过“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把周天子作为圈序认同的最内一层,把鲁作为第二层,把诸夏作为第三层,把夷狄作为第四层,但并不以周礼而否定夷礼,常常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夷夏移位,故韩愈有评论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至中国则中国之。”(15)这从最初的意义上看,圈序认同完全是以一种变化和辩证的文化视角来划分世界的。梁漱溟也谈及圈序认同中的人并不是等级森严,互不来往的,而是“它由近以及远,更引远而入近;泯忘彼此,尚何有于界划?”(16)受到圈序认同的影响,中国人总是以发展的、辩证的眼光来处理外部事务,这种变动中的圈序认同模式影响了儒家文化圈的诸国。它们在处理多边主义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进程取向的多边主义,其核心是“交感而化”,即“通过交往互动而导致利益和身份的渐进变化”。(17)而西方国家则较多地从固化的结构出发,从二元对立的结构出发,或者从结构化了的制度设计出发来处理各种关系。
最后,圈序认同的潜在政治哲学理念是天下一统、远近相宜,而二元认同的潜在政治哲学理念则是国家至上、对抗思维。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圈序认同,表面上由近及远的远近亲疏,实质上是要在远近亲疏中达到一种仁与礼的最终一体,把近的亲与善主要通过感化和礼治的方式推向远方,最后达到圆满,形成仁治或礼治的天下(而二元对抗思维则主要通过优胜劣汰甚至武力征服的方式统治对方)。无论是孟子关于仁的递次外推学说,还是与此相对应的荀子关于礼的递次节制学说,都从一个侧面发展了孔子的仁礼思想,形成了“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境界。(18)反观西方世界的二元认同,则强化国家与民族的竞争兴废。正如梁启超先生评论的,若明乎中国人的“同类意识”之“举斯心加诸彼”(《孟子·梁惠王》),“则知儒家之政治思想,与今世欧美最流行之数种思想,乃全异其出发点。彼辈奖厉人情之析类而相嫉,吾侪利导人性之合类而相亲。彼辈所谓国家主义者,以极褊狭的爱国心为神圣,异国则视为异类,虽竭吾力以蹙之于死亡,无所谓‘不忍’者存……(而)同类意识,只有日求扩大,而断不容奖厉此意识之隔断及缩小以为吉祥善事”。(19)简言之,若从民族文化与政治哲学背景看,圈序认同强调了天下的渐次礼治与圆融和谐,而二元认同强调了国家的新陈代谢与强权政治。
当然,正如文初所言,圈序认同与二元认同均不能代表中国与西方认同思维的全部,中国历史中的某些时段不乏对立性二元认同的影子(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而西方历史中的某些大国的外交行为中也偶有圈序思维的成分(如俾斯麦、丘吉尔的同盟体系或三环外交,尽管与中国的圈序思维仍有差别)。然而,圈序思维与二元思维毕竟分别构成了中国与西方思维模式的主流。它的确影响了传统中国对于国际体系和外交战略的建构,并仍对今天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产生作用。
三 圈序认同及其在中国外交上的历史显象
较全面地理解圈序认同,除了与西方人擅长的二元认同相比较之外,还要认识它在中国生成的基础与背景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的显象。
(一)圈序认同的基础与背景
1.圈序认同的物质基础是地缘与安全因素
在中华民族结束氏族公社阶段向中世纪过渡的历史时期,由于中原文明的基轴是大河农业文明,这种文明较海洋文明更加受制于血缘宗族、(20)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因素,因此,地缘中心意识与个体安全感的结合成为古代中国人观察世界时的圈序认同的一个重要基点。安全感是圈序认同的一个出发点。个人由于不能依靠自身获得安全感,因此,必须有一个集体的安全感,但是,这个集体不是平等组织起来的集团,而是根据圈序认同建立起来的集体。正如孙隆基指出的,“事实上,中国文化本身就排除了将其他的‘人’当做同等人类看待的可能性。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人,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借‘自己人’这个圈圈来支撑起自己。他们即使在同胞之间也在划小圈圈,因此在面对‘非我族类’时,就会划出一个‘大圈’。唯有如此地躲在自己人的圈中,中国人才会感到安全”。(21)中国人的这种圈层意识是有物质基础的,这个物质基础就是地缘经济因素。中原是大河农业文明,经济较为发达,周边多为游牧民族,经济较为落后,因此出现了以经济文明为基础的差序结构,从而治理上也出现了“五服”、“九服”等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天下治理结构,经济文明较为发达的中原人居于天下的中心,而经济文明落后的边疆人则居于天下的边缘。对于中原人而言,中原人是自己人,由近及远地形成了亲疏关系和差序的认同。由于经济发展中心是在变化的,而且王朝也是兴衰更替的,国家的安全重心也随着政治中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圈序认同的物质基础也不断变化,并不构成圈序认同的恒常因素。
2.圈序认同的核心是文化中心意识与礼治序列
中国人讲究圈序认同,除了地缘方便、血缘亲疏和原始安全感等初始性因素之外,文化上的优越感是一个突出的甚至是根本的因素。中原地区既是统治中心和物质发达地区,也是开化较早、文化程度较高的“文明”地区,比起周边茹毛饮血的野蛮民族而言,自然有一种文化优越感,而千年以降则形成了费正清所谓的文化最优的华夏中心主义。有中心,就有半中心、边缘、半边缘,随着文明与文化程度的递减,中国人倾向于把文化同质性最强的民族或地区视为自家人,把文化同质性次之的视为近邻,再次则是可以归化为自家人的外人,最后是蛮夷。可以说,圈序认同的核心是文化差序。但是,如果仅仅把圈序认同简单地作为文化认同,则是不对的。在古代中国的语境里,圈序认同中涉及的文化其实是伦理本位的,与德治或礼治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这种圈序认同的文化从精神的角度来说是德,从形式的角度来讲则是礼。德主要对于中央而言,着重讲厚往薄来,以德治天下;礼主要对于臣属而言,着重讲安于名分,履行等级。总之,圈序认同影响下的天下体系,是由“本不相干的方位观、层次观和文化的夷夏观交织而成。天下由诸夏及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即诸夏,为诗书礼乐之邦,在层次上居内服,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形同鸟兽,在层次上属外服,在方位上是四夷。方位和层次可以以中国为中心,无限地延伸;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也可以无限地扩张。最后的理想是王者无外,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于大同”。(22)
3.制度背景是朝贡国际体制
礼只是圈序认同制度化的一种形式,具体到天下治理上,还有一种更为世俗化和政治化的制度形式,即我们常说的朝贡体制或封贡体制。在周朝时期,朝贡制度和五服制度、九服制度,其实都是来表明离天子远近的一种统治制度和理念。比如,方圆每隔五百里依次称之为侯服(岁一见,贡祀物)、甸服(二岁一见,贡嫔物)、男服(三岁一见,贡器物)、采服(四岁一见,贡服物)、卫服(五岁一见,贡材物)、要服(六岁一见,贡货物)、蕃国(世一见,贡贵宝)。(23)在明清时期,中国皇帝对于各国来朝的次数进行了限制,这种限制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认同关系。明太祖曾下诏:“古者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番邦远国,则惟世见而已……今高丽去中国稍近,人知经史文物礼乐,略似中国,非他邦之比,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或比年一来……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渤尼、三佛齐、暹罗斛、真腊等国,新附远邦凡来朝者,亦明告以朕意。”(24)从此,朝鲜成为中国圈序认同外国的最内一层,可以一年三贡;尔后便是琉球,两年一贡;第三圈则是安南、占城、暹罗、爪哇、哈烈,三年一贡;撒马儿罕、鲁迷则更次之,为五年一贡;至于日本、真腊、吕宋等国,则几乎为最外圈,要么十年一贡,要么无定期而贡。根据朝贡体制中贡者多获的历史常态,明朝几乎与后者的认同程度递减,深入交往的需求也下降。朝贡国的序列常常发生调整,但总体上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是与中国朝贡体制与国际认同的相对稳定有关。而这种既稳定又不失灵活、集国际认同的开放性与差序性于一体的天下体系,造就了宽泛意义上独树一帜的国际体系模式。
(二)圈序认同在中国外交上的历史显象
1.古代中国外交中的圈序认同
圈序认同作为古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其表现是有规律可循的:它往往是潜在的影响行为,对于个体而言有其无意识性;交往愈成体系性愈明显,故在国内交往中一般较国际交往中更易体现;当国力强盛且具有整体的外交大战略时,圈序认同思维更加容易辨认。
中国外交意义上的圈序认同思维是一个不断发展和递嬗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随着中国历史的进步、人的概念变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变化而变化,并最终落实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上。正如有学者认为的,“从殷商的内外服制到战国后期的夷夏之辨,从血缘亲疏到文化异同,经过历史的长期演进,中国人对于世界图式的叙述至此大致确定下来”。(25)我们认为,在这个“长期演进”的历史过程中,上文所讲圈序认同生成中的地缘安全、礼治文化和朝贡制度三个方面,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地缘安全方面在先秦早已具备,朝贡体制方面秦汉两代也有实践,但礼治文化与德治天下的盛行则似在唐及之后。在唐代,如果一个大的同心圆的核心是唐王朝的话,那么向外的第一圈是安东、安南、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六大都护府;向外的第二圈是更具自治性的突厥、回鹘、吐蕃、南诏、渤海;第三圈是具有一定依附性的国家,如新罗、林邑;第四圈是仅有朝贡之名的主权国家,如大食、日本。(26)到了宋代之后,中国出现了几个强大政权并立的局面,宋朝对东南方向的外交也有圈序的特征,但无法形成整体性的朝贡体制。元朝统治较短,礼治天下文化未及内化与体现。明代是朝贡体制盛行的朝代,明太祖的朝贡制度将中国人的圈序认同体现得淋漓尽致,具体原则上文已述。到了清代,中央政府“对招徕海外诸国进贡等方面已无兴趣,但在处理北方、西北、与东北疆域方面则胜过前代”,出现了明显的圈序外交:清本土是满汉两族的内地与东北各省,外围第一圈是藩部,即内蒙古、蒙古、新疆、西藏;第二圈是属国,包括伊犁将军执行羁縻政策的浩罕、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阿富汗和乾竺特以及东南的朝贡国朝鲜、安南、琉球,还有缅甸、暹罗、南掌、廓尔喀、坎世提和苏禄等;第三圈是仅有“朝贡”虚名的俄、英、法、美、西、葡、荷等国。(27)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圈序认同如同前朝一样,都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并不僵硬地划清界限,而是根据国际互动的情况而加以调整,其核心还是德治天下和怀柔政策。“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附近浙闽,有慕义投诚纳款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28)晚清之后,中国渐衰,朝贡体制瓦解,中华文化面临危机,近代中国外交充满了屈辱,原本意义上的圈序认同根基动摇,逐渐被二元认同所替换,以夷制夷、依附外交、均势思维等长期成为主导性思维。
2.现当代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圈序认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力日盛和国际主义的复归,圈序认同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更加明显。到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之时,新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圈序认同体系,(29)其核心是毛泽东关于建立最广泛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这个认同体系的国际政治基础是处于美苏争霸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特别是以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为主要构成的新近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它们不满于美苏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希望日益强大的新中国成为它们的战略依托和领导核心,并对于中国的革命与发展模式十分认同。其经济基础是,中国对世界上与自己较为亲近的国家特别是核心圈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亚非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援助。这一点与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所赖以生存的政治与经济基础虽然在本质上迥异,可在形式上何其相似!它还生动地体现在有关毛泽东丧礼纪录片中外国使节的吊唁顺序中:最核心的一圈显然是中国的“自己人”,即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第二圈是中南半岛三国;第三圈是第三世界国家;第四圈是第二世界国家;第五圈是没有国家身份的巴勒斯坦解放阵线,最外部的一圈则是没有邦交的美国。1976年前后的中国外交身份正处在一种变动之中,其中最难处理的就是苏联与东欧国家,故其使节穿插在各圈之间参加吊唁。
然而,从总体而言,综合“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中国外交的实践,这个时期中国认同体系的内圈(即“立足点”)是第三世界,而在这个内圈中最里面的一层是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但不包括日本),这里面显然也有地缘因素与历史文化传统因素;(30)其次是非洲,正是亚洲与非洲的朋友最终帮助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周恩来总理20世纪50年代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和60年代出访非洲14国,重点都是亚非国家。第三世界的较外层是拉丁美洲。中国认同体系的中圈是第二世界,它们主要是指以美国的欧洲盟国(德国、英国等)、北美盟国(加拿大)和亚洲盟国(日本)为代表的中等发达国家。(31)而最外圈则是超级大国。“三个世界”理论所包含的圈序认同体系虽然不能包括所有的中国对外交往对象,但是总体上涉及最重要的战略力量,反映了两极体系时期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期间对于国际体系建构的努力。当代中国外交的圈序认同实际上很长时间内是以“三个世界”理论为核心的。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由于两极体系的瓦解和中国战略环境的变化,中国政府逐渐放弃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但由于“三个世界”中的内圈认同是近邻的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的国际身份定位仍为发展中国家,因此“三个世界”的思维不会轻易消失。90年代以来,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俄罗斯、法国、英国、美国等构建起程度不一的伙伴关系,就认同度强弱而言依次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如与东盟)、“基础性伙伴关系”(如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与俄罗斯)、“全面伙伴关系”(如与法国)、“建设性伙伴关系”(如与英国)、“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如与美国)等。当然,中国伙伴体系中最核心的还是后来提得较明确的“好邻层、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如与巴基斯坦)和“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如与古巴),这些伙伴关系虽然与时而变,但大致上构成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圈序认同底色。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建设“和谐世界”,这个概念不同于西方人的和谐理念,本身就拥有中国人圈序认同的特征。在西方人看来,和谐的世界是所有地区的和谐同时实现;当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一方有难”时,国际社会应该本着一个共同的文化标准来“八方干预”,因为文化的同质性对于世界的和谐是至关重要的,对于那些文化或文明的“异端”,应该加以改造或者消灭;为了和谐与和平,应该诉诸积极的努力甚至暴力与战争。中国人的理解序列是相反的:和谐世界固然是全天下人的共同事业,但它的实现又是从局部到整体而递次渐进实现的,在国际互动与对话中有一个相互不断学习和影响扩展的过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圆心国如果实施国内和谐进而天下仁政,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效仿之并可能成为和谐的国家。对于中国而言,它首先应该把邻居的关系搞和谐,和谐周边是和谐世界的第一步,其次才是亚太地区的繁荣与和平,最后是世界的和谐。和谐源于一圈一圈地扩大,一层一层地深化,一段一段地实现。
四 圈序认同对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多重影响
圈序认同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基础部分,尤其成为中国人观察与处理社会关系和外部世界的集体无意识,也深深地影响着不断走向开放世界的外交文化心理。一方面,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体现了远古时代以来中国人的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以及实践理性,(32)民族复兴与文化创新的任何努力都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另一方面,它与封建思想、封闭意识和文化中心主义也有着一定的联系,若不注意警惕,其消极影响会不利于中华文明与世界政治文明的积极对话。有必要认真对待圈序认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发挥其正面作用,使之服务于中国外交软实力建设。
(一)圈序认同模式研究的潜在警醒
晚清之后,中国文化包括外交文化都几乎被彻底批判,差序结构、圈序认同、家族社会、朝贡体系自然也在其之列。圈序认同多有诟病之处,最为明显的一条是,其包含的内外有别、先内后外、重内轻外之类意识,在内政外交几乎日益难以分清的国际政治大背景下,堪称落后的政治思维。华夏中心主义是圈序认同在国际政治观上的反映,在东方强于西方的条件下尚能勉强支撑,但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却易成为激起国际社会“中国威胁”论调的催化剂。另外,还有至少三个方面也值得研究者们加以关注。
1.圈序认同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相抵牾。圈序认同之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将中国视为圆心而卫星国、朝贡国为辅卫的层层隶属的不平等国际体系。在秩序优先的价值取向之下,朝贡秩序及其相联系的圈序认同思维有其天然的合理性。这种等级观念根本上来源于农业经济和封闭经营的生产关系,受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的深刻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支持了或者至少暗合了国际关系的压迫行为和不平等逻辑。在天下大势特别是世界生产力的冲击之下,工业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瓦解了圈序认同先前赖以存在和支持的经济基础,形成了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近代国际体系。随着主权制度的全球化特别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国家间相互尊重和平等互惠等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圈序认同模式对于建设世界政治文明只能有借鉴意义,而不能成为主导文化。中国外交既然也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为要旨,就需谨防圈序认同危及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当然,我们也不能断定圈序认同理念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格格不入。完全平等的国际关系是个理想的目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难以实现。理想的目标需要现实的手段。在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目标中的平等关系需要某个阶段的不平等或不完善作为现实条件,而全球社会或者地区社会客观上都存在着权威中心的示范作用和目标实现的先后顺序,国际社会实际上总是存在着权威分层的现象。(33)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世界大同实现之前,圈序认同也许仍有其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是以纠正和补充二元认同之缺陷为基础的,但毕竟不能达到人类价值上的完满性。
2.以积极的国际责任意识弥补圈序认同的自我自利。在古代中国人的交往思维之中,有一个消极的方面,即圈子的利益高于集体的利益。当然,如果圈子本身就是集体,即国家就是皇帝一人的,那么皇帝就讲“天下为公”了。但其本质还是“天下为私”的。由于圈序认同结构中,圈子是不断伸缩的,而且圈子也是有层次的,因此,既定圈子内的行为体对于更大圈子的利益往往不是很关心。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更大的消极方面是,为了小圈子的利益而牺牲大圈的利益,对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曾有精彩的阐述:“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是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34)当然,中国进入世界体系以来的现代化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人的人类贡献意识大大增强了,但阻碍“中国应该为人类做更大的贡献”和成为世界大国的诸多意识因素中,圈序认同与自保意识概莫能外。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大的全球责任意识,加入到诸如气候控制、公共卫生应对之类的全球治理上,以展示和增强泱泱大国的软实力。
3.当代外交情势下“圈序认同”之核心价值的缺失及其重建。从中国外交文化的角度看,如何构建当代中国外交圈序认同的主导内涵,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文初所涉及的几对概念可见,中国外交在围绕和谐文化、周边外交和战略伙伴等几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圈序思维。但是,这些圈序认同主要是基于地缘和战略利益而展开的。关于中国目前国际身份这一重大问题上,核心认同问题并没有解决。虽然国家利益是国家外交的根本出发点,但是国家利益并不能维系一个国家的本体所在。再说,国家利益也不是简单的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相加,它还包括国际利益、国际制度利益、国家信仰体系以及国际政治文化等因素,而后者才是国家国际认同的主要对象范围。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核心问题是价值体系重建问题,对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建,对外是有中国特色国际政治文化体系重建,而内与外都是统一的、一体的。由于圈序认同首先要有一个圆点,因此,有关圆点的建设就很重要。先秦时代,这个圆点是周王朝的血缘;汉唐乃至明清时代,这个圆点是仁礼义文化;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曾把它定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实质上把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和发展中国家身份作为圈序认同的圆点。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外交的认同圆点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不断从伟大的外交实践中总结并构建新的国际政治文化与国际身份。没有了认同圆点,就没有了外交之本,就无从构建世界秩序。
(二)圈序认同对中国外交及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意义
在以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二元认同基础上的西方国际政治文化挟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威风而独领风骚400年之后,人类在继续肯定这种文化主体性和合理性的同时,更加注意从包括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等非西方文化中寻找世界政治思想,圈序认同思维若进行重建,或许会在以下四个方面产生积极的启示。
1.重建后的圈序认同将赋予主流国际政治文化以更多的和谐性与多样性。由于近代以来的国际社会是由西欧早期基督教国家建立起来并不断扩展形成的,因此,主流的国际政治文化带有较明显的基督教文化的二元认同特征。如前文所述,这种认同模式的优点是泾渭分明,操作简易,容易机械化,技术理性强,科学化特征明显,在征服自然和机械性地改造社会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在工业革命、现代化、殖民化、商业战争和强权政治的时代比较有效率,但其机械性、对立性、强制性、侵略性在19世纪末就已初显端倪。与二元认同相比,圈序认同虽然讲亲疏,讲差别,但重点是讲差序之下的统一,讲行为主体与外面世界的不同程度的和谐。它既讲由此及彼,又讲由彼及此,后者虽然在内外之间好感程度有所差异,但总体上还属于认同对象的一部分,圈序思维的出发点还是希望把自己的认同体系推广到外部世界得以自由地承认,其隐含着灵活性、包容性、多样性和互认性的一面,更加符合后现代社会和全球治理条件下的国际政治求共存、求共赢、求和谐的潮流。然而,由于主流国际政治文化长期由西方霸权及其二元认同模式等因素所构建,因此,世界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全面改造尚需时日,研究圈序认同的理论意义并适度发扬光大,无论对于推动国际政治文化的多元发展,还是对于构建中国理论都有特别的意义。
2.圈序认同凭其道德文化的内在参照可以促进全球治理理论的本土化。从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来看,国际政治二元认同模式的内在参照主要是物质文化(市场经济模式),强调的是自我物质利益的扩展,虽然其终极目标和外在形式上有着浓厚的宗教意识和民主救世思想;而中国古代国际关系则表明,圈序认同的内在参照主要是心的体认与德的外化,强调的是中华理想(天下仁政)的递次实现,大致遵循一条内圣外王的路线,朝贡体制的基本考虑是为了维护以德治国和礼治天下。西方学界目前热衷的全球治理理论已经开始超越现代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政治观,强调多元行为体国际合作的一面,有其可取之处,但其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二分,强调共同利益而非共同文化方面,仍有着传统二元认同的较强色彩,需要中国外交文化的有力补充。中国外交文化中的圈序认同中固有的道德文化本性,可以从德治天下、天下同心的角度来诠释全球治理理论,这样,或许会开辟出一条本土化的道路来。
3.吸收圈序认同的合理成分,可以对世界政治与世界秩序有更加丰富的制度思考。这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圈序认同的思维模式从根本上讲与二元认同思维所引申出来的关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分野的国际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如果说天下体系的基础是无外原则及(与之并不根本冲突的)圈序认同的话,那么民族国家主权体系则以二元认同为基础。如果当今的主权体系适当吸收天下体系的若干合理成分,对于正在到来的全球治理时代是很有裨益的,因为后者有着理论上和美学上的完整性,更能适应全球一体的未来政治发展形势。在赵汀阳所称的天下无外原则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圈序认同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会有“以自己为中心的‘地方主义’,但仅仅是地方主义,却缺乏清楚界定的和划一不二的‘他者’以及不共戴天的异端意识和与他者划清界限的民族主义。……这样一种关系界定模式保证了世界的先验完整性,同时又保证了历史性的多样性,这可能是唯一能够满足世界文化生态标准的世界制度”。(35)第二,圈序认同下的国际制度化更强调模糊性、符号性和松散性,有助于世界秩序变革中的软性制度化模式。国际秩序问题是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可回避的问题。秩序无疑是权力、制度与文化的统一,三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立。其中,制度与制度化是大国成长中处理与既有世界秩序的关键问题,它是权力折冲的焦点,是文化冲突的外化。我们认为,不同的认同模式和文化传统影响着制度化的方式,二元认同模式下的制度化更容易体现为硬制度化,而圈序认同模式下的制度化则更容易体现为软制度化。二元认同往往要求权力安排和利益划分的文本规范(立宪、国际法),要求敌我之间和内外之间的边界明确(主权制度),要求制度的严格执行以及监督财政司法保障体系完整(均势体系和联合国等强大机构),甚至要求将制度上升到神圣的程度(法治精神及“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相比之下,近年来,东亚的地区一体化和多边主义较欧美地区更加松散,一体化建设目标相对具有原则性,多边协商表现出强烈的象征性和随机性,会议声明用语往往较为模糊,但是仍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一体化的发展和共同体的建设。这一地区的软性制度化现象之所以十分明显,除却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和政治价值观大相径庭等因素外,该地区总体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外交思维上可能摆脱不掉传统的圈序认同模式,是不能轻易排斥的重要因素。
4.圈序认同的基础是实用的过程理性,这对于和谐世界的理性实现仍有着理论启示。中国文化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缺乏西方文化具有的宗教性,实用性极强,且重视过程甚于重视结果。圈序认同的各个方面显然体现了这种实用理性与过程理性的结合:中国人喜欢在一种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由实到虚、由易及难的社会纽带中生活,喜欢量力而行,在逐渐的变革中贡献自身的力量或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强调从身边做起,但并不把脚下的行动与远大目标割裂开来。国际利益(“国际责任”)理论与世界秩序(“和谐世界”)理论研究是与大国社会性成长联系较为紧密的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目前又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息息相关。我们若能在圈序认同的重建过程中,创造性地诠释和谐世界理念,使之既能够符合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潮流,又能符合本土化的理论旨趣和不断成长的国家利益,就可能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p.22-27.
②并不是所有的东亚国家在外交文化上都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明的影响。
③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④李云泉认为,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缺少与其他发达文明之间的对等交流,增强了华夏人的文化优越感,华夏中心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观点与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观点是一致的。参见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⑤黎虎认为,古代世界形成了两个最主要的外交圈,即在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高原以东的东亚外交圈与在其以西的西方外交圈。西方外交圈由于古代航海技术的发达与贸易的盛行,其中心不断转移,形成了多中心的特征,如汉唐时期,西方出现了以安息帝国等为代表的西亚北非外交中心、以孔雀王朝等为代表的南亚中心及以罗马帝国为中心的欧洲外交中心,而且各个中心内部也不断转换主导国家。东亚则不同,中国始终是东亚世界的中心。参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⑥《国语·周语》。
⑦《国语·晋语四》。
⑧J.F.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
⑨[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页。
⑩许倬云:《许倬云观世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155页。李泽厚先生也指出过古代中国更强调对立面之后的互相补充与互相渗透而不是波斯哲学中的光暗排斥和希腊哲学强调的斗争成毁。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11)许倬云:《历史大脉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5页。
(12)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13)在这一点上,二元认同的思维模式近似于赵汀阳所说的文化的异端模式。赵汀阳认为中西文化模式之分可归纳为天下模式与异端模式,而异端模式在表达他者问题时以宗教分歧为底色。赵汀阳:《没有世界的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1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北京: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15)韩愈:《原道》。
(1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80页。
(17)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7~8页。
(18)关于孔子、孟子和荀子关于仁之外推与礼之克制的探讨,参见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代研究者的思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398页。
(19)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87页。
(20)有研究认为,周之前,华夷之防有一定的血缘标准,但在西周、春秋时期,夷夏的区别主要建立在礼的不同上,血统的区别被文化的区分所代替。参见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代研究者的思考》,第493~494页。
(21)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386页。
(22)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载刘岱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454~455页,转引自陈廷汀、周鼎:《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页。
(23)《周礼·秋官·大行人》。
(24)《明太祖实录》卷76,洪武五年十月甲午。转引自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第73页。
(25)陈廷汀、周鼎:《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第4页。
(26)石源华:《中外关系三百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页,转引自肖佳灵:《国家主权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27)石源华:《中外关系三百题》,第8~11页,转引自肖佳灵:《国家主权论》,第263页。
(28)《清史录》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1页。
(29)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外交虽然有着和平共处的旗帜以及“一边倒”的战略方针,但总起来没有形成制度化和理论化,因此,它的圈式认同并不明显。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中苏关系是核心,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次之,然后才是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最后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最外圈是美国。
(30)当时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多次为中国内政外交搭起秘密桥梁的国家多为东亚国家,即朝鲜、柬埔寨、越南和巴基斯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31)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49-1979)》第三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3页。
(32)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第20页。
(33)国际社会分层是国际政治社会学(IPS)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其核心是权威分层和价值等级。也有学者认为等级结构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另有学者认为类似于“亲亲尊尊”的等级在人类社会中是要保存的。分别参见王逸舟:《对国际社会等级结构的一种调研》,载《欧洲》,1996年第3期,第4~12、45页;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34)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4~25页。
(35)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二元经济论文; 二元对立论文; 二元关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朝贡体系论文; 国际文化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核心意识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