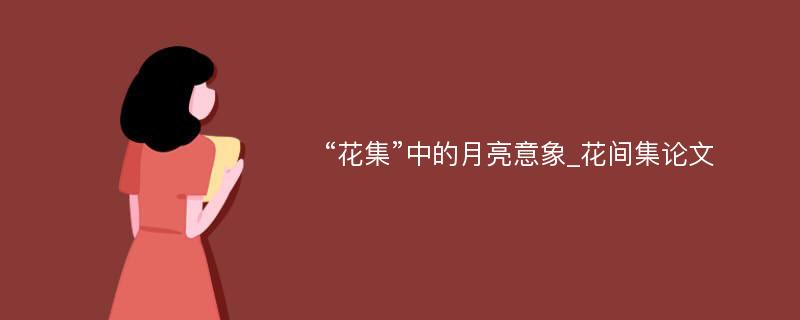
《花间集》中的月亮意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月亮论文,意象论文,花间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通过对《花间词》月亮意象的归纳分析,揭示“月亮——女人”模式背后的心理基础——女人原则及其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月亮意象 女人模式
女人原则
价值意义
月亮与文学,月亮与中国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月亮是古代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自然物象,也是饱含作者浓烈感情色彩的一种意象。本文拟探求《花间集》中的“月亮意象”,看花间词中的“月亮意象”是怎样体现“柔性的、春意的、女人的”这一词之本质的,并着重揭示隐藏在“月亮意象”之后的心理基础,挖掘其内在的价值和意义。
一
从数字统计来看,《花间集》五百首词,直接写月者达九十六首,还不包括以月喻发髻、以月喻人体者。若凡言及月者皆算在内,则总数超过一百首。单凭这一点,就足见花间词人对月亮是多么情有独钟了。那么,《花间集》是怎样描写月亮的呢?翻开《花间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量的“残月”:
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温庭筠《菩萨蛮》)
星斗稀,更漏残,帘外晓莺残月。(温庭筠《更漏子》)
门外早莺声,背楼残月明。(孙光宪《菩萨蛮》)
冷雾寒侵帐额,残月光沉树梢。(和凝《薄命女》)类似这样描写残月意象的词句,在《花间集》中可谓信手拈来。写“满月”(明月)的也同样数不胜数:
心事问谁知?月明花满枝。(温庭筠《菩萨蛮》)
插月走马落残红,月明中。(张泌《浣溪沙》)
深秋寒夜银河静,月明深夜中庭。(尹鹗《临江仙》)
三五夜,偏有限,月明中。(欧阳炯《献衷心》)
深夜独处时谁能不被天边升起的一轮圆月深深地触动呢?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即使由于数千年的文明进化史而失去了昔日先人拥有的那种宁静的社会环境,但是在内心深处,当我们面对一轮清辉满月的时候,心中也常有股难以言说的激动、惆怅和忧伤,仿佛远古之夜的朦胧意象苏醒了,是张若虚笔下的月亮还是李白酒杯中的月亮,我们都分不清。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看看月影,想想月亮,于是月亮在我们心中便朦胧起来。这就是《花间集》中大量描写的“朦胧月”了:
灯在月胧明,觉得闻晓莺。 (温庭筠《菩萨蛮》)
玉阶华露滴,月胧明。 (薛昭蕴《小重山》)
小屏古画岸低平,烟月满闲庭。(顾敻《甘州子》)
烟月重,秋夜静。(毛熙震《临江仙》)
等待是漫长的,星移斗换,直到月落之时,这种情境使我们想起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斜月”是迷人的,却又是最忧伤的:
梦觉半床斜月,小窗风触鸣琴。(韦庄《清平乐》)
情似还深酒杯深,楚烟湘月两沉沉。(薛昭蕴《浣溪沙》)
香阁掩,眉敛,月将沉。(顾敻《诉衷情》)
月沉沉,人悄悄。(尹鹗《满宫花》)
月亮总是随着时间之流在改变。《花间集》里描写月亮也是多角度的,除上述四种基本的形态外,还描写了宫中月,庭中月,窗前月,城上月,山月,水中月;有秋夜月,也有春朝月;有冷月滴露,也有孤月徘徊;有眼前之月,也有他乡之月,可谓集月亮描写之大全。
二
月亮是女人的上帝。有一个古老的说法:“月亮对男人是毁灭性的,却是女人天性的一个本源。她是女性的赞助者与守护神。”美国分析心理学派学者M ·艾瑟·哈婷在其名著《月亮神话——女性的神话》一书中,对女人和月亮的关系有深入独到的研究。她称:“人的本性之一是女性明显区别于男性的女性特征,而不是男人与女人的相似。这一差别的超越一切的象征符号便是月亮。无论在当代还是古典诗歌中,从时代不明的神话和传说里,月亮代表的就是女人的神性,女人的原则,就象太阳以其英雄象征男性原则一样。对于原始人和诗人以及当代的梦幻者,太阳就是男性,而月亮则是女性。”(《月亮神话——女性的神话》)可以说,对月亮的崇拜,是全世界大多数民族所共同的现象。对早已发达的中国文明来讲更是如此,在此用不着多加罗列,值得注意的是,类似《花间集》这样的文学作品,对月亮的描写其隐蔽性的关系是“月亮——女人”模式。这种模式在《花间集》中表现得那样强烈,以至我们对词集中大量模式化的月亮描写所暗含的关系有点熟视无睹了。我讲《花间集》中的月亮描写所隐含的关系是“月亮——女人”模式,是有根据的。在“残月”意象群中,伴随的意象有杨柳、晓莺、绣阁、香灯等等;在“满月”意象群中,伴随的是花、残红、芳颜等等;伴随着“朦胧月”的是玉露、烛灯、轻烟等。我们知道,这些事物大都是用来描绘女人的,在温词时代,有的干脆是女人的代名词,更不用说词集中描写月亮——女人关系了,如“残月出门时,女人和泪辞”,“月落星沉,楼上美人春睡”等等。其实以月喻女人,或者说月亮和女人同时出现在作品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早就有了。这主要是因为,月亮在人类的心目中,很早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从各方面“干预”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多方面催化人的情感的触媒,并提供一种表现人的情感的氛围。远在人类社会早期,原始文学中就有许多作品与月亮有着难分难割的关系,如神话中“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的故事,民间传说中月宫娘娘,月下老人的故事,这是月亮和女人较早在文学作品中结合的范例。随着文明的进步,月亮和女人更是有意识地结合在一起。《诗经》中的《月出》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月出皎兮,佼人僚兮”。以月起兴,以月喻人。朱熹评说此诗是“男女相悦而相念之辞”。《古诗十九首》中,《明月何皎皎》便是典型的闺中望夫之作,其它《迢迢牵牛星》、《孟冬寒气至》莫不如此。《花间集》中大量描写这类故事,不能不说是文学的继承性在起作用。六朝时谢庄《月赋》中那句“隔千里兮共明月”引起多少旷男怨女、游子离人的共鸣!李白除了在月下饮酒、弹琴、行歌、起舞外,还留给我们大量的宫怨诗,这些诗写的句子更是脍炙人口:“玲珑望秋月”、“深宫望秋月”、“月皎昭阳殿”、“相思如明月”,所有这些都启迪了花间派词人的诗思。
为什么人们常常把月亮和女人联系起来?
首先,这与月亮本身的特点分不开。月有阴晴圆缺,时隐时现,朦朦胧胧,且洁白晶莹,似冰雕,似玉琢。哈婷认为,月亮的性格和女人的性格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月亮的周期与女人的生理周期在内在含义上是相通的。月亮的光辉是那样的轻柔,它的面孔又是那样的冰冷,这就使男人想起了可望不可及的“伊人”。神话学研究表明,月露和光辉是受孕的一种象征,象征爱和魅力。在希腊,月亮女神被当作雨露的给予者;在雅典,人们为她举行洒露仪式,露珠少女们围绕着月亮女神翩翩起舞。人类的心灵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花间集》中,与月亮伴随的也有玉露清辉之类。这些特点,是把月亮和女人联系在一起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古代人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理解“月亮——女人”模式的一把钥匙。古代交通及通讯手段不象我们今天这样发达。那些上京赶考的学子,边走边读直到京城;男人外出征战,一走就遥遥无期;还有久留在外的游子。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恋人、情人、妻子只好盼月亮、望星星那样去守候等待了。什么“高楼颙望, 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仍“不见伊人倩影”是常有的事;更难熬的是夜晚独守闺房,一次又一次地往外望,能望见什么呢?只有月亮和星星。可是,“山月不知心里事”,夜仍是这般深沉,心灵仍如冷月般孤寂,哪怕我一再“礼月求天,愿君知我心”,也是无济于事。这就是《花间集》中为什么多写月亮,多写女人,多写夜晚的原因所在,只有月亮才是闺中女人凄凉的伴侣,不胜幽怨的精魂。
再次,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也是把月亮和女人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中,一直是主张阳刚与阴柔相辅相成的。《周易·系辞上》载有“一阴一阳谓之道”之句;古代著名哲学家周敦颐曾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程颐也说过“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之语。中国的太极图也意味着阴阳的结合。中国的书法讲究刚柔和方圆的相济,形方就要神圆,形圆就要神方。阴是月,阳是日,阴是女人,阳是男人,这些观念如此根深蒂固,自然地在人类的意识深处易把月亮和女人联系在一起。
月亮本身就有“团圆”的象征意义。《花间集》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伤离伤别,如“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早是出门长带月,可堪兮袂又经秋”。月亮特别是前面提到的满月意象与眼前的分离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愈觉伤心,“所谓月圆人未圆”是也。
综上所述各种原因,我们知道“月亮——女人”模式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种必然的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在《花间集》中得到了突出表现。在这种心理因素作用下,月亮意象被反复加以描写,最后走上模式化道路。仔细看下《花间集》我们就可以归纳出“晓莺——残月”、“杨柳——残月”、“残红——满月”、“芳颜——满月”、“烛灯——朦胧月”、“轻烟——朦胧月”等多种模式,它们都被广泛地应用。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花间集》中写月亮之词竟超过百首了。
三
揭示《花间集》中月亮意象所暗示的“月亮——女人”模式,也是为了揭示这种模式背后深刻的心理基础——男人身上的女人原则,这仍是使得花间小词成就了其幽微要妙且含有丰富之潜能的一项重大原因。
女性批评主义代表卡珞琳·赫贝兰在其《朝向雌雄同体的认识》一书中,提出了“雌雄同体”这个概念,意指性别的特质与两性所表现的人类倾向,本不应强制划分,并在书前序中引用批评家罗森梅尔的《悲剧与宗教》一书中的话,以为希腊神话中的酒神戴奥尼萨斯既非女性,亦非男性,乃是女人中的男人,男人中的女人。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曾提出“知其雄,守其雌”的说法。可以说,在神话、宗教、哲学和文学中,“双性人格”应该是种完美的美学特质,同样,花间词人所描写的月亮意象,蕴含着“双性人格”,体现了一种特别的美学特质——男人身上的女人原则。
《花间集》的作者都是士大夫,而其主要内容和风格却是表现女性生活——其主要的表达手段是月亮意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男子作闺音”的现象呢?作为花间词的创作主体——晚唐五代的士大夫,自身有何特点呢?在此,我还是借哈婷的有关观点来作解释。她在《月亮神话——女性的神话》一书中指出:“同一个女性原则,对男人和对女人一样发生作用。但对女人,这一原则直接左右其意识的个性;对男人,与厄洛斯(即女性原则——引者注)相联的不是其意识,而是其无意识。他的意识特点是男性的,受逻各斯原则所左右。但在无意识中,他却交给了—‘另一面’—那里他的灵魂是统治者。而这一灵魂人类一贯是把它当作女性的。男人的这种女性灵魂是一种本质存在。”用赫氏所提出的“雌雄同体”概念以及哈婷所指出的男人身上的这种心理事实来解释晚唐五代词人创作大量的月亮意象的心态是可取的。对此问题,在这里特别提出三点:
第一,我们应该看到,花间词中大量描写月亮意象,出现“男子作闺音”的现象,不管怎么说,至少体现了社会(主要指男性作者群)对妇女的注目和关心。晚唐五代前,在男性作品中(花间词都是男性的作品),通常都是以男性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女性,在娱乐中作为被欣赏的对象,在战争中作为财富的象征。因此,妇女的命运,妇女喜怒哀乐的内心世界,在文学的舞台上,一直是个“被遗忘的角落”。除了民歌,如《木兰词》、《陌上桑》,以及少数女性所写的为数极少的作品外,男性作者向来忽视占人口约半数的妇女。这些情况到唐代已有所改观,如不少“宫怨”、“闺怨”诗和元、白的一些妇女诗篇以及唐人传奇中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以女性为主角的名篇,就开始触及妇女问题,这无疑是文学表现领域的一种开拓。但到了晚唐五代士大夫才彻底放下架子,不惜泼墨用大量的“月亮意象”来代女人言,写女人心,“设身处地”、“体贴入微”地去体会女性的内心世界,为那些地位低微的歌妓侍妾“写心”、“立言”。这反映出社会的进化,“人性”抬头所带来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微妙变化和某些新的信息。同时,也可从中看出“女性美”描写的历史进步。《卫风·硕人》中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仅仅只是化“美”为流动的“媚”,将美人的姿态、神韵刻画出来;屈原的“若有人兮山之阿”、“既含睇兮又宜笑”、“美目眇兮宜修”,风流宋玉笔下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对女性美也仅仅是肤泛的刻画,粗线条的的勾勒,缺乏深刻的审美内涵。可花间词人对女性美有独特的审视角度,用所敬畏的月亮来写女性。在他们的笔下,女性不仅仅是外表的清丽秀美,更主要是她们超脱尘世,冰清玉洁,玲珑剔透,内在美和外在美完美结合,相得益彰,真正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和关注。故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月亮——女人”模式更是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如朱淑真《生查子》中“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清代黄景仁《子夜歌》中“思君月正圆,望望月仍缺,多恐再圆时,不是今宵月”等等,可以说,“月亮——女人”模式已成为民族审美心理积淀下来,成为艺术创作和审美联想的社会心理基础。
第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人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在语言的运用上,花间词人在描写月亮意象时采用了一种女性语言。什么叫女性语言?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女性根本没有出仕的机会,因此以“行道”、“仕隐”为主题的作品当然乃是一种男性意识的语言。而花间词却打破过去“载道”“言志”的文学传统。在内容上,往往用女子之感情心态来叙写牵眷之情和幽怨之思,是女性审美意识的流露;在形式上,用一种破碎的语言形式,这种形式代表的是非理性、混乱、具阴柔之气。同男性所代表的理性、明晰、秩序、充满阳刚之气相反。但这不仅不是一种低劣的缺点,反而形成了词之曲折幽隐,引人言外之想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温庭筠有两句关于明月意象的描写——“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头一句写明月之下,玉楼之中有一个女子怀念心中的恋人,但“柳丝袅娜”和“玉楼明月”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温庭筠还有一首词说:“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这是关于“山月意象”的描写,前二句是说,山中明月不知我的心事,水面之风无动于衷地吹落眼前的花朵,但接下来呢?“摇曳碧云斜”,一下就离开了原来的思路,这是一种突然的跳跃,看起来和前面承接不上,实际上却微妙曲折地表达了女人的心态感受。再如顾敻《诉衷情》中有“斜月意象”——“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这首词借“斜月”写女性化的“透骨情语”恐怕已至丰满细腻之化境。
月亮意象的描写大量采用女性的语言,除了深刻细腻地表达了女人的心理感受之外,又有利于促进形式的发达,技巧的变幻,语言功能的不断扩大,对形式主义美学的发展是一大贡献。真正有美学意义的文学实践是在先秦民歌和汉乐府中产生出来的,后逢魏晋南北朝生命文化的蕴籍,形式主义美学得到了发展和明确化。不幸的是,这种美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屡遭攻击。继初唐陈子昂的“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的辛酸感叹,经韩柳的“古文运动”,形式主义美学历遭压抑之苦,气息也极其微弱。而花间词人在生命源的强烈鼓动下,用大量的月亮意象,刻画女性心理,表现了对形式技巧和声韵的追求,这又是对形式主义美学自觉地做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尝试,是对形式美学的大胆张扬。“词的本质是审美的”,作为词之鼻祖的《花间集》对形式美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此后,不管是文化专制,还是“文以载道”的正统艺术心理的强化,这股形式美学总是或隐或现,或强或弱地发展着,体现出旺盛的潜能,强大的生命力,不能不说是这种女性化的语言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女性原则在晚唐五代士大夫身上表现得非常强烈。对于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来说,对这种心理事实是难以察觉到的,也是难于认可的。儒家素来重男女有别,男人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一贯强调“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的传统原则,强调“刚”之文风,如孔子即感叹“吾未见刚者”(《论语》),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孟子·公孙丑),都是提倡“刚”而贬低“柔”的。花间词人怎么能自身带有女性原则,并且用大量的月亮意象来写女人呢?事实是,一方面,中国文学史上自古就有香草美人的传统。屈原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李商隐的“长眉己能画”,都是这种心理的折射。另一方面,五代十国之际,西蜀偏安,远离中原战事,当时“以艳为美”和“以柔为美”的审美心理决非当时少数人所有,而是一种普遍的弥漫于社会上及词坛上的思想潮流。吴任国《十国春秋》载:“蜀王衍,奉其太后太妃,祷青城山,宫人皆衣云霞之衣。”《北梦琐言》载:“蜀主裹小巾,其尖如锥,宫女多道服,簪莲花冠,施脂夹粉,名曰‘醉妆’。”时间往前推,晚唐风气亦如此,《花间集》序中所言:“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有香径之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至于钟鸣鼎食之家蓄妓纳妾,互相攀比,更是为大家所熟知了。正如物质产品领域一样,精神产品的“生产”也受到“消费”的支配与制约。从这个角度看,花间词人之所以大写“妇人语”,大写那“男子作闺音”的诗篇,就是投合了当时读者和听众的迫切需要;也是他们为实现“以艳为美”和“以柔为美”的审美理想而寻觅到的一种颇为得意的方式。而月亮本身的特点,传统的哲学观念,古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学实践又造就了月亮意象,使之成为花间词人实现他们的审美理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美国杰出思想家赫伯特·马尔库塞说:“一个自由的社会将是女性的社会,的确,只有男性或女性单方面成熟或统辖的社会是不完整的畸形的社会,有无法摆脱的落后性和局限性。……女性意识的确立、发展对人类的完善化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我认为,每个人的心理本身都是阴阳合一的,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两个方面,他只是半个人,他的人格就不健全。这样,在晚唐五代这样的社会风尚中,士大夫自身的“女性原则”被极大地唤醒和激发了。他们为女人代言,模仿女人的心态写词。而和女人有特殊联系的月亮自然地大量出现在花间词中。可以说,如果没有“女性原则”这股心态,而以男人心态写出的“花间词”便决不会是“花间”词了。
由此可见,《花间集》及其它文学作品中的“男子作闺音”,有其深刻的心理事实——男人自身的“女人原则”。在《花间集》中,这种“女人原则”主要是通过月亮这一意象以及月亮意象所暗示的“月亮——女人”关系来表达的,并显示了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收稿日期 1995—0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