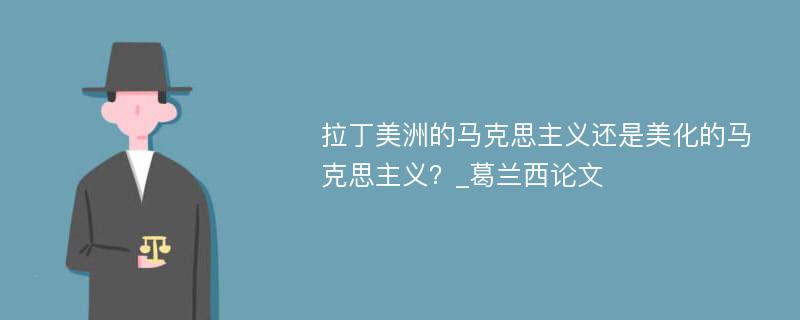
拉美的马克思主义抑或拉美化的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拉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拉丁美洲(以下均简称拉美)化的马克思主义,总处在一种半欧洲式(也许更严格地说是半美洲式)的“临界”状态,因此,这种混杂的概念在拉美产生重大反响并非巧合。然而,说原原本本的马克思主义渗入拉美,这是不恰当的,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就像我们把马克思看作与拉美大陆的一场奇遇是不恰当的一样。但是,马克思主义确实在这里扎根生长,例如,秘鲁思想家和活动家何塞·卡洛斯·玛利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1894~1930),就像是一个蜚声于拉美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我们追溯一下早期的发展,然后对从斯大林领导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发展轨迹进行勾勒;再进一步概括新近出现在智利的马克思主义复兴,以及其他明显的“新”趋势,例如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s);有关依附理论和民族大众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之贡献,也将在下面予以考虑;最后一节,则从不同形式的、新世纪的拉美的马克思主义来考察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展望。实际上,是否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拉美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我们需要考察的问题,但是最终这个问题是无定论的。 一、拉美的马克思 1873年,位于阿根廷的第一国际领导人雷蒙德·魏玛(Raymond Wilmart)建议马克思,如果没有欧洲移民浪潮的推动,阿根廷几乎无法取得任何进步,因为当地人“除了骑在马背上,什么都不会做”。马克思在阿根廷的驻地记者展示了拉美在独立后时期同复杂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交战中的完全无能。这背后潜藏着一种对新世界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天自信,魏玛与其他无数移民都共有这种自信。不幸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实现拉美对进化论的打破以及他在后期著作中提及的有关爱尔兰和俄罗斯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评注对该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变得多少有些尴尬。例如,谁会支持恩格斯在1847年脱口而出的评论“我们目睹了墨西哥被征服,并为此感到高兴……这关乎墨西哥自身发展的利益,在未来它将置于美国的监护下”①?恩格斯(也有人假设为马克思)坚持“富饶的加利福尼亚”而反对“懒惰的墨西哥人”②。 也许,比马克思在拉美公开的进化论声明更为重要的是,他参与了南美独立运动英雄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领导的运动,并因此成为1858年《美国新百科全书》的一个条目。马克思专注于玻利瓦尔的独裁统治,而非关注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玻利瓦尔喜欢庆祝盛典、慷慨激昂的宣言和初期的个人崇拜,使马克思把解放者作为拉美反思法国拿破仑三世的一个次要编目。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完全未提及有关玻利瓦尔的历史地位、原著民族的现状以及独立斗争中不同阶级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的分析。看来,马克思在此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将美国视作一片飞地,在那儿即使有事发生,也只是对发生在欧洲的事件的一阵回音或无力反映。马克思对单一民族国家如何在欧洲形成的理解,至少模糊了他对美洲的印象,而他的政治概念几乎无助于他理解拉美独有的通往现代性的路径,更不用说同情。 马克思不得不说印度引导了他对拉美的态度:“印度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没有已知的历史,我们所称的印度史只是连续的入侵者的历史。”③马克思渗入拉美的背后,隐藏着这种欧洲中心论和殖民主义核心论的偏见。例如,它使马克思将欧洲大陆视为仅仅是对西班牙革命的一种制动,视为波拿巴主义者扩张的腹地。马克思甚至无视玻利瓦尔的革新泛美计划,他关心的是如何防止南美洲的巴尔干化,这自然是他和恩格斯同情欧洲的共同目标。在何塞·阿里科(José Aricó)看来,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都认为“美国只存在于欧洲,或者准确而言,拉美只能根据它对欧洲的反映情况来从外部予以考察,因为它的内部实在难以理解,因此其不存在”④。不仅是马克思忽略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拉美的特殊路线,而且他的那些范式似乎也无法把握那里发展的经济、政治和种族的特殊性。在历史唯物主义被证明是一个分析和指导拉美革命家活动的富有成果的工具之前,马克思主义不得不通过“民族化”的程序。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其欧洲中心主义依然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 马克思的思想通过一代代移民或欧洲知识分子、社会思想家和活动家在拉美发芽,或许象征性的人物是来自阿根廷的胡安·B.胡斯托(Juán B.Justo,1865~1928)。胡斯托是这群追求“拉美化”的马克思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力图使他的思想适应这片他似乎不甚了解的土地。1895年,胡斯托不仅完成了第一次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西班牙语翻译,还帮忙成立了阿根廷社会主义党。尽管他声称他的灵感来自于马克思,但胡斯托发展道路上的主要导师是“修正主义的”的社会主义者伯恩斯坦、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尤为重要的是,还有早期社会进化论者斯宾塞。他的马克思主义“拉美化”将被完全烙上进化论的思想。其实,他把马克思误读为一个进化论者,事实上,这将是一种对国家形成时期拉美的领土扩张论的释然解读。他在阅读时喜欢采用马克思的综合历史视野,但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帝国主义理论没有多大感觉。胡斯托反对像曼努埃尔·乌加特社会主义党的成员对美国统治和甚至同化的雄辩警告,认为外国资本对于发展来说是必要的,它将加速拉美大陆的进化过程,并最终(虽然从来没有明确何时实现)奠定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基础。 从本世纪初起,拉美的马克思主义有时以一种混杂的形式反映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分裂和转变。由胡斯托和横越拉美大陆的思想家们一起领导的社会主义适应了一种议会制程序,这种程序有时能取得重大成就。他们建立了一种仍沿用至今的话语和实践模式,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参与了一场重要的复兴运动。他们实证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有移民愿望的工人以及后来的移民企业家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有助于强迫农业寡头承认基本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促进了新世界的“文明”。这种进化的趋势被1917年的俄国革命所瓦解,其影响犹如一场海啸横扫拉美,其世界末日式的语调和救世主式的预言在拉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它并不处在列宁主义思想和共产国际的连续性的拐点之前列,但就其组织承诺、革命热情和其活动分子的切实品格而言,拉美完全是一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沃土。共产国际主宰了拉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至少直到1959古巴革命。拉美的思想家没有像何塞·卡洛斯·玛利亚特吉那样坚决却不浮夸,人们称他为拉美大陆的葛兰西。 二、玛利亚特吉和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 秘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领导者玛利亚特吉,在流亡欧洲的那几年里,他可能遇见过也可能没遇见过葛兰西,但是,他们两人的思想却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如果葛兰西是那篇将十月演绎为“反对资本家的革命”的文章的作者,那么玛利亚特吉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拉美革命的发动者。他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流动的、开放的,与共产国际迂回曲折的教条主义学说格格不入。和葛兰西一样,他欣赏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作品,这使他的思想中产生了一定的“唯心主义”,或许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倾向。他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想象成终结的或封闭的思想体系,而是一种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分析的非教条的、流动的和创造性的指南。玛利亚特吉尤为理解这种政治策略被迫得以实施的文化语境的变化,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全基于现实、依据事实的方法,而非像某些人错误理解的那样,是一堆严格控制结果的原则,它与所有的历史气候和社会纬度是不同的”⑤。在他所强调的主观因素中,玛利亚特吉驳斥了所有的决定论,并认为马克思主义“表明自己是革命的,严格的决定论从来都不是被动的”⑥。 今天还存在着一个多产的玛利亚特吉神话产业,他的记忆往往为那些不同的武装力量诸如改良主义的秘鲁将军们和光明之路的原教旨主义游击队们所宣称利用。然而,多数人认为,玛利亚特吉的是一种“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对他而言,社会主义党“使其实践适应该国家的具体情况”⑦。整个殖民世界的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随之被想起——而他则强调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的、文化上的特殊根源。葛兰西亦是如此,普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地说是列宁主义)在于更好地理解现实而不是它的发源地的那种能力,以及将新现实转化为原始推动力的那种能力。所以,对玛利亚特吉而言,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作为一种普遍真理“应用”于秘鲁的,而是有必要变成一种真实的对秘鲁社会现实的表达。玛利亚特吉有时(像葛兰西一样)被指控为折衷主义,例如,他对乔治·索雷尔(George Sorel)的革命工团主义表示赞赏。当然,玛利亚特吉似乎与被称为“实际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因素维持着一种冲突关系,但是他的多面性和积极从事秘鲁现实以及可行的政治实践和建设的活动,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本人的优良传统。 玛利亚特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拉美化的重要贡献就在于第三国际所谓的“本土问题”中。正如何长新(José Aricó)所记载的那样,“本土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交汇,或偶然的关联”在于玛利亚特吉对秘鲁历史问题分析的核心⑧。玛利亚特吉不仅根据土地问题来解读本土问题,而且也从广泛的文化主义视阈来理解。他基于印加帝国的共同价值观,设想在秘鲁建立印度—美洲社会主义。如果秘鲁没有相当庞大的工业无产阶级,那么玛利亚特吉就会自然趋向土著和农民群众。然而,玛利亚特吉“复兴本土”的信仰比正统的工农联盟转化为秘鲁国民而言更进一步。他与本土运动之间的联系使玛利亚特吉接触到如他所见的“现实的”或“隐蔽”的秘鲁。与此同时,中国的毛泽东正在阐述同样的思想和以农民为中心的行动路线,以及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土地改革问题,这也许不是巧合。 虽然玛利亚特吉是国家化马克思主义者和本土社会主义理论家,但他也是一位拉美的国际主义先锋。他的思想不是狭隘的本土的民族主义,他一直承认他形成的欧洲经验(例如,他参加了1921年在利沃诺举办的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大会)。他的日记《Amauta》(在盖丘亚语中表示“老师”)促进了与古巴和尼加拉瓜革命运动的团结和早期的俄国革命。在其著名的短文《国际主义和国家主义》(Mariátegui,1973)中,玛利亚特吉不仅清晰阐明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还预言了当前网络社会全球化的问题。 通信是国际主义和人类团结的神经系统。我们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迅速、快捷,借此,理念被传播,思想与文化趋势被传送。在英国所开的新思想之花不一定就是英式思想,除非它花时间去印刷。一旦被报社推出,那么只要这个思想表达了一些普遍真理,就可以瞬间被打造成一个国际思想。(摘自Waterman,1998:257~8) 玛利亚特吉的思想不是抽象的国际主义,而是立足于国家现实的。他仅仅是相信资本主义能使人类的生活国际化,因此,国际主义已成为一种历史现实。 像玛利亚特吉这样如此有潜力且独立的思想家与领导者一定会与共产国际的“官方马克思主义”起冲突。很多问题都迫在眉睫,包括玛利亚特吉强调的农民阶级和他的原住民主义。他死后,拉美的第三国际与“平民主义者”对“玛利亚特吉主义”的背离展开了斗争。在1929年拉美共产党会议上,玛利亚特吉因称其党为“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而遭到谴责。人们花了太多的精力去讨论这场论辩的意义,以及玛利亚特吉在多大程度上背离马列主义,但似乎有代表性的仅仅只是他强调改变马克思主义去适应具体国家现实。基于“社会主义”一词的合法性而与“共产主义”相对比,它可能仅仅是一个决定,但它似乎也可以被视为玛利亚特吉从教条的中央集权教义组织中获得独立的象征。第三国际及其忠实的秘鲁追随者对“平民主义者”的谴责予以答复,其次,只有“托洛斯基分子”才是偏离真正的共产主义的词汇。后来在1959年的古巴革命和1979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起义革命中,人们发现玛利亚特吉大部分思想的统一表达(虽然并不总被认可)。 三、从斯大林到卡斯特罗 1929年的拉美共产党会议对“玛利亚特吉问题”进行总结之后,共产国际在拉美的实践进程则反映出了俄罗斯和欧洲策略的曲折性。这种意识形态的依附性就是会议上复杂的“本土问题”的减少和刻板的“国家问题”的增多,这就导致了不少拉美代表抱怨说,他们罔顾拉美大陆的现实痼疾而不加思考地运用欧洲纲领。共产国际的“阶级对抗”的第三阶段导致了1932年萨尔瓦多一场灾难性的农民暴动,尤其是1933年的古巴叛乱,见证了在蔗糖工人间“苏维埃”的形成。由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领导的反对美国占领尼加拉瓜的民族主义斗争,却在完全错误的基础上被共产国际解散,这种错误的基础就是认为:“斗争最后以桑地诺的投降结束,而让反革命阵营得以横行。”(Aguilar,1968:199)在1935年之前,在共产主义者圈内仍有许多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且在革命历史阶段和主导的共产国际阵线之间存在某种和谐或“契合”。1935年以后,随着人民阵线的开创一直到1945年,在玛利亚特吉的回忆中,最终由于缺乏“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以致古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领袖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Julio Antonio Mella)和智利工人领袖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Luis Emilio Recabarren)惨遭失败并成为历史。 在智利,人民阵线战略得以最坚实地运用,在那里曾产生了培育民主传统的效应,以议会为基础的改良主义于1970年以人民统一胜利而告终。对工会和社区活动家的整个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一种新的“共识”,并且激发了艺术家对作品的创作,如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不过,随着智利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中心论却造成了阿根廷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历史分离。在1941年以后,苏联共产党的“与民主相对立的法西斯主义”路线却为阿根廷带来了官方马克思主义(连同英国大使馆),并以此来反对民粹—民族主义者庇隆将军及其已经成为“法西斯主义”支持者的工会。直到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都与正在扩张、充满自信的劳工运动相分离,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一词却以相反的涵义在流行。更富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包括一些托洛斯基分子)与在全国流行的庇隆主义工党传统相结合,并做出了一些原始分析。问题是,无论它以某种方式起作用与否(智利的抑或阿根廷那样的),从外部植入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创造革命性共生状态的最好方式。 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沉睡在1959年突然被古巴革命所打破,卡斯特罗在1961年宣布他确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后来古巴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参与了这场革命,但是它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一场“反对马克思”的革命,或者正如古巴思想家所说的,是一场“革命中的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影响持续了20年甚至更久。通过克服重重困难,以及其“输出革命”的大胆见识,它所唤醒的团结力量横扫了拉美政界,从而古巴革命逐渐支配了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然而,这样一来,它可能会被苏联国家利益所吞并深陷于此,在某种程度上,卡斯特罗今天的表现恰似一片旷野上的正统之音。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大部分70年代的时间里,古巴革命在拉美创造了一个坚定的新马克思主义混合体。卡斯特罗主义或格瓦拉主义为曾经陈腐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在拉美,托洛斯基分子对永久性革命的见解似乎重获新生,正如尘封课本中的革命在武装斗争的效力下“分阶段地”消失在准弥赛亚信仰所制造的漩涡中一样。 古巴混合体已经扎下了根,并且在1967年拉美团结组织(OLAS)断然作出了总结声明:“古巴革命的教训表明,在欧陆范围内的表达人民真情实感的游击战武装斗争是最有效的,并且是我们国家展开革命战争的最佳形式。”⑨虽然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逝世的那一年可能都无法停止对武装斗争的讨论(武装斗争已然呈现出自身的生命力),但那些作品却被奉为经典。因为这些“教训”有时会轻率地用于一代活动家,并给巴西和阿根廷的街道上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游击战策略的缺陷凸显了出来。首先,武装斗争的支持者的“自动评论”是三心二意的,它们只评论特殊的战略应用模式,但是,道德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治基础开始逐渐遭到质疑。我们在随后的章节中将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改变民主的价值,而政治(而非蛮力)开始再次崭露头角。回顾过去,正是官方共产主义中的穷困潦倒的马克思主义为古巴混合体创造了蓬勃发展的空间。 1979年桑地诺起义的成功就像是另一波于1959年开始的古巴革命浪潮。国际力量的平衡似乎更顺利,并且人们期望的新阶段、重新调整、重新装备和决心似乎正在展开。然而,10年后,官方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的经历结束了,而选举出来的桑地诺在1年以后也失去了权力。也许桑地诺经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尤其是涉及经济困难、民主社会主义政权和原住居民的民主行为的复杂性这几方面。桑地诺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军国主义、“人本主义”、性别歧视的危害性的教训。虽然,其核心在于桑地诺主义是在拉美的一种民族—大众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绝唱,而不是新浪潮的开端。桑地诺主义从未在美洲中部特殊地区之外产生过多大影响,并且,在智利(见下一节)迥然不同的政治动荡却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的圈子内。桑地诺主义的倒台,也标志着作为左派可行战略的“武装道路”的终结。尽管哥伦比亚还持续发生“传统的”共产主义暴动,但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在20世纪90年代展开的和平进程,则开启了更为典型的后冷战的政治阶段。 四、革新者和萨帕塔主义者 1973年,智利的皮诺切特(Pinochet)将军推翻人民统一政府,是另一个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事件。而少数托洛斯基分子却相信这一事件证明“唯一的道路”就是“武装道路”,对智利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它开启了意义深远的反思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革新论者——今天主导智利的左派——并且成为后皮诺切特政治体制的指导力量。他们批判拉美经典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目的论维度,并且表达了一种新的、更民主、更灵活的愿景。他们试图将革命活动的轨迹从对国家政权的正面攻击,转移到公民社会和新民主领导权的重建上。他们把法治作为一种绝对的人性善,而不是一种狡猾的资产阶级诡计。如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在皮诺切特独裁统治之下,“正式的”和“真正的”民主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首先,反对先前的孤注一掷的政治零和博弈概念(例如原产地或守法者:国家或死亡),革新者开始提出妥协阶级的禁忌问题,为了跳出独裁政治,我们有必要与整个“资产阶级”政党形成一种稳固的民主契约。 革新者不仅主张一种撤退战略,而且还要求对他们的意识形态进行美化。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出现的一个分水岭就是,它不仅影响南部角落,而且还影响中美洲及其他地方。在传统上,拉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多元化、和解或妥协的整个概念抱有怀疑。政治在本质上是摩尼教的构思,往往被视为一个扩展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战争而占据上风。20世纪80年代,这种救世主式的政治概念面临一种政治“神圣化”的号召,民主随着改革倾向的非军事化得到革新,政治也由此被突显了出来。随着民主和公民社会开始崭露头角,改革不再是对拉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简单阐释。正如智利的政治科学家曼努尔·安东尼奥·伽雷通(Manuel Antonio Garretón)所阐释的新观点:“社会主义模式并不存在,存在的是社会主义的过程……社会主义不能被定义为建立一种一劳永逸的社会模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消灭各种异化、压迫与剥削的社会转型原则……这种原则是基于社会解放和赋予人民权力的理念之上的。”⑩ 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不能与它的标志性影响孤立开来理解,这种标志性影响就是葛兰西的思想观念,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就在该领域产生。尽管拉美既不算东方也不是西方,但葛兰西在20世纪20年代对意大利的精确分析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然而,古巴的新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鼓吹成完全的替代品,受葛兰西影响,他们允许霸权主义概念和迥然不同的、开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葛兰西式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鼓励了对拉美现实的一连串有力分析,该现实围绕霸权主义、公民社会和“进化论”等概念而展开。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的理解远比单纯的压迫工具的理解更为细微,并且历史上的集团概念指向所属阶级发展的新战略。阶级还原论和经济主义变得不再普通,政治变得不再本质主义。新的革命战略轴心是由这样一个群体所构成的,他们可以在过渡性的表达人民(印第安村民)需要的计划的建设中获得领导权。存在着一段隐藏的葛兰西加入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理论和实践的历史(11),并且该实践为新旧左派之间的政治提供了关键性的链接。 1994年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以及它的国际分支似乎与界内的葛兰西式的革新趋势背道而驰。再者,似乎更可能的是“暴风骤雨”,武装斗争是有效的。正像在拉美经常发生的那样,萨帕塔的事业以某种简化方式流传到了国外。丛林中的土著叛乱分子在网上公布公告的蒙面形象绝对是惊人的。然而,萨帕塔主义的社会与政治现实相比之下更平凡、更复杂,它的一些活动分子来自毛派团体,他们在1968年的学生大屠杀之后拿起了武器,其思想观点中包括了一些“持久战”战略,以及长期的和秘鲁光明之路所采取的方式相异的武装力量的积累。但是,正如桑地诺主义者所说,他们的话语更多地带有葛兰西式(或玛利亚特吉式的)的语调,他们的政治实践更多地带有一种实用主义的非教条化的倾向。复杂的拉坎敦人地区本土政治无法渗透到这里,但是他们的计划和需求在参与开发的成果方面,却和他们的“民族个性”一样多;确实,在过去,民族认同将不同的本土群体分离开来。所以,萨帕塔主义获得了什么呢?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称萨帕塔主义为“首个信息化游击运动”(12)。然而,所开展的武装斗争却过于政治化,它的目的是作政治声明,而非赢得战争。一个相对薄弱的起义运动是能够利用现代通信手段来捕捉墨西哥人民的想象力和动态的国际团结运动的。政治领袖和恰帕斯州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比起由上而下金字塔状的共产国际和其激进的接班人,它与民族精神的新社会运动更为一致。萨帕塔主义者明确表达了一种对全球化蹂躏的个别地区性回应。然而,它也充分唤起了他们作为墨西哥爱国者和民主主义人士要求政府尊重它们自身宪章的需求。墨西哥社会广泛的共鸣,反映出了他们开放革命民族主义人民传统的能力,是萨帕塔记忆中的代表。如果将拉美的政治视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萨帕塔主义则反映出大陆——从“前现代”到“后现代”——它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它的自然而不走极端的安全界限,以及在西方及其余地区之间的混合的短暂性。但请记住,鲜为人知的(从一种激进的民主观点看来)秘鲁光明之路也反映了这一反常的后现代状况(13),寻求湮灭其他声音的那种主张是行不通的。 五、知识分子的贡献 必须指出,拉美马克思主义往往是在发达国家被作为从格瓦拉到萨帕塔主义的一系列偶像而“消耗殆尽”。然而,根据欧洲人的理论,它是由拉美来决定行动的。而拉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即使是行动浪漫派的象征——格瓦拉都似乎有过独创的经济分析,从而为社会主义转型期的批判性理解做出了贡献。(14)如果我们要列一张拉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清单的话,那么它将包括:(1)依附理论;(2)“民族—大众”理论;(3)激进民主理论。 在拉美,各种发展与欠发达的理论都紧紧围绕着“依附”概念,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时刻和在该领域内的激进思想。在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将它推广到西方之前,拉美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发展列宁抛弃掉的“依附”一词,将那些政治独立但经济仍受帝国主义控制的民族国家描述得相当复杂,并具有细微差别。它不仅形成了全球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必要联系,还探讨了这些经济关系本质上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在一个被忽视的调查中,凯岛(Cristóbal Kay)详细考察了不同的依附学派,并总结认为,如今在这个曾经无所不能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枯竭之后,这种对发展的批判性观点或许会再次获得一些影响(15)。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是作为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感知上的失败的一种自觉反应,从而直接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前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关注的是世界体系和西方世界,而不是殖民地的发展问题和后殖民世界。过激的依附理论往往可以追溯到在西方简化了的传播,的确,迄今为止,这一观点给拉美史提供了一些最为思辨的结构性/历史性的参考读物。考虑到阶级与族群关系,国家的作用和“文化依附”的问题都是全球化时代流行的问题。依附理论争论的一个分支就是围绕“边缘化”这一问题开展的,即拉美贫民区的流动人口无法被还原为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一本源自非欧洲中心论的“社会排斥”争论的结论性读物表明,其许多争论的主题都在20世纪70年代拉美有关边缘性问题的辩论上有过兆头。 “民族—大众”的范畴——部分地说——进入了拉美政治词汇并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一部分,但它也代表了大陆葛兰西运动所做的一大贡献(如果可以那样说)。在依附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葛兰西主义者认为,底层群众的阶级意识形成了一种主要的民族大众的形式。他们反对阶级还原论和操纵党派的各种形式,民族—大众的概念代表着正统说法的断裂。阶级民粹主义的解读已经证明了其机械性,而新方法直接关注的是重要的、散乱的领域。当然,机械模式基于马克思自身对社会阶级的粗略分析,这种社会阶级在例如拉美的一些社会中几乎没有市场。在这里,并没有出现原原本本的无产阶级,而是与玛利亚特吉和葛兰西的分析语调更为一致的“大众阶级”。就民族维度而言——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盲点——它在拉美几乎没有崭露头角。这是一种“民族—大众意愿”的葛兰西式主题,它将为反对独裁的民主斗争提供依据,并帮助构建民主的替代性选择。这些都是已经被大量应用于南非斗争中的概念(16),南非在此之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后则成为了第三世界中的独裁主义的发达国家。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阿根廷政治理论家拉克劳的影响业已变得非常有意义。在他的著作中,我们不仅发觉了一种很“拉美式”的葛兰西影响,而且还可以发现具有庇隆主义民族—大众话语的持久影响。有着广泛影响的“激进民主”观念(17)以此方式明显地在拉美扎下了根。拉克劳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裂可以在他现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中找到,“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社会蓝图,而开始成为一种激进的社会组织民主化的一部分”(18)。显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对解放的需求是多样化的,而围绕任何“重大转机”而形成的统一似乎都是不可能的。然而,新社会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为民族自决所做的斗争可以与拉克劳所谓的“一系列民主对等”联系在一起。这些观点已经引起了一场广泛持久的国际争论。我们在此唯一的目的是在拉美找出它的起源。正如拉克劳在自传性政治访谈时说的那样:“我开始系统性地读葛兰西和阿尔都塞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的解释基本上是政治的并且是非教条主义的,因为我可以将它直接与我的阿根廷经验联系起来”。就个人主观或空间术语而言,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看起来不同于拉美,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主观的和/或空间的条件中去解释。 或许最后我们需要去拷问:是否存在如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拉美化”这样一个抽象概念呢?我的基本结论是,在拉美,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尝试并没有导致一种根本上新的混合体。在阿根廷,在实现这种混合的庇隆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会议上,民族主义话语权往往占上风。所以,马克思主义拉美化是一种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最教条的到最创新的。尽管它在西班牙语系之外的世界并不是十分出名,但玛尔塔·哈内克(Marta Harnecker)的第一本阿尔都塞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却在一个高文盲率的地区卖出了百万印数的四分之三。简化版阿尔都塞主义惊人地受欢迎,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拉美传播过程中的一个显著关键。哈内克的系统性说明和马克思主义的贫瘠在《社会革命:列宁和拉美》中达到了新的深度,它通过一种文字记载的俄国革命镜头来解读拉美,可谓是一种奇异的尝试。在另一个范围中,许多拉美文化理论家复兴了一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在此没人比得上内斯托尔·加西亚·康克里尼(Nestor García Canclini),他的《关于1992年的混合文化》具有相当大的跨学科影响力,并且曾被第一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詹明信大加赞赏。(19)文化转向同样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并进一步真正意义上把拉美的根留住。 六、复兴革命 对于拉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发展前景,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要么被废弃并且最好被忘记,要么它正在经历一场华丽转身。许多昔日的信徒现已成为新自由主义狂热的拥护者,并铭记蒂娜(TINA)的箴言(别无选择)。这种反应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前共产党人指责的“失职的上帝”(20)那样,只能作为一种可以理解但不是特别富有成果的回应。前游击队指挥官时不时地热情接受国际新秩序的起因,社会运动的前领导人已经进入智利政府并继续推行本质上属于皮诺切蒂斯塔(Pinochetista)的政策。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激进依附理论之父或甚至可能是始祖)于1994年到2002年间在巴西掌控着一个反人民的政府。即使这样,简单地背诵这些背叛的事,会错过一些当前形势的某些细节,并陷入道德批判的危险中。或许看待拉美左派的发展前景更恰当的方式,是将1989年的世界历史事件视为一个契机而非终端。在许多方面,共产主义的崩溃已经解放了拉美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再需要保卫站不住脚的观点(或无休止地辩论的对苏联社会主义的严格批判),并且可以更自由地控制无疑在拉美左派中储备的创造力和活力。 我们从“忏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向诸如杰姆斯·佩特拉斯(James Petras)的“复兴者”,他对左派来说,是一个新的黎明的到来。对佩特拉斯而言,“拉美的左派正在筹划一场重要的复兴……大量的反对派运动正在增多并及时挑战整个自由市场权力结构的统治”(21)。他指出,巴西的失地运动,哥伦比亚的可卡种植户、智利的共产党,当然还有萨帕塔主义者副司令官马科斯,都是真正的新马克思主义先驱。对佩特拉斯而言,“两种动力处于愈发对抗的模式中:农民与美帝相对抗”。根据佩特拉斯所说,这种新的动态(重演了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二元对立)受到了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他们将自己隐藏于非政府组织中,通过帝国主义日常工作计划来从事研究。人民斗争的新浪潮似乎真的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而许多革新者也确实没有理睬曾经引起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然而,人们却很难看到,这样一种对20世纪60年代思想的不加批判的情绪和联想,是如何为下个世纪引出一个可靠的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作为一个改革论者的转换战略——与最受压迫的社会群体代言人萨特相比——它缺乏市场人气,并带有浓烈的殖民主义高贵的野蛮人神话色彩。 今天,对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较冷静的观点是,致力于对以往实践的认真重估以及对未来的世俗化看法。首先,由于反对佩特拉斯问题,他们意识到应义不容辞地提供一种可行的政治经济学来替代新自由主义收益递减的经济方案。豪尔赫(佩特拉斯嘲讽的特权接班人)就是这一倾向的典范,他的《手无寸铁的乌托邦》一书具有广泛读者。对豪尔赫而言,拉美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像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那样,再次成为社会融合的动力。在拉美更有必要的是采取发展工业的民族战略,包括复兴福利国家。民族、工业化和福利国家,这种老式的三角关系是一项改革计划,也是一项民族—大众计划。据豪尔赫所说,如果这些没有实现,那么森德罗斯·卢米诺索(Senderos Luminosos)反而会考虑他们国家的社会分化,哥伦比亚的制药行业和里约热内卢的暴力用的也是同样方式。豪尔赫在拉美取得的反响并非由于广泛的改革派背离,而是他及时地提出了一种民主、公平、可持续的选择来代替现状的需要。这就是批判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不曾及时参与其中的一项任务,这项任务在20世纪70年代曾被严重地误判。 在拉美的马克思主义比它之前有过的形态更加多元化。不仅有潜藏于相同标签下的大范围的政治信念,而且政治实践也已经扩展到多个领域和形式中。正如康克里尼指出的那样,现在新左派面临的任务是权力的文化重组:“分析从纵向的、两极化的社会—政治关系观念转移到偏离中心的、多重决定的观念所产生的政治后果。”(22)在社会、文化和当地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新形式的激进思想(23),但它们不能被还原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闲思而对美帝的挑战毫无作为。正如葛兰西所言的,当旧范式明确被淘汰时,新范式仍在成形中。 拉美“复兴革命”的机会在何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古巴后卡斯特罗的终结,和墨西哥左派挑战体制革命党(PRI)的能力。为这些国家中复兴的或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突破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国际联络部的阿米罗·阿伯(Ramiro Abreú)来说,“拉美左派正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很少有左派能够具有这样明确的认识——资本主义无力解决我们的问题以及我们对政权的那种期望。但是左派也面临许多道德、政治、社会、思想和心理问题”(24)。拉美左派的认同危机比1989年以后社会主义典范国家的瓦解具有更广泛的根源。武装斗争已经留下了沉重的遗产,当然也带来了镇压。对马克思主义拉美化而言,要彻底清除基础主义者从来都非易事。同时它也缺乏与女权运动的交互,女权运动从另一个维度做了诸多努力来改造左派。当理查德·哈利斯(Richard Harris)指出“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25)仍可以作为拉美的行动指南时,我认为,如果他们想要实现其目标,那么这些“修正”也一定是重新来过。 七、展望 哪怕我们把刚发生的事写入上述章节,没经过几年,那些事件又在拉美(或别处)迅速地发生了变化,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一次把社会主义或至少是社会转型提上了议事日程。佩里·安德森在拉美说道:“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将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的对抗和文化、社会、民族联系起来。”(26)这一结论无疑与我们对拉美马克思主义历史梗概的阐述相一致,这说明了势不可挡的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既是社会同时又是文化的政治方式的重要性。安德森也强调了拉美连续革命的历史,从近乎一百年前的墨西哥革命直到今天。尽管这种连续性和革命性质可能会遭到质疑,但安德森的第三个特殊观点是相当有说服力的:“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发现政府和群众运动在反抗新全球霸权的前线形成联盟”。拉美不仅见证了世界社会论坛在阿雷格里港市的诞生,还有半外围性国家强大的G-22集团在坎昆的建立。 世界社会论坛聚集了世界上无数地区性和民族性议题,这个论坛于2001年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市开始产生影响。工党通过其典范的参与式预算经验控制了南里奥格兰德州和阿雷格里港市民,是抱有全球化野心的变动的关键因素。“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一观念反映了其拉美的起源。同样,工党先是在南里奥格兰德州,继而又在阿雷格里港市失去执政权力,这使得2005年的世界社会论坛的组织变得非常复杂。这种拉美的动态或根本的循环动力和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社会论坛本身存在的理由在2005年后变得不那么透明或易懂。现在,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更为持久的组织来提供具体的政治策略?或者,它是否足以对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构成另一种道德选择,用以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的国家、政党与政权的观念呢? 根据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挑战的理论化,其必然的参照目标是哈特和内格里的(Hardt and Negri)帝国。(27)它在拉美得到认可,完全不同于它唤醒全球大片领域内的左派的欢庆基调。虽然拉美的评论家无人怀疑这个内格里计划的政治品格,但内格里计划还是因其大体上乐观的全球化视阈和内在的欧洲中心主义而受到猛烈谴责。“帝国”这个特殊概念作为一种去中心化和无领土化的主体,看起来是专门从拉美的视角抽取出来的,它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概念,正如典型的欧洲帝国主义概念一样现在已经结束了,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获得霸权。但批评人士内斯特·科汗(Nestor Kohan)发现“有关帝国最具诋毁性、最挑衅性的论题之一”(28)在于哈特和内格里的反依附概念,他们认为,诸如拉美的这些地区在种类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于在美国流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体制,更确切地说,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另一种尝试改写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革命的理解的,是约翰·霍洛韦(John Holloway)的《不用掌握政权而改变世界》。这本书的知识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部分左派分子赞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自治论者的激情。因此,它并非与内格里大胆尝试反全球化的政治和战略无关。但是霍洛韦的知识/政治事业,实际上与萨帕塔主义的出现与反思是不可分割的。夸张而又奇怪的是,将类似于雷吉斯·德布雷《革命中的革命》关系作为一种参照,也包括对古巴革命的部分解读。霍洛韦的基本信息实质上很简单:我们必须区分“把权力强加于(power over)”(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制特征)与“把权力赋予(power to)”(需要为那些力求改变世界的人所用)这两个概念。在阿根廷2001年危机后,这一思想虽然获得了一些追随者,但总的来说是迫于强权政治的压力、党派政治的现实,一个真正发达的公民社会的缺乏,就使得实践中的政治信息稍稍边缘化了。 为抵制内格里和霍洛韦的自治论激进主义,一些知识分子趋向于重新阐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来予以反对。因此,佩特拉斯和梵特迈耶对于2000年后出现在拉美的中间偏左政府的评论,在涉及地区发展或改革选项上是非常尖锐的。对这些作者而言,简单地是:“选举政治约束了现行政府的任何党派,将其转向新自由主义——统治现行政府的武装力量……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争取国家权力的‘时刻’已经……失去了。”(29)国家权力的转变方式并不是通过地区政治或可选择的发展战略(由世界银行推动从而分散大众能量)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构建一种关键性的人民起义武装力量,并动员他们加入到运动中来隐性地打击政府,同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仿佛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当时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国家和政权在现实的政治界获得了共鸣。虽然这些观点将会持续下去,但是,改革选项却不会使可持续发展或适当的生活水平再传递下去了。 在当下的拉美,要想描绘一幅乐观的“历史行进”图是很容易的。直到2006年,许多国家仍存在左翼或左派政府:在巴西有卢拉(Lula)和工党,在委内瑞拉有查韦斯,在厄瓜多尔有古铁雷斯,在玻利维亚有莫拉莱斯,而纵观南锥地区:在智利有西尔维亚·巴切莱特(Silvia Bachelet),在阿根廷有内斯托·基什内尔,而在乌拉圭有广泛阵线(Frenti Amplio)的塔瓦雷·巴斯克斯(Tabarévazquez)。当地区主义和民族主义再次摆动起来时,全美自由贸易区的美国梦便完全破碎了。社会运动尤其是在安第斯国家的本土运动再次积极表达了他们的需求,并提出了另一种未来的愿景。只有哥伦比亚处在独裁主义政府和一种老式的共产主义叛乱间进退两难,似乎难以得出进步性的结果。通常民主正在加深,反动势力处于混乱之中,而新自由主义霸权备受争议。如果不完全是革命的话,似乎一场改革浪潮正在席卷拉美大陆。 然而,也可以采用更为批判性的观点来看待现下的拉美政治,它并没有为国际左翼提供令人欣慰的革命思想。首先,我们需要提及卢拉领导下的工党,它是巴西整整一代社会主义者的希望所在。佩特拉斯和梵尔迈耶悲痛地写道:“为了证明工党是一个可接受的与巴西财团的对话者,所以它在早期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身份。”在拉美,不论最成功的社会党的这种转型是否由于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妥协,何时执政至今仍不清楚。在2006年,工党深陷一场贪污丑闻(贿选),甚至由此毁坏了它的形象。尽管卢拉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在该过程中毫发未损,但卢拉的首任“工会主席”不再被视为新的民主的、非斯大林主义的、非中央集权的、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的象征。 委内瑞拉和其现任总统查韦斯在定义当代拉美社会主义和社会转型的意义上又是另一个深刻且重要的案例。而古巴、尼加拉瓜和最近的萨帕塔主义者的情形是,有很多国际评论家以救世主的角度来看待查韦斯。在2005年阿雷格里港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上,查韦斯的能量几乎使参加的人充满了巨大的吉岗汀湖体育场,他因此成功地成为拉美反新自由主义、反新帝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2006年的地区社会论坛因此毫不令人奇怪地在加拉加斯举行。但这并非没有反对者,这些反对者来自反中央集权和男女平等主义者的左派,他们看到了“大人物”在拉美政治中的再次重现。查韦斯还以非常雄心勃勃的地区愿望,与委内瑞拉的石油富翁们进行政治交易。时间会告诉我们,到底查韦斯是否是一个近乎庇隆的或者确实代表整个拉美左派的大胆的新领导人。但是,毫无批判的支持态度并非一种明智的社会主义策略。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仍在见证新旧左派之间的冲突,并且始终无法履行理论上的复兴承诺。在拉美大陆,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仍然坚持完全正统的阶级斗争观点,并将其视为“历史动力”、“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以及自由民主的冒险。对其他人而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条道路已经见证了自由民主甚至所谓经济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必然性的稳固归宿。最近,已经与另类全球化运动形成交会,另类全球化运动不仅已经生效,而且也可能引起分裂。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就是,拉美的世界社会论坛“看起来”与新世界秩序的全球标志有所不同,并且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全球发展不平衡的残酷现实和帝国主义超出其明显的表面意义的持久存在,意味着在拉美,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对抗将会采取不同于发达的工业或后工业社会中所采取的形式。 这就是我曾经想将我的思想寄托于“前进道路”的地方。然而,在今天没有一个理智的或政治的傲慢是能令人信服的。真实的情况是,拉美一如既往地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而它未来的政治既复杂又渺茫。我们已经看到政治观点如何倾向于二元对立的分化,在对本土权利的承认和阶级斗争的“回归”问题上,要么“支持”查韦斯,要么就是“反对”他。我们真的必须在两条道路——追求“征服”国家权力和相信可以无需利用国家来改变世界之间做出选择吗?在现实的政治领域,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二难选择几乎是没人去做的。拉美的左翼正在经历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含义正在被不断改造。如果超越乐观与悲观的情形,那么我们不仅能假设一个连续扮演拉美左派、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政治行动的角色,而且也能有信心地预言,这种思想和实践将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编译者郑祥福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超超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外国哲学专业研究生。 注释: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文集》第7卷,伦敦1976年版第527页。 ②《马克思和恩格斯文集》第8卷,伦敦1977年版第365页。 ③S.Avineri(ed.),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Anchor Books,1969,p.132. ④J.Aricó,Marx y América Latina,Alianza Editorial,1982,p.100. ⑤Mariátegui,Ideologia y Politica,Amauta,1969a,p.112. ⑥Mariátegui,Defensa del Marxismo,Amauta,1969b,p.65. ⑦Mariátegui,Ideologia y Politica,1969a,p.153. ⑧Aricó,"Introducción" in J.Aricó(ed.),Mariátegui y los Origenesdel Marxismo Latinamericano,Siglo XXI,1980,p.x. ⑨OLAS,"General Declaration",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28,6(November-December),1967,p.58. ⑩Garretón,"The Ideas of Socialist Renovation in Chile",Rethinking Marxism,2(Summer),1989,p.26. (11)参见J.C.Portantiero,Los usos de Gramsci,Folios Editor,1983,以及Aricó,1988。 (12)M.Castells,The Information Age,volume II:The Power of Identity,Oxford:Blackwell,1997,p.79. (13)参见Munck,“Culture,Politics and Postmodernism in Latin America”,in A.Jones and R.Munck(eds),Cultural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London:Macmillan,2000。 (14)参见M.Lowy,The Marxism of Che Guevara:Philosophy,Economics and Revolutionary Warfar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5)参见:C.Kay,Latin America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London:Routledge,1989;Munck,p.199。 (16)参见A.Norval,Deconstructing Apartheid Discourse,Verso,1996。 (17)参见E.Laclau and C.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Verso,1985。 (18)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xv. (19)参见F.Jameson,“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in F.Jameson and M.Miyoshi(eds),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p.66。 (20)参见A.Koestler et al.,I.Silone and A.Gide(2001[1949]),The God That Faile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1)J.Petras,The Left Strikes Back:Class Conflict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ism,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9,p.13. (22)García Canclini,Hybrid Cultures: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Minneapolis,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1995,p.323. (23)参见Alvarez et al.,Dagnino and A.Escobar(eds),Cultures of Politics:Politics of Cultures-Re-visioning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Westview Press,1998。 (24)E.McCaughan,Reinventing Revolution:The Renovation of Left Discourse in Cuba and Mexico,West View Press,1997,p.9. (25)R.Harris,Marx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Westview Press,1992,p.3. (26)P.Anderson,The Role of Idea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lternatives,UCLA(mimeo),2004,p.42. (27)参见M.Hardt and A.Negri,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8)Kohan,Toni Negri y los desafíos de Imperio,Campos de Ideas,2002,p.69. (29)Petras and Veltmeyer,Social Movements and State Power:Argentina,Brazil,Bolivia,Ecuador,Pluto Press,2005,p.233.标签:葛兰西论文; 拉美国家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