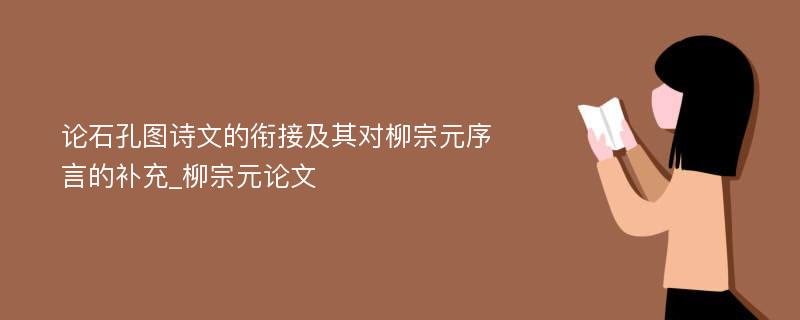
司空图诗文相通论及其对柳宗元一篇序文的补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序文论文,诗文论文,其对论文,司空论文,柳宗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0)05-0527-03
不同文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面很广。就作家而言,一人往往会兼有几种文体的创作,这些创作的异同优劣,可以作为考究辨析文体关系的一种依据。唐代作家柳宗元、司空图于此皆曾发表过意见。并且司空图在对柳宗元诗与文均予高度评价的同时,对其关于文体关系的言论,则有所辨析补正。回顾这两位作家的有关论述,对我们认识两家的文学思想,深入研究诗与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试予介绍。不妥之处,希专家指正。
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云:
金之精粗,效其声,皆可辨也,岂清于磬而浑于钟哉?然则作者为文为诗,格亦可见,岂当善于彼而不善于此耶?思观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始皆系其所尚,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于不朽。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各异,而皆能济胜以为勍敌也。
愚常览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深搜之致,亦深远矣。俾其穷而克寿,玩精极思,则固非琐琐者轻可拟议其优劣。又尝观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张曲江五言沉郁,亦其文笔也,岂相伤哉?……因题柳集之末,庶裨后之诠评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①。
司空图以金属被铸成不同乐器的发声和力士持不同武器的格斗,比喻作者用不同文体写作,即“文人之为诗”和“诗人之为文”。认为:同一作家虽然所用文体不同,但都基于作者的素质而可见其精粗,可辨其格调,即具有某种统一性。他用“驱驾气势”等语评论韩愈诗歌,用“深搜”、“深远”评论柳宗元诗歌,跟韩文给人的“气盛言宜”、柳文给人的幽深旨远的印象是一致的。显然,在司空图看来,韩、柳之诗,与其文相通,有其统一性。同时,他又用杜甫祭房琯文、李白佛寺碑赞,以及张九龄之诗文皆具有沉郁的特征,进一步说明作家为诗为文,格调往往通之于其人。
司空图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以具体作家作品证实了诗文之间的联系和相通。但他为之题跋的《柳柳州集》中却有一篇《杨评事文集后序》,序云:
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彖)》《系》,《春秋》之笔削。……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兹二者,考其旨意,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以著术之馀,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其馀各探一隅,相与背驰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亦甚矣。若杨君者,少以篇什声称于时……晚节遍悟文体,尤邃叙述。学富识远,才涌未已。其雄杰老成之风与时增加……用是陪陈君之后,其可谓具体者欤!……宗元以通家修好,幼获省谒。故得奉公元兄命,论次篇简,遂述其制作之所诣,以系于后。
柳宗元这里所提出的“文有二道”与司空图所说的“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可以相兼的理论,有无抵牾呢?司空图既然为《柳柳州集》作题跋,不可能绕开文集中的这篇文章。并且,追究其题跋的动机,很可能即与这篇文章有关。他的题跋,既要在当时人们普遍推崇韩愈而对柳宗元的认识尚有不足的情况下,正确评价柳宗元,又不能不对柳宗元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有所补说分辨。究其实,柳宗元“文有二道”说,不过源于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辨。由文笔的区别,推到二者难兼。但难得兼善,并不是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兼,更不是说二者没有任何联系和相通之处。就连柳文本身也没有将问题绝对化——“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所谓“偏胜独得”,只是恒见常有的现象,而并非尽皆如此;“兼者”只是“罕有”,而并非没有。否则,便不可能出现陈子昂了。对于诗文可以相通,司空图除了在理论上予以说明,并举出包括柳宗元自己在内的作家为证外,还进一步就柳文中所提到的张九龄作了申述:“张曲江五言沉郁,亦其文笔也,岂相伤哉!”虽只是点到为止,未曾展开。但张九龄在文坛的地位和成就,唐人是熟知的。作为开元时期的重臣和文坛盟主,他与张说都是继陈子昂之后,在诗文革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其以《感遇十二首》为代表的五言诗,抒写被贬后的忧国伤时之情,深于比兴,妙于寄托,沉郁蕴藉,为文学史上的名篇。除诗外,他的文赋也有很高成就。著名的《荔枝赋》被杜甫在《解闷十二首》中隐括成诗②,可见他的赋确实通之于诗。又其《荆州谢上表》,抒写怀抱忠贞,无辜被贬的心情,与其《感遇》情感相通,也足以印证司空图所说的“五言沉郁,亦其文笔也”。根据其针对张九龄予以申辩,可见司空图的议论与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是相关联的,虽未直接点出柳文,却对柳文有所补说和辨正,所阐述的理论很重要,但下笔微婉,表面上似乎只是单方面陈述自己的意见。
关于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司空图无疑是了解其背景和写法的。他的这篇题跋,用笔微婉迂曲,跟能够理解柳文的特殊背景,当有一定关系。柳宗元是为人作序,此种序文,一般总是要赞美对方的文才。且柳宗元为其文集作序的杨评事(名凌)是其父亲柳镇的朋友、妻子杨氏的叔父③。此次写作,更是“奉公元兄命”,即奉其岳父杨凭之命,因而格外需要推崇对方。序文说唐朝只有陈子昂诗文兼善,张说“以著述之馀,攻比兴而莫能极”;张九龄“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兼善是这样困难,但杨评事却是晚节“遍悟文体,尤邃叙述”,可以陪“陈公(子昂)之后”,可见说文之难兼,原来是一种铺垫,用意在子突出杨评事能够兼美。这是中国古代文人为人作碑铭、作序常用的以宾衬主之法。司空图读柳宗元文集为之题跋,知道柳宗元序文的背景和语境,当然不宜过分较真,只要能让人避免对柳文产生误解,即算达到目的,写法则不妨含蓄一些。
《杨评事文集后序》还有一层值得思考和玩味,即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不免以具有宏观的精鉴的眼光自矜,他看到前人有的诗文兼美,有的不能兼美,看到杨评事能“遍悟文体”等等,而柳宗元自己既写诗又作文,并且在文坛上早已有名,其成就又如何呢?此处当然不便说及或点破,但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却可供参悟,其中说他自己的创作: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柳宗元在这里交代他是“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继承吸取的对象既有《书》、《春秋》、《易》之类,同时亦有《诗》、《骚》,可见他认为诗文之间是可以相通的,创作上是可以而且也必须多方面吸取。既然如此,则柳宗元之能够“遍悟文体”、诗文兼善,也就不待言。司空图没有援引柳宗元在不同场合的言论作对照分析,而只是对《杨评事文集后序》所论及的诗文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观点很明确,但由于表达上稍近含蓄,不免需要深入体会。除本文以上所述者外,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对于一般认为属于散文家的韩愈和柳宗元,司空图着重提出的是二家的诗歌,从其风貌特征通之于二家之文方面,给予准确描绘,高度评价,不仅推许其诗文兼善,且特地于文章结尾强调:“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意即不要以“偏胜”之说掩盖了柳宗元等人实际上的“(诗文)全工”。言外,当然也包括提醒人们对柳宗元在特定场合下所谓“偏胜独得”之说,不要产生误解④。
收稿日期:2010-06-01
注释:
① 引文据《四部丛刊》本《司空表圣文集》卷二节录。清编《全唐文》题作《题柳柳州文集后序》。
② 参见钱谦益《钱注杜诗》卷十五《解闷十二首》第九首后笺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1年版,第529、530页。
③ 参见《柳河东集》第十二卷《先君石表阴先友记》,第十三卷《亡妻弘农杨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