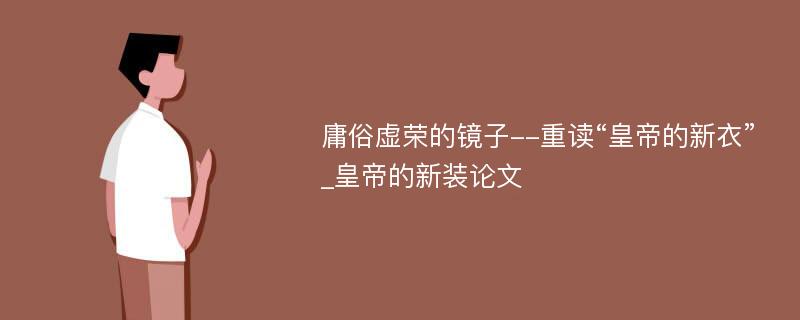
媚俗与虚荣的一面镜子——重读《皇帝的新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装论文,虚荣论文,一面镜子论文,皇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是世界家喻户晓的作家,语文教材编者将其重要作品《皇帝的新装》选入教材可谓慧眼有识。然而,编者所写的课文提示却不甚确切:“作品……以‘新装’为线索,以皇帝爱穿新装成癖为故事的引子,描述了一位骄横一世的皇帝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出丑的闹剧。作品以皇帝这个典型形象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本质。”(注:《初中语文》第一册,北京出版社、开明出版社,1994年6月。)尽管编者在提示的最后, 也写了“在理清故事的情节之后,细细品味,你会懂得这则童话更具一层深意的。”(注:《初中语文》第一册,北京出版社、开明出版社,1994年6月。 )提醒教师学生深入思考,但语焉不详,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前引的论断,而近些年来的有关评论、教案及课堂实录持这种论断的更绝非少数。
那么,作品真的是“以皇帝这个典型形象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本质”吗?
先看一看安徒生写作此篇童话的时代背景。
1835年春,安徒生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和童话《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相继出版。“小说很快就蜚声文坛,引起了普遍的重视,人们争相阅读,议论纷纷,出现了大块大块的评论文章。”(注:分别见原苏联·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227页,马昌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5月。 )“而对他的童话却给予毁灭性的打击:《打火匣》——‘行为不道德’,《豌豆上的公主》——‘没味道’,《小意达的花儿》——‘“道德”训诫意义不深刻。’”(注:分别见原苏联·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228—229页,马昌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5月。)1835年底,安徒生出版了第二个童话集, 依然没有获得评论界的支持和赞许。于是他不得不顺应潮流,将主要的希望寄托在“走正路”的小说创作上。
1837年,安徒生收到了作家豪赫的一封信,信中谈到了倍受推崇,甚而被有些人认为成就在安徒生之上的丹麦青年诗人巴鲁丹·缪勒。豪赫把安徒生与缪勒进行了比较后,说:“而我却坚持认为,你是大手笔,而巴鲁丹·缪勒只会矫揉造作地拿一些华丽的词藻以取悦读者;而您却有一颗真正诗人的心。”(注:分别见原苏联·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237页,马昌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5月。)豪赫的信,激发了安徒生的创作灵感,他“老早就打算写一篇故事,讽刺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对‘时尚’顶礼膜拜,为了不致被人视为傻瓜,而不敢陈述自己见解的人。”(注:分别见原苏联·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238页,马昌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5月。)同年4月,包括《皇帝的新装》在内的安徒生的第三个童话集出版了。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在当时人云亦云的社会中,人们看重的只是外在的虚荣的东西,安徒生创作童话是逆潮流顶习俗的。他是借《皇帝的新装》讽刺了当时弥漫于丹麦全国的媚俗虚荣之风。在安徒生阅读哥本哈根舆论界评论童话的文章时,他曾情不自禁这样想:“有时候,这些卖弄聪明的行家简直愚蠢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注:分别见原苏联·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256页,马昌仪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5月。)因为“安徒生对事物的可笑一面毕竟了解得太透彻了,……”(注:分别见原苏联·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263页, 马昌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5月。 )而这些可笑之处通过皇帝光着身子游行的故事得到了最集中最富戏剧性的体现。
还值得注意的是,安徒生《童话集》前言的标题是“致成年读者”。安徒生以此表明他创作童话是为了使成年人受到教益,而非仅仅哄哄小孩。这一创作信念本身就包含着对习俗、成见的违抗,也是他始终不渝的创作追求。1875年4月2日,安徒生接到为他建造纪念雕像的设计草图:他坐着讲童话,周围簇拥着一大群孩子。对这样的构思,安徒生断然予以否定,他说:“我的童话与其说是为孩子们写的,不如说是为成年人写的!”(注:分别见原苏联·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314 页,马昌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5月。)他童话创作的重心, 是要针砭成年人的种种恶习、种种弱点,为他们竖一面照照自己的镜子。在这一点上,《皇帝的新装》以其卓越的艺术洞察力和感染力实现了作者的意图。
《皇帝的新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两个骗子自称能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不仅色彩和图案都分外地美观,而且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怪的特性: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对此,皇帝的反应是,“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在我的王国里哪些人对于自己的职位不相称;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是聪明人,哪些人是傻子。”而“全城的人都听说这织品有一种多么神奇的力量,也都渴望借这个机会来测验一下:他们的邻人究竟有多么笨,或者有多么傻。”于是,骗子们的骗术初步得逞。之所以得逞,则源于社会上因袭而来的一种盲目的迷信与依赖。正是这种未经严格理性检验的迷信与依赖,为他们日后的愚蠢埋下了伏笔,皇帝则更为自己的轻信付出了出乖露丑的代价。既然存在着轻信的土壤,就必然会长出盲从的果实。既然这块布料能试出人们是否称职和愚蠢,那么这种无中生有的东西反而成了左右人类言行的唯一标准。在具有戏剧性的荒谬中,也透出了社会的某种真相。
第一个被测试对象是“诚实的老大臣”,尽管皇帝认为“他这个人很有理智,同时就称职这点说来,谁也不及他。”然而当他真的什么也没看见的时候,他想,“难道我是愚蠢的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此时他开始怀疑自己,却并未怀疑那块试金石的真伪。多年来的自信竟如此不堪一击!他面临的是诚实与虚伪、真与假的抉择。尽管诚实是真正的聪明,但当诚实被视为愚蠢与不称职时,谁还有勇气去面对呢?于是虚荣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这个“诚实”的人以不诚实的方式确认了布料的特性,也以此向外界宣布了他的聪明与称职,从而迈出了媚俗的第一步。无形之中,他又佐证了那个实际尚待检验的“试金石”的真实,也使得后来者在敢于说出真话之前,需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需要付出加倍的勇气。
第二个被测试对象是“另外一位诚实的官员”。同样的虚荣以及前一个人的“佐证”,使得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口是心非,又迈出了媚俗的第二步。
有了这两位“诚实”大臣的验证,第三个被测试对象是“皇帝”,第四个被测试对象是“一群特别圈定的随员”“一群最高贵的骑士”“典礼官”及“内臣”,第五个被测试对象是“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前有车后有辙,他们自然是也不甘居人下了。骗子的骗局于是获得了成功。
这种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当然“诚实的老大臣”是始作俑者,他最初的抉择引起了连锁反应。如果说“老大臣”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名誉的话,那么每一个后来的判断者由于前者的确认而更增添了一重顾虑,由此产生的作用力不断叠加,从而演出了一场范围波及全城的闹剧。
唯独最后一个被测试对象是天真未凿的小孩子,由于毫无功利之心而道出了真情:“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聪明的成年人是如此的愚蠢,少不更事的孩子方是真正的聪明者。这里寄寓着安徒生对世俗世界的习惯及传统的深深谴责和对纯真本然事物的热切向往。
“单是《皇帝的新装》这一篇童话,就足以使安徒生获得社会讽刺大师的称号。”(注:分别见原苏联·穆拉维约娃:《安徒生传》第319页,马昌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5月。)从《皇帝的新装》中,我们能看到安徒生周围人的影子,他们像童话中的多数人一样,自做聪明、人云亦云、浅尝辄止,并同样的愚蠢可笑。正如勃兰戴斯所指出的:“有很多事情,人们由于怯懦,由于害怕自己的行动跟‘所有的人’不同,由于担心他们会显得愚蠢,往往不敢说出真相。这个故事永远是新颖的,它决不会过时。”(注:丹麦·勃兰戴斯:《安徒生论》,易潄泉等选编《外国文学评论选》上册第530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不错,媚俗在任何时代都会使人们规避事实,使社会裹足不前。那么,在这出闹剧中,到底是谁骗了谁?我们说,正是人类的虚荣、做作,不能正视现实,不敢承认对他们来说是苦涩的真理,而使他们自己欺骗了自己。
作品写了身份不同但颇具共性的形形色色的人,与其说是描写了一个宫廷,不如说是描写了一个社会。作品不是揭露一个皇帝,而是抨击人类共有的媚俗与虚荣。这两种表述的区别是:前者仅把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后者则使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安之若素,都须反躬自问,找出“自己皮袍下的‘小’”,克服天性中的弱点,逐步走向完善。
应该说,《皇帝的新装》中的皇帝并非“骄横一世”,也让人看不出有多少“丑恶本质”。两个自称织工的骗子为他织布,他照样付钱,并不强征暴敛;布料纺织过程中,他先后派两个诚实能干的大臣前去考察,而非自己贸然作出结论,可谓谨慎至极;当新的布料被认为织好以后,他及时奖赏两个织工,可谓赏罚分明;当百姓们议论他什么也没穿的时候,他也仅仅是“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而未对百姓的不恭采取镇压措施。假若他是个暴君的话,两个骗子纵有天大的胆,也不敢到老虎嘴里拔牙。他的主要弱点是虚荣心重,而“每一天每一点钟都要换一套衣服”正是这种心理的一种外化。这种弱点导致了他的另外一个弱点:主次颠倒。他“既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看戏,也不喜欢乘着马车去游公园”,使他不是被称作“议会中的国王”,而是“更衣室中的皇帝”。出于虚荣,当最后骗局被揭穿时,他强撑脸面,要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而这也是任何一个有身份、有自尊心的人此时此刻所能做出的唯一抉择)安徒生“以戏剧性的轻松活泼,以对话体的形式,说出他那篇描写一位爱慕虚荣的皇帝的美妙故事。”(注:丹麦·勃兰戴斯:《安徒生论》,易潄泉等选编《外国文学评论选》上册第 53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这样一个皇帝,尽管有着作为人的弱点,但并非十恶不赦。如果《皇帝的新装》“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本质”的话,那么《海的女儿》中的人鱼公主、王子,《野天鹅》中的艾丽莎公主及十一个王子等,是否也算是封建统治者的一员呢?那种按图索骥式的阶级分析的阅读早已不适合时代的发展了,它已像那件具有“奇怪的特性”的新装一样经不起推敲了。然而,这种阅读分析方法还在课文提示中、分析文章中及语文教师的课堂实录中屡屡出现,可见中学语文教学观念的更新迫在眉睫。让我们更深入地钻研教材,愿我们的语文教学中也少一些“人云亦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