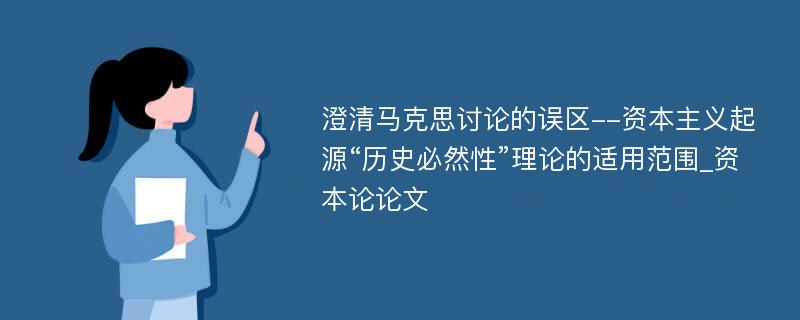
澄清对马克思一段论述的误解——资本主义起源运动的“历史必然性”理论的适用范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必然性论文,适用范围论文,资本主义论文,论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2)06-0017-05
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1]马克思对俄国主观社会学者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的曲解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认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说:“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3]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转述了《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的另一段论述:“它被消灭的过程,即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残酷的剥夺,就是资本的起源……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4]马克思在这封信的正文中指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5]
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的论述呢?我国不少学者把这段论述理解为马克思认为只有西欧各国才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都不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我认为这种理解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是对马克思有关论述的误解和曲解。下面对这种不正确的观点做具体剖析,以澄清对马克思论述的误解。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的思想,是在特定的意义上、针对特定的问题讲的,不应该离开这种特定的意义、特定的问题把它普遍化。这个特定意义和特定问题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首先,马克思说的只是《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而不是说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都不具备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也不是说《资本论》其他章节中所讲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同样也只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更不是说他的其他著作中所讲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也只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马克思的《资本论》采用的是典型研究方法,他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6]除英国这个典型外,马克思也涉及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其他西欧国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既然是以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为典型和对象的,所以他的概述就只“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而不包括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但这并不是说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讲完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以英国为典型以后,紧接着说了下面一段话:“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7]意思是说,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它正从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扩展,即从英国以及西欧其他国家向西欧以外的国家扩展。至于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也没有把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仅仅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如1848年2月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
其次,马克思说的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运动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只是说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相分离、剥夺农民、变多数人的小财产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变个体小生产为资本主义大生产这种资本主义起源运动的具体形式和具体道路,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而不是说只有西欧各国才具有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都不会产生资本主义,或者说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不是说俄国农村公社及其土地公有制肯定不会解体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以后的19世纪70年代,还明确表示过,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及其土地公有制并不抱乐观态度,认为俄国的土地公有制面临解体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危险。他在给拉法格夫妇的信和给恩格斯的信中,均高度评价了俄国民粹派理论家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马克思认为,它“是一部卓越的著作”,在这本书里“第一次充分地描述了俄国的经济状况”,热情地称赞“作者在十五年中周游全国,从西部边境到西伯利亚东部,从白海到里海,唯一目的是研究事实,揭露传统的谎言”。同时,马克思又批评他“对俄罗斯民族的‘无限完善的能力’和俄国形式的公社所有制的天意性质还抱有一些幻想”。[9]马克思明确表示自己对俄国公社发展前途的态度:“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10]意思是说,俄国公社属于原始的、落后的农业生产组织,它及其土地公有制有可能解体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马克思不仅在评价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时,认为俄国公社及其土地公有制有可能解体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且在专门论述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著中,也没有否定俄国农村公社及其土地公有制有解体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例如,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概括地论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公社发展前途的看法:“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11]我国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明确表示了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其实不然。我们仔细推敲一下这封信,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不仅没有明确表示赞同,甚至可以说婉转地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同看法。他叙述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以后说:“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俄国‘文学家’(指民粹主义者赫尔岑——引者注)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争论得出我不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他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12]接着马克思又讲了下面一段话:“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3]表面看来,马克思这段话是在环顾左右而言他。其实不然。马克思是在郑重声明,他有着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立看法,没有受到俄国民粹派错误观点的任何影响。在他看来,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开始的农奴制改革以来所走的道路,它也将像西欧国家一样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又如,俄国民粹派女作家维·伊·查苏利奇在1881年2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希望马克思回答他是否“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14]而且对马克思讲道:“在我看来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们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尤其如此。甚至我国革命的社会党人个人的命运也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究竟如何。”[15]查苏利奇的信可以说是步步为营,咄咄逼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复信才反复思索,精细构思,以至四易其稿,而在正文中作了十分微妙的回答,委婉地表达了与她不同的见解:我“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要排除从各个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16]马克思这里说得十分清楚,他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有两种发展前途:或者在条件具备时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共产主义的起点,或者继续坚持1861年以来农奴制改革的方向,像西欧各国一样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里根本没有表示赞同查苏利奇的观点。
再如,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在说明俄国公社有可能不解体、“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时,都明确指出这是从“理论上”讲的;而他在讲到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有可能解体变为土地私有制,从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则是从俄国当时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讲的。马克思在复信初稿中说:“为了从纯理论观点,即始终以正常的生活条件为前提,来判断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农业公社有两种发展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7]马克思又说:“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18]这就是说,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理论上”、甚至是“纯理论观点”上说的,是“先验地”说的,是“以正常的生活条件为前提”的。一旦“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就可以看到俄国农村公社及其土地公有制正面临着解体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危险。马克思在复信的二稿中说:“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育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19]从这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可能变为土地私有制从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论证,则不是逻辑上的“历史必然性”,不是“纯理论观点”上的,不是“先验地”说的,而是“把一切多少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撇开不谈”,从俄国公社面临着各种破坏因素的实际情况讲的。我国研究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学者,很多人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的这种独特的思考方式、构思方式和论证方式,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论述俄国农村公社两种发展前途的不同论证方式的差别,即对第一种前途的论证是从“纯理论观点”上讲的,是“先验地”讲的,而对第二种前途的论证则是从俄国现实的实际可能性讲的;没有注意到关于第一种前途实现的可能性仅仅是“理论上”的,而对第二种前途实现的可能性则是现实的。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致使不少人不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真实思想,甚至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种种误解。很多研究者都认为,马克思强调的重点是第一种前途实现的可能性。其实不然。马克思强调的重点在于警告俄国民粹派理论家要警惕和防止第二种前途的实现。
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的论述的真实意义,防止对这一论述的误解,需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需要弄清马克思论述的这一思想的适用对象。马克思论述的这一思想主要适用于当时的俄国公社及其发展道路,不能离开俄国公社的特点及其发展道路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运动,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而俄国是把农村公社及其土地公有制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国家,既然土地从来没有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所以不能将马克思关于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的概括,运用到根本没有土地私有制的俄国农村公社上去。
第二,需要弄清马克思论述这一思想的具体针对性。马克思的论述是针对俄国一些理论家对《资本论》中有关论述的误解讲的,不能离开马克思的具体针对性孤立地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俄国民粹派女作家维·伊·查苏利奇在1881年2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向马克思讲述了俄国一些人对《资本论》的一种误解:“最近以来我们经常听到一种意见,说农村公社是一种陈腐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而言之,所有一切最不容争辩的东西,都已断定这种陈腐的形式必然灭亡。宣扬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您的真正的门徒,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最有力的论据是:‘马克思是这样说的’。”“有人反驳他们说:‘你们是用什么方法从他的《资本论》中推论出这一点的呢?他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分析土地问题,也没有谈及俄国啊’。”“您的门徒们回答说:‘要是谈到俄国的话,他是会说这个话的。’……也许,他们有些过分大胆了。”[20]马克思正是为了澄清查苏利奇所讲述的这些人的这种误解,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才说:我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运动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离开马克思论述的具体针对性,孤立地理解马克思论述的这一思想,必然会对这一思想发生误解。
第三,马克思论述的这一思想和他与俄国民粹派一些理论家的特殊关系密切相连,不能离开这种特殊关系孤立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与俄国民粹派的一些理论家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微妙的。一方面,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及其发展道路的看法与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的看法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他与俄国民粹派的一些理论家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俄国革命的民粹派对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特别感兴趣,马克思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交往频繁,特别是丹尼尔逊、弗列罗夫斯基等人为马克思提供了很多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很有价值的资料。马克思对俄国民粹派的革命实践活动十分关注,给予很大的同情和支持,并将其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认为他们所从事的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活动,既有利于俄国社会的发展,又有利于推动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批判他们的错误观点的同时,又要保护他们的革命热情。所以马克思对他们错误思想的批评采取了比较友好、曲折、隐晦和含蓄的方式,不公开谴责他们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不得不批评他们的错误观点时,很多情况下都是极其隐喻和婉转的。例如,俄国革命者曾多次要求马克思公开发表论述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文章,马克思都婉言谢绝了。对一些不得不发表意见的问题,为了避免发生正面冲突,都是采取通信的形式。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及其发展道路这类敏感问题,马克思发表意见就更为慎重。正是为了妥善处理他与俄国革命民粹派理论家的关系,才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说:我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运动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离开马克思与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的特殊关系孤立地理解马克思这一思想,也必然会对这一思想发生误解。
第四,马克思论述的这一思想及其历史意义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不能离开历史条件的变化,把马克思论述的这一思想及其历史意义凝固化、教条化。马克思认为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运动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不适用于俄国,是以俄国公社及其土地公有制在全国范围内完整地保存下来为前提的。一旦俄国公社土地公有制解体、土地私有制产生和发展起来,这个限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马克思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就论述了俄国农村公社及其土地公有制正在遭到严重的破坏,很可能抵挡不住从各方面袭来的对它的打击而瓦解。马克思在他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狂热”在俄国已经“迅速盛行起来”。[21]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多次谈到俄国农村公社及其土地公有制解体并迅速地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恩格斯认为,俄国在1853—1856年进行的克里木战争中失败以后,除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指出:“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大遭破坏的俄国公有制从那时以来已经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大规模修筑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农民的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22]到20世纪初,列宁更是多次明确肯定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第五,马克思的思想也和任何其他的思想一样,是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判断其正确与否的,不应该离开实践的检验而把马克思的某一种思想或设想,当作永恒真理加以应用。首先,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并没有变成现实,亦即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不是马克思关于“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证实,而是对它的证伪。[23]其次,不仅俄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国家,都通过民族民主革命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且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再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各国,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再不厌其烦地把马克思所说的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的思想,当作普遍适用的理论加以宣扬,就是很不合时宜的了。
第六,马克思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规律。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没有研究其他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也不等于说他没有研究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无论在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个别规律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还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章中,马克思都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共同体和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特点及其解体过程。同时,马克思认为,掌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有助于理解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的意义”。[24]所以,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掌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以后,又对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作了专门的深入研究,并在晚年写了《古代社会史笔记》(或称《民族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前者研究了原始社会的特点及其解体过程,后者利用世界历史的实证材料,研究了私有制社会如何通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样马克思就说明了人类世界历史由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前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全过程,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普遍规律,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那种认为马克思没有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及其普遍规律的观点,是与事实不符合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标签:资本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