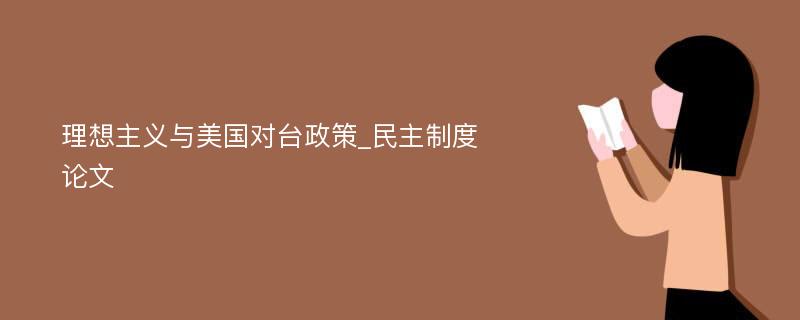
理想主义与美国的对台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理想主义论文,对台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国家。建国200多年来,美国的对外关系就是在理想主义和国家现实利益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一种本质源自基督教信仰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的美国理想主义所体现的美国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美国使命及国家目标始终是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重要因素。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出现了几次重大调整。导致这种调整的直接动因显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我们还应看到,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念、在东亚甚至整个亚太地区推进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也是美国维持和发展美台关系的重要因素。虽然这一理想主义目标时而显露,时而隐蔽,但却始终存在,并成为贯穿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台政策的一条主线,而且随着台湾“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美国理想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在台湾问题上,今后一段时期,美国理想主义与国家利益会比过去更为一致,美国理想主义将对美台关系、中美关系乃至中国的统一大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
二战结束后,随着实力的增强,美国更多地从理想主义目标和价值观念出发思考和制定美国的全球战略,同时对其他国家的理想和价值观念作出反应。美国认为,保卫美国在内的“自由世界”是一项全球“任务”,世界上任何地方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都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亚洲,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朝鲜、越南革命政权是对美国理想、价值观念的一种“威胁”,美国不仅不能袖手旁观,而且必须进行干涉,必要时动用美国军队,以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美国的对华政策、对台政策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制定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政府并没有看重台湾的价值,也无意对“腐败”、“独裁”的已经退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承担防守“义务”。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美国试图与中共建立某种关系的幻想。加上美苏冷战的不断加剧,美国认为它所“面对的问题是严重的”,它涉及的“不仅是这个共和国,而且是文明本身”。美国的“自由社会”正受到“苏维埃制度在道义上的挑战。再没有其他价值体系同我们的价值体系是这样整个地不可调和的了”(注:霍世亮:《美国理想主义与东亚》,载《美国研究》1992年第2期。)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更进一步促使美国彻底改变对台湾的价值,尤其是保护国民党政府对于提卫美国价值观念意义的看法。美国政府从美国的整个亚太战略出发,转而将“努力使台湾保持自由,不使其落入共产党控制之下”作为其远东战略的重要目标。根据上述目标,美国迅速决定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以“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
为了更加有效地保卫台湾的“安全”,并使保卫台湾安全“合法化”,以达到其长期控制台湾的目的,1954年12月,美国政府与蒋介石集团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当局的联合美国、增强针对大陆的防务以及“反攻大陆”的力量的意图不同,美国政府则更多是从两种制度斗争的角度考虑这一条约的。美国企图利用这一条约使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成为封锁和遏制社会主义中国锁链上的重要一环,通过既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又阻止台湾当局“反攻大陆”这样的方式,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杜勒斯解释该条约时声明,美国同包括台湾在内的太平洋国家和地区间所订立的各种共同防御条约,“为保卫西太平洋地区已自由的人民抵御共产主义侵略提供了基本的组织结构”(注:转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240页。)。
不仅如此,美国企图以台湾为立足点,将台湾的“民主”、“自由”之光照向大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3年4月关于远东政策的一份文件曾明确宣布:美国在远东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对美国和“自由世界”所造成的威胁,“因此美国远东政策的基本目标必须是促使中国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消除其对自由世界的安全的威胁。”(注:朱天顺主编:《当代台湾政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302页。)为此,美国加紧围堵和孤立中国,并胁迫有关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严格的封锁和禁运,极力拼凑反共军事条约体系,还力图发挥台湾的“民主桥头堡”作用,达到迫使共产党政府在大陆垮台、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其后,美国一直坚持这一对台方针。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继续强调美国的理想、价值观念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意义以及美国建立“新世界”的使命感。在处理与两岸关系时,美国政府仍然坚持过去的对台、对华政策。1963年12月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西尔斯曼发表演说宣称,美国决心对中国大陆改变的可能性敞开门户。他强调指出:“我们相信,在决心准备谈判的同时,坚定有力的政策将会最终有效地促进那些在中国大陆必然要发生的转变。”(注:朱天顺主编:《当代台湾政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308页。)
由上可知,50至60年代,美国的对台政策是在捍卫和推进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理想主义精神的指导下,结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而设计的。该政策的核心是建立和加强与台湾当局的政治军事关系,把台湾当作在亚洲抵抗“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环节,并企图通过遏制以及台湾“民主制度”的示范作用,搞垮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最终促使中国朝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演变。从结果来看,正是美国的出自美国外交传统的理想主义对台政策,使美台关系特别是美台军事关系在50年代后的20年间不断加强,从而为国民党政权提供了在台湾得以为继的基本条件,造成海峡两岸的分离与对峙。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台政策目标。而促使中国“变化”的目的却因为中国人民的坚持斗争而没有得逞。此后,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被迫大幅度调整对华及对台政策,不过,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台湾岛内政治气候的变化,美国的理想主义对台政策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
70年代,由于苏联奉行霸权主义扩张战略,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美苏战略态势由原来的“美攻苏守”转为“苏攻美守”。为扭转战略上的颓势,出于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现实主义考虑开始占上风,美国被迫暂时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主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发表了上海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美国表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1978年12月,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公报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随后,美国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终止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
然而,在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过程中,美国的理想主义始终隐藏在追逐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背后。表现在台湾问题上就是,在一方面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另一方面又力图维持与台湾的安全关系,从而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不过,由于美国已经承认“一个中国”,因而它不便于公开插手台湾问题,而是将对台政策的重点从“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转向促进台湾政权本地化和“民主改造台湾”。1971年7月,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台湾问题提出了一份“台湾政权台湾化”的报告,该报告提出的基本政策是:“首先要推出一个‘得到美国充分支持、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台湾化计划’,通过‘台湾政权台湾化的途径’,建立一个‘由台湾人控制的代议制’政府,而台湾政权‘一旦掌握在台湾人手里’,美国就可以运用它‘设法就台湾的最终法律地位问题与中国对话’,或者是‘造成一种政治局势,使中国人同意一个友好的台湾独立’。”(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转型期的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时事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150页。)1979年4月,卡特政府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根据这项美国国内法,美国可以向台湾当局提供“防御武器”。应该指出的是,《与台湾关系法》再次透出美国理想主义的动机。该法声言一旦台湾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遭受威胁,因而危及美国利益时”,美国总统将“决定美国应付上述危险所应采取的适当行动”。该法还规定台湾必须确保“人权”进展,内政改革必须纳入美国既定的“民主”规范。该法第二条载明:“本法中任何条款都不应违背美国对人权的关心,特别是对大约1800万全体台湾居民的人权的关心。兹重申,维护并促进全体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注:《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156、168页。)
进入80年代,台湾和大陆的政治气候都出现了使美国感到“鼓舞”的变化。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后,其国际社会人格被逐渐剥蚀。为了摆脱孤立,重获国际支持,国民党当局将推进“民主政治”作为“谋求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同情支持”的“不二法门”(注:廖光生:《台湾打破党禁的良性影响》,载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1月。)。与此同时,自70年代末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否定了过去许多极左的说法、做法,思想领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美国朝野对此一片欢欣鼓舞,有些人还对按照美国的理想来影响和改造中国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注:资中筠:《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载《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而且,80年代后,美国开始在亚洲奉行一种被称为“新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在“支持民主化”的同时,确保美国的利益和影响。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积极促进台湾的“民主化”,力图“形成一种‘以独制蒋,以蒋制共,以共制苏’的一环套一环的连环套”,以便从中渔利(注:王晓波:《解严后台湾前途问题的思考》,载台湾《中华杂志》1987年1月总第282期。)。出于上述目的,美国“民主改造台湾”的愿望日益强烈,对台湾党外运动特别是主张“台独”的民进党的关切和兴趣与日俱增。
1986年美国参议员肯尼迪、索拉兹等成立“台湾民主促进委员会”,该委员会迫使政府放弃对一些东亚国家独裁政权的扶植(如菲律宾马科斯政权),使国民党加快政治改革。国民党当局一有新的政治民主化措施推出时,美国政要总是及时表示赞赏与鼓励。8月上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民主决议案》,呼吁国民党当局“允许人民组织反对党,停止新闻检查制度,确保言论、集会自由,朝真正的代议制制度迈进”。8月底,佩尔、克兰斯顿、索拉兹、里奇、赛门等五人就联名致函国务卿舒尔茨,要求政府支持台湾党外组党,指出,“台湾地区出现真正的民主制度合乎美国利益,台湾加速向多元化目标迈进,将可能使双方经济领域逐增的紧张关系消除,并增进对台湾安全的了解。”(注:台湾《民众日报》1986年9月10日。)9月28日,民进党宣布成立。次日,国会议员里奇、托里西里、索拉兹等人马上发表声明,对该党的成立表示支持,称新党的成立“有助于台湾政局的稳定和安全”。10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认为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是令人振奋的迹象(注:王景弘:《华府看台北政治风云》,载[美国]《世界日报》1986年10月5日。)。此后,为促进台湾政治体制由“军事戒严”和“一党专制”进一步向西方式的“政党政治”过渡,某些自称“自由派”的国会议员更是打着维护“台湾民主”的幌子,或发表声明,或提出议案,或邀请访问,积极支持民进党活动,甚至公然鼓吹“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1987年2月民进党组团访美,美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法赛尔、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芮孝俭、国家安全会议官员包道格、前副总统蒙代尔先后与其会面交谈。美国国防部、国家安全会议等官方机构也与其“进行了深入接触”。美国国会还将民进党访问团提交的《台湾人民自决问题决议案》列入国会讨论案(注:常燕生、辛旗主编:《转型期的台湾政治》,华艺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178页。)。1989年7月1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等人提出的《台湾民主前途决议案》,该决议案称“台湾的前途必须和平解决,其方式必须是免于限制,且为台湾的住民所能接受”(注:台湾《民众日报》1989年9月24日。)。
可见,70至8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中的理想主义主要表现在促使台湾岛内的政治变化上。从推进台湾政权的本土化、敦促国民党当局尊重人权到或明或暗地支持主张“独立”的民进党,美国的着力点都在于按照美国的标准和模式改造台湾,使台湾不仅进一步融入西方社会,成为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的一员,而且企图通过这种“改造”达到长期分裂中国的目的,以巩固和扩大五六十年代的对台政策成果。从这一意义上讲,70至80年代的对台政策是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的延续,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对台政策目标在美台关系中表现得更加隐晦,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三
两极格局崩溃后,美国成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再次点燃了美国人心中的理想主义“圣火”。美国前总统布什曾提出要按照美国的“理想”,建立一个新世界。克林顿上台后接过布什理想主义大旗,并将阻止战略对手的崛起,建立一个属于美国的单极世界,确立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为此,克林顿政府把在全世界推进“民主”视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
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不复存在,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易位。而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的平息又使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落空,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美国看来,中国正在崛起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为阻止中国的进一步强大,克林顿政府在制定对华“接触与遏制”政策,试图将中国纳入按美国方式建立的世界新秩序之中的同时,还力图将对台政策纳入美国的对华政策之中加以考虑,进一步重视加强美台关系,尤其是进一步重视发挥台湾“民主制度”对大陆的“样板”作用。美国认为,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发展,将有利于西方意识形态向中国渗透,“逐渐为在中国大陆出现更加多元化、其管理者更具人情味的社会创造条件”(注:转引自王缉思等:《美国人眼中的“大中华”》,载《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具有最长远意义的可能是台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帮助培养企业家的作用。随着企业家阶级在大陆的成长,其价值观和影响力将继续侵蚀共产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通过加强和‘中华民国’的接触,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可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注:《简评冷战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调整》,载《台湾研究》1997年第3期。)“改革的决策必需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但是存在一个成功的改革模式对美国是有利的。‘新台湾’就是这样一个模式。”(注:Brett Lippencott,Taiwan Should Be Allowed to Join the World Community,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s,August 24,1994.Backgrounder No.132.)台湾的“民主化”将证明“一党制的儒教社会可以转变为多党‘民主’……”(注:《简评冷战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调整》,载《台湾研究》1997年第3期。)。
由于存在上述认识,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至1994年间进行了所谓的“台湾政策审议”,并于1994年9月对美国的对台政策进行了调整,试图提升美台关系。1995年,美国甚至作出了允许李登辉访美的决定。其后,由于这一倒退政策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美国从战略大局出发,被迫调整了对华关系,并一再重申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坚持“一个中国”立场。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时还提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由主权国家加入的国际组织”的对台“三不政策”。然而,美国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手中的“台湾牌”,相反,美国却高度重视台湾领导人选举对台湾特别是对大陆的意义,积极支持台湾岛内的“民主化进程”,并以维护台海和平为借口,反对我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政策,力图维持两岸的分离局面,从而在两国三边关系中谋求最大的主动和利益。
不仅如此,美国还将维护和加强台湾安全与保障台湾的“民主制度”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一方面不断加强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增强台湾的“自卫”能力。据统计,1992~1995年,台湾是美国第二大武器出口地,军售总额达83亿美元。1997年美台军售签约额和实际交货额分别为3.54亿美元和2.16亿美元。1998年,已分别上升到4.41亿美元和15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还时而摆出架势,试图充当台湾“民主制度的卫士”。1996年3月,针对大陆在台海附近为遏制“台独”而进行的军事演习,美国国内介入台海危机捍卫“台湾民主制度”的呼声高涨。曾任里根政府国防部长的温伯格说,台湾实行的是“民主制度”,“我们应该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它不受大陆的攻击(注:美联社华盛顿1996年2月28日英文电。)。在克林顿政府向台湾海峡地区派遣航空母舰前后,参院和众院起草了决议,强烈批评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试验,并要求美国作好准备,向台北提供防御武器。众院共和党领导人提出的决议案声称,美国“应保持与台湾民主政府的友好关系及对它的承诺,帮助它抵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导弹进攻或封锁”(注:路透社华盛顿1996年3月11日英文电。)。该党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政策声明:“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不应该对如下一点抱怀疑态度:美国绝不会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动用军事武力或者阻断她的空中或者海上通道。为此,美国必须作好准备,同台湾一起保卫她,使之免遭将会危害她的安全的任何诉诸武力的或者其他形式的感受。”(注:新华社华盛顿1996年3月5日电。)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抛出“两国论”。7月20日,克林顿总统在向记者通报他同江泽民主席的热线电话时说:“我明确说明,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认为,美国要认真对待任何缩减和平对话的行为。美国的这一观点没有改变。”(注:杨洁勉:《克林顿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载《美国研究》1999年第4期。)7月30日,就在辜振甫对“两国论”作出“澄清”后不到12小时,克林顿政府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5.5亿美元的先进武器。
近年来,美国的亲台势力再度掀起强大的反华逆流,“中国威胁论”又一次在美国甚嚣尘上。1999年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台湾海峡的安全形势》报告称,“大陆的导弹对台湾的军事目标和军事设施构成严重威胁”(注:〔美〕《世界日报》1999年2月27日。)。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等人看来,这是共产主义国家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因而它对美国全球利益“造成危害”。美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台湾免受大陆的“武力威胁”。2000年2月1日,在国会亲台势力的一片鼓噪声中,众院以341票对70票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法案。这是继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之后,美国国会再次企图以国内立法的形式通过有关加强美台军事关系,蓄意阻挠中国统一的法案。该法案要求国防部必须同台湾军事部门建立直接联系,帮助台湾增加军事训练,允许台湾派遣更多的军事人员到美国军事院校受训,并要求国防部每年就“台湾安全遭受到的威胁”向国会提交报告等。2月21日,为反击台湾岛内日益嚣张的“台独”倾向,系统全面地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政府有关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立场和政策,我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美国的一些亲台分子公开指责白皮书。他们大肆叫嚷台湾“民主”受到大陆的军事威胁,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帮助加强台湾防卫。一向台湾情结浓重并在美国国会有相当政治能量的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不仅在给台湾新领导人的贺信中公开鼓吹美国应承认“两个华人国家”,而且还在《华盛顿邮报》(2000年3月31日)上发表题为《两个华人国家》的长文,大肆鼓吹美国必须推行“两个华人国家政策”。这项政策的内容包括:在安全上,批准台湾提出的包括“宙斯盾”级驱逐舰在内的所有武器采购要求,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国会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在政治上,美国应接受“两个华人国家的事实”,支持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最终进入联合国。
四
综观50年以来的美国对台政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外交中的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一贯的,其理想主义外交传统对美国的对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50和60年代的利用台湾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70和80年代的促进台湾政权“本土化”和促进台湾“民主化”到90年代后的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鼓励和维护台湾的“民主制度”并发挥台湾“民主制度”对大陆的样板作用,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台政策目标的理想主义追求。虽然决定美国对台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也是美国制定对台政策的基本考虑,但理想主义同样是贯穿半个世纪美国对台政策的一条主线,只不过这条主线时而显露,时而隐蔽。它与对台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并行不悖,彼此交织,相互促进。它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最终“分化”和“西化”中国。
由于美国不仅将台湾的政治制度看作是在美国影响下“民主化”的成果,而且将台湾当作在亚洲移植美国模式的样板,加上在台湾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因此今后美国仍会继续使用它手中的“台湾牌”,而且,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强大,美国在亚洲甚至全球推进“民主”的欲望也会进一步强烈。这就决定了美国今后会较过去更加同情日益“民主化”的台湾,更加顽固地坚持保障台湾“民主制度”、干涉中国统一大业的做法。对此,我们应该:第一,高度重视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尽可能减少美国因素对我们统一大业的负面影响;但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做到“斗而不破”;第二,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增强综合国力特别是以海空力量为核心的国防实力,以便给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和支持“台独”的外国势力以更大的威慑;第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照顾台湾的“民主”现实,更加坚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决心和信心,并为此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两岸对话,增进两岸信任,早日完成祖国统一,从而最终粉碎美国“分化”和“西化”中国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