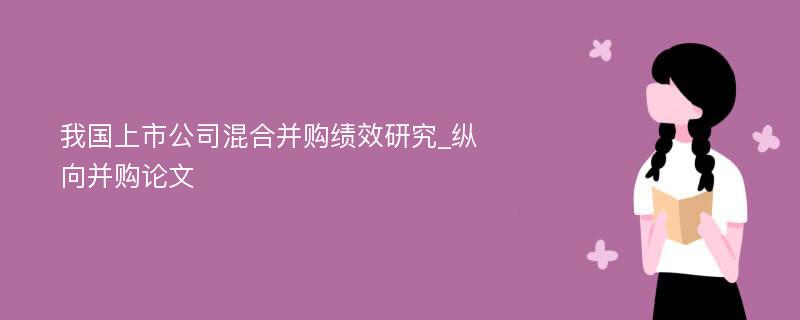
我国上市公司混合并购绩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效论文,上市公司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并购双方的行业相互关系,并购可以分为横向并购(Horizontal Merger)、纵向并购(Vertical Merger)和混合并购(Conglomerate Merger)。在我国上市公司1995—2001年的并购实践中,横向并购发生得最多,在发生的所有并购事件中占60%以上,为绝对多数;其次是混合并购;最不常发生的并购类型是纵向并购。三类并购的动机不一样,因而其绩效也可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已有的理论一般认为混合并购较难成功。本文从理论和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实践两方面对混合并购绩效进行了分析,证实混合并购的确是有较大难度,对此,提出了实施混合并购中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一、混合并购绩效的理论分析
三种不同类型并购的经济学解释不一样:横向并购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并取得市场力优势;纵向并购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获得垄断利润;混合并购则能够使并购公司获得组合优势,并且分散单一经营的风险。这样说三类并购应该可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促进并购公司获得市场竞争优势以及效率的增进等等好处。但是长期以来,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的好处多次得到证实,而混合并购对并购公司的作用却多次受到实践的质疑。比如,在60年代,混合并购成为美国第三次并购浪潮中最主要的并购形式,但却并没有取得公众所预测和期望的并购收益,混合并购使企业利润大幅下降,迫使企业将亏损的子公司或部门出售给其他企业,导致80年代剥离和分拆成为当时并购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家H.Levy和M.Sarnat(1970)用数学模型证明了纯粹的混合式并购并不能取得经济优势;D.C.Mueller(1969)则从代理问题角度部分解释了这种失败。
1.协同效应和利润稳定:混合并购的两个理由
获取协同效应是混合并购曾经被广泛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协同效应是指不同品质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有时能产生1+1>2的效应。在混合并购中,这种协同效应被认为可以体现在生产、原材料运用、管理、市场等各个方面,另外金融协同效应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纯粹的混合并购是将生产过程毫不相关的企业置于同一控制权下,很难产生各种期望的协同效应并增加利润。对此,有些经济学家指出,即使没有带来协同作用和利润的增加,纯粹的混合式并购却可以稳定利润来源,因而具有明显的经济收益。Samuels和Smyth(1968)曾用实证分析证明企业规模越大,经营越多样化,其利润波动就越小。可是,Levy和Sarnat采用公司普通股中的风险与收益一对一的方法证明,在完全的资本市场竞争条件下,纯粹的混合式并购不能取得经济优势。简单的论证如下:
假定2家在业务上完全互不相关的公司合并,在缺少协同效应的条件下,合并后对新公司持股者的收益来说是2家公司合并后的平均值。
Z=Wx[,1]+(1-W)x[,2]
式中:Z——新公司持股者在合并后收益的随机变量;
x[,1]、x[,2]——分别表示在合并前2家公司持股者收益的随机变量;
W——第1家企业的相对规模;
1-W——第2家企业的相对规模。
合并后的预期收益(UZ)就等于2家公司合并后预期收益(U[,1]和U[,2])的平均数。
U[,z]:WU[,1]+(1—W)U[,2]
那么,合并后的总方差(σ[2][,z])就是:
σ[2][,z]=W[2]σ[2][,1]+(1-W)[2](σ[2][,z]+2W(1-W)cov(x[,1]x[,2])
既然假定各家公司收益间并不存在完全的联系,总的合并方差要低于各家公司方差的简单相加数。同时也假定,合并后的预期收益是各家公司收益的加权平均数,则新股的风险——收益特征就是一种有效的结合,即在收益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减少总的风险。新公司的股票就可能以升水出售,而不是各家公司在合并前的加权总数。然而,这种升水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上并不立即实现,因为只有投资者才能获得这种风险——收益的结合,而在未合并情况下,各家公司的股票是以W和1-W比例的组合来实现风险——收益的结合。
根据数学模型的证明,混合式并购后的最优投资价值是合并前分别投资2家公司之和。因此,混合并购没有带来市场力量所形成的新市场优势,也没有改变合并前股票的市场均衡价格。研究的结论是:纯粹混合式合并产生的多角化利润稳定效果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上并没有产生经济收益。
2.Mueller的管理者主义解释
如果把出于规模经济、效率提高、市场优势获取等企业发展目的的并购称作理性的并购,那么出于企业发展之外其他目的的并购可以称作非理性的并购。比如,企业不是为了获得协同效应或是稳定利润而进行的混合并购就是非理性的混合并购。Mueller的理论正是解释了这种非理性的混合并购。
本文的前面曾提到Mueller的管理者报酬与企业规模成正比假说,其实Mueller的这个假说是为了解释混合式并购。因为用利润最大化很难解释混合并购,于是他提出用企业成长最大化假设来解释。
企业成长最大化的假设是,企业的管理者以公司资产的增加,而不是以利润最大化或股东收益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管理者的收入同公司的成长率有着密切的联系。管理者的薪俸、奖金、股票期权及晋升等因素与公司规模扩大的密切程度要比利润增加的关系更大。同样,管理者的地位和权利也是如此。为了追求公司成长,扩大公司规模,管理者采取扩张性的投资策略。
这个理论说明存在一种不是为了追求公司利润增长而是盲目追求公司规模的混合并购。对于寻求成长最大化的管理者来说,所有企业都是有吸引力的,那么必然会促使盲目的并购活动的增加,至于并购后企业的利润增长、效率提高,则是次要的问题了。
二、我国上市公司混合并购的绩效分析
1.样本的选取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君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CSMAR财务数据库。1995-2001年间发生混合并购的上市公司有365家,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客观,在经过一系列的剔除和筛选后,从中选择了182家纯粹的混合型并购作为分析的样本。样本的年度分布如下:
表1 并购样本各年分布
并购类型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合计
混合并购 4
111
29
34
48
55 182
2.模型的构建
本文采用以财务数据为基础的比较分析法来研究混合并购的绩效。财务指标用的是檀向球、提云涛、强立等(1999)提出的资产重组鉴别指标体系中的绩效评估体系,包括4个指标:
G[,1]:每股收益;G[,2]:净资产收益率;G[,3]:主营业务利润率;G[,4]:总资产报酬率。
为了便于对并购前后公司的业绩进行对比,必须构建一个综合得分函数,将这4个指标压缩成一个综合得分。目前较为理想的综合评价方法是因子分析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对若干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共因子,称为因子变量,然后利用旋转方法使因子变量更具有可解释性,再计算每个因子的得分,最后以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与该因子的得分乘积的和构造综合得分函数。
在本文中,将对g[,1]、g[,2]、g[,3]、g[,4]4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为消除行业经济景气的影响,笔者构建了g[,1]、g[,2]、g[,3]、g[,4]4个新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令AG[,1]、AG[,2]、AG[,3]、AG[,4]分别表现不同年度该公司所处的行业的G[,1]、G[,2]、G[,3]、G[,4]的平均水平,则g[,1]=G[,1]-AG[,1];g[,2]=G[,2]-AG[,2];g[,3]=G[,3]-AG[,3];g[,4]=G[,4]-AG[,4]),提取4个公共因子Y[,1]、Y[,2]、Y[,3]、Y[,4],再建立4个因子的综合得分函数:
Fi=αilYil+αi2Yi2+αi3Yi3+αi4Yi4
其中Fi是第i个公司业绩的综合得分,αij是第i个公司第j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Yij是第i个公司第j个因子的得分。
我们以主成分法对样本公司并购前后各年剔除行业经济景气影响后的4个指标g[,1]、g[,2]、g[,3]、g[,4]按并购前一年、并购当年、并购后一年、并购后两年和并购后三年分别进行因子分析,提取4个公共因子Y[,1]、Y[,2]、Y[,3]、Y[,4],然后再根据各因子的得分和方差贡献率,得出5个综合得分函数,再由这5个函数计算出各样本公司并购前后相应年份的业绩综合得分。
并购前一年:F[,-1]=0.56342Y[,1]+0.19006Y[,2]+0.17198Y[,3]+0.07454Y[,4];
并购当年:F[,0]=0.50555Y[,1]+0.23002Y[,2]+0.19365Y[,3]+0.07078Y[,4];
并购后一年:F[,1]=0.51276Y[,1]+0.22522Y[,2]+0.17075Y[,3]+0.09127Y[,4];
并购后两年:F[,2]=0.50025Y[,1]+0.26627Y[,2]+0.16218Y[,3]+0.0713Y[,4];
并购后三年:F[,3]=0.5233Y[,1]+0.21342Y[,2]+0.16802Y[,3]+0.09525Y4。
表2揭示的是利用各年得分差值进行比率检验和均值检验的结果,同时也显示,并购当年及并购后若干年的得分均低于并购前一年,且并购后三年的得分最低,表现在得分差值均小于0,且F[,3]-F[,-1]的值最小。混合并购的公司在并购后业绩一直大幅下降。可以说,我国上市公司在混合并购上的运作并不成功。
表2 混合并购样本的比率检验和均值检验结果
F差值
F[,0]-F[,-1]F[,1]-F[,0]F[,1]-F[,-1]F[,2]-F[,1]F[,2]-F[,-1]F[,3]-F[,2]F[,3]-F[,-1]
样本量n
182
182 182
127 12779
79
正值比率0.32580.4365
0.38740.4652
0.4753 0.7245
0.3470
-0.3352
-0.7291 -1.48930.5393 -1.3575 1.3883 -2.4273
均值[*]
(-1.653) (-1.474) (-1.992)a (0.652) (-1.244)(1.096) (-1.704)
注:1.F-1、F0、F1、F2、F3分别表示并购前一年、并购当年、并购后一年、并购后两年和并购后三年样本公司的综合得分;
1.正值比率是指综合得分差值为正的样本公司个数占当年全部样本的比值。
2.*行括号里的数值为各年均值的t检验值,a、b分别表在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三、对混合并购问题的几点思考
理论和实证分析都证明,将两个毫不相关的产业置于同一控制权下的纯粹的混合并购很难成功,笔者认为公司在确定实行混合并购战略时要注意以下二点。
1.混合并购最好只是作为产业退出的一种方式
当产业部门面临过度的生产能力时,管理者一般不愿意承认市场需求正在下降,企业的规模必须缩小;相反,管理者们总是将退出市场的任务留给其他企业,而他们的企业则继续投资。一旦所有的企业管理者都采取这种方法时,企业的退出就决定性地推迟了,结果导致社会实际资源的巨大浪费。其实这种行为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损失,对公司本身也是效率和价值增加的贻误。
混合并购无疑为企业退出市场提供了一种最好的方式。在企业尚未到达衰退边缘的时候,尽早寻找其他具有潜力的产业作为进入方向,利用在原有产业积累的现金流并购处于新兴产业的公司,在顺利退出的同时又抢先进入了新的市场。
而此时的新兴产业由于还没有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同时开发和生产的成本极高,且面临着失败的风险。所以,新兴企业的领导人往往承受很大的压力,有时候很愿意将自己的企业出售。这样就正好为有意于退出的企业提供了并购的目标。
我们提倡产业退出的混合并购,就是鼓励公司尽可能进入有发展前景的领域。而从我国上市公司的混合并购来看,的确能看到一些产业退出的迹象。在我们的并购样本中,混合并购的目标企业基本集中在新兴或成长性的产业,如生物医药、邮电通信等。
而其他为了追求协同效应或者利润稳定而进行的混合并购我们已经证明很难对公司的利润增加有什么效果,所以,我们不提倡非退出动机的混合并购。
2.以关联为基础寻找混合并购的目标
就是在混合并购时要尽量选择与原产业有一定关联的企业作为并购目标。关联的概念出自波特的《竞争优势》,指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业务之间的联系,包括有形关联和无形关联。有形关联的产生是由于共同的客户、渠道、技术和其他因素的存在而使相关业务单元之间的价值链活动有可能共享。如果共享所降低的成本或增加的产品歧视性足以超过共享成本,则有形关联将导致竞争优势。无形关联涉及不同价值链之间管理专有技能的转化,没有活动可共享的业务单元在某些基本的经营项目方面却可能相似,比如客户类型、客户的采购类型、采用的制造流程类型及与政府的关系类型等。通过从一个业务单元向另一个业务单元转让基本技能或管理特定类型活动的专有技术,无形关联也可以导致竞争优势。
以市场、生产和技术三大类最显著的有形关联为基础进行的混合并购可能最能给公司带来价值的增加。和三类关联相对应,市场导向的混合并购战略致力于向共同的买主、分销渠道或地理市场推销新产品,能够获得市场关联的好处;生产导向的混合并购战略致力于使用共享的生产价值活动生产出相似的产品;技术导向的混合并购战略致力于以相似的核心技术为基础开发或进入新产业,包括售向现有市场或新市场的产品。
市场扩展型的混合并购和产品扩展型的混合并购就是以有形关联为基础进行的混合并购,和纯粹的混合并购相比,它们更能增加企业获利可能。公司在寻找混合并购目标时,应该尽可能寻找与公司现有产业之间存在市场、技术等有形关联的企业。
纯粹的混合并购增加公司价值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当沿着有形关联进行混合并购的机会很少或已经用尽而只能并购和现有业务毫不相关的企业的时候,可以考虑以无形关联为基础选择目标企业。寻找使无形关联导致竞争优势的机会是一个微妙的过程,因为无形关联可能只是某些价值活动中的基本相似性,任何两个业务单元之间也许都能找出某些相似性。
所以,公司在以关联为基础选择混合并购目标时,应该尽量选择和公司现有业务具有市场、生产或技术等有形关联的业务(企业),进行市场扩展型或产品扩展型的混合并购;在不得已进行纯粹的混合并购时,则只能尽量选择和公司现有业务具有无形关联的业务(企业)作为并购目标,但是在这种方式下,对公司鉴别和判断无形关联的能力的要求就很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