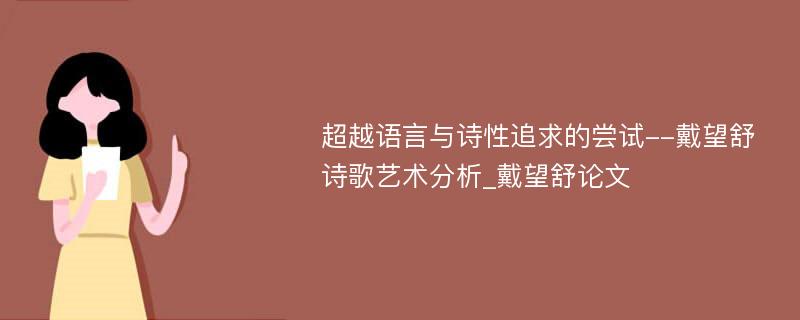
超越语言的企图与诗意追寻——戴望舒诗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艺论文,探析论文,诗意论文,语言论文,戴望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48(2003)02-0018-0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新诗坛,戴望舒(1905——1950)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诗人,上 承早期象征派与新月派的余绪,下启艾青等人的散文化追求[1],作为现代派的领军人 物[2],开拓现代主义诗艺的疆域,呈现了新诗整合的趋向和诗艺流变的多种可能,以 异常丰富的色彩,透明悬空的语言,朦胧蕴藉的诗境,融合中西诗艺的功力以及不倦而 执着的艺术探险,成就了中国新诗史上独特的艺术图景,成为新诗发展史上一块重要的 标志性碑石。从最早对音乐性的追求和象征性意象的融铸,到后来口语语吻美舒卷优雅 、精致细微的探寻,贯穿了诗人企图超越语言,倾心整体诗意追寻的艺术之旅。
一、音乐性与象征性
“望舒最初写诗,多少可以说,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3]最初写 诗的时间是指他1922年到1929年的诗歌创作。这正是最早的写实派与后继崛起的浪漫诗 派渐次隐去,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格律诗派居于诗坛主流的时期。也许有时风所及 的熏染,也许有着特殊人生经历的痛切体验,他在大革命一开始,即以青年人的满腔热 忱,投入革命文艺活动,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但大革命的失败使他陷入极度绝望的深 渊;爱情屡屡受挫,心境异常空寞。也许有着特殊的敏感,倾向于内心苦苦地思索,极 其恶劣险象环生的环境使诗人更加内敛。但选择低徊、幽怨的艺术感悟,我以为更得力 于诗人对诗艺探寻的深入思考和艺术追求的自觉。他在达成诗意美的追寻中,更加忠实 于自己对特定情况下内在生命感受。在前期《雨巷》一诗中,诗人用契合内心情绪节奏 的音乐性,传达了行走中的彷徨、惆怅、哀怨和寂寥。音乐性的追求并不是诗人的终极 目的,《雨巷》的音乐性也不同于闻一多和徐志摩的音乐美追求,在闻、徐,有着外在 形式整齐、划一的均衡,戴望舒的音乐性追求,有着更多摇曳多姿的情态。难怪叶圣陶 先生要感赞《雨巷》“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4],其实内涵的深刻理解则 是《雨巷》的音乐性更符合现代新诗传达现代人丰富多蕴、曲折多变的情感体验。一句 话,戴望舒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接着闻一多、徐志摩格律诗的接力棒,使音乐性更容 易贴切自然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心灵颤动,意即“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精妙的去处”[5] 。
音乐性服从于内在生命体验和情绪细微复杂的曲变,语言则更退居其次了。诗歌,作 为文学样式精炼、纯粹的一种体裁,较之其它文学样式,诸如小说、戏剧、散文,更是 语言艺术的塔尖,一般的理解是诗歌应有所谓“警句”、“诗眼”之类作点睛之笔,体 现诗歌语言艺术的精妙。但戴望舒追求的是散文的语言无法转述的东西,借助语言的音 乐性,传达整体地对生命形式意味的把握。语言在戴望舒的心中是一番超越的图景,当 诗意的追寻渐入佳境,语言的音乐性使语言消隐,音乐性也虽之遁去,给我们敞开了心 灵深处秘密的殿门,内心宇宙的星空繁星点点,一片神秘的闪烁,丰富而迷蒙。戴望舒 拒绝片断的诗歌语言,而在于整体的团状生命的体现。
初期象征诗派的第一人李金发,以“诗怪”的形象突现于新诗坛,在语言的移植上显 得生硬和隔膜,与中国传统的融合缺乏会心的感悟。戴望舒显然在前人的缺陷中发现了 新诗的追求目标,将中国古典诗歌神韵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技巧融为一体,力图让中西 诗歌的长处在新诗中发展,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创新之举。仍以前期的代表作《雨巷》为 例,诗人把法国象征派魏尔伦等人“模糊和精密兼备”的表现方法,与中国古典诗词“ 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商隐《代赠》)和“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 雨中愁”(李璟《浣溪沙》)的中心意象“丁香”,演绎成现代版的《洛神赋》,转化 成具体可感的“丁香姑娘”,在诗歌形式意味上,较之李金发食洋不化的情况,显得更 纯粹和具有透明性,惆怅、寂寥、彷徨、哀怨的“丁香姑娘”,她有着东方所特有的诗 情与甜蜜的感伤,但这一意象分明又注入了现代主义的风神,以超越直观的形象层面, 成为现代人寂寥彷徨心态的象征,那个时代特有的寻梦者、“倦行人”的象征,并使得 全诗的音乐也富于象征意味,整体性的诗意在象征所特有的蕴藉中,既完成了陈旧典故 的现代性转化,又实现了“姑娘”、“雨巷”的深藏意蕴,语言透明,力避了西方象征 诗晦涩的弊端,创造出一种属于汉语文化传统透明的朦胧之美,既“化古”又“化欧” ,带有诗人鲜明的个性,又极具民族特征,视野开阔的中西融合诗意追求,唱出了古老 民族本色的现代歌声。这种创造性的转化,自戴望舒的手中完成,真正实现了西方象征 派诗歌于与中国古老文明的对接和再生。
二、语吻美与现代口语
新诗建立之初,作为民族的新的诗歌品种,很自然地要落实到白话特征上来,使白话 成为新诗语言的正宗,胡适认为“白话是活文字”[6]而“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 ”[7],将新诗的白话定位于说诗的语言,“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 说。这样方才可以有真正的白话诗。”[8]新诗的语言就是说出的白话?朱自清在《论白 话》中说:“什么叫‘白话’?它比文言近于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的口语,可是并非真正 的口语。”“新诗的白话跟白话一样,并不全合于口语,而且多少趋向欧化或现代化。 ”[9]如果说着眼于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建设,在开手做起时,可以当作说话一样的提 倡,所谓矫枉过症,是一种切迫而必要的选择,然而到了白话文站稳了脚跟,着眼于建 设的阶段,白话诗就不能简单视为说白话了。因此有了朱自清先生的反问和解说口语问 题。可是为什么新诗的白话反而会是欧化的呢?白话遵循的语法是从西欧引进的,正象 说话不一定有诗意一样,白话诗也不一定纯是口语,因为它必然要在语法修辞规范下进 行。然而经由规范之后的白话,和书面表达的白话就别无二致。这也不一定达成诗意。 这需要再次打破语法修辞的锁链,适度调整和超越语法规范,再选造诗的语言(即白话) 的诗意。这个担子幸运地落在了戴望舒的肩上。
戴望舒中后期的诗歌创作(1929-1945)诗风为之一变,大力提倡新诗语言的口语化,追 求语吻美。所谓语吻美,是在一定的语言情境中,面对具体对象,表达者采取的相应口 吻、语态、节奏、韵味等诸要素达成的口语形态之美。这种语吻美的呈现,应和着表达 者内心的需要和诉求,随着表达者内心情感思绪的波动,导向体现内在情感的节奏。戴 望舒自己视为杰作,也的确在新诗史上专心追求语吻美的一首诗就是《我的记忆》。在 阅读大量法国象征派的作品之后,他意识到诗情的内在节奏的表达比新月派诗人所看重 的诗形外在的节奏更为重要。“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不能 借重绘画的长处”,“单是美的字眼的组合不是诗的特点。”[10]对新月派提出的诗歌 “三美”主张断然进行了否定,这里的“音乐的成分”指外在的音节节奏美;“绘画的 长处”指华丽词语构建的画面感;“美的字眼的组合”是指片断的意象的拼装以及诗歌 外形的均衡美。《我的记忆》开首的一句“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开始了自言自语的 独语式的表达方式的试验和探索。大量的铺排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烟卷、百合花笔 杆、破旧的粉盒、颓垣的木莓、酒瓶、花片、诗稿、灯……又在句末加上“的”、“了 ”的状态助词,显示了现代口语的舒卷优雅的风姿,不拘泥于片断的精致、漂亮、耀眼 ,而是让诗意整体弥漫升腾在整个诗句之上,所有日常物品之间,宛转溜走,构建超越 单个语词或语言意象片断的整体诗意。《独自的时候》、《游子谣》、《印象》、《百 合子》、《寻梦者》、《乐园鸟》等诗作,又大量使用语气助词“吧”、“呢”、“吗 ”和疑问句式,表达诗人内在情绪的迟疑、探问、关切、自问自答的犹豫不定,以平常 的亲切的口吻,独自思虑时的情绪波澜,席卷起语词的琐碎,升华为诗意朦胧、风姿绰 约、语言透明、极具现代风格品质的诗歌境界。
独语的姿态还表现出语吻之美的另一特征:潜入内心世界,执着表达诗人个人极为敏 锐而又独特的生命感悟与体验。即使是后期在狱中创作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这篇代表 作品,对诗人个人的感喟、疑惑、落寞、彷徨和忧愁,延伸为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深沉 挚爱,扩展为对内心世界之外的广袤土地的泣血忠诚,依然保持了诗人独语式的抒情个 性。在如锦障的繁花、嫩柳枝的芬芳、长白山雪峰的冰冷彻骨、指间划出的泥沙、寂寞 憔悴的岭南荔枝花、江南水田新生的禾草等意象之间,舒卷着依然是语吻自内心的幽微 精妙的美感,它们与灰烬、血和泥等指向的侵略者暴行,并没有直露的喊叫和外在渲泄 ,而是在整体诗情的自然波动中,深藏起诗人的至痛和至爱,仿佛沉默已久将爆发的火 山,又从极柔情的“恋人的柔发”、“婴儿手中乳”等意象,最后喷涌而出“那里,永 恒的中国!”的呐喊。全诗自然而然地顺着情感的河流穿山越岭,走岩出缝,最后汇入 浩瀚而凝聚几千年文明与传统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海洋,使得这首诗无论从主题意蕴到表 达形式和艺术成就上,都堪称新诗史上不朽与经典的篇章之一。忠实于诗人自身的内在 生命体验,并企图超越语言,让诗意自然相拥和渗透,这是戴望舒诗歌语吻美追求所启 迪我们的一个真谛:现代口语诗意的达成是内敛的、是沉潜的,是诗意的寻求,是别样 的抒情话语的创造,也是现代诗艺开辟的极具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新路。
三、诗意追寻与文本书面语言
诗歌肯定是语言的艺术,诗意的追寻当然离不开语言的革新与创造。戴望舒诗歌语言 之美的追求是现代口语独语形态的语吻美。但毕竟落实在文本上,成为一种文本的书面 语言。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完全等同于说戴望舒诗歌语言纯然是口语的诗化。口语中 的非诗化倾向,如化欧化不开,化古不成功,民歌中的复古和方言,对于新诗而言,都 是潜在的诱惑的陷阱。流于口号的口号诗,滥情而淹没个性的一些政治抒情诗,夸张而 矫情、虚假的大跃进诗,20世纪九十年代絮絮叨叨的琐碎私语,都是现成的值得镜鉴的 例子。在这些诗歌创作的散漫追求中,戴望舒的存在提醒我们,必须有开阔而博大的胸 襟,充分的中西诗歌传统的深刻领悟,坚守个性的独特体验,勇于且执着于诗美创造的 毅力,不断突破自己的冒险和探索,才是新诗保有存在价值和永恒艺术魅力的内在原因 。
书面的文本语言也不能因为语吻美的现代口语的成功排斥在诗歌语言之外。中国的新 诗即将走过百年的历程,其间诸多杰出诗人的心血凝聚成多样丰富的累累果实,然而, 我们在探索的路上还有两个参照系统的威压,使得现在正走在路上的诗人感到气短,古 典的辉煌与摹仿的痕迹(面对西方),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之中,常常使得无所适从。戴 望舒诗意追寻的启示更深刻的启迪还在于:融合而创新的中国新诗,首先是属于个人的 ,民族的独创性,任何失去自家面目而俯就的诗人,必然是没有生存能力的乞儿。
收稿日期:2003-0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