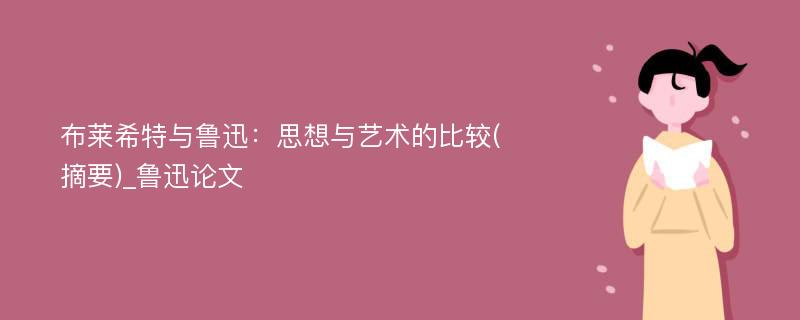
布莱希特和鲁迅——思想与艺术的比较(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布莱论文,摘要论文,思想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和鲁迅(1881-1936)是活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闻名世界的两位思想家和作家。青年布莱希特以其独特的“史诗剧或叙述体戏剧(Episches Theater)”和“陌生化或间离效果(Verfremdungseffekt)”理论反叛传统的,即亚里斯多德式的,以“共鸣(Einfühlung)”和“净化(Katharsis)”为主要艺术工具的西方戏剧,使戏剧成为社会批判的有效艺术形式。而鲁迅则以揭示病症,促人“反省”的小说和“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创作使艺术肩负着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使命。尽管他们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都从各自的思想出发点上,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探索,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取了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并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投入到了反法西斯文学潮流中去。他们都主张文学艺术的社会批判功用,迫使观众(读者)对社会现状进行理性思考,从而激发他们变革社会,改造Volkstümlichkeit(民族性或国民性)的愿望和意志。因此,鲁迅和布莱希特在创作思想和艺术技巧方面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尽管他们终生没有任何接触。本文尝试从他们各自对中国传统戏剧的态度入手,讨论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和鲁迅小说所表现的思想和艺术的差异和一致,进而揭示这相似的艺术形式的
一、中国传统戏剧:快乐的发现和清醒的批判
1935年2-4月,梅兰芳在苏联的访问演出引起了布莱希特的极大兴趣,鲁迅也恰好在梅兰芳苏联之行的前夕卷入了一场有关此事的文坛纠纷。这是我们今天得以了解两位思想家和作家艺术趣味的良好契机。
1.布莱希特1935年春的苏联之行及对梅兰芳京剧表演方式的初步观察。
布莱希特对中国传统戏剧(京剧)的真正接触是在1935年苏联之行中。(注:有关布莱希特此行详情,Vgl.Werner Mittenzwei:Das Leben des BertlotBrecht oder Der Umgang mit den Weltrtseln(Berlin-Weimar:Aufbau-Verlag,1986)Bd.1,SS.540-546.事实上,1925年布莱希特在柏林就观看了根据元曲李景道同名戏曲Klabund编剧,莱茵哈特(Max Reinhardt)导演的《灰阑记》,Vgl.Reinhold Grimm:Bertolt Brecht und Weltliteratur(Nürnberg,1961),S.19.)他的苏方接等待人特莱杰亚考夫(Sergej Michailowitsch Tretjakow)也是梅兰芳访问演出的组织者。(注:有关梅兰芳1935年访苏详细情况,请参阅王长发、刘华(编)《梅兰芳年表》(未定稿),收入《梅兰芳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也可参看许姬传《许姬传艺坛漫录》(中华书局,1997),页165-168,以及王长发、刘华《梅兰芳年谱》(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页126-130。)在莫斯科,布莱希特抱病观看了梅兰芳《打渔杀家》以及他的台下表演并参加了以梅兰芳为主题的座谈会。(注:W.Mittenzwei(1986),Bd.1.S.544.有关这次讨论会情况及发言记录请参阅由拉尔斯·布莱堡整理,梅绍武译《论京剧和梅兰芳表演艺术——1935年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讨论
2.鲁迅1934年对梅兰芳访苏的反应和对京剧艺术的态度。
1934年10月,国内文坛对梅兰芳出访苏联有两种反应,一派认为梅氏艺术之所以受苏联之邀是迎合了苏联正在流行的“象征主义”艺术思潮,而梅兰芳的表演将是“国粹的发扬”;一派认为梅兰芳的传统京剧是与苏联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因此对此加以嘲讽。对前者,鲁迅反对京剧是所谓“象征主义”或“象征手法”的观点,在他看来,京剧脸谱和手势是“优伶和看客公同逐渐议定的分类图”经过“夸大化”和“漫画化”而形成的类似但并非象征手法的东西,并且将随着舞台、观众和时代的变化而失去存在的价值。(注:《鲁讯全集》第6卷页134。)对于后者,鲁迅批判了这些试图超越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苏联文艺政策的歪曲。(注:《鲁讯全集》第5卷页582-583。)在《略论梅兰芳及其它(下)》中,鲁迅评价梅兰芳的艺术本是“俗人的宠儿”,但这种民间艺术却为士大夫们雅化,“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已经趋于没落而为梅氏所不知。(注:《鲁讯全集》第5卷页579-580。)
3.布莱希特对京剧表演艺术“陌生化”因素的合理想象和吸收。
梅兰芳京剧不能为无产阶级戏剧直接所用是1935年参加座谈会的戏剧家们的共识。但布莱希特看重的是它的艺术特征。就是说,他从中看到了“力求唤醒觉悟,而不是魅惑”的新型戏剧可以借鉴的表演技巧。他并且坦然承认,他和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在德国无产阶级戏剧实验中已经开始应用京剧中的“面具(脸谱)”、“姿态示意”、“舞台装置”等等艺术手段,这一新型戏剧被他们称为“史诗剧或叙述体戏剧”。(注:《梅兰芳艺术评论集》,页732。)
“史诗”(Epik)概念来源于古希腊语epós,亦即“言说”、“报告”、“讲述”之意,而形容词“史诗的”(episch)是指某种合乎此类特征的基本内在结构(注:Wolf Gewehr:Epik,Handlextion zur Lite-raturwissenschaft,Hrsg.vonDiether Krywalski (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1978)Bd.1,SS.116-117.)。皮斯卡托正是在叙述因素的意义上使用“史诗剧”这一术语的。20年代初期,皮斯卡托在他的戏剧实验中,就运用电影、幻灯等现代艺术手段于舞台,拓展了戏剧的表演空间以及对于大众的宣传和教育作用。(注:Erwin Piscator:"über Grundlagen und Aufgaben des proletari-schen Theater",In Manifeste und Dokumente zur deutschen Liter-atur1918/1933,Hrsg.von Antonkaes(Stuttgart:J.B.Metzlersc-he Verlagbuchhandluug,1983)SS.417-418.)他的“政治戏剧”(Der piscatorsche Versuch)给予布莱希特很大启发。他们之间曾保持过3年之长的合作。在布莱希特看来,皮斯卡托尝试(Der Piscatorische Ve-rsuch)是从戏剧(Theater)方面进行的“史诗剧”尝试,它与恩格尔(ErichEngel)导演的莎士比亚的《科里奥兰》(Coriolan)从戏剧(Drama)方面的“史诗剧”尝试不同。(注:Bertolt Brec
质即不再诸诉情绪,而应更多地诉诸理性。(注:GW,Bd.15.S.132.)因此,上述对观众的要求是“史诗剧”所追求的重要艺术目标之一。1930年前后,布莱希特开始了一段教育剧的实验时期。他认为“戏剧实验”是对世界的把握,或者说是对“事件”的把握。它促使演员既成为剧中人物,又要成为把握人物、事件、世界的观众,既是剧中人,又是受教育者。(注:W.Mittenzwei(1986)Bd.1.S.341.)教育剧的概念“原则上不需要观众”,(注:GW.Bd.17,S.1024.)表演者是戏剧舞台的重心,既表演行动者,又表演观察者。因此,布莱希特在1935年第一次观看京剧表演之时,除了对观众的“旁观”态度的观察之外,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梅兰芳所谓“观察自身”(Sich-selber-Zusehen)的表演方式之上,而对特莱杰亚考夫对于中国戏剧宣扬“忠诚和谦恭”的批判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后者关于中国戏剧形式上“有意识地使意味深长的部分直扣观众”的说法也许深深地影响了布莱希特,以致使他把“旁观”的态度误认为是观众理性思考的前提条件。(注:特莱杰亚考夫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是一位远东专家,《怒吼吧,中国》(Brülle,China!)的作者。1930年,当他访问柏林上演《怒》剧时,布曾撰文分析其艺术方式并为其辩护。1931年,特氏再次访问
关于这一概念或术语产生的历史,格里木(Reinhold Grimm)教授做了很细致的考察。但我根据上引1935年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讨论会上的发言内容发现,1933年(即他的第一次苏联之行)以后,布莱希特已经在试用“陌生化”这个术语了。(注:《梅兰芳艺术评论集》,页734。格里木(Grimm)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英国学者魏勒特(John Willett)的观点,认为1936年之后"Verfremdungseffekt"才出现。案:魏勒特是根据布氏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打印稿上的铅笔记载:“1935年春梅兰芳一行人在莫斯科进行表演,这篇文章即缘此而作”就断定"Verfrem-dungseffekt"直接产生在1935年梅兰芳表演之后,是不确的,See,John Willett:The Theatre of Bertolt Brecht.A study from eightaspe-cts.(London:Methuen,1959),P.178.格里木教授文章参看张黎编:《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科版,1984),页206。另他又在另一篇文章里把"Verfremdungseffekt"思想端倪追溯到布莱希特发现俄文"Ostra-nenie"(尖锐化)的1933年之前的"befremdend""befremdich"两词那里,Vgl.Reinhold Grimm:"Brechts Dramen-und Theatertheorie",In Brechts Drame:neue Interpretation,Hrsg.von Walter Hinderer(Stuttgart:Reclam,1984),S.24.)这说明在观看梅
4.布莱希特和鲁迅对中国戏剧的批判。
布莱希特说:“中国艺术家从魔术的符录里取得他的陌生化效果。”(注:GW,Bd.16,S.627.)演员只表现神秘,而不向观众揭示谜底,这暴露出一种“非科学”的认识自然或世界的原始方式,即缺乏对事件的理性思考。这也是鲁迅对中国旧戏批判的起点。
A.对“看戏心态”的批判是鲁迅一生的思想主题。所谓“看戏心态”是指戏剧观众不以情感、思考介入戏剧内容的纯“鉴赏”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戏剧的嘈杂场面妨碍了观众的投入。而内容上的假象、“梦境”又使他们不容易相信。久而久之,造成了中国民众“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的观念(注:《鲁讯全集》第1卷页186-187。),对一切都不认真加以对待和“事不关己”的冷漠、麻木的国民性。在他看来,中国戏剧传统造成了“无操守”的观众(民众)。(注:《鲁讯全集》第6卷页131。)这同布莱希特批判“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的‘无立场’”是相一致的。思想家鲁迅对民众的“无操守”的“看戏心态”表现出极大的悲愤和幻灭。(注:《鲁讯全集》第4卷页21、24。)他在著名的“幻灯事件”和小说《示众》里描绘了这样的“看客”。后来,鲁迅在题为《复仇》的散文诗中对此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他借“复仇”的方式将自身与周围的看客分离出来,形成了自身的批判立场。
B.“恐惧”(Frucht)、“同情”(Mitleid)、“共鸣”(Einfühlung)、“净化”(Katharsis)是亚里斯多德式戏剧的主要艺术工具(Organ)。在古希腊文化中“同情”与“命运”紧密相连。亚氏甚至把同情定义为人当“他人的厄运逼进时”的情绪反应。(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第八章,页89。)赫拉克里特把命运视作“自然规律的一致性”。(注:文德尔斑(Wilhelm Windelband):《哲学史教程》(Lehrbuch der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商务印书馆,1987)罗达仁译,下册,页55-56。)古希腊悲剧表达的观念是人类对命运的臣服。但“史诗剧”要把“同情”置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语境中来具体分析并指出命运是为人类所造就、掌握和改变的东西。(注:Gw,Bd.16.S.679.)鲁迅也认为“运命”是人事后的解释(注:《鲁讯全集》第6卷页131。),和布莱希特一样,他断言所谓命运是可山人类意志加以改变的。在《三分钱歌剧》里,“同情”被表现为资本,鲁迅也曾说过“惯用同情一类美好言辞作为‘放债’资本”的话。(注:《鲁讯全集》第3卷页498-500。)在《铸剑》中,他借人物之口指出“仗义”、“同情”之类是“受到污辱的名称”。(注:《鲁讯全集》第2卷页425。)可见,“同情”的
C.对马克思的同期接受及运用:布莱希特和鲁迅几乎都是在1926年接近并学习马克思学说的。这一年的十月,布莱希特集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投入《资本论》的研究之中。(注:Vgl.W.Mittenzwei(1986),Bd.1,S.343.)马克思的“异化”观被认为是“陌生化理论”最直接的来源。“史诗剧”的社会批判立场及历史化手段的哲学根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甚至布莱希特有关戏剧是生产资料的说法也受到马克思生产力学说的影响。而鲁迅则在与创造社的争论中逐渐借马克思思想来解释社会并认识到了政治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那种“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的品格,最终使他们的艺术成为批判的武器。
D.把反对“同情”的价值观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精神结合起来运用到艺术创作中去,就是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和鲁迅那种为读者开启“反省之路”的小说创作。“史诗剧”的反叛意义在于阻止“完全转换”(restlos Wandelung)即演员完全化为舞台上的人物,破坏“共鸣”(Einfühlung)以唤醒观众的批判能力,使观众采取一种批判的“立场”(Haltung)。(注:Vgl.GW,Bd.15,S.377.)服务于这一目的,“叙述体戏剧”要求表现事件产生的原因和其中隐含的矛盾(注:Vgl.GW,Bd.15,S.278.),并运用能够产生“陌生化”效果的手段使事件表现出一种新奇的、令人惊愕的面目。鲁迅也多次强调他的创作“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注:《鲁讯全集》第4卷页512。)布莱希特的戏剧利用歌曲、木牌、语言及角色互串来防止观众完全投入剧情,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亦“杂取”种种类型,以期读者不要将他误认为是“我”或某一特定的人,这也是“叙述体戏剧”那种“不表现个人,而表现集体和大众(Mass)”的艺术理想。此外,鲁迅一再强调不希望自己小说的读者受到作者情绪的感染:“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注:《鲁讯全集》第11卷页471。)因此他力求与读者保持某种适当的距离:“凡
E.布莱希特和鲁迅出于相似的艺术趣味都看重大众戏剧或民间戏剧(Volksstück)的艺术样式。《潘蒂拉和他的男仆马狄》就混合了民间戏剧的多种形态,造成了高雅与通俗、风格化和现实主义相间的艺术效果。在布莱希特看来,民间戏剧放弃了统一的、惯穿的寓言而成为松散相连的“速写”(skech)(注:Vgl.GW.Bd.17,S.1163.),并使全剧建立在一个特定的观点(即“立场”)之上(注:Ebenda,S.1163.),在这个意义上,它类似皮斯卡托的“史诗剧”所尝试的结构方式。在戏剧实践中,布莱希特甚至尝试给民间戏剧增添一些现实主义成份将之改造为一种新型戏剧。同样,鲁迅对于幼年所看到的绍兴目连戏久久不能释怀。这种戏剧“描写人情世故”亲切、情节简单、表演随意,并且以“活无常”等半鬼半人的形象作为人间正义裁判官的象征,它深深地打动了鲁迅。(注:参看《社戏》、《五猖会》、《无常》。)这甚至影响了他始终以民间戏剧的艺术标准来评判梅兰芳京剧艺术的行为。此外,布莱希特还学习吸收了日本民间戏剧“能剧”、“花道”和“歌舞伎”的传统艺术技巧。(注: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日]河竹登志夫:《剧场与观众》(节译),收入《现代西方艺术美学文选·戏剧美学卷》(页392-398)。)作为留日学生的鲁迅也对* 二、“陌生化或间离”理论与鲁迅小说的“叙述表演”。
布莱希特的“史诗剧”理论要点在于增加戏剧的叙述因素,其手段则是制造“陌生化效果”。在哲学层面上,“陌生化”要求认识主体与客体保持一定距离,在黑格尔的认识论里就是要求主体的自我反思,那么作为反思对象的“自我”与主体是一种疏离的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异化(Entfremdung)观念。(注:参见Reinhold Grimm:"Brechts Dramen-und Theatertheorie"In,Walter Hinderer(Hrsg.1984),S.22.)“间离”的效用在于使事件以一种陌生的方式被描述,并且完全以这种方式被把握。(注:GW,Bd.15,S.364.)鲁迅小说本身作为叙述文体也具有“史诗剧”的“间离”效果,其“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带有表演的性质,正如布莱希特在《街景》(Strassszene)中所描述的那位街头讲故事者一样,我把它称为“叙述表演”。
1.鲁迅小说第一人称叙述和“陌生化效果”的创造。布莱希特曾建议剧作家采取第三人称写作的技巧来创造“陌生化”效果。(注:GW,Bd.15,S.344.)在他看来,第一人称叙述容易使观众进入剧情并产生幻觉。而鲁迅小说中的大多数叙述者“我”则具有多重的结构。首先,“我”并非作者自身,其次“我”不仅是叙述他人行为或事件的完成者,而且也是他人(即剧中主要人物)的行为或事件的观察者或参预者。在艺术效果上,“我”实际已经承担了比第三人称叙述者更多的功能,它造成了叙述者、人物和读者间程度各异的距离感。
A.《狂人日记》、《孔乙己》和《祝福》中“我”离人物的距离最远。《狂人日记》中“我”以那短文言序中报告佚事的态度,说明了“狂人”的发疯、清醒的经过;《孔乙己》中,“我”以小酒倌的身份像经历一件趣闻趣事一样,叙述了旧知识分子孔乙己没落之路;《祝福》中的“我”则以一个转变中的知识分子的冷漠态度“参预”了乡村妇女祥林嫂的自我毁灭的过程。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代表着作者并不认同或反对的立场来看待故事中所发生的一切,使其具有明显的反讽意味。作者借对叙述者的态度描述,把评判的权力交给读者,逼迫读者采取反思的立场。
B.《在酒楼上》、《孤独者》中,“我”切近人物。“我”与吕纬甫在故乡的不期而遇,激起了后者的感伤和忧愁。“我”作为询问者和倾听者,好像也受到了感染并给予了同情。《孤独者》中,“我”目睹了魏连殳的几桩苦事,心里不免为他感到忧伤。但在这两篇小说的结尾部分,“我”忽然都从沉重中解脱出来,变得异常轻松(《祸福》中的“我”也是这样)。(注:参看《鲁迅全集》第2卷页34:“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页108:“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另还可参看《祝福》的结尾。)对此,西方学者赫特斯认为是“代表在那失望的梦、顽强的不能忘却的记忆、异己的生活都被驱开以后的净化的瞬间”。(注:赫特斯:《雪中盛开的花》,《中国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三期)。)而我认为,这一轻松的瞬间恰恰是作者理性的设计和安排,它在故事行将结束之际忽然把读者从叙述者的叙述行为里拉了出来。本来读者和“我”同处于“沉重”的情绪状态之中,但“我”的瞬间变化有效地避免了读者与叙述者的认同,起到很好的“间离效果”。而“我”对魏连殳和“我”对吕纬甫的同情被限制到叙述过程之中。布莱希特“史诗剧”并不排斥情绪,而是把情
C.《一件小事》和《伤逝》中的叙述者“我”虽然本身就是事件的参预者,但“我”的痛苦自责则把自己推为被评价的对象,同样达到了“陌生化或间离效果”。《三角钱歌剧》中尖刀麦基和波莉在幕间歌曲中反躬自评,与此手法是相一致的。
2.第三人称叙述造成的惊讶的艺术效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里,布莱希特让“大胆妈妈”拉着货车和孩子们走过了漫长的“三十年战争”而始终未使她认识到战争的危害,相反,她永远沉迷在“靠战争发财”的梦里。这出戏所表现的事件虽然平凡,但却使观众惊奇:大胆妈妈为何始终没有任何改变?鲁迅的《阿Q正传》与此十分相似,它在使我们惊奇之余,产生了惶惑和疑问: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阿Q为何也没有一丝改变呢?这立即使我们对革命本质发生质疑。鲁迅的阿Q是“杂取种种”制成的模型(“国民性”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大胆妈妈”还是“阿Q”,作为人格形象他们在作品里都是恒定不变的,这是与两位作家的变革立场相左的。因此,这里运用的是一种以创造“陌生化效果”为目标的“非自然”的表现方式。(注:Vgl.GW,Bd.17,S.1150.)而《阿Q正传》读者的惶恐、危惧心理则能够逼迫他们对自身进行批判和改变,这正是“史诗剧”要求观众采取的理性思索的立场。类似的“陌生化”手段还表现在《示众》那里。鲁迅把一群街头看客的神态表现得如此令人惊奇,不能不使我们关注、愤怒,进而思索这种怪诞的现象本身。
3.通过历史化达到“陌生化或间离效果”。“历史化”是“史诗剧”取得“陌生化效果”的重要手段。希莱希特说,“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曾经发生过的,并同特定时代相联系的事件。人们在历史事件当中的行为并非是人性的、不变的,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为历史进程所检验并是能够检验的行为而被投入到从后来的时代的观点的批判当中。持续的发展使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件对我们来说陌生起来。”(注:GW,Bd.15,S.347.)作为一种“陌生化”技巧,“历史化”首先应当把事件表现为“历史事件”,即在历史的流程中透视事件的本质、性质、原因,其次在于以一种当今的观念对这些事件进行评判,并以一种寓言的方式来关怀、回答现时代的问题。布莱希特把“大胆妈妈”的故事推向了遥远的“三十年战争”,借此呼吁人们警惕法西斯战争的危险。伽利略对科学的背叛发生在科学诞生的黎明,这事件阐明了科学的纯研究态度对社会产生的恶果,又一次回应了现时代的种种危机。(注:参阅恩斯特·舒马赫(Enst Schmach):《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是怎样通过历史化达到陌生化的》,收入张黎编《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鲁迅的《故事新编》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对现实问题通过历史“陌生化”的尝试。(注:陈* A.将时代现象拉回原始的神话时空中去,反衬它的无价值性。《补天》把人类的历史推向生命起源的年代。生命是伟大而粗野的,但人类却又发明了种种毁灭生命的手段:战争和摧残人性的封建思想。这篇小说做于1922年11月,就在上个月(10月)鲁迅写下了《兔和猫》,借家养的黑猫残酷地吞食了年幼的小兔的故事,发出了“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的感叹。(注:《鲁迅全集》第1卷页552~553。)女娲用紫藤飞速“抡”泥造人的颛顼、共工用暴力争夺天下的情节以一种历史隐喻的方式将发生在世俗世界里的事件在神话结构中“陌生化”了。更不用说将那汪静之的批评者化为了“古衣冠”的小丈夫,作为封建思想的代表者,它同样具有生命毁灭者的寓意。《补天》原被收入《呐喊》从侧面证实了作者寄予它的深刻现实意义。《奔月》把高长虹等曾受过鲁迅沤心沥血的帮助的青年对他的背叛借嫦娥、逢蒙对后羿的利用和谋害“历史化”、“陌生化”地表现出来。鲁迅又一次悲叹生命的无端浪费和损失。
B.将时代问题纳入具体历史情境之中,寻求真正的合乎历史发展的答案。《理水》里的“文化山”影射1932年北京“文化城”事件。而潘光旦的人种学研究和顾颉刚的“古史辨”讨论也被拉入“文化山”上。(注:《鲁讯全集》第2卷页387-388。)在鲁迅看来,潘、顾两位学者纯粹的学术研究没有真正的社会价值,反倒起着延误、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理水》向现代中国提出的问题是要保存传统文化,还是寻求变革;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还是将它导入实践。这关涉到现代中国的两次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之争和“科玄论战”,是有关中国现代性方案的设计问题。将这些抽象的问题以“历史化”的手段、技巧加以“陌生化”,势必引起我们深刻的思索。
C.将古老的观念置回历史,揭示其后果,并给予现代的评价。《出关》中,面对孔子虔诚的问学,老子出言甚微,而“大而无当”,讲学则亦无人能懂,终于没落而骑牛出关。《出关》宣告了传统的、思辨哲学的终结,呼唤哲学和思想的实践精神。作者借关尹喜之口说出了自己的评价。(注:《鲁讯全集》第13卷页318。)有意思的是,一位叫邱振铎的读者却从《出关》里读出了“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感觉着读者是会堕人孤独和悲哀中去,跟着我们的作者。”(注:《鲁讯全集》第13卷页312。)这种“自况”的“曲解”说立即遭到鲁迅的否认,可见,“陌生化效果”是作者刻意的艺术追求。
4.除了以上三种主要的“陌生化”手法之外,鲁迅还运用了“文体”(《狂人日记》“序”和“正文”,《采薇》中的诗歌)、“语言”(如《理水》中的“古貌林!”、“好杜有图!”)以及“情节中断”(《幸福的家庭》)等技巧同样收到了良好的“间离效果”。
三、思想、战斗和文学的乌托邦
(暂缺)
1.改造“民族性”或“国民性”的思想;
2.文学的战斗品格;
3.作为乌托邦的文学。
标签:鲁迅论文; 布莱希特论文; 戏剧论文; 梅兰芳论文; 陌生化论文; 艺术论文; 1935年论文; 文化论文; 祝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