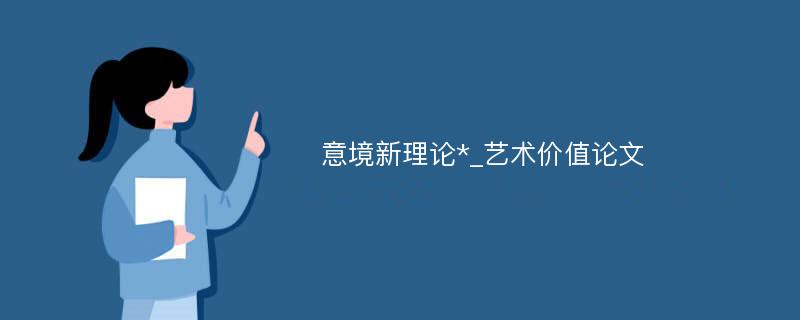
意境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意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古代文论;意境
一、意境范畴的含义与性质
意境概念现在用得很滥。这可以理解,因为在词语学意义上,凡“形象感人而又有一定意味和情调”的,都可以意境称之;但许多研究者也把作为美学范畴的意境和作为一般词语的意境相混,因而把它的含义无限扩大,似乎凡有感情有形象的作品都不出意境的范围,这样实际上等于把意境的美学特性给取消了。
意境范畴的词语构成,可以看作并列式:意与境;也可以看作偏正式:意之境。两种构词形式具有不同层次的意义:前者是从意境的构成层面讲的,后者才是从意境的性质层面讲的。一般对意境的论述,都忽略了这一区别,认为“情景交融”就是意境,这样就用意境的构成层面取代了意境的本质层面。
古今论意境的文献几乎可以车载斗量,当然其中各有各的价值,但真正抓住意境心理本质的,要数宗白华先生。他说:意境不是物理学上的,而是心中的。意境是“画家诗人‘游心之所在’,是他们独辟的灵境”。“游心之所在”和“独辟的灵境”揭示了意境的真义。它表明:意境之“境”(按“境”字本义为疆域),不是人现实生存的疆域,而是人心灵生活的疆域。有人用“意境是……的世界”这种形式来给意境下定义,其实,意境中的“世”界非世界,其中的世(人间世),意义是打了引号的,指的是审美感动中心理所呈现的境界。宗白华先生用两则引文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
方士庶在《天慵庵随笔》里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之间──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
恽南田《题洁庵图》说:“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洁庵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将以尻轮神马,御泠风以游无穷……时俗龌龊,又何能知洁庵游心之所在哉!①
文中重点,都是笔者所加,通过这些重点,意境的主体心理世界的性质应该是很清楚了。
二、意境的超越性
“境”(疆域)是时空的延展存在,而意境恰恰是要泯没时空的延展存在,所以它必须把现实时空变为心理时空。心理时空就是超时空。意境的呈现是没有过程的,它是直觉,是突入核心,是瞬间的闪光(王国维《人间词话》:“夫境界之呈现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同时,它又是没有疆界的,是无边无界的领域,也就是《庄子·齐物论》所说的“振于无竟”、“寓诸无竟”(“竟”晋崔譔注本作“境”,竟、境为古今字。释德清:“无竟者,乃绝疆界之境”),是王昌龄所谓“心超诸境外”(《宿天竺寺》)。时间失去了延续性,空间失去了广延性,成为超时空,从而与“无”冥合。不粘滞胶执于实有,与无冥合,才能摒除现实的时空范围(作动词理解),体验到无限、无穷的意味。摒除时空范围,与无冥合,在现实界是做不到的,只有在心理世界中才能实现,所以它是人皈返自身、向主体升华的灿烂成果。正如宗白华所说:“艺术意境,是诞生于一个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②
1 情景相生的超越
中国美学的情景相生说,可溯源于《周礼》《礼记》提出的“兴”和“感物”说,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给予了有力论述,但说得最透彻的还是数宗白华:
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替世界开辟了新境。③
情景拥抱、交合,相互激发,构成一种旋转突进力量,一层推进另一层,层层推进,达到“最深”;但是最深并不是“到底”,最深前面还有“更深”。在现实时空中,最、底、极,就是一定范围的边界、顶端,不可能还有“前面”,还有“更”。在最之上加更,这种矛盾修辞恰恰是要中断现实时空,打开心理时空,从而达到无限、无穷。无限无穷就是庄子说的“无境”和王昌龄说的“超境”。所以宗白华看重情、景相生,但并不止于情、景二元论,而是紧接着就不避重复地回到“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的主体一元论。
2 “景外”、“象外”的超越
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对“境”、“意境”作为美学范畴与作为一般词语严格区分,而抛开它在语源学上的种种意义,透彻地指出:“意境说的精髓,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境生于象外’”。他认为:境不同于象,“象”是某种孤立的、有限的物象,而“境”则是大自然或人生的整幅图景。“境”不仅包括“象”,而且也包括象外的虚空。境不是一草一木一花一景,而是元气流动的造化自然。这里抓住了──“意境”这个范畴所以不同于“意象”这个范畴,关键就在于“境”,可以说别具只眼。从这个关键出发,说得更清楚些,一物一象,万物万象,象尽于物,止于物;而境因物却不受物的限制,可以在有限中包涵无限,在一象中包涵大全,在尺幅中包涵宇宙乾坤,就象布菜克所说的:“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限放在你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中收藏。”④这样的“境”,泯没了时空界限,也只有在心理世界中或经由心理世界才能做到。因为“景外”、“象外”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人借助自己的精种超越有限的物质世界,而达到无限的人的精神自身的世界。
三、意境的终极价值依托
我们说,意境不是现实物质世界的境域,而是精神、心理世界的境域。物质世界的境域是客观实在的,而精神、心理世界的境域是“虚构”的,是瞬间生成的,是要主体自己建立的──而这就不能没有根,不能没有依托。根和依托就是:必须有一种终极价值作为归宿之地。在“虚境”中,有了这块“地”,境才有“疆域”。
这一点向来无人注意,超码是未见论述。其实,从意境的文化构成来说,道家的“道”,佛家的“佛”,儒家的“天”,这些超越有限事物有限时空的终极存在,是意境学说生长出来的直接的根。中国历代文人(官员也多是文人),尤其仕途受挫,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常是借助道家哲学、佛学或儒家天人合一的人格理论,把现实的偃蹇失意或打击迫害抛开或加以淡化,而在自己内在精神中建立一个自信自足、自适自怡的世界。因为人把握住了自身存在的最终依据,对现前的遭遇、得失、贫达、荣辱就不会一意胶执、耿耿于怀了。“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庄子·天道》)与这浑涵万有、生生不息的大道相比,一己的成败得失又有什么大不了呢?“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弘明集》卷一)成佛是大解脱,解脱之后,即有大自由,即有净土乐地,所以现世的一切也就可以捐弃。“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万物皆备于我也,反身而诚,乐莫大矣。”(《孟子·尽心上》)人的精神与天的意志本是相通为一的,所以人首要的是需培养这种精神,获得一种顶天立地的伟大人格,而不必牵就现前利害。这里,并不只是简单地否定个体生存或现实人生,而主要是设定一种无限的存在形式,使人能够超越有限的生存,使人能够超越眼前的得失。没有这种设定,超越是不可能的。而没有上述两方面的超越,也就没有意境可言了。只是,道也好,佛也好,天也好,都不过是人的精神的信念、追求、向往的一种表现罢了。所以,所谓超越,不能超到别处,只有超越向精神;所谓终极价值,也就是人的精神的最后皈依之所,或曰人精神的家园和住所。
因此,推开一步说,一切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都是为人提供精神的住所或家园的根据,都为意境提供一种可能,如西方世界的“神”(无论是人格还是自然神──泛神论的神),近代所追求的“人性”,一般人对爱和亲情的信念等等。《红与黑》中于连临刑前,百感交集地说:“要是有一个真正的宗教……一个真正的教士……那么,温柔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集合点……我们不会是孤立的……”(按省略号原有,表示于连边思索边自言自语)“人孤独地活着!……多么痛苦啊!……”⑤加缪也说:人能有所信仰──哪怕只是盲目的信仰──多幸福啊!因为没有信仰的我也就“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⑥“真正的宗教”、“真正的教士”、“信仰”都是保证人有一片和谐圆满的精神国土的基础,从而也就是产生意境的基础。这一点和现代生活、现代派艺术一比,就更加清楚了。当真正的上帝死亡之后,价值失去了依据,判断失去了准则,人的终极信念、信仰碎裂瓦解,精神的住所或家园骤然溃毁,人成了无所依靠的弃儿,领受的是失去存在根据的焦灼与荒诞,这就是为什么意境与现代派艺术是格格不入、南辕北辙的,现代派艺术与意境是恰成反对的!加缪正确地指出:现代艺术所失去的“首先是悠然自如”,代之而起的则是“惊慌而固执的神情,忧心忡忡的愁容及其突如其来和崩溃。”⑦
1 精神世界的统一性与终极价值依托
在提出与现代生活和现代派艺术的焦灼与荒诞对比的视点之后,我们得到一个十分强烈的认识:人趋向某种精神价值并获得自足感,与奠基于其上的主体世界的内在统一性,是意境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它的一个本质规定。统一性是一个自身圆足的闭合性概念,与我们前面论述的无边无际的无限性概念看起来似乎是彼此矛盾的,但实质上却恰好是相互依存的:没有统一性,也就没有无限性,无限性恰恰是统一性的结果。因为,世界只是碎片的堆积,鸡零狗碎,互不相干:人吃饭就只是吃饭,做爱就只是做爱,看书就只是看书……事尽于物,人尽于事,就根本无所谓无限性了。所以,在“无限”这个概念中,虽然是“无”修饰“限”(界限),但同时也是“限(界限)成全了“无”。这样就保证了“无”是可以永远充实的虚空,是不断的生成和延展,是无限,而不是无所运载的空虚,不是僵死凝寂的无谓,不是无有,不是无聊。意境论与道家哲学关系最深,道家讲的“无”,是在“道”的统一性前提下生成万有的无,它与作为终极存在的道是一体而二名的。意境中与无冥合的天也正是这样。所以,统一性保证了意境在无限中达到与无冥合,同现代生活和现代派艺术终极存在崩溃,终极价值碎散,无依无靠,无聊无谓,一无所有是截然相反的。
2 和谐与终极价值依托
从根本上说,意境是一种和谐美。而和谐的基础,也在于有一种终极价值作依托。简单地说,和谐在于有以和谐者。这“有以和谐者”从理论上说,就是某种终极存在或终极价值。意境的本原是心境,尤其是良好的、和谐的心境。外在的矛盾、不协调如万箭穿心,使五内俱焚,破坏心境同时对意境也有破坏性;但如果主体有某种终极价值作支撑,自身统一性坚固,还可以在相当程变上超越、包涵外在的矛盾与不协调。最为要害的是,主体内在的矛盾、交锋使心境完全瓦解,使人怀疑自己和整个人生的价值,这样意境就在根本上被破坏、被杀死了!正如加缪所说:“一旦人们觉察到战斗就在艺术家内心中发起时,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也更为致命了。”⑧所以意境需要以主客体的和谐,尤其需要以主体自身的和谐为基础。
四、意境的社会基础
应该承认并重申从社会基础理解文艺和美学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只有领会意境说孕育生成的社会基础,才能真正深刻地把握意境的独特本质──因为意境说的历史性使意境的产生受到一定的时代心理的制约;而一定的时代心理自有它的客观社会基础。
从世界文学的总体看,意境是一种古典美的艺术理想。它产生于我国中古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它以朴素的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强调景与情、情与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以人与自然、物与我的和谐为美,基本上属于古典主义范畴。它要求静态的形式的和谐,也要求社会伦理的和谐。⑨除了说意境“以朴素的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要求静态的形式的和谐”两点之外,这段话和我个人的认识十分契合。它以一种社会历史观点,揭开了意境范畴的深层内涵。
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在下述三个方面对意境的形式具有决定的意义,从而为意境本质诸方面提供生成土壤。
1 人的生产、生活直接依赖自然
这里需要先从“自然经济”这个概念说起。在经济学上,这是一个与“商品经济”相区别的概念,指以自己消费而不以交换为主要目的从事生产的经济形态。毛泽东用“自给自足”四个字最好地概括了它的特性。但从美学上看,它的内涵应更大些,还包括:第一,生产的对象是直接的自然,即土地、作物、森林、海洋等;第二,生产形式是凭借或通过人自己的体力;第三,生产单位是自己的家庭;第四,与家庭生产单位相联系的是相当固定的、与外界交流甚少的社群──村社。这一切合起来,构成这样的事实:人需突出地观察自然、认识自然、驾驭(其实主要是适应)自然,并通过这一切来开辟自己的生活。由于直接在自然中开辟出自己的生活,所以自然对人就特别亲近,以至在心理上它被升华为人们的家园或庇护所,成为人精神的寄托之地。同时,人由于直接面对自然而求取自己的生活,因而他赖以生存的中间环节就少,而在那种种中间环节中产生的互为依存纠结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新奇事物相对来说也就十分微少,人的生活、欲望是简单的,心理、情感是淳朴的。这样,就在经济基础上造成了最一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的和穆性质。
历史地看,自然就是在一个这样的时代走到人的意识、审美中来的。所以,它带有一路走来所源所经之地的强烈信息。因此在文学艺术中,自然事物和风光决不止是景物,而是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的某种寄托和象征;尤其,诗中间以陶渊明为首,散文中以柳宗元(《永州八记》)为首的一路,自然成为人们逃避社会的纷争,抚衡人世的污浊,放情怡志,保留人的自由与真性的产物。柏格森说:“当人的知性置于无生命的事物中,会觉得安全舒适,悠然自得。尤其当人们在物体中获得行动基础和劳动手段时,更是如此。”⑩只要把“无生命的”、“物体”两个词换成自然,这段话说出了中国古人其所以放情山水最深刻的根源。人们在长久的劳动生活中从自然中获得生存与庇护,发现、体会到自然的和悦与亲切,当他认识到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或在社会中偃蹇失意的时候,自然就成为与社会相对应、相抗衡的一个世界,供他们从精神到肉体在其中栖息游弋。文人们就是在这种生活中,或者通过以这种生活为艺术创作对象,来表达、创造中国艺术的意境的。当然,中国的艺术意境还有以宋词为代表的另一路,以自然景物作为情绪的烘托和象征,表现的不是现实的平淡化,而恰恰是更加浓丽;不是后退一步天地宽,而恰恰是在执着、沉溺中深化、强化一种心境。但尽管有这样的不同,自然却仍是作为人的接受者、作为人的感情的同情物,而它所烘托、象征出来的,即使是哀情愁绪,也仍然是一种美好,是所谓“蜜甜的忧愁”。
艺术作品的意境创造,基本可以说都是以描写自然为主,或者至少是与自然相关──把人物、事件放在自然的背景之下的。脱离自然或自然背景而创造意境的,恐怕很少或者干脆就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人的生产、生活直接依赖自然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
2 以人伦道德为基础的社会关系
前已指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不以交换和流通为生产目的,由交换和流通所产生的种种中间环节,以及由这些中间环节所派生出来的种种社会存在和人生形式也不发达,生活是封闭自足的,是缺少变动、刺激与骚扰的,因而人的心理也是简单淳朴的,社会关系一般来说也是和穆的、安定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基本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男女、长幼与乡党三种。前两种有坚强的血缘系带,后一种则以长期厮熟居处为根基,这样,人情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忠信谦让等一套伦理道德成为人们的共同规范。这一切在理论上,或者说在理想的情况下,确实能达到一种熙宁和乐的境界。人们常说的“田园牧歌”情调,即源生于此。我们曾说,意境是一种和谐美。意境的和谐美就是建立在淳朴的心理,和穆的社会关系,温情脉脉的生活形式这些基础之上的。在现代突出交换和流通的社会里,强调的是竞争和竞争意识;由交换和流通形成的庞大的中间环节充满了机会,人人都在寻求机会或失去机会;而这当中也充满了种种刺激,不是令人兴奋、狂热,就是令人失意、绝望。欲望成了创造杠杆的力臂,同时也把人高高地翘起,使他脱离坚实的大地,吊在空中晃荡。竞争意味着利害取代人情,流通意味着人际关系的多元、变动,甚至意味着辗转迁徙。一切都趋于不固定,趋于赤裸裸。因而由生活到心理,人都是无定型、不安定、焦灼、紧张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意境自然就失去了它现实的土壤。从基本性质上说,意境与现代城市生活具有不相容性。田园情调的消逝,就是田园诗的消逝,田园意境也就跟着一同消逝。
3 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
封建社会是政治统帅和决定一切的社会。在经济领域,政府对生产进行管理;在思想领域,当局确定一定的思想为正统思想,并且通过教育而加以贯彻,全国上下男女老幼都共同遵循这种钦定的思想,不能有所怀疑。这样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思想成为信仰。思想成为信仰之后,统治和压制的痕迹不见了,每个人都似乎得到了精神的最高原则和最后归宿。于是,也就不用自己在彷徨中去寻求人生的根据和行为的准则。个体也不需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而只需进入一定的模式或扮演一定的角色就行了。同时,思想的一统阻扼一切新思想的产生,避免思想的多元引起的混乱,使人在意识上呈现出一种愚昧的单纯。无论好坏对错,这客观上保证了意境所必须的终极价值依托。
在社会意识形态以个体或个性为主导的时代,情况就不是这样。偶像打翻了,权威没有了,人不能毫无怀疑、不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而获得生存和行为的根据,他怎样活着、该做什么,再不是只被动地听命于某种外在的教条,而是要经由自己独立作判断和选择。这样,自己怎样活着和做些什么,责任就只能由自己承担。而且由于价值的多元甚至是无限多元,有限的个体常常只能作一元选择,人很容易陷入对未被选择的企慕和选择的不安中。不得不选择,而选择却缺乏终极根据,个体就这样受到两难的折磨。勃兰克斯说得好:
在过去人一生下来就接受一种明确的没人怀疑的信仰,它提供了据信是从上天得来的答案,充满了安慰和希望。到十八世纪这个信仰被抛弃了,但人们仍然从小就接受一种同样教条式的、至少同样是灌输进来的信念,相信文明和启蒙的救世作用;他们认为当他们的哲学家们的学说被普遍接受的时候,幸福和和睦就会在全世界实现。到十九世纪这种信念的基础也被破坏了。历史似乎告诉人们,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于是人们的思想陷入混乱。(11)
这里,丝毫没有意思要说以个性意识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不好,也丝毫没有意思要说以政治意识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更具有优越性。实际上,前者比起后者来,是较高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我们这里不是要比较两种意识形态的优劣,而只是要说明:后者为意境的产生提供了保证,而前者不能提供这种保证,相反,它使意境解体。也就是说,意境是古典社会的产物,是一种古典美,它对于现代社会,对于表现现代生活,是格格不入的。
五、意境的诗意内涵
要给“诗意”或“诗意性”下一个定义很难做到尽如人意。尽管如此,“像诗中表达的给人以美感的意境”(《现代汉语词典》)这样一个简单的解释,在我看来还是抓住了其中最根本的内容:这就是“给人以美感”。意境的内涵就是诗意,并且可能只能是诗意。因为意境是一种和谐美,是主观心境及由主观心境所决定的人与对象世界的(瞬间的)相洽相得,所以它是矛盾的克服或超越,是人生的美化,在根本上只能是美,而不能是丑。也就是说,意境是美感的产物,艺术作品的意境所激发的也只能是美的、和谐的感情,而不能是压抑、荒诞、恶心等类的感情。(这里只是从逻辑层面着眼,若从历史层面说,意境作为美学范畴,首先是从我国古代的诗歌艺术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这一历史情况对它的诗意性内涵亦具决定作用。)
1 情感调质的诗意性
从构成要素上说,意境确乎可以分析为情与景两个方面。只是,意境中的情与景,并不简单地就是原始自然的实情实景,而是经由主观心境所美化了的心情与心景。这当中首先是,情感的调质是诗意性的,或者说,是美的。这样的情感具体表现为爱、欣赏、愉悦、留恋、低迴、旷达、豪迈、和穆、忧伤……这一类正面的、对事物有所肯定的情感;而仇恨、厌恶、鄙弃、不安、斤斤计较……等负面的或者对事物持否定态度的情感,很难成为意境的构成要素。
2 描写对象的诗意性
意境的“境”离不开一定的风景、环境或事件,它需要由一定的风景、环境或事件所激发,并且要以之为依托。但是,那些不能成为人的生存风景的自然物(灾难性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等),那些肮脏的、丑陋的、杂乱的、险恶的环境,那些争权夺利的、残酷的、无人性的事件,因其不能激发人的和谐的、达到对无限的体认和向往的心境,所以也就不能成其为意境的构成要素。意境中的风景、环境或事件,只能是美的,或者是能调动人的审美感情的,一句话,是人的精神所能掌握住,并能在其中获得自由感,感到自身的充实弥满的。这就是为什么意境的创造多写自然、家庭、友朋相与的原因,也是现代城市、交易所、为噪声废气所污染的工业生活很难或很少得到富有意境的表现的原因。
美的情感和美的景物、环境、事件相结合,或者说,美的景物、环境、事件激发美的情绪、心境,就是诗意,就是意境。所以意境在本质上是诗意的、美化的,是人、人的精神的肯定形式。正因为如此,人人都愿意获得一种意境盎然的心态,人人都愿意过一种富于意境的生活。
3 诗意的创造性
意境既然是美化的,那就不是原始自然的,而是由人的心境所创造的。用加词尾(或词缀)的方法构成的新词在汉语中很少,而形容词加词尾“化”构成的动词,却都有很妙的意义,如“美化”、“文化”、“绿化”、“诗意化”等等,它们表示了人的创造性,是对人的力量的肯定。所谓诗意化,就是把生活化为诗、提高为诗。而“诗”西文源于古希腊语,本义是生产、创作;把生活化为诗、提高为诗,就是要创造生活,创造健康而美好和生活情绪。
美化、诗意化就是不断地生成、创造。但所创造出来的,又不能固定地、实实在在地持有、存放,它是即生即灭的。作家艺术家用文字或线条等创造意境,似乎把意境固定住了,但其实也只是编织了很好的“索引”,要体验、进入这一意境,仍然需要读者(包括作者重读之时)重新创造。中国古人所谓“诗在境会之偶谐”(许学夷《诗源辩体》)、“夫境界之呈现于吾心而见于外物,皆须臾之物”,即是此意。这里,我们在新的层次上又碰到了本文第二节所论述的内容:诗意内涵的获得又把意境带到了时空之外。由于瞬间性即是不能固定地、实实在在地存放或持有,也由于时空之外就是“象外”、“景外”、“言外”、“韵外”,所以它避免了有限性(固定的、实实在在的景、象、言、韵总是有限的),而与无限、大全联成一体。
4 诗意的朦胧性
诗意或美是把人从有限性中解放出来从而与无限、大全相通的一条重要通路,但这条通路却是无迹可寻的,一如马祖荣所说:“冥冥濛濛,忽忽梦梦。沉沉脉脉,洞洞空空。莫窥朕兆,伊谁与通?”只有是“无”才是无限。所以诗意总离不开朦胧混融性,至少要有所隐默含蓄。西人罗滨逊说:“诗设法告诉我们不可言喻之物”,不可言喻之物不在逻辑和理性认识之中,而在意境或诗意之中,同时这不可言喻之物又赋予诗意或意境以朦胧混融的性质。
*收稿日期:1994-03-18.
注释:
①②③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9、219-220、211页。
④见梁宗岱译《天真的预示》。
⑤司汤达:《红与黑》,闻家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版,第637、638页。
⑥⑦⑧参见《文艺理论译丛》3,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313、469、470页。
⑨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页。
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1)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