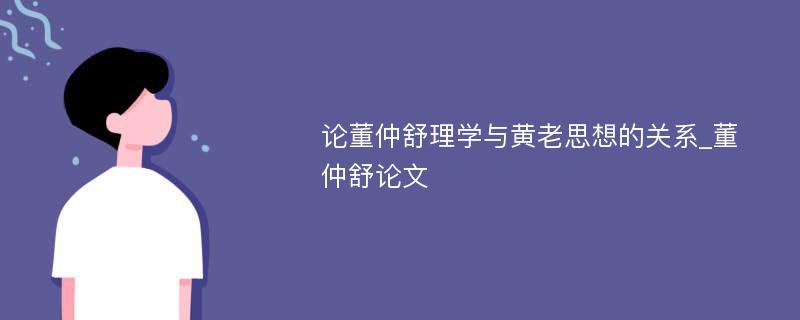
論董仲舒新儒學與黄老學的思想聯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仲舒论文,思想论文,新儒學與黄老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學自孔子開創起,經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倡大,於先秦諸子中雖非一統天下,但也一直貴爲顯學。《韓非子·顯學第五十》云:“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①至秦並六國,始皇焚書坑儒,一度沉落,經殘學暗,淪爲潜流,微息尚存。漢承秦制,也承其弊,與民休養生息,黄老學應時而起,風靡朝野,成爲時之主流思想。漢武帝召賢良對策,接受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之對策,“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儒家思想隨之定爲一尊。在這一過程中,就儒學發展來說,先秦儒學與董仲舒儒學之間有一個斷裂,在這個斷裂之中,有處於主流思想地位的黄老學。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概括黄老學②“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對儒家思想進行了吸收。而從黄老學到董仲舒新儒學是怎麽過渡的,黄老學與董仲舒新儒學之間關係如何,前人很少論及,也未受到相關哲學史、思想史著作的重視。吳光先生發現了這一重要的關聯,指出:“從黄老之學對董仲舒新儒學的影響來看,證明黄老之學在由先秦諸子之學向以董仲舒爲代表的漢代儒學的轉變過程中間,在思想史上起了承上啓下的中間環節的作用。”由於該書重點在論述黄老,故對此尚未展開具體分析。因此,本文擬在吳光先生思路的基礎上,通過具體分析,進一步論證黄老學黄老學與董仲舒新儒學的關係。 一、黄老學與董仲舒新儒學都具有相容諸子、吸取衆家思想爲我所用的特點 “秦漢時期學術思想的相容互補過程,不再是無規律可尋了,而是存在著兩大主流,即沿著兩條基本綫索而發展。一條是經《呂氏春秋》、陸賈等,並由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一文予以總結的綫索。它以道家學說爲主幹(集中體現在天道觀、發展觀上),並廣泛吸取儒、墨、陰陽等學說的重要內容(主要是社會政治思想方面的內涵),而建設起來的新的思想體系……另一條是以董仲舒爲主要代表,以墨家的“天志”觀和陰陽五行理論爲哲學理論基礎,以儒家仁義禮樂思想爲社會政治學說之核心,並結合法家的統治手段與墨家的“尚同”觀點而系統形成的漢代‘新’儒學體系”。③說明黄老學與董仲舒新儒學都有根據時代要求吸收諸家之思想的相容特點,這一點毋容置疑。 對於黄老學這種相容諸家思想的特點,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給予了系統而準確的總結,“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④對“陰陽之大順”、“儒、墨之善”、“名、法之要”進行了吸取。司馬談所謂的“陰陽之大順”、“儒、墨之善”、“名、法之要”中“大順”、“善”“要”具體是何內容呢?就是他在分析各家得失時所肯定的各家所長,即陰陽之術“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强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淮南子·齊俗訓》中也對此進行了論述:“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如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於體。”⑤肯定各家學說理論的合理性,積極吸取這些合理成分,並認爲各家可以互補。當然,黄老學相容各家思想的前提是堅持自己的主體性和核心理念,首先要求“整齊輿論”“統一思想”,《呂氏春秋·執一篇》:“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亂。”⑥《呂氏春秋·不二篇》:“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异則亂;一則安,异則危。”“統一思想”是用黄老學統一,並統一到自己的核心理念中來,即“自然無爲而無不爲”的“道”。《淮南子·原道訓》稱:“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裏天地,稟授無形;原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冥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纖而微。”這就是老子所稱的“惟恍惟惚”“恍兮惚兮”的“道”。所以說黄老學是在不背離道家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對各家進行融合吸收的。司馬談總結道:“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⑦黄老學吸取各家之長,這是黄老學與先秦道家不同之處,是黄老學所“新”之處;但黄老學又堅持了道家的主體性和道家的“道”論,這是黄老學歸宗於道家之處。所以,有學者稱黄老學爲新道家,也未嘗没有道理。道家通過吸取各家所長來充實自己,形成新道家學說,即黄老學,在漢初七十年間蔚然成風,成爲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這必然對董仲舒新儒學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使董仲舒新儒學也具有這樣開放納异、相容衆家思想的特點,而且是在堅持儒學基本原則前提下的納异相容。 先秦儒學有不足之處,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指出:“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董仲舒新儒學要想得到生機並獲得最高當局的認可,必定要吸取諸家之長,建立切合社會發展的思想體系,況且前已有黄老學的成功典範。正如徐復觀所說:“董氏的天的哲學是一個大綜合:他所用的方法,也是一個大綜合。”⑧於是,董仲舒新儒學中或明或暗、或多或少都有諸家思想的影子,而且有些是直接拿來的。吳光先生認爲:“(董仲舒新儒學)是以先秦儒家的思想資料爲骨架,吸收並改造了先秦諸子之學和漢初黄老之學的主要內容以後,建立起來的一套內容比較完備、結構比較精緻的新儒家思想體系。”⑨鍾肇鵬先生明確地提出:“董仲舒的思想更是相容法家、陰陽家、道、墨各家。”⑩首先他吸收道家思想並對之進行改造,《漢書·董仲舒傳》:“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11)把儒家的仁義禮樂統攝於“道”,此“道”的本質與道家之“道”不同,但卻是借用了道家概念。還有他讚嘆舜繼堯之大業,“垂拱無爲而天下治”,“爲人君者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静而無形,執一無端,爲國源泉”(12)(《春秋繁露·保位權》),肯定了道家的“無爲”思想。法家講“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韓非子·八經》),董仲舒也講“人主居德之位,操生殺之勢,以變化民”,吸取了法家“勢”的精神;“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韓非子·難三》),强調“術”的神秘性,而董仲舒改造爲“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春秋繁露·立元神》)。君主應神秘莫測,纔可駕馭一切。還吸收了法家“循名責實”的思想,“考績黜陟,計事除廢;覽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春秋繁露·考功名》)。對於墨家,董仲舒吸收了“尚同”和“兼利”思想。《墨子·尚同上》曰:“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13)董仲舒講“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爲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爲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爲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兼利”爲墨家用語,董仲舒也提到“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春秋繁露·諸侯》)。關於陰陽思想,《漢書·五行志上》:“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14)董仲舒新儒學雖吸取了諸家思想,但其主體性還是儒家,他認爲:“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春秋繁露·玉杯》)並强調儒家“仁政”和“德治”思想,主張:“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春秋繁露·基義》)又進一步提出了“德主刑輔”的治理理念:“刑主殺而德主生,天親陽而疏陰,任德不任刑……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輔也。”在融合諸家思想因素的基礎上,董仲舒也提出了思想統一的要求,並且是統一到儒家思想上來。他對策道:“今師异道,人异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5)(《漢書·董仲舒傳》)在這裏更加體現了董仲舒尊孔述經的儒家色彩。董仲舒新儒學納异融合諸家之思想,這是它與先秦儒家不同之處,是其所“新”之處;同時,又推明孔氏和祖述六經,提倡仁政和德治,這是它歸宗於儒家、其思想實質上爲儒家思想之處。因此,稱董仲舒學說爲新儒學,實爲的當。 黄老學和董仲舒新儒學都是在堅持自家思想主體性的前提下,針對時代之所需,相容諸家思想之長,形成各自的新的思想體系,這是它們的共同之處,也是黄老學對董仲舒新儒學影響的結果。至於黄老學是如何具體影響董仲舒新儒學的,或者董仲舒新儒學思想是怎麽從黄老學那裏吸取營養成分的,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探討。 二、黄老學對董仲舒新儒學的影響 黄老學對董仲舒新儒學的影響在兩個方面比較明顯,一是“無爲無不爲”的思想,積極進取,把天道與人事緊密聯繫起來,達到無爲而治的政治目的;二是陰陽刑德思想,使董仲舒形成了“陰尊陽卑”統理下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念。 (一)“無爲無不爲”的思想 黄老學與先秦道家的重大不同之處是由消極避世變成了積極入世,所講的“無爲無不爲”已發生重大的變化。《黄老帛書·十六經》云:“欲知得失,請必審名察刑。刑恒自定,是我俞静;事恒自也,是我無爲。静毆不動,來自至,去自往。”(16)《道原》篇亦云:“上虛下静而道得其正。信能無欲,可爲民命。上信無事,則萬物周扁。分之以其分,而萬民不争;授之以其名,而萬物自定。”這樣的“無爲”不是無所作爲了,而是上下有分,各在其位,各擔其責的“無爲”了。《文子》作了進一步的說明:“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卷握而不散;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17)“無爲”不是不作爲,而是不以“私志”害“道”的無爲,是循理舉事、因資立功的有爲了。《淮南子·原道訓》中也有這樣的論述:“萬物固然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所爲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這裏是“不先物爲”的無爲,“因物之所爲”的無不爲;“不易自然”的無治,“因物之相然”的無不治。並通過“不先物爲”的無爲達到“因物之所爲”的無不爲,“不易自然”的無治達到“因物之相然”的無不治,進而由“因物之所爲”的無不爲達到“因物之相然”的無不治。一是這樣的“無爲”不是不爲,二是這樣的“無爲”是爲了達到“無不治”,下貫到了社會治理。這些思想在早期道家中是没有的,是到黄老學者纔具有了這樣思想。董仲舒吸收黄老學“無爲無不爲”的思想,“故爲人主者,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立無爲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群臣效當,故莫見其爲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春秋繁露·離合根》)。“爲人君者,居無位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静而無形,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春秋繁露·保位權》)。這是“乘備具之官”上下有分、各擔其責的“無爲”,是“執一無端”的不需事必躬親的“無爲”,而不是不理朝政、放任臣下的“無爲”;是君無爲而臣有爲的“無爲”,而不是君無爲臣也無爲的全都“無爲”。在這裏,董仲舒還吸取了黄老學的“道”論,將天道和人事聯繫起來,“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异……人道者,人之所由”(《春秋繁露·天地陰陽》)。把“道”下貫社會人事正是黄老學與早期道家的重要區別之一,正如《淮南子·要略訓》所云:“言道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把“道”和“事”聯繫起來,只言“道”不言“事”,就無法經世致用,只言“事”不言道,就不知所止。從這些對比分析來看,董仲舒吸取的這些道家思想資源,在早期道家中是没有的,而在黄老學中都能找到其根源,這說明黄老學對董仲舒新儒學的直接影響。 (二)陰陽刑德思想 關於陰陽思想,裴駰《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録》:“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鄒衍及其後學主要是“言天事”。而到了黄老學這裏,就有不僅僅盡言天事的內容了,《呂氏春秋·應同》云:“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見祥乎下民。黄帝之時,天見大蟥大螻。黄帝曰:‘士氣勝。’士氣勝,故其色尚黄,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春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文五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大。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徒於土。”把談天事落實到了人事之上。而董仲舒的“天人”陰陽觀更加落實到了人事之上,《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已受之於天也。”《漢書·董仲舒傳》中也記載:“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這一“天人”陰陽觀統理下,下貫到人事的陰陽刑德思想,“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春秋繁露·基義》)。這段名言的依據來自《黄老帛書·稱》所論陰陽大義,“凡論必以陰陽之大義:天陽地陰,春陽秋陰,夏陽冬陰,晝陽夜陰……主陽臣陰,上陽下陰,男陽女陰,父陽子陰……諸陽者法天……諸陰者法地”。董仲舒對之改造爲“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王道之三綱。《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中又言“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這就是“陽尊陰卑”的思想。在此基礎上,董仲舒把陰陽和刑德相聯繫,以陰陽論刑德生殺,“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漢書·董仲舒傳》),並宣傳“陽爲德,陰爲刑……天之任德不任刑”。董仲舒的陰陽刑德思想在先秦儒家那裏找不到相關的根據,而黄老學中卻有這樣的思想,《黄老帛書·十六經》云:“春夏爲德,秋冬爲刑,先德後刑以養生。”“是故爲人主者,時控三樂,毋亂民功,毋逆天時……夫並時以養民功,先德後刑,順於天。”這裏講“先德後刑”,董仲舒講“任德不任刑”,“任德不任刑”首先具有“先德後刑”的意蘊,相對來說更注重了“德”的主導性。但同時董仲舒也並不是完全否定“刑”的作用,也不是不需要“刑”,“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爲春,賞爲夏,罰爲秋,刑爲冬。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不可不發,若暖暑清寒,當其時不可不處也。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副》)。意思就是罰刑不可不具,同時要刑當所正,說明了“刑”的需要性。這一思想同樣可從黄老學那裏找到類似的論述,《黄老帛書·十六經》云:“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繆繆天刑,非德必頃。刑德相養,逆順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刑微而德章。其明者以爲法,而微道是行。明明至微,時反以爲幾。天道環於人,反爲之客。”可見,董仲舒新儒學從黄老學那裏吸取了陰陽刑德的思想,不過是站在儒家“仁政”的立場,更加注重“德治”,强調以德爲主以刑爲輔的“德主刑輔”的政治理念。 三、董仲舒新儒學對黄老學的發展及其流弊 董仲舒新儒學從黄老學那裏吸取了許多思想資源,並對之加以融合改造,形成了自己的適合社會發展的新儒學體系,並取代黄老學被最高統治者定爲一尊,成爲當時社會的主導思想。就黄老學和董仲舒新儒學來說,黄老學之所以被取代,表明有其局限;董仲舒新儒學成爲主要思想,表明其有發展。同時,相對於黄老學某些思想,董仲舒新儒學改造過頭,或推向了極致,從而導向了片面化,導致流弊。 黄老學相對於早期道家思想雖有積極進取之處,但畢竟它屬於道家,建立在“虛無”“因循”的基礎上,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中總結爲“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淮南子·修務訓》云:“循理而舉事,因事而立權,推自然之勢。”《黄老帛書·十六經·姓争》云“静作得時”,這就導致了其因循保守、虛無放任的局限。雖然它的思想符合了漢初休養生息的需要,曾風靡一時,但卻不能長久。隨著西漢各方面實力增長到一定程度,已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至“雄才大略”漢武帝時,積極有爲,需要新的思想指導,黄老學隨之沉落,而積極主張“更化”的董仲舒新儒學也隨之興起,成爲了當時的主導思想。相對於黄老學來說,董仲舒新儒學更加强調積極有爲的政治治理,一是把天道下貫人事,“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异……人道者,人之所由”(《春秋繁露·天地陰陽》),“道”不僅是物之道,還有人之道,“人之所由”人道也。二是把“無爲無不爲”的主體具體落實到君主身上。黄老學所謂的“無爲無不爲”的範圍很廣大,没有具體的落實者。而董仲舒新儒學明確了“人君”“人主”的主體,比如《春秋繁露·保位權》云:“爲人君者,居無位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静而無形,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春秋繁露·離合根》也有這樣的論述:“故爲人主者,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立無爲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群臣效當,故莫見其爲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這樣就更加具有政治落實性了。 相對於黄老學,董仲舒新儒學也有倒退之處,一是把“道”人格化。在黄老學那裏,“道”一般是客觀性的自然規律,《黄老帛書·經法·論約》云:“始於文而卒於武,天地之道也。”“三時成功,一時刑殺,天地之道也。”這裏所謂的“天地之道”是“一立一廢,一生一殺,四時代正,冬而復始”,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具有客觀性。而董仲舒所謂的天道是有意志的人格化的,這就導向了神秘主義。二是接受陰陽家“禨祥度制”,把陰陽五行導向了競言灾异的讖緯之風。誠如劉師培所說:“周秦以還,圖籙遺文,漸與儒道二家相雜。入道家者爲符籙,入儒家者爲讖緯。董、劉大儒,競言灾异,實爲讖緯之濫觴。”(18)所謂“董、劉大儒”就是指董仲舒、劉向等西漢大儒。而黄老學是不接受陰陽家“禨祥度制”的。“黄老哲學家不過是‘因陰陽之大順’而已,他們對陰陽家那一套‘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論六家要指》)的‘禨祥度制’是有所捨弃的,他們所强調的主要還是‘道’的‘無爲無不爲’的特性”。(19) 綜上所述,黄老學與董仲舒新儒學都具有在堅持自身主體性的前提下相容諸家思想爲我所用的特點,這是它們的共同點。作爲取代黄老學而起的董仲舒新儒學形成受到了黄老學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也是不容置疑的。同時,董仲舒在黄老學基礎上的發展也具有自己的弊端,這也是要辯證地看待的。總之,黄老學對董仲舒新儒學的形成具有重大影響,是先秦諸子之學向以董仲舒爲代表的漢代儒學轉變過程中重要的中間環節,具有思想史上承上啓下的重大作用。 本文是在業師吳光先生指導下完成的,其中有些論述採用了吳光先生《黄老之學通論》的內容,在此表示感謝。 ①本文所引《韓非子》內容是據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版《諸子集成》第5卷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②關於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所指“道家”實際是指黄老道家的論點,可參見吳光《黄老之學通論》第七章第二節的論述:“《論六家要指》是一篇站在道家立場上(確切地說,是站在黄老道家立場上)概括和總結先秦至漢初主要學派的學術要旨的思想史著作。班固曾批評司馬談、司馬遷父子‘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過去許多人以爲班固批評錯了。我卻認爲,班固所持儒家立場雖然並不正確,但就這一批評說,班固的見解是符合事實的……司馬談所謂的‘道家’,並不是老、莊一類的早期道家,而是指秦漢之際的黄老學派,只不過他未能將二者加以具體區分罷了。”見吳光:《黄老之學通論》,桂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6、230頁。 ③黄樸民:《天人合一——董仲舒與兩漢儒學思潮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13年,第27頁。 ④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58頁。 ⑤本文所引《淮南子》內容是據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版《諸子集成》第7卷高誘《淮南子注》,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⑥本文所引《呂氏春秋》內容是據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版《諸子集成》第6卷高誘注《呂氏春秋》,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⑦《史記》,第759頁。 ⑧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40頁。 ⑨《黄老之學通論》,第27頁, ⑩鍾肇鵬:《董仲舒和漢代儒學》,《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年第2期。 (11)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562頁。 (12)本文所引《春秋繁露》內容是據中華書局版《新編諸子集成》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13)本文所引《墨子》內容是據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版《諸子集成》第4卷孫詒讓《墨子間詁》本,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14)《漢書》,第570頁。 (15)同上,第216頁。新儒學,實爲的當。 (16)本文所引《黄老帛書》內容是據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馬王堆漢墓帛書》,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17)本文所引《文子》內容是據中華書局版《新編諸子集成》王利器《文子疏義》,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18)劉師培:《國學發微》,載《劉師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54頁。 (19)《黄老之學通論》,第2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