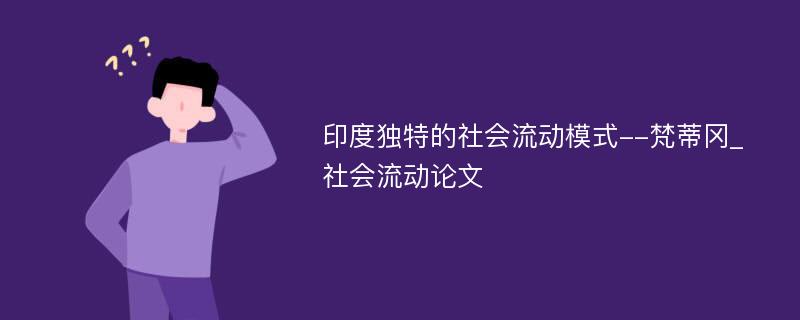
论印度特有的社会流动模式——“梵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特有的论文,模式论文,社会论文,梵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印度的种姓制度已经存在了3000多年,它是以印度教为依存载体,“纯洁—污秽”观念为核心价值概念的人类等级制度,在印度社会里,这一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等级最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对印度社会的影响就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其本质而言,种姓制度是统治阶级实施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工具,这个等级制度曾被马克思称为“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人民出版社,1972,第73页。)但从古至今,不论是莫卧儿帝国的穆斯林军事力量,还是英国近200年的殖民,甚至在圣雄甘地的伟大号召力下,都不能使它土崩瓦解。那么,在种姓制度这种钢性的社会等级制度下,低种姓的印度人能否通过某种途径来改善先天赋予的种姓身份而达到提高社会身份的目的呢?本文通过对印度社会独特的“梵化”社会流动进行分析,来探讨印度低种姓群体社会身份改善的途径。
一、种姓制度对印度人社会身份的影响
(一)种姓制度的等级特性
种姓制度的起源,在时间上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10世纪,那个时期,古印度哈巴拉文明已日趋没落,从中欧入侵的雅利安人征服了古印度的土著居民,从此揭开了印度大陆上的雅利安文明史的序幕、随后,雅利安人为了巩固其在印度土地上的统治地位,创造了“血统决定论”的“瓦尔纳等级制度”,在印度“吠陀教”(即“印度教”的前身)的“吠陀经”经典文献中可以查到,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三个等级的雏形已有所记载,到了吠陀后期(即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700年),首陀罗等级出现,就形成了四个高低等级组成的瓦尔纳制度,后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最终形成种姓繁多,等级划分精密的种姓制度,在印度教对种姓制度的解释中,种姓的高低是按照出身是否沌洁而决定的,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三个种姓出身被认为是纯洁的,被称之为“再生种姓”;首陀罗种姓被认为是不洁的种姓;而在种姓等级之外的“贱民”,被认为是“污秽的”,也是最受社会歧视的弱势群体。
种姓制度作为一种等级制度,它最主要的特征是:“一、不同的种姓拥有不同的世袭不变的职业,并且相应的保持有严格的界限;二、严格的内婚制度;三、在共餐,居住、社会交往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四、在法律上对各种姓有不平等的惩罚。”(注:邱永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9页。)由此可知,种姓制度通过对种姓制定劳动分工和职业世袭,切断了低种姓通过职业变更而获得经济改善的途径;实施严格的内婚制度,消除了低种姓通过婚姻向上流社会迁移的可能性;再加上对各种姓居住、饮食等生活方式各方面的禁忌和法律约束,最终形成一道坚固的“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在理论上把低种姓群体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可能性给剥夺了,正如印度人常说的:“一个人出生在一个种姓里,最终就会死在同一个种姓里。”(注:A.R.Gupta,Caste Hierarchy and Social Change,New Delhi,p.99)
(二)种姓身份的社会重要性
在社会学研究中,身份类型主要被分为两类:“一种被称之为自致身份(achieved status),即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作为个人努力与否的结果而获得的身份,这种身份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的;另一种是先赋身份(ascribed status),即某人所拥有的,被指定的,并且通常不能被改变的社会身份。”(注:[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96页。)大多研究印度社会的学者认同的结论是:印度社会中的个体都拥有两种身份,即仪式身份(ritualstatus)和世俗身份(secular status)。仪式身份,即宗教意义上的身份,换言之就是种姓身份,它是每个印度教徒与生俱来的,是根据出身血统的纯洁与否,由种姓制度赋予的身份,是一种典型的先赋身份;而世俗身份则属于自致身份,是通过个人后天努力所获得社会身份,与其它西方社会中的社会身份无大大区别。
那么,仪式身份和世俗身份对印度人来说,哪一个更具有社会重要意义呢?首先,在印度这个宗教国度中,绝大多数国民是印度教徒,在这个虔信印度教“达摩”和“轮回”思想的国度里,印度教的一切正是通过种姓制度得到了最好的落实,比如业报轮回学说和宗教义务观,表现在种姓制度上就是,这种制度让人相信低种姓受奴役是前世作恶的结果,只有充分完成种姓义务,来世才能变成高种姓”,(注:邱永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1页。)因此,为了忠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来世获得高种姓身份,所有人都必须遵循印度教义和按照种姓制度来规范自己的生活;其次,正因为种姓身份是一种先赋身份,且在理论上是不能靠后天努力再一次获得或更改的,从而更显示出它的权威性和珍贵性;最后,高种姓身份出身的印度人更易获得更多、更好的社会资源,自古以来,高种姓身份和高世俗身份之间一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高种姓人群更易成为社会统治阶级成员和社会精英分子,可以享有极大的社会行政权力和富裕的物质、精神生活。因此,不难看出,种姓身份是更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身份。
(三)种姓制度限制社会身份提高
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身份是指“个人在某一群体或社会中某一确定的社会位置。”(注:[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96页。)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所谓“身份”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的肯定和否定的特权,它建立在如下一种或数种因素之上:(1)生活方式;(2)正式的教育过程,(包括经验性或理性训练和相应生活方式获得);(3)因出身或因职业而获得的声望。”(注:David B.Grusky,Social Stratficatton,Westview Press。第125页。)从印度社会现实生活来看,种姓制度可以说是建立在上述基础上的一套由印度教义,印度教法典所规范认可的身份制度体系。种姓制度作为一个封闭的社会身份等级制度,其所造成的各种姓的不平等社会身份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印度人社会地位的可改善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种姓制度所制约。首先,印度教经典赋予了各种姓不同的出身声望:在印度教经典《梨俱吠陀.愿心篇》中,《普鲁沙赞歌》就展示了四种姓形成的神圣起源:
“当众神分割普鲁沙时,
他们把他分成多少份呢?
他的嘴是什么?
他的胳臂是什么?
他的大腿和脚又是什么呢?
婆罗门是他的嘴,
他的胳臂成了罗吉尼亚,
他的大腿变成吠舍,
他的脚则变成首陀罗。”(注:《梨俱吠陀》,第10卷第90节。)
正是按照巨人身体部位的功能和高贵程度不同,将各种姓的社会职能和优劣固定下来,婆罗门用嘴来传诵经典,罗吉尼亚(即刹帝利)手执武器保护本族,吠舍四处奔波从事经商,首陀罗处于社会最底层,支撑着整个社会,由此不同的种姓就拥有了不平等的出身声望;其次,种姓制度决定于各种姓群体的生活方式。正如在前面种姓制度特征中所提到的,种姓制度决定了各种姓的职业世袭和劳动分工,内婚和居住饮食,为不同种姓塑造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并剥夺了各种姓群体改变生活方式的权利;最后,种姓制度决定了各种姓的受教育程度:按照种姓制度所规定的“纯洁与污秽”的标准。只有“再生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有资格受到最基本的教育,在传统社会里,所有的学校也只接受这些所谓“再生”种姓,虽然独立后的印度在教育方面制定了教育机会平等的政策,但低种姓的教育情况仍然十分恶劣,处于现代教育的边缘地带。
由以上对种姓制度的分析可知,出身在低种姓的印度人不但在出身声望上被种姓制度不可抗拒地打上劣等的烙印,并且其生活方式改善和受教育机会也被种姓制度所垄断,在理论上造成了印度社会向上流动途径的断裂。但是,不断改善自我生存环境和提升个人社会地位是每个社会人的天性,印度这个宗教社会也不会例外,因此,印度社会中就一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社会流动模式一“梵化”。
二、梵化(Sanskritisation)
梵化,原义是指用梵文梵语表达,而不用俗语或地方语言表达,周为梵文是具有严格语法的正统标准语言,使用梵文就意味着向正统看齐,最后也就引申为遵守吠陀正统,服从婆罗门的精神指导,而且在行为举止上向婆罗门看齐的意思。在社会流动研究中,“梵化”可以表述为:“指低种姓遵循高种姓特别是婆罗门的生活习俗、宗教仪式和人生信仰,采取高种姓特别是婆罗门的生活方式的过程。”(注:邱永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22页。)下面就“梵化”的实现过程、特征和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对这一社会流动模式进行分析。
(一)“梵化”的实现过程
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从理论上杜绝了一切种姓变更的可能性,但在印度现实社会中,印度社会的种姓和亚种姓的数量极其繁多,“一个语言地区大约有200个种姓和2000多个亚种姓。有人估计,全印度共有种姓和亚种姓一万个”,(注:邱永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3页。)因此,在印度社会,实际上只有极少数最高种姓和最低种姓能得以公认,而大多数种姓群体的种姓身份则处于不确定状态,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就出现并长期存在着种姓变更的可能性,“梵化”正是利用这一契机,给予低种姓在种姓等级的阶梯上向上攀爬的机会。“一个种姓的等级地位,往往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仪式方面、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注:邱永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23页。)对各种姓来说,通常三个方面的地位高低是一致的,高种姓的人一般情况下就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占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而低种姓在三个方面都会处于劣势。但有时,三个方面的地位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低种姓可以通过某些非常规的方式诸如财富积累、宗教运动、“顺婚”(即高种姓的男子可以娶比他们低的种姓的女子为妻)等等,提升自己种姓的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与传统社会相比较,在英殖民时期和印度独立以后,低种姓对较高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获得机会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而在他们获得较好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后,他们往往就会实施“梵化”过程,来提高自己的仪式地位。
“梵化”的过程通常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1、职业的变化:种姓制度规定了职业的“洁净”与否,“凡研究和传授宗教经典、作宗教仪式,以及从事其他‘洁净’职业者,地位就高;凡从事所谓残害动、植物生命的职业者,如渔人、猎人、屠夫、榨油等,以及从事接触污秽东西的职业者,如理发、接生、洗衣、看守火化场、搬运死牛等,地位则低”,(注:邱永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9页。)因此,进行“梵化”的低种姓就必须变更自己原来所从事“不洁的职业”,改而从事“洁净的职业”。2、饮食习惯的变化:种姓制度规定,“不同的种姓有不同的食物。不可混吃,高种姓吃素,包括牛奶、奶制品、米、多种水果蔬菜,即所谓‘洁净食品’,低种姓吃荤,如肉、鱼、蛋、洋葱、辣椒等‘不洁食品’”(注:邱永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0页。)因此进行“梵化”的低种姓就必须丢弃以前吃荤的饮食习惯,像高种姓那样成为素食者。3、其它生活习俗的变化。抛弃掉一切低种姓的生活习俗,而接受一切高种姓的生活习俗,“例如低种姓是允许寡妇再嫁、杀牲祭神的,为了“梵化”成高种姓,就必须改为童婚,不许寡妇再嫁,用鲜花祭神等高种姓习俗”。(注:邱永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24页。)同时,因为种姓的名字通常代表着种姓等级的高低,居住在同一个地区内其它人都是知晓的,所以一般在“梵化”过程中,改变种姓的名称或进行居住地的迁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梵化”的过程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常常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
(二)“焚化”的社会流动特点
一个健全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主要有两种社会流动存在着:一种是水平流动,一种是垂直流动。水平流动就如同人的新陈代谢,社会中的各个功能性职位不断的有新人来代替旧人,使社会各种机能正常持续地运转:而垂直流动就如同一个筛选机制,将优秀的精英人才选出并放到社会最重要的位置去,领导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
“梵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向上流动的手段和模式,它是低种姓通过后天努力获得较高的自致性世俗身份以后,转而寻求获得先赋性身份提高的过程,总的来说,印度种姓“梵化”有四大特点:1、“它是一个团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变化形式”(注:邱永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27页。):因为种姓不是针对个人的种类划分,而是一种对社会地位不同的集团的划分,所以个人是无法脱离整个种姓而独自“梵化”自己的种姓身份的,必须在同一种姓的所有成员一起实施“梵化”的条件下,个人的种姓身份才能得以改变。2、“这个过程明显地是仿效高种姓所建立的生活方式”(注:邱永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27页。):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梵化”是有确定目标的向上流动过程,其过程就是抛弃一切低种姓的生活方式,全面接受高种姓生活方式的过程,只有全面接受了高种姓的生活方式,才能被世人所承认为高种姓。3、“它以利用传统神话、传说等作为达到新的、更高地位的踏脚石”(注:邱永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27页。):印度教在印度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种姓制度作为印度教的产物,自然也被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制度,作为虔诚的印度教徒,是绝不会公然挑战种姓制度而宣称抛弃种姓制度所赋予的种姓身份的,所以为了达到“梵化”种姓身份的合理、合法性,创造出他们原本是某高种姓后代的神话或传说,就很巧妙地绕开了这一矛盾。4、“它是以接受整个等级制度为基础的、仅谋求个别种姓地位的变化,对于处于最底层的表列种姓几乎是不可能的”(注:邱永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27页。):“梵化”本身不是对种姓制度的挑战和更改,正是遵循着种姓制度规则而进行的向上流动,并且其所实施的前提条件是低种姓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才具有了实施“梵化”的物质基础,表列种姓是属于种姓制度外的“贱民”阶层,处于印度社会的最低层,大量的社会资源都被剥夺,对他们而言,温饱问题的解决才是生活的重点,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实施“焚化”的。
(三)“梵化”的社会功能
印度种姓制度是一个全封闭的身份等级制度,它使人更看重先赋性身份的社会价值,并且在印度教所倡导的“各安天命”的生活哲学下,整个印度社会结构和社会公平机制都存在严重缺陷,造成印度整个社会的垂直性流动缺乏,进而影响印度社会发展。而梵化的存在,不仅给予低种姓以种姓身份改善的希望和机会,更重要的是由于“梵化”是以较高的世俗社会地位为基础的,因而给予社会广大低种姓致力于提高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动机和动力,在印度社会中造成一种潜在的社会人才竞争机制,有益于低种姓人群不断向社会上层流动,在改善社会结构的同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梵化”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首先,“梵化”有助于社会稳定:社会学家克伯指出,“社会流动首先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在一个没有社会流动的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往往会出现暴力;而社会流动机制能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其生活的窘境。”(注:Harold R.Kerbo,Social Strstificationa and Inequality,Class Conflict in Historical and Conparative Perspective,Mcgraw Hill Inc.1991,P369.)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最突出的影响就是造成制度性的社会不平等,广大低种姓群体不但被预先设定了人生模式,并且还被限制了后天重新选择生活的权利,在这样高度不平等的制度压迫下,印度历史上低种姓多次以宗教运动形式对以“婆罗门”:为代表的高种姓进行了斗争,“这些宗教运动通常作为梵化的工具,并且在它们从低种姓中吸收成员的同时,帮助他们提高身份。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一个宗教运动团体又成为另一个新的种姓。”(注:M.N.Srinivas,Village,Caste,Gender And Metho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88)可以说,正是“焚化”一次次地缓解了尖锐的种姓社会矛盾。其次,“梵化”有助于社会人才向上流动。印度传统社会结构在种姓制度的长期影响下,一直是个封闭的自循环结构,虽然在近代和印度独立后社会结构有所改观,但仍是一个缺少自由垂直性流动的社会,而一个理想的开放社会必须有一种精英筛选机制,从而保证社会最重要的职位由最具有能力的人来占有,“梵化”给予广大底层低种姓改变一切的希望,使他们产生在经济、政治、科学教育等各个社会领域里奋斗的强烈动机,进而为社会产生更多更好的精英人才。最后,“梵化”有助于种姓制度的延续。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之所以能拥有强大的生命力,除了其与印度教相辅相承的关系外,“梵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梵化”实际上是种姓制度内部矛盾压力释放的手段,它给予了低种姓改变生活的希望,使受压迫的低种姓放弃对种姓制度的不满,转而寻求向高种姓“梵化”的方法。
综上所述,“梵化”是印度宗教社会中存在的独特社会流动模式,它对种姓制度内部矛盾的缓解,个人社会身份的改善,乃至印度社会分层结构都有着调节性功能作用。在印度近代,特别是在独立后,随着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低种姓的改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机会也相应增多,“许多团体并未把新的经济机会给他们带来的财富投于再生产,也未投于他们急需的教育事业,而是投向了传统取向一‘梵化”’,(注:邱永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26页。)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印度社会在现代化高科技和全球化的观念冲击下,许多落后的、封闭的观念和习俗正在被抛弃,整个社会正在经历着一次漫长的社会变革,但毕竟种姓制度和“婆罗门至上”思想已经影响了印度社会达数千年,时至今日,婆罗门生活方式仍然是印度传统最高生活境界的象征,且高种姓身份仍旧是所有印度低种姓群体的精神追求,所以“梵化”这种社会流动模式仍将会在印度社会长期存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