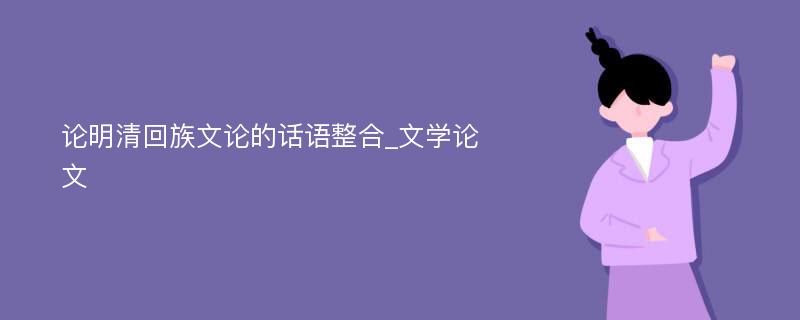
明清回族文论的话语融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文论论文,明清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5)04-0158-06 在中国民族文学发展史的进程中,话语融通是各少数民族文学、文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何进行话语融通?话语融通产生怎样的文学效应?话语融通背后又沉潜着怎样的文化蕴涵?本文结合明清时期回族文论的一系列言说为文献依据,试做一些初步的理论探索。 之所以选择明清回族文论为研究视点,乃源于两个基本的学理判断。其一,与回族古代文学的书写形式一样,回族古代文论也以采用汉族文字书写为载体。因而,回族古代文学(文论)与以汉族文化为构成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学(文论)最为亲近,亦容易延展出可比性的论题。其二,时至明清时期,回族文论的发展进入一个相对繁盛的阶段,一批文论家走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场域,如海瑞、李贽、马世俊、孙鹏、沙琛、丁炜、蒋湘南等人都有文学批评的理论言说,并且,他们对于文学功能论、文学表现论、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论等论题的探究各有独到的见解。因而,选择此时回族文论的言说内容作为话语分析的突破口便具有代表性的意义。换言之,本论题具有个案分析的用意,我们试图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互融的视域中,对回族古代文论中的“话语融通”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况且,学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还未展开,还存在相应的理论提升的空间。 一、话语融通的呈现层面 “话语融通”指的是文学发展过程之中,熔铸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话语(包括文论话语)所表现出的融合、通达的姿态和气度。甚或言之,话语融通是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中的本质力量。具体到本文所论,“话语融通”所指的是在明清时期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场域之中,回族文论话语所呈现出的融合与通达的情状。 原始察终,隐约至显。明清时期回族文论话语融通之状貌尤为突出地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积极地有建设性地投入到以汉族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古代文论的理论建构之中 有论者指出:“中国回族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汉族语言文字来表达其独特的民族心理和人生经历,因而儒家诗歌理论,必然渗透于回族诗论之中。”[1]106此论已初步感悟到回族文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有些文论观念乃吸收儒家文学观念而来。相应地,古代回族文论自觉融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建构之中,已经没有必要区分族别身份和言说身份。他们与古代诸多评论者同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文论批评者。 在这样的语境中,明清回族文论观念、范畴术语含义、思维方式特征和理论形态早已融通儒家诗学立场。诸如尊崇诗歌讽教传统、崇尚儒家兴观群怨的思想、提倡温柔敦厚的诗学理念、讲求人品与诗品的关系、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等观念,俱显明地表现于此时的文论话语之中。明代回族作家金大车在《浮湘稿诗序》中论及文学的功用时曾说:“是故以恤民隐,以敦礼教,以尊遗经,以咏皇泽,以表懿风。”[2]165册272-273即是秉承了儒家文论关注现实、宗经立义的思想。清代回族作家蒋湘南在《唐十二家文选序》中曾云:“是以六经之语有奇有偶,文不窳而道大光也。”[2]191册220亦可见其尊崇六经的思想。而清代回族文论家马时芳则在其《挑灯诗话序》中直接称颂孔子诗学思想的核心为:“我夫子蔽以一言曰思无邪。”[2]197册97又足可看出他折中于儒家文论的旨趣。尤其是此时回族文学评论者们贯常使用的“风雅之旨”“言志抒情”“文以明道”“文道合一”等术语范畴,更是颇有金相玉振、言雅中和的君子情怀。且以清代回族文论家丁灦的《名山柱史亭集序》为代表,文中指出:“尝闻尼山诗教,于兴观群怨外,独及于事父事君,盖千古之诗人,千古之敦伦人也。夫《黄华》《天保》,可以教忠;《南陔》《蓼莪》,可以教孝;《杕杜》《行苇》,可以教悌。不读《伐水》诸什,无以处交游;不读《鸡鸣》诸篇,无以处家室。凡此皆诗也,其义蕴不尽于诗也。”[2]194册24这段评论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称颂儒家诗教的伟力;二是标举《诗经》诸篇的经典价值;三是抒发诗外有诗的意蕴。而旨归却是传达儒家诗学的文学力量和社会意义,于行文之间分明延展着明经述道的思想观念。 不唯如此,明清回族文论者的思维方式亦与汉族文论者的思维方式无所区分。他们重视感兴,善于类比,突出妙悟,旁及实证。又长于理性发散,精于纵横论说,故属于东方式感悟性的思维方式。其主要特征为:感悟灵妙,诗性意识,发散自由,意境深远,颇有生命律动感。而且,回族文论家的文论表达方式自由开放,诸如在文牍、序跋、碑刻、书信、杂说等载体中,都可见文学评论的见解和主张。并有专门的诗话著作行世,代表作即为马时芳的《挑灯诗话》。 《挑灯诗话》先成八卷,后补一卷,共九卷。涉及诗评、诗史、考证、诗人趣事、诗坛风韵、典章故事等内容,也不乏露才扬己的成分。根据作者马时芳道光年间所做的序言及文末的跋文可知,此著非一时之作,乃多年累积而成。在《挑灯诗话》之中,马时芳阐发了诗学史的发展脉络、重要诗学范畴(包括儒家诗学观念)、唐风宋调的关系、明清诗人的定位等中心论题。如评论李杜自为大家,但“少陵尤胜,其识高,其思深,其竖义崇高而坚确,偶一涉笔必无细响”[2]197册368。诸多论说纵横捭阖,沁人心脾,较少腐儒气。因此,此著不仅与儒家诗学的要义相统一,且拓展更大的诗学阐释空间,将评论的视域延伸到诗学史的各个层面。尽管此著中并没有提出创新性的诗歌理论,但立足诗学批评史的发展轨迹,其诗学思想的折中性质和祧唐祢宋的价值取向依然传达出那个时代的文论声音,从而保持了一位诗论家独立审慎的诗学立场。 进一步说,置身于以汉族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古代文论的理论语境中,明清回族文论家也同样吸收了审美派的理论资源进行文学批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论批评话语和审美派批评话语可谓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两种话语形态,且两种话语形态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包容,从而呈现出互动互补的性状。明清回族文论家的文学批评中蕴含的大量的属于审美批评的话语,同样具有这种功能。如明代作家马之骏在《高苏门先生集序》中评价明代著名诗人高叔嗣的诗歌“高古玄澹之致”“神韵性情”并举,与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李梦阳“江河并行,辰跃双丽之不相掩胜”[2]170册182。此处的“高古玄澹”“神韵性情”皆为审美批评话语。又如马时芳在《挑灯诗话》之中,也擅长运用审美批评话语评论诗词,兴趣、风格、韵致、绮丽、妙悟、意境等关键词时常涌现于他的笔端。他曾说:“诗以兴趣为主,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略涉滞机,便成笨伯。一部《离骚》,直是荒诞远离,却令千秋读者往复歌思,津津不厌。”[2]197册159这些论说即是审美批评的产物。此外,在海瑞、李贽、马世俊、孙鹏、沙琛、丁炜、蒋湘南等人的批评话语中,他们也自如地运用审美批评的方式进行论说,或言诗意高远,或言意境清真,或言诗主性情,目的是为读者提供审美意蕴,向后人传达审美情趣。当然,明清回族文论者的批评声又时常将审美批评话语与儒家批评话语融合起来,从而产生“视域融合”的批评效果。如沙琛所言:“平生慕风雅,独嗜古人真。厥道属性情,千载长斯新。”“真境要自得,天地不腐陈。”[2]195册63-64此数语虽为诗句的形式,然而却是古人擅长的论诗诗,沙琛着意表达的是诗歌创作应讲求美质和创新的统一,从而使诗歌风神谐畅,意境深婉,并具有卓尔不群的艺术风格。由此看出,明清回族文论家秉持的批评标准,一方面与儒家传统批评的要求相一致,另一方面也与审美批评的视角相对应,他们同样建构着中国古代文论主流话语的言说模式。 (二)秉持独立言说的立场进行文学批评活动,且不乏理论创新的因素 明清回族文论者自觉融入以汉族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古代文论的理论建设中,又自觉进行着独立的言说方式,实际上就解决了理论话语的继承与发展的问题。当然,话语融通的并不意味着明清回族文论者忘却母族文学观念的存在和母族文学作品的影响。的确,因限于地域、时空、语言等因素的障碍,有的回族评论者已经无缘与母族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文学接触,加之他们的生活空间有限,母族文化的辐射也难以投身到他们的生活区域,于是,有的回族评论者仅仅于祖先的遗训中感悟母族文化和母族文学的力量。如福建丁氏家族(丁炜家族)和福建萨氏家族(萨玉衡家族)的族谱中,还依然传诵着母族文化的精髓。但是,一旦具有接触母族文化和母族文学的条件,回族评论者也自觉运用母语的文学思想品诗论文,阐发文学见解和文化诉求,这是非常自然的文化选择。且评论者们一方面秉持儒家文化的话语体系言说文学现象,另一方面也秉持阿拉伯文化的话语系统言说文学现象,从而在比较的视野中,领悟和融合不同民族文学思想的相通要素和共有的价值取向。其中,以清代马德新、马安礼师徒二人的文学见解最为代表。两人生活于同治、光绪年间,因翻译阿拉伯名著《天方诗经》而闻名。《天方诗经》,原名《衮衣颂》,又称《斗篷颂》,是阿拉伯著名诗人补虽里(1121-1191)的代表作。在两人的汉译序言中,值得关注的文学思想有:一是重视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二是强调诗歌的审美意义;三是认同诗歌的教化作用和劝善惩恶的意旨;四是中国诗歌与阿拉伯诗歌都有本真的情趣。如马德新所言:“天方之诗固有合于兴观群怨之旨,而可以感发后人,兴起百世者。”[1]94又如马安礼所评天方之诗歌:“约举数端,而其歌功颂德,劝善惩恶之意,固已昭然如揭矣。况天方之诗,玉轴连云,金韬丽日,盍止三百。”[1]100这些论说,也促成马安礼借助《诗经》来解释《衮衣颂》,并由此看出比较文学的通脱眼光。 当然,话语融通的理论呈现还表现在逻辑思辨的诗性发散、语言运用的空灵诉求、文学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的探寻等次要方面。所以,明清回族评论者的“话语融通”既打上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烙印,也不失自身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在融合汇通的语境中开展文学活动和文学诉求,并由此看出理论兼备与理论吸纳的开放姿态与言说气度。 二、话语融通的文论效应 从当代文学理论来看,明清回族文论话语融通的书写行为,不失为一种与古代汉族文论、与古代各民族文论对话性的表现。同时,也不失为一种创造性的理论文本呈现。在这样的状态中,话语融通会产生怎样的文论效应呢?我们借鉴“互文性”理论的方法试做探究。 一般而言,互文性的基本内涵是指“文本与其他文本,文本及其身份、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之关系和过程”[3]5。构成互文性必须具有三个要素:文本A、文本B和两者之间的互文性联系。参照这样的理解,明清回族文论话语融通既符合基本内涵的要求——多民族文论文本之间历史地逻辑地存在着关联性和转化型的关系,也符合三个要素的构成条件——明清回族文论、汉族文论和两者之间的互文性联系,因而,明清回族文论的话语融通与互文性理论之间就搭起了互参互通的桥梁。本于此,我们结合批评文本的“互文性”内容,略谈三个方面。 (一)彰显理论远见 话语融通意味着回族文论者在进行文学评论时,一方面能够历时性地审视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时间性文学问题”,另一方面能够共时性地思考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空间性文学问题”,并游刃有余地行走于文学批评的场域中。而那些秉持特立独行思想的评论者更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乃至提出非常有突破意义的观念,如李贽的“童心说”和马世俊的“体备而气下”论。李贽的“童心说”一扫复古思潮中的守旧思想,破除祧唐祢宋的窠臼,转面以“童心”及由此延伸出来的“赤诚”“真心”“赤子”等富有生命力的话语及话语组合而论文,显示出独步文坛的理论勇气和学术品格。马世俊在《丸阁集诗序》中提出一个比较新的理论观点:“诗之衰也,体愈备而气愈下。”[2]184册43他认为“古人诗体未备”,然而创作却别有清新之味,比如乐府诗,甚为典奥而幽思质响,足以相称。可是,“诗体莫备于今”,作诗却常常模拟古人的外表,“不能自命一题,创一格”,缺乏应有的内蕴。这个观点虽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意义,但从一个截面解释了明代诗歌之所以缺乏气力的文体学原因,所论并非没有道理。明清回族文论者诸如此类的言说自然是理论远见的表现。 (二)富于批判精神 话语融通还寄寓着明清回族文论家的批判精神,他们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主流价值,他们用文学批评的方式,切入人们的文学理想中,不仅引导文学的创作,更重要的是告诉人们什么样的价值是最值得坚守的。如明代马之骏批评明代后期诸多的诗歌创造沿袭后七子派的文学思想而不拔,径直陷入模拟的窠臼,缺少文学创新精神。他在《苕园集序》中云:“古今文章得失不过两端,曰是与非而已。”并结合万历之际的诗歌表现,批评奇怪的诗坛:“其蝉缓也,似温柔;其寂寥也,似高简;其萎靡也,似深婉;其肤末也,似清旷。”[2]170册261意思是文章通变之道要么是正常化的,要么是非正常化的。他认为,诗歌迈入万历年间后,虽然号为繁盛,但是多为“似是而非”之诗,根本无关诗歌表现的真精神,属于非正常化的创造态势。于是,他在这篇序言的结尾直接用富有感情性的一个词语“唾骂”来表达他的愤慨,由此见出他对明代后期诗坛模拟之风的批判之情。 另一位是清代的马世俊。在《丸阁集诗序》之中,他曾深切地批评明初的刘伯温(刘基)、宋景濂(宋濂)、高季迪(高启)之辈,整密太甚,与宋元末流的诗歌一样带有种种的滞涨之气。又批评明代七子派的诗歌“馆阁之气多于泉石,学问之气多于性情”[2]184册44,缺乏诗味。并指出袁宏道的诗歌纤缛柔靡,转而称赞徐渭的诗歌苍郁古挺,驳斥时人关于“袁徐同体”的说法。这些见解直指明代诗歌的弊端,自然是马世俊批判精神的写照。 (三)影响文学创作 理论话语的融通常常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文学创作活动,即文论话语的融通也带来文学创作的新气象。如马时芳的《南朝诗》:“绍兴无气尚偏安,明到南朝眼倦看。伴食中书能粉饰,无愁天子忘艰难。江河空洒孤臣泪,旗鼓谁登大将坛。独有胥江东去水,千秋犹带怒涛寒。”[2]197册180再如清代作家沙琛虽然没有留存单独的文学批评文本,但是在他的论诗诗之中,在他的序文之中,依然能感受到他的文学思想是浸染于古代文论的熏陶中而立意,游历于古代文学的海洋中而驰骋,他熟读《诗经》《楚辞》,推崇汉魏、三唐,偏爱左思、阮籍、陶渊明、谢朓、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欣赏苏轼、陆游、元好问等人,故文学观念守正而不僵化,文学风格神秀而不乖张,正如沙琛外曾孙王廷治在《点苍山人诗钞·后序》中评价其诗所言:“发为诗章,又能抒写性情,得古人风雅之旨。”[2]195册188 客观地看,由于个人才性、时代风潮及审美情趣等创作因素存在着差异性,很多回族文学家的创作成就不一定能够进入明清文学史一流作家的行列。但是,诸多的文学作品以“探龙得珠”为追求的目标,以“手诗竟作蛟龙吼,海神哑哑知音乎”为最大的满足[4]261,取得不菲的成就,在古代文学史上留有自己腾跃的空间。 三、话语融通的文化意蕴 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应着力把握其中的深层意蕴。如同论者所言:“我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阐释所面对的并不是历史事件,而是思想观念,是精神趣味,它们蕴涵在古代文论话语中,是可以通过阐释活动而把握到的。”[5]6而探求明清回族文论的文化意蕴无疑为解读其深层蕴涵提供了一个可延伸的视角,也是彰显“话语融通”文化张力的一个深刻论题。 论及文化意蕴是一个庞杂而多元的话题,我们选择一个界面而展开。按照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的说法:“文化是以使用符号为基础的现象体系。它包括行动(行为规范)、客体(工具,由工具制造的事物)、观念(信仰和知识)以及情感(心态和价值)等。”[6]136由于明清回族文论的话语融通之中主要涉及“观念(信仰和知识)以及情感(心态和价值)”两个方面的蕴涵,或者说这种“话语融通”与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的关系最为紧密。所以,依据这样的语境,我们越发体味到明清回族文论话语融通背后沉潜着历史条件下的种种文化意蕴:从观念层面说,如文学儒士身份的自我确认、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抉择、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文道与世道的表里关系等观念,都生发出一定的文化意味;从情感层面说,如认同儒家诗教说、认同审美感悟说、赞赏唐诗宋词的风采、感慨李杜诗歌的魅力、心悦文学经典的风骨、敞开胸怀吸纳历代文论的精髓、秉持独立的批判精神、向往个性的自由等价值判断,俱流露出与情感要素相关的文化意味。这些文化意蕴是明清回族文论显现话语权、营造话语方式、抒发文化自信的思想依托,也折射出当时社会(包括上层社会、民间组织)赋予其具有这样的言说权利。当然,观念和情感两个层面互相融合而最为显著的两种文化意蕴更值得我们探究。 (一)“话语融通”背后显示出一种文化认同性 文化认同,意味着明清文论家在秉承母族文化精神的同时,也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视为自己思想的来源之地,此境地可称得上是汇聚一体的思想结构模式。例如,在明代李贽的思想观念之中,已经将母族文化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各种文化思想整合起来,实现了自由言说的话语组合。他的哲学思想,乃至文学思想,主要是由追求解脱的性空理论与讲究真诚的童心理论所构成。具体而言,他主要吸取了心学的个体受用、老庄的自我关注与佛教的生命解脱思想,进一步分析,他所吸取的心学理论,除阳明一系的思想家之外,还有宋儒周敦颐、杨时等人的思想。[7]89故而,李贽文学思想的理论依托恰恰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这种文化取舍,淡化了族属的区分,应视为是当时文化人自觉的一种文化归属。再如,在清代回族文学世家——泰州“俞氏”家族的思想观念里①,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本身就存在沟通的途径和思想契合之处,家族中的著名诗人俞楷在叙述回族学者刘智的著作《天方性理图说》时曾说:“世之人皆以其不同于中国之文,而不知其深合于中国之学。”[2]24册64并且,俞楷将伊斯兰教的“五功”(念、礼、斋、课、朝)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五行”相提并论,认为“深者自深,浅者自浅”,真诚终能悟出两者的相合之处和其中的纹理。所以,置身这样的语境,李贽的文学思想与俞氏家族的文学思想,都自觉融入“多元一体”、相合相契的中华文化精神的苑囿之中,而共同担当文化认同感的承载者和发扬者。 这样的认同颇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从一定的层面看,明清回族文论的文化认同一方面显示出各民族文化精神原本就存在互通互融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古代中华文化自身不乏文化整合的力量,从而使回族母族的文化价值观与以汉民族等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价值观融合起来,搭建起彼此认同的桥梁,并见证了话语共融的可能。同时,明清回族文论家做出的融合努力,也强化了他们在中国文论史上的话语优势,越发彰显自身文化的开放性和适宜性,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在《原始艺术·前言》所说:“随着各个民族变化着的精神背景,许多分散的现象变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各种文化因素结合的越好,这种文化形式本身就越显得富有价值。”[8]11 (二)“话语融通”背后体现出一种文化自主性 文化自主,意味着明清回族文论家在文化认同的大背景之下,秉持自己的独立立场,发出自己的批评声音,将中华文化的文明符码延续下去,体现着每一位参与者的个性价值。也就是说,面对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他们都具有发言权、评论权和创造权。这种自主,表现在文学领域,自然容易形成包容、和谐、开放的文学姿态,故而,“话语融通”的背后可以实现言说行为的自由表达,可以实现文学创作的自由书写,进而在更高的层面发出种种关于文学价值观的讨论。如在清代回族文学家丁炜的文学评论中,既有对当时文风的指摘评点,又有对传统文学精神的理性反思。无论是指摘,还是反思,都言之凿凿,颇有气度,显示出回族文论家的文化底气和对时代风潮的把握能力。他曾说:“诗三百而后,由汉魏以迄三唐,作者代兴,美备亦略可睹矣。今谈诗家,不务宗汉魏三唐,以渐追夫三百而顾变,而之宋之元,争为诡胜,究且失其邯郸之步。”[2]187册64这段话,是丁炜针对清初宋诗风的兴起而谈论的,他批评当时的诗坛尊崇宋元诗风而陷入诡怪的境地,主张诗歌创作要学习唐人笔法,尤其是学习杜甫诗歌的精髓,以此领略汉魏诗风的韵致和追溯《诗经》的文学风骨,最终达到变化万端的地步。显然,这些文学观念是非常有见地的。丁炜的言说尽管没有脱离清初“唐宋诗学之争”的大背景,但更传达出一种对文学传统的尊重感和自豪感,也由此展现出批评主体的自信心。 《四库全书总目》曾评价清代回族作家法若真的文学风格时说:“其诗古文词,少宗李贺,晚乃归心少陵。不屑栉比字句,依倚门户。惟其意所欲为,不古不今,自成一格。”[9]1641实际上,明清时期其他的回族作家、文论家也不乏这样的独立性品格。在这样的自主状态下,回族文论与各民族文论之间构成的是对话关系,是共同参与的关系。换言之,文化的自主性表明,每一位运用汉语写作中国古代文论的人,都是文论意义产生的参与者;每一篇文论文本,都参与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构建。所以,文化的自主性也是一种文化多样性的表现。 文化的认同性和文化的自主性是紧密联系的,前者是践行条件下的心理认知,后者是认知条件下的实践活动,两者统一于互动的文化实践活动之中。于是,中国古代文化既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属性,又附着了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因子,由此彰显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内部多样性和文化多源性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回族文论话语融合的文化意蕴是古代中华文明与古代阿拉伯文明交汇的产物,也是每一个文化的承载者参与文化建构的产物。 从间际的关系看,以上关于明清回族文论特质之三个方面的探究依托一个基本的学理判断,即话语融通是回族古代文论发展的优势资源;理论远见、批判精神是话语融通的前提下回族古代文论自觉的理论建构;创作影响是话语融通与理论远见、批判精神互相支撑下的现实诉求;而文化意蕴则是话语融通背后文化家园的基石底色。几个方面既是逻辑推进关系,也是互为条件关系,共同营造回族古代文论演变发展的动力机制。当然,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演变发展的语境一样,它的理论兴衰与价值影响伴随着文学样式的发展、近代文学题材的要求、时代风潮的审美改变等变革因素的来临,而呈现出历史选择的迹象。然而,触摸中国文学批评史宏阔的发展脉络便可发现,回族古代文论不啻是中国古代文论有益的话语补充,它本身就是中国古代文论多元一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中国古代文论的主体部分一样,颇具有东方感悟性诗学的属性。这也是明清回族文论“话语融通问题”存在的大环境,其中的话语资源与价值得失必须历史地去理解。本于此,明清回族文论的理论特质同样打上“理论的历史性”与“历史的理论性”的双重烙印。同时,“话语融通问题”也是观照明清回族文论如何走入近代文论的视野、如何进行近代转型及转型困惑的一个窗口。其中的深层次问题还需要我们进行再探究。 ①关于清代泰州“俞氏”家族回族族属身份的确定,参见杨大业所著《明清回族进士考略》中的论述,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287页。在朱昌平、吴建伟主编的《中国回族文学史》中,也有专章“泰州四俞的诗词”加以论述,阳光出版社2012年版,第352-353页。标签:文学论文; 诗歌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回族论文; 文化论文; 明清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马世俊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