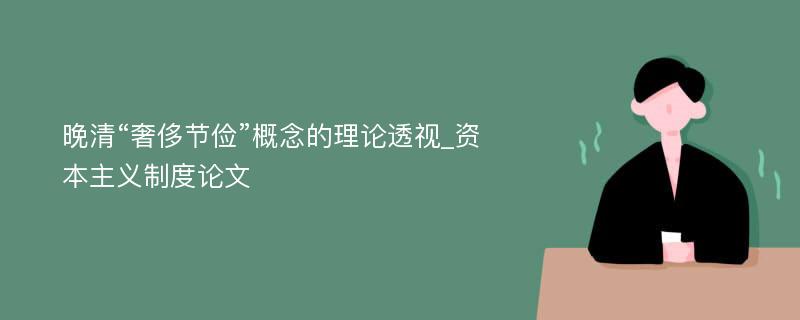
清末时期“奢俭”观的学理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文,清末论文,透视论文,时期论文,奢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10-0105-07
清末时期乃中国传统社会深刻裂变的历史阶段,与之密切相联的诸多传统观念亦发生近代嬗变,其中传统“奢俭”观颇为突出。迄今为止,学术界相关研究基本以魏源、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人的相关经济思想为核心展开。① 如此考察虽不乏一定合理性,但仍比较褊狭薄弱,尚需深化。事实上,清末社会的复杂性客观上决定了此一价值观近代演化的复杂性,仅仅囿于经济领域的理论诠释颇难把握其内在实质。本文拟以现存研究成果为基础,将其置于当时社会语境下对此作一社会文化式探讨,以窥探其真实深刻的历史文化意涵。
清末时期,中国传统社会裂变伴随甲午战争中国败北而加速。当时社会诸多危机交织在一起客观上促使传统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而作为传统文化核心之一的“黜奢崇俭”的“奢俭”观乃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条件下的思想产物,其社会影响既深且巨。在此环境中,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应对危机、重振国威,清末时论立足于社会现实与发展趋势两方面,主要从肯定论、否定论与综合论三方面解读其现实意义。其中,前二者显得截然对立。
就肯定论而言,它着眼于严峻社会现实,力图从传统“奢俭”观中抽绎出积极价值,引导社会舆论潮流,以消弭尚“奢”给社会国家带来的消极作用。有关此方面的时论又多围绕国本、官德、风俗等展开。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否定“奢靡”,崇尚“节俭”以舒缓国家财政压力可谓时论关注政治的首要议题。在探寻摆脱财政危机之道上,统治阶级自然而然地视传统“奢俭”观为救世良法,于是,“黜奢崇俭”之声不绝于耳。如皇帝颁布上谕,强调“朝廷尝胆卧薪,务崇俭德”。[1] (43)并要求“凡在官者皆有表率士民之责,务必敦崇节俭,力戒奢靡”。[2] (P107)当时的地方秉政大臣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亦主张:“国家当多难之际,创痛之余,欲求振兴,未有不以节俭为先务者。”[3] (P20544)类似之言在逐渐成长的舆论界亦不少见。如《申报》强调道:“谋国之道,以节用为本。”[4] (P655)《民国报》要求人民“尚朴俭”以扭转经济困难局面。[5] (P717)《集成报》在其所论八项“安内之策”中,“崇节俭”即为重要一项。[6] (P72)可见,“黜奢崇俭”被时论视为解决国家财政危机、培植国本的重要手段,得到主流社会的青睐与大力提倡。其主旨虽存在浓厚的保守性倾向,但不容否定,其所蕴涵的思想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同时,官吏“尚奢”之风日盛、吏治日趋腐败,客观上要求时论提倡“黜奢崇俭”以端官德。时人戴恩溥针对吏治日趋腐败现象在上奏中指出:“州县为亲民之官,其洁己奉公廉俭素著者,固不乏人,而暴戾贪横苛虐百姓者,亦所在多有。”[7] (P395)《申报》亦载文指出:今日不崇俭之病,尤以宦途为特甚。其饮食必珍馐,出必裘马,第宅必金碧,姬妾必珠玉以至于贪墨,而举凡寡廉鲜耻,忍心害理,隳纲黜纪,殃民误国之事皆缘之而起。[8] (P375)《武学》杂志甚至认为:相对于战争之祸害,污吏之贪残,名为沉清而实虐杀者,不知其几百倍。至若宴安奢靡,虚伪腐儒,生于太平而死于鸩毒者,又不知其几百倍。[5] (P213、467)因此,时论认为,对这些祸国殃民之害,倘若追其根由,“原其始,罔不由于不崇俭。然则一人不崇俭,而贻之烈。”[8] (P375)如此将官吏之“尚奢”视为祸国殃民之罪魁祸首可谓入木三分、切中时弊。
不仅如此,社会上贪图享乐、生活奢侈式恶风陋俗反过来将“黜奢崇俭”推到当时社会舆论的中心。如《申报》描述道:“民情至今日可谓浮薄极矣,风俗至今日可谓奢侈极矣。”[9] (P537)对天津一地情形,有论者指出:此十年间,天津之人民,不但不知刻苦自励,以求恢复旧日之光荣,而风俗日益奢华,人心日益浮荡,酣歌恒舞,兢胜争强,竟不知今日之天津,为何等之天津!今日之中国,为何等之中国![10] (P3)如此奢靡之风与积贫积弱之国势形成鲜明对比。时论认为,“当此凋残之际,似宜格外俭约,乃纷华靡丽之风,日新月盛,是真不可解者矣。说者谓此皆官场之应酬阔绰有以开其端也。”[11] (P15)针对如此恶风陋俗,诸多报刊如《普通学报》主张讲节用以改良风俗。[5] (P3)而时论将其根源也归之于吏德堕落可谓洞察细微、认识深刻。
与此相反的否定论则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趋势,认为传统“奢俭”观消极影响甚大,如有碍思想进步、落后于时代、阻遏经济发展等。
对传统“奢俭”观中有碍思想进步之弊端,时论多简单地斥之为“陋俗”。如梁启超认为:“崇俭”乃“上古不得已之陋俗”,导致货弃于地,人们穷蹙不可终日。痛斥那些“食不熏肉,妾不衣帛”式守财奴藉“崇俭”之名壅塞全国之财,断绝廛市之气,称此辈实为“世界之蟊贼,天下之罪人”。[12] (P37-44)谭嗣同认为:俭与陋是相辅相成的,“惟俭故陋”,愈俭则愈陋,民智不兴,物产凋窳。“故私天下者尚俭,其财偏以壅,壅故乱。”[13] (P321-325)严复分析道:“中土旧说,崇俭素,教止足,故下民饮食虽极菲薄,其心甘之,而未尝以为不足也”。“所贵乎俭者,俭将以有所养,俭将以有所生也。使不养不生,则财之蟊贼而已,乌能有富国足民之效乎?”[14] (P66、339)这里,梁、谭侧重于将“俭”与“陋”等量齐观,而谭还视“俭”为“私天下者”阻遏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严反对将崇“俭”推向极端,甚至与“生”对立起来。他们的言论带有明显近代色彩,可谓对传统“奢俭”观负面影响的深刻批判。
从社会进步而论,传统“奢俭”观具有明显等级守旧特征,已落后于时代发展。谭嗣同认为:统治者视“崇俭”为美德乃其“以奸猾桀黠之资,凭藉高位,尊齿重望,阴行豪强兼并之术,以之欺世盗名”之资,故它实为一种“贼德”、“禽道”。[13] (P321-322)而在严复看来,中国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混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衰。”认为这只能使“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15] (P2)康有为以欧洲近代社会发展为参照,认为中国“守旧闭塞无知无欲之国民”只知“崇俭”,而以享乐为浪费、为耻辱。在世界各国相互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必不能苟延性命”。在他看来,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今已入工业之世界,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中国宜审古今之时变,知非讲明国是,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2] (P226-227)以上诸言表达出他们努力揖别传统农业社会,藉尚“奢”以走上近代工业社会的积极追求。
此外,时论认为传统“奢俭”观阻遏经济发展,影响国计民生。中国传统自然经济铸就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思维定势,传统工商业遂深受其制约。对其危害,谭嗣同指出:“崇俭”之俗导致开物成务,利用前民,励材奖能,通商惠工,一切制度文为,经营区画,皆当废绝。如此“崇俭”导致人人贫穷,天下大事,遂乃不可以支。至贫极窘之中国御侮“败亡之由,咸此而已矣”。[13] (P323)梁启超也认为,“举国尚俭,则举国之地利日堙月塞,驯至穷蹙不可终日,东方诸国之瘠亡,盖以此也。”[12] (P35-46)在严复看来,“今使一国之民,举孜孜以求富,既富矣,又不愿为享用之隆,则亦敝民而已。”[14] (P288)“滞财之致贫,其害烈于侈靡。昔者之印度,今日之中国,以庶富之国而有贫乏之形者,害端在此。”[16] 如此言辞颇为尖锐,切中传统极端“奢俭”观之痼弊。
综上所述,清末肯定论与否定论对传统“奢俭”观的态度涉及政治、伦理、经济、社会风俗、思想文化诸方面。此二者虽契入角度不同,立论各异,但无不是对社会现实道德堕落、风俗败坏的严正抗议。同时,它们也蕴涵着积极合理的思想因子,有的是顺应历史潮流、追求社会进步之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发展需要,其具体合理性不言而喻。
相对于肯定论与否定论,清末综合论解读传统“奢俭”观体现出明显的理性色彩。它依据社会实际,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出发,充分利用中外思想资源,对“奢俭”观作了比较平实的理论诠释。概言之,主要有以下数端。
首先,在思想上认识到中西均有“奢俭”观。综合论一派注意到中西均重道德,[17] (R50-51)认为相对于中国之五伦,“西教之中未尝不言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诸大端,以为人生之本”。[18] (P631)具体到中西“奢俭”观,时论认知经历了一个逐步理性化的过程。起初,偏颇之论甚嚣尘上。如有论者认为,西方尚“奢”,中国尚“俭”,视中西较量为“俭”与“奢”的较量,主张以“俭”胜“奢”,[19] (P177)将道德作用泛化。继之而起之论渐趋理性,认识到中西均有“奢俭”观,只不过是“西国之人俭,中国之人奢”。其所言“中国之人奢”侧重于具体实际:如绅富之家子弟骄奢淫佚,挥金如土。至其妇女之华奢亦骇人耳目,而西人无有如是之豪侈无度者。观于闾里,细民亦复奢华成习,强调留心国是者当先示之以俭,才可寻得与西人争富强之术。[20] (P479)此言从事实而非空洞理论来评判中西奢俭,并流露出积极学习西方“俭”德的浓厚兴趣。与之相似,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大臣戴鸿慈等在奏书中如是描述西方社会:“其人民习俗,亦觉有勤俭质朴之风,与中国最为相近。”[21] (P8)革命党人熊希龄也指出:近而考察各国,兵力之强,西方推德,东方推日,然究其内容,则两国之勤俭实非各国所可比。“故以勤俭而敌骄奢,未有不操左券者矣。”[22] (P283)《教育世界》刊载文章介绍了英国学者斯迈尔斯的《勤俭论》以利人们道德修养。[6] (P130)由上可知,“奢俭”观中外所同已渐成时论共识,蕴涵着融合中西“俭”德以富国强兵之深意。
其次,“奢”与“俭”具有相对性,不宜绝对化。除传统以社会等级为衡量标准外,综合论根据社会进化状况,从古今、贫富、地域等不同角度论证“奢”与“俭”实为相对性概念,不宜绝对化。以古今论者首推康有为和章太炎。前者强调“人之愿欲无穷,而治之进化无尽”,[2] (P225)社会进化与文明发展,人们之于“奢俭”的认识必与时俱进。后者则认为:“天下无所谓侈靡也,适其时之所尚,而无匮其地力人力之所生,则是已。”强调智慧愈开,侈靡愈甚。[23] (P21-26)此与当时近化论大行其道颇相吻合。而贫富论则在《申报》和谭嗣同的言论中均有体现。如《申报》认为:“处富有之时,而民俗奢侈,犹可说也。”[11] (P15)其字里行间透露出在贫穷之时不宜追求奢侈豪华之意。谭嗣同则认为:“试量出入以定奢俭。”在他看来,“溢则倾之,歉而纳焉,是俭自有天然之度,无待崇也。”[13] (P321-324)如此以经济能力为判断“奢俭”的标准富有浓厚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色彩。至于地域论主要体现在严复思想中。他指出:“国为小费者,于彼国可为穷奢。法之巴斯獭,英之耶方斯,皆论之矣。”具体判断宜依时间、地点、环境等而定。他鼓励积极消费,反对挥霍浪费。[24] (P878、880)此一判断实际蕴涵着以进化程度与经济能力高低为尺度的韵味。综合论从古今、贫富、地域等不同角度加以论证,表现出与传统以等级定“奢俭”准则的突破,具有浓厚时代特色,体现出明显的历史进步性。
复次,理性对待传统“奢俭”观,肯定“俭”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如“俭”德有利于国家强盛。前述皇帝颁布上谕中明确指出:“但使官场能省一分浮费,即可为闾阎多养一分元气,藏富于民,诚为根本之计。”[2] (P107)刘坤一、张之洞也强调国家多难,当以节俭求振兴。而《申报》认为崇实黜华,风俗渐臻于敦厚,不求节财用,而财用自节。[25] (P65)不难看出,综合论提倡以尚俭黜奢以节其流,[26] (P1488)肯定“俭”于国家富强作用之重要性。
同时,“俭”亦有利于道德修养。《申报》明言:“处今日之时势而欲思变化人心,荡涤污俗,要莫急于崇俭去奢。大抵俭之一字,足以养廉耻,足以勤学。”[27] (P551)《东方杂志》认为道德进退与社会奢俭关系密切。俭则道德易于维持,而奢则道德易于堕落。[28] (P27-28)实业家张謇提倡:“俭为美德。”[29] (P81-82)把节俭列入家训、校训及企业规章之中,成为他对学生、家人和职员的重要要求。[30] 综合论注重“俭”之于道德修养的作用体现了时代现实要求。
不仅如此,“俭”还有利于吏治风俗。《申报》强调:为今之计,欲挽回风俗,当以崇俭为第一义。官俭则无枉法贪贿之事,民俭则无荡检踰闲之习。官俭则自无贪,农俭则农家皆有盖藏。“苟一切之人皆能崇俭而去奢,则四方盗贼酷之弊,而吏治清矣。”[27] (P551)去官吏之奢,惩官吏之惰,则有事之官吏,固可望其俭且勤,而致力于国之富强。[31] (P575)在他们看来,方今世俗奢僭罔极。“欲清其缘,务在警民之淫佚,教民以敦仆,然后教化可行,风俗可移也。”[4] (P655)
“俭”也有利于近代创业。《申报》认为:尚俭则商务自有起色。[27] (P551)天津商会认为欲挽浇风而杜后患,需“崇俭朴以固商源,讲信义以维商俗,议赏罚以励商志”。[32] (P37)张謇视崇尚“节俭”为兴办实业和教育等救亡图存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认为节俭可以立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也可降低产品成本,改变民族资本企业在“商战”中的不利地位。[30] 经元善也重“俭”斥“奢”,认识到“俭”之于商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与之相似,荣德生也指出:“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33] (P291、24)不难看出,“黜奢祟俭”在民族资本家那里已被改造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34]
最后,从积极方面认识“奢”之于近代社会的实际作用。梁启超认为,富人“尚奢”虽有损于家庭和个人,但却加速财富流通,刺激生产,利于社会与国家。他鼓励富人“出其财以兴工艺贸易”。[12] (P37-44)与之相似,谭嗣同呼吁“尚奢”。所谓“尚奢”即积极投资于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它包括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两方面。前者乃“尚奢”之重心,“奢”体现为“其财均以流”,存在于“流注灌输之间”。即大力发展农工商业等商品经济,规劝富人拓展传统的生财之道,投资建厂,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如此则“穷民赖以养,物产赖以盈,钱币赖以流通”。生活消费也是“尚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3] (P327、323-324)康有为主张用西方日新日智之业取代中国守旧日愚之业。如此举国移风,争讲工艺,日事新法,日发新议,民智大开,物质大进,庶几立国新世,有恃无恐。[2] (P227)严复也指出:“支费(消费)非不可多也,实且以多为贵,而后其国之文物声明可以日盛,民生乐而教化行也”。[14] (P289)章太炎在《喻侈靡》中指出侈靡对生产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指出:“侈靡者,百工之所自出也。”[23] (P20、26)如此“尚奢”表明时人已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生活消费对商品经济发展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此论虽不够系统深入,但已触及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实质,闪烁着他们的智慧光芒。
此外,综合论倾向于“奢俭”并重,因时而异以发展经济。此一思想可谓自上而下,一以贯之。如皇帝在谕旨中指出:“物力匮乏,理财之道,固在开源,尤贵节流。”[2] (P107)如果说皇帝之谕旨多为一般传统之论,那么,维新派的表述更具近代色彩。在谭嗣同思想里,“俭”体现的是“节流”,而“奢”突出的则为“开源”。他虽未否定“俭”之于消费的重要作用,但从总的方面看,“奢”却占有更重要地位。他说:“理财者慎毋言节流也,开源而已。源日开而日亨,流日节而日困。始之以困人,终必困乎己。”在生活消费中,他认为奢侈性对社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需要有效利用。[13] (P323-324)严复指出:过于强调节俭而不用,则务富之本旨荒矣。况无享用则物产丰盈之后,民将缦然止足,而所以励其求益之情者不其废乎?约而论之,财如粟然,其专尚支费而不知母财之用者,获而尽食者,其独重母财而甚啬支费者,罄所收以为子种者。是故理富之术,在一国之母财、支费,相酌剂为盈虚。[24] (P880-881)他认同崇俭,又提倡积极消费。《东方杂志》从世界“奢俭”之历史出发也明确指出:“生利之道,治国之经,节流实与开源并重。”[35] (P29)而一些实业家如张謇既积极扩大投资,大办新式企业,以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现出尚“奢”的一面;又注重节俭,以培养良好道德和积累更多发展资金,赋予崇“俭”以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如此“奢俭”并重,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清末综合论中的“奢俭”观涉及到丰富多彩的理论蕴涵,反映了时人关注社会国家前途与命运的爱国激情,彰显出他们认识日趋成熟与自觉适应社会发展的积极健康心态。相对于肯定论与否定论,综合论以其全面性而渐居清末时论主流价值取向。
清末时论对“黜奢崇俭”的“奢俭”观所作的颇具时代内涵的理论诠释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当时社会现实需要在人们思想上的必然反映。由于清末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时论从多角度对“奢俭”观展开讨论,从而使之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由于言说者立场不同,知识背景各异,导致思想混杂,彼此间矛盾之处在所难免。肯定论多立足于维持国脉,培育元气、整顿吏治、改良风俗、增强国力以期重振中国雄风。而否定论则着眼于社会进化、思想解放、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以迎头赶上西方近代国家。二者契入角度不同,而追求富国强兵之旨则毫无二致。而综合论亦莫不如是。以群体而论,统治阶级和部分革命志士以提倡崇“俭”论为多(但各自内在追求迥异),改良派着眼于学习西方以促进传统社会改革,走近代资本主义道路侧重于尚“奢”论,而严复及一些实业家则遵从经济发展规律,主张“奢俭”并重,表现出明显的理性态度。群体间认识的差异体现了时论的复杂性。在具体论述中,时论中的“奢俭”观实际上超出了经济领域,使之与政治、社会、吏治、社会风俗、道德情操等融为一体,难以截然分开。正因为如此,对清末时论中丰富而深刻的“奢俭”观颇难纯粹简单地从经济方面加以诠释。此一思想既是时代需要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基本特征,诸如主流群体与时代精英自觉参与、社会现实与理想未来力图兼顾、丰富情感与深沉理性交相辉映、一元价值与多元价值彼此互动等。不仅如此,清末时论中的“奢俭”观产生于社会急剧变化的社会时期,不免对其产生重大而深刻的现实影响。
(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从内涵上而言,它可谓中国传统“奢俭”观的近代发展。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财富,中国传统“奢俭”观本身具有其具体历史合理性,诸如利于节约资源、稳定经济、促进发展、约束贪欲、积累财富、弘扬美德、改良风俗、缓和矛盾等。但过度节俭也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如桎梏了人的思维、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片面宣扬“黜奢崇俭”,往往导致“黜奢”不力,而“崇俭”有余,成为统治者穷奢极欲,掩盖社会分配不公,调和阶级矛盾的舆论工具。[36] 清末时论对传统“奢俭”观有廓清之功,使之合理内核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并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对接起来(详后)。它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还泛化于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诸方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了传统文化的近代化。
(二)有助于中国近代经济伦理的形成。清末时论虽在某些群体或个人身上存在偏颇之论,但从整体而言,并没有对传统“奢俭”思想予以全盘否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具体分析。如对“俭”之于国家、社会、官德、道德修养、近代创业精神等方面的积极诠释,赋予其近代新义,展示出时代活力。而对其妨碍思想进步、阻碍经济发展等消极影响也予以客观分析,理性对待。至于对“奢”,时论强调以古今、经济、地域等而非等级来判断。此乃对那种视之为对上层等级的傲慢和冒犯的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深刻革命,表现出人们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无疑有利于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
(三)促进了吏治澄清、风俗改良、近代伦理道德重构。中国传统“奢俭”观具有明显等级意识,享受份内之财均属“俭”,对统治阶层颇具警戒意义。清末时论并未否定其对于官德建设的积极价值。综观此期言论,主张政府官员崇“俭”之论甚多,如强调其一般消费均应节俭,以为民之表率。至于那种因非法收入而尚“奢”之举更应坚决反对。前述《申报》言纷华靡丽之风日新月盛皆官场之应酬阔绰有以开其端。对此而提倡崇“俭”显然具有疗治社会痼疾的积极社会意义,因为官员尚“奢”不仅有违官德,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比较而言,论及政府官员应当尚“奢”之言几乎从未出现过。这说明:注意用崇“俭”来防范政府官吏的奢侈行为可谓时论“奢俭”观中之重心所在,是对传统“奢俭”思想积极合理内涵的创造性继承。而时论还将端正官德与改良社会风俗联系在一起,无疑有利于近代伦理道德重构。
(四)客观上有利于近代经济发展。时论积极挖掘与利用传统“奢俭”观的积极社会价值,如对“俭”的提倡,强调以“俭”去“固商源”,提高企业道德形象、视之为实业之本,降低成本提高与外货的竞争力等。如此一来,“俭”一举而成为具有明显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内涵,有利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至于“奢”,时论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出发,认为围绕生产消费而展示的所谓“奢”不仅无害,反而有利于发展近代工商业,因为它的实质是开源,实为消费之基。其实,如何对待开源与节流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时论将“尚奢”与“崇俭”有机融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思想,客观上有利于其发展。
(五)加速了中西文化融合,促进了思想解放。清末时论中的“奢俭”观可谓古今中外思想交融的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其内涵主要是传统文化近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传统文化中具有诸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合理思想内涵,而“奢俭”自不例外。时论结合社会实际将其积极思想因子加以继承与发扬光大,促其获得新生。同时,它也受到西方近代文化深刻影响,也是积极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的产物。那些对西方近代“奢俭”风俗和思想的介绍体现了此一融合的实际过程。而肯定“奢”则主要体现为促进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凸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反传统精神及重人的启蒙思想,突破了传统思想桎梏。而时论认为“俭”非中国专利品,认为西方社会无不尚“俭”,实际将中西文化贯通起来,有助于中国人思想观念及价值观近代化,深化了当时国民性改造的历史主题。
当然,清末时论中的“奢俭”观的所蕴涵的思想虽很丰富,但囿于客观实际,所论仍不免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如理论探讨局限于各自群体,论证比较分散,尚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更不用说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偏颇之论的存在使具体阐释“奢俭”并重的理论仍很薄弱;理论论说与社会实践尚非完全一致,脱节现象明显,等等。尽管如此,其积极社会价值则是显而易见的。它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近代嬗变的复杂性、艰巨性与长期性。那种纯粹从革命或从近代取代传统出发剖析此期“奢俭”观的学术思想不免失之偏颇,难以全面把握其时代内涵,还其真实的历史本来面目。清末时论中的“奢俭”观虽已成为历史,但蕴涵其中的积极价值对当代政治道德、公民道德、经济伦理建设等仍弥足珍贵,值得认真反思,加以合理地继承与弘扬。
注释:
①除诸多论文外,张鸿翼的《儒家经济伦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有所论及,但仍较薄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