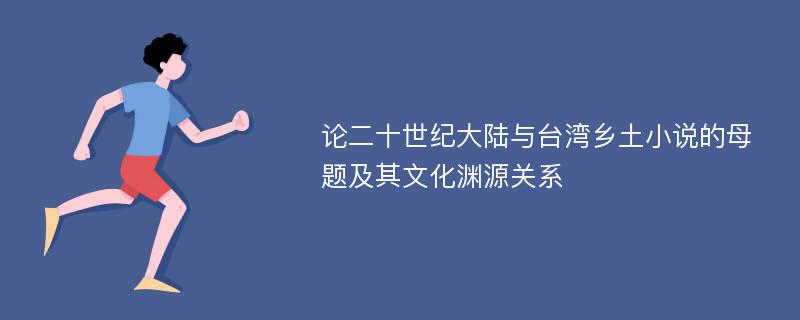
罗显勇[1]2003年在《论二十世纪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的母题及其文化渊源关系》文中提出全文由四个章节组成。第一章:共同的文化语境中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的崛起与变迁。纵观二十世纪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日趋逼近,中国稳态的农业社会结构已经开始面临着解体,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幻化出的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严重对立与猛烈冲击的社会景观和人文景观呈现在人们面前。本章以此为立足点,论述了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的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下崛起的过程及特点;“乡土小说”在不同的语境中所体现的不同的文化蕴涵;乡土小说在大陆与台湾发展的基本概貌及各阶段的异同。笔者既注意到了大陆与台湾的乡土小说因不同政治、地域和文化背景而造成的概念上的差异,发展的不同步性,又对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因两地相同的传统文化背景,以及互为影响的政治文化而产生的相类的文本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各自的发展规律,探索了其背后蕴涵的深层文化内涵。并得出结论:正是由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冲突与刺激,乡土作家的文化觉醒;以及文学自身发展、选择的结果,大陆与台湾的乡土小说在二十年代中期异乎寻常却又真实自然勃兴起来。这种勃兴的文化氛围、历史条件、乡土作家的文化自觉等,为本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经验和话题。对于“乡土小说”文化蕴涵的理解,台湾乡土作家所主张的“乡土小说”内涵十分广泛,由于本土文化明显地受到了全球一体化文化的影响和猛烈冲击,由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严重对峙,乡土小说创作的观念主体发生了质的变化。然而,虽然大陆与台湾的乡土小说的发展不是完全同步的,但是,就其文化内蕴、民族情感、审美经验、生存观念等诸种因素来看,其相同之处却是不言而喻的。第二章: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共同的文化母题。作为超越个人经验感受的文学母题,它反映的是一民族世世代代普遍性人生经验和心理经验的存积,是历史和文化在民族集体记忆中的投影,它的情思内涵将由于优秀作家个性感受的加入而呈现增殖。母题往往生存于既定的、文化层的语境中,其题义联想,体现着传统的力量,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所熟悉,遂使作品不是囿于“自我情感”,而是让母体文化的声音在人们心中共鸣。由于历史文化环境不<WP=6>同,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有着不同的文化品性,大陆乡土小说表现出浓郁的怀乡恋乡情结,台湾乡土小说则一方面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存在显示它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作为与城市文化、城市文学相比较而存在的文化、文学形式而呈现出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小说的特点。本章在论述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的文化母题时,在突出它们之间共同的文化品性之外,更注意到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因不同的文化特质而彰显出的独特的魅力。在阅读了大陆与台湾大量的乡土小说文本后,笔者发现了现代乡土作家所书写的相同的或相类似的文化母题。比如桃源母题、苦难母题、忧患母题、漂泊母题、乡愁母题;同时也发现了因不同的文化语境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作家所书写的各自独特的文化母题,如台湾乡土作家书写的孤儿母题,大陆乡土作家所书写的负心母题。本章在高度概括的基础上共论述了四个文化母题:怀乡母题、孤儿母题、悲情母题以及负心母题。怀乡母题作为最重要的文化母题之一,联系于人类生存的最悠长的历史和最重复不已的情感经验。怀乡意识可以说是一种宿命的悲哀,然而它对于人的意义又决不只是负面的。这正是那种折磨着因而也丰富着人的生存的诸种“甜蜜的痛楚”之一。怀乡母题源自传统,它又是和漂泊意识、羁旅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台湾乡土小说作家来说,怀乡母题体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突破了单纯的乡思范畴,而注意从作品的整体上呈现悲剧气氛。孤儿意识是台湾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民族意识,日据时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同时也不容易得到祖国的信任,于是产生孤独感、自卑感,这就是当时台湾知识界相当普遍存在的一种孤儿意识。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具体描述了这种孤儿意识。通过仔细阅读文本以及联系当时台湾的社会情形,我们发现,台湾知识分子的这种孤儿意识始终贯穿着浓浓的民族意识、爱国意识、家园意识。而由孤儿意识延伸出的漂泊意识更是人类普遍的一种情感意识。联系中国古典文学名着《赵氏孤儿》,我们发现台湾知识分子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下,具有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在忧患意识中产生了孤儿意识。台湾乡土小说作家在书写孤儿母题的时候,是一种无家可归的放逐者的凄凉心态与尴尬处境,然而这种凄凉心态与尴尬处境,不但没有使台湾知识分子消极沉沦、放浪形骸、自甘堕落,而是促使他们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并逐渐由书写哀怨悲愤的孤儿母题发展成书写富有阳刚之美的悲情母题。悲情母题是“诗可以怨”的历史延伸。悲情母题在大陆与台湾的乡土小说中不断繁衍。乡土作家们在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深刻解剖与批判的同时,字里行间隐藏着浓浓的悲愤之情;乡土作家们在表达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怒和反抗情绪的时候,那种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悲痛之情,无不诉诸于笔端。同时,作家的悲情意识又是和作家们始终保持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是息息相?
史硕婷[2]2018年在《“别处”的乡愁——从徐则臣和童伟格看新世纪两岸乡土写作的新发展》文中提出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乡土的写作就成为了两岸知识分子共同的选择,而乡愁也成为了他们无法割舍的文化母题。从时间上看两岸乡土小说的发展基本保持平行,但这种平行关系却在70年代前后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产生了一个十年的"时差"。直到80年代中期,大陆与台湾出现了类似的文化格局,这才促使乡土小说的写作方向在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后转向了同样的价值基点,对于乡愁的抒写也开始呈现出共同的文化内涵。这其中以两岸70后作家对乡土的抒写最为典型。大陆的徐则臣和台湾的童伟格是70后中的代表作家,通过对这两人文本的具体分析,试图来揭示两岸70后作家在抒写乡土时的精神共鸣,从而更好地把握新世纪两岸乡土小说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 论二十世纪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的母题及其文化渊源关系[D]. 罗显勇. 复旦大学. 2003
[2]. “别处”的乡愁——从徐则臣和童伟格看新世纪两岸乡土写作的新发展[J]. 史硕婷.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