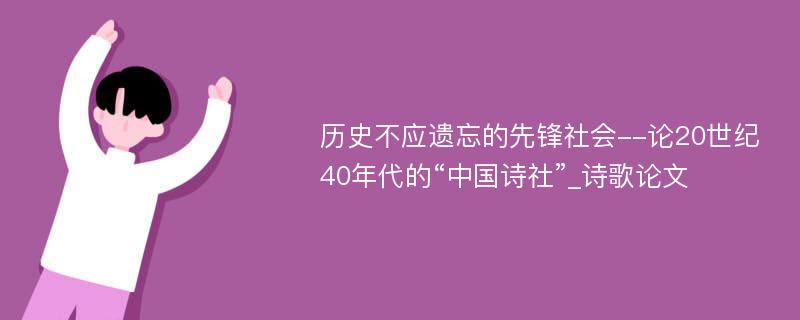
不该被历史遗忘的先锋群落——1940年代“中国诗艺社”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艺论文,先锋论文,群落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6-0032-06 论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通行文学史中几成定见的观点是:抗战的隆隆炮声一响,便“炸死了抒情”,宣告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从此步入消歇;直到经冯至导引的“九叶诗派”在1940年代中期横空出世,它才重获自己的声音。其实,这是一种必须纠正的错误认知。 诚然,战争的残酷容不得柔婉的娱性诗生长,而迫切地呼唤杜鹃啼血与鼓手迭出。于是,由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从崇尚竖琴之音,到标举匕首投枪之力,成为众多饱具良知的诗人的不二选择。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现代主义走向衰微以至沉落乃是必然。沉落并不意味着彻底消失,它“并没有中断,它的影响依然存在”[1](p.373)。其具体表现为三股力量:其一,卞之琳、何其芳等现代派诗人,“皈依时代”后在解放区写下的反映抗战、爱国热忱之作,仍未割断和现代主义的思想与精神联系;其二,沦陷区在战前已成名的南星、路易士、朱英诞,以及战后崛起的黄雨、闫青、顾视、刘荣思、成弦、金音、沈宝基、黄烈等为代表的诗歌群体,基本上继承、延续了战前的“现代派”诗风[2];其三,在国统区出现的既能接通古典传统,又具有向现实开放品格,艺术水准较高却鲜有人从整体上论及的准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中国诗艺社”。 一、向“蔽塞的小天地”外放眼 自1938年春天开始,长沙的诗歌空气日渐浓郁,先是常任侠、孙望与力扬主持的《抗战日报》副刊《诗歌战线》面世,随后寄居当地的常任侠、孙望、吕亮耕、林咏泉、葛白晚与陆续途经长沙的程千帆、绛燕(沈祖棻)、汪铭竹、吴奔星、李白凤、徐愈等诗人,不断召开诗歌座谈会和朗诵会。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孙望、吕亮耕等人,还组织成立了“中国诗艺社”,于1938年8月10日出版《中国诗艺》月刊,撰稿人即以上述诗歌活动的参与者为主体。可惜,由于战火纷扰,刊物只出了一期就被迫中断。好在没过多久,徐仲年又领衔主编了“中国诗艺社”丛书①,并且事隔两年多后的1941年,大部分诗社成员纷纷转移、积聚到重庆,经汪铭竹、孙望、吕亮耕的多方筹划和常任侠、林咏泉、徐仲年、徐迟的热心赞助,刊物又于6月在渝复刊,至同年10月分别在重庆、贵阳各出两期。虽然诗社的刊物最终没有摆脱再次停刊的命运,但是,“中国诗艺社”仍在抗战文学史上留下了绚烂的一笔,它在无意中修补、弥合了国统区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断裂,架起了一道从“现代诗派”通往“九叶诗派”的先锋桥梁。 明眼人极容易捕捉到一个信息:“中国诗艺社”并非突然拔地而起,乃是从《诗帆》与《小雅》②自然衍化过来的一个诗歌群落。事实上,在活跃于《中国诗艺》杂志和“中国诗艺社”丛书的抒情分子中,有施蛰存、冯至、李广田、柳无忌等“老诗人”亮相,也有上官柳、严小章、郭风、郑广旃、邹荻帆、杜运燮、刘北汜等“新诗人”闪回,但频繁出镜的中坚力量,却还是汪铭竹、程千帆、常任侠、绛燕、李白凤、林咏泉、孙望、吴奔星、徐迟、吕亮耕、徐愈等构成的《诗帆》《小雅》的核心层。只是有别于“久居书斋,与当时的现实距离较远,对整个民族的深重灾难缺乏痛切的体验”[3]的《诗帆》及《小雅》倾向,“中国诗艺社”成员蛰伏于记忆深处的“好诗”经验,使他们一方面对抗战诗坛情感直露、思想薄弱、停浮于标语口号的非诗盛行的流弊强烈不满,一方面更积极反思前辈“现代诗派”和自身以往脱离现实的过度个人化写作的过失,而且在刊物创刊号的《征稿小笺》中断然表明,那种“老是在蔽塞的小天地中回旋”的作品,乍看起来“虽冠冕堂皇而实际上却空无一物”,因此,明确地将办刊宗旨和原则定位为“内容与艺术并重”,“只刊反映时代的好作品”,复刊号的“社语”再次强调,“凡是反映(讴歌)时代的好作品,我们绝对破除门户之见”,一概欢迎。在这种企望重新调整诗与时代、现实关系的观念统摄下,“中国诗艺社”的诗歌尽管仍然沿袭着“走心”的路线,把内在小宇宙喜怒哀乐、风雨潮汐的咀嚼作为诗思资源的发祥地,如绛燕的《水的怀念》:“你的梦应当是一只小船,/扯满了风帆驶入我的梦里”,“让浅紫的夜色掩上桅杆/你在温柔的河流里放棹吧/或者停泊在无风的小巷/静静地做一次平安的晚祷”,诗复现了一段缠绵的青春心理戏剧,是男女至上爱情的曲折书写,夜阑之际,诗人从满地月色联想到澄澈之水,心中顿起怀人念远之意,走笔温婉沉静而含蓄美丽,蕴含着慰安、净化生命的神奇力量。再如,葛白晚的《囚人》:“窗外有一片白云,/我被雨囚在室中,/而心已乘白云去了,/飞向万里以外之家乡。//家乡也在蒙蒙的雨里,/心乃似铅魂已坠落了,/白云已任自飘去,/于是我永远作个囚人。”诗中的思乡意蕴也乃创作主体瞬间的情绪滑动,流露出诗人对故土的爱之深切与真挚,容易唤起羁旅异地的浪子的共同惆怅。这些小儿女的微妙心理、人类永恒的情愫等纯粹内涵,在意象化艺术手段辅佐下的揭示,皆可视为“现代”、“诗帆”、“小雅”诗风的隐现和延伸。 但是,“中国诗艺社”的一个有目共睹的价值取向更值得人们注意,那就是他们在观照生命情绪的律动体验的同时,均不同程度地开始向“蔽塞的小天地”外放眼,关注、表现时代的现实语境,拉近诗和生活、政治的距离,有的诗人甚至将从亲身体验的生活、斗争里攫取的诗情真实作为艺术的生命。“就其内容而言,则比当年的《诗帆》更接近了现实,更受到读者的欢迎”[4]。可贵的是,他们的介入始终坚守着艺术的独立性和诗性方式的前提,很少去直接描写现实,而是审美地把握对象,以内视性的“我”之角度去折射外部世界,写现实在自己心灵中留下的投影或回声,即立足现实的具体形态又不为其束缚,而获得一种超越性的提升。这种开放的现代主义诗歌姿态,使“中国诗艺社”笔下的现实比纯粹现实主义诗歌中的现实更灵动与内在,也比现代派诗歌的现实更广阔和繁复。同是那位女诗人绛燕,一边吟诵温热的爱情,一边却在逐渐地扩大诗境。她在《卢沟桥》中写道:“三年不是短短的日子,/让岁月负起沉重的记忆,/卢沟桥还有如霜的月色吗,/怕也像泪水一样凝成冰了”,“但桥堍月光下长眠的战士,/曾在这桥上发出第一声怒吼”,“月色曾描绘下这悲壮的图画,/流水也永远记住这伤心的故事;/更让我们趁着每年初夏的南风,/招唤桥下百万不死的英魂”。由月色、流水、石阑等组构的卢沟桥,一直是大气与美之所在,在此却因泪水、伤心、长眠等意象或语汇的因子融入,幻化成仇恨、抗争和血的见证,对英魂悲凉壮举及其背后同仇敌忾精神的标举不宣自明。如果说绛燕的《卢沟桥》还是在传达着战争期诗人的特有感受,那么,孙望的有关“江南战后”组诗就更接“地气”,战后乡村破败、荒凉景象的描绘,仿佛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满贮着控诉的意愿和呼声,如“野寺没有钟声,/焚香炉的僧侣已经十月不归,/山花松子,也随流泉杳然了,/倾圮之禅房乃一夜牵满蛛丝。//如今朝山节又近,/而朝山人却已绝迹了,/我因此想见一片青苔,/深闭着寂寂的院子”(《野寺》)。禅房倾圮,院子深闭,青苔蛛网遍布,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掠抢连乡野寺庙都不放过,其残暴程度和损害幅度可见一斑了,野寺而无钟声、朝山节该有的热闹喧腾与朝山人的杳然绝迹的悖论呈现,隐含着强烈的愤慨与同情。至于吕亮耕的《望金陵》、白鹤的《志愿军出征》则完全在抗战时期的现实风景线上采撷诗意,已经进入民族劫难和抗争的政治中心。前者有“哀思是千里芊芊的青草,/从湘江畔绿到了凤凰台”的新愁,更有“而我伫视着,哪一天——壮士血去染透栖霞的红叶,/火树千嶂里,龙盘虎踞的雄城上/重飘起红旗一面”的吁求和渴望,已无哀怨情调的踪影;后者写志愿军“负满头明月,/夜继日顺流波而下,/像一支箭。/二百一十只不倦的眼,/一百单五个头脸,/红的佩徽在人心里头发亮,/你可不必知道去的方向”,那份机警专注,那份敏锐迅疾,那份燃烧的斗志,昭示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希望,字里行间氤氲着向上、必胜的情绪气息。可见,“中国诗艺社”没有沉湎于私人性体验而向身外世界放眼的选择,不但沟通了诗人的内心波澜和广阔的历史图景,使始终悬而未决的诗与现实关系被协调得愈加紧密、深入,克服了诗思狭窄枯涩的窘境;而且诸多从个人与心灵出发的诗歌汇聚在一处,客观上起到构筑风雨与愁云交错的民族心灵历史的作用,使个人化的情思鸣唱竟获得非个人化的效能。 正如吴晓东先生所言,“哲理化的倾向构成了抗战时期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征”[5](pp.318-319),理趣化的特质在汪铭竹的《致苏格拉底》、李长之的《人生几何》、常任侠的《列车》、丹丁的《拉纤夫》等大量“中国诗艺社”的诗作中也相当显豁。如“弃置道侧,闲静地自观,/吐出之灰白吁叹,随风倾斜。//反正当年生命,/曾辛辣地燃过她的红唇。//可瞑目无声息而熟睡了,/于此暮秋天之霜夜。//新的默契突来心头,/一如渊明当年悠然见南山”(汪铭竹《烟尾》)。说的是烟尾,实则在隐喻人生,一个人不论最终的结局如何,是被人弃置还是珍藏,是辉煌还是永久寂灭,只要曾经拥有灿烂、幸福的时刻,与人爱恋抑或事业成功,就是生命价值的一种实现,而比之更重要的人与万物的交融,那是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诗在凡俗意象观照中旋起的积极生命哲学启人心智。再如:“明窗净几/脑海里另植珊瑚树/移我储温玉的手心/笔底下/掀拨大海的尾巴/鳞甲辉耀日月/缀一颗眼珠于一声叹息/添几朵彩云/借一份蓝天的颜色吗/梦与眼波与轻喟的惜别//水是够了/忘却就忘却罢/我卑微的圈子内生或死/都为装饰别人的喜悦”(林蒲《鱼儿草》)。很多人或物看上去光鲜美丽,但有时骨子里早已失却自我,成为任人摆布操纵的玩偶,只配充当他人生命甚至情感变化的装饰。诗由此所触及的生命的悲凉,无形之中暗合了很多人的深层经验,揭示了生命的实质。好在诗人们对事物的凝思和顿悟没有“单凭哲学和智力来认识”,而是依靠感性化的诗歌方式完成的。为什么“中国诗艺社”的创作具有如此充盈的理趣,这说起来一点也不奇怪。这既是由于国统区放逐抒情的时代黑暗背景,必然淡化诗人们青春期的浪漫和感伤,又是因为抒情主体具体生活的平静淡泊、清苦寂寥,时间久了会养就他们注意对个体生命凝视、沉思的品性,加之后期象征主义那种象征性思维、意志化文化特征的影响,也垫高了他们抒情的品位,几个原因聚合使他们的诗歌自然多了理趣和思考的力度,常常充满一种形而上的内涵。而这种理趣化特质,实际上又增加、拓展了新诗本体观念的内涵,质疑了诗歌仅仅是生活、仅仅是情感或仅仅是感觉的传统观念的合理性,让人感到诗歌有时也是一种主客契合的情感哲学,并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继起者“九叶诗派”关于诗是经验的提纯或升华观念的萌生进程。这就难怪在《中国诗艺》上发表过作品的杜运燮,后来直接转向“九叶诗派”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创造了。 二、出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抗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诗都没有走出困惑,它在主流的大众化驱使下,进入了一个探索误区。很多人以为,当时配合政治的鼓动宣传才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最高旨趣,诗歌的功利观念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程度,而审美价值被降为附属、次要之维,于是诸多非诗因素乘虚而入,“最普遍的现象则是情感的不够深沉,思想力的薄弱”[6](p.172),也就是说,所谓的抗战诗歌并未传达出抗战丰富而复杂的本质。在广阔而严酷的时代拷问面前,如果沿袭现代诗派,以及《诗帆》《小雅》群落的诗风去抒情表意,就更难以奏效。因为如前者在走进人生的同时却走出了艺术一样,他们在走进艺术的同时却走出了人生。正是在诗坛深陷迷茫之际,“中国诗艺社”应运而生,并开始了综合人生与艺术、平衡现实与诗歌的艺术之旅。诗社成员难以苟同抗战诗歌重功利、轻艺术的内在矛盾,认为唯有美的灵魂与美的形式统一,诗才会获得真正的生命,所以,倡导“内容与艺术并重”,并且在艺术反思的同时,由于他们曾经在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派诗中多有浸淫,受过先锋艺术的系统训练,起点较高,所以,在创作中能够以上达的现代技巧抒放现实的心理感受,为现代主义艺术赢得在新历史条件下生长的可能和空间,也为新诗的再度发展提供了诸种艺术启迪。 “中国诗艺社”诗歌古典风和书卷气浓郁,与延伸感时伤世的传统忧患同步,启用了意象化的思维方式,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善以积淀着深厚民族审美意识的意象表现感情和生活体验,暗合着古典意境范畴,朦胧洗练。调和异域营养与古典传统的关系,是新诗诞生以来就面临的一个难题,缘于新诗和传统诗歌乃对立的“敌人”的认识,许多诗人常下意识地排斥古典,更多时候偏于向西方取经。直到1930年代的现代诗派才开始自觉反观传统,寻求传统和现代的融汇途径,而“中国诗艺社”中孙望、程千帆、绛燕、汪铭竹、常任侠、吕亮耕等许多人都有学院背景,古典文学修养超群,曾经“鼓吹风雅,追踪唐宋”[7](p.606),落笔时自然不乏典雅的氛围。如吕亮耕的诗从不赤裸抒情,而选择了意象派的技巧,故是感情的而非滥情的,《索居》念远情怀的传递就是靠情思对应物“远远的秋砧”完成的。“当寒霜堆上土蟀的破琴/老松也噤无一言/而朔风偏为人送来感慨/你听:远远的秋砧//仿佛记起那一个人的叮咛/一句句从砧声里透/梦回后:远塞一声鸡——啼湿了梦中人手绣的枕头”。寂寞又单调的捣衣砧声在萧索的秋日回响,令孤寂之人无法不起愁思,惨淡、苍茫的意趣借秋砧意象寄托,隐显适度,可解又朦胧,含蓄却不晦涩,“一个人”究竟是代指情侣还是代指母亲,诗人并不直说,随你想象,韵味陡增,理想地统一了古典意象与现代情绪。汪铭竹的《苦春雨》情感、语象和韵味都是典型的“中国制造”,“菜花又黄了;我所履的/却非故乡之熟径了……我想念一个响晴的天;/蓝天下,看我们铁鸟去长征”。走在异乡的路上,想起家乡稔熟的小路,尤其是那一片一片的金黄的菜花,怀念的惆怅和回忆的温暖兼有,这种典型的家国情怀含蓄温婉,清丽浏亮而又不无感伤的情境,浓淡相宜,极易唤起读者心中蛰伏的审美积淀和情绪记忆。“中国诗艺社”的传统意象和现代意象不但不抵牾,而且常常相得益彰,如孙望的《舞乐》写道:“华尔兹慢展于掌上,/足的回旋,击出清越之节拍……眯起海伦迷人的眸子、温柔的发上,/翩然飞来只蝶绛色之轻翅。/彻旦疲欢的舞伴呀!明午/会烂酣于流线式之梦境里。”时髦的移植意象华尔兹、海伦和温柔的发、轻翅、梦境等中式意象熨帖地交织在一个共享空间里,外化出都市的腐化与堕落,仍朦胧婉约又透明可鉴,给人一种古典韵味十足的和谐亲切感。至于绛燕的情诗,则“既有传统的矜持与含蓄,又富有现代的新感觉和新气息”[8](p.46),打通了传统和现代间的甬道。“中国诗艺社”的古典意象传达,因有西方象征诗的制衡、牵拉,没蹈入泥古的深潭,反而相对自然活脱,获得了现代的品质与创造的风采。 随着结构意识的觉醒,大剂量地运用象征和隐喻,以在文本有限的空间内收获最丰富的诗意包孕,也是“中国诗艺社”诗歌的醒目特征。古诗魅力之一在于象征之道,以此言彼,用具体代抽象,其中颇多原型象征意象,西方现代派诗歌也擅长象征思维,求暗示和间接的表现。对中与西、传统与现代融合、参悟的结果,敦促“中国诗艺社”的诗常在写实和象征之间飞腾,底层写实视象上浮动着形而上的象征光影。如常任侠收在诗集《收获期》中的抒情长诗《列车》,通篇写车厢里的人们——一等车里的贵人,二等车里的大腹贾,三等车里的小市民、学生、浪子,四等车里的工人、农民,在列车向前奔驰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情态:既有贵人与大腹贾生活的苍白、贪欲与空虚,也有下等人的疲惫和希望。“一等二等只有少数人的舒适,/三等你再动摇也得向着同一方向走,/四等只有这样一条长长的路,/走尽了黑暗总有光明的日子”,但无论贫贱富贵、男女长幼,都只能随“机关车的力”前行,“谁都不能转过一个方向,/只有这一条铁的轨道/不停止地奔驰奔驰”。仔细发掘即会发现,它是在表现现代机械文明对人类命运的操控,尽管在前行过程中每种人的承受有所不同,但“走尽了黑暗总有光明的日子”乃是历史和人类的未来的现实,在从容客观的走笔里,对都市机械文明的礼赞已溢于言表。吕亮耕的《眼》也以象征思维营构全诗,多言外之旨:“比目鱼,比目鱼,——神话中曾传说过的名字。/我不敢轻道临渊的羡语,/袖手看盟鸥自来去。//哪是洋洋的鱼乐园?——我亦志在乎水。/愿思维是一笠帽,一垂纶,/我好肩一肩细雨不须归”。诗发于此处之兴归于彼处,从传统意象比目鱼之“目”写开,转看鸥鸟自由来去,婉转地寄寓着对自由境界的神往,结尾处由旧体诗词衍化而来的佳句,同“鱼乐园”关系的建立,愈见出渴慕自由情意之深切。吴奔星的《汗之颂歌》中的“汗”意象:“它是成串的珍珠,/一颗更换一粒谷子,/它是连纲的炮弹,/一颗要拼掉一个敌人”,显然人身体上的实在之“汗”因农业背景和战争语境的介入,已成象征之“汗”,因之结构的文本空间也就有了更多的象征内涵。而绛燕在《诗帆》时期多以“燕子”、“紫色”、“萝蔓”自指,以“小白帆”喻恋人程千帆,并由其引出航海、水等意象象征离别和相思,则是公开的秘密。她进入抗战后象征的诗思维仍在,如“燕子还飞到屋檐下筑巢吗,/但主人流亡到何处去了呢?/三月的江南是可怀念的,/梦中已迷失旧日的家园;/春之羽又一度掠过游子的心,/但春风知道她眉宇的重量”(《忆江南》)。燕子与未直接出现的“我”已不分主客,泾渭难辨,象征性意象燕子的启用,使诗人对家乡故园土的怀念、担忧和复杂的爱有了可以触摸的重量和形状。“中国诗艺社”的象征、隐喻思维术,为诗之山峦罩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亦真亦幻,虚实相生,余味缭绕。 在向融汇传统和现代、平衡诗与时代关系的精神共同趋附的过程中,“中国诗艺社”的成员之间没有走完全相互求同的道路,而是每人都保留自己个性追求的“太阳”,姚黄魏紫,各臻其态,达到主体风格与多元个性的统一。成员个体间性别、地域、年龄、性格、文化等因素的不同,决定他们不由自主地将差异性凸显出来,或者说使诗歌创作的个人化本质落到实处。如同样是寻找理趣,大家走的路线却千差万别。程千帆善于冷眼观照,在事物悖谬性的发现中展开睿智的思维。他在《一个“皇军”的墓铭》中写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帝国的臣民?可是/你的手册使来者翻开了/日本现代史……或许有一个怜悯的会晤,/你和你卧轨的妻”,以第二人称谴责日军的侵略,从凄婉的人道观照角度表达反战主题,已属别具一格,而将肃穆、庄重的墓志铭和侵略的“皇军”扣合,顿然露出了复杂的况味,戏谑、揶揄的运笔更平添了滑稽之感。绛燕尽管比一般的女性诗人大气,抗战后诗中又多一份理性思考的苍凉,但仍以精致幽婉做底色,像“于是我有五百年的寂寞/对浩荡的大漠风而高歌/将一双泪珠寄与流水”(《寂寞》),那种深入骨髓的寂寞人生滋味品味,堪称“不见前人”也少“后来者”,但“流水”意象的引入则浸染了一丝温情。汪铭竹的理性常潜伏在现代、前卫艺术技巧的外衣之下,跳跃、隐约与悖论式的机智连接,《控诉》阐释了血债总难泯灭,它会滋养仇恨和坚强的道理,“然而埋在这死城里之尸身们/是不会不萌起芽来的//指着这作证吧,长江里一个浪花,/悄语着一个尸身:朋友,我们明天见”,尸身萌芽,与尸身相约,这怪诞反常的思维既给人陌生的美感刺激,更强化了反抗和仇恨的力度。而到了李白凤那里则又是一番模样,“被钉在虚无的十字架上/命中注定要你终生寂寞……没有朋友的环境里/你高歌宇宙生命的久长吧/在没有了解的人群里/写诗乃终生的苦行”(《诗人》),虽然也有意象的帮衬,但它对诗人命运和遭遇的凝眸基本是在直抒胸臆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透明质朴,易于把握,诗和诗人一样老实。诗人们个性的缤纷绽放,是自由心性的张扬与象征,而诗人之间多色调、多风格的对立互补,则使“中国诗艺社”的风格肌体更增添了绚烂的活力。 三、未完成的探索及其启示 由于现实的战乱环境牵拉和存在持续时间过短的限制,“中国诗艺社”在它生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形成什么显豁的潮流,甚至尚未脱尽稚嫩之气的艺术形态,还未完全将自己从《诗帆》诗群那里剥离开来。比如,它努力想沟通个体内心和大众的心灵,也因之留下了不少珍贵的民族情绪记忆,但是,由于作为抒情主体的诗人都是相对弱质的知识分子,对进行着的社会图景这种陌生的表现领域不够熟悉,难以很快适应,所以在赋予其形式能力方面经常捉襟见肘,特别是仅仅具有一定的思考力而匮乏坚实的哲学意识支撑,决定诗人们自然无法从微小事物和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掘诗意之美,使情感与表达泛化、形和质硬性焊接的痕迹不时显露,也就失去了走向大诗人的可能。像常任侠的长诗《麦秋》,对土地“母亲”的热爱之情真挚而热烈,有着感动读者的机制,只是这种情感及其传达上都存在明显的同质化倾向,很多地方都没有走出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的荫蔽,因为过于拘泥而少绵长旷远的韵味。再像汪铭竹有时还停浮于本能欲望的渲染和“官能的爱”,他不厌其烦地礼赞贵妇人之“乳”,像《三月风》写“三月的风,溜入/少妇之胸际/双丘更毓秀了”,《乳》写“春风昨晚在你胸前作窠/一双小斑鸠/乃得比邻而居了”,都无太多的深意,也看不出表情达意的需要,有的还不无为写性而写性的嫌疑。同时,还有像《往者》(孙望)、《猫之恋季》(汪铭竹)等许多作品因为作者长期在旧体诗词中浸淫,知识分子腔和书卷气过于浓重,内容相对比较私密,固然有传统色彩的辉光闪烁,但也让一些读者体会到一种深深的隔膜。 不论“中国诗艺社”有多少缺憾,我们都必须承认,它的存在本身即昭示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写实与呐喊风气盛行的抗战最初几年,服务于政治成为所有具有正义感的诗人的不二选择,战前还十分活跃并且很有市场的先锋和现代潮流悄然分化,部分作者投入时代的合唱,有些人则关闭了歌喉,“提倡通俗晓畅的大众化语言,注重节奏和朗诵的自由体形式,构成了沦陷区和大后方共通的诗歌艺术标准”[2],诗人们俯就与走低的做法,使中国新诗的艺术水准事实上呈现出一种整体下滑的状态。值此现代主义严重受损受压的时节,“中国诗艺社”没有在原有的现代派诗歌的老路上前行,而是以一反思立场和开放的气度,努力融汇中西,综合艺术和人生、形式和内容,向现实主义的广阔空间放眼,不啻弥补、修复了现代派诗歌存在的断裂,打破了抗战到194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沉落的迷信,让人们感到在现实主义诗歌君临天下的一片雄浑激越的战歌之外,当时的诗坛还有这样一种鲜活、深沉的诗歌景观存在,对主宰诗歌命运的大众化的褊狭、平庸之风有一定的抗衡和矫正作用,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达成互惠共赢的诗坛生态平衡格局,在保证自己活力的同时,丰富了现实主义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或许,与思想意蕴上的探寻相比,“中国诗艺社”的诗学价值和启示意义更高一筹,它那种兼顾意味和形式二维因素的浑然的诗歌观念,那种带有理趣化的诗歌形态,那种调整现代主义、力图建立中国式现代主义诗歌的探险,尤其是敢于在艺术上取法海外、稳妥而超前地“提倡中国新诗在世界诗坛的地位”,“给标语口号化的浅薄的恶习以纠正”[9],它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表达以及对人民、自我的体验思索结合,不仅常常能够沟通个人体验和民族意识与情感,超越了1920年代、1930年代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纯诗追求;而且与大量的粗豪也粗糙的抗战诗歌比较,又表现出感受方式和传达技巧上的优越性,因为诗社多数成员具有古典文学的深厚功底,又注重民族诗歌精神的体现,所以,诗歌的情感、思维和语汇都有浓郁的中国化色彩,少欧化的弊端,加强了处理日常生活和审美对象的能力,促进了人们对新诗本体内涵丰富而绵长的思考。“中国诗艺社”的探索对未来的诗歌方向构成了一种引导和启迪,它虽然没有在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上走多远,但至少提供了一个路向、一种可能,而这些质素的输送对新诗来说,比一般性的“锦上添花”更有价值。 从1938年8月创刊,到1941年10月停刊,《中国诗艺》杂志只断断续续地出版过五期,存在了三年零两个月,即便后延至诗社丛书的最后一部,即程铮的《风铃集》1943年8月出版,“中国诗艺社”的历史也仅仅刚满五年。除了刊物的发刊词,它甚至没有自己的纲领、组织和宣言,只是相近的艺术主张与美学追求,将诸多诗人聚拢为一个相对自觉的诗歌群落。如果说“中国诗艺社”在新诗史上具有怎样特别重要的位置,显然是不现实的,同样,说它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恐怕也是违背历史主义批评原则的估衡误差。对它准确的态度就是打开存在的遮蔽,还其本真的历史面目。在文学社团和文学期刊研究渐成显学的当下,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的重要一环——“中国诗艺社”与《中国诗艺》杂志,也理应进入更多人的观照视野。 注释: ①由徐仲年主编,在重庆的独立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包括李白凤的《南行小草》(1939年11月)、常任侠的《收获期》(1939年12月)、绛燕的《微波辞》(1940年2月)、汪铭竹的《自画像》(1940年3月)、孙望的《小春集》(1940年)、吕亮耕的《金筑集》(1940年5月)、杜蘅之的《哀西湖》(1942年1月)、李长之的《星的颂歌》(1942年7月)、程铮的《风铃集》(1943年8月)、莫文来与徐愈的《黑鸟的歌》等。本文引用的例诗均出自《中国诗艺》杂志和“中国诗艺社”丛书,不再单独标注。 ②《诗帆》为南京“土星笔会”的同仁刊物,1934年9月创刊,1937年5月停刊,共出版17期,主要作者有滕刚、章铁昭、程千帆、孙望、常任侠和当时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学生霍焕明、沈祖棻、李白凤、吕亮耕等。《小雅》1936年6月于北平创刊,由吴奔星、李章伯主编,主要成员有吴奔星、林庚、李白凤、陈残云、锡金、柳无忌、吴兴华、路易士等。两个刊物上的诗人大多旧学修养深厚,注意吸收西方诗风,兼具古典与现代的风韵。标签:诗歌论文; 先锋艺术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小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