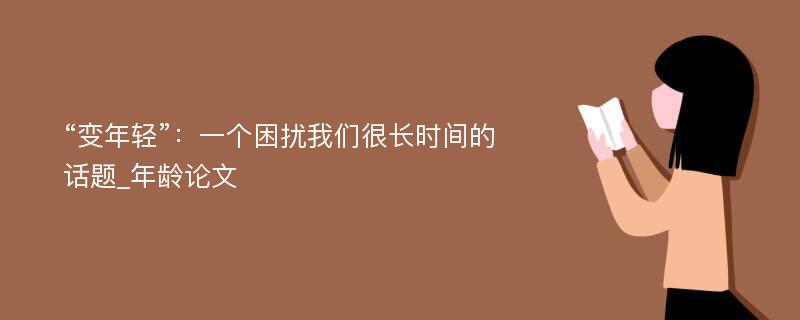
“年轻化”: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扰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文选》1—3卷,共205篇文章,谈及“年轻化”的计20篇文章(加上注释中提 到的1964年1月11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报 告》一文,共计21篇)。如果将这21篇文章涉及的“年轻化”问题与我国的改革开放的 历程结合起来学习研究,可以引发我们对“年轻化”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年轻化”为何仍然还是困惑我们的重要问题
从1964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年轻化”以来,到现在已经38年了。这些年来“年轻化” 虽然不断被提及、强调,但效果却始终不尽人意。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军委座 谈会上尖锐指出:“干部年轻化,军队提了多年,要求选拔比较优秀的、年轻的,台阶 可以上快一点。但应该说这件事情这几年做得不理想。”其实,军队由于加强了精简整 编的举措和转业的机制,这些年干部年轻化的问题相对来说还解决得不错。而地方从80 年代初的第一次机构改革到现在,有关年轻化的办法没少想,文件没少发,规矩没少定 ,措施没少用,但回头一看,“年年都在年轻化,岁岁提拔又老化”的状况依然。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对“年轻化”的认识有偏差,把权宜之计当做了长久之计。其实从邓小平同志38 年前提出“年轻化”的认识历程来看,由于当时军队尚未建立正常的转业机制,“年轻 化”最早是为解决作战部队指挥员年龄偏大的问题,“文革”后重提“年轻化”,是为 解决“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各行各业领导班子都存在老化的问题”。可以说,“年轻化 ”作为当时解决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使一大批老同志得以顺利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使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无论对解决军队干部老化问题,还是 解决“文革”后各级领导班子老化问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收到了应有的效果。从 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当时大刀阔斧的“年轻化”,就没有2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 绩,也没有今天大局的稳定。然而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同志,却把专门用以解决“文革” 十年浩劫遗留问题的权宜之计,当做了安邦治国可以包医百病的长久之计;把特定时期 解决领导班子普遍老化的暂时之策,作为了实现长治久安的既定方针。以至于忽略了干 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适时推进,特别是忽略了从领导干部“能下”方向实施战略突破。这 种忽略也就造成了把“年轻化”简单化、概念化。于是就有人把30岁左右的团长、40岁 左右的师长、50岁左右的军长的作战部队指挥员年龄标准,硬往地方县、市、省级领导 干部的年龄标准上套,硬要坚持各级领导班子一定要像军队那样保持10岁左右的年龄差 。于是,有的地方为了在“年轻化”上出“政绩”,一些40岁出头的县长、书记、处长 ,50岁左右的市长、书记、司长,不得不“闲赋”起来,让位于更加年轻的干部。50岁 左右的任省长是“年轻化”,如果当县长则要“一刀切”。由此推理,似乎50岁左右的 人能管得了一个省,却管不了一个县。幸好这种10岁左右的年龄差没有成为各行各业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否则,如果大学教授60岁“下课”,中学教师就得50岁“下课” ,小学教师就得40岁“下课”。而且,要求大、中、小学教师保持这种年龄差,比要求 省、市、县级领导干部的年龄差有更为充分的理由——所教对象(大中小学生)本身就有 年龄差。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决策上的失误。由中央往下,每下一层,年龄竞争的残酷性 便增添几分。于是,改户口的越来越多,岁数越长越小,甚至出现有的领导干部的“年 龄”居然比自己的同母弟妹还小十来岁的咄咄怪事。“七上八下”这句成语,在成为组 织部门用以解决用谁不用谁这一复杂问题“杀手锏”的同时,也成为相当一批干部头上 的“紧箍咒”。事实上,权宜之计一旦当做长久之计,“年轻化”之风就会从上层一直 刮到基层。“年轻化”的思维定式,“年轻化”下的“一刀切”,已经成为干部队伍建 设中最为严重的硬伤。
二是在贯彻“年轻化”上有误区,把治标之策当做治本之策。“年轻化”无疑是解决 领导班子“老化”病症的解表之药,在改革开放初期用此解表之药以应“老化”之急, 是必须的,也是正确的。然而解表之药的功效在于治标,治领导班子“老化”这一顽疾 重症,绝非“年轻化”这一解表之药所能完成。80年前建党之时,中国共产党何曾有“ 老化”之忧;半个多世纪前建国之初,各级领导干部何曾有不“年轻化”之虑?邓小平 同志1987年6月12日接见南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各 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中国的干部老化僵化问题比你们严重,比如,我们党的中央委员 会的平均年龄恐怕比其他各国党的都要大,我们党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 的平均年龄也都偏大。我们建国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领导人都比较年轻。从党 的十一大开始出现这个问题。这有客观原因,一大批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 打倒了,后来解放了,重新恢复领导工作,所以领导班子年龄偏大。”各级党政领导班 子、各行各业领导班子之所以都存在老化的问题,直接原因是十年“文革”,间接原因 是建国以来没有及时建立正常的“能下”制度,因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各级都普遍 并实际存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数千万公职人员队伍,能进而难出,想要不僵 化绝难做到;上百万各级领导干部,能上而不能下,欲使其不老化实在太难。面对干部 人事体制、机制方面的制度缺陷,有的地方和部门却希望用“年轻化”的治标之策去解 决,其做法无疑于扬汤止沸,而非釜底抽薪。邓小平同志认为解决这个“我们中国最特 殊的问题”,可以从“年轻化”入手进行治标,但治本之策则是“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 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最近,党中央所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总 则的第一条里明确提出“建立科学规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形成富有生机与 活力、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人用人机制”,符合“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精神,也是邓小平同志“制度建党”思想的一贯体现。
三是在对待“年轻化”上有禁锢,过分拘泥于某些个别论断和说法而忽视与时俱进、 制度创新。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 ,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 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因而江 泽民同志提出“三个解放出来”。实际证明,我们在对待“年轻化”问题上也或多或少 地存在着一些“拘泥于”,从而影响了我们在“年轻化”上的与时俱进。首先,从主要 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转化来看。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仍然还在强调“年轻化”,至少 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从方法上看,我们没有抓住主要矛盾;二是从效果上看,领导班子 老化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实践证明,“年轻化”作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并不等于仍是 现在的主要矛盾;整体换班作为解决当时各级领导班子普遍老化的有效方法,不等于现 在的有效方法;改革之初的班子老化只能用“年轻化”去解决,20年后领导干部的老化 完全可以通过“能下”的途径去解决。矛盾在发展,解决矛盾的方法必须与时俱进。其 次,从纵向与横向的比较来看。上溯五千年,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朝代的掌权人 把“年轻化”作为长期的既定方针;横看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地区的执政者没有一个 在长达数十年时间里反复强调“年轻化”。可以说,如果没有十年“文革”,我们的干 部队伍不会如此老化,“年轻化”也不会强调到如此程度。我们党和国家曾有过不知“ 年轻化”会成为如此严重问题的时期,只要认真借鉴中外官吏队伍建设的经验做法和制 度建设,不需要太多的时间,我们也肯定会有无须强调“年轻化”的这一天。第三,从 少数人的积极性与多数人的消极性来看。“年轻化”是干部“四化”中最能量化的指标 ,因而成为进出领导班子的“杀手锏”。有人曾根据有关“年轻化”的各类红头文件, 推导出“两大定律”。其一,称之为“头班车定律”。即在“年轻化”政策的导向下, 凡能在30岁左右坐上县级主要领导“头班车”的人,就有50%的几率在40岁左右,凭“ 年轻化”搭上地市级主要领导的“头班车”;如此,就有75%的几率在50岁左右,凭“ 年轻化”搭上省部级主要领导的“头班车”;还如此,几乎就有100%的几率凭“年轻化 ”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其二,称之为“末班车定律”。即一个22岁本科毕业的大 学生,安排到乡镇工作,并按有关岗位正常晋升提拔,按理论测算职务究竟能升多高。 结论是——如果他不被“年轻化”标准“一刀切”下,且每次都能搭上“末班车”的话 。那么,其退休前理论上的最高职务有可能做到乡镇党委书记。以敢向总理讲真话而闻 名于全国的李昌平(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了近17年才被任命为乡镇党委书记,如果 李是学士又会工作多少年后才会被任命呢?如果此时他年龄偏大是否还会被任命呢?。由 这“两大定律”而观之,不难想见,如果简单化地执行“年轻化”,一方面虽然会调动 几十、几百、几千人的积极性,使其正效应能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却可能引发几万、几 十万、几百万人的消极因素,甚至会刺激其中有的人因前程无望而产生负效应。这就不 难理解为什么有的搭上了“头班车”的人,尽管干劲百倍,可是却因为没有大多数人的 积极性相配合,常常陷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少数人的空忙”境地;为什么有些人为了 搭上“头班车”,发疯似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为什么个别人甚至铤而走险,骗官杀 官。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59现象”、“49现象”、“39现象”乃至“29现 象”;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产生“为没有机会腐败而痛苦”的心理变态?
其实,简单化、概念化的“年轻化”,在某些地方和部门已经成为一种“问题化”。 对此有人不胜感慨:“年轻化”下,只许我少年得志;“一刀切”来,不准你大器晚成 。面对群众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不断增加,安全事故、恶性案件逐年上升的态势,一些 提拔无望的干部竟在旁边偷着乐,一些过早“赋闲”的领导也在冷眼旁观。我在基层调 研时与一些三四十岁的乡镇长谈话时了解到,简单化的“年轻化”,不仅让大多数被排 除在“年龄格”外的同志每每心灰意冷,而且使少数暂时留在“年龄格”内的同志也常 常担惊受怕。因为一旦今天“一格”被落下,今后“格格”都没有了希望。
解决“年轻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
我以为,解决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缺乏活力、素质不高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能上能下 ”、“能进能出”,特别是“能下”和“能出”方面的制度创新,而不是“年轻化”。 “年轻化”虽然可以直接缓解班子老化问题,但并不能因此而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增强 领导班子活力。“年轻化”从考察的内容看,不能代替干部的另外“三化”;“年轻化 ”从质量的标准看,不等于优化,也不能涵盖高素质;“年轻化”从激励机制的作用看 ,也不利于调动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性。其实,面对建国半个多世纪来所形成的“两化” 现象,即各级领导班子老化,数千万公务员队伍僵化,断不可用“年轻化”这一味药去 医治,否则,病非但不能治愈,反而会加重。
让大多数人对未来抱有希望,这是干好任何一项工作的先决条件。对加强党的干部队 伍建设这项工作而言,“年轻化”能让大多数人对未来抱有希望吗?最近我去山西省长 治市调研,了解到这么一个典型人物。1983年,在“年轻化”政策的作用下,年仅38 岁的吕日周被破格提拔为原平县委书记,创造出令人称道的“原平经验”。任闲职十多 年后,2000年已过55岁的他又出任长治市委书记。仅仅两年时间,他率领市委一班人又 创造出更加成熟的“长治经验”,为全国新闻媒体所关注和赞誉。可以说,没有20年前 的破格,也就没有了当年的那颗“新星”;如果两年前吕日周因“年龄格”而被“一刀 切”下,也很难有今天的“长治经验”。目前“长治经验”还限于“人治”阶段。人们 担心吕日周一旦调走,长治的新闻舆论监督就会“人亡政息”。而吕日周已经57岁了, “年龄格”不破,“七上八下”势在必然,干部群众的担心并不多余。由此可见,“年 轻化”中有人才,但年轻并不等于人才;人才有老有中也有青,人才断不会被“年轻化 ”这一格所拘。一个好的用人之道,既会使少年英才辈出,也不会把大器晚成者埋没。 否则我们就只会有周瑜,而不会有廉颇;只会出甘罗,而不会出姜尚(子牙)。
为解决领导班子老化问题,我们曾在80年代初搞过整体换班。然而,用这种形而上学 的“年轻化”去解决班子老化、队伍老化,问题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治本之策,还 在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当务之急,一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能下”、公职人员“能出 ”这一主要矛盾,二是要尽快破除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所形成的那些或明或暗的“年龄 、台阶、文凭”等格。用“能下”、“能出”解决干部队伍过分膨胀的“空间”问题, 用“不拘一格”解决老中青干部各尽其才受制于年龄的“时间”问题。通过建立健全有 关制度,使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必须下”的前提下逐步“愿意下”,使 各类公职人员在“能够出”的前提下逐步“愿意出”;使千里马不因毛的长短或颜色深 浅而被拒于赛场之外,使人才不因发现晚而终不被用或难有大用。从而使影响大多数人 积极性的问题得到认真解决,为造就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邓小平 文选》第2卷,322页)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只要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不拘一格”、“人尽其 才”的机制、体制和制度下,科学、合理、健康地流动起来,不仅“年轻化”自在其中 ,而且增强领导班子的活力,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等深层次问题也定会迎刃而解。
标签:年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