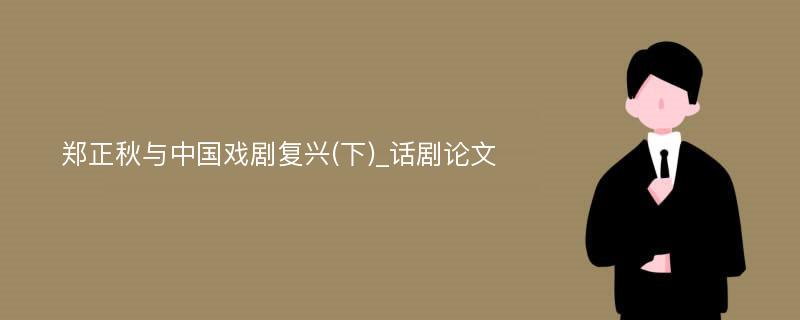
郑正秋与中国话剧复兴〔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中国论文,郑正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黄金与美色》之后的第4个月,郑正秋编演了《阶级刀》(1920·4)。该剧共分3幕,描写一个贫穷的农家女,不甘心受人歧视的地位,但是又找不到出路。有一天她突起奇念:嫁给贵族做少奶奶。出嫁之后,她的父亲为了保持住既得的虚荣,竟拿刀杀死了村里平日欺负自己的阔人,犯下人命案,成了被告者。最后在她的周旋下,上下都同情她——无情的侦探良心发现,作威作福的贵族大少爷也向她请罪,她父亲幸免一死。按郑正秋的意图,该剧的宗旨,是在于穷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靠自己起来抗争,冲破贫富命中注定的旧观念,实行破除贫富的阶级对立。这里,我们可以批评郑正秋这种个人主义的抗争方式是极其幼稚,不会起根本性作用的;但是同时不能不给他献上一首赞美诗,感谢他为我们的话剧舞台塑造了一位大胆、泼辣、能干的乡下姑娘形象,把农民对地主的暴力斗争引入话剧,而这一切又是首次的,特别是在共产党成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的。
至于《新旧家庭》(1921·3),则是郑正秋全部政治戏中影响最大,因而最成功的重要作品。在这出连台本戏中,郑正秋以新与旧作对比,从穷媳妇自己生孩子自己守生开始,着重揭示一夫多妻制的旧家庭给妇女带来的巨大痛苦,这种家庭常常演着各种悲剧:大小姐大闹结婚场;二小姐害贤妇;穷媳妇从旧家庭的无形监狱被投入有形的监狱;坏老婆杀害亲夫;无止息的嫉妒风潮使人与人之间弥漫着鄙视与不和……经过种种痛苦的折磨之后,人们终于开始醒悟,有的承认罪过,有的悔过请罪,有的舍身救人。总之,郑正秋在戏中把“各处(专制)家庭同家庭中长幼、尊卑、主仆、男女、老少各人的所以恶所以善……种种痛苦”,一句话,“旧社会的恶制度、恶习惯的罪状”,“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使它成为“攻击专制家庭的急先锋”,激发起观众的憎恨情绪,进而下定改造社会的决心并付诸行动。戏中有一首主题歌:《觉悟歌》由郑正秋自编自唱,歌词有力,曲调高昂,大大强化了该剧的主题。
从艺术效果上考虑,这出戏的特点是有很强的刺激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戏的支点,使人不由已地出泪,咬牙,发狠。这是郑正秋在分析了国风民情之后有意的所为,他认为,“把悲剧刺激人们是现在中国的大要点”。但是郑正秋没有把它编演成为纯粹的悲剧,而是适当地揉进喜剧的成分:逗乐的事实。演员笑梧、啸天、双宜、毓秀等的表演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趣味性,甚至滑稽。之所以这样,主要是郑正秋对话剧出路包括内容和形式,以及观众欣赏层次的综合探索的使然。这位艺术家当时面临的形势特点是:一、他要依附于资本家,演什么、怎么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家;二、与此相连的,是迁就观众,迎合大多数男女看客的心理,要做到故事有头有尾,趣味性浓,戏是连台戏,不能运用外国“三一律”的编剧法,只求突出事体的中心;三、剧社演员多,如果许多人排不着戏,不但资本家不愿意,演员们也动醋劲,所以要考虑在戏里给他们,尤其是滑稽演员一个适当的位置。欧美戏剧里一出戏往往只有四五个角色的做法,在中国行不通。从这种复杂的形势出发,郑正秋在话剧危机时期探索其出路机制时,摈弃了两种极端的做法:要么就是严肃的悲剧;要么就是活泼的喜剧,而在悲喜剧中间寻找它们的交叉点,按照这交叉点原则创造一种与众不同的戏剧模式。当然,这依然要符合他那条以严肃为主、愉悦为辅的原则。从戏剧样式上来讲,《新旧家庭》可以说是一种新样式,即悲喜剧。
郑正秋在五四运动后创作的政治戏,构成了郑正秋剧作的主流倾向,因为郑正秋公开宣称它们是为“助新文化运动一臂之力”而作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本身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主潮和历史的前进方向。观众从中可以倾听到五四思潮的民主、自由、解放的强烈新音,应该说是此时期我国话剧的一份独一无二的新收获,是正秋对我国话剧的不可磨灭的新贡献,为后来话剧将要昌盛半个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下面讨论伦理道德型。这一类型一般表现人伦的关系,特别是家庭的人伦关系,这种人伦关系的变化由理智,一种外在的灌输式的理性而不是感情所支配,善的方面受到肯定,恶的方面则被否定。
郑正秋在1913年9月下海,首先推出的便是伦理道德型话剧,通过描写家庭故事,来反映现实,移易人性情,裨益社会。借用徐半梅的话说:郑正秋“一上手便把家庭戏来做资料,都是描写家庭琐事”。
郑正秋创作了中兴话剧的第一出家庭伦理戏是《恶家庭》,共12本,22幕。他之所以编演该剧,是封建家庭窒息性的积淀促成的。他在报上广告说:“世风不古,谈起家务就皱眉头者多,郑正秋乃编《恶家庭》新剧……使剧场为教育场,借艺员为教务员,将家庭中种种恶现状,形容得淋漓尽致。”
这出戏,清楚地表明了郑正秋的关于伦理道德的创作意图,也透出了郑正秋的巨大的创作才能。如果说,在他的处女作《铁血鸳鸯》中,他作为编剧的才能开始形成,那么,到《恶家庭》,这种创作才能已经臻于成熟了。他以人物的命运际遇作为线索,编织起一个曲折离奇的封闭的长篇故事,足以抓住观众。随着故事的进程,他又以人物之间的对立、排斥或同情、支持,来调动观众的喜怒哀乐,足以掀起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浪。正秋作为一个导演和演员,他的艺术才能在这出戏里也获得了比较充分的体现。他可以在戏里同时饰演凶残而淫乱的卜静丞和被损害被侮辱的奶娘,演员身分、言语都相当恰当,生角、旦角一齐来,戏路宽广。朱双云说:“奶娘一角,演之有王惜花,有冯怜侬,有罗笑倩等。然匪失诸蹇滞,即失诸矫操。责备求全,正秋尚已。”集编、导、演于一身,多才多艺。
《恶》剧于9月14日晚首映,地点在南京路谋得利戏园,上座率很好。每晚,常常9点左右,座位就满。有时演至晚11点钟,仍有观众纷纷买票上楼观看,致人多场狭,正秋在散戏时向观众表示抱歉。
舆论界的反应显示该剧的份量是何等地沉甸甸。各报如《申报》、《新闻报》、《时报》、《民报》等,纷纷报道该剧备受欢迎,饮誉上海,并因此重倡话剧,为其正名。王钝根说:“《恶家庭》三、四本,较前更见进步,阿蓬被卜静丞打死,弃尸于野……《恶家庭》七、八本,愁云惨雾,几乎无幕不苦。”“新剧之感人,胜于旧剧万倍。”朱双云说:“《恶家庭》一剧,时颇流行,显为中兴新剧之成绩品。”
《恶》剧的震撼效应惊动了出版者,有些人把注意力转移到话剧上。一家新剧小说社应运而生。它首先把《恶》剧改编成小说,于翌年初出版。国体书局于翌年6月也将该剧编为小说出版,易名《不情人》。
在《恶》剧之后,郑正秋在两个月内,一股作气成功地创作了20余部家庭戏。徐半梅说:它们“俱是绝好的剧材。于是部部有精彩,出出能号召。”在这一家庭戏系列中,又数下面几出最为优秀。
《火浣衫》。这出戏叙述的是一个奸犯的一段故事。
在这出戏里,显而易见郑正秋是企图通过这段故事,告诫人们,不要色迷心窍,乱伦害理,贪一时的欢乐,要理智办事,循规蹈矩,维持正常的伦理秩序。否则害人害已,落个可悲的下场。在艺术家看来,万恶淫为首,它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行为,是社会罪恶的现象,也是民德衰颓的现象,要克服这一现象,必须普遍涤荡淫乱。这无疑是积极的思想。郑正秋不仅有力地鞭打了邢汹的淫乱行为,而且谴责了巨商卜施仁的淫乱行为。这个衣冠禽兽的家伙,竟乘章义之危,想占有章义的妻子。生怕自己的太太知道,那天晚上还吩咐家人卜良望风,不料卜良也乘这机会,同他的妻子通奸了。这对卜施仁来说,是个莫大的嘲笑。艺术家通过卜施仁和卜良这两个穿插事件,说明在旧社会里,淫乱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地破坏了人们家庭生活的幸福。我们仿佛听到,艺术家在大声呼唤建立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否则人们的精神生活将永远陷于不安宁的痛苦之中。
在戏里,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在鞭挞奸犯的同时,艺术家对他们的犯罪行为的开脱。在这点上,《火浣衫》与《恶家庭》两剧都是相同的。《恶》剧中的卜静丞,其犯罪的原因,有一个姨太太新梅在作怪。《火》剧中则有个嫂子岳氏的合污,推波助澜。特别是戏结束时,卜静丞在死前幡然悔悟;邢汹被判死刑后,其言也善。
其次是有意识地设置悬念。悬念有两种:一是大悬念;一是小悬念。戏的开头,邢汹刚获释回家,就重犯奸罪,观众看到这里,就很自然地发问:“这家伙会不会‘二进宫’呢?”观众怀着这疑问,一直看到戏的结尾才得到回答。这是大悬念,贯穿全戏的。小悬念比比皆是。邢勉士从外乡回来,这时章义已经向他暗示他弟弟同他娘子的关系了,他弟弟和他娘子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章义开始被诬为诱奸,后来又被诬为谋物害命,因此被判死刑,这冤案还会不会得到平反昭雪?等等。这些从观众心里引发出来的疑问,都是在戏中经过一场或若干场之后便获得解决的了。而且它们只附于戏的小段落之中,套在大悬念之中。依靠这些大、小悬念,戏就能够自始至终抓住观众,收到挽留观众的效果。
再次是注意噱头。当时上海人最喜欢噱头,正秋深深懂得他们这一心理状态。因此,他创作一出戏时,总是先想一想,哪些地方该放点噱头,作为佐料。但是它们没有流于一种庸俗的、廉价的笑料,而是包含一种又微笑又辛辣的讽刺。因而它们在戏中获得了存在的意义。
《义弟武松》(1914·6)是一出历史戏。此时郑正秋从编演家庭戏转入编演历史戏。这并不是艺术家的一时心血来潮。他痛感辛亥革命前后政治戏不随社会环境变化和观众情绪变化而变化,而依然重复呼喊革命,谩骂皇帝的原初阶段,甚至变本加厉地成为演员的“自我表现”,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他说:“新剧得有今日,小子(指郑正秋)颇费心血,独惜人多避重就轻,戏多平易无物,长此不图进步,窃恐熟极生厌,不是持久,是故提倡历史戏,实为当务之急。”不断给予新鲜信息,避免“知觉饱和”,即经久不变的刺激,确是保持观众对话剧的兴趣,也是保持话剧发展的重要方法之一。他的历史戏创作并不表明他勃发了思古之幽情,逃避现实;相反地,他仍然是立足现实向前看,有着重大社会责任感的。他把他的进步思想和高尚道德,从家庭戏的形式里移植到历史戏的形式里,借历史来批评现实的弊端,结果表明,郑正秋这一转移是正确的。
中国历史是一条长河,里面可以入戏的东西很多,郑正秋为什么首先看中了武松呢?他回答:“《水浒》是小说中绝妙好书,武松是《水浒》里第一好汉,我敬其人,我服其言,我壮其行。我恨世间多兄不兄弟不弟之混蛋,我恨世间多以肉欲败风化之狗男女,我于是编此剧,以警之。”
在《义》剧中,郑正秋鉴于观众对清朝的反感情绪,在服装打扮上,一律革除掉过去小帽大辫、方褂长袍的仿清装束,全部采用古装,但又与旧剧有别,开古装历史话剧风气之先。
该剧公演后,以其内容的家喻户晓和服装的别开生面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它与稍后出现的《木兰从军》(舞台上出现了真马)和《貂蝉》等古装话剧一起,称雄于舞台。其它仿效郑正秋,仍演家庭戏,清朝装束的话剧团体,因此受了很大的打击,急起直追。话剧登上了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