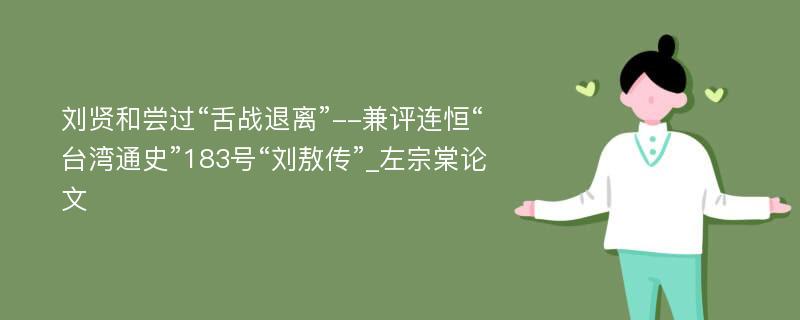
刘璈何尝“舌战退孤拔”——兼评连横《台湾通史#183;刘璈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连横论文,通史论文,台湾论文,退孤拔论文,刘璈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省前的末任实缺台湾道刘璈,是台湾近代史上的有争议人物。台湾史学家连横称他为“有经国之才”的能吏,在所著《台湾通史》中为其作专传,其他章节中记述刘璈的政绩亦甚多。对于刘璈在中法战争期间被督办台湾事务的福建巡抚刘铭传参劾,革职籍产,流放黑龙江,最后死于戍所的结局,认为“士论冤之”〔1〕。1985年, 台湾史学家许雪姬先生发表了长篇论文《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为刘璈作了全面的辩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事实上,刘璈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十分杰出,在防戍上,法船始终无法在南部越雷池一步,在外交方面,除尽力保护外商,屡获好评外,且欲利用外交手段解决台海封锁之困;尤以在法舰上面见孤拔时所表现的勇气,更令人折服。”因而“有关二刘之争,今人的研究,较倾向于同情刘璈。”〔2〕
最近,我因研究台湾近代抗法战争的需要,搜集了一些有关刘璈的资料,发现他被黜的原因与上述说法并不尽相同,刘璈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并非“十分杰出”,而是令人失望。现将我的研究所得写出,以供参考。
一
刘璈是怎样发迹而得任权势颇大的台湾道的,对此,连横先生作了这样的说明:“刘璈字兰洲,湖南岳阳人,以附生从军,大学士左宗棠治师西域,辟为记室,参赞戎机,指挥羽檄,意气甚豪。及平,以功荐道员,光绪七年,分巡台湾。”〔3 〕后世学人谈及刘璈的早年经历,多遵循连横先生的说法。一些大陆著作还据此演绎成刘璈曾参加左宗棠领导的收复新疆和抗俄斗争云云,而不察连横先生的说法颇多讹误失实。
首先是关于刘璈的籍贯。据沈葆桢于光绪元年二月十七日片称:“据营务处浙江候补道刘璈禀称:该员于本年二月初一日在风港营次接到家信,知父品章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湖南临湘县本籍病故,恳请奔丧,回籍守制。”〔4〕据此, 可知刘璈的籍贯应为湖南临湘县,而非湖南岳阳。清时,在岳阳城设岳州府,附郭巴陵县,辖下有临湘等县。民国时,始改巴陵为岳阳县。因此,将刘璈的籍贯指实为岳阳(城或县)人都不准确。
其次是刘璈的道员资格何时取得?刘璈早年确实投在左宗棠麾下襄办营务,因参予镇压浙江太平军有功,被左宗棠奏保为浙江台州府知府。然而,当左宗棠于同治六年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主持平定甘陇回乱时,刘璈却没能跟去,而是继续留在浙江官场浮沉。不过,至迟在同治十三年,他已由实缺知府改以道员候补了,而不必等到平定西域以后。
同治十三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奉命赴台交涉日军侵扰牡丹社事宜并筹办台防,经台湾道夏献纶举荐,刘璈被札委为总理营务处。从同治十三年九月至光绪元年二月的短短6个月时间里, 刘璈颇得沈葆桢的赏识,刘璈能由丁忧前的候补道改为丁忧后的遇缺题奏道,可能即得力于沈葆桢的奏保。这番际遇,成为刘璈日后得授台湾道的契机。
清制,父丧,儿子为官宦者须丁忧守制三年。光绪元年二月,刘璈因父丧回籍奔丧守制三年,至光绪三年五月始服阙。而左宗棠的筹划和收复新疆,恰好也是光绪元年至三年间的事情。这段期间,在籍丁忧守制的刘璈,显然是不能分身到新疆辅佐左宗棠了。
刘璈再次投到左宗棠麾下是比较晚些的事情。大概在守制期满时,刘璈考虑到自己日后的出路,可能曾与老上司联系。光绪三年十月十四日,左宗棠上奏请调刘璈到营“以候差委”。清政府下旨将刘璈交左宗棠差遣。由于通讯和交通落后等缘故,当刘璈奉旨赶达左宗棠营中,已是光绪四年底至光绪五年初的事了。光绪五年初,恰逢左宗棠部下总理关内营务处及统领三营军兵的王诗正丁忧,左宗棠遂将遗缺札委刘璈。同年下半年,兰州道出缺,左宗棠又“即以刘兰洲暂署”,从此,刘璈便逗留在关内兰州一带,可能并未出关到达新疆,和所谓的左宗棠抗俄斗争也不沾边。连横先生称左宗棠将刘璈“辟为记室”,显然是并不了解刘璈已负有具体职司这一事实。虽然在此期间上奏朝廷时,左宗棠免不了要为刘璈说些好话,但在私下里,左宗棠却多次函告他人,流露出对刘璈的不满。如于光绪五年底函告杨昌濬:“刘兰洲好察多疑,弟所不取。”〔5 〕光绪六年四月有两函谈瓜子沟番乱,认为刘璈应负一定的责任。〔6〕可见, 左宗棠并不是十分赏识刘璈。光绪七年正月,左宗棠被命为军机大臣。这时,中国又因琉球问题与日本有隙,为恐日本重蹈故辙侵扰台湾,四月间,清政府在调贵州巡抚岑毓英为福建巡抚,前往台湾筹办防务的同时,又因台湾道张梦元升授福建按察使,遂简授刘璈为台湾道。其中,左宗棠是否在军机处起了作用不得而知,但是,刘璈在台湾时得到沈葆桢的大力提携和称誉应该是影响这个任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任台湾道的最初几年中,刘璈颇得几任上司的好评。光绪七年九月,岑毓英奏称刘璈等“晓畅戎机,熟悉情形。”〔7 〕光绪九年底,清政府命令沿海各处筹备防法,已调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左宗棠奏称:“台湾孤悬海外,为南洋七省门户,防务最关重要,台湾道刘璈本有为之材。”〔8〕福建督抚也奏报将台湾防务责成刘璈。
二
如此倍受上司青睐赏识的刘璈,是什么时候因何原故而开始走下坡路的呢?连横先生等人的看法认为是由于遭受刘铭传排挤的结果。而我们搜集的资料却表明:早在刘铭传赴台之前,刘璈已因筹办台防不力而失宠了。
台湾防军在平日无事时仅有十几营人,防法事起,迅速增加至40营。刘璈等将全台划分为5 个防区:前山自恒春至凤山及台湾县之曾文溪为南路,统军5000人,由刘璈自领;曾文溪至嘉义及彰化之大甲溪为中路,统军3000人,由台湾镇总兵领之,如总兵他调,则由刘璈兼统;自大甲溪至新竹、淡水及宜兰之苏澳为北路,统军4000人,由新授福宁镇总兵曹志忠领之;后山自花莲港卑南至凤山界为后路,统军1500人,由副将张兆连领之;澎湖为前路,统军3000人,由澎湖协副将领之;此外,另设数千机动兵力,亦由刘璈掌领。“各路所统之军分半扼守,余作游巡,临时自为战守,并救应他路,是路与军虽分,而势力仍合。”〔9〕
经过这样一番布置后,刘璈认为台湾防务已有把握,遂于光绪十年四月得意洋洋地上禀福建督抚称:台湾本有为之地,为之亦非无把握,端赖有治人,有治法,又有治权,则事可得为,地方亦可制治。今筹防分派五路,因地制宜,其南路、中路、后路的新旧营勇,皆经职道挑选,训练紧严,及另备活营,皆属器精兵锐,能战能守,兼以水陆团练,认真操演,虚实互用,三路陆防固已可恃。如能得前路、北路一律整齐,则不患台防之不振。〔10〕
台湾防务是否真象刘璈所说的那样可靠呢?结合后来的战事来看,刘璈的部署至少存在着这样的一些致命弱点:
一、防御重点选择不当。台湾与澎湖接邻而居,唇齿相依,安危与共。当年郑成功、施琅等攻取台湾,都要先夺澎湖,因此,澎湖素有“台湾门户”之称,“守台必先守澎”乃一般的军事常识。此外,法舰越洋来攻,补充燃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盛产煤炭的基隆地区将会成为法舰首先夺占的目标,也是稍有近代战争知识的将帅所应该想到的事情,但是,刘璈却将道衙驻地台南定作防务的重点。因此,他所定的南、中、后三路及机动兵力万余人,实为拱卫台南而设。对于台北、澎湖防务,刘璈虽亦提及,但只是略作敷衍,并未认真设防。
二、守军的器械不精,训练不良。在刘璈关于筹划防法的多次禀报中,只强调治人、治法、治权,却很少提到武器装备和训练士兵的问题。如他提到:法军陆路之长,止任器精令严,队整耐战;而所短却在笨直平板。如我能尽其精严整耐之长,化其笨直平板之短,则彼为我制,自操必胜之权。〔11〕这说明他对于使用热兵器的近代战争缺乏了解。他按照中国的传统军事思想,只强调民心向背和军队数量的重要,却没认识到,对于一场短时期的小规模战争来说,武器装备的优劣和士兵素质的好坏,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忽视了给台湾防军更新补充武器装备及加强训练士兵的问题。后来,刘铭传严劾刘璈,这也是他的主要罪状之一。〔12〕
三、内部争权夺利,以致不能形成统一的指挥。中外军事水平的巨大差距有着客观的历史原因,要弥补这一差距,清军的内部团结、统一指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左宗棠曾批评过刘璈个人性格上的缺点:气局不甚阔大,好察多疑,横生异议等,导致他在筹备防务的紧要关头,导演了一出与台湾镇总兵吴光亮争权夺利的丑剧。原来,台湾设道治民,设镇治兵,防法初期,刘璈虽被责成办理台防,但职权并不分明。为了达到大权独搅的目的,他恶毒攻讦和要求调走吴光亮。福建督抚迫于左宗棠的压力,只得将吴光亮调署漳州镇,但并未因此让刘璈督办全台防务,反而借口:“台南北相距甚远,军情瞬息变迁,恐台湾道刘璈鞭长莫及。”改派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渡台督办台北防务,〔13〕结果,台湾防务仍不能做到统一指挥,全力对敌。
刘璈筹防的种种弱点,很快就在法舰骚扰基隆的“三月十八日事件”中暴露了出来。
虽然台湾早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已开港,各国洋商云集,一些国家还在台湾设立领事馆,但却没有一个法国商人或游客、一艘法国商船或军舰到过台湾,因而,法国朝野对于台湾缺乏了解。据说,后来来华担任远东舰队司令的孤拔,所拟攻击的中国港口只是上海、福州、烟台、旅顺等,却从未考虑过台湾。只是经过光绪十年三月十八日法舰到台湾的实地侦察后,利士比了解到基隆煤矿质量优良和防务薄弱的情况,便电告法国政府,极力主张必要时将基隆以及整个台湾列为夺取质押物的首选目标:“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非常顺利地占领该地,在战争时期,这个地方将是颇为宝贵的。占领整个台湾大岛,也不会有多大困难,而留守那里的军队,对我们说来是微不足道的。”〔14〕法国政府采纳了利士比的意见,决定“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15〕显然,正是由于刘璈的无能,使台湾防务处于不堪一击的薄弱状态,才招惹了法舰的侵犯祸心,在这方面,刘璈咎无可辞。
刘璈筹划台湾防务的情况传到京师后,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非议和弹劾。如刘铭传在赴台前就根据京津流言奏称:“惟闻台湾驻防之兵虽为数不下二万,而器械不精,操练不力。”〔16〕显然,这类流言对刘璈是十分不利的,成为言官奏参刘璈的理由。光绪十年三月有旨称:“有人奏参福建台湾道刘璈肆意贪横,办防松懈,设遇有警,恐致偾事,请旨饬查。”〔17〕四月十九日,翰林院编修朱一新上奏,建议将刘璈调离台湾:“台湾道刘璈前守浙之台州,尚称果敢,近闻镇道意见不合,闽督驾驭失宜,古未有上下失和而可共兵事者,应请饬查更调。”〔18〕这些参奏动摇了清政府对刘璈的信任,加上又得悉台湾当局处理法舰骚扰基隆事件不当的消息,遂决定临阵易帅,仓促任命刘铭传前去督办台湾事务。可见,刘铭传的赴台,是刘璈不再被清政府信任和重用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所以说,在刘铭传赴台前刘璈已经失宠了。
三
从刘璈于光绪十年三月被参劾,至光绪十一年四月被撤任,相隔了1年多时间,其间还发生了长达10个月的台湾抗法战争。 刘璈完全可以在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有所作为,以稍赎前衍,挽回天心。但他却没能这样做,反而将派系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为了掣肘和刁难刘铭传,对台北抗法战争持消极抵制态度,以至越滑越远,最终身败名裂,遭受清政府的严历惩处。
按照分工,刘璈统领南路军兵,并在署台湾镇总兵章高元北援后,兼统中路军兵,并节制调遣杨金龙所部机动兵力,而后路统领副将张兆连又是他的亲信,因此,他能掌握和支配的军兵达到万余人。无可否认,刘璈在筹划这些防区的防务时,是做了不少事情,但是,由于法军并未攻打这些地方,因而是无功可录,只是尽了本身职责而已。
连横先生对刘璈有所偏爱,他在《台湾通史》的《外交志》和《刘璈传》中,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记述了关于“刘璈舌战退孤拔”这样的一则轶事,作为刘璈在台南的抗法功绩:光绪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孤拔亲自率舰泊安平,通过英领事请刘璈相晤。刘璈欲往,左右说曰:法人狡,往将不利。璈曰:不往,谓我怯也。咄!乃公岂畏死哉!戒炮台守将曰:有警,即开炮击,勿以余在不中也。遂登舰,孤拔相见甚欢,置酒飨。语及军事,璈曰:今日相见,为友谊也,请毋及其他。孤拔曰:以台南城池之小,兵力之弱,将何以战?璈曰:诚然。然城,土也;兵,纸也;而民心,铁也!孤拔默然,尽醉而归,法舰亦去,而台南得以无害。〔19〕这则记载将刘璈描绘成一个智勇双全,大义凛然,为保卫台南安全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英雄,一些大陆史学著作也曾引用了这则记载。连横先生没有注明这则轶事的出处,许雪姬先生的文章在提及此事时,注明是出自洪弃生所撰《寄鹤斋选集》。〔20〕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无论从情理上和事实上看,都不可能发生刘璈舌战孤拔事。
从情理上看,在六月十五日的基隆首战后,刘铭传“以我国体制有关,不便率往”为由,拒绝了法酋利士比邀请登舰晤谈。事后,刘璈曾向人提及引事。〔21〕清政府闻知,有旨明确指示前敌:“刘铭传不登法舰,具有识力,嗣后如有此等诡计,切勿为其所绐。”〔22〕严旨煌煌,先例具在,刘璈不可能公然违旨破例,贸然登临法舰。其次,自法舰侵扰台湾以来,刘璈或亲禀或转禀有关法舰残虐往来台湾海面的中国船民事件多起,其中伤心惨目情景,令人发指。那么,又怎能设想刘璈会在战火未熄、仇寇猖狂之时,腆然与敌酋握手言欢,觥筹交错,畅谈所谓“友谊”呢?这样做,岂不是有些不伦不类吗?最后,孤拔是侵略中越的急先锋,他在越南攻山西,在中国侵马尾、占基隆、轰镇海、袭澎湖,做下多少坏事!是双手沾满中越军民鲜血的刽子手。这样的人,怎可想象用几句话就可以打消他的侵略念头呢?
从事实上来看,帮办福建军务的杨岳斌于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潜由台湾卑南登岸,二十四日向台南进发,二月初二日前在旗后炮台会晤刘璈。他于二月十二日奏报此行的见闻称:“沿途接见文武官绅,访察地利民情,适台湾道刘璈在旗后炮台,臣即前往详阅一切,二月初三日同抵台湾府城,随率先看安平炮台。”〔23〕据此,可知杨岳斌在二月初二日前后一直和刘璈在一起,但并未报告刘璈初二日在安平会晤孤拔事。再据法方资料,二月初一日(3月17日), 孤拔正在宁波港外指挥法舰封锁甬江,以禁止中国从海路运输米谷。为了亲自执行法国政府攻夺澎湖的指示,孤拔命令还在基隆的利士比前来替换他,二月初五日(3月21日)利士比到达宁波港外接替孤拔。第二天, 孤拔离去,于二月初七日(3月23日)回到基隆。〔24〕可见, 在二月初二日,孤拔也不可能在安平约见刘璈。既然两个当事人都不可能在二月初二日相晤于安平,则所谓“刘璈舌战退孤拔”一事就是虚构出来的。
中法战后,刘璈被逮治。当时,上海《申报》曾连篇累牍地刊载为刘璈“鸣冤”的材料,其中历数了他在台南防御法军的“功绩”。但是,即使在这些夸张失实的材料中,也没有提及“刘璈舌战退孤拔”事,可见,有关此事的传说纯系后来好事者的杜撰。连横不察,误采入书,实为败笔。
在台南既然不能建立抗法业绩,那么,刘璈能不能采用诸如积极支持台北抗法战争的方式来作出贡献呢?作为大权在握的台湾官府头号人物,他完全有责任、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主要的就是派兵北援。这是早在刘璈实施分军分区防御方案时已考虑到的,各路所统之军只分半扼守,另半则援救敌军所攻之路。在这方面,刘璈又做得怎样呢?
在刘铭传到达台湾之始,很快就发现刘璈的分军分区防御方案存在着南北轻重倒置的致命缺点。六月初四日,他奏报清政府:“查全台防军共四十营,台北只存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所部三营,曹志忠所部六营而止,台南现无大患,多至三十一营。南北缓急悬殊,轻重尤须妥置。”〔25〕清政府览奏后,支持刘铭传的意见,于六月二十一日有旨:“闻台南兵数尚足,可否调赴前敌,著刘铭传酌度办理。”〔26〕然而,刘铭传除顺利地调到旧部章高元两营外,再调其他军兵时,就遭到刘璈的消极抵制了。以至尽管台北形势危急,刘铭传从台南调兵仍困难重重。清政府闻报后,觉得事态严重,于七月十九日有旨,欲派另一淮将周盛传赴台,“统办台南防务”,〔27〕尽夺刘璈军权,以与刘铭传南北合作,更好地调动台南兵力支援台北军民的抗法战争。此事虽因周盛传未能成行而罢,但却是刘璈失宠的又一迹象。
八月,清政府闻知法军攻占基隆的噩耗后,即“著刘铭传乘其喘息未定,联络刘璈,同心协力,合队攻剿。”〔28〕但是,刘璈胆大妄为,固执地拒绝抽调台南军兵北援,为了制造理由,他在八月二十一日就禀称:台南“地阔兵单,防不胜防。”〔29〕九月二十九日干脆奏称:“台南合前、后、中共支应四路计大小三十营,各路犹以地阔兵单,纷纷请添防勇,势不能不酌予添招。”〔30〕言下之意,即是台南自顾不暇,援应台北更无从说起。总之,终台湾抗法战争,除章高元两营不计外,由刘璈部下调赴基隆、沪尾前敌作战的,仅陈永隆、柳泰和两营而已,这区区数字与刘璈所统近30营相比,实在是太少了。因此,说刘璈是按兵不动,不救台北危局也不算过份。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刘璈不但不积极调兵援应台北,反而抓住刘铭传“撤基保沪”一事,采用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手法,煽风点火,大作文章,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地制造舆论,竭力损害刘铭传的威信,动摇清政府对刘铭传的信任,干扰刘铭传的作战部署,差点葬送了台北的抗法大局。其中原因,据李鸿章的看法,是由于不满刘铭传在六月初四日奏报中批评他的筹防方案轻重倒置:“省初至台即奏劾刘璈,彼衡恨,因基隆之退,到处谣诼。”〔31〕当他设法收集到一些台北官绅在沪尾战前不满刘铭传的意见,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讦和倾陷刘铭传,造成极坏的影响。
刘璈的鬼蜮伎俩很快就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八、九月间接到丢失基隆的噩耗之初,清廷内外还能保持冷静,认为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事情,并未追究刘铭传个人的责任。但当刘璈的蜚语传播后,舆论为之突变。一方面是左宗棠及一些言官推波助澜,以刘璈的禀报为依据,多次奏劾刘铭传。激烈的如左宗棠,将刘铭传比作丢失北宁的前广西、云南巡抚,要追咎他“失地辱国”的责任;宽容一些的言官,也认为清政府即使不予严惩,也应对刘铭传“从宽罢斥,解其兵柄。”企图动摇清政府对刘铭传的信任。另一方面,在议论纷纭之中,清政府也失去了对于台北战局敌强我弱形势的冷静分析,多次催促刘铭传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进攻和收复基隆,从而干扰了刘铭传“固守待援”的作战部署,造成进攻基隆的台北抗法军民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要不是清政府始终坚持信任刘铭传,以及刘铭传能够力排干扰,坚持不动用主力去作进攻基隆的无谓尝试的话,刘铭传的个人前程及台北抗法战争的结局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一面是刘铭传在台北前敌,率军与法兵反复鏖战,浴血奋斗;一面是刘璈躲在台南后方,公然违抗朝旨,按兵不救台北危局,反而播弄是非,制造混乱,干扰战局。清政府综览全局,把握事态,当然很容易就看到二刘行为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反差。十一月,当刘铭传电称刘璈意在掣坏台北时,清政府就指示他考虑撤换刘璈:“刘铭传身任巡抚,属员用舍是其专职。台南地方辽阔,刘璈统率台营办防,职任极重,如果可用,该抚当屏除畛域成见,督率妥办。如竟不得力,另易生手,不致贻误防务,即将刘璈撤去,派员接办,毋稍姑容。”〔32〕虽然刘铭传顾及当时的台湾战局及杨昌濬等人的反对态度,而没有立刻照办,但刘璈垮台的命运却是已定下来了。
光绪十一年三月,中法议和,台湾解严。四月,刘铭传以刘璈侵吞公款为由,将其撤任。后又专折严劾刘璈,并在奏报他事时词连刘璈,前后参款达二三十条。但清政府多未采纳,仅派刑部尚书锡珍等查处其中有关贪污的二三款,最后以刘璈父子侵冒公款二万六千余两结案,“已革台湾道刘璈著照所拟斩监候,即由该督抚派员解交刑部监禁,其应缴之款除抄产备抵外,余著勒限追究。知府刘济南素行不检,物议滋多,著一并革职。”〔33〕后刘璈改流黑龙江,死于戍所。
综上所述,可知刘璈的失宠,肇殆于筹划台防不力,招致法舰的侵扰,他的悲惨结局,虽由刘铭传的参劾而起,主要原因却是因他在台湾抗法战争中无功有过之故,可谓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注释:
〔1〕〔3〕〔19〕连横撰《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修订第二版,第648—649、645、288、647—648页。
〔2〕〔20 〕许雪姬撰《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转引自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编辑《历史研究》1987年第4 期《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4〕《沈文肃公(葆桢)政书》卷3,页40。
〔5〕〔6〕《左文襄公(宗棠)文集·书牍》卷23,页65、卷24,页29、39。
〔7 〕《岑襄勤公(毓英)遗集》卷17,页20。
〔8〕〔9〕〔13〕〔27〕《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634、1546、1640、2746页。
〔10〕〔11〕〔21〕〔29〕刘璈撰《巡台退思录》第3册,第256—257、262—263、267、285页。
〔12〕《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10页2。
〔14〕法国海军部档案BB—4,1961。
〔15〕〔25〕《中法战争》(三),第539、142页。
〔16〕〔22〕〔28〕《中法战争》(五),第409、504、576页。
〔17〕〔26 〕〔33〕《清德宗实录》(三),第493、630、 1056页。
〔23〕〔30〕《中法战争》(六),第360、140页。
〔24〕法国海军部档案BB—4,1968。
〔31〕《中法战争》(四),第221页。
〔32〕《光绪朝东华录》第1861页。
标签:左宗棠论文; 刘铭传论文; 连横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孤拔论文; 清代论文; 台湾通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法战争论文; 光绪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历史学论文; 史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