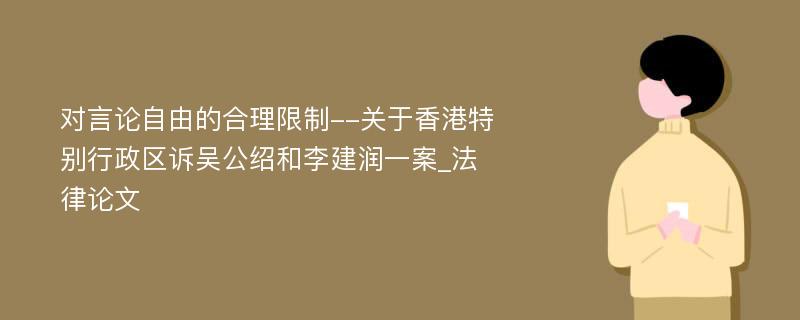
对于表达自由的合理限制——评香港特别行政区诉吴恭劭、利建润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论文,自由论文,利建润案论文,诉吴恭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特别行政区诉吴恭劭、利建润案(HKSAR v.Ng Kung Siu and Lee Kin Yun)于1999年11月22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受理并作出终审判决。该案因类似于著名的Texas诉Johnson案而引起广泛关注。两名被上诉人吴恭劭、利建润于1998年1月1日参与游行,游行期间他们手持涂污了的国旗及区旗,在游行结束时把涂污了的国旗及区旗缚在栏杆上。两人随即被控违反《国旗及国徽条例》(香港法例1997年第116号)(下称《国旗条例》)第7条及《区旗及区徽条例》(香港法例1997年第117号)(下称《区旗条例》)第7条,在初审法院被定罪及各判缴纳保证金2000元,并判处守行为规范12个月。两人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称其所行使的是表达自由的权利,并认为《国旗条例》和《区旗条例》违反了《国际人权公约》第19条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称《基本法》)第39条而无效。高等法院随即就这两条法律是否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和《基本法》进行检视,作出判决,称这两条法律违反《基本法》,并撤销对于两人的定罪。控方遂向终审法院上诉。一项刑事诉讼,因其涉及《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与法律是否违宪的问题,遂成为重要的宪法诉讼。
一、国旗和区旗:受到保护的象征符号
吴恭劭、利建润两人所违反的《国旗条例》和《区旗条例》所保护的是国旗和区旗的尊严。在1998年1月1日的游行中,两人手持的两面旗帜均被严重涂污。国旗的中央被剪掉一个圆形部分;大颗的五角黄星被涂上黑色墨水,星型图案本身更被刺穿。旗帜的背面也有类似的损毁情况。还有,旗帜上的其余4颗较小的星型图案,均被人用黑色墨水写上“耻”字,而在旗帜背面,4颗较小的星型图案之中位置最低的那一颗被画上一个黑色交叉。那面区旗则被撕去一截,失去部分紫荆花图案,该图案也被画上黑色交叉;余下四颗红星的其中3颗各被画上黑色交叉;旗帜被人用黑色墨水写上“耻”字;旗帜上面还有另一个中文字,但由于旗帜被撕毁,那个字已不能辨识。旗帜的背面也有类似的损毁情况。①《国旗条例》第7条规定:“任何人公开及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或国徽,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可处第5级罚款(即50,000元)及监禁3年。”《区旗条例》第7条规定:“任何人公开及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区旗或区徽,即属犯罪:(a)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第5级罚款(即50,000元)及监禁3年;及(b)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第3级罚款(即10,000元)及监禁1年。”
初审法院根据这两项法律,认定两人在游行中的行为构成了侮辱国旗和区旗的罪行,因此定罪处刑。然而在终审法院受理此案时,利建润的大律师提出,“没有证据显示,任何一位被上诉人公开以玷污方式侮辱该两面旗帜。控辩双方所同意的事实记载了两名被告人携带着或挥舞着涂污了的国旗和区旗,从铜锣湾游行至中环期间他们继续这样做,及于游行结束时两名被告人将该两面他们曾经挥动的旗帜缚在政府总部外的栏杆上。公开及故意展示破损或污损的旗帜并非刑事罪行。”②律师认为,两人的行为不应适用《国旗条例》第7条和《区旗条例》第7条,而应适用《国旗条例》第4条和《区旗条例》第4条的规定:不得展示或使用破损、污损、褪色或不合规格的国旗(区旗)。展示或使用污损的国旗的行为,并不是第7条所规定的刑事罪行。对此,终审法院大法官包致金作出回应:“本席无法接纳这论点。第4条的指令旨在给予那些欲对国旗区旗及国徽区徽表示敬意的人士一些指导。但是与此相比,第7条却截然不同,该禁止条文旨在保护国旗区旗及国徽区徽免遭蓄意侮辱。公开及故意在游行时展示一面经刻意选择的涂污了的旗帜或徽号,就是玷污这旗帜或徽号,亦因而侮辱了这旗帜或徽号。”
因此,从初审法院与终审法院对于两名被上诉人的行为的认定来看,其行为所影响的客体,是作为象征符号的国旗与区旗。它们不仅在香港受到《国旗条例》与《区旗条例》的保护,还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国旗法和刑法的保护。《国旗法》第19条规定:“公众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处罚规定,由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刑法》第299条则规定:“在公众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国旗条例》与《区旗条例》,实际是《国旗法》这一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1997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基本法》第18条第2款,将《国旗法》与其他法律一起增列于“附件三”的法律中,从而需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法律进行适用。因此,特区立法机关(当时的临时立法会)通过立法制定了《国旗条例》,在香港特区内实施。《区旗条例》则是直接由《基本法》第10条第1款及第10条第2款授权立法机关就使用及保护区旗事宜制定条文。因此,国旗和区旗受到法律保护,不仅来自于《国旗条例》和《区旗条例》,来自于本地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所传递的民意,还来自于国旗与区旗所表达的内涵:国旗象征着团结、统一和领土完整;至于区旗,如当时《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姬鹏飞称:“区旗是一面中间配有五颗星的动态紫荆花图案的红旗。红旗代表祖国,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花蕊上的五颗星象征着香港同胞心中热爱祖国,红、白两色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③因此,法院认为,对于国旗和区旗的保护和尊重,就全国和香港社会秩序而言,存在着重要的意义合法的公共利益。
辩方并未对这一合法公共利益的存在提出质疑,而是质疑这一合法利益的保护,是否应通过刑事手段实现。尤其是为了实现这一合法利益将限制《基本法》所确保的公民权利时,这一限制在什么范围内是合适的,而越过了哪一条边界,即成为了对于公民权利的干预。因此,争议的焦点即由国旗与区旗所代表的利益,转向了公民权利与自由及其合理限制的问题。
二、表达自由:基本权利及其边界
辩方认为,两名被告人在游行示威过程中,通过展示污损国旗和区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根据利建润所说,他是在表达对于非民选政府的不满。他们不过是在以某一种方式行使自己的表达自由。表达自由是受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保护的:“(一)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预之权利。(二)人人有表达自由之权利;此种权利包括以语言、文字或出版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它方式,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及思想之自由。”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通过《基本法》第39条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香港法例第383章)对于该公约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进行了适于本地的国内化。其中,《基本法》第39条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16条,亦用同样的文字对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所保护的表达自由,进行了毫无二致的表述。
显然,表达自由是受到《基本法》保护的基本权利。控方亦承认,此案确实与发表自由有关。法院在论及这一权利时,将其称为“民主社会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会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对其宪法性的保障必须采纳宽松的解释。这种自由包括发表大多数人认为令人反感或讨厌的思想,及批评政府机关和官员行为的自由”④。所谓宽松解释,即对于表达的内容不需要进行限制,即使是错误的、令人反感的、讨厌的思想,也应有表达的自由。因此,用侮辱国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使令社会大众反感或者讨厌,仍然受到有关“表达自由”的宪法性保障。如同当年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保护你说话的权利。”⑤
事实上,以侮辱国旗的方式来行使表达自由的案例,在世界各地都曾出现过。在美国最著名的是Texas诉Johnson案。1984年,共和党在达拉斯举行全国大会,詹森等大约100名反对里根当局的示威者,在大街上游行并高呼政治口号。当示威者来到市政厅门前,詹森接过一面美国国旗,使之浸上煤油并开始焚烧。示威者一边焚烧,一边欢呼歌唱:“美国——红、白、蓝,我们对你吐痰。”⑥而在此前,美国也曾发生过多起以侮辱国旗方式来表达思想或观点的案件。比如1969年的Street诉纽约州案:Street从广播里得知第一个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念书的黑人詹姆斯·梅雷斯遭到枪击,愤怒地走上街头,当众焚烧一面美国国旗,并向人们高喊:“我们不要他妈的国旗!”又如1966年的Radich诉纽约案:纽约市某画廊主人Radich因在画廊中展出了3尊美国国旗雕像而被捕。这3尊雕像分别为国旗包裹的子弹箱、人形的国旗吊在绳圈中、国旗包裹着男性生殖器状的东西。1970年5月的Spence诉华盛顿州案:西雅图的大学生斯彭斯在自家的楼上从窗口倒挂下一面美国国旗,并用胶带粘住国旗的两头,以表示反对越战并抗议政府对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开枪,他被控违反了华盛顿州的保护国旗法。Kime诉美国案:凯姆和他的伙伴属于“革命共产主义党”的成员,为了表达政治意见,在公众场合焚烧美国国旗。⑦在这些案件中,侮辱国旗被视为一种表达政治或社会观点的途径,并从属于表达自由的范围。
然而问题在于,表达自由并不意味着不受限制。如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在前两款确认缔约国公民享有表达自由之后,在第3款中特别说明,表达自由必须因某些原因受到限制:“(三)本条第(二)项所载权利之行使,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故得予以某种限制,但此种限制因由法律规定,且为下列各项所必要者为限:(甲)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或(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同样,《香港人权法家条例》也作了完全一致的表述。一个社会保障其成员的权利和自由,并非纵容其为所欲为,而是以明确可预期的法律来规定自由的范围。这个道理早在孟德斯鸠那里就说得很清楚:“自由是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⑧具体到表达自由而言,假如法律不对于自由的边界进行规定,看似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他可以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反对他意见的人也可以用更大的嗓音发表反对的意见。他只好用更高的声音来重申自己的观点。嘈杂声中,谁都无法听清别人的观点,谁的表达自由都无法真正实现。人们随后发现,只有采用轮流发言、轮流倾听的受克制的方式,表达和交流才可能真正实现。于是渐渐发展出固定的“发言—倾听”机制。而假如表达的方式或内容越过某一边界,从而使得潜在的倾听者不愿意再遵守“发言—倾听”机制,转身离开、堵住耳朵或者干脆用机制外的力量(可能是暴力,也可能是经济力量)让表达者“失声”,这样的情况下,表达者也无法实现自己传播观点的愿望。因此,无论是由丛林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化过程中出现的“发言—倾听”机制,还是在后世渐渐发展出的对于表达内容与方式的限制,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表达愿望而对于表达自由进行的克制与自我克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称这种合理的自我克制为表达自由的自我保护与自我实现。因此,当辩方提出表达自由受到《国旗条例》第7条与《区旗条例》第7条的限制时,辩方并未从根本上否认这种限制存在的意义,而是质疑用刑事手段来进行限制,是否超出了“合理”的边界,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从而使得表达自由受到了“过多”的限制。假如《国旗条例》第7条与《区旗条例》第7条的限制超过了合理的边界,那么它们的存在就不再有利于表达自由的自我实现和自我保护。因而将违反这个文明社会的核心理念,从而体现为违反基本法律规范(基本法、宪法)而被宣告无效。因此,对于表达自由之限制是否“过多”,即成为本案控辩双方及终审法院需要考虑的关键争议点。
三、表达自由之限制的正当性
首先,法院需要考虑的.是《国旗条例》第7条与《区旗条例》第7条所限制的到底是什么。香港政府认为,这两条法律所禁止的是侮辱国旗和区旗这一表达方式,而非禁止所表达的内容。而两名被上诉人则认为,这两条法律不仅禁止了一种表达形式,而且通过将一种政治抗议形式列为非法行为,也禁止了可以发表的内容。终审法院就这一点作出的判断是,政治抗议者侮辱旗帜,采取的是一种象征的或非语言的表达形式,或许是希望表达某些政治观点,但这种方式不必然能够表达某种清晰的信息。他希望表达的,可能是对一个国家的仇恨或反对,或是对当权政府的抗议;又或者该名有关人士欲对政府的一个现行政策表示抗议,或想表达某些其他信息。侮辱旗帜的表达方式与他希望传递的内容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即使在国旗或区旗上书写拥护赞美现存政治体制的文字,也会因构成对于国旗区旗的涂划而构成侮辱旗帜的行为,从而受到禁止。如同李国雄大法官判决书中所说:“有关条文不但禁止以这一形式发表抗议的信息,而且也禁止以这种形式发表其他信息,包括赞美的信息。”⑨无独有偶,2009年2月22日,深圳仙湖植物园内曾经出现了饱受争议的一幕。当日,一群在深圳打工的湖南怀化青年打算进行老乡聚会,但他们平时聚会时使用的“环化人聚深圳”的旗帜恰巧不在身边,他们便在一面国旗上书写了“怀化人聚深圳”的字样,以便公园内的其他老乡能够看到并参加聚会。⑩他们的行为显然符合侮辱旗帜的特征,但其传递的信息,却与政治抗议无关。此外,香港终审法院认为,对表达方式的限制,并不会影响两名被上诉人观点的传播。换句话说,两名被上诉人除了侮辱国旗这种不明确的象征方式之外,完全可以找到其他的、更有效率的传递抗议信息的方法。因此,禁止侮辱国旗,所进行的并不是一个广泛的、对表达内容的限制,而仅仅是对于表达形式的禁止性规定。
其次,法院需要讨论的是,这种对于表达方式的限制,是否具有其《基本法》上的正当性。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3款,对于表达自由的限制需要符合以下两个条件才可被视为“合理”。第一,以法律的形式进行规定。第二,限制目的为:(甲)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或(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在本案中,《国旗条例》和《区旗条例》均属于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而第一项条件不难达到。这两项法律禁止侮辱旗帜,其目的应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3款(甲)项“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无关。因而,能否证明禁止侮辱国旗区旗与(乙)项“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之间的关系,成为对表达自由之限制是否合法的关键。
终审法院对于这一关系的证明相当慎重。首先,法院根据“明报报业有限公司对香港律政司一案”(Ming Pao Newspapers Ltd v Attorney-General)确定的规则,认为在考虑对于表达自由进行限制时,必须对于限制的范围进行狭义解释。即,“除非限制的范围狭窄而明确,否则根本不可能把此种限制视为与此种权利或自由兼容”(11)。比如说,假如政府一方只是笼统地说“为了维护公共秩序、社会公德”,而不能说明是哪一项“狭窄而明确”的“公共秩序”或“社会公德”时,这样的限制是不合法的。(12)其次,控辩双方都认为,证明“禁止侮辱国旗”与“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之间的关系,需要由政府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及控辩双方都认为,自由是理所应当的,对于自由的限制则是一种例外。因而政府需要对这种例外进行特别的证明。
因此,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麦高义先生提出,禁止侮辱国旗区旗这一项限制,是出于“保障公共秩序[public order(ordre public)]”的需要。(13)法院就此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何为这里所说的公共秩序[public order(ordre public)]?其与单纯的public order有何不同?第二,这里所说的公共秩序(ordre public)与本文第一部分法院所承认的国旗区旗的合法利益之间有何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法院认为,所谓公共秩序[pub-lic order(ordre public)],其概念并不局限于公共治安范畴之内。这一点已经由“谭庆义诉胡大伟案(Tam Hing-vee v Wu Tai-wai)”、“律政司司长诉东方报业集团有限公司一案(Secretary for Justice v Oriental Press Group Ltd)”以及“黄阳午诉律政司司长案(Wong Yeung Ng v Secretary for Justice)”等判例得以证明。“public order(ordre public)”较“public order”的意义更为丰富,不只是普通法传统上的公共治安之概念。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麦高义先生提请法院注意“律政司司长诉东方报业集团有限公司一案(Secretary for Justice v Oriental Press Group Ltd)”判决中的一段话:
“保障……公共秩序……条文把括号内的字眼(ordre public)也包括在内,显示应给予“公共秩序”这词一个比在普通法适用地区通常对该词所理解的更为广泛的涵义。‘公共秩序’这词的涵义应包含欧洲律师所熟悉的ordre public的概念。……在公法范畴内:……ordre public的意思包含国家组织的存在及运作,不仅容许国家组织在国内维持安宁及秩序,也透过满足集体需要及保障人权从而确保公众福祉。法院是‘国家组织’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机构。法院是法治的化身,在满足社会‘集体需要’及保障‘人权’方面担当关键角色。一旦为‘public order’下如此定义后(即该词并不限于防止骚乱),依我等之见,第16条第3款(乙)段中‘保障…公共秩序’一词显然包括维护法治这一概念,至少在公众对适当执行司法工作的信心被削弱以致法治遭破坏的情况下是如此……”(14)
法院随后援引了多项资料,来说明公共秩序[public order(ordre public)]不仅包括公共治安,还包括公共机构的妥善运作,为维持社会安宁及良好秩序而制定法规、安全、公共卫生、美学及道德层面的考虑及经济秩序(消费者权益的保障等)等等。(15)法院引用1984年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关系》内自由之克减的“锡拉库扎原则”(The Siracusa Principles)对于“公共秩序[public order(ordre public)]”一词的论述:“在‘该公约’中,‘公共秩序[public order(ordre public)]’一词可界定为确保社会运作的规则的总体或建立社会的一套基本原则。”(16)以及1986年美洲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发表的第6/86号咨询意见(Advisory Opinion No.DC-6/86):“制定法规必须以公众利益为依归,这要求是指这些法规必然是为了‘公众福祉’才获通过[第32(2)条]。这概念在民主社会必须诠释为属于公共秩序[public order(ordre public)]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类必不可少的权利,并创造环境让人类获得精神及物质上的进步和幸福。”(17)因此,社会安宁、良好秩序特别是公共机构的妥善运作,可以视为公共秩序[public order(ordre public)]的应有之意。
至于第二个问题,国旗区旗保护之利益是否包含在上述公共秩序[public order(ordre public)]之中,法院特别强调,在1997年7月1日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已经处于全新的宪制秩序,国旗所象征的国家统一、区旗所象征的一国两制,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公务机关之妥善运转有着特别的意义。假如国家统一与港人治港的基本原则受到冲击,那么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都将受到影响,通过政府努力而实现的社会安宁、大众福祉及整体利益,也会受到影响。因而,对于国旗区旗的保护应受到公共秩序[public order(ordre public)]这项更高价值的支持和保护。
由此,法院得以证明,《国旗条例》和《区旗条例》禁止侮辱国旗区旗,作为对表达自由的方式施加的限制,因其对于公共秩序[public order(ordre public)]有着具体的合法利益,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3款(乙)项的要求。其属于对于表达自由的正当限制,未违反《基本法》第39条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因而合宪有效。
四、结语
或许是因为与著名的Texas诉Johnson案的结局不同,香港特别行政区诉吴恭劭、利建润案并未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Texas诉Johnson案曾被贴上“星条旗保护焚毁它的人”的华美标签,一度令许多学者心向往之。相比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诉吴恭劭、利建润案的判决似乎显得不那么“勇敢”,不那么“保护人权”。再加上判决对于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之区分语焉不详,对于比例原则的证明也不够细致,似乎并不是那么值得重视的判例。
然而细读该判决之后,判决中另一些价值浮现出来。一方面,终审法院对于表达自由的保护,未因这一判决而受损。通过区分对于表达方式的限制和表达内容的限制,法院发展出新的规则。当限制仅仅局限于表达方式时,所需要证明其正当性的程度相对较低,而当表达方式之限制可能影响表达内容时,其所需要的证明程度相对较高。如包致金法官在判决的协同意见中所说,“依本席之见,本港两条保护国旗国徽及区旗区徽免遭公开及故意侮辱的法例……完全没有对人们可以发表的内容施加限制。甚至关乎人们可以用何种发表形式这方面,法例所施加的唯一限制,只是禁止侮辱一些即使没有法例禁止,人们连做梦也没想过要侮辱的对象而已。这限制不会压制任何思想的表达。不论是政治意见的坦率表达,还是任何其他意见的坦率表达,都不会因此而受到抑制。”(18)另一方面,终审法院表现出了与其最高法院位置相应的审时度势与大局观。其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早在10年前通过Texas诉Johnson的经典判例,树立了“权利保护者”的形象。假如香港终审法院依样画葫芦,简单地以“表达自由”作为判决理由,宣布《国旗条例》和《区旗条例》违宪无效,这并不困难,也能得到法学界的支持,甚至有希望在华人世界里也树立起Texas诉Johnson案一般的经典。然而他们考虑得更多。在判决书中,终审法院多次提到,香港处于新的宪制秩序下。尽管这种宪制秩序还不稳定,但其基本特点是:必须考虑到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其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地位,决定了其必须力求统一与自治之间的平衡。香港所处的宪制秩序与美国是不同的,与回归前也是不同的。终审法院所考虑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表达自由”及其限制,他们所遵循的“宪法”,也不仅仅是《基本法》,而需要更多地考虑香港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这一判例的价值,或许还将在未来的香港与内地关系中得到更多的揭示。
注释:
①HKSAR v.Ng Kung Siu and Lee Kin Yun,FACC4/1999。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ju/ju_body.jsp?DIS=18937&AH=&QS=&FN=&currpage=,2009年6月2日访问。
②HKSAR v.Ng Kung Siu and Lee Kin Yun,FACC4/1999。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ju/ju_body.jsp?DIS=18937&AH=&QS=&FN=&currpage=,2009年6月2日访问。
③姬鹏飞:《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及其有关文件的说明》,http://www.law-lib.com/fzdt/newshtml/20/20050722182744.htm,2009年6月1日访问。
④HKSAR v.Ng Kung Siu and Lee Kin Yun,FACC4/1999。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ju/ju_bodyjsp?DIS=18937&AH=&QS=&FN=&currpage=,2009年6月2日访问。
⑤然而有趣的是,后世有一种说法认为,伏尔泰并没有说这句话,这句话是Evelyn Beatrice Hall于1906年出版传记《伏尔泰的朋友们》中表达伏尔泰主张时所记下的。参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F%E7%88%BE%E6%B3%BO,2009年6月1日访问。
⑥张千帆:《美国经典案例:〈焚烧国旗案〉》,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3179,2009年6月1日访问。
⑦邵志择:《表达自由:言论和行为的两分法——从国旗案看美国最高法院的几个原则》,载《美国研究》2002年第1期。
⑧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⑨HKSAR v.Ng Kung Siu and Lee Kin Yun,FACC4/1999。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ju/ju_bodyjsp?DIS=18937&AH=&QS=&FN=&currpage=,2009年6月2日访问。
⑩《关于“网友曝光湖南怀化公园某人侮辱国旗(图)”一文的道歉信》,载http://bbs.news.163.com/bbs/photo/120845397.html,2009年6月1日访问。
(11)请参见包致金法官的协同意见,HKSAR v.Ng Kung Siu and Lee Kin Yun,FACC4/1999。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ju/ju_body.jsp?DIS=18937&AH=&QS=&FN=&currpage=,2009年6月2日访问。
(12)相比之下,我国内地法院的判决常常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条之规定,判决吉某夫妇可以行使隔代探望权,黄女士须予以协助”(河北承德法院:有关隔代探望权的判决)的笼统之语。法院在对于父母的监护权进行限制时,仅仅是以《民法通则》第7条的“社会公德”为限制目的,而丝毫没有说明是哪一项具体的社会公德,更不用说对于某一项“狭窄而明确”的社会公德与监护权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证明。参见阿成、杨秀莲、张火旺:《看望孙子引出探视权纠纷》,载《法制日报》2003年6月第5版。
(13)ordre public为法语,法院认为其不同于普通法传统中的public order,具有更多的意涵。
(14)律政司司长诉东方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案(Secretary for Justice v Oriental Press Group Ltd),[1998]2 HKLRD 123,第161页。
(15)参见A.C.Kiss,"Permissible Limitations on Rights",Louis Henkin(ed.),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The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p301.
(16)Human Rights Quarterly,1985.7,p3~14.
(17)Human Rights Law Journal,1986.7 ,p231.
(18)同注(11)。
标签:法律论文; 公共秩序论文; 国旗论文;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论文; 香港区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