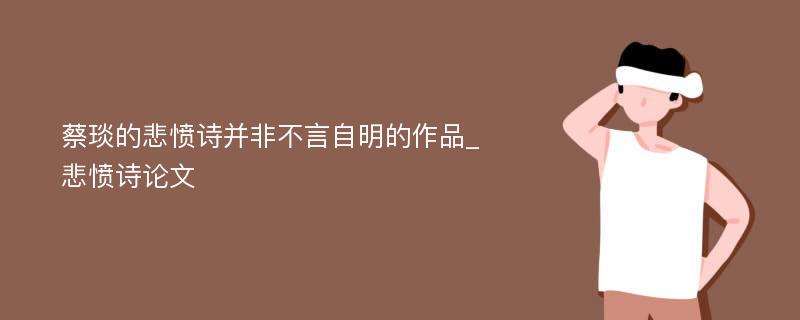
蔡琰《悲愤诗》非自述身世之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愤论文,之作论文,自述论文,身世论文,蔡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苏轼提出《悲愤诗》非蔡琰所作的观点以后,后来的人们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意见不一。现代学者大多倾向于五言《悲愤诗》为蔡琰所作,并认定这是蔡琰的一篇自述身世之作,有人干脆称之为“自传体”作品。笔者通过对《悲愤诗》进行认真的解读,并考察当时的历史事实后认为:蔡琰对《悲愤诗》的著作权固难否定,但此诗并非蔡琰自述身世之作。
苏轼在其《题<蔡琰传>》中说:
今日读《列女传》蔡琰二诗,其词明白感慨,颇类世传木兰词,东京无此格也。建安七子,犹涵养圭角,不尽发见,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离,必在父死之后。董卓既诛,伯喈乃遇祸。今此诗乃云为董卓所驱入胡,尤知其非真也。盖拟作者疏略,而范晔荒浅,遂载之本传,可以一笑也①。
在这里,苏东坡提出两个理由证明《悲愤诗》非蔡琰所作:一是《悲愤诗》明白感慨,不似东汉诗风格;一是既然蔡琰是为匈奴所掠,但“此诗乃云为董卓所驱虏入胡”。这两点都很有意思,特别是第二点,可说是解读此诗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但此两点都不能证明此诗非蔡琰所作,却可以说明,此诗并非蔡琰自述身世之作,而是蔡琰对汉末战乱中广大妇女悲惨遭遇的巧妙概括和形象表现。以下将依照人们对此诗惯常的解读方法,结合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判断。
全诗可分三部分。开头四十句为第一部分,叙写董卓部下滥杀百姓,掳掠妇女财物。这当是蔡琰亲眼目睹,至少是亲耳所闻。据《后汉书·董卓传》载,董卓入朝后,骄僭跋扈,残暴凶恶。“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又“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后文又说:
初,卓以牛辅子婿,素听亲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②。
董卓是陇西临洮人,其部下将领也大都是西北边地人,如李傕是北地人,郭汜是张掖人,他们所率将卒也大多是羌胡人。这一点史有确证。《后汉书·董卓传》载:“(中平)六年,征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③蔡琰诗中叙述:“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这些恰与董卓部下暴行相符。蔡氏乃陈留大族,董卓入朝当权,蔡邕因名重天下而得到董卓的敬重和提拔。蔡邕无子④,当时虽然仓猝入朝,他也极有可能携爱女文姬一同入京任职,即使文姬未随父入京,董卓的部下也决不至于胆敢公然劫掠蔡邕之女。因蔡邕不仅名满天下,且当时正受到董卓宠重,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又荣封高阳乡侯。那么,蔡琰不在诗中所写的遭难妇女之中,当无可疑。但董卓部下劫杀淫掠家乡陈留的暴行,蔡琰肯定是或亲眼目睹,或亲耳所闻的。她用悲悯哀伤的笔触,记下这令人碎心断肠的情景。
宋蔡宽夫在其《诗话》“蔡琰诗”条中反驳苏轼说:
《后汉·蔡琰传》载其二诗,或疑董卓死,邕被诛,而诗叙以卓乱流入胡,为非琰辞(郭绍虞案:此指东坡语)。此盖未尝详考于史也。且卓既擅废主,袁绍辈起兵山东,以诛卓为名,中原大乱,卓挟献帝迁长安,是时士大夫岂能皆以家自随乎?则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诛之后。其诗首言:“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共欲诛不祥。”则指绍辈固可见。继言:“中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纵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则是为山东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则邕尚无恙,尤亡疑也⑤。
苏轼提出的问题,实有灼见,蔡宽夫指责苏轼“未尝详考于史”,实则他自己既不知历史,又未读懂蔡琰的诗作。他一则依据蔡琰诗的叙事,说“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诛之后”,又曲解蔡琰的诗句,说蔡琰“是为山东兵所掠”。难道蔡琰是被山东兵所掠而入胡的吗?诗中明明说“来兵皆胡羌”,难道山东兵可以称为“胡羌”吗?追究蔡宽夫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也把这首诗看作是蔡琰的自述身世之作。否则,他就不会依据“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之句而说蔡琰入胡时,蔡邕尚无恙了。
其实,历代都有文人学者因为误将蔡琰《悲愤诗》看作是自述身世之作而得出不恰当甚至错误的结论。如当代学者陆侃如便在他的《中古文学系年》中将蔡琰入胡的时间定为献帝初平元年。他引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之说:
沈钦韩曰:《南匈奴传》:灵帝崩,天下大乱,于扶罗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寇河内诸郡……玩文姬诗词,则其被掠在山东牧守兴兵讨卓,卓劫帝入长安,遣将徐荣、李蒙四出侵掠,文姬为羌胡所得,后乃流落至南匈奴也。时邕尚在,故有“感时念父母”之语。其赎归也,家门灭绝,故有“既至家人尽”语。此当为初平年事,传云兴平非也。兴平则李、郭之乱,非董卓矣⑥。
沈钦韩也将蔡琰《悲愤诗》看作是自传性作品,于是他根据诗中的叙述,断定蔡琰是先为董卓所派四出劫掠的羌胡兵所得,后乃流落至南匈奴的。这比蔡宽夫说得圆满一些,但试想此时蔡邕正得到董卓的宠重,连连提升,甚至被封为侯,他的爱女竟会为董卓的部下所掳掠,以至流落匈奴,这可能吗?沈钦韩也像蔡宽夫一样,依据“感时念父母”之语,认定文姬入胡时蔡邕尚在。这些都是因为误读蔡琰诗意所致。陆侃如引用王先谦、沈钦韩的话而未加讨论,说明他也是同意他们的意见的。
第二部分次四十句,叙写被掠妇女不习惯边荒之地的生活,她们思念父母家乡,期盼着能早日回归故里。因为羁留太久,有些妇女生有孩子。当有人侥幸被亲人接回时,又要面临骨肉分离的痛苦。关于这一段的内容,通行的看法是写蔡琰在南匈奴的生活及被赎回时的情景。如余冠英在其《汉魏六朝诗选》中总结此段大意说:“次四十句叙在南匈奴的生活和听到被赎消息悲喜交集以及和‘胡子’分别时的惨痛。”这是人们在读了《后汉书·蔡琰传》,又误读了本诗第一部分后的曲解。董卓的羌胡兵,烧杀劫掠,但他们把妇女当作财物保留下来,或随军享受,或运回老巢。如《后汉书·董卓传》载,董卓被杀后,其部将李傕等人遣使乞求朝廷赦免,未获允许。贾诩劝其攻打长安,于是“各相谓曰:‘京师不赦我,我当以死决之。若攻长安克,则得天下矣;不克,则钞三辅妇女财物,西归乡里,尚可延命’”⑦。董卓久处羌中,中平元年又因功封为斄乡侯,故西部羌胡地区是他的大本营。董卓未败之前,他的部下很可能已将大量妇女财物运回老巢,为将来退守故地打算。蔡琰诗中所写,正是这些被董卓将卒劫掠到西部边地的妇女。这些不幸的女性,被迫远离家乡父母,有的失去丈夫子女,在边远荒凉之地,经受奴役的苦辛,甚至遭受肉体的蹂躏,而当有人侥幸被赎回的时候,在同伴们羡慕她终于可以离开这伤心之地的时候,她又要经受骨肉离别的哀伤。“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正是说偶然、侥幸有人得遂心愿,有亲人来接回自己。此处“邂逅”一词最可注意。蔡琰的诗,正是要反映战乱加予广大妇女身心之上的无限痛苦与哀伤。
第三部分最后二十八句叙述侥幸得归的妇女归途中的感伤和回家后的凄凉。此处所描述,乃战乱中遭受流离之苦的妇女悲惨情景的典型概括,而非叙写蔡琰自己的遭遇。因为这里的叙述描写与蔡琰当时身世遭遇情景不合。理由有二。其一,蔡氏是陈留大族,本传载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灵帝时,蔡邕为议郎,其叔父蔡质为卫尉。后蔡邕得到董卓的敬重和提拔,“邕恨其言少从,谓从弟谷曰:‘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⑧是其叔父从弟皆在朝做官。由此可知,蔡氏家族庞大,其在朝廷也有一定势力。蔡邕罹难,未闻累及家属,则陈留蔡氏家族未受大损。如此说来,蔡琰还家时,如何会有“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的情况?其二,曹操既然顾念自己与蔡邕的亲密关系而将蔡琰赎回,必然会给予她妥帖的照顾,定然不会让她“茕茕对孤影”,悲苦无所依靠。所以,这一部分叙述的是有的被掠妇女虽然侥幸能还归家乡,但面对的却是家人丧亡,园舍榛芜的情景。她们哀伤欲绝,孤苦无告,不得已改适他人,又担心因为自己的被掠流离而遭到嫌弃。
由以上分析可知,蔡琰的《悲愤诗》叙写的是汉末战乱中广大妇女所经历的无比曲折悲惨的遭遇及她们在肉体和心灵上承受的巨大痛苦。因为融进了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感,所以诗歌写得格外沉痛感人。
文章说到这里,就自然地引出了两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第一,蔡琰为胡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问题。
关于蔡琰没入匈奴的问题,除《后汉书·列女传》的记载以外,最直接的证据便是建安时期曹丕与丁廙的两篇《蔡伯喈女赋》,按情理来说,曹丕的赋要比范晔《后汉书》的记载更为可靠。可惜曹丕的赋仅剩一短序,且连此序也不知是否完整。其中说:“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壁,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都尉使者。”⑨此文说得比较笼统、模糊,若将此文与《后汉书·列女传》的记载相比较,就会发现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蔡琰为胡骑所获之事容或有之,但谓其没入南匈奴左贤王,则很令人怀疑。我们若考察一下《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便可证明这一点。其中记载:
持至尸逐侯单于于扶罗,中平五年立。国人杀其父者遂畔,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而于扶罗诣阙自讼。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而兵遂挫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止河东。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单于于扶罗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单于呼厨泉,兴平二年立。以兄被逐,不得归国,数为鲜卑所钞。建安元年,献帝自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与白波贼帅韩暹等侍卫天子,拒击李傕、郭汜。及车驾还洛阳,又徙迁许,然后归国。二十一年,单于来朝,曹操因留于邺,而遣去卑归监其国焉⑩。
由这段记载可知,南匈奴在灵帝中平年间至献帝建安二十一年这段时间里,除单于于扶罗即位之初,因国人叛乱,向汉廷求助而不得,遂趁天下大乱之机而寇掠河内诸郡以外,在其他时间里,与汉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甚至帮助汉朝军队对付董卓余党,翼卫天子。建安二十一年之后,更直接为曹操掌握大权的汉朝所控制。汉献帝兴平只有二年,在此前后的几年里,未见有南匈奴抄掠的记载,不知蔡琰是何时为南匈奴所掳掠,最有可能的时间就是李傕、郭汜等人攻入长安,董承、杨奉招引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共同对付李傕、郭汜的这段时间。这里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从他在这一段时间里的活动情况看,他应该是南匈奴仅次于单于的第二号人物,也就是说,他应该就是南匈奴左贤王。因为匈奴左贤王是国君储副。事实上,《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去卑正是南匈奴左贤王:
(兴平二年)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舆,战于东涧,王师败绩,杀光禄勋邓泉、卫尉士孙瑞,延尉宣播、大长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声校尉沮儁。壬申,幸曹阳,露次田中。杨奉、董承引白波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率师奉迎,与李傕等战,破之(11)。
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蔡琰正是在兴平年间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这与上引材料正相合。可问题是,根据《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去卑作为左贤王一直留在汉庭,直到建安二十一年南匈奴单于呼厨泉来朝,曹操才扣留单于而遣去卑归监其国。如果身为天下名士、高阳乡侯蔡邕之女的蔡琰归于身为南匈奴储副的去卑,这应该不是一件小事,为什么史书上一点记载也没有?去卑就在汉庭,如果蔡琰嫁给了左贤王去卑,曹操想赎回,何必派人持璧去匈奴?根据以上论述,笔者认为,蔡琰或许真的在董卓被杀、蔡邕遇难后的长安之乱中被匈奴人虏掠过,但绝不是归于左贤王,而且她并未在匈奴滞留很久,很快即被赎回。
第二,关于蔡琰滞留胡中十二年并生有二子问题。
上文已经论证,蔡琰没入匈奴之事容或有之,但她未尝嫁给南匈奴左贤王,也没有在匈奴滞留太久,更不可能生有二子。笔者认为,《后汉书·列女传》中的记载,是范晔误读了蔡琰的作品,将《悲愤诗》看作是蔡琰自述身世之作,因而想当然地认为,既然生有孩子,那么停留匈奴的时间必然不会太短,于是由误解而推测,或许还加上传说,便认定蔡琰停留匈奴十二年,并生有二子。试想,如果蔡琰与南匈奴左贤王生有二子,那么这两个孩子将来至少也是匈奴王子,历史上为什么没有一星半点的记载?王昭君以普通宫女嫁匈奴单于,其子女尚明记在史,蔡琰以名士、公侯之女,自己又是旷世才女,她的儿子为何没留下任何记载?再有,蔡琰的时代,虽然儒家礼教对妇女的约束尚不严,妇女再嫁尚属寻常之事,但流落异族并生有孩子,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以蔡琰这样的大家之女,当不至于将这种事发露于诗作之中。苏东坡曾说到蔡琰的《悲愤诗》“明白感慨”,不够含蓄,实际上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由上论述可知,蔡琰滞留匈奴十二年并生有二子之记载,是范晔误读蔡琰作品的结果。范晔乃刘宋时人,其时距东汉已数百年,故而范晔之《后汉书》,多采野史、传说入传,其人物事迹多有不相连属甚至扞格难通之处,也多有虚假不实之记载,这一点,前辈学人早已指出过。《后汉书》有关蔡琰生平和创作情况的记载,也同样存在着很多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合理地解读和接受蔡琰的作品。
注释:
①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集·苏轼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8、5569页。
②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25、2332页。
③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第2322页。
④范晔:《后汉书》卷六十《蔡邕列传》,第2002页;卷八十四《列女传》,第2800页。
⑤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8页。
⑥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页。
⑦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第2333页。
⑧范晔:《后汉书》卷六十《蔡邕列传》,第1980、2006页。
⑨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四,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页。
⑩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2965页。
(11)范晔:《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第3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