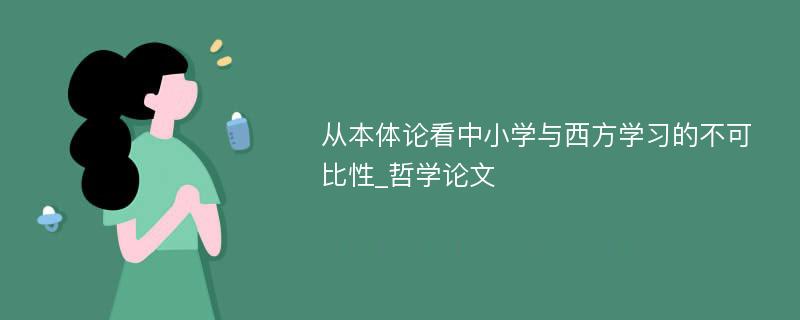
从Ontology看中学与西学的不可比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可比性论文,Ontology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1)02-057-008
任何一个研究过西方哲学的人都知道,ontology(中译万有论,存在论,本体论等等)是西方哲学两千年来的一个核心范畴。自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以“存在”(是)与“非存在”(非是)作为区分真理的道路与意见的道路的标准以来,“存在”(是)就已成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家的核心问题。在西方中世纪哲学中,在从笛卡尔到休谟的近代哲学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直是一切哲学认识论的前提。同时,它无疑也是康德以后德国古典哲学的中心:通过回答关于彼岸世界的ontological argumentation(本体论的证明)的问题,康德试图为未来形而上学开辟新路;黑格尔将“哲学”这门科学分为三部分,即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三个部分都研究“存在”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且不说像雅斯贝斯、海德格尔、萨特等公认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以ontology为哲学的中心,而且许多其他的哲学家也是以ontology为其哲学的中心课题之一。如胡塞尔、哈贝马斯都曾将自己的哲学称为“生活世界的本体论”(ontology of life-world),维特根斯坦、蒯因则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了“是”及ontology的问题。
为什么ontology会成为两千年来西方哲学的中心范畴呢?本文认为这既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寻求普遍性的结果,也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西方语言的独到特征,而是希腊哲学自从泰勒斯以来求“是”或以事实判断为前提的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本文认为,如果我们用“是”和“应该”分别代表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及中西方学术思想在出发点上的一个根本差异的话——前者以事实判断为前提,以求“是”、求“知”为特征,后者则以价值判断为前提,以求“应”(该)、以“做”(又可称为“行”,包括做人、践履、身体力行、安身立命等)为特征——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发现西学与中学在发展过程及其后果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看来不可思议的差异均可从中找到答案,而且更重要的是,西学与中学之间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不可比的。
一、ontology=“是”之学
让我们先从ontology一词之本义开始讨论。Ontology一词在学术界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译法,本体论、存在论、生存论、万有论、有论、是论等等不一而足;从词源上讲,ontology来自希腊语onta一词,该词又是由希腊文on演变过来的。On常译为英文being,而onta在英文中可译为beings,在中文中常译为“是者”,“在者”、“存在者”、“存在物”等。它们都与另外几个更加基本的、表示“是”的希腊文字母eimi(=am),estin(=is),einai(=to be)等相关[1-p23~24;2-p77~80;3-p419~437]。希腊文中又有to on一词,一般译为being,但不少学者均以为该词相当于德文中的Das Seiende,英文中当译为what is或that which is而不是英文being[3-p428;4-p173,178]。由此可见,古希腊以来的ontology实即“是”之学。要理解希腊以来的ontology,关键在于搞清希腊文中的“是”是何义(注:俞宣孟新著《本体论研究》称“本名ontology所指的内容是以‘是’为其核心范畴的、逻辑地推论出来的范畴体系。中国哲学中并没有这样的内容。然而‘本体论’这个译名却很容易将人引向另一类内容,即以为它是关于本根、本体、体用等的学说。于是人们误以为中国哲学史中也存在着类似西方ontology的部分,甚至把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当作专题作肯定的研究。这真是谬种误传了。这种误解的要害是把‘本体论’这个名称中所包含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特殊形态和思想方法掩盖掉了”(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573),此言甚是。)。
希腊文中的“是”(eimi,estin,einai),学术界一般皆以为同时有中文“是”“有”、“在”或“存在”等意义。维特根斯坦曾指出,“是”“作为联系词,作为等号,作为存在的表达而出现”[5-p34]。俞宣孟指出该词兼有存在、本质、真理三个规定性[6-p12],赵敦华先生则分析了在西方哲学史上人们是怎样分别在“是(系词)”、“有(本质)”、“在(存在)”这三种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的[7-p331~417]。谢遐龄先生认为“是”(ist,德文)有五重含义;“正号(肯定),等号,从属于××集合;系词,存在”[8-p271]。其实他所讲的五个方面中“正号”、“等号”、“从属于……”、“系词”四者在使用时均是以系词出现的,而“是”表述本质时也是用作系词。但是如果我们把“是”在希腊文中的用法归纳成作“系词”使用和表达“存在”两个方面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西方语言中的“是”在作系词使用时本身即可表达存在[9-p1~p18](注:西方学者有关“是”及ontology的观点参Paul Edwards(ed.in chief),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 The Free Press,London: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1967),volume five,pp.542-54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323,页34;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页1-18,等。)。
本文认为,“是”在希腊哲学中的含义有如下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首先,“是”代表最大的共相,或称之为最大的普遍性。陈康先生在《巴门尼德斯篇》译注中曾举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他说:“设以‘甲’代表‘每一个’,‘甲’是‘子’、‘甲’是‘丑’,‘甲’是‘寅’……‘甲是’决不同于‘甲是寅’。正如‘甲是’不同于‘甲是寅’,它也不同于‘甲是子’,‘甲是丑’……中的任何一个。‘是’和‘是子’、‘是丑’、‘是寅’……的分别,乃是前者是分化了的,后者是未分化了的。‘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代表一个范畴,‘甲是’事实上表示‘甲’+‘是’,即‘甲’和范畴‘是’的结合。”[10-p107~108]
其次,尽管希腊文中的“是”有多种不同含义,但是在实际使用时这些不同的含义之间其实并不总是区分得很清楚,毋宁说在希腊哲学家看来“是”的多种不同含义之间是内在地相互关联的,尤其是“是”作系词使用时有时可以表达本质,有时也可以表达存在,有时同时表达本质、存在及属性等多种不同含义。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家中首次对“是”的含义进行全面总结的哲学家,他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第七章分析“是”的四种不同的含义——属性、范畴、真假、潜能与现实——时,就没有将“是”作系词用与“是”表示存在两种用法区别开来[11-p57]。
最后,“是”在古代还有一些今人所不知的特殊含义。海德格尔对这个问题作过较深入的剖析[12-p71~72]。根据陈村富先生的总结,在印欧语系中,“是”的词根有两个。一是"es",原来的意思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能运动、生活和存在”;另一个是"bhu"、"bheu",原来的意思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能自然而然地生长、涌现、出现。”在希腊语中,es词根的eimi,后来变成系动词“是”,而后一个词根最后变成physis(自然、本性)[13-p610;12-p23]。
二、求“是”是希腊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特征
“是”为什么会成为希腊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呢?有的学者曾提出这是由于希腊哲学家用它来指称各种现象之间的统一性[14-p124]。然而问题似乎并不如此简单,因为追求各种不同现象背后的统一性乃是人类所有伟大文化中的共同主题,但是这些不同的文化最终却走向了一系列迥然不同的道路上去了。另有不少人认为导致“是”成为希腊哲学主要范畴的原因是希腊语的特殊语言结构,即系词“是”本来在希腊语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而这一现象在汉语等其它语言中并不存在。然而这一解释其实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就“是”这个单词的用法来说,人类其它一些伟大文明的语言中并不是没有与希腊语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它们却没有走上希腊哲学同样的道路。例如希腊语属印欧语系,其中的“是”(eimi)字是从印度日耳曼语中的词根es而来的,其语法结构当与印度语相类[12-p70~72];陈村富先生更指出,“在拼音系统的文字中,大体上最后都形成了一个最通用的系词。”[13-p611]因此,我认为要找到上述问题的真正答案需要从思维方式上入手,即希腊哲学家们在使用“是”这一术语时是从什么思维方式出发的,而不能单纯地停留在所谓“追求统一性”或语言、语法结构问题上。
我们注意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即伦理学中以“是”和“应该”为标准所区分的两种判断。即表示“事物实际上是什么”的事实判断和表示“事物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前者揭示事物的“实然”状态,以求“知”为特征;后者表达事物的“应然”状态,以求“用”为特征。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说“此人是位老师”时,就是一个事实判断;而当我们说“此人是个畜生”时,却是一个价值判断。因为我们必先有“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之价值前提,才能下此判断。从事实判断的角度讲,我们不能说此人不是人,但从价值判断的角度讲我们却可以这么说。可见既不能以事实判断来否定价值判断,也不能以价值判断来代替事实判断。现在我们先来说明希腊哲学中的求“是”传统:
首先,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寻求世界的本原(或译作始基、基质、元素等)几乎是所有哲学家的共同目标。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总结,本原就是万物由之产生又复归于它的那个东西,它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本体”。“本体”一词在希腊文中写作ousia,该词是从另一个希腊文单词oua演变而来。Oua在希腊文中是“是”(eimi)的阴性分词,与英文中的being相当。后面我们将谈到,ousia这个术语并非亚里士多德自创,在柏拉图的著作里它是“理念(eidos/idea)”的别名。汪子嵩说,ousia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是其它范畴的主体(hypokeimenon,在背后或底下的东西,一般译为‘载体’或‘基质’,即‘是的东西’),通过拉丁文翻译成为substance,我们主张译为‘本体’。‘本体’的意思也是‘是的根本’或‘基本的是’。”[1-p24]可见亚里士多德的话是想表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试图描绘或发现“世界实际上是什么”。
其次,从寻求本原(始基)的cosmology(宇宙论)发展到直接思考“是”的ontology,希腊哲学在思考本原的方式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从对可感世界的经验归纳中寻找世界本质上“是”什么,发展到从思维的逻辑规则中去寻找世界本质上“是”什么[8-p20]。巴门尼德首先提出“能被思想的与能‘是’的是一样的”[3-p428~429]的著名论断。正是由于巴门尼德的发现,苏格拉底、柏拉图苦心孤诣地试图通过对概念的精确定义找到世界本质上“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竭诚于综合辩证,他以‘这是什么’为一切论理(综合论法)的起点,进而探求事物之怎是。”[11-p266]而到了柏拉图,则更是如此:在柏拉图哲学中,“是(estin)”或“是者(to on)”一词使用得极为频繁。尤其在中期代表作《巴门尼得斯篇》中,柏拉图系统地论证了“一”之“相”(理念)与“是”的相互结合和分离所分别产生的各种结果,试图全面地说明万事万物的存在及其性质的“是”与“非是”的问题[10-p44~45,87~89,……]。柏拉图常常把理念(相)说成是“真正的是(存在)”(true existence),“自在的是(存在)”(注:参《斐多篇》65D,78D,等等。);表达为to on(是者),to noein estin(可以思想或理解的),ho estin(那个“它是”),ho estin auto(那个“它是”本身)[3-p429]。陈康先生指出,柏拉图对话中作为狭义范围的“是者”的“相”(理念)的含义是:
它是永是者(aei on)或者严格地是者(onton on,直译“以是的样式是者”)。onton on(“以是的样式是者”)是o estin on(“那个是‘是’是的”)的最好的解释。[10-p89]
总之,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万物的原型,是现象世界永恒不变的本质,所以它也是世间万物之所以成其所“是”的根本所在。
最后,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对“是”进行最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的第一人[1-p31]:
1)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声称一切学问都是研究“是”的,要么是讲究“是”的一个部分(各门具体学科),要么是直接研究“是”本身的,而直接研究“是”本身——to on hei on——的学问则是人类一切学问中最高的学问,被他称之为“第一哲学”[11-p120]。今按:to on hei on,拉丁文作ens qua ens,英文作being qua being;苗力田先生译为“作为存在的存在”[15-p84],吴寿彭先生译为“实是”或“实是之所以为实是”[11-p56],汪子嵩以为应当译为“作为‘是’的‘是’”[1-p31]。
2)亚里士多德把本体(ousia)当成形而上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并认为本质也是本体[16-p106~120](注:参《形而上学》,1017b23,1030a2-6,1031a15-16,等。)。关于本体一词,根据汪子嵩先生的分析,它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主要是指“基本的是”或“是的根本”。这一理解与该词在柏拉图著作中的含义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对于什么是“是”的根本或基本的“是”的理解不同,柏拉图理解为抽象的、脱离感性事物的“共相”,亚里士多德理解为具体可感的“这一个”与“那一个”。在他看来,“世界本质上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本体或第一本体。
3)亚里士多德把寻求事物的“本质”当作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并从定义、种属关系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如何抓住事物的“本质”,还说“本质就是一事物确切的所是”[11-p130]。他所使用的希腊文的“本质”一词写作to ti estin或to ti en einai,在英文中可直译作what it was to be so and so,what the "to be"(of something)is,what it was (for something)to be,余纪元、汪子嵩、王太庆以为可译作“恒是”或“向来是”,认为其意义是指“一个事物的真正的‘是’的东西”,意在强调“事物中恒久不变的东西”[1-p35]。而吴寿彭先生将此词译为“怎是”,他说:“to ti en einai,事物之所以成是者,兹译‘怎是’。”又说:“‘怎是’(to ti en einai)为某物之所以成其本体者,包括某物全部的要素。”[11-p6,56]苗力田先生在《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形而上学》中译本中将此词译为“是其所是”[15-p33]。希腊哲学中的to ti en einai后来在英文中多译为essence,或essence of things,后者亦是来自于拉丁文esse[是]。总之,希腊文的“本质”一词与“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其本来意义就是指“(世界、事物、人、万有)从根本上是什么”。
三、求“是”是西方哲学及整个西方学术的主要特征之一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发现,在ontology背后有一个比ontology含义更广的以求“是”为旨归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我们认为,这一思维方式不仅是希腊哲学自诞生以来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而且从整体上说也代表了整个西方近现代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特征:欧洲中世纪的哲学受宗教神学支配,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但哲学家们醉心于如何论证上帝的存在,而不是象神学家那样把上帝的存在当作不容置疑的前提,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哲学关注的还是“世界本质上是什么”,而与从“应然”出发对上帝的存在不加置疑的思维方式判然而别。近代哲学以理性代替神学,则是在求“是”的ontological(万有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从笛卡尔到休谟,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认识论几乎都是以ontology(万体论)为前提的。一个本体世界的设定本身表明哲学家认为先要解决世界本质上是什么,才能探讨人类知识的来源问题。康德虽然在休谟的启发下认识到关于意志自由、灵魂、上帝的万有论证明(或译为“本体论证明”)是不可能的,但这一事实仅仅表明康德抛弃了一切关于彼岸世界存在的证明,但并不意味着他要抛弃关于此岸世界本质问题是什么的证明。恰恰相反,对“未来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的探索是对经验世界赖以存在的根本前提的探索,实际上就是对经验世界本质上“是”什么的探索。《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本质上是ontology(万有论、本体论)而不是epistemology(认识论),正是因为它的根本任务在于回答经验世界本质上“是什么”。这一思想不仅贯穿在康德以后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中,即使在当代哲学中也往往如此。
求“是”这一思维方式不仅是整个西方哲学中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而且是西方哲学所有其它部门——逻辑学、伦理学、宇宙论、认识论、美学等——得以形成的根本条件:
1)求“是”是西方逻辑学十分发达、并在很早就独立出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求“是”迫使人们对“事物本质上是什么”不能预设任何结论,任何结论都必须诉诸严格有效的方法,于是方法的重要性超过了结论的重要性,所以逻辑问题自然很早就受到高度重视。20世纪西学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分析哲学把哲学问题从形而上学下降为语言的逻辑分析问题。哲学问题完全变成了逻辑问题。这些都与西方哲学中求“是”的思维方式有关。为了求“是”就不能随便预设任何结论性前提,任何对于存在是什么的结论都必须诉诸方法的合理性。
2)求“是”导致认识论与形而上学长期不可分离。形而上学的原始含义是追问“终极实在”,即最高层次上的“是”;因而它实际上也是最高层次上的认识论,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另一个重要含义:“知识的第一原理”。从柏拉图的“认识就是回忆”,到笛卡尔把形而上学当成了知识这棵大树的根,以及康德对纯粹数学和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问题的探索最终还是为了确立作为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这种不相分离都与西方哲学中求“是”的思维方式有关。
3)求“是”导致宇宙论、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一系列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作为单独学科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希腊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把学术研究分成这么多门学科,柏拉图以为世界本质上“是”什么只要一门学科(哲学)来研究就可以了。但是在对世界的本质(一开始理解为本原)进行探讨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而每一个领域的“是”都可成为一门学科对象。从柏拉图那儿无所不包的“哲学”到亚里士多德明确划分形而上学(第一哲学)、伦理学、政治学、逻辑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修辞学、诗学等诸多学科,完全是为了求“是”的需要。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话说,形而上学是从整体上求“是”,而各门具体学科则从“是”中切下一段来研究,即研究一个具体领域的“是”。因此这些学科的分化、独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希腊哲学为了搞清世界本质上“是”什么的必然结果。
4)求“是”导致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要搞清事物本质上“是”什么,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搞清它产生的根源,亚里士多德反复指出哲学是求取原因的知识[11-p3~4]。他提出“四因说”的同时其实也把本体当成了万物的第一原因、终极原因或根本原理。在寻求事物原因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发现不仅事物的原因多种多样,而且不同性质的事物有不同的原因,甚至同一种事物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其原因也不一样,于是存在着将这些不同的事物分别开来加以研究的必要,这就是他提出把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独立出来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原因。
四、中国古代学说一般不以求“是”为旨归
中国古代的学术是否也象希腊一样以求“是”为思维方式上的主要特征呢?答曰:否。
首先,从宇宙论的角度说,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大量宇宙论学说,但这些学说从思维方式上讲都不具有求“是”的特征,与希腊的宇宙论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史上在很长时期内对宇宙本原的思考走的是一条求“是”的道路,而其得出的结论——如“水”、“气”、“原子”、“物质实体”、“精神实体”之类——代表对宇宙的本原实际上“是”什么的回答,而不是个人在自我修炼所应追求的价值理想。在古希腊,哲学家们所说的宇宙的本原并不代表任何与人生的价值、人生的理想、人生的追求相关的东西,而纯粹是指一个事实意义上的存在。但在中国思想史上,对宇宙本原的思考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其所得出的结论——如“道”、“无”、“太极”、“一”之类——在中国文化中却代表着一些文化的理想、人生的价值、人格的境界,这些东西不能用逻辑的或科学的方式来证明,中国学者历来都主张用他们的人格实践、道德修为、内心体验来验证之,它们在文人学士们心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上帝在一个基督徒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中国人的宇宙论的核心不是求“是”,而是以求“应”(该)为特征、以价值判断为前提的。《周易》可以说最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周易》的宇宙观表面看来与古希腊人的宇宙观颇为相似,似乎也是在求“是”,但这种相似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周易》中所谓“天尊地卑”,所谓“生生之德”,是不能从事实判断的角度来论证的,而只能说是对自然现象的拟人化的想象,因而它们不能代表一种事实上的存在。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宇宙观都是在表达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体验。从思维方式上看,这种宇宙观与人类许多宗教的宇宙观一样,都是以价值判断为前提的。总而言之,这种以价值判断为前提、以求“应”(该)为特征的思维方式不仅体现在《周易》的宇宙观中,同样也体现在《尚书》和老子的《道德经》等其它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中。这充分证明中国人的宇宙观不具有求“是”的根本特征。
其次,从人性论的角度说,中国人的人性论也不具有西方人那种求“是”的特征,不管古人自身是怎么说的。中国人一讲到人性立即把一切关于人性的探讨归结为人性是善还是恶之上,两千年来不出此藩篱,这种情况在西方哲学史上并不存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对人性感兴趣完全不是由于它们对人性事实上“是”什么有兴趣,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人生的价值、人生的终极归宿。他们表面上似乎都是在说人性实际上是什么,其实都是以价值判断为前提、以“怎么行”为旨归的。例如,孟子所谓“性本善”表面上似乎是事实判断,但事实上他所说的“性”乃是一种理想的价值。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这个“性”和《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自诚明谓之性”之“性”一样,都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是儒家学者们所应努力追求的东西。相反,西方哲学研究人性,是从“本质上或事实上是什么”的意义上讲“人性”,正因为如此,他们所说的人性多与任何人生的价值取向无关,也往往不带任何价值色彩。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将人性的本质归结为一不死的“灵魂”,亚里士多德则千方百计地证明了人性可归结为那个不具有任何价值色彩的“第一本体”——“这一个”——之上;从笛卡尔到贝克莱等人皆以人性的本质为一“精神实体”,即一个能思想、能怀疑的东西;而康德以来的哲学家们在否认了精神实体的存在可以证明之后,就将人的存在归结为那个“先验自我”,都是从事实判断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从价值判断出发来思考人性。他们所说的人性往往没有任何价值色彩,对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做人,如何找到人生的价值、人生的终极归宿没有任何直接帮助,这种情况直到当代才开始发生变化。
最后,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中国古代学术在讨论宇宙及人的本质的时候之所以不象西方人那样注重逻辑论证的方法,其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学术的精神实质就不以求“是”为旨归。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讲终极实在时竭尽全力进行逻辑论证的做法相反,中国人在讲天地宇宙的终极实在时并不认为逻辑的论证有什么用,而是强调一种伟大的人生体验,一种参与宇宙生命之流的精神追求,一种无止境的自我修炼过程。过去我们总是批评中国人不讲逻辑认知、所以导致科学没有发展起来,却没有去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比之下,我们发现:西方哲学之所以一直十分注重逻辑,乃是因为这种学说在思维方式上的出发点是为了求“是”的缘故,求“是”决定了方法比结论更重要。而中国人的宇宙观由于以价值判断为前提、以求“应”(该)为旨归,一开始就为自己设立了若干永恒的价值(如“道”之类);而且和人类其它宗教学说一样,这些价值一旦设立,就不再变化,变化的只是不同时代的人们自我修炼的方法。这种只重体验不重论证的宇宙论不能说是一个错误,因为它本来就是从“应该”出发、以价值判断为前提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基督教及人类一切其它宗教中同样存在。
五、从“是”与“应该”看西学与中学的不可比性
是不是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以求“是”为特征的呢?当然不是。首先,我们的观点主要是针对理论科学而非实践科学而言。其次,不要认为一个学说在思维方式上求“是”就意味着这一学说的提倡者不可能有求“应”(该)的抱负。其三,我们并不排除或否认在西方哲学史上也有个别或少数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不具有典型的求“是”特征,但我们是从宏观的历史高度出发,针对西方历史上那些有根本影响的思维方式进行论断的。其四,要将当代西方哲学中个别流派在思维方式上的转向与西方历史上曾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维方式区分开来。我们不能否认,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特别是在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海德格尔等人那里,对“存在”(是)的思考带有深刻的价值判断性质,并似乎已有与东方思想合流的迹象。但是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历史上两千多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没有求“是”求了几千年的“本质主义”、“认知主义”或“基础主义”,现代哲学家又如何会苦心孤诣地赋予“存在”(是)以某种全新的含义。最后,我们说西学与中学不可比,是从整体上而言,但绝不是认为“中学”中的所有部分与“西学”中的所有部分之间都不可比。
如果说西学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事实判断为前提,探究事物的实然状态,它以求“是”、求“知”等为旨归;那么中学思维方式的特点则是以价值判断为前提,探究事物的应然状态,它以求“应”(该)、求“善”等为旨归。前者把“知”(knowing)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方法比结论具有更加优先的重要性;后者把“做”(doing,又可称之为“行”)——“修身”,“践履”,“慎独”,“做人”等等——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结论比方法更加重要。如果把由前者所导致的学术称之为“科学”的话,那么由后者所导致的学术则可称之为宗教、准宗教或信仰类型的学问。这两种学问之间的不同我们可以通过下述这样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获得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可以把伦理学称之为一门科学,但没有人把同样是研究道德问题的宗教学说当作科学。现将这两种思维方式作如下对比(注:“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是西方哲学史、特别是伦理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人们一般认为这个问题首先是由英国经验论哲学家休谟提出来的,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道德哲学引论》,汤姆·L·彼彻姆著,雷克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页514-515。):
是
知 实然 事实判断 论证 求真 方法优先 →……科学
应该 做 应然 价值判断 体验 求善 结论优先 →……信仰
用“是”和“应该”来代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及中西方学术思想在出发点上的一个重要差异,不仅可使我们发现:西学与中学在发展过程及其后果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看来不可思议的差异均可从中找到答案,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西学在多数情况下与中学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问,它们之间的一系列差异在多数情况下是两种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学术之间的差异,而且在多数情况下盲目地用西学的标准来要求中学,或者用中学的标准来要求西学,都是极其荒唐的。比如说,有的人指责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儒家学者几千年来都只是声称自己在为圣人作注,而没有人象亚里士多德向柏拉图挑战那样向孔子的学说挑战,这是导致中华民族缺乏生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说法显然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任何一种以求“应”(该)为特征、以价值判断为前提的学说,都具有此特点。它总是先设立若干伟大而永恒的价值,后人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去推翻它们,也不是去论证它们,而是去体验它们、实践它们。“无为”对于道家而言,“耶稣受难事件”对于基督教而言,“仁、义、忠、信”对于儒家而言,几千年来都是作为永恒的价值而被人们信奉和实践的。对于那些批评中国人缺乏反叛精神的观点,我们这样向他们:为什么你们没有想到去批评基督徒们几千年来一直不敢反叛《圣经》和上帝呢?我们既不能因为西方学术中没有中学中的某些思想而谴责西学,也不能因为中学不重科学等特征而将之归咎于中国人的国民性。20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进行中西文化、思想、学术比较的过程中,由于忽视这一事实而犯下了一系列几乎是致命的错误,这些错误几乎都是由于不了解西学与中学在思维方式的出发点上的不同所致。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用西方现代分类体系来肢解和重新整理国学。
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普遍倾向于认为中国古代的学术体系是“一半断烂,一半庞杂”[17-“序”],主张用西方现代的学科分类体系来分割和重新整理古代的学术,即把原来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框架的分类彻底抛弃(注:“四部”分类法严格说来不是学术分类而是图书分类。从学术分类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儒家学术分类的整体框架应该可以概括为以“六艺”为核心,并以此为基础向外延伸,首先是“经学”中可从“六经”发展到“十三经”,其中包括“大学”和“小学”;其次是区别“经学”与“史学”,“子学”则是服务于经学和史学的。),转而按照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数学、自然科学等一系列现代西学分类体系来分割和重新归类之。这种做法未考虑导致中国古代学术分类体系与西学分类体系的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未考虑中国古代学术是否与西方相应的学科属于同一类型的学问,未考虑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分类体系的形成有没有它自身的内在合理性,实际上严重地忽视或掩盖了另一个异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古代学术与西方现代学科在多数情况下建立于不同的思维方式之上,它们之间在很多方面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例如,同样是思考宇宙的本原,中国人所谓的“道”并不单纯指一个事实上的存在,而更主要地是被作为一种价值来追求的,代表了人生的终极理想。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们所说的宇宙的本原比如“水”、“气”、“原子”、“第一本性”等等并不代表任何与人生的价值、人生的理想、人生的追求相关的东西,而纯粹是指一个事实意义上的存在。因为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它们得出的结论之间本来就缺乏可比性,现在我们将中国古代关于宇宙本原的学说用西方的ontology一词来称呼之,把本来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种学问混同一气,其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用西学与中学之间一些表面现象上的共同之处掩盖了它们之间一系列本质性的差异。
[收稿日期]2000-12
标签: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人性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柏拉图论文; 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