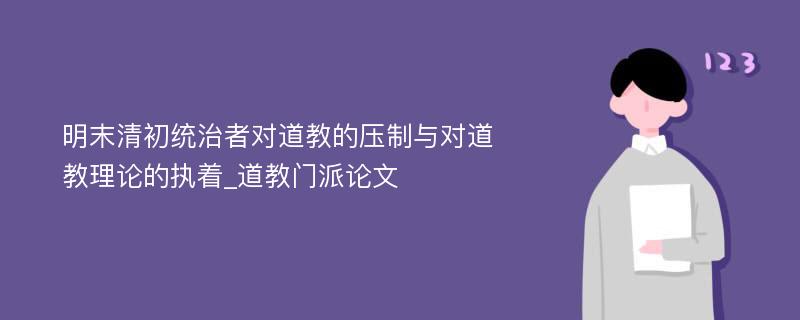
明后期至清嘉道间统治者对道教的打压及道教的理论攀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统治者论文,后期论文,理论论文,至清嘉道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历史,道教的兴衰存亡与封建统治者的喜恶取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明中叶后,历代帝王一面继续利用道教作为统治工具,一面对其严加限制,勤于防范。这与道教从一诞生之日起,所具有的既可为统治者服务,又能为被统治者利用的鲜明二重性有着紧密关联。道教正是在这一大势所趋之中,自身影响和实力不断衰微之时,及时调整自己的理论框架和信徒择向,开始了其既献媚于上又取悦于民的世俗化进程。
(一)
明世宗以后诸帝,以明穆宗以最,对道教进行严厉限制。一方面严加惩治世宗时受宠的道士方士,如剥夺邵元节、陶仲文的官爵和诰命,械系王金、陶世恩、申世文等入狱治罪;另一方面,对正一天师大加贬降,先革去天师张永绪正一真人封号。后直到明神宗,天师张国祥虽复号,但仍不准朝觐,也不准借祝圣诞入京。清统治者信仰萨满教,后笃信佛教,故而对道教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既严厉限制、排斥,又有条件利用的政策。从顺治帝起,这一政策形成雏形,后逐渐成为清统治者一以贯之的宗教政策,极大地打击了道教的发展。
顺治帝认为,道教与佛、儒一样并称三教,不同于“无为”、“白莲”、“闻香教”等应严加取缔的邪教,应该采取保护政策。“儒、释、道三教并重,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1]因此,顺治帝对清初道教活动予以适当支持,如王常月在北京“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2],就是得到了顺治帝的直接支持。尽管如此,顺治帝对道教的扶持只不过是他利用道教实现其统治的一面。从他对天师张应京颁给的诏书中对道教的严厉言词中,暴露了其对道教排斥、防范的真实心理。他要求天师张应京“兹特命尔袭职,掌理道录,统率族属,各使异端方术,不得惑乱愚民。……尔其中申饬教规,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属,贤愚不同,悉听纠察,此外不得干预。尔尤宜法祖奉道,谨德修行,身立模范,禁约该管员役,俾之一守法纪,毋致生事”[3]。
康熙帝玄烨则对道教之说持批判态度,认为道教流而成弊,于世无补,但是“今日之僧道,实不比昔日之横恣,有赖于儒氏辞而辟之。盖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养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将此数千百万无衣无食游手好闲之人,置之何处”[4]。除此之外,保留已经衰微的道教还可以“留资画景与诗材”[5]。道教在皇帝看来是如此之无用,应该说更是满清统治者对汉民族传统信仰充满逆反心理的一种表现,而不应真正理解为对道教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够。否则,则不能解释统治者康熙帝对道教进行严厉限制甚至是无情打压,而雍正帝则力倡三教为其统治服务。康熙帝认为,“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改妄为”。“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严行禁止”。[6]而雍正帝则认为,“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释、曰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主于功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道家所用经录符章,能祈晴祷雨,治病驱邪,其济人利物之功验,人所共知”[7],“三教虽各具治心、治身、治世之道,然各有所专、其各有所长,各有不及处,亦显而易见,实缺一不可者”。[8]因此,他反对打压佛道,而采取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肯定道教的治世作用,以利用其为统治阶级服务。雍正帝宗教政策的基本点在于实行区别对待,对于出家人佛道者,“其中违理犯科者,朝廷原有惩创之条;而其清修苦行、精戒有宗者,则为之护持!……凡有地方责任之文武大臣官员,当诚是朕旨,加意护持出家修行人,以成大公同善之治”[9]。
尽管清朝早期统治者对道教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其道教政策的总体走向是趋于严厉防范和约束,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历代天师的地位不断贬斥;二是对道教活动的极力限制,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八九,载“(乾隆)4年(1739年),议奏: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选道士、受录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议处”。将道教组织发展,限制在龙虎山一带,禁止到其他省区。道士在宫廷的地位,朝不如夕,一日千里,乾隆12年(1747年),下令正一真人由二品改为五品,31年(1766年)又升为正三品,至乾隆54年(1789年),令正一真人“五年一次来京”[10]。与此同时,一改多年来由道士充任太常寺乐宫的制度,改由儒士充之。至嘉庆、道光年间,正一真人的地位继续被贬降,而在此时,道教不仅在理论上疏于建树,教团如全真道及其支派、正一道及其支派的势力日渐衰落,大不如前,对社会的影响自然也就愈加衰微。至道光元年,清王朝敕令第五十九代天师张钰“停其朝觐,著不准来京”[11],道教从此被赶出宫廷的政治舞台。
(二)
随着道教在宫廷的失宠而衰微,道教不得不重新走向社会中下层,逐步褪去其神秘而尊贵的外衣。一方面,继续大倡三教合一思想,以寻求其理论上的完善和上层社会的认可;一方面则以斋醮符录取信于百姓,开始其世俗化的进程。而这,正是迎合了清王朝统治者的诉求,“不废其教,亦不用其言,听其自生自息于天地之间”[12],用以达到其利用道教宣扬的对神灵的崇奉,笼络士民,防止其“犯上作乱”,维护统治的根本目的。
明末以来,一直就有道教理论家力倡三教合一。清初著名内丹学家陆西星、伍守阳于此颇有心得,并将其作为他们丹道的理论基础。陆西星自幼习儒,中年修道,晚年又精研佛理,其丹道理论在于“孔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且夫造化二五,陶铸百物,象形虽殊,体本无二,莫不定阴阳之位,构真乙之精,顺施化之理,立性命之基。故曰,天地氤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如所而论,可谓本末兼该,上下俱尽者矣。故天不变则道不变,道不变则体是道者,亦可使之不变,而长生久视之道,端在于此”[13]。陆西星认为《易》之阴阳,是修炼长生之道的源头,要获得长生久视之道,就必须修性炼命,释儒二家亦主张道家丹法的重要内容“修性”。他说:“夫佛无我相,破贪着之见也;道言守母,贵无名之始也。不知性安知命耶?既知命矣,性可遣矣。故论性而不沦于空,俞在其中矣;守母复归于朴,性在其中矣。是谓了命关于性也,是谓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也。”[14]在他看来,释儒道的区别只在于作用之不同,其宗旨是一致的,“三教圣人同一宗旨,但作用不同,故有三者之别耳”[15]。他认为佛、道之学的本旨都是为了使人的真性不受后天形质的蒙蔽,保持其湛然澄澈的本来面目,教人返朴归真,都是修养之学。二者之不同在于“仙者主修、佛者主养”[16],将其内丹之学看作是融合儒、释、道而成的最好的修炼之学,“仙佛圣丹同具同证”。因此,他主张儒释道三者消除纷争,同证一道。
伍守阳也禀承全真道三教融合的基本观点,认为仙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将忠孝礼仪纳入修道的规范体系,认为“君当忠而忠,亲当孝而孝,兄长当顺而顺,朋友当信而信,谓之纯德”[17]。他进一步将三教的共同点建立在理念、修炼的同一之上,都讲求的性命双修,讲求依照三教圣人的教导行事,才可成仙、佛、圣。
随后的一些道教理论家和实践家,则不仅继续重弹三教合一旧调,而且将儒家忠孝礼义提到相当的高度,甚至直接站出来为清王朝的统治大唱赞歌,粉饰太平。全真龙门派的第七代律师王常月颇受顺治帝的信任,赐为“国师”,三次公开传戒,声名大振,他的道教思想特点除了其鲜明的三教融合色彩之外,强调持戒为先,反对“着相修行”,以修性为最高目标。他极力调和出世与入世、人道与仙道、凡人与圣人的差异,认为圣贤仙佛是世间出世间最完善的、毫无暇疵的楷模,是真善美的化身,凡夫要想修道成真,就“要依那圣贤仙佛的实话”,“须要立起圣贤仙之光”、“修下圣贤仙佛之因”、“种下圣贤仙佛之根”,“积下圣贤仙佛之德”,“行出圣贤仙佛之事”,[18]而不问结果,自然会获酬报。在“人道”、“仙道”,的关系上,他认为,“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未修,仙道远矣”[19]。进而将“人道”、“仙道”比附儒家的“治家”、“齐身”。关于“出世”与“入世”的关系上,他认为“天地之大,世界之广,哪里算是世外”[20],从而否定“出世”与“入世”之差别。他宣扬出世之法存在于世法之中,因而出世法要从世法中去修,仙道来自人道,所以必须先行老道、遵王法、爱惜身体。他要求道徒们除了持戒外,还必须遵守“王律”;教悔教徒“舍绝受缘”,但又不忘报答天地、日月、帝王、父母四恩,须要忠君王、孝父母,先要做一个忠臣孝子,完人道,从世法中修出性命双全。他说“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不了此八个字,人道就不全了,如何进得仙道”[21]。由此可见,王常月所宣讲的宗教思想,既可以得到清王朝的支持,又可以受到许多明朝遗民、儒士的拥护,从而开创了全其道龙门派在沉寂多年之后的又一次“中兴”。
净明道的核心教义是修习忠孝,以涵养忠孝为修道的根本,以修习人道为成就仙道的基础和阶梯。认为不修忠孝,无由入仙道之门,不经人道不能达成仙道。清嘉道间,净明道著名道士缚金铨在论述他的性命双修、阴阳双修的内丹说,以及去欲存真的心学之后,对人道为仙道之阶梯进行了大力发挥。他认为:“欺诈者,杀佛之戈矛,忠孝者,成仙之阶级。不尽三纲五常,必入四生六道,求道之士,恶可以不忠孝耶?”[22]讲强调“人道不修,仙道远矣!人道是仙道之阶,仙道是人道之极。不有人道,安求仙道”?“三教鼎立,如一屋三门,中无少异。儒立人极孝弟之道,报本反始,正心诚意,道德之原,此范围形体之道,人世之法也。仙佛在声臭之表,形气之先,出世之法也。出世必基于入世,欲求出世之功,先进入出之道,儒其大宗矣”。[23]
(三)
清初至嘉、道间,道教受到统治者的打压、限制,进入自创立以来的又一次低谷。道教理论家、实践家正是以自己不断迎合统治者的理论改造和实践,以求得一席生存之地。而正因为此,道教理论为统治者所认可,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的次级结构补充,道教也逐渐从着力于取得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宠幸、利用,转而开始在社会中下层寻找广阔的生存空间,开始其世俗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