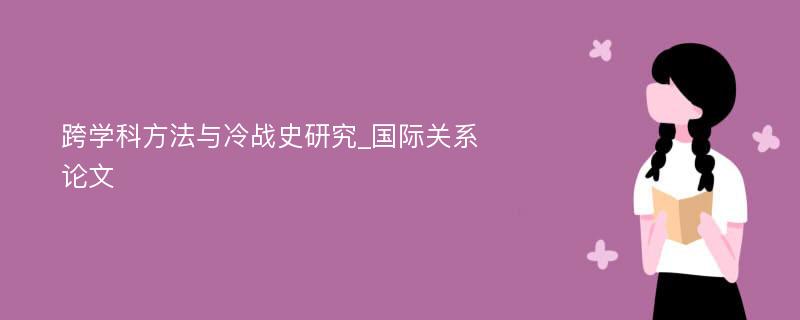
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史研究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叙事史学的局限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近年来突飞猛进地发展,在档案整理、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成果出版等诸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绩,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就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而言,进步并不明显。特别是与国际冷战史研究近年来的发展潮流相比,中国冷战史研究在方法论变革方面还相当迟缓,具有宏大的理论视野并运用跨学科方法的著作还不多见,绝大多数成果属于以档案研究和传统叙事为主的兰克式史学。
兰克式的传统叙事史学无疑有其优长。其优雅的叙事技巧、诉诸常识的历史解释、广被运用的教化功能和资治作用以及成果的可读性等等都使传统叙事史学仍然有其生命力,但是兰克史学重叙述、轻分析,重过程、轻问题,重事实、轻意义的特性使其落后于当代史学发展的潮流,在以下三个方面制约着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中国的冷战史研究需要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入。
第一,传统叙事史学方法限制了冷战史学家提出新问题的能力。当代史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史学研究的“问题取向”,学者的研究是以提出问题开始,以收集资料回答问题,并最后解决问题而终,能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学者的水平,也决定了研究的成败。兰克式史学强调的是叙事,而不是问题,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再现事件的来龙去脉、政策的制定过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史学家即使提出问题,也主要是在常识范围内追问因果关系,而难以从新的角度提出引入深省、别开生面的有意义的好问题来。这就造成史学家“提问”的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大多数成果成为事件和政策过程的“始末记”,加上一些点缀性的分析或经验式的总结。而跨学科的素养和知识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具体说来,国际关系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都可以为冷战史学家提供观察历史现象的新视角,从而帮助学者提出新问题。举例说来,在中美关系史领域,由于对各种政策、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都已经相当充分,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新问题的空间十分有限,但时殷弘和吕磊在1996年发表《美国对华态度与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一文,提出“中国对待国际社会的态度以及美国如何影响加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的问题,令人耳目一新。①国际社会是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重要概念,如果对国际社会的理论缺乏了解,就不会提出这一有深度的问题,时殷弘等人正是借用了牛津大学教授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在《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②中提出的国际社会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中美关系史做出了新的解释。再如,对冷战初期美国对外政策以及相关的冷战起源的研究已经有大量成果,按照传统史学的思路,在这一领域提出新问题几无可能,但是约翰·福赛克(John Fousek)提出冷战初期“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指出美国人普遍把美国的国家身份界定为“(自由)世界领袖”,这一身份认同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对冷战初期一系列事件的反应。③国家身份显然不是传统叙事史学关注的问题,而是来源于社会学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当前外交史和冷战史研究中的很多新问题,都是来自于跨学科的视野。
第二,传统的叙事史学对历史的解释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通常是通过寻找经验事实之间的关联来发现因果关系,较少能在“常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之外提出对历史的解释。比如就冷战的起源这一问题而言,传统叙事史学关注的是冷战初期美苏之间一系列政策、行动和局部冲突,把冷战的兴起归因为美国或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或归咎于两国领导人的“邪恶”,对美国或苏联进行道德的讨伐。而以约翰·加迪斯(John L.Gaddis)为代表的后修正派史学家则另辟蹊径,提出冷战源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际政治永恒的冲突逻辑带来的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美苏之间的安全困境又由于战后初期双方的一系列误判而出现螺旋式上升并最终导致了冷战。这一解释显然是借鉴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战争根源的研究,比单纯指责美国或苏联为冷战的兴起负责要深刻得多。关于1949-1950年间中美对抗形成的原因,一般的解释是认为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历史上的恩怨、美国的敌视政策和中共强烈的反美主义导致两国缺乏和解的起码基础。但高龙江(John W.Garver)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提出根本不存在一个中美和解的“机会”。他认为中国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都经历了几个阶段:革命之初相对温和,然后迅速激进化,接着走向狂热,直到革命者筋疲力尽之后,革命开始去激进化,最后逐渐又回到社会常态。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革命正进入急风暴雨的激进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执行与其革命意识形态相矛盾的政策,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而只有到了中国人的革命激情大大消退,革命者开始疲倦的文革后期,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才有可能。④这一解释可谓别开生面,其依托的理论资源是政治学关于革命,特别是意识形态与革命的关系的研究。
其三,传统的叙事史学重视政府档案,但解读档案的视角较为单一,不善于发现档案的多重意义。在冷战史研究中,学者们为了学术创新而往往对新档案和新材料趋之若鹜,一批新档案的解密往往会导致一批新成果的出现,接下来是一段时期的沉寂,然后新档案的发现又带动一批新成果。由于观察的视角是一样的,对档案的解释也就大同小异。比如,关于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近年来中国学者出版了不少成果,但这些成果所讨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非常相似。而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可以帮助史学家从新的角度解读老的史料,从而得出新的结论。以尼克松时期中美关系解冻问题为例,关于中美关系解冻的背景、过程和双方改变政策的原因和动机,学者们已经相当熟悉,如果按照传统叙事史学的思路解读史料,则难以写出新意来。张曙光教授的新著《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则从一个新的角度、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尼克松改变对华政策的过程,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作者不是去再现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过程和解释中美各自动机与目标,而是把尼克松对华政策转变视为美国实施接触战略的过程,运用国际战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尼克松时期美国对中国接触外交的设计、实施、评估和调整。⑤该书跳出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解释,提出了新的解释,推进了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研究,实现了学术创新。
简言之,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可以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为冷战史研究开辟新的局面。
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研究
冷战国际史研究作为广义的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与国际关系学无疑具有亲缘关系,这使冷战史研究中应用国际关系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事实上,在学术史上不乏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冷战史研究的成功范例。比如,杰出的冷战史家约翰·加迪斯对战后美国遏制战略的演变和特性的研究、对二战后“长期和平”(long peace)的解释以及对冷战起源的分析都反映出加迪斯良好的国际关系理论素养。正是这一理论素养使其著作不仅在史学界获得极大的声誉,而且也在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冷战史学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首先体现在运用国际关系学一般知识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素养来观察和解释冷战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国际关系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关于个人、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体系的一系列理论思考,发明了诸多重要的概念和范畴来理解和阐释国家行为和国际体系的演变,如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均势、国际体系、(大)战略、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等,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家行为和国际体系进行了系统的解释。一般说来,历史学关注变化、关注具体,把人类生活的变化归结为人的行为,从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对历史进行解释。而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关注变化,而且关注状态,并试图发现重复出现的国家行为模式和机制,探究国家行为的深层动力和国际关系演变的规律,不仅从人的行为出发来解释战争与和平,更重要的是关注人类行为之外的更深层次的力量,如体系和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制约等等。了解和熟悉这些知识可以扩大史学家的视野,提高其理论思辨能力,有助于冷战史学家从不同角度观察历史现象,对历史进行更全面和更深入的解释。
比如,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方法——层次分析法就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冷战史研究中。所谓层次分析方法是指从四个层面对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态或事件进行分析,这四个层面是全球、地区、国家和个人。全球层面是指影响国家行为的外部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际权力分布的状况,也就是国际体系;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制约国家行为的环境因素还包括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而在建构主义看来,则包括国际舆论、道德和风尚。而地区层面的因素则是指塑造国家行为的地区环境,包括地区国际体系。国家层面是指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国家利益、政治文化、经济需要、政治制度、利益集团等等。个人层面是指决策者的个性和策略。层次分析法可以被用来解释冷战的起源以及结束等两大事态。
把这种层次分析法应用到冷战起源的解释,我们会发现,冷战至少起源于三方面的因素:在全球层面是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冲突的国际体系;国家层面是美苏两国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的根本需要和思想观念;个人层面则是美国和苏联两国领导人的外交行为和策略。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从多级体系向严格的两极体系转变,而当国际体系处于巨大变动的时候,特别是新体系取代旧体系的时候,国际冲突会加剧。在这一过程中,美苏两国都抓住机会扩大各自的影响,利用欧洲帝国解体、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动乱和经济重建的需要被吸引去填补权力真空,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观念建立战后秩序。同时,由于原子武器的出现,原来的安全地理界限被打破,美苏之间的相互不安全感大大增强。但是,冲突的国际体系并非必然导致冷战,体系虽然孕育着冲突,但如何对国际体系做出反应则取决于国家的需要和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国家并不是简单地、被动地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而是主动适应甚至试图改变外部环境,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国家利益(安全、经济、战略)需要会影响国家对国际体系反应的方式。战后美苏之间在国家传统、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对国际秩序的设想等诸方面根本不同,决定了两国无法进行合作。就个人层面而言,战后初期,由脾气暴躁、目光狭隘、缺乏外交经验并对苏联抱有极大偏见的杜鲁门接替富有耐心、理解苏联同时与斯大林有良好私人关系的罗斯福领导美国,无疑加剧了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从而加深了两国的猜忌与矛盾。外交政策的根本动力虽然不是源于领导人的个性和偏好,而是根植于美苏两国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国家利益,但是领导人的外交行为和策略仍然对美苏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会加剧或者缓和双方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说,国际体系的特点和两国截然对立的根本需要和思想观念决定了美苏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是领导人的行动和策略影响了冲突的广度和深度。简言之,国际体系、国家需要和领导人策略一起共同制造了冷战。⑥这一解释无疑是比较全面的。
这一层次分析法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冷战的结束。关于冷战结束的原因,学术界的解释包括美苏争霸疲倦论、里根强硬政策胜利论、美国接触政策胜利论和苏联领导人代际更替论等等。⑦这些解释大多各执一端,不免失于偏颇,如从全球、国家和个人等多个层面解释冷战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末逐渐结束可能更有说服力。从全球权力分布,即国际体系层面来看,导致冷战结束的最大事态是自70年代末期以来逐渐出现的国际权力的分散化或多样化(diversification),正是这种分散化导致美苏无法控制其他地区,使两极体系趋向解体。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标志的伊斯兰世界的崛起和伊斯兰教成为吸引第三世界反西方极端分子的意识形态;中国退出冷战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逐渐成为美苏两极体系之外的独立力量;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分散了美国和西方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不仅使西欧逐渐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而且对中东欧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从而逐渐瓦解苏联阵营。如果说,冷战的兴起是由于多极和权力分散的国际体系演变为僵化的两极体系的话,冷战的结束则是由于两极体系逐渐向多极趋势发展和国际权力的分散。在国家层面,冷战结束的背景是东西方交流增多、国家间相互依赖增强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共同导致苏联在安全需要、国际秩序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趋向于美国的巨大变化。在个人层面则是美苏两国领导人的作用,特别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巨大作用,戈氏不仅对苏联制度和美苏关系进行了深刻、全面的反思,而且主动放弃针对美国的冷战政策。显然,综合多种因素的层次分析要比单一因果关系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的应用还体现在不同流派的概念、理论与方法都可以被冷战史学家所借鉴。现实主义理论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发生的体系环境,研究历史上战争与安全问题几乎无法绕开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预设和概念,诸如“均势”、“地缘政治”和“大战略”等,这些概念已经成为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学家经常使用的标准术语。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曾用“均势”来解释历史上的美国外交政策,把美国外交政策解释为对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反应以及建立和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均势的过程。⑧毫无疑问,现实主义理论非常有助于冷战学者研究美苏两国在冷战时期的安全政策和国家战略,甚至可以说,离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概念,安全政策的研究可能无法进行。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研究国际组织和跨国行为体,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的成长,以及全球化进程。就冷战史而言,从自由主义的视角可以使我们看到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另一个潮流,即由国家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所推动的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化的加快,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由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而带来的非政府组织的爆炸性增长。而这些是冷战史研究长期忽视的国际关系现象。⑨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把1947-1990年间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归因为美苏冲突的冷战决定论,开辟冷战国际史的新领域。实际上,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冷战时期的活动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
建构主义作为冷战后兴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建构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物质主义解释,强调非物质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从表面来看似乎无法解释冷战时代高度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但学者们发现,建构主义关于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的身份与利益如何塑造其行为的论说,特别适用于解释冷战的结束。建构主义把国家身份与利益视为观念的产物和社会建构的结果,而非给定的和客观的,⑩认为观念的变化会导致国家利益的变化,并继而导致政策的变化。冷战的结束源于苏联政策的改变,而苏联政策的改变源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的苏联领导人观念的变化,特别是国家利益观念的变化。苏联领导人不再把德国的统一视为对苏联安全的威胁,不再把充当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视为其国际角色,不再把美苏关系视为一场零和竞争,而是看到美苏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一切导致苏联不再把美国视为敌人,这样,冷战就逐渐结束了。也就是说,是苏联人观念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转变,而非美国的军事力量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正如亚历山大·温特所言,正是在戈尔巴乔夫对美苏关系进行深刻的重新评估基础上,苏联决定“单方面地迅速结束冷战这个似乎已经固化的冲突”,“可能存在客观条件,使苏联‘不得不’改变冷战观念,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观念就是冷战,正因为如此,改变这些观念,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改变了事实”。(11)
温特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安全观念、身份意识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按照这一思路,研究美、中、苏等国冷战时期的身份认知和国家安全观念与其政策的关系,以及价值观和国际规范如何塑造冷战时期的国家行为都可以成为冷战史研究学术创新的有效途径。
除以上流行于美国的国际关系三大流派外,前述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和巴里·布赞等人提出的国际体系理论都可以被借用来理解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演进。布赞等人提出的五个分析层次非常有助于理解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内多种行为体,特别是国家以外的行为体的作用及其互动如何塑造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12)用布赞的话来说,他提出的国际体系思想“能够使我们在世界史学家的著作与国际关系学的社会科学理论之间架设起跨学科的桥梁”。(13)
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在较宏观的意义上为史学家提供新的视角,帮助史学家提出新问题和开辟新领域,同时也可以在微观层面为史学家提供研究决策过程的工具。以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为代表的国际关系认知学派提出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促进冷战史学家在微观层面的研究,即研究决策者的认知过程。众所周知,对外政策是基于决策者对国际形势、国家利益和外部威胁的认知制定的,而决策者认知形成的过程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决策者并不能总是合理地估价本国的利益和外部的威胁,常常形成错误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错误的政策,历史上很多战争实际上就是由错误认知造成的。罗伯特·杰维斯对影响认知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结了导致错误认知生成的因素,包括僵化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错误的历史类比(也就是对历史教训的误用)以及一厢情愿的想法(或愿望思维)等等。(14)其理论就可以被国际关系史学家所借鉴,来研究历史上美国对其他国家意图和国家形势的误判以及由此导致的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众所周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就大大低估了中国干预的决心,从而做出了越过三八线的决策,结果招致了中国大规模的军事干预。而研究越战的学者们发现,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是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的认知基础上的:第一,错误地认为胡志明是一个受中国和苏联操纵的共产主义者,而没有看到他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反对大国和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英雄,忽视了越南革命的民族主义起源。这一错误认知使美国把越南内战视为共产主义扩张的一部分。第二,错误地相信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应验到东南亚,担心一旦南越被北越征服,印度支那其他国家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都会倒向共产主义。这是基于错误的历史类比,从慕尼黑教训中得出的错误结论。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厄内斯特·梅对冷战时代美国决策者如何运用历史类比来理解国际形势,历史教训如何被滥用导致美国战后的干涉主义进行了精辟的分析。(15)
冷战史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冷战史学家可以从国际关系理论中获益良多,从而使中国冷战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知名国际关系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W.Schroeder)曾这样评介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史学家的价值:
我个人的经历使我相信,国际史学家可以从国际关系理论中学到很多东西,并且在他们的技艺中有效地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例如,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帮助历史学家避免幼稚的经验主义,提供多种多样的解释模型和范式,促使他们更加认真地思考他们自己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前提,帮助他们发现反复出现的模式和历史现象的共同本质(否则他们可能只看到独一无二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以及从总体上帮助历史学家做出更宽广、更深刻、更有说服力的概括性判断。(16)
文化研究与冷战史研究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新兴学术领域,文化研究致力于对人生活其中的意义世界进行解释,关注的核心是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近年来,在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潮流的影响下,冷战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向,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研究文化如何塑造冷战以及被冷战所塑造。(17)随着冷战史研究越来越关注文化问题,文化研究的概念、方法和理论开始大量被运用到冷战研究中去,特别是福柯的知识-权力思想、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以及文学批评中的修辞和话语分析等等,被一些学者用来进行冷战史研究。
福柯的知识-权力思想是后殖民研究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这一理论被外交史学家用来分析历史上美国知识的生产与美国全球权力,即霸权之间的互惠关系。戴维·恩格曼(David C.Engerman)把美国知识与美国权力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是“知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权力”(American Knowledge for Global Power)。冷战时期,很多学者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撰写研究报告,或在政府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在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之间实际上长期存在一个旋转门(revolving door)。美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学、政治学、区域研究和现代化理论以及行为科学的兴起无一不打上了为冷战服务的烙印。一些大学通过承揽美国政府项目获得迅速发展,出现了一批所谓的“冷战大学”。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利用自己的知识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辩护,或直接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成为所谓的“冷战知识分子”。(18)这些都是知识服务于美国权力的明证。其二是“知识诠释美国的全球权力”(American Knowledge of Global Power),意指美国学者以教师和作者的身份向学生和一般公众提供了大量关于外部世界、美国自己以及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知识,强调大学的国际化和学生的世界主义眼光以及美国的使命与全球责任等等,这些知识帮助美国人理解世界和美国自己,同样有助于美国全球权力的扩展。其三是“美国知识成为一种全球权力”(American Knowledge as Global Power),指美国生产的知识被当作不证自明的真理和普遍的标准,塑造了各国人民的行为,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和社会生活,从而产生强大的规训能力,对现代国际关系和现代世界本身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视角研究冷战史,就是关注美国的知识生产如何促进了美国利益的全球扩张,知识如何成为支撑美国权力的工具。恩格曼建议外交史家应该“像分析利益那样认真地分析思想,像对待回忆录那样认真地对待学术专著,把教授们的工作置于与政策制定者和电影制片人同样的地位”。他认为“更加认真地关注学者的思想——美国知识,可以使我们更广泛、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的国家角色——全球权力(global power)”。(20)恩格曼的观点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指出了冷战史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
受文化研究的影响,一些外交史学者致力于对外交决策者的思想观念和意义世界的探讨。他们借鉴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试图对外交决策者认识外部世界和过滤外部信息的意义体系观进行人类学式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在这方面,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为很多学者所青睐,用于分析美国决策者对第三世界的观念以及这一观念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布拉德利(Mark P.Bradley)借用东方主义理论对美国卷入越战根源的重新解释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是东方主义理论应用到冷战史研究的成功范例。过去学者们主要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对美国卷入越南的根源进行解释,将美国的干涉归咎于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自由资本主义贸易秩序的需要,中国的共产主义扩张对东南亚的威胁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等等。但布莱德利认为这些解释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充分的,忽视了文化力量在美国决策过程中的持久性和重要性。作者通过对美国人撰写的关于越南的著作和美国外交文献的研究发现,美国决策者实际上是通过由欧洲的东方主义和美国土生的种族主义遮蔽的认知透镜来看待和认识越南的,对越南的印象充满东方主义偏见,越南人被视为懒惰的、胆小的、不诚实的和心智不成熟的,严重缺乏自治能力,因此,其反殖民主义活动是来自外来的煽动,是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美国必须干预。正是决策者头脑中对越南的东方主义偏见导致美国做出错误的政策选择,不深入研究美国人对越南的种种错误观念就不可能理解这场冲突。(21)
美国这种偏见绝不仅仅限于对越南的观察上。实际上,美国在冷战时代对整个第三世界的政策都受到这种源自欧洲,盛于美国的东方主义认识论的影响。美国长期把中国视为苏联的傀儡,拒不承认新中国与美国领导人持有的对中国的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偏见实际上有密切的关系。(22)分析冷战时期美国领导人的思想世界和看待非西方世界的种种观念无疑可以扩大冷战史研究的范畴,包括东方主义在内的后殖民理论可以提供有力的分析工具。
冷战史学者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借鉴还表现在对重要外交文献进行语言分析,通过研究外交决策者的修辞战略和话语体系,探究决策者政治修辞艺术对现实的“建构”和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这方面最成功的研究是弗兰克·科斯蒂格利奥加(Frank Costiglioga)对乔治·凯南著名“长电报”的修辞分析。科斯蒂格利奥加发现,凯南在其著名的长电报中为了使其观点被接受,发挥了他高超的修辞艺术,特别是运用社会性别隐喻,暗示苏联政权是野蛮残忍的(男性)强奸犯,苏联人民是遭受苏联政权“蹂躏”的(女性)受害者,而美国则是具有男子气概的英雄,负有打败邪恶的压迫者解救受害者的使命。凯南还用病理学隐喻把苏联领导人描绘成心理不健全的精神病人,与之进行理性的对话是不可能的。这一修辞战略的后果就是凯南遏制苏联的政策主张被广泛接受。(23)也就是说,凯南关于苏联威胁的描绘并非是对现实的客观、冷静的评估,而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极度修饰造作,并依赖各种修辞艺术来让人信服的偏见,但在当时却成为被美国决策层广泛接受的事实,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对现实的“建构”作用。实际上,这样的文本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数不胜数,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领导人依赖修辞力量和雄辩术来推销自己的主张和争取支持是司空见惯的,威尔逊、肯尼迪和里根都是这方面的高手。例如,冷战时期“自由”和“自由世界”的话语就具有强大的宣传力量,分析冷战时期“自由”的话语如何动员民众、团结西方和妖魔化苏联阵营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题目。对重要的外交文献进行语言和修辞的分析以及对流行的公共话语进行研究可以成为冷战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新课题。(24)
社会性别理论与冷战史研究
1986年,学者琼·斯科特(Joan Scott)发表《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25)标志着社会性别理论开始应用于历史研究,历史学家们开始用社会性别来理解权力问题。由于外交决策者和外交人员大部分为男性,他们讨论的是战略、安全、地缘政治、市场等问题,外交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被认为不适用于性别分析。但是,在斯科特看来,战争、战略、外交等高端政治(high Politics)同样适用于性别分析,因为它们本身已经被赋予了性别意义的概念,其重要性是建立在排斥女性参与基础上的。斯科特说:“性别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参照,通过它,政治权力得以被构想、合法化和被批判。……性别和权力的意义是相互建构的。”(26)这里的权力当然包括外交权力和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控制。实际上,国家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性别关系的观念被理解和被合法化的,强国和宗主国通常被赋予成熟男子的特征,而弱国和殖民地常常被女性化。领导人也常常通过诉诸男性气概和荣耀,通过号召男性承担起保卫妇孺的责任而使战争政策合法化。在领导人的言论中,国家力量通常与男子气概(masculinity)联系在一起。因此,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研究是无法避开性别问题的。知名的外交史家埃米莉·罗森堡(Emily Rosenberg)在1990年《美国历史杂志》组织的关于如何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圆桌讨论中发表《性别》一文,提出了研究美国对外关系时关注性别因素的方式。(27)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悄然兴起,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研究开始大量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性别因素逐渐被视作与战略、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同等重要的塑造美国对外关系的力量。
社会性别理论应用到冷战史研究的第一个路径是研究外交决策者的性别观念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外交决策固然受到一系列客观因素的驱动,但是决策者对客观条件的认知总是通过文化的意义体系来过滤,而领导人头脑中的意义体系就包括性别观念,性别观念是一个人世界观的要素之一。历史上,美国外交决策者长期以来是清一色的男性白人精英,所以对性别因素感兴趣的学者大多讨论美国外交决策者对男子气概和男性风尚的追求和捍卫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如,学者罗伯特·迪恩(Robert Dean)把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与肯尼迪总统的性别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肯尼迪在越南实施的反叛乱行动与和平队计划深受当时美国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迪恩发现,肯尼迪政府的高官们是在美国上流社会中通过磨难来培养男性气概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都是当时美国社会的出类拔萃之辈,是美国男性的典范。而在当时极具竞争性的、深受冷战影响的美国国内政治气氛中,整个社会崇尚的是具有开拓和冒险精神的所谓“新边疆人”(New Frontiersman),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与领导人表现出来的“新边疆人”式的男性气质密切相关,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对越南共产主义的软弱不仅会带来政治上的风险,也与肯尼迪等人的自我认知不符。简言之,肯尼迪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仅有反共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考量,还受到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正是“内在化的男子汉(manliness)理想影响了肯尼迪等领导人对来自外国威胁的认知”和“对政治代价与收益的考量”:对越南除了表现出男性的强硬(masculine toughness)之外别无选择。(28)埃米莉·罗森堡则把好莱坞在冷战初期拍摄的两部电影——《外交事务》(A Foreign Affair,1948)和《穿法兰绒西装的人》(A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1956)作为素材,把国际政治与性别政治相联系,研究冷战初期在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责任观念”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取向。罗森堡发现,那个时期美国社会流行的话语就是强调男性和超级大国的责任,男性的责任体现在对家庭的主导,超级大国的责任则是对世界的领导,这被认为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充当服从的伙伴被视为没有男子气概”。大体上,“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有关战后性别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政策都是在同一种坚定地把男性(美国的代码)置于主宰地位的主导性话语结构下形成的”。战后美国奉行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与美国试图重建传统的男性主宰、女性配合的性别角色是密切相关的,支持外交上的国际主义与主张家庭内部的男性主宰是一回事。(29)也就是说,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被用来通俗地表达国家间关系,性别话语和国际关系话语之间存在着象征性的关联,国际政治成为性别政治的引申和放大。
迪恩和罗森堡等人的研究证明了决策者头脑中的性别意识形态是多么深刻地塑造了他们对国际事务的认知和外交政策的选择。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对外交决策者头脑中的意义世界进行分析是美国外交史家近年来比较热衷的方法。正如埃米莉·罗森堡所说的那样,“通过鼓励文化分析,特别是性别分析,国际政策研究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30)
社会性别理论应用到冷战史研究的第二个路径是关注研究社会性别观念如何影响了美国人对自己和其他民族的认知,特别是决策者和政治精英持有的关于其他国家的性别化形象(gendered imagery)如何塑造了美国的政策。
在美国历史上,决策者和外交精英们常常通过社会性别语言,通过把国家和民族间的关系性别化而使美国对弱小民族的控制和征服合法化,这些弱小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被武断地赋予女性特征,因此应该依附于强大的美国。在19世纪末美国对外扩张中,妇女、非白人种族、热带国家被美国外交决策者赋予相同的个性:感情用事、不理智的、不负责任的、不稳定的以及孩子气的,因而需要美国的监护和保护。正是这种性别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变得被理解,美国的扩张与征服政策被接受。(31)
在冷战时代,决策者和政治精英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性别化认知继续塑造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学者们发现,同早期一样,美国人继续把本国社会流行的关于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观念赋予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人民,从而形成对该国的认知和理解,同时这种对其他国家的性别想象又同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联系在一起,导致美国强调非西方社会的柔弱和国内社会的混乱,把非西方社会女性化,从而为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和主宰提供正当性。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成功的研究。安德鲁·罗特(Andrew Rotter)通过对印美关系的研究发现,在西方出版物中,印度长期以来被描绘为雌性国家:受感情驱使,缺乏理性。印度男性被赋予了三个特征:被动服从,情感脆弱(emotionalism),缺乏征服异性的活力(heterosexual energy)。总之,印度像一个需要保护的柔弱女子,而西方则是强壮勇武的男子。正是这种印象帮助论证了美国在南亚次大陆采取更积极的反共遏制政策的合理性。(32)迈克尔·马特(Michelle Mart)讨论了冷战时代美国人心中的犹太人形象如何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犹太人被美国人想象为斗士和雄武的象征,曾经受到迫害,而现在则战胜了自己的敌人。这一积极的形象与放纵和柔弱的阿拉伯人形象相对照,帮助培育了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关系。(33)
运用社会性别理论研究冷战史的第三个路径是对跨国性行为(sexuality)的研究,关注跨国性行为对国家间关系的意义,研究的对象通常是冷战时代美国的海外驻军与驻在国女性之间的性关系,并通过这种性关系来阐释国家间关系。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凯瑟琳·穆恩(Katharine H.S.Moon)的《盟国之间的性:美韩关系中的军妓》。穆恩指出,在冷战时代,美国在韩国有大量驻军,在这些驻军周围,性产业非常发达,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同时也使美国舆论越来越要求美国削减在韩国的驻军。在这一背景下,韩国政府与美国驻韩军事当局在20世纪70年代初合作发起“清洁运动”(clean-up movement),整顿和加强管理性产业,以说服美国民众支持保持在韩国的驻军。作者在书中描写了韩国娼妓与美国士兵之间的关系、“清洁运动”的过程、韩国妓女在“清洁运动”中的命运。但是作者的兴趣不是描述过程和历史细节,而是把娼妓与美国大兵之间的关系、韩国政府与美国驻军当局的合作作为一个切入点,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来观察和透视两个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韩国虽然不是美国的附属国,但其主权由于美国的军事保护而受到了限制,是不完整的。作为女性,这些韩国妓女传达的是韩国柔弱的、女性化的形象,提高了美国驻军对当地人的优越感,因此,韩国妇女与美国驻军的关系成为美韩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缩影。作者还指出,美韩之间的高端政治是以牺牲和主宰韩国女性为条件的,韩国政府的利益和美国驻军的利益超越国家的界线得到了汇合,却与韩国当地妇女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美韩关系的稳定和韩国的国家安全恰恰是以韩国女性个人的不安全为代价的。作者通过这一点从更深刻的角度解释了国际政治与性别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34)冷战时代,美国在很多国家有驻军,穆恩的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意义,可以成为研究美国海外驻军与当地居民关系的一个新视角。显然,没有社会性别理论的观照,妓女和普通士兵的关系不可能进入学者的视野。穆恩的研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跨学科的视野会极大地改变冷战史学者的观念,扩大冷战史研究的范围。
应用社会性别理论考察性别因素的影响需要冷战史学家运用除外交档案和个人回忆录以外的非常规的史料和文献,包括图片、漫画、大众文学、旅行日记、游记、电影、戏剧等等。同时还需要从新的角度对政府外交档案进行解读,不仅关注政策过程,更关注反映决策者性别观念的内容,如对其他国家人民性格特征和外国领导人个性的评价等等。对大多数外交史家来说无意义的文献在那些对性别与文化感兴趣的外交史家眼中可能是至宝。
运用跨学科方法进行冷战史研究显然并不局限于以上几个方面,就美国学者的实践而言,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都被用来解释冷战史,(35)以上只是举其大者。
结语
在冷战史研究中应用跨学科的方法并不是要消解冷战史研究的史学特性,而是要在保持其史学特性的前提下丰富和深化冷战史研究,即发现新领域、提出新问题、挖掘新材料和建立新解释。实际上,文化研究方法和社会性别理论的引入不仅不会削弱冷战史的史学色彩,反而会加强冷战史的人文特性,并有助于建立起关于冷战史的新叙事。只要抱着向人文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开放的心态,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就能不断地推陈出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布罗代尔在谈到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趋势时曾说:“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畛域分明的人文科学。它们中的每一学科都是向着社会整体敞开的大门,都通向所有的房间,都通向屋子里的每一层,只要研究者在行进过程中对相邻学科的专家不吝惜敬畏之情。如果我们需要,就让我们使用他们的门户和他们的楼梯。”(36)这段话对冷战史研究无疑也是适用的。借用其他学科的门户和楼梯,冷战史学者将会发现更多的宝藏,看到更旖旎的风光。
收稿日期:2009-12-15
注释:
①时殷弘、吕磊:《美国对华态度与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概观》,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美国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②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③John Fousek,To Lead the Free World: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
④John W.Garver,"Little Chance:Revolutions and Ideologies",Diplomatic History,Vol.21,No.2 (Winter 1997):71-105.
⑤张曙光:《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⑥参见Thomas G.Paterson,On Every Front: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New York:W.W.Norton & Co,1979;又见Thomas G.Paterson,"The Sources of the Cold War",Thomas Paterson,ed.,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Documents and Essays,Vol.2:Since 1914,D.C.Heath and Company,1984,pp.335-358。
⑦参见Thomas Paterson,"Superpower Decline and Hegemonic Survival"; John Lewis Gaddis,"Hanging Tough Paid Off"; John Lewis MccGwire,"Generational Change,Not US Bullying,Explains the Gerbachev Revolution"; Daniel Deudney and G.John Ikenberry,"Engagement and Anti-Nuclearism,Not Containment Brought an End to the Cold War",in Thomas Paterson and Dennis Merrill,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Documents and Essays,Vol.2:Since 1914,D.C.Heath and Company,1995,pp.726-753。
⑧在摩根索看来,对美国的威胁主要来自欧洲,因此美国对欧洲的政策是保持欧洲的均势,以免欧洲的霸主垂涎美洲。摩根索认为,无论是汉密尔顿和威尔逊的外交思想有多么不同,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美国加入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加入弱的一方,类似于英国在欧洲大陆保持均势的政策。在亚洲,美国在世纪之交才真正开始关注亚洲,亚洲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一直都不像在美洲和欧洲那样显而易见和可以得到清晰的界定,“结果美国的亚洲政策从未像欧洲和美洲政策那样毫不含糊地表达出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是“更从属于道德影响”。但在背后还是能看出一脉相承的永久性的国家利益的支配作用,即保持均势,而门户开放原则就是这种利益的表达,因为中国被另一个国家所主宰会导致力量失衡,威胁美国的安全,特别是菲律宾的安全。摩根索称这是海约翰门户开放照会的深层次动力。Hans 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New York:Alfred A.Knopf,1951.引文引自第6页。
⑨美国杰出历史学家入江昭对此有卓越的论述。参见入江昭著,刘青等译:《全球共同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5章。
⑩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提出建构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1)“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2)“有目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玛莎·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也提出,国家利益不是放在那儿,等着去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的”,“是由国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所塑造的”。参见[英]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玛莎·费丽莫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11)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65页。
(12)布赞等人提出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五个分析层次是指: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国际次体系(international subsystem)、单位(unit)、次单位(subunit)和个体(individual)。[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等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13)布赞、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第29页。
(14)[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15)Ernest R.May,"Lessons" of the Past: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16)Paul W.Schroeder,"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Not Use or Abuse,but Fit or Misfi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1 (Summer 1997):70.
(17)关于美国外交史和冷战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可参见王立新:《试论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
(18)相关研究参见Noam Chomsky,et al.,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New York:New Press,1997; Michael E.Latham,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Chapel Hill,NC,2000; Jonathan Nashel,"The Road to Vietnam:Modernization Theory in Fact and Fiction",Christian G.Appy,ed.,Cold War Constructions: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1945-1966,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0,pp.132-156; Bruce Kuklick,Blind Oracles:Intellectuals and War from Kennan to Kissinger,Princeton,NJ,2006。
(19)David C.Engerman,"Bernath Lecture:American Knowledge and Global Power",Diplomatic History,Vol.31,No.4 (Sept.2007):599-622.中国学者的研究可参见牛可:《国家安全体制与冷战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10月号。
(20)David C.Engerman,"Bernath Lecture:American Knowledge and Global Power",Diplomatic History,Vol.31,No.4 (Sept.2007):601.
(21)Mark Philip Bradley,Imagining Vietnam and America:The Making of Postcolonial Vietnam,1919-195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
(22)例如,艾森豪威尔认为“无论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和语言上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俄国人都是人类,他们想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中国人则是不同的,狂热、非理性和歇斯底里,不能像西方人那样“理性地(logically)思考”。他称东方人就像“头撞南墙的骡子”(the mule who walked into the brick wall),对他们来说,“面子是最重要的,东方人宁可失去一切也不愿丢了面子”。参见Dwight D.Eisenhower,White House Years,2 vols.,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3-1965,Vol.2,p.369;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of the 237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Feb.17,1955,FRUS,China,1955-1957,Vol.2,p.285。
(23)Frank Costiglioga,"Unceasing Pressure for Penetrating:Gender,Pathology and Emotions in George Kennan's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3,No.4(March 1997):1309-1339.
(24)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通过对鸦片战争前后中英之间签订的条约文本和往来外交文书的研究发现,关于汉字“夷”的含义的争执是这一时期中英关系中的重要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英国人认定汉字的“夷”等同于英文的barbarian(野蛮人),并认为清政府公文中指英国人为“夷”带有蔑视和侮辱的含义而引发了战争。尽管清政府官员曾极力辩明“夷”字并无野蛮、劣等之含义,而不过是“西洋”或“外国”的意思,但英国还是坚持在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规定,以后中国官方文书中提及英国人时,不得使用“夷”字。在刘禾看来,包括费正清在内的西方国际关系史专家所津津乐道的“中国中心主义”和作为英国发动战争理由的中国的“傲慢”都源自对“夷”字的错误翻译和《天津条约》第51款的支持,并不符合事实。而关于“夷”字这一词语的冲突“绝非小事”,“它凝聚和反映的是两个帝国之间的生死斗争,一边是日趋衰落的大清帝国,另一边是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谁拥有对‘夷’字这个汉字的最后诠释权,谁就可以踌躇满志地预言这个国家的未来。”刘禾进一步研究了由“夷”字的含义之争引发的英国的殖民话语政治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帝国是如何被帝国的话语政治“塑造”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参见刘禾著,杨立华译:《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二章,引文引自第52页。尽管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赞同刘禾的观点,但其研究说明了语言学的方法,包括修辞、话语分析以及翻译和跨语际交流的研究会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国际关系。
(25)Joan Scott,"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5 (Dec.1986):1053-1075.
(26)Joan Scott,"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5 (Dec.1986):1073.
(27)Emily S.Rosenberg,"A Round Table: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Gender",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7,No.1 (June 1990):116-124.
(28)Robert D.Dean,"Masculinity as Ideology:John F.Kennedy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Diplomatic History,Vol.22,No.1 (Winter 1998):29-62.引文引自第30、62页。
(29)Emily Rosenberg,"'Foreign Affair' after World War II:Connecting Sexu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Diplomatic History,Vol.18,No.1 (1994):59-70.引文引自第70页。
(30)Emily Rosenberg,"'Foreign Affair' after World War II:Connecting Sexu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Diplomatic History,Vol.18,No.1 (1994):70.
(31)有关研究可参见Michael H.Hunt,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 Kristin L.Hoganson,Fighting for American Manhood:How Gender Politics Provoked the Spanish-American and Philippine-American War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 Mary A.Renda,Taking Haiti:Military Occup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US Imperialism,1915-1940,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
(32)Andrew Rotter,"Gender Relations,Foreign Relations: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sia,1947-1964",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1,No.2(Sept.1994).
(33)Michelle Mart,"Tough Guys and American Cold War Policy:Images of Israel,1948-1950",Diplomatic History,Vol.20 (Summer 1996).
(34)Katharine H.S.Moon,Sex among Allies:Military Prostitution in US Kore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35)如德博拉·拉森运用心理学对美国遏制政策起源的研究,托马斯·麦考米克运用世界体系论对美国霸权兴衰的解释,迈克尔·霍根借用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合作主义理论对马歇尔计划和战后初期美欧关系的考察,都被外交史学界公认为经典之作。参见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 Thomas McCormick,America's half-Century: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 Thomas McCormick,America's half-Century: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and Afte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Second Edition; Michael Hogan,The Marshall Plan:American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1947-1952,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36)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0页。
标签:国际关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美国史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苏联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